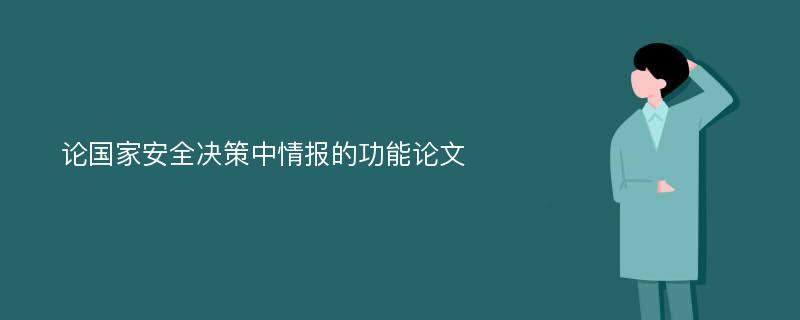
论国家安全决策中情报的功能*
高金虎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9)
摘 要: [目的/意义]梳理国家安全决策中情报的作用,重新定义情报对决策的引领作用。[方法/过程]从分析战略环境、监控战略态势、评估对策选择等多个角度,分析情报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结果/结论]情报在国家安全决策中发挥引领作用,而不仅仅是“服务”和“保障”作用。
关键词: 国家安全情报;国家安全决策;情报作用;战略;情报分析
国家安全情报的基本功能是研判国家安全战略形势,帮助决策者塑造一个透明的国家安全决策环境,辅助其做出睿智的决策。但传统上,有人认为情报的主要功能是向决策者提供信息,而非真知灼见。因此,情报被定位为“支援”“保障”功能,这样的功能定位弱化了情报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因此,本文试图勾勒情报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阐明其发挥作用的限定条件。
1 国家安全决策流程中情报的地位
王桂芳等在《国家安全战略学》一书中梳理了有关国家安全决策程序的各种观点,认为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安全决策程序存在不同的认识,但基本程序应包括研判国家安全战略形势、确立国家安全战略议题、做出国家安全决策、确定国家安全战略方案、颁布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五大阶段[1]。这种表述细化了中国古代兵家的“庙算”程序,也是对毛泽东同志相关论述的另一种表达。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2]侦察、判断、决心和部署,构成了一般决策的基本程序。这与博伊德于1966年提出的“观察—调整—决策—行动”循环实无本质区别。
在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中,情报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情报组织的目标和职能在于,在和平与战争期间,向那些决定政策、制定计划和做出决定的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知识,正是这些知识,使他们耳聪目明,做出明智的抉择。20世纪50年代美国洛克菲勒委员会指出:情报是为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搜集的信息,它为政策制定者指明了可供选择的范围,使其能做出判断。好的情报不一定能导致明智的决策,但若无准确的情报,国家的政策决定和行动就不能有效地反映实际情况,也不能体现国家的最高利益即确保国家安全[3]。
此外,雷可夫和约翰逊将过去的一切哲学观统称为客观主义。哈泽尔(Haser)认为这种“客观主义”只是他们为论证自己的观点而杜撰的“假想敌”,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他们的论述缺乏准确的引用信息,极少列举具体的参考文献或指出持该观点的学者姓名。同时,雷可夫和约翰逊还多次扭曲和误解了所谓的“客观主义者”的观点,对西方哲学思想也存在着诸多混淆和模糊的理解。哈泽尔还指出,雷可夫和约翰逊一方面把某些学者的观点归入客观主义的范畴,一方面又多次引用这些学者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证,这显然犯了论证自相矛盾的错误。[12]
在国家安全决策程序中,战略判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情报分析,居于首要的地位,也是国家安全决策的基础与先导,其基本目的是判明威胁,区分敌友,揭示对手的企图,计算双方的力量对比,权衡各种利弊得失,从而为国家安全决策与指导提供正确的结论[4]。
精读部分,笔者按照文章段落设置,分成三个环节,每个部分设计了不同的任务;三个环节的任务设置由易到难,并且每个环节结束都有小结,忠于原文而又高于原文。第一段的阅读任务是将原因和结果匹配起来(见图1)。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宫颈鳞癌及子宫内膜腺癌标本及对照组标本,对其MTSS1的表达情况进行判定。应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测引物序列及Western 蛋白印迹法对MTSS1的表达情况进行判定。
2 国家安全决策流程中情报的作用
2 .1 分析战略环境,消除情况认识的不确定性
战略环境是影响决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和。决策是否科学,能否顺利实施,实现决策目的,取决于战略环境以及决策者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判断。因此,了解战略环境,分析构成战略环境的各个因素,评估战略环境,消除情况认识中的不确定性,构成了战略评估的首要任务。
黑鹰山铁矿床磷灰石的引人注目之点是其稀土元素含量颇高。根据两个磷灰石精样品的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结果,其稀土氧化物总量w(TR2O3)为2.5407%~2.6948%,可称为含稀土磷灰石[2]。
一般而言,一国在国家战略、安全战略、安全观或相应的文件中,必定会对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安全态势进行阐述,作为安全总体目标和各领域目标的依据。情报人员必须准确感知国际安全环境,帮助决策者确定国家安全目标,为决策者动用哪些战略手段和资源,考虑如何确定安全需求的实现途径奠定基础。
不确定性是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一个突出的认识论问题。对手的意图神秘难测,保密和欺骗措施常常使人误入歧途,所以,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雾,是或多或少不确定的”“战争中的一切情况都很不确定……”[5]。
解决不确定性的关键在于情报。孙子指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知是行的基础,“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美国学者迈克尔·汉德尔(M.I.Handel)强调,决策时面临的不确定性是决策中的重大难题,而情报就像是“一面镜子”,可以帮助看清“对手手中的牌”,从而“掌握可以了解对手意图的最佳信息”[6]。有了准确的信息,关于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就可以减少,指挥官在作出关于部队战备、部署和行动的决策时,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可能的代价和好处。信息如果能够及时得到处理和分发,还可以为决策赢得更多的时间,从而确保行动的成功。一句话,信息可以帮助决策者高效地管理资源[7]。所以,为国家安全决策系统提供有关决策的环境、对手、威胁、机遇等方面的信息,塑造一个“尽可能透明的”信息环境,是国家安全情报机构的首要任务。
本文通过求解非定常不可压缩RANS方程,对某空泡水筒流场进行数值模拟,探究空泡水筒不同位置处的流场分布特征。对试验段流场的特性进行分析,重点分析工作段不同断面处的流速分布及流场参数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均匀性、湍流强度和附面层厚度等流场特征。采用皮托耙对工作段不同断面进行流场测量,以验证数值结果的准确性。
1.2.1 细胞培养 TU686细胞用含10%胎牛血清、1%青霉素-链霉素双抗的RPMI1640完全培养液放入37 ℃、5% CO2培养箱中培养。以1∶3的比例传代培养。取对数生长期细胞进行实验。
在生产力比较落后、战争结果取决于交战双方的有形物质能力的冷兵器战争时代和机械化战争时代,情报的先导作用表现得不够明显,鲁莽的指挥员有可能凭蛮力侥幸取胜。但是,在非传统安全威胁肆虐的时代,情报的先导作用就更为突出,没有情报,就没有办法遂行任务,更不可能取得胜利。1997年英国皇家督察出版《警务与情报》研究报告正式提出“情报引导警务”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很快被国际警界所接受。在“9·11事件”后的美国情报改革中,联邦调查局提出了“以情报为驱动”的改革目标。2006年联邦调查局设立国家安全分局,情报处是国家安全分局的组成部分,2014年情报处从国家安全分局独立,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情报先导”这一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执法工作中,它必将渗透到整个国家安全工作中。
在冷战结束前,各国国家安全情报机构主要关注传统安全威胁,特别关注领土主权完整和政治军事安全;而随着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格局和安全环境的剧烈变化,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渐成为情报机构关切的问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安全威胁中,把握住最为关键的威胁及其要素,阐明其威胁的原因、影响等是国家安全情报机构的基本任务。美国2008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阐述了非传统安全对于美国的威胁,其中包括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等内容,但最为关键的仍然是对美国本土、国民产生直接、现实影响的因素。2009年美国《国家情报战略》在分析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时认为,美国面临着复杂而快速变化的安全环境,在传统安全领域,具有挑战性的是伊朗、朝鲜、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具有传统安全(军事)实力和意愿的国家;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美国面临暴力极端组织的恐怖袭击、武装叛乱分子对美国海外利益的颠覆,以及跨国形态的经济危机、气候变化、能源竞争等产生的安全利益冲击等[8]。
理解、洞察国际态势,不仅要求掌握基本国际形势,更要对国际态势进行深层次分析,摸清其本质和规律,预测其发展趋势,为国家安全决策提供基本依据。例如,1994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阐明美国“面临的危险更加多种多样……种族冲突已经蔓延,狂暴的国家给地区稳定造成严重的危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提出了主要挑战,人口迅速增长使大范围的环境恶化更加严重”,而与此同时,“民主国家大家庭正在扩大,使实现政治稳定、和平解决冲突和世界人民获得更大的尊严和希望有了更大可能性,国际社会正着手采取共同行动解决紧迫的全球环境问题”[9]。这样的认识,无疑为美国决策层澄清了决策环境,使其可以把力量放到更容易发生危机的地方。而与之相对,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局势主流的20世纪80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却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通过核战争灭亡苏联,为此,情报机构制定了雷恩计划(Ryan Project),把主要的情报力量投入到监测英美等国发动核战争的动向方面,很明显,苏联情报机构没有把握国际态势的本质与规律,令决策误入歧途。
2 .2 监控战略动向,发现影响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与机遇
世界是发展的,对手的基本情况,基本的国际态势,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必须严密监控这种变化,敏锐洞察新变化中的新动向。因此,持续跟踪与更新情况,就影响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与机遇发出预警,是国家安全情报机构的基本职能。例如,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动向,民族主义、宗教问题、恐怖主义、经济安全成为影响国际格局的重要因素。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必须及时掌握新动向,判断其发展脉络、意义及影响。
海湾战争前后,美国情报界始终将信息更新作为保障决策的关键,在不同的阶段,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各种来源的信息。1990年2月,伊拉克在阿拉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对科威特和沙特提出了强硬立场,中央情报局沙特情报站对此进行了跟踪报告,中央情报局也因此加强了对伊情报监控工作。4月,萨达姆发表的针对以色列强硬讲话的军队内部讲话被美国情报界获得,美国以此为依据,决定取消对伊优惠贷款、禁止进口潜在军事用途物资。7月后,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机构对伊科边境、伊军动向进行了不间断监视,先后提交了伊军在边境集结、坦克等重装备集结、伊军建立供应线、大批后勤支援卡车机动等情报,到7月底,中央情报局已经能够提出伊军集结在边境的军力状况[10]。
2 .3 参与战略方案制定,优化国家安全决策
从本质上来说,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就下列问题向决策者提供咨询,即:当前和未来的趋势,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推进国家利益的机遇,等等。为此,情报机构应提供所需的战略评估、战略判断、战略影响、战略预测等咨询意见,必要时还可提供相关应对建议,帮助国家安全决策者和决策层作出适时、科学、正确、有效的国家安全决策。
制定战略计划,需要国家安全情报机构持续跟踪、反应并进行不间断研判,从而给予决策者以实时的情报支援,帮助决策者解决决策中面临的“信息匮乏”问题,促使决策者综合各种方案内容,形成最优方案,这是国家安全情报机构的常态任务。例如,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置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多种政策选项,包括无所作为,接受苏联造成的既成事实;对建设中的导弹阵地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武装入侵古巴;封锁古巴……在进行政策选择的过程中,情报分析人员扮演着重要作用。他们提供信息和分析,以说明各种政策选择及可能的后果,并就苏联最可能的反应等问题进行了准确评估。分析人员估计,苏联的反应主要是为了“政治投机”,其军事反击不会超出古巴边界,这一判断为肯尼迪的决策提供了明确的情报支撑。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以色列明确了战争的6个目的,即消除紧迫的入侵威胁、打破蒂朗海峡封锁、狙击阿武装力量活动、保卫边境、夺取阿军先进武器、占领新领土。其中最后一项与其他5项均有关联,为此,以内阁确定了4个决策方案[11]。在对各种战略目的进行分析对比的过程中,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了有关阿以双方兵力对比的情报,明确了在西奈、叙利亚和约旦三个方向面临的不同军力,判断西奈方向的兵力是整个阿拉伯国家军队的主要力量,而要达成占领地面地域的战略目的,以色列必须拥有制空权。埃及空军的战斗机数量占据了整个阿拉伯国家空军的80%以上。这也使得要完成作战任务,作战计划必须建立在消灭埃及空军的基础上。以色列最后形成的作战方案就是遵循摧毁埃及空军、陆军快速推进占领西奈半岛、打败埃及陆军、解除海峡封锁的顺序[12]。
在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中,分析人员应提供基本事实,减轻决策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检验决策者对事件发展的判断是否符合现实情况,帮助决策者考虑影响事态发展的主要因素,勾勒事态发展的可能选择,评估各种对策选择可能引发的后果及对方的可能反应。在支持决策时,分析人员必须清晰阐明其结论背后的推断。例如,假定某分析人员认定某国政局高度稳定,那他应该清楚地知道是什么样的证据和逻辑让他得出这样的观点,并在情报产品中予以明确的表述。如果影响某国政治局势的因素发生变化,那么分析人员应该立即向决策者说明,并就变动可能给某国的政治稳定带来的影响作出清晰判断。
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政策山机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情报工作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艾森豪威尔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政府中最重要的部门,是情报与政策的支点,情报要在他的决策工作中起中心作用[13]。他要求改进国家安全决策机制,融入中央情报局的战略情报分析。在他的主导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形成了“政策山”决策机制。在政策山机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被设计为美国军事、外交、国内安全事务政策形成与执行的主要机构。它有权提出政策性建议,要求所有部门进行研究,成为协调国家安全部门向总统提供建议和情报的主要工具,而且具有指挥职能和监督执行总统决定的职能[14]。
如前所述,情况认识是进行国家安全决策的第一步,这一点无论是政策制定人员还是情报分析人员均无异议。然而,如果说要把情况认识纳入国家安全决策过程,并把情报分析人员视为决策体系中的一分子,回答就因人而异了。从心底里,绝大多数决策者对情报工作存在不正确的认识。漠视情报,将决策视为自己的领地,阻碍情报深度介入决策领域,是绝大多数决策者的通病。
2 .4 评估对手的反应和可能选择
情报工作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对抗,对立双方的情报机构为保证己方的决策体系能够高效运行,一方面采取各种情报行动获取对方的情报,了解其实力与意图,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拒止与欺骗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止甚至破坏对方的情报行动,阻止其获得正确的认知。因此,情报分析实际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分析人员要判断对手的棋路,并根据“对手会对我们这一着怎样反应”来决定我们的策略。在认知对抗的过程中,分析人员要对对手做出深入、详细的分析,了解其如何看待当前局势,详细理解对手所掌握的战略优势,理解其面临的战略困境,以及解决这种困境的手段,判断其行动的基本轮廓,其受到威胁时可能做出的反应,以及对己方构成最大危险的行动方案。所以,美军《联合情报》明确指出:判定敌人的企图是情报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分析人员要从敌我双方不断互动的动态过程中得出结论,为此情报军官要了解己方计划未来要采取的行动,同时对下列因素作出预测:敌人发现己方行动的可能性;敌方会如何解读己方行动;以及敌人最可能做出的反应[15]。
公民在民主程序中的表意行为是有偏好倾向的,这种倾向对民主价值是减损的,甚至是负面的,这是民主不可回避的问题。从古代到革命时代都是如此,特别是自毁式偏好和不道德的偏好影响了民主的价值体现。民主偏好的存在不仅影响到公民民主意识的形成,也影响到了公民和政府的良性互动。传统的研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公民意志表达的这种缺陷,但是没有改变这种状态的进路,至少在“互联网”之前都是如此。
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在危机处置过程中,分析人员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些导弹具备作战能力、可以随时打击美国的目标前,美国决策者还有多少时间做出反应?这一重大问题要求对U-2飞机拍摄的图像做出精确解读,并对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奥列格·潘可夫斯基(O.Penkovsky)提供的人力情报进行深入分析。受过严格培训的技术分析人员估算出苏联导弹安装还需要的时间。1962年10月19日,在发现导弹后的第5天,分析人员得出结论,导弹将在10月27日具备作战能力[16]。这一重要结论不仅限定了美国决策者做出反应的时间,还将时间上限延伸了3天,从而让美国决策者获得了宝贵的时间,以在苏联有能力对美国城市发动核打击之前处理危机。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高水平的情报保障,肯尼迪总统几乎不可能达成这一圆满结局。
2 .5 参与评估我方的行动方案
制定行动方案是决策者的职能,在已经设计的各种方案中进行选择,是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一步。由于掌握的战略手段不同,达成战略目的的方案可能不止一个,各方案内容各异,实施后所导致的后果也会大相径庭。决策者选择哪一种方案,不仅要权衡方案与国家安全目标、政治目标、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也要权衡各种方案所可能导致的后果。评估各个方案的优劣,根据对手可能的反应选择最优方案,就成了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天职。在这一过程中,情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提供有关对方的情报,确保决策者始终跟进情况的发展,了解各种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并对对手所有可能的行动方案进行确认、评估和排序,就已经制定的行动方案进行兵棋推演,以预见敌我双方行动方案之间的“行动—反应—反行动”的动态过程。
评估我方的行动方案,情报分析人员应该扮演对手的决策者,并将己方的行动方案与对手最有可能的行动方案进行推演,而后与对手最危险的行动方案进行推演,从而决定己方的行动方案。在这一评估过程中,情报人员和其他人员要回答下列问题:敌方的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图,我方的实力,可能的反应计划。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决策者下定最后决心。
在评估的过程中,情报分析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对比各种方案,清晰地列举影响行动计划的各种因素及其状况,为决策者进行对比提供依据;转换身份定位,扮演对手,站在对手的立场上思考问题,预测对手可能的反应,帮助决策者选择并优化方案。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决定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其重要举措就是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农业部的评估表明,美国是苏联最大的粮食进口地,任何国家都不能取代美国的地位,对苏联实施粮食禁运能够达成美国的战略目的。然而几天之后,阿根廷就宣布将对苏联出口粮食,以部分代替美国对苏联的粮食出口,美国的禁运政策失败了。在这一例子中,农业部的情报评估显然是错的,它没有能估什到美苏博弈中第三方可能施加的影响。在启动“沙漠风暴”行动前,美国决策者于1990年8月初召开了多次会议,就美国应当采取何种应对方案进行研究。美国情报界围绕出兵海湾进行武装干涉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评估,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困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等诸多问题而无暇他顾,不会再出现美苏严重对抗的局面;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已严重感受到伊拉克的军事威胁,将会支持美国出兵;西方盟国则由于自身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受到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危害,将会与美国保持合作;伊拉克国力有限,势单力孤,美国完全有战而胜之的把握[17]。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分析,布什政府作出了出兵海湾的重要决策。
这样的做法同中国古代的“庙算”传统完全背道而驰。先秦兵书《军谶》指出:“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22]。《管子》认为“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阵也”[23],敌情不明根本就不应有所行动。“先计而后战”“计利以听”,成为中国的兵学传统。在进行“庙算”的时候,决策者必须先“计利”,后“为势”,只有在分析结果有利于己的情况下,决策者才做出开战的决策,并通过“诡道”等各种手法,将之转化为“势”,以争取胜利,而不是盲目开战,摸着石头过河。正如杜牧指出,应“于庙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计算优劣,然后定胜负;胜负既定,然后兴师动众”[24]。孙子指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并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情报是“兵之要”,是三军行动之基础。冯·克劳塞维茨也认为,情报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一位统帅只有“考虑到战争涉及多少重大的问题”并且具备了“非凡的洞察力”[5],才能制定出基本符合战争客观情况的战争计划。这同样体现了“先计而后战”的特点。
2 .6 分析战和大计,为制定战后政策提供基础
战和大计是指国家高层决策采取战争或和平的手段解决国际冲突、维护国家主权或实现国家利益。战和大计事关国家存亡和未来发展,是最高等级的决策事项,同时也是国家领导层或决策者最为关注的事项。情报机构在国家战和大计决策中的作用是为决策者提供全面的决策信息和情报分析支援,以及基于科学情报评估提出对策建议。从情报研究的角度讲,情报机构在战和大计中的任务主要就是战争前景分析。
前景分析是决策的重要依据。在事关生死存亡的战争问题上,对战争前景进行预测,是决策是否发动战争以及制定战争计划的基本依据之一。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情报机构仔细分析了萨达姆被推翻后伊拉克的经济状况和安全形势,讨论了驻伊美军的作用,以及阿以矛盾变化,指出了美国的挑战和机遇,确定战争对美国有利,从而说服了美国国会和民众。战争前景预测以战争胜负为核心,还包括战争持续时间、代价、利弊和战后形势等。
首先,预测战争胜负。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包括: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国内、国际支持程度以及第三方是否干涉等。预测战争胜负要对上述诸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敌我战争力量对比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敌我战争力量进行综合考察,对双方可投入战区的军事力量进行研究和比较,并借助多种技术手段得出结论。国际支持程度是指国际舆论对战争的基本态度,国际道义将站在哪一边,双方可以从国际社会获得哪些支援,有哪些盟友,有无可能组建联军部队,战区周边国家可能提供哪些便利或设置哪些障碍。第三方评估是指对可能直接支援敌国的第三方力量进行判断,并评估其参战的动机、方式、规模和程度。
其次,预测战争的持续时间和代价,即战争可能持续的时间和各方将付出的代价,尤其是我方的伤亡和损失。仍然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具有中、小国家不可比肩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但是美国国内民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执政党的地位,国内舆论直接影响政府的战争政策。如果战争持续时间过长,或是人员伤亡超过了民众心理的承受力,那么民众就会起而反对战争。1972—1973年,美国尼克松政府之所以做出从越南撤军的决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美国民众对持续十多年的对外用兵和大量的人员伤亡提出质疑,进而积极反对继续干涉越南事务。美国之所以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人员伤亡估算还应包括敌国民众。在西方国家民众普遍要求将军民伤亡降到最低的情况下,“不能和不愿评估战争伤亡的做法是不可能被国际社会接受的”[19]。因此,美国政府首脑在决定对外用兵之时,都会要求情报部门和咨询机构就战争可能持续的时间和美国即将付出的代价作认真的评估。
是“红富士”的早熟变异。2011年通过贵州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其主要的优良变异体现在成熟期上,在威宁县8月下旬成熟,成熟期较普通“红富士”提前25~30天。果实近圆形,果形指数0.85,单果重170~200克。果实底色黄绿,果面偏红,着色均匀。果点中大,果肉黄白色,硬度10.82公斤/平方厘米,肉质细、致密,脆而多汁,香味浓,可溶性固形物14.42%。
3 情报在国家安全决策中发挥作用的前提
3 .1 恰当定位情报的作用,定位情报与决策关系
在政策山机制中,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公室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的每一项政策文件,都有国家评估办公室的情报支持。国家评估办公室就美国面临的问题,定期撰写《国家情报评估》。《国家情报评估》正是政策山机制正常运转的基础。中央情报局督察长莱恩·柯克帕特里克(L.B.Jr.Kirkpatrick)曾评价说:“《国家情报评估》可能是我们政府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文件了……一份《国家情报评估》就是一项声明,叙述着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局面将要发生的事情,而且尽可能地预测最远的未来。”[13]威廉·邦迪指出:“我们的系统要求在起草政策文件一个月或半个月之前,就写出《国家情报评估》文件。我们要消化《国家情报评估》,以便能把它们直接用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策文件中。这个方法是艾森豪威尔在大战期间他的参谋人员中开创的。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准备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附带性的文件是什么?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头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他系统地考察了全部争议问题,并做出了决定。”[13]
在漫长的战争史上,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交战双方的硬实力,而像情报这样的战争指导艺术并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战争实践使不少人对情报工作形成了错误的认识。传统情报理论认为,情报与决策是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因此有“情报支援”“情报保障”和“情报服务”的说法。在许多指挥员眼中,情报属于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们可以忽视情报的存在,完全凭一己之见做出决定。例如,欧洲的十字军东征大多没有情报支持;希特勒在发动侵苏战争时根本不考虑德苏两国的实力对比;美国第二任中央情报主任霍伊特·范登堡(H.S.Vandenberg)证实,珍珠港事件前,美国人民“有一种情绪,认为要打赢一场战争——如果再发生另一场战争的话,只需要有准确射击的本领就可以了”[13]。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积极参与长江大保护和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先后完成了数十项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专题研究,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技术支撑;为沿江湖北、湖南、安徽、江西、重庆等省、市政府提供了长江大保护高端咨询服务,为多个城市或区域提出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和保护整体解决方案,项目涵盖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等多个领域,涉及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运行维护全生命周期。
评估我方的行动方案,必须严格区分情报与决策的关系。谢尔曼·肯特(S.Kent)指出,情报人员并不是政策目标的确定者,也不是政策文件的起草者,计划的制定者,更不是政策的执行者。他是上述各项因素的附庸,是为上述因素而存在的。他是一个服务者。他的工作是使决策者耳聪目明。他站在他们身后,当他们需要的时候,把书翻到他们需要的那一页,对他们有可能忽略的问题,他要提醒他们,引起他们的重视,并在他们的要求下,鉴别和评估实现目标的各种选择方案,但并不指出他们应该作何选择[18]。因此,在评估我方的行动方案时,情报官员应当保持职业客观性,不侵入决策领域,不推动某种具体政策、对策选择或结果,而只提供客观的评估,而将真正的选择权留给决策者。
消除情况认识的不确定性,需要情报机构恰当地评估国际态势。态势分析(态势理解)是指对事物发展的形势和状态进行研究,把握其本质内在联系,揭示发展规律和未来可能的状态。态势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际格局、国际战略力量及其分布的发展演变,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社会领域发展中的重要进展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影响,等等。态势分析的任务是对这些重大变化、重要进展和重大事件进行研究,掌握其本质、内在联系,揭示国际关系的发展规律和可能的发展动向。
消除情况认识的不确定性,情报机构首先要判断决策所处的战略环境。战略环境,是指国家或集团在一定时期内所面临的影响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全局的客观情况和条件,主要包括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地理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战略态势,特别是战争与和平的总态势[4]。战略环境是实施国家安全战略过程中必须重视的因素,只有对本国所处的战略环境进行准确的分析与评估,才能判明威胁的来源、性质和程度,才能趋利避害,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因此,清晰地认识战略环境,是制定战略的前提。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庙算”传统有独到之处,如果我们承认毛泽东同志关于战略判断的论述,那么,我们就必须意识到,我们过去可能低估了情报在整个决策流程中的地位。最典型的例证是,当我们言及情报时,我们的表述是“情报支援”“情报保障”,而不是“情报主导”或“情报引导”。显然,“支援”或“保障”与“引领”有着霄壤之别。
所以,要发挥情报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决策者必须具有恰当的情报观念,认识到情报是决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决策者应倡导情报与计划的同步,在政策倡议起始阶段,就把情报人员纳入进来,使其了解政策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情报工作。同时,决策者也应意识到客观性是情报的生命。为保持情报的客观性,情报机构应该独立于行政部门,情报不应成为政策争论的工具,更不应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决策者应该让情报人员了解政策需求,适时对情报人员提供政策指导和反馈,但不能把自己的政策预期强加给情报人员,也不能选择性地对待情报。
3 .2 知彼知己,完整把握国际态势
对国家安全情报机构而言,了解对手的基本情况,是其基本职能。但对于己方的情况,情报分析人员也必须了然于胸。从军事辩证法的角度看,知彼和知己是情况认识过程中的两个环节,两者互为依据。离开对己方情况的认识,我们对彼方情况的认识是不完整的。割裂彼方情况与己方情况之间的联系,不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就不能认清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预测事物发展的方向。我们常说不能过低估计敌人,过高估计自己,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过低估计了敌人,也就是过高估计了自己,反之亦然。因此,孙子在讲“知”的时候,把“知彼”与“知己”联系在了一起,在“五事”和“七计”中,特别提出要就双方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以得出最终结论。克劳塞维茨指出,“知道了敌人最多有多大的力量,自己不致遭到完全的毁灭就有了相当的把握;意识到自己力量有限,就会选择适当的目标。既然不致遭到极端的打击,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极端了。”[5]谢尔曼·肯特明确指出,无论是驻外秘密人力情报人员,还是情报分析人员,首先都应了解本国的情况,了解决策者的决策需求[18]。在评估敌方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时,需要用到“形势评估”这一著名公式。这个公式大体遵循以下几条:①环境知识,即地理、天气和气候、水文地理、后勤等;②对敌人武装力量及其部署的了解;③己方力量;④敌方可能的行动方案[18]。这种评估被称为“纯净评估”(Net Estimate)或“司令官评估”(Commander’s Estimate)。在这一评估过程中,情报人员和其他人员要回答下列问题:敌方的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图,我方的实力,可能的反应计划。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决策者下定最后决心。因此,要认清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洞察事物的本质,就必须把彼方情况与己方情况联系起来。自己的计划与实力必须与对方的计划与实力进行对比分析,这样的决策才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再次,预测战后战区形势发展。对战争结束或主要作战行动结束后战区形势的预测也是战前对战争前景分析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随着海湾战争及其后一系列对外用兵取得胜利,美国情报界和决策层在战前对战后战区形势的评估往往过分乐观,对战后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估计不足,由此导致决策失误。1999年初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制定对南联盟进行空中打击的“联盟力量”行动期间,美国情报机构和咨询机构根本没有预料到,战后北约在该地区“必须面对多达140万的难民和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科索沃人丧生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20]。同样,美国情报界也没有真正研究过在推翻塔利班统治后,美军的重建将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和挑战。这一状况在伊拉克战争前有了改观,对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美国可能面临的地区形势,情报界指出:美国在战后伊拉克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府的努力将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可能面临大规模骚乱的挑战[21]。这一评估基本贴近现实。
3 .3 选择恰当时机提供情报支援
研究表明,情报机构提供情报的时机也会影响情报产品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使用。情报分析人员判断过早或过迟,都会影响到情报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使用。
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的葛里高利·特拉沃顿(G.F.Treverton)指出,情报通常在三个阶段对政策有用,其一是问题出现阶段,其二是政策选择阶段,其三是决策阶段。三个阶段情报对决策的支持力度不同,决策者对情报的重视程度也有很大差别[25]。在第一个阶段,由于问题刚刚出现,决策者对问题的前因后果还不清楚,他需要情报机构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帮助他解读这一现象,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后果。这个阶段的情报有如久旱甘霖,最受决策者重视。但遗憾的是,情报分析人员很少表现出先知先觉,他们往往与决策者一样缺乏先见之明,因而经常没有情报可供。
第二个阶段是大部分情报人员经历最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问题已经呈现,危机已然形成,决策者正在考虑各种对策,以消弭危机。情报机构要对事态的背景、进程与后果进行详细分析,帮助决策者消除“战争迷雾”,思考每一种可能的对策选择,思考对手可能做出的每一种反应,从而为其做出选择做准备。这个阶段的情报也为决策者所看重。
在第三个阶段,问题已经充分显现,危机已经暴露无遗,决策者依赖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形势做出判断,并定下了最后决心。但是,情报机构反应迟钝,只在决策者做出最终选择之后提供了情报。但决策者对这种马后炮式的情报没有兴趣。如果情报支持他的观点,他会接纳但并不会表示赞赏;如果情报与其决策相悖,那毫无疑问他会把它当成废纸。由此可见,选择恰当的时刻提供合适的情报产品,对情报在决策中的作用意义重大。
3 .4 提供机遇分析,贴近决策需求
情报的根本目的是优化决策,对此,大多数明智的政策制定者都有清醒的认识,但决策者未必会依据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进行决策,他们在考虑情报信息时,会把情报置于大的背景下,包括他们从其他信息来源处得到的信息、每种选项对政策的影响,以及他们能够承受的风险。情报可以让他们的判断更合理,但很少能够决定他们的决策。情报与决策者的关注不相关,情报产品的形式不符合决策者的要求,是情报得不到使用的重要原因。里根政府期间,美国国务院曾批评情报机构:“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解析数据,列出问题,然后告诉我形势很严峻。这我都知道。我需要你们提供的是对我手中筹码的评估——告诉我该怎么对付这些家伙!”[26]诚如杰克·戴维斯(J.Davis)所说,决策者经常对情报预测不感兴趣甚至充满偏见,其原因在于这种分析对他们的政策议程没有帮助。决策者喜欢的是行动分析(Action Analysis)。分析人员应该像用户那样去定义情报问题,关注用户在决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他应该模拟用户的思考过程,像用户一样思考问题;他要善于发现存在的机遇,分析对方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27]。这些问题都是决策者需要考虑的问题,但鉴于其日理万机的工作性质,他显然没有条件这么考虑,只能由分析人员代劳。分析人员应该明确指出推行某项政策的机会和障碍,充分展示其所掌握的证据以及分析技巧,在做出预测的时候不失其职业底线。
3 .5 加强情报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情报分析的质量
除了决策者的因素外,情报能否在国家安全决策中发挥作用,还取决于情报产品的质量。如果情报分析人员提供的情报存在明显谬误,那它不会对政策制定人员产生影响;如果情报分析人员提供的情报产品过于学术化,不对政策制定人员的口味,这样的分析也不会对政策制定人员产生影响。只有客观、及时、准确、可操作性强并且能跟踪事态发展,不断调整以满足政策制定人员需要的情报才是好的情报。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是劳动创造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同样的劳动者在退休后,退休待遇却相差甚远,有调查数据显示:同样为30年工龄公务员平均退休工资7000元左右,而同一地区的同样工龄的企业人员退休工资2600元左右,退休工资悬殊巨大。有研究指出,我国公务员养老金替代率高达80%~100%,而企业员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为仅为40%左右。
老田陪着侯大同蹲在无花果树边。老田每次来,侯大同要么在伺弄他的无花果,要么就是抱着他的女儿。两件事都让老田摸不着头脑,一个大男人,喜欢花草倒也勉强说得过去,没听说过有谁喜欢果树的。何况,还这么痴迷。那女儿呢,都六七岁了,侯大同还整天抱着,累不累啊?老田觉得这个菜农真是怪。
提高情报分析质量的关键在于提高情报分析人员的水平。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和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公室的评估工作之所以受到决策者欢迎,首要原因是吸收了一大批顶尖级专家学者到情报部门服务。以威廉·兰格(W.L.Langer)和谢尔曼·肯特为代表的一大批学术界精英投身战略情报局,以自己的学识为国家安全决策服务。他们的努力赢得了决策者的尊重。中央情报局成立后,这批学术界的精英人物再次加入情报界,成为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公室的成员。他们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与决策者关系密切。他们的研究贴近实际,符合决策者需要,为《国家情报评估》赢得了声誉。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以谢尔曼·肯特为代表的老一代情报分析家悉数隐退,与大师们同时隐去的还有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质量。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关于对方意图方面的中长期评估的质量明显降低,重大情报失误也屡屡发生。国家评估办公室低估了越共通过柬埔寨获得补给的能力,低估了苏联核力量建设的目标和建设步伐,在1979年的伊朗危机发生时,也显得极为被动。1989年,美国情报界再次对苏联、东欧巨变表现得手足无措,其过程正如乔治·舒尔茨所描述的:“中央情报局未能意识到苏联的巨变正在发生。当戈尔巴乔夫首次出现在苏联政治舞台上时,中央情报局说他仅仅是口头说说,只不过是苏联的又一次欺骗努力;当这种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又改变口径,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问题上是严肃的,但苏联有一个强大的僵化的体制,这使得任何变革都不可能成功。”[28]这些失误严重影响了情报评估的声誉,成为决策者忽视情报的借口。实践证明,只有招聘一批具有全国性声誉的专家学者到情报分析部门任职,只有培养一批洞悉国际事务,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外交、历史知识与相当情报协调能力的人才,情报与决策之间的鸿沟才能得到有效的缝合。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一结论同黄新英,黄新丽,李玲等[2] 相一致。
4 结束语
本文认为,在国家安全决策中,情报不仅要提供基本信息,帮助决策者感知态势,更应该用自身的专业素养,帮助决策者理解态势,并对未来态势做出预测。恰当地定位情报的作用,知彼知己,提供高质量的情报产品,是情报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参考文献
[1] 王桂芳.国家安全战略学[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8:169-170.
[2] 《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163.
[3] Commission on CIA activitie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report to the president.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EB/OL].[2019-03-20].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78-00300R000100010052-4.pdf.
[4] 王文荣.战略学[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79,117.
[5] 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68,121,176,871.
[6] HANDEL M I.Intelligence and military operations[C].London:Frank Cass,1990:6-7.
[7] STARES P B.Command performance:the neglected dimension of European security[M].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1:19.
[8]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National intelligence strategy,Aug.2009[EB/OL].[2018-10-09].https://www.scribd.com/document/19785855/National-Intelligence-Strategy-of-USA-August-2009/.
[9] 梅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243.
[10] 塞林格,洛朗.海湾战争——秘密档案[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6-7,18-19,56,65.
[11] 徐国平.国家安全决策新论[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1:78.
[12] 田上四郎.中东战争全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112-116.
[13] RANELAGH J.The agency: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6:56,242,421.
[14] 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应对危机——美国国家安全机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47.
[15] Joint publication 2-0,Joint Intelligence.22 June 2007[EB/OL].[ 2019-02-21].https://www.jcs.mil/Portals/36/Documents/Doctrine/pubs/jp2_0.pdf/.
[16] GARTHOFF R L.US intelligence i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C].BLIGHT,WELCH.Intelligence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London:Frank Cass,1998:27.
[17] 孙建民,汪民敏,杨传英.情报战战例选析[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0:305.
[18] 谢尔曼·肯特.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52,58,195-196.
[19] 安东尼·H·科德斯曼.伊拉克战争:战略战术及军事上的经验教训[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211.
[20]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索沃战争(中)[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281.
[21]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Report on prewar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about postwar Iraq (July 9,2004):6[EB/OL].[2019-01-28].https://www.intelligence.senate.gov/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11076.pdf/.
[22] 中国古代兵法[M].北京:军事科学院资料室,1982:491.
[23] 姜涛.管子名言[M].济南:齐鲁书社,1992:114.
[24] 曹操,等.十一家注孙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
[25] TREVERTON G.Reshaping national intelligence for an age of inform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83-185.
[26] GEORGE R Z,BRUCE J B.Analyzing intelligence[M].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4:83.
[27] 李景龙.情报分析:理论、方法与案例[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7.
[28] SHULTZ G P.Turmoil and triumph: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s[M].NY:Scribner’s,1993:864.
On the Function of Intelligence in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Abstract : [Purpose/significance] To review 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in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process,and redefine the guiding role of intelligence in decision-making.[Method/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nalyzing strategic environment,monitoring strategic situation and evaluating strategy selec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in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Result/conclusion] Intelligence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not just as “service” and “support”.
Keywords :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role of intelligence;strategy;intelligence analysis
DOI: 10.16353/j.cnki.1000-7490.2019.10.00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17ZDA291。
作者简介: 高金虎 ,男,1966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录用日期: 2019-04-30
标签:国家安全情报论文; 国家安全决策论文; 情报作用论文; 战略论文; 情报分析论文;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