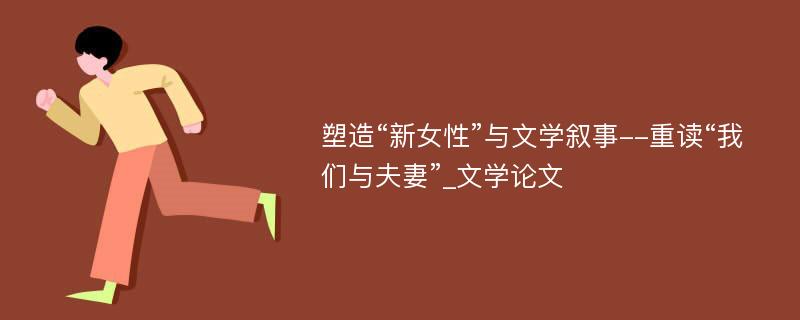
塑造“新妇女”与文学叙事——重读《我们夫妇之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夫妇论文,妇女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77(2009)01-0043-06
建国之后受到批判的第一篇小说是《我们夫妇之间》,这是萧也牧的一个短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对出身不同的夫妻进城后思想上出现矛盾,调和矛盾重归于好的经历,小说发表后反响非常大,《光明日报》等四家报刊发表了推荐文章,上海昆仑影片公司很快将它推上了银幕。当时的许多批评家都认为,这是一篇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作品,情节单纯明显,描写细腻委婉。尤其在语言上更显得生动朴素,读起来也动人,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有感染力的短篇。但是很快形势急转,批判是从1951年6月开始的,《人民日报》、《文艺报》同时发表文章批评萧也牧及其小说。《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一文说,近年来文艺创作思想上存在着一种“脱离生活,或者是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不健康倾向”[1]。文章还认为《我们夫妇之间》的主要问题,小说描写夫妇之间的矛盾,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两种思想斗争庸俗化了;歪曲了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和丑化了工农干部。这篇文章是一个信号,不少报刊从此对萧也牧创作展开批判。丁玲此时发表文章指出,对萧也牧作品必须“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因为它“已经被一部分人当着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2]。小说被从阶级的角度来解读是很正常的,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传统是倾向于从这个角度分析文学作品的价值的,另一方面在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的危机与变革中,阶级性质还是一个斗争与自我约束的工具。也正是这样的环境给小说的解读带来另外的空间,据作者自己说,他写《我们夫妇之间》原想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一个新的人物。
批评者们和萧也牧之间存在严重的误解,萧也牧是一个敏感地觉察时代需要的知识分子,批评家关注的是他展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矛盾,尽管平反以后人们给它的评价还是“干预现实的好小说”[3],对于他要塑造一个“新的人物”的初衷却集体忽略和误解了,这个新人物是一个新妇女——“我的妻”。1950年是新中国的建立初期,是一个树立政治权威、新社会规范、新人伦秩序、新生产关系的年代,这需要有新政策的推动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革新,也需要具有巨大稳定性的道德力量的协助完成。可以说,叙事作品之所以追求新人物的描写也是出于时代的需要,新人物所表现的那种理想的人格精神力量,热烈的投入革命的激情,一心一意忠诚于革命和国家等,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凝聚力,重整支离破碎的世道。“我的妻”原来是一个倔强认真的革命者,“我”也是因为这个爱上她的,但是进城后,我对她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从基本的外貌打扮到性格都产生了厌烦情绪。
妻子调走以后渐渐发生了“转变”,服装渐渐整洁起来,“他妈的”“鸡巴”一类口头语也没有了,见了生人也有礼貌了,用妻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组织上号召我们:现在我们新国家成立了!我们的行动,态度,要代表大国家的精神;风纪扣要扣好,走路不要东张西望;不要一边走一边吃东西,在可能的条件下讲究整洁朴素,不腐化不浪费就行。”我们之间矛盾的解决不是自己调解而是另外的力量促使的,首先是我对于矛盾的认识——“我对她依然还很留恋,还没有决心和勇气断然和她决裂!特别是当我比较清醒的时候,仔细想来,我们之间的一切冲突和纠纷,原本都是一些极其琐碎的小节,并非是生活里边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决心用理智和忍耐,来帮助她克服某些缺点!”最根本的东西没有说是什么,可是我们能猜测是共同的革命经历和信仰,甚至可以延伸出对于新生国家的热爱与忠诚。其次是妻子的转变,她的某些观点和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甚至因为以前自己看不上的女工打扮,认真地教训起我来了:“你不能从形式上、生活习惯上去看问题!她们在旧社会都是被压迫的人!她迫切需要解放!同志!狭隘的保守观点要不得!”妻子的转变应该归结于“她又学了一套新理论啦!”,所以妻子已经从对于一个阶级的朴素认同转变成对于一个新兴国家的认同。大到国家政党的政策都表现出一种宽容与涵纳的意识,建国初期的新气象里文明的概念与新生,脱胎换骨一样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在趣味的对立,价值观的抵触上起到了调和的作用,不说脏话,注重仪表,与对一个新民族新国家的呼唤是殊途同归,它从生活方式入手,想象并虚拟一个新的社会,生活风格,话语,肢体语言,性,交往等方面都包括在内。比如民国初期宣布废除“老爷”、“奴才”等不平等称谓,代之以“先生”、“小姐”等平等称呼,然而在后来的极左时期,“先生”、“小姐”成为极其难听的骂人的话,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称呼的转变是和不同的想象有关的。我的妻现在所担任的工作是女工工作,在那些女工里边,也有不少擦粉抹口红的,有不少脑袋像个“草鸡窝”的……可是她和她们很能接近,已经变得很亲近。转变与亲近的原因就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对现实有了新的认识,从一个单纯朴素疾恶如仇的革命者的立场转变成包容宽广高瞻远瞩的建设者的立场。
这里存在着一个看起来水火不容的矛盾:在“讲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故事”的过程中,阶级的故事与新兴国家的故事的矛盾。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就以阶级这一现代性概念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细致分析,而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精辟地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地位做了一个颠倒: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否定了“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准——西方文化模式,建立起另一个标准——中国大众(主要是中国农民)的需要,他强调知识分子唯有背叛自己的教养,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改造思想、脱胎换骨,才有可能适应新的文化规范。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既定的关系是作品安排角色的一个考虑,代表了工农干部的“我的妻”自然是要教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的,而且明显能感到叙述者对于“我的妻”的谦卑与认同,他把自己置于一个阶级尚不具有合法性的位置上,他的言语与行为都是这个意识的结果。然而妻子的改变却是另一条路上的事情了,妻子对于涂脂抹粉的女工不再强烈本能的憎恶,而且自己的衣着打扮,甚至肢体动作都有了改变,温柔浪漫了,总之和“我”私下批评的“小资产阶级”方向靠近了,摆脱了“土气”,符合了“我”的要求(这也是敏感的批评家们迅速觉察到阶级方向不对的原因)。叙述者本着一个阶级故事的原则却讲了一个违背阶级原则的故事。
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写于1949年秋天,初稿于北京,重改于天津海河之滨,原载1950年《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时间上正是一个中国与妇女命运改变的时机。同时期出现的还有许多表现新妇女的作品,但是与这篇小说不同的是,其他的诸如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新事新办》,还有方纪的小说集《新人新事》,基本是贯彻《婚姻法》的指示的,《我们夫妇之间》这篇小说的编辑是秦兆阳回忆,“解放以后彼此是怎么相识的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几次约我去中山公园的茶室喝茶,跟我谈论他的写作构思,征求我的意见。那时他颇有些青年气,单纯、直率、随便,对自己颇有信心。于是他给我寄来了《我们夫妇之间》。”解放初期,作家们有的处于观望状态,有的开始积极真诚地投入新国家新社会的赞美中,萧也牧应该就是年轻而富有激情的投入对新国家赞美和憧憬的一类作家。与后来的作家写作相比,他的自觉性源自激情的驱使,迎合修饰的成分不多,侧重原生态的生活,也是别人评价“活泼生动”的原因所在。从作者的“单纯,直率,随便,对自己颇有信心”,似乎也能想象一个乐观,热情,没有阶级自卑感的萧也牧,而他的这种想象并非空穴来风。近代以来,中国新旧文化的斗争以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为界限,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以前,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文化)与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封建文化的主导力量。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各民主阶级的共同利益是第一位的,他们的不同利益则是第二位的。他们应当为了这种共同利益而实行阶级合作。他们的不同利益应当服从于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的不同要求和他们之间的阶级矛盾,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任务,应当和可以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在这种调节之下,他们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各项建设任务。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调节阶级关系,实行阶级合作,是第一位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则是第二位的。[4]
但是,叙述者让“我的妻”的思想行为走得太远了,以至于超出了一个新生时代的容忍范围,虽然在它的初生期有过大量的类似容忍与宽容政策,无论是文学还是政治。萧也牧的乐观热情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期望国家富强的一个延续,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欢迎党,就是因为他们珍视党有统一国家的能力,“人”的问题应该和“国”的问题相提并论,国家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晚清以来尤其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就是民族独立和政治主权,“中国社会的兴盛与灭亡实际上正是几代启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动力与归宿,无论他们提出什么样的思想命题,无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这个原动力如何冲突,民族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5]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给人灵光一闪的感觉,新妇女其实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被塑造,在强调阶级冲突的时代承担了一个朦胧的阶级共存的意图,新妇女表征着一个国际性的受压迫的群体,以“劳动”为特征,是无产阶级阵营中的重要力量,是与资产阶级针锋相对的。“妇女”不是“女性”,不是那种烫了头发进了学堂整天想着爱情想着自我的群体,而是实现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因此,当共产党的主要活动范围仍然集中在城市之内时,“妇女”基本等同于女工,“妇女解放”因此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相连。叙述者让女工认同了烫发涂口红注意穿着打扮这些一度受到批评的特征,向警予在20年代的一系列评论中就曾经将这样的“女性”归为资产阶级的范畴,指出要与这种女性形象决裂,投身真正的解放事业(转述自TaniE.Barlow,1994)。这种意识是建立在“中国社会的兴盛与灭亡”的期待基础上的,随后如潮的阶级批评把这个微弱的光给淹没了。值得回味的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新历史即将开始的时候,文学中有这么一个瞬间,不管作者是否有这个意识,新时期开始的时候,巧合的是在小说《内当家》中,这种意图才有一个明确的表示。在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名列榜首,作者自己说:“《内当家》是我试图运用阶级观点描写新的社会、新的人物的一次探索。”有的论者鲜明地指出,“《内当家》在错综纷纭的社会现象中,捕捉到的是这样一个矛盾,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过去属于两个敌对营垒中的人们的关系,特别是小说的主人公接待的,是那样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华侨?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影响到党的农村政策的落实,影响到人民和国家的尊严,甚至还影响到今后农村的发展。”[6]
家庭与“新妇女”
如果从抽象国家意义上来谈新中国妇女,容易有缺乏现实感的弊端,这也是在“国家”向度上塑造新妇女不能走得更远的一个原因,它往往要落实到家庭中去。传统中国的家庭并非纯粹的“私人空间”,它除了担负繁衍后代的责任外,在经济生产和技术传承上是一种组合形式,此外还兼备某种公共空间的功能:家庭在家庭成员内部,一是信仰和精神寄托,二是公正和公平的仲裁,在家庭成员外部,它是连接着“国”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同构”。“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家国同构”的传统,而战时中国文学则开始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异,“家国同构”的传统在民族命运和无产阶级政治的层面上得到重构。
1950年《人民日报》关于妇女解放的报道题目有4月26日《受尽封建家庭迫害的傅玉兰解放了》、7月16日~17日《婚姻法给了我自由!》、9月22日《咱们胜利地结婚了》,《解放日报》9月1日的《一个童养媳的新生》,无论是报道者的还是被采访者的语言,都使用了“压迫”“解放”“国家”“党”“自由”这些概念,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解放,新生联系起来,妇女合适而恰当地演绎了国家的理论,但是这些也只能是一些报道与词汇,缺少现实感,正如唐尼·白露论述的,早期共产党人毫无异议地接受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和生育机器理论、目的论、阶段论、国家社会二元论,以及这类话语声称的国际的普遍意义。白露指出:如果把欧洲作为中心(这是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观点),中国历史就不可避免地被排挤到次要边缘地位,变成文化意义上欧洲的半殖民地,中国妇女史也就成了欧洲工人阶级历史的附属品。然而20世纪30年代在农村根据地的实践改变了他们对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盲从,欧洲妇女的模式被中国农村革命中的妇女所取代。当然这一时期的“妇女”是苏维埃政权组织机构、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产物。作为一个理想模式,妇女应该打破家庭观念,服从国家的需要,投入到当地政治活动中去。对此美国女性主义者最初的解释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家庭革命的目标,从而牺牲了妇女利益。白露则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集权政治渗透家庭关系的开始。“妇女”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概念,它暗示着社会主义的光明未来,但忽略了与过去的联系:它所包含的“妇”与“女”与中国传统家庭有着天然的联系。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它与女性千百年来的作为“妇”“女”被压迫被侮辱的地位联系在一起,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劳动)/再生产(生殖)理论想象在一起,是一个包含过去痛苦,拥有先进理论参照,同时允诺一个未来的概念,但是它缺少中国的现实感。如果按照这朦胧的阶级共存的方向发展,新妇女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理念的演义。白露追溯了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妇女政策的演变并指出,到了20世纪40年代,苏维埃条例改变了把妇女作为家庭外的政治力量的提法,开始强调家庭本身的民主化以及男女在家庭中的政治作用。194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明确强调:“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任务;妇女能纺织、能养蚕、能种地、能喂猪……”。妇女是在日常家务劳动中与男性取得平等地位,并且和宏大的革命目标联系起来的。妇女还继续承担“贤妻良母”的角色,她们一如既往地延续历史上“岳母”的传统,精忠报国,默默支持,她们把儿子丈夫送上前线。这个政治化了的家庭符合农民的现实主义,比起鼓动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政策更受农村妇女的欢迎。白露强调:“毛泽东主义的国家和家庭互相渗透,妇女政治化是关键;这种通过家庭中的妇女政治化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做法既非传统也非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调和。”[7]
《我们夫妇之间》从另一个角度看,除了是叙述者自豪地讲述“我的妻”的故事外,还是一个“夫妇之间”的故事,夫妇成其为家庭,家庭在中国的语境中是女性的土壤与现实感的保证。《我们夫妇之间》里人物的设置和角色功能是新颖的,这在之前的小说里是不多见的,晚清“五四”运动以来,文学作品中男性作为女性精神导师已经成为一种范式,在男女精神关系上男性启蒙者的变成了受教育者。“我”不是一个像《创业史》里的梁生宝那样的兢兢业业为社会主义做贡献的男性,也不是革命小说里具有思想上指导意义的领路人,而是一个来自城市小知识分子阵营的内心上带有自私狭隘念头,回到城市后,革命意识有些须丧失,虚荣而又不失可爱的一个形象放矮了的男性革命者(他的形象和角色功能和《李双双小传》里的喜旺有类同的地方)。“我的妻”则是一个来自乡村饱受苦难的女革命者,解放后来到大城市仍然不失革命本色,时时刻刻遵守革命者的最初承诺和原则,对于反“革命”的东西有一种圣徒般仇恨。这里边首先是叙述者所默认的小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意识,把妇女放在教育者的位置上,引导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我”走出误区。《我们夫妇之间》里男女角色的功能划分是一个时代的体现,和之后出现的《李双双小传》是类似的,一对夫妻之间进步与落后的对比中,女方在思想和行动上总是处于先进的位置。但是也应该强调在男女角色这样的划分中,男性并不是一个单纯受教育者的代表,他们不是和落后粘合在一起的,而是有一种疏离。正是这个距离使得男性角色不是惹人讨厌,坚决反对的,而是带有某种可爱滑稽但不失纯真的特点。家庭已经成为新中国继续革命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男女之间不是对立,而是为着一个国家的目标互相砥砺促进的亲密伙伴关系。把女性作为一个文本的主角,还是要继续讨论下去的,这和福科在谈到希腊的婚姻与之后婚姻形式时有一个相同的问题:这种例外,罕见,是不是一种未来新道德的预示?福科在《性史》中[8]把丈夫和妻子德行的反思与家庭和家政的反思联系在一起,认为这远不是在以后道德中出现对等约束的先兆,而是对一种现实不对等的风格化。其实在以后的文学叙述中,妇女的政治化也不是出现对等的先兆,而是作为一种叙述方式来完成对现实不对等的风格化。
作为一种叙述特征出现的新妇女在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功能的转变,有具体的原因。在1949年的时间里看,文学作品中这类女角色的出现也不是偶然为之的,现实社会里妇女地位的迅速上升,解放初期的妇女政策与宣传,已经把妇女地位提高到国家主人的位置。妻子已经掌握了一套理论,比如压迫,解放,并且自觉地用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我们的行动,态度,要代表大国家的精神”,妇女已经自觉地站在了国家一边,妇女形象也有崇高化的倾向。从文本中看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妇女思维和行动的潜在支持力量,从我们夫妇之间矛盾的解决能体会到国家作为一种超越性力量已经支配着平凡夫妻的日常生活。《婚姻法》制定以后,中央政府在1950年到1953年下达了一些涉及到《婚姻法》的重要文件,从各全党的通知,实施法令,法律条文,到实施总结报告,贯彻情况都有具体的要求。此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以及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中明确规定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1953年3月,全国还专门举行了贯彻婚姻法运动月,这一年出版的《婚姻法带来的幸福》[9]描述了很多家庭竞赛,都是女方提出要同新郎比赛,看谁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贡献大。AL·斯特郎曾经谈起过中国的“大家庭”,它由父母,几个儿子和媳妇以及许多孙子孙女组成。这样的家庭尽管总是夹杂着争吵、疑忌,但它一旦合乎传统的常规,便是很难透悉的了。于是统治者要求拆散这样的家庭,“婚姻政策也是助长小家庭成立,许多妇女亦常是策动分家最有力者。其实每个人都明白,妇女爱分家是出于私利的考虑:减少劳动负担,但同时可以继续自家收入。但革命就是利用了妇女这一点,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家庭的土地和财产被合法地分成更加细小的份额。“妇女在这里便是作为革命的盟军探入家庭,成为革命安排在家庭中的内应。”[10]这样的安排也是有经验的,1945年浦安修在《五年来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初步总结》里针对妇女提出与贫农离婚的现象,提出要开展讲习班教育妇女,并利用妇女的善感和自私来做妇女工作和完成政治任务。党和妇女的结盟在这个时候要比党和农民的联盟来得稳固,当时的一份工作报告赞扬了妇女群众的情绪特别热烈,富有罕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时常走上了农民的前头,农民反而落后了。”
妇女在文学作品中的特殊地位,除了政治策略的要求以外,还有古代文学,民间故事中的原型因素,比如古代《聊斋》故事中的女鬼花妖,民间故事中的快嘴,“巧媳妇”形象。这类女性基本的特点是:生存本事突出,能言善辩,热心肠,风风火火,经常为人排忧解难,性格乐观。这种性格符合意识形态宣传所需要的革命型改革型新人,也容易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快乐达观的生活态度易于渲染革命的乐观主义情绪,此种女性原本是社会的不协和之音,此时反而容易转化成革命式的批判先锋。《李双双小传》里的李双双、浩然《彩霞》中的彩霞、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里的张腊月、王宗元《惠嫂》中的惠嫂……都是这种类型的新妇女形象,“我的妻”从性格的直爽,做事的利落与认真,工作作风的雷厉风行也是属于这个谱系的,所不同的是“我的妻”在实践中性格的因素已经成为一个从属的部分,真正在行动中发挥作用的不再是性格(林黛玉的性格因素是《红楼梦》里女性在精神上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和动力),李双双也是。穆桂英,花木兰等女英雄,虽然是故事的绝对主角,推动故事发展,情节转换的是性格,巾帼不让须眉,在男女关系上,她们还是在一个辅助与从属的位置上,她们只是供人观赏的传奇逸闻,不会成为一个文学和社会的角色模范。
新妇女在新建国家的欢乐与抱负里获得了认可与庇护,文学中的“新妇女”在这样的动力与刺激中几乎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继承的知识分子理想和倍受鼓舞的新气象创造了文学叙述上的一个契机。但是,当国家依靠妇女宣传自己政策的时候,它进入家庭的领地,所有的开天辟地的激情都落入现实的土壤,新妇女也顺势成为纠结在建国初期所有问题矛盾里的一个文学叙事的内容。
[收稿日期]2009-0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