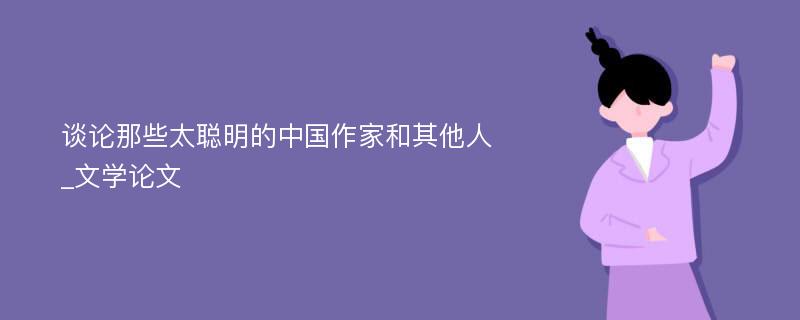
再谈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谈论文,及其他论文,中国作家论文,聪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于聪明……》一文,在《文艺争鸣》1994年第6期刊载后,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所谓反响。不少人说好,也有些人恼怒异常,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我当然为此而高兴。恼怒异常么,这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正可理解为“骂”到了痛处。某种人,某种一向很“得体”者,一向长袖善舞者,一向鼓吹“宽容”和“幽默”者,在一个“文学青年”的几句“骂”面前,便“露马脚”了,“得体”和“宽容”的面具都撕去了,所谓的“幽默”也全不见踪影,只剩下泼皮式的谩骂,终于让世人看到了他的真面目。要说“贡献”么,我想这便可算作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对“当前和今后的文艺建设”所做的“一点”。
用不着隐讳,我这里说的是王蒙先生。回到乡间老家过年之前,我先读到了王蒙先生发表在1月17日《新民晚报》上的《黑马与黑驹》一文。要说“骂”,王蒙先生的这篇文章才真是货真价实的骂。读这篇文章,我当即想到王蒙先生的长篇小说《活动变形人》中姜静珍的隔墙骂邻,而且跳着脚(我曾把某些晚报文章称作“喷嚏”,而王蒙先生的这篇文章则是在喷血了。)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黑马与黑驹》一文,也让我有了一点专业上的收获,即明白了作者何以能把姜静珍这个很有特色的人物形象刻画得那么生动(我以为这是这部小说中最精彩之处,其他都并不特别值得称道:这算是顺便再“骂”一次吧。)领教了《黑马与黑驹》中姜静珍式的谩骂后,不几天我又在王蒙先生发表于《上海文学》1995年第1期上的《沪上思絮录》一文中,见识了王熙凤式的夹枪带棒。我真没想到,对于一个过去文章“一篇也发表不了”的“文学青年”,王蒙先生泼起污水来竟如此不择手法。捏造、歪曲、诬陷、构陷、影射,以及手法低劣的人身攻击,以及变相的“告密”,全来了。曾几何时,当某些人对王蒙先生的《坚硬的稀粥》进行用心险恶的构陷时,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同许多人一样为此而愤怒。而现在,当时别人用于他的那一套,王蒙先生又都用来对付一个“文学青年”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真不知该让人说什么才好。
我1986年跳槽到中文系当文学专业研究生后,就觉得,一个从事文学评论的人,应该尽可能地说点真话,尽可能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光是吹吹捧捧,“啃招牌边”实在无聊。1987年到现在,我发表的百余篇习作(确实只不过是习作)中,有“骂”,也有赞,即使对同一个作家,也两者都有。例如,我推崇过张炜的《古船》,而对其《九月寓言》表示过不满;我肯定过张承志近年的散文也对其《金牧场》发表过异议;我喜欢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但又认为过分的“汪曾祺热”有害;我赞赏过余华前期的小说而对近期的《活着》一类作品表示了厌恶,我佩服王晓明对张贤亮、高晓声等作家的评析,又对他的鲁迅研究发表过不同意见……至于《过于聪明……》以及近期的一些短文,我自己并未特别看重,但居然有了这样的“影响”,我没有理由不为此“庆幸”。借用王朔先生的话说,写作么,不就是为了出名吗?索性学一回王朔,庶几能得到某种曲意的蔽护。“王朔不是理论家”,我也不是;王朔是“大腕作家”,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文学青年”;王朔骂人骂得比我刻毒,甚至说“知识分子”是“灵魂的扒手”,而我骂得远不如他。对王朔宽容者,主张对王朔的话不较真者,理应对我更持此种态度。不然,便太令人费解了。
《过于聪明……》这篇数千字的其实并不怎样足道的文章,写于1994年4月,先寄一家文论报纸,编辑很喜欢,来信说写出了他心中同样的感受。但其时恰逢春末夏初,文章暂不能发表,而不久,报纸决定停刊(后在停刊半年后又复刊),我于是把文章寄《文艺争鸣》。寄出后一直无音讯,我也懒得催问,甚至把此事都忘记了。文章发表后,我一直未读到,迄今也未见到样刊。文章中一些具体论述都记不清了。现在在乡间,不可能找到这本刊物,所以这里只能就文章主旨再做些说明。
在几次与朋友谈天时,我说,中国作家也许在怎样立身处世上用的心力太多了,在怎样做人上智慧太发达了,而对文学创作来说,可能是一种心理障碍。朋友表示赞同,并鼓励我把这种想法写出来,我于是写出来了。因此,这篇文章是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来谈论问题的,其主旨,并不是从伦理学的立场来评价作家,甚至也不是在谈论文化人格问题,而是在谈论中国作家的一种创作心理缺陷。我以为,形而下的做人的聪明,形而下的生存技巧,形而下的全身之术,过于发达后,形而上的哲理探寻,形而上的艺术情思,形而上的文学感觉,必然会受到阻碍。前者,如果是冰,后者便是炭,冰炭原不可同器。但不得已而同器后,冰过于多,则必然要使炭焰受到压制。生存之道意义上的聪明,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心理障碍,当然通常并非是有意识的,自觉的,而近乎一种下意识,一种“本能”。当作家的这种下意识,这种“本能”,大于他的艺术直觉,大于他的“文学本能”时,当作家做人的聪明大于他做人的天真时,他的创作当然会受到不利的影响。某种意义上,没有天真便没有艺术。杜甫有“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晴蜓款款飞”的诗句,宋儒却说“道此闲言语做甚!”这是因为理学把他的欣赏艺术所必需的一点天真都泯灭了。同样,立身处世上的聪明过大,当然也会把艺术创作上的天真挤小。中国有俗语云“糊涂油蒙了心”。糊涂油蒙了心,便丧失立身处世上的聪明。相反,“聪明油”蒙了心,便丧失文学创作上的天真。艺术创作某种意义上正是一种愚笨的事业。为什么西方有许多大作家大艺术家,在立身处世上都像个孩子?为什么中国古代有不少人都是在人生失意,不求进取,对做人不再有那么多的顾忌时,才写出好作品?一部分道理也正在这里。而所谓“诗穷而后工”,所谓“文章憎命达”,某种意义上道理也正在这里。
所以我这篇文章,本意只是在陈述一种创作心理上的事实,并不是从伦理道德的意义上指责作家不够“壮烈”,并不像王蒙先生说的那样“骂”作家没有在“文革”中“壮烈牺牲”。创作心理障碍与文化人格上的缺陷,虽然有联系,但毕竟属于不同的问题。偷换概念,七绕八绕,把你绕进他的伏击圈,真是王蒙先生的拿手好戏。
过于聪明,有个体的原因,也有文化的根源。中国是一个做人之道过于发达的地方。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中国文化是早熟文化,而特征便是做人之道,便是形而下意义上的生存智慧极早地便很发达。这种文化特性,给中国学术带来某种严重缺陷。与西方学术的“静心求知,绝不急于功利”相比,中国则几乎无“学”。中国“学不能独立于术之外而自行发展”。“中国几千年来学术不分,其所谓学问大抵是术而非学,最为大病。其结果学固然不会有,术亦同样不会发达,恰落于‘不学无术’那句老话。”梁先生说,“中国人不能离用而求知”,“不能离术而有学”。中国在学术的方向方法上的这种特性,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我在《过于聪明……》一文中所谈论的在文学创作的方向方法上的特性。而二者都根源于文化的早熟,都根源于形而下的做人之道,形而下的生存智慧的过于发达(指出这种特性,并非意味着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为防止歪曲和构陷,特此说明。)
其实,做人太聪明有碍于文学创作的观点,前人也提出过。明代的李贽力倡“童心说”,指出文学创作要有童心,要有赤子之心,要有真性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问题的。
在《过于聪明……》一文中,我顺手引用了几条材料。这里再顺手引用一条。回家的江轮上,读到了王蒙先生发表于《读书》1994年第12期上的《名士风流之后》一文。文中,关于嵇康,有这样的话:“山涛向朝廷推荐嵇康代已为官,看不出有什么恶劣的用心,辞谢是可以的,写‘公开信’与之绝交,就有点不合分寸。”在做人之道的意义上,这的确表现了嵇康的“性格弱点”,表现了立身处世上的“不聪明”。但也正是这种“性格弱点”,这种“不聪明”,成就了嵇康一种堪称伟大的人格,使得中国文学史上有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倘若嵇康做人世故一点,聪明一点,懂得一点“分寸”,中国文学史上不是便少了一篇名作么?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史上,如果没有一群嵇康这样的人,不是便如头顶上没有星辰么?要真正做到嵇康这样,当然不易。但要对这种人格表示敬仰,总还可以,后人对这种人格“虽不能至”,但总应该“心向往之”的。嵇康是鲁迅所喜爱者。鲁迅在思想、性格、文风上都颇受嵇康影响,也曾在二十年间十次校勘《嵇康集》。后人妄自“粪土”嵇康,也正用得着“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句诗。
《过于聪明……》一文发表后,据说有位先生在批驳文章中说:这是不是某某派在以这种面目出现?我只得苦笑。这某某派也真可悲,想不到如今成为另一类人的保护伞,挡箭牌。遇到批判,指责时,便把批判指责者“打”成某某派,而只要对手是某某派,也就意味着自己的正确。也正由于这种原因,近些年,文学界、文化界在许多问题上呈颇为暧昧的状态,为避帮派嫌疑,许多人有话不敢说,不愿说。这种局面实在应该结束了。
写到这里,无端地想起《聊斋志异》中的一则“盗户”故事。虽然不很对景,但殊堪玩味。好在不长,抄在这里,作为结束:
顺治间,腾、峄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复相苦,烦有司稽籍焉。适官署多狐,宰有女为所惑,聘术士来,符捉入瓶,将炽以火。狐在瓶内大呼曰:“我盗户也!”闻者无不匿笑。
异史氏曰:“今有明火劫人者,官不以为盗而以为奸;逾墙行淫者,每不自认奸而自认盗:世局又一变矣。设今日官署有狐,亦必大呼曰‘吾盗’无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