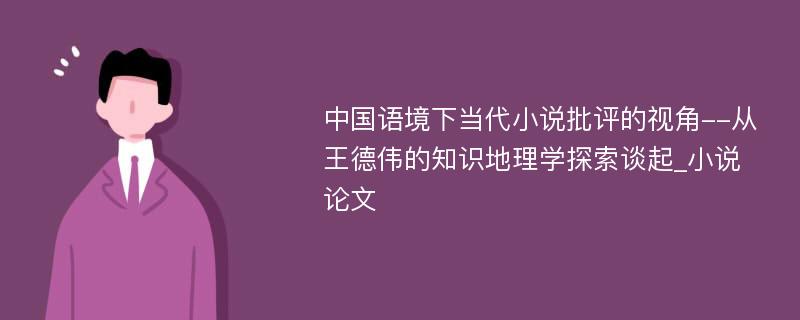
“华文语境”中的当代小说批评视界——从王德威的“知识地理”探勘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视界论文,批评论文,地理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63(2002)3-0017-06
我间或从事当代小说批评,不时暗自嘀咕:大陆批评界的理论言说是否碍于知识谱系凌乱或受限于它种藩篱,因而缺乏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中的对话能力;同时也有杞忧:当代批评恐怕已经无人具备“囊括四海,包举宇内”的能力,面对所有中文写作了。然而看到王德威的《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注:王德威:《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的工作成绩,不由地惊讶其“跨越政治地理的狭隘藩篱,探勘知识地理的无限天地”(注:王德威:麦田人文编辑宗旨,见麦田人文系列封面勒口介绍。)的成效。讶异之余,不禁要问王氏何以能?不禁要追问其学术路径,要求为他活跃其间的这一片批评领域命名。
王氏自明路径如上所言,可效法与否,正应是我们探询批评发展的问答之一。循着他“知识地理”探勘的工作路径前行,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有着极为广泛的对话空间的批评视界,它超出了我们习惯的大陆当代文学批评范畴,包揽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通常分工:台港澳、马华、欧美及澳洲。更重要的是其间越过的绝不止于空间与国界,它整合了所有以中文叙事构成的意义空间,既构成了历时性的上下文关系,又构成了平行的交互文关系。我姑且代为命名,称这一前所未有的批评视界为“华文语境”。命名的目的在于充分揭示其内涵,王氏指涉整个当代中文小说的评点恰恰为“华文语境”的内涵揭示提供了必要解释,理解了他的批评中的主要追求,理解了他是怎样追求的,理解了他为什么追求,就接近了“华文语境”的要旨。我们仍要先行了解《众声喧哗以后》结集出现的意义,此后才谈得上对它的知识地理路径的复现与勾勒,至于是跟进呢还是另辟新径,那要在充分理解了我们的评说对象以后才能决定。
王氏《众声喧哗以后》的首要意义在于其于广泛的对话中的伦理向度的思考,这是他对80年代批评富于建构性的超越。当年,王氏从巴赫金的多声复调的社会对话及实践方式中引申出“众声喧哗”的概念,产生了广泛影响,已经为整个中文批评界广泛接受。新世纪初,他将90年代的批评成果结集,既是对这十年中文小说批评工作的总结,也是一次重要的“盘整”。他提出“众声喧哗以后”,致力于从自己开始一个“后众声喧哗”的文学创作实践与批评的新起点。这不仅仅是一个修辞(社会?)伦理的思考方向或是个人当下的批评自觉,当今的文坛上的小说实践仍处于“众声喧哗”之中。他所要凸现的是批评主体的作用,以及示范在不同主体间如何“折冲群己,出入众声的对话性”,不过只有他一人意识明确地践行并显出了成效。他的“囊括四海,包举宇内”的批评工作没有霸权的意味,却颇有“温柔敦厚”之风,遗憾的是那种理想的“社群中人我交互定义,安顿彼此位置的过程”仅在他那里开始,整个批评界短期内还不一定能超出“有话要说”的主流阶段,还会继续话语霸权争夺的喧哗,但知其难而为之的努力弥为珍贵。
这一著作的另一重意义在于将一般人视为难以相提并论的90年代中文小说作一统整观。说它难,是因为除了都用中文写作以外,90年代的各个批评对象间既没有过大一统的历史,也没有试图建立乌托邦的努力,只有现状的裂痕处处。批评对象有着世纪末的种种症候,批评家坚持以一“己”之衷对这“症候”之“群”进行“望、闻、问、切”的对话,折冲群己而不被诸症感染——我们习见的当今大陆某种批评的声音常常消失混迹于创作的喧哗杂音之中,真是一桩不易的事情。面对32个台湾作家、31个遍及全世界(包括大陆)的各社群中的作家的创作,面对多种小说创作的文坛现象,王氏显示出来的主体的独立与坚定性保证了这一工作的统整与逻辑一致性。
与“华文语境”一词的巨大包容性相符,王氏以巴赫金的“对话”哲学为理论基础,展示出对种种复杂的对话关系的思辩。90多篇评点,他由一个个文本剖析展示着90年代在台湾出版的中文小说的无所不在的对话:台湾文学的内部对话(存在于过去与现在、现在与现在及将来,诸如:《现代文学》的健将、“三三”的“老灵魂”、当今的文字爱欲者们之间),大陆与台湾的“竞写”式的对话,晚清、“五四”与当今的对话,后现代叙事技术手段与“古法”的对话,当代生活(政治、文化、性)与虚构叙事的对话,诸种文类之间的对话,乃至当代种种批评理论话语间的对话……。其中的复杂丰富性,正是华文语境的深邃广阔的内涵,也体现着批评家的学养;其中的辩证,正是王氏的出入众声的折冲努力的立场与印记。
要在王德威近百篇90年代小说批评中寻找其“知识地理”的路径,实在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所以我必须确立一个工作“主脑”,并由此而理出几个头绪线索,以便得其真意。我以为,王氏的“小说观念”正是这样一个主脑,其中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广域对话”的美学原则,批评的身份及艺术策略,既是小说观念的有机内涵,也贯穿了知识空间;而且这样的观念中也处处体现着伦理向度的思考与追求。
王氏小说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的思考对象是小说的虚构性想象与历史(现实)的关系。无论小说还是历史都要用文字来表现,文字意义的真实并不因叙述标示的文类而定。历史叙事的可信度与小说想象的真实性,孰优孰劣真不好一概而论。王氏通过对莫言等的当今小说的阐释告诉我们:“当历史不能满足我们诠释现实的欲望时,寓言升起。”又说:“在历史的尽头,小说升起。”他强调“如何把历史变为寓言甚至预言的努力,才是我们的用心所在”(注:王德威:《众声喧哗以后》。下引用同一出处的原文,将不再注明。)。回想起一百年前的严复、夏曾佑和梁启超的“小说出于经史之上”的说法,我们看到了百年间前后对话的意义所在,王氏乃至绝大多数的小说实践者已经排除了“经书”的绝对神圣性质。至于“史书”,即使不说它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绝对权威价值也已经动摇,小说的意义表达功能作用可以比历史走得更远。文字的多义性赋予了小说比任何文类更大的象征、暗示、多重指涉的作用,即使小说成了“小众文类”,它仍然最有表现力。跨越百年进行小说价值重估,语言学在王氏那里的中介作用当不可忽略。
所以在小说与历史之间,王氏宁可接受杂言纷陈的断裂,也不愿接受缺乏个人立场的大一统叙述;他宁愿欣赏对历史情境的疏离的编造,对单一主流声音的颠覆,也不愿接受一种“写实主义”的宏大叙事。断裂的叙述构成对阅读的挑战,唤起参与的“阅读愉悦”,若言轻松安稳地接受那种陈旧的忠实于某个权威声音的叙述,没有任何因应的话语空间,则与王氏由历史进入与现实的对话的立场大为抵触。王氏解释苏童为什么写不好《武则天》,正因为它本应该是历史的尽头升起的小说,是靠想象支撑的世界,但苏童们重新书写历史时,却受到了历史本事的限制,叙事与虚构掉落到历史物质之阵中。想象的困境必然构成作家的发声障碍。
小说中的想象空间应该有多大?中文小说无论写历史还是现实,都是为着在想象中构建民族国家。因而小说的五彩缤纷的叙事就是多途径的想象中国的方法,想象要靠文字来呈现,如何赢得文字欲望的更有效的表现,便是王氏最关心的小说观念的内涵之一。所以,他将极大的批评兴趣放在了富有强烈表现欲望的创作对象身上。在台湾作家中,他用了四篇文章来论述张大春,对大陆作家则将此项偏爱置于“莫言”身上。评前者的《大头春的忧国新招——<撒谎的信徒>》,对作者用魔幻写实的手法在有限的篇幅中容纳大量的历史人物的肯定,还不如对他的瞎掰的大人物行止的插曲的欣赏。评后者,他说“《丰乳肥臀》是最不典型的母爱加革命历史小说”,评“共和国吃喝撒拉狂想曲”《酒国》,最为欣赏的是其文字的欲望呈现。他欣赏孟晖《盂兰变》“把武则天短暂的世AI写作成中国中古‘工艺复兴’的奇特时刻”,因为“从人与人、人与物的描写间,她看出了一段特属唐代的历史风采”。这大概更接近于我们惯常说的艺术的真实。走出政治意识形态的荫蔽,我们的小说观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王氏:小说事业无他,移花接木,假戏真作而已——文字的变装演出。
王氏不太看重教科书式文学史的定性(型)叙述,但在他的批评中常常显示着颇为精警的文学史的透视。他对现代中国小说的传统很尊重,对大陆上的小说家们也常常满怀敬意,对当今小说家与传统的对话关系的揭示也很精辟。“苏童这样的抒情集锦风格,堪称重对沈从文(《湘行散记》)、萧红(《呼兰河传》)、师陀(《果园城记》)这一脉小说传统,赋予一种世纪末的诠释”,这既是肯定中国现代小说史传统,也是对苏童的现代变奏的赞誉。他善于从类似王文兴的《家变》与巴金《家》的延续对话中看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曲折进程。王氏理解的“文学史”不是以历史来取代文学,而是获得种种看文学的路径。他有许多的文学史的思考,但却不愿重复那种简单的历史规律的叙述。当然,在较为单一的当代作品批评中还很难集中表达深入的文学史思考,这样的工作在《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中表现得更有成绩,近期读他在北大《现代中国》上发表的《魂兮归来——历史迷魅与小说记忆》,发现他在文学史中穿行得更自在了。
小说中的知识地理有了时间深度方能更显立体的纵深,历史与小说想象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大陆批评家应有更多的自觉。我没有特别评述王氏经由小说评点对现实生活的思辨,诸如政治解严、身体解放、文化解构与小说表现关系的观念内涵,也值得我们注意。
源于巴赫金哲学的“对话”构成了王氏小说批评的美学原则,也是其小说观念的重要内涵。现在看来,“无边的对话主义”要比我们曾经熟悉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持久。王氏批评对话的广域特征与知识地理的穿越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表述。他在空间领域里的对话努力,是我们建立“华文语境”的最为有力的根据;他在批评中表示的与文学史上的诸种创作理念、潮流的对话不偏不倚,颇有“温柔敦厚”的折衷风范。
自晚清到20世纪末,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与发展历经各个主流阶段,混杂于不同的思潮,也被人为地隔上了种种藩篱。而当今的小说观念,后现代的、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乃至魔幻现实主义等等,仍是一片众声喧哗。王氏不孤立地评价任何一种潮流,而注重其与创作现实对话的活力,即使对当今批评理论中最被忽视的浪漫主义也不轻纵。对90年代台湾作家的创作,不论现实主义的还是“后设”的小说,他一视同仁,决不赶时髦、追浪头。郑清文的传统写实与张大春的“古灵精怪”同样地得到批评的好感;他看“后设”风格技术在于怎样写,“写得好固然给与读者意外的回味,反之也易成为搪塞情节,逃避逻辑的借口”。
在王氏的批评对象中,绝大多数都是有话要说者,或者说他们都“有话已说”,这些对象本身即构成了一派“众声”。就台湾岛内而言,40年来的声音经久不息,有陈映真的信念,有郑清文的写实主义,有王文兴已经成了传统的一部分的现代性,更有众多的新锐们作种种的“发声试验”。这许多声音在王氏的批评构架中再也不孤立存在,王氏在评论王文兴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后现代“表演”的应答。台湾文坛上有诸多怪力乱神的声音,王氏能见怪不怪,全凭有伦理向度的追求作为立场,而非犬儒的态度。对不能发声的批评对象(如古华的《色审》),因为它无法形成有价值的对话,王氏也老实不客气地点明其“止于有趣”而已。他的大陆小说的批评也和大陆批评家们构成对话,由于尺度的种种差异,其评语和大陆批评家也常常失之交臂,例如对大陆上的莫言的批评,他止不住发出“千言万语,何若莫言”的婉讽。他也总是预留另外的批评发声的立场,行文中屡屡可见:女性主义有话要说、酷儿理论家也许有话要说等类的字眼。
王氏看重在对话的批评构架中的意义的衍生。象陈染这样的私语写作,以及她们所显现的带有鲜明特色(不同于华文语境中的任一地点)的世纪末风格,是作者主体对前此的文学潮流与气候氛围的反拨造成的,所以其与大陆文学历史的对话,就必然形成一种特殊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世纪末风格”。此一世纪末风格与台湾、香港和其他华文语境中的世纪末风格之间的互文性对话,又是一重对话的境地。“世纪末”因此充满了时间概念以外的内涵,其间有颓废、暧昧、绚丽、五花八门、精灵古怪,充满着叙事想象与表演的繁富景象。王氏小说批评中揭示的意义衍生,构成其批评观念与行文的一大特色。
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的直接对话当然是评点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评点”二字且可作分别解:“评”语注重对意义的揭示判断,“点”语则更体现王氏对小说家阶段创作下一步的发展可能性的预设。王氏既不在评语中一味谀赞,也不故作酷评。他并不因作者的情面而屈己奉人,面对《尔雅》作者对“中品”的抗议,王氏敢于坚持自己的判断,并将其付诸公论。对在大陆享有盛名的格非,王氏直言,从《边缘》的自我拆解看其先锋变成了新套路,变成了注册商标,因而丧失了先锋和边缘的意义,成了创作力趋疲的预警。王氏在对许多对象评说之后,常有这类点拨的文字:“如能……必能(将更)”,或“正是……方向”,也有“不妨作为他(她)未来创作的起点”。这类文字亦可视作对写作者知识地理探勘中知识资源的通幽曲径的示明或是指点迷津。王氏的对话特征在这些文章辑集之后还有特别的显示,他在许多文章的后面都添作有《后记》,这与文章写作当时的预期又构成了一重对话关系,有的恰如预见,有的则是料想所不及——这不及处往往失望与惊喜并存。“点拨”是要冒险的,“评语”原可任意发挥。我们在大陆批评中见到的往往是后者,批评家总是乐意显示自己的后见之明,因而批评的价值也打了折扣。
把批评的身份及艺术策略也归入小说观念,是因为小说文本在其自身提供的对话语境中预留了专业阅读完成的意义空间,因小说本身的未完成性,批评与创作实践便共同完成着小说的艺术生产,批评与创作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注:法国批评家塔迪埃在《20世纪的文学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中有言:“20世纪里,文学批评第一次试图与自己的分析对象文学作品平分秋色”,王德威的批评亦可作如是观。)。王氏的批评策略之一在于身份立场的本土化,而艺术手段则是多样的,只能择其一二论述。
王德威以独特的身份从事着中国当代小说的批评。他在美国大学任教,然而他的身份却是本土的,是他将中国当代小说作为中国学中的重要内容放在美国乃至世界讲坛上。他不以现成的西方理论作为中国小说的发展轨范,总是在寻求中国小说自身可以充分发展的依据。他敢于承认:“言情是中国近代小说的主流。”这一点,在大陆一般文学史家看来是保守,但其中起码可见他不愿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路径比附西方的种种思潮。他愿意在张大春的小说中勾勒“新台湾人”的素描;他由诸多作品完成现代中国的国族想象,既承认“从大中国的观点来看”,《来自热带的行旅者》马华作家“心向祖国的深情”,也肯定其地方经验的独特性;在“九六年保钓风云再起时”怀念“当年的战将安在?”他热情地关注当代大陆小说家,是海外学者中最特出的一位。其知识分子的高度的身份自觉让他避开政治的藩篱而关注全球范围,可他的中华文化的根却又让他对“中文”小说的地方性特别钟情。
研究他王氏评点文章的修辞手段,首先值得注目的是他的文章题目。由意象到意图是他的文题的修辞特征:意象的来源在于批评对象,意图却在于和批评对象的应答关系;意象的择取是对批评对象的尊重,对创作主体的意图的揭示则有审慎的思辨寓于其间。文题所挑选的意象具有特别的征指作用,它征指家国关系、食色之性……,总而言之,直指作者的命意、挑明言外之意,也直抒出于批评者应答批评对象并可能使之惊讶的意外之言。当然,这样的文章题目最合适报章文艺栏目,不是典型的论文题目的规矩,这也是其有别于王氏其它论文题目的原因。
对王氏题目细加分析是有必要的,因为王氏的批评对象本身也是当今知识地理范围中的个别区域。如何去标志它们在版图上的位置,非细加勘验不可。方法之一就是标题的限定与揭示。解释或限定类的标题很易看出评家的用意,一些隐喻性的标题则颇费读者的思索,另外也有标题中暗于春秋褒贬的。解释性标题如:《什么花?恶之花?——评张启疆<如花初绽的容颜>》用设问的方式,抓住“花”的意象,与对象形成直接的对话关系;限定式标题如:《回忆的暗巷,历史的迷夜——评杨照<暗巷迷夜>》由两个定语的修饰,直接达到了内容解释的目的。隐喻的标题有曲径通幽之妙:《“听香”的艺术——评郑文清<合欢>》,“听香”借助于通感,“香”既关涉到“合欢”,也有“一瓣心香”的借用,因为郑氏的心理小说的抒发心曲的特征,这一通感手段的采用就有天然之趣——倾听幽然的心曲。也有同理的逆命题,如:《女性、生产与生殖——评凌明玉<复印>》,把隐喻说白了。《童年往事又一章——评蔡逸君<童颜>》一个“又”字,将题材的老生常谈点明,上文说到的《止于有趣》也是同样暗藏褒贬。总的说来,王氏的评点文章的标题,几乎没有不具备应答功效的。看完《众声喧哗以后》全书,回头来看目录,会产生“当代小说对话录”的印象。
其次,他的报刊评点式批评的行文态度与模式特点也值得注意。以态度论,他的批评显示着大陆批评少见的自由姿态。作为一个学院内的研究人员,他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最不喜欢教科书演绎式的创作,因此许多受制于教科书理论的后现代作品并不能入他的法眼。当然他也不喜欢教科书演绎式的批评。他快乐地接受阅读中的“将错就错,意义的分歧衍生”,并不执意回避“以志逆意”、“以讹传讹”的误读。我以为若没有这一种自由活泼、挥洒创造的批评,评论要与创作实践平分秋色会成为空话。
就模式而言,王氏的评点文章的开头不拘一格,是地道的文艺批评。若非是对文集的直接描述,便是由各种比兴开端,一篇是一篇的模样。文章的主体部分却是中规中矩,先是对批评对象作一个总体判断。凭只言片语的判断,将一个作家的努力方向与贡献明白了当地道出,这是眼力与笔力的结合的典范。然后是对批评的作品集的总体描述性批评,此后便是对特别篇目的剖析。走到这一步,王氏常常显示出对篇目的别具慧眼的选择,往往将众口一词的赞誉置于不顾,不容怀疑地说出他的选择与见地的精辟。批评做到这里本来就可以打住,王氏总忍不住要给小说家进忠言。这是很冒险的事情,因为这样的进言起码要求两点:一是合乎小说家的才情和现在发展的路数,再是点拨的方向一定是一种丰富小说艺术的可能性,二者缺一,所进之言都不免平庸,幸而王氏没有掉进平庸的陷阱。
对王德威的路向,我也不能尽信无疑。知识地理探勘也还会遇上一时无法穿越的藩篱,“后众声喧哗”的出入众声无碍的预期不等于“后政治藩篱”的构想。知识地理的穿越也会被政治藩篱阻碍,想来他也约略感觉得到,所以常在一些措词上体现出越过藩篱时要躲避划破衣裳和肌肤的小心翼翼。譬如,在《众声喧哗以后》中对“世纪末”的关键词有浓厚的理论探勘兴趣,可是轮到在北大《现代中国》上发表《魂兮归来——历史迷魅与小说记忆》时,就换上了“20世纪末”的字眼。因为大陆意识形态对其中的“颓废”意味还是有所忌讳的。
穿越知识地理的时间与空间,走中规中矩的老路固然便当,可总是让人意犹未尽,旁逸斜出地穿山越岭则可能更有创造性,所以,我在看多了“张腔”、“张派”等字眼以后,便有了点不耐。王氏本来善于不断地给富有创造的作品以鼓励,也许张爱玲在华文文学中的祖师奶奶的地位太重要了,所以王氏也躲不开她,以至于过度地推崇。
尽管如此,王德威的伦理取向与知识地理的探勘仍然对我们的批评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我们的批评何时能够真正地摆脱自己设置的藩篱,呈现一个开阔的视界?他的路向很大程度上是可取的。我们需要用包藏英锐的雍容大度与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文学实践进行对话,我们也应该对华文文学研究现状不满,应突破以种种局域文学现象为学术门径的陋习,不应该再以大陆小说,港台文学的地理藩篱把研究领域隔离开来了。最值得我们努力的就是构成一个宏阔深邃的“华文语境”。
标签:小说论文; 王德威论文; 当代小说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地理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读书论文; 王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