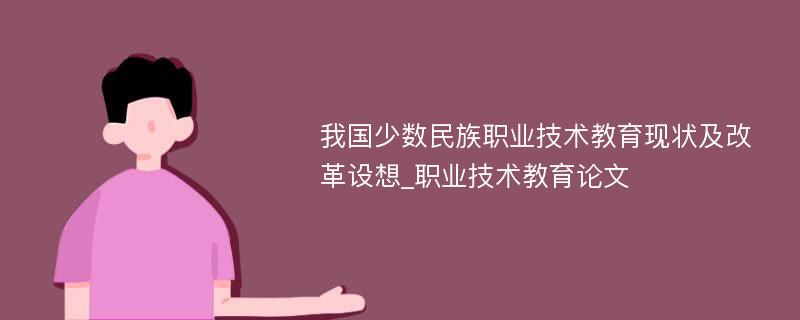
中国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现状及其改革设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职业技术教育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对于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实施的教育称为少数民族教育(亦称民族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这一作为加工、提高、更新劳动力重要手段的教育类型,是少数民族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中极其薄弱的一环。要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必须首先了解我国少数民族存在的如下一些特殊情况。
其一,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广阔而边远。人口不到8%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非常广阔,其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3.8%,且大多分布在边疆地区和边境地带。主要聚居地为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宁夏五个自治区以及一些省的部分地区。其环境大多闭塞,交通不便,地理条件恶劣。而且少数民族大都是同汉族杂居或交错聚居,从全国来说是一种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
其二,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存在多语、多文性。55个少数民族中,除了回族和满族使用汉语外,其余53个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新中国成立前,有21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回、满、畬三个民族使用汉文,其余没有文字。建国后,党和国家为一些民族创造了文字。加之多民族性和文化、历史各不相同,因而形成了55个民族使用80多种语言和40种文字的局面。
其三,大多数少数民族跨越不同的历史阶段进入社会主义,从而经济和教育比较落后,且发展不平衡。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除汉族和一部分少数民族中资本主义经济有某种程度的发展外,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力还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因而教育形态各异,有的甚至处于原始社会残余形态。例如,云南省西北部的独龙族,还存在家族公社。怒江怒族的社会分工还不明显,手工业和商业还未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其生产力水平很低,仍停留在“刀耕火种”阶段,其教育还融合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之中。凉山的彝族,直至建国前还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奴隶制度,其教育是奴隶主的特权。还有封建形态的寺院教育。例如,藏族、蒙古族中的喇嘛寺庙,维吾尔族、回族等民族的清真寺,过去不仅是学习、研究宗教的机构和进行各种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学习、研究和传授一定社会文化知识的教育机关。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我国少数民族中的回、壮、满、苗、朝鲜、布依、土家、侗等十几个民族和蒙古、彝、黎、藏等族居住的部分地区,约3000万人口,在发展阶段上同汉族地区大体相同,是封建地主经济,有的还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因此,近代教育在这些少数民族中已有所发展。
上述诸种特殊原因,必然形成今日之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以及在发展上相对落后于全国教育的局面。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不仅同样如此,而且还是少数民族教育中极其薄弱的环节。本文拟就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现状及改革设想等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 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概况
旧中国,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十分落后,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还是空白。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办国立职业技术学校大约始于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到1936年底,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仅开设8所国立职业学校[1]。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全地区仅有3所中专学校,在校生455人,教职工51人;新疆在1944年办有国立职业学校7所,至1949年除师范学校外,中专仅剩有伊宁的一所卫生学校,有教师8人,学生80人;1949年解放前夕,宁夏仅有高级助产士职业学校、国立宁夏实用职业学校、宁夏农业职业学校等3所,在校生91人[2]。西藏的中专教育至和平解放之前一直是一片空白。广西、云南等省区在解放前夕职业技术教育虽有所发展,其规模仍很小。至1949年底,广西仅有中师13所,中技校9所;云南只有中等技校9所,中师7所,共有在校生1819人[3]。总之,解放前少数民族地区仅有极少数职业技术学校,且多为规模小、设施简陋、教学质量不高的学校。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的职业技术教育在历史基础极其薄弱的条件下,开始有了较大发展。40多年来,虽几经波折,历尽艰辛,却终于克服重重障碍,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发展大致经历如下几个时期。
解放初期至1960年,是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的时期。例如,云南省至1960年中等技术学校增加到64所,在校生达20804人。广西壮族自治区1960年中师发展到55所,在校生比1950年增长6.9倍,中等技术学校发展到79所。宁夏回族自治区1960年中师发展到10所,中等技术学校发展到22所。新疆1960年全区中等技术学校增加到66所,中师发展到14所,在校生共有28523人,比1949年增长13.4倍[4]。由此可见,50年代末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已达一定规模。
1961年至1963年,是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调整时期。例如,至1962年,广西的中师调整为16所,中等技术学校调整为27所。宁夏的职业中学从56所压缩为6所,在校生从1856人减少到557人。新疆的中等技术学校减为24所,中师减为8所,在校生仅剩9345人。1963年云南中等技术学校调整为17所,在校生剩6290人[5]。这一时期的调整,使少数民族的职业技术学校和在校生都大幅度地减少了。
1964年至1965年,是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恢复时期。由于当时贯彻实行中央关于试行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各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创办半工(农)半读中等技术学校,职业技术教育重新得到很大发展。至1965年,新疆农、牧业初高级中学恢复为388所,在校生17430人;中等技术学校恢复到43所,中师恢复到14所。宁夏创办了半工半读中等学校45所,在校生48611人;农业职业中学106所,在校生5526人。云南有半工半读大学1所,在校生716人;中等技术学校21所,在校生9600人;中师17所,在校生6520人;半工半读学校45所,在校生10300人;农业中学1140所,在校生52440人。广西中等技术学校恢复到65所,农业中学发展到1659所,在校生达121928人。内蒙古中等技术学校恢复到21所,在校生9316人;农业职业中学从1962年的193所发展到1030所,在校生达53312人[6]。1964年至1965年的恢复,使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重新获得了生机。
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是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受到严重摧残的时期。此时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纷纷下马,校舍被占,教师流散,整个职业技术教育处于凋零状态。
1978年至今,是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走上正轨并取得大发展的时期。根据国家民委发表的《民族工作四十年》,1988年全国中等技术学校少数民族学生在校人数达88286人,比1951年的660人增加了133.7倍,中师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校生人数达61780人,比1951年的4531人增加了13.6倍。自国务院1991年颁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以来,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更有了长足的进展。至1993年,全国中等技术学校少数民族学生人数达14.3万;中师少数民族学生人数达7.7万;职业中学少数民族学生人数达18.6万[7]。
二 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但是,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相比,尚有很大差距,甚至存在许多问题,面临重重困境。
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薄弱,发展滞后,经费短缺,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
1.基础薄弱
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基础薄弱,与其历史基础薄弱有关。民族教育中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历史较短,有的甚至是从空白起家。因此,其师资和基础设施的历史积累很少,40多年来,较为系统的发展又几经波折。由于民族教育本身的整体就不发达(相对落后于全国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又是其中极其薄弱的环节;加之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仅需要具备普通教育的基础条件,还需要一些普通教育所没有的特殊实施环境和设施,其投资成本比普通教育高。因为按需要,职业技术教育的师生比例比普通教育低,其教育设施的投资、消耗和维修却比普通教育高得多,使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基础与普通教育发展的基础形成较大反差。而且,职业技术教育昂贵的投资成本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不发达状态也形成了巨大反差。由此造成职业技术教育经费不足、教学设施陈旧和师资严重短缺、质量普遍偏低等连锁反应。因此,职业技术教育的基础要相对薄弱得多。
2.发展滞后
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滞后与其基础薄弱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经济相对落后有关。其表现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民族教育系统来看,职业技术教育落后于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长期以来,我们比较重视民族高等教育,对民族基础教育重视不够,尤其忽视了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导致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成为民族教育中很薄弱的环节。例如,1993年全国普通中学少数民族在校生共有354.28万人[8],而中技、中师和农业职业中学的少数民族在校生总共仅40.6万人[9],约占前者的11.5%,大大小于全国中等教育结构中职业技术教育在校生所占的比例。由此可见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明显落后于民族普通中等教育。
其二,从职业技术教育系统的产生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起步较晚;而与全国职业技术教育相比,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起步更晚,并且相对落后于汉族的职业技术教育。例如,1993年全国中等技术学校的在校生209.8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仅占总数的6.8%;全国职业中学的在校生362.59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仅占总数的5.1%[10],比例显然偏低。
其三,从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来看,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供给总量上看,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建设的需要。由于就业准备和职业训练不足,使得少数民族就业人口职业素质普遍偏低,因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普遍低下,阻碍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3.经费短缺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口负担过重,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一直偏低,因而造成的教育经费短缺一直是困扰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尽管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资,总的说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对于边远少数民族的教育投入高于一般民族地区。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社会条件特殊,一般说来,发展同等程度的教育所需资金比内地要高得多,如寄宿制学校和双语教学,所需的校舍、设备、教师等都比较多,从而费用也较大。而在我国教育总投资短缺的状态下,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必然受到国家投资总规模的限制,因而也就很难争取到较多的投资。经费的短缺成为影响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
4.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
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师资严重短缺,一是表现在统计表上的师资数量不足,难以适应扩大教育规模的要求;二是表现在现任教师中未达规定学历和岗位不合格的比例较大,师资质量普遍偏低;三是表现在现有师资老化,专业结构不甚合理等方面。师资数量、质量的问题严重影响到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办学规模的扩大。
此外,还存在着对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职业技术教育的布点和专业设置缺乏统筹规划、结构单一、协调不够等问题。
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诸多问题,并不可怕,重要的问题在于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三 发展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意义
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意义可见于1991年10月17日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仅是提高劳动者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建设,而且对于进一步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不仅同样具有上述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它的实用性和鲜明的针对性,其经济功能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发挥如下重要作用。
其一,职业技术教育可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厂、企业培训出掌握科学知识和较高生产技能的合格劳动者。民族地区工厂、企业生产效益较差,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劳动者素质差、生产技能低,这是由劳动者缺乏必要的职业、劳动技能的培训,就业准备不足而造成的。因此,要提高民族地区工厂企业的生产效益,就必须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少数民族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使其成为掌握科学知识和较高生产技能的合格劳动者,从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其二,职业技术教育可以促使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业生产经营的科学化,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农村、牧区,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推广适用技术和综合开发技能,一方面可使传统农业、畜牧业得到逐步改革,使农、牧业生产经营逐步科学化,提高其产量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还可以促使一批有文化有技术的劳动者从农、牧业中分离出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兴办乡镇企业,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其三,职业技术教育可以广泛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就业人口的就业素质和职业适应能力,为全国振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而培养各种所需人才。社会成员普遍的低文化和缺乏科学知识与生产技能,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严重障碍,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的最深刻根源。职业技术教育一方面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社会成员进行广泛的就业培训,提高其就业素质和职业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可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和课程,培养大批社区发展所需要的实用性人才。这样,不仅能广开就业门路,使就业多样化,而且可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新产业的发展和全面振兴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其四,职业技术教育是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有效手段。有些民族地区脱贫无方,致富无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技术人员和必要的生产技能,对本地区的经济资源开发不足,自然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并结合本地区资源开发的需要,为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者提供实用的科技知识和技能,使其能利用学得的一技之长,回家科学种田、养殖、放牧、多种经营,更合理、充分地利用本地资源,加速地区经济开发,尽快地脱贫致富。
其五,职业技术教育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民间工艺技术发扬光大,满足具有地区特色的经济发展项目对人才的需求。我国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发明了许多精巧的工艺技术,生产了许多富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例如,新疆的小花帽,西藏的氆氇,苗族的蜡染,壮、侗族的锦绣以及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等地的各色地毯等等,历来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通过开设相关的职教培训课程,聘请专业技师和能工巧匠传授技艺,使民间工艺技术得以系统总结和发扬光大,并培养出本地区有特色的民间工艺发展项目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加快地区经济开发。
总之,职业技术教育对于振兴发展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全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由于8700多万的少数民族人口中70%住在占全国面积约2/3的西部地区,那里富集着90%的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矿藏、能源、建材等资源,引起2000年全国建设战略重点的西移[11]。可以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决战区就可能在西部民族地区。该地区是我国自然资源最富集的地方,也是我国经济最不发达地区。如果不积极发展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来提高广大民族地区劳动者的就业素质,就不可能更快、更好地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富集资源,从而促进其经济发展,那么,我国整个现代化的进程势必受到严重牵制。因此,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也是关系到我国整个实现现代化的大事。国家和各级政府应当采取必要的倾斜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四 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设想
发展和改革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必须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一是要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生产力水平的实际,提出适度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确定具体的培养目标和专业;二是要考虑职业技术教育如何适应少数民族各地区的经济结构;三是要考虑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资源的开发,不能囿于原来比较落后的生产力状况,要通过开设相应专业来挖掘、开发当地的经济资源。
总之,发展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要特别注意其办学方向,必须面向民族地区,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其培养目标、专业和课程设置、层次结构、办学形式等,都要从少数民族的实际出发,与民族地区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
具体的改革设想包括如下几条措施。
1.在普通教育职业化上下功夫
普通教育的职业化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把一部分民族普通中学改为职业技术学校,特别应把一部分办学效益差或生源无保证的普通初中和高中转向,分别改为初级职业技术学校和中级职业技术学校,分别招收高小、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就读,以改变少数民族中等教育结构中普通教育大于职业技术教育的不合理现象,增大职业技术教育学校所占的比例。另一方面要在民族普通教育系统内部挖潜力。一是在民族小学开设手工课和劳动课,使小学生学到一定的生产劳动技能和了解工、农、牧业生产的一般知识;二是在普通民族中学开设职业技术选修课,学习有关的职业技术知识和技能;三是在普通民族中学设立职业技术班,开设有关职业课程,培养中学生能掌握适应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知识。特别在学生毕业之前应普遍进行适当的职业行为训练,指导中学生作好职业选择和就业准备。这样便使职业技术教育有效地渗透到各个层次的普通教育过程之中,从而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2.建立三级分流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首先,应进一步办好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职业技术学校,使其巩固、提高,发挥骨干作用。各地尤其要注意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先办好一两所具有示范性的职业技术学校,取得好的经验,加以推广。在此基础上,要积极创造条件,建立起三级分流的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各少数民族地区对人才需求是多层次、多规格的,应本着先培训、后就业的原则,创建一批分别能适合小学毕业后、初中毕业后和高中毕业后就读的职业技术学校。这样,既有实施初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校,使受教育者获得简单的劳动技能;又有实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校,使受教育者掌握较为复杂的劳动技能;还有实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校,使受教育者获得系统的职业知识和专业管理能力。而这种三级分流,务必要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人才相协调,与本地区就业结构相协调,并根据不同需求有所侧重。在广大农、牧地区,应以发展农、牧业初级职业技术学校为主,学习内容以传授实用的农牧科学技术和基本技能为主。例如在农村,要适应农民科学种田以及离开土地从事其他产业的需要;在山区,要适应山区开发及发展多种经营的需要;在牧区,要适应畜牧业、草原建设、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需要;在林区,要适应森林开发和保护森林的需要,等等。在少数民族的城市中,由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则应侧重于建立中级职业技术学校,设置对口专业,使受教育者掌握一技之长,以适应提高企业技术、管理水平的需要。
总之,在民族教育的整个中小学教育阶段,陆续有一部分青少年将离别学校走向社会,这些不同文化程度的待业队伍必须在走向社会前得到小学后、初中后和高中后三级分流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掌握程度不同的生产技能和科学知识,使其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振兴所需的各级建设人才。但必须注意的是: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比例要适当,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以各占一半、甚至职教大于普教为宜。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离这个比例差距较大,应努力增大职教比例,并提高其质量。
随着教育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最终完全有可能形成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衔接与沟通。
3.办学模式多样化
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不仅应当具有三级分流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而且还应当具有多种类型的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要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结合其本地实际需要,不拘一格建立各种各样的职业技术学校和培训机构。既要设立三至四年制的正规中等专业学校,一至二年制的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也要进行几个月甚至几天的短期单项培训。职业技术学校教育不仅要与职业培训双管齐下,还要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实行正规教育与部分时间制并举,以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半牧半读、夜校、函授、电视教育、进修甚至帐篷学校、马背学校等各种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教学和培训,以满足不同层次各类人员提高职业素质的需求。特别应注意,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要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地区需要什么就开设什么,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使各种各样的职业技术学校和培训班成为当地发展经济、开展多种经营、从事生产、进行技术革新的重要基地。
4.多种渠道办学
职业技术教育的多种渠道办学,即要根据各民族地区的实际需要和具体条件,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广开办学门路。正如国务院1991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中所指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充分调动企事业单位和业务部门的积极性,并鼓励集体、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办学。要提倡各单位和部门自办、联办或与教育部门合办各种职业技术学校。这些学校除了为本单位和部门培训人才外,还可以接受委托为其他单位培训人才并招收自费生。”我国的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应当广开办学门路,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共同兴办,逐步建立起与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国家、集体、个人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等多种渠道兴办的职业技术教育新体系。
特别要提倡民族地区的工矿企业办学,以发挥工矿企业的财力、智力优势。并要加强学校与企业的联系,以联办、定向培养的方式培养人才。还要鼓励各社会团体的智力支边,派技术人员传授实用生产技术,扶持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而且,要重视个人或群众的集资办学和积极引进外资办学。
总之,在当前国家教育投资短缺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地区应当多渠道筹措资金,兴办职业技术教育,这是促进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
5.抓好与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配套的师资培养与培训
要振兴少数民族的职业技术教育,必须抓好与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配套的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成败,这必须在稳定师资队伍的前提下,做到以下四点。
一是逐步建立健全完善的师资培训制度,加强对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在职培训。任职教师中有许多未达规定学历和岗位不合格者,急需提高其业务能力。因此,在各种教师进修学校和教育学院以及函授和电视师范教育中,应当增加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培训项目,以多种方法对其进行在职培训。脱产和不脱产相结合,以不脱产为主,以便不断提高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质量。
二是逐步建立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教师的考核制度。目的在于促使在职教师积极参与在职培训,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以确保师资质量。但考核制度应与培训制度相配合,使民族地区大多数不合格教师逐步达到合格。不要急于求成、要求过高,脱离少数民族地区教师的实际。
三是要建立一些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师范院校,培训合格教师。由于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师资数量严重不足,急需补充,因此,可考虑建立一些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师范院校,面向少数民族学生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分配,确保少数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能够分配到合格的毕业生,增加新鲜血液。
四是要多渠道培养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师资。除了师范院校应当培养职业技术教育师资之外,还应广开师资渠道。比如,全国12所民族学院、民族地区的综合大学、民族地区的理工院校,均可开办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班,培养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师资。并可借鉴内地办民族班、办民族学校的经验,试行一批内地办的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班和学校,培养更多的合格师资。另外,要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各行业的专业技师和能工巧匠,增强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师资力量。
上述措施,不仅能提高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师资质量,还可以不断增加合格教师的数量,这样便能确保其教学质量,使职业技术教育能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仅是关系到我国整个教育改革的大事,而且也是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振兴和我国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大事。
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而大力发展,这方面各国都有不少有益经验。我国自80年代以来调整中等教育的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职业技术教育的国际经验和国内经验,都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1]谢启晃《中国民族教育史钢》,1989年版,第52页。
[2]孙若穷等《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1990年版,第450页。
[3]孙若穷等《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1990年版,第450页。
[4]孙若穷等《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1990年版,第451页。
[5]孙若穷等《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1990年版,第451页。
[6]孙若穷等《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1990年版,第452页。
[7]《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1993年》,第14页。
[8]《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第47页。
[9]《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1993年》,第2页。
[10]《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1993年》,第14页。
[11]谢宁《面向21世纪的基础教育和民族教育》,1992年版,第1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