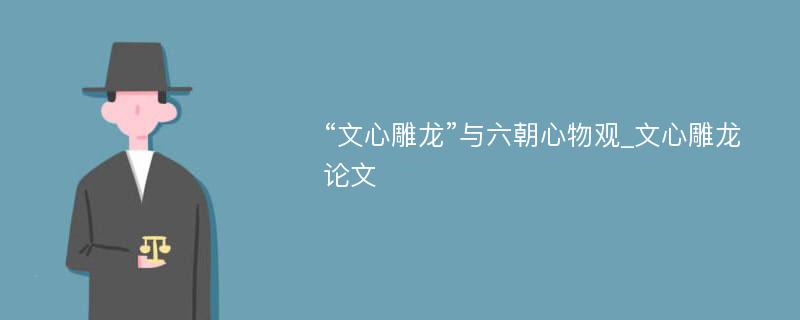
《文心雕龙》与六朝审美心物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心物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就六朝审美心物观的逻辑展开过程来看,从嵇康《声无哀乐论》主张“自然之和”,以反对儒家诗乐理论所宣扬的心性学说与道德迷妄,到陆机、宗炳等人的心物交融思想,虽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上存在着缺点和片面性,但基本已涉及到审美心物观的各种理论问题,而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天、地、人、文相统一为其宏观构架的审美心物观,自然就达到了一个逻辑“终结”阶段。
关键词 阴阳五行 自然之和 本无宗 言意之辩 心物交融
笔者拟先从《乐记》谈起,然后即以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宗炳《画山水序》及陆机《文赋》为主,具体联系《文心雕龙》的心物观点,分析一下刘勰是如何在六朝审美心物观的逻辑发展基础上,进行理论整合的。
一、《乐记》——阴阳五行——《文心雕龙》
《礼记·乐记》杂采《左传》、《国语》、《荀子》以及《吕氏春秋》的乐论,糅合了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思想,形成代表儒家乐论的思想体系,联系董仲舒《春秋繁露》、班固编撰的《白虎通》中这些后来的有关内容看,《乐记》的儒家乐论确已相当完备。
就审美心物观看,《乐记》从儒家的心性学说出发,提出了“物感”说,又明确包含有“心物互感”的思想。但其“物感”说,是建立在“心性本体”说的基础上的。《乐记》云: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①]
又云:“夫民有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这种心性学说乃是从两个假定出发,建构其“物感”理论的。首先,它假定人生本来就具有一种“静”的天性,也就是“天理”,而同时又具有一种“感物而动”的“欲”的功用,亦即“静”是性之体,“欲”是性之用。实质上,从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角度讲,人性本身的“性”与“欲”是不可以加以割裂的,也不存在什么“静”的天理。由此回到《乐记》开篇的论断:“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可见,“物使之然也”的根据与前提,在于人本身有一种“性之欲”。其次,它假定了这种“性之欲”本身即是一种“性之情”,只是“感物”之前处在“静而不动”的状态中。
这种理论所依据的就是阴阳五行学说中“同类相动”的原理。《乐记》云:“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以类相动”说,是《乐记》“心物互感”论的建构原则。剔开《乐记》中心性学说的先验内容,《乐记》的审美心物观还是较为科学的。乐本于人心之动,人心之动又本于“物使之然”,这是讲“物对心”的感发作用与同类相动的现象;同时“致乐以治心”,人们有了“易、直、子、谅”之心,就会对“物”产生作用,从而风俗归正,家和国安,这是讲“心对物”的作用。《乐记》中的“物”字,孔颖达《礼记正义》均释为“外境”,包括社会与自然两个方面,更多的是指前者。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物”字,也是包括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的“外境”,但有时是专指自然外境的,如《物色》篇的“物”字即是如此。
《物色》篇具体讨论了自然“外境”对审美主体心灵的“感召”作用: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②]
这明显受到儒学化的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可以直接从《乐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找到源头。《乐记》的阴阳五行思想,虽然较《春秋繁露》为朴实,但其基本理论框架亦已定型。如其将“五音”比于“君、臣、民、事、物”,将仁与义视为春与秋之德,所谓“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等等。阴阳五行学说被糅合到儒学体系中来,最初可以《易传》为代表,到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得以进一步的发展,从而成为汉代儒学发展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到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齐、梁之际,阴阳五行思想早已成为儒学的血液,成为儒学体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的融会,其原因是很多的,如秦汉之际社会政治的变迁、儒士地位的升降、今文经学的兴起、纤纬学说的影响等,从思想逻辑上看,也是与儒家“比德”说及其所采用的类比思维方式直接相关的。如《乐记》中,由“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进而说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目的在于以天尊地卑的自然现象,说明封建礼教的合理性。这种以自然界阴阳五行现象类比社会人文现象,又正是后来魏晋玄学从“儒学”内部——即着眼于“自然合理论”——来破除其“神学目的论”(主要是汉今文经学)的迷妄,并运用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对“儒学”进行重新“解构”的逻辑基点。按照《乐记》的逻辑,乐是一种人心之动,而人心之动,源于感物而动,而这“物”(外境),就大自然的层面讲,乃是一种“和而有序”的宇宙,“人声”本之以成乐、本之以成诗。
刘勰非常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但也受到嵇康等魏晋玄学家的“自然论”的影响。其《明诗》就直接下了这样的断言:“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总之,《乐记》的审美“物感”说,到了魏晋时期,由于道、玄、释的思想作用,或以“自然”之无、或从“般若”之空的本体论出发,对之进行了新的阐释,最终被刘勰整合会通于《文心雕龙》之中。
二、嵇康——自然之和——刘勰
嵇康《声无哀乐论》云:“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于不善,虽遭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③]这就是说,音乐“其体自若”的本体,既为“自然之和”,所以音乐也就“无系于人情”。
从审美心物观上看,嵇康的乐论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主张“心声二分”的观点。嵇康从自然本体论出发认为:“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意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刘勰的心物交融论,也包含着“心声二分”的内涵,其《声律》篇云:“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指出了乐之声与言之声的异同性。《物色》篇又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学创作中,心对物的“气”与“貌”的把握,以及在“意象”构筑完成后,运用有“采”有“声”的语言来表现,是与音乐不同的。音乐是由一定之“数”与“度”的五音构成的,因此,刘勰认为“言之声”比“乐之声”更难于运用。尽管汉语文字有平上去入的“声调”,有宛转附物的“色采”,也还是存在一个陆机《文赋》所讲的“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玄学家所倾心讨论的“言意之辩”的问题。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明确主张“得意忘言”的观点,他说:“吾谓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言”,因为“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以证心也”。刘勰主张言是可以“达意”的,可以通过一定的“言之数”——语言规律与文术技巧——来达意称物。但刘勰也认为这种“达意”只能是相对的,所谓“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通变》),因此,他特别重视“隐秀”、“比兴”等达意的表现方法。第二,嵇康认为要把握“自然之和”的音乐本体,应当洗涤主体喜怒哀乐之情的干扰,在审美虚静中实现这一目的,故云:“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以听静而心闲也。”刘勰也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审美主体应当虚静为怀,要做到“入兴贵闲”,反对过分地“苦思”,因为“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养气》),将虚静以观物视为一条普遍的审美规律。第三,将嵇康《声无哀乐论》、《琴赋》与阮籍的《乐论》相比,阮籍论乐的旨尚与嵇康不完全相同。阮籍也认为“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同样以“自然之和”为乐之本体,但其目的是要说明“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乐论》)。这与《乐记》的“声音之道,与政相通矣”的思想,出发点不同而归趣相似。盖阮籍主张名教即自然,而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要极力说明音声是以“自然之和”为体的,本来与“哀乐”之情无关,“审音知政”的传统理论根据,是认为声音本身就有哀乐,嵇康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从这种错误的理解出发,就永难把握声音的“自然之和”。故他慨叹道:“斯义久滞,莫肯拯救。”为了说明问题,他深入地解剖为什么一般人会视音声有哀乐的问题。这就是因为常人不能像圣人那样做到应物而无累于物,没有这种“圣人之情”而又使其“心志以所俟为主”,也就易于“移情”于物、“应感而发”,而“声音以平和为体”,“和”则“感物无常”,就是说主体移什么“情”入“和声”这个审美对象,就会以为这种“和声”本来就具有什么样的情感意志。嵇康的这种解析,说明了“审美移情”的道理,后来刘勰吸收的正是这一层面的思想,这真可谓是“反其意而用之”了。其实,如果文艺创作历来都是如此“言比成诗,声比成音”的,作家、批评家就是如此“审国风之盛衰,吟咏情性,以讽其上”的,那么探讨“为文之用心”,正当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这于刘勰亦可谓是当然之理了。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嵇康《声无哀乐论》的立论主旨是一回事,他所揭示的这种移情于物、“应感而发”的审美现象又是另一回事,刘勰完全可以接受后者而置前者于“不论”的。刘勰的这种“不论”,并非就以为嵇康的立论主旨不当,其《论述》云:“……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亦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许之以“独见”、“精密”,评价甚高。但从其《乐府》等篇看,刘勰仍然坚持了《毛诗序》、《乐记》的主要诗乐观点,盖刘勰认为文学创作是以“言”为媒介的,与有“度与数”的乐不同。音乐之声,可以“弦以手定”,而“言”就复杂得多,对作家来说,如果完全“忘言得意”,就毫无创作可谈。只有在创作中,调动“达意”之言的各种“文术”,最终去表现“意”,虽然不能完全“尽意”,但必须以“言”的限在,去表现“物”的无限、“意”的无限。这样对鉴赏者讲,才能超越作品“言”的限在,去领悟“无限”,去体认“自然之道”。
综上所述,从“自然之和”与“言意”关系去看,《文心雕龙》又是与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相互贯通的。其实,具体的一曲音乐之声,也是与一部文学作品之言一样,都是一种“限在”、一种“媒介”,在六朝人的审美眼光中,均是一种“得意”的筌蹄。而《文心雕龙》的审美心物观与“言意之辩”的问题,正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对此不可不察。
三、宗炳——本无宗——刘勰
六朝画论受到这一时期品评人物重视“神鉴”的风气影响尤重,遂使“形神”问题成为当时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山水画的兴起与当时人物品藻多用山水语言的启发有关,“晋人从人物到山水画可谓为宇宙意识寻觅充足的媒介或语言之途径”[④]。而同时山水诗亦由之而起。《世说新语·言语》载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林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在这位大画家的眼中,大自然的美,充满了生命的精神,这与刘勰所谓“物色相召,人谁获安”(《物色》)的精神义旨,正是血脉相通的。东晋时期,玄学与佛学通过“格义”的方式进一步合流,此后又逐步摆脱“格义”的束缚,走向了“独立”,从以玄解佛走向了以佛补玄的道路,加以山水诗、山水画的创作日趋繁荣,于是诞生了两篇著名的山水画论,这就是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其思想基础是并不相同的。宗炳说“神本亡端,栖形感类”,主张的“形灭神不灭”的观点,王微讲“本乎形者融灵”,表现的是“形神相即”的义旨,这要联系二人遗留下来的几篇作品,作整体的研究,才可以明确看出。
从王微的《与从弟僧绰书》、《报何偃书》等内容看,王微受道家影响较深。其《叙画》强调由心即物,当以传“神”为主,而不必拘泥于目见之“形”,因为:
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也。灵亡所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⑤]
不拘于“形”而求其“灵”(神),才能将“孤岩郁秀,若吐云兮”的生命精神表现出来,使之“纵横变化,故动生焉”。同时,王微也指出了“物”对“心”的感召作用,所谓“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圭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其立论明显与刘勰《神思》、《物色》枢机相同。王微的思想基本是儒道兼融的,而与之不同的宗炳明确主张以佛统儒、以佛摄道的三教合一思想,其《明佛论》云:
彼佛经也,包五典之德,深加远大之实;含老庄之虚,而重增皆空之尽。高言实理,肃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风,非圣谁说乎。[⑥]
宗炳曾师事慧远,慧远是道安的弟子,就般若学而言,慧远和宗炳都属于本无宗一派。两晋时期,在“格义”方法的影响下,佛教大乘空宗学者,比附玄学,形成般若学六家七宗的不同学派,其中以本无宗、心无宗与即色宗为主。据《高僧传》卷五《竺法汰传》,支敏度的心无宗——主张“无心于万物,而万物未尝无”的观点——曾“大行荆土”,当时宣传“心无义”思想的是心无宗派传人道恒。后来法汰、慧远等设席与之攻难,遂使“心无之义,于是而息”[⑦]。但宗炳又与慧远不同,并不拘限于本无宗一家(本无宗本身又并非纯一的,道安与法汰不同),其《又答何衡阳书》所谓“若孙兴公所赞八贤,支道林所颂五哲,皆时所共高”云云,对支道林和包括支敏度在内的“八贤”均加称赞,于此亦可见其“般若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兼融性。下文又云:
夫佛经所称即色为空,无复异者,非谓无有,有而空耳。有也,则贤愚异称;空也,则万异俱空。夫色不自色,虽色而空;缘合而有,本自无常,皆如梦幻之所作。
所谓“色不自色,虽色而空”,正是即色宗创始人支道林的核心观点。吕澄曾说,道安的“本无”思想,强调“照本息末”之旨,实质上是一种“性空宗”[⑧]。慧远作为道安之徒,其“本无”思想当与竺法汰有别。宗炳可能从慧远那里受到“性空”思想的濡染,加以受儒、道两家有关观念的影响,形成他自己的“本无”学说。其《答何衡阳书》云:
佛经所谓本无者,非谓众缘和合皆空也。垂荫轮奂处,物自可有耳,故谓之有谛;性本无矣,故谓之无谛。……贤者心与理一,故颜子‘庶乎屡空’,有若无,实若虚也。
“庶乎屡空”,本指颜回贫匮空乏之义,被玄学家、佛教徒用来指“虚心知道”或“法识性空”之境,由此可见其时“格义”之风未息。对此,钱钟书论之尤详,并云:“宗炳攀援释说,与何晏附会道家言,若符契然。”[⑨]可见,要了解宗炳《画山水序》中一系列美学范畴,如“道”、“灵”、“形”、“神”等,必须从其“本无”学说这一核心思想去把握。
宗炳的心物观的独特性,就是一切从“法识之性空”理论出发。其《明佛论》云:
夫圣神玄照,而无思营之识者,由心与物绝,唯神而已。故虚明之本,终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与物交,不一于神,虽以颜子之微微,而必乾乾钻仰,好仁乐山,庶乎屡空。……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识息,则神明全矣。
“心用止而情识息”的思想,正是宗炳与王微、刘勰的心物观的不同之处。联系《画山水序》看,宗炳把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比德说,与道家的“乘物以游心”的观点,从般若空宗的理论基础上进行融合,贯彻了“自然”为本的思想。不过,其心物交融理论,是从“法识之性空”出发,所谓“法识之性空,梦幻影响,泡沫水月,岂不然哉”云云,最后又归结到“悟空息心”的“神明之全”的终极,也就是说由“心与物交”而归本于“心与物绝”,这就是《画山水序》所谓“澄怀味象”等一系列观点的理论实质。《画山水序》云:
夫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焉。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丛,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暎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
宗炳是把画笔作为一种通向“山水以形媚道”之“道”的媒介,从这个角度讲,是与王微《叙画》“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的精神相通的,主张的是“得意忘象”,追求的是“象外之意”。宗炳也揭示了审美过程中心物交融的现象,并强调要以“应会感神”为目的。所谓“目亦同应,心亦俱会”,正当为刘勰“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物色》)的观点之所本,但这仅是就审美心理活动形式而言的,实质上,宗、刘二人主旨不完全相同。
从上面我们所重点探讨六朝的嵇康乐论和宗炳画论看,或以“自然之和”为音乐的本体,或以“般若之空”为山水画的本体(以“山水以形媚道”的理论面目出现),并都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审美心物关系的并构与交融现象。但画与乐的媒体与“言”不同,具体到文学创作上来讲,深入地研究并建构文学创作中的独特的审美心物观,是先后由陆机和刘勰等文学理论家完成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洗涤了玄佛理论的玄虚精神,又吸收了他们的有益思想,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四、《文赋》——文、物、意——《文心雕龙》
陆机出生于经学传家的江东士族,《晋书》本传称其“伏膺儒术”,其《文赋》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尊奉儒家诗学的风雅体制,要求文学应当起到“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的教化功用。但是我们也可明显看到《文赋》也兼容并取了道家、玄学的有关思想观点,生动描述了创作构思的全过程,深入剖析了文、物、意三者的复杂关系。
在审美心物关系上,将“言意之辩”的问题,直接引入文学创作过程进行研究,陆机当是先于刘勰的第一人,在此之前,许多理论家虽已涉及这一问题,但并未将“言与意”和“心与物”联系起来作周密考察。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看,任何一个语言艺术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无法回避“言”的问题。《文赋》序云: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⑩]
序文说明《文赋》所探讨的“为文之用心”,就是分析并试图解决“文、物、意”的统一问题。《易传》“言不尽意”的论点,后人所发挥的理论层面并不一致,关键在“不尽”二字的理解上,至少有这样三种看法:一是将“不尽”当作“不能表达”讲,这是“言不尽意”的绝对论者;二是将“不尽”当作“不能完全表现”讲,“尽”就是“穷尽”之意,一般“言不尽意”论者都是持这种观点的,笔者以为陆机和刘勰均是持这种相对论的;三是将“不尽”当作“不必要完全表现”讲,刘勰论“隐秀”,已触及这一层面,后代如皎然、司空图、严羽等人,都明确主张这种审美言意观。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认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意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言、象、意三者明显与陆机所说的文、物、意三者存在一种“对应”关系,或者说后者正是受到前者影响而提出的。但文学创作必须以“言”来构筑意象,意象与客观“物象”不同,因为在审美过程中,无论是由心即物还是因物动心,心中“物象”已包孕了审美主体的主观内容,移入了主体的情感。陆机认为作家要达到“文、物、意”的统一,是“能之难也”,也就是说“言”是可以称物逮意的,不过很难而已,一般只能相对地达到这个目的。《文赋》将“伫中区以玄览”与“颐情志于典坟”结合了起来,强调主体“玄览”观物的“学养”基础与“情志”的导向作用。这与刘勰《神思》篇所谓“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和“积学以储宝”等观点,正是相互应照的。陆机在描述构思中的心物交融现象云:“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始终是将言置于心物关系中来进行剖析的。从“物感”之始,将“玄览”观物与“典坟”之学并重,到构思之中,对“沈辞怫悦”、“浮藻联翩”情形的描绘,说明了“文、物、意”三者的“称合”,是一个“非知之难,能之难也”的问题,这是符合创作的实践活动的。
《文心雕龙》心物关系、心物与言的关系的研究,对前人的理论进行了有机的“整合”,远较《文赋》为周密。《神思》云: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释“神与物游”云:
此言内心与外境相接也。内心与外境,非能一往符合,当其窒塞,则耳目之近,神有不周;及其怡怿,则八极之外,理无不浃。然则以心求境,境足以役心;取境赴心,心难于照境。必令心境相得,见相交融,斯则连城所以移情,庖丁所以满志也。[(11)]
联系《物色》诸篇看,刘勰对心物关系的论述,指出了审美过程中有“以心求境”的一面,也有“取境赴心”的另一面。如《诠赋》云:“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睹物兴情”与“物以情观”正是审美心物交融中两种相反相成的心理活动形式。其《物色》“赞”最为全面地表述了刘勰的这种“心物观”,“赞”云:“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目往而心纳之、目还而心吐之、兴来而情赠之,在审美过程中是一种有机的统一。在创作构思中,确会发生黄侃讲的“境以役心”和“心难照境”的情形,故刘勰强调虚静,要求“入兴贵闲”。在“神与物游”的审美过程中,艺术的想象力得到极大的发挥,具有陆机《文赋》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空间驰骋力度,与“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时间透视功能。无论是以心击物还是取境赴心,都离不开心灵的“神思”活动。而这种“神思”活动,就其“心物交融”的“心”的层面讲,主体的精神状态和情感意志(志气)是起着主导作用的。审美主体精神萎顿、情志暧昧,也可以“瞻万物而思纷”,那只能是一种感触良多而思理不清,是构思不成完整的审美意象的;就其“心物交融”的“物”的层面讲,无论是物色感召于心在前,还是以心取境居始,最终“物”要成为心中之“物”——客体物象变成心灵意象——构思方得以完成。而“心”(枢机)孕育“意象”时不仅离不开“言”(辞令)的功用,而且最后心中“意象”表现为具体作品,也是由“言”致用的,所谓“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神思》)。刘勰认为心物交融的过程,正是以语言作为其“交融”的思维形式的。这种“思维形式”不是一种外在的工具性的东西,因为“语言”实质上也是作为“心物交融”过程的具体内容而存在的。刘勰在“言能否尽意”这个问题上,是持“相对论”的态度,故《神思》又指出:“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
总之,刘勰联系具体的艺术创作实践过程,舍弃了道、玄、释中一些“忘言”、“无名”的神秘直觉论的观点,又吸收了其“心斋”、“坐忘”的心物思想中合理的内容,因为审美心物交融的过程,与道、佛论者所阐述的悟道、证佛体验,确有相通之处。但文学创作毕竟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审美心物交融过程中,正要积极地开展“言”的活动,振奋起“神思”的精神,而不能“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艺术鉴赏可以只求个人心灵的“意会”而不求“言宣”的,达到“心行处灭”之境,但文学创作必须“意会”与“言宣”并举。
注释:
① 本文所引《乐记》语,均据孔颖达《礼记正义》,见《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② 本文所引《文心雕龙》语,均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③ 本文所引《声无哀乐论》文,均据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④ 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第3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⑤ 本文所引王微文,均据《全宋文》卷十九,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⑥ 本文所引宗炳文,除《画山水序》外,均据《全宋文》卷二十、卷二十一。《画山水序》引文,据《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第177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⑦ 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192—193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⑧ 吕澄《中国佛教源流略讲》第5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⑨ 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28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⑩ 本文所引《文赋》语,据《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1)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91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