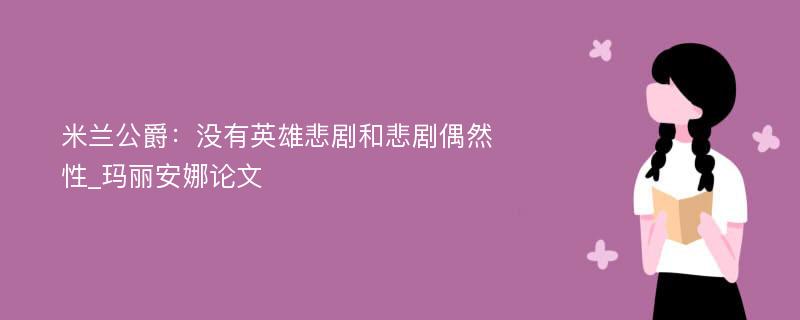
《米兰公爵》——无英雄悲剧与悲剧偶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剧论文,米兰论文,偶然性论文,公爵论文,英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麦辛哲在完成他的悲剧《荣名女》不到一年就写出了《米兰公爵》,这后一部作品在探索人生悲剧经历和运用悲剧技巧方面更具传统特色。与前一部作品不同的是,《米兰公爵》把它的人物焦距移向一组主角和情欲与奸诈的交叉画面上。它的主题围绕一个腐朽颓唐、悲怆哀怜的社会展开。但作者突出描绘了微妙举止在悲剧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同代剧作家韦伯斯特和杜赫勒不同,麦辛哲没有浓墨重彩地表现正义和尊严堕落成维持邪恶势力的祭品。他对人性瑕疵和缺憾作了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描绘。同其他詹姆士一世悲剧相比,此剧关切之情减弱,哀怜之鸣剧增。《米兰公爵》从人性堕落和道德力量虚弱出发,深刻探索了悲剧的社会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联系。(注:雷伯纳指出,詹姆士一世时代悲剧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围绕剧中道德因素展开的人物性格、剧情和诗歌的创作。参见Irving Ribner,Jacobean Tragedy:The Quest for Moral Order(New York:Barnes,1962),11页。)该剧显示,如果负心忘义成为普遍的主导的道德力量,人生将是充满险恶和恐惧、奔向苦难与绝望的旅途。作为一个文艺复兴后期的悲剧作家,麦辛哲将伊丽莎白悲剧对个人感情和能力的关注转移到詹姆士一世时代对人物的情欲放纵,孤陋偏执上,使得结局倍感凄凉。正义丧失殆尽,英雄与反英雄比肩并立。他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爱情悲剧和英国复仇悲剧传统,使用独特的舞台语言和技巧,创造出一组鲜明的悲剧形象。
一
《米兰公爵》故事情节较为离奇,以意大利阴谋悲剧为基础,全剧围绕爱情和复仇两条线索铺展开来。米兰公爵斯福沙疯狂地爱着自己的妻子玛赛丽亚。一次他为了缔结和约不得不出使西班牙,但因此次旅途凶多吉少,他密令自己忠实的宠臣弗朗西斯科,一旦获悉他遇害的消息,便立即处死玛赛丽亚。但弗朗西斯科因自己的妹妹尤金尼亚三年前被斯福沙诱奸而久藏复仇之心,而弗朗西斯科长期以来对玛赛丽亚的美貌垂涎欲滴。此时他便将斯福沙的密令出示给玛赛丽亚,企图以此为诱饵诱奸她。在遭公爵夫人拒绝后,弗朗西斯科恼羞成怒,决心向公爵夫妇伸出复仇之手。斯福沙顺利完成使命,安全返回,弗朗西斯科面对阴谋败露的危险,不得不铤而走险并同时警觉自己的安危。最终他成功地诱骗福斯沙因疑恨妻子不忠而亲手将其杀死。弗朗西斯科的复仇并未停止。剧终时,他设计使悲痛欲绝的福斯沙在亲吻了妻子被涂了毒药的嘴唇后死去。
评论家们一般认为《米兰公爵》是作者在1623年以前单独为“国王剧团”所写的作品。该剧在1623年1月20日列入“出版注册”。(注:The Stationers'Register,伊丽莎白时代伦敦官方负责戏剧出版和商业演出的注册薄。)但在该剧第三幕第三场中提到被囚禁的作家乔治·韦德:“我因诋毁伟人而获罪;苍白而低劣……”韦德因写讽刺诗“韦德警铭”而激怒詹姆士一世,于1621至1622年间被囚禁。所有这些与当时重大事件相关,似乎预示着麦辛哲一定是为1622年“黑牧师”剧院冬季演出而作。(注:The Blackfriars Theater,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伦敦著名的私人剧院,主要为伊丽莎白宫廷上演剧目。相对于它的The Globe Theater主要面向广大伦敦市民。)但是我认为,对于该剧的写作日期至今没有准确的论证,所以这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米兰公爵》的主要内容取材于约琴夫斯的作品《以色列古董》和《以色列战争》中的赫罗德—玛瑞安娜的故事。(注:Flavius Josephus(37-95?),以色列历史学家,曾参加罗马人与以色列的战争。参见Philip Massinger,The Plays and Poems of Philip Massinger,ed.P.Edwards,and C.Glbson,5 vols(Oxford:Clarendon,1976),vol.1,201-202页。)在约瑟夫斯的故事中,赫罗德两次出使,一次去会见安东尼,另一次去会见凯撒。他命令如果他不能幸存返回,便将妻子玛瑞安娜处死。麦辛哲在他的剧中模仿编制了斯福沙密令的故事情节。而弗朗西斯科这一人物则是将约瑟夫斯原著中三个仆人的特征揉合塑造而成。(注:Flavius Josephus(37-95?),以色列历史学家,曾参加罗马人与以色列的战争。参见Philip Massinger,The Plays and Poems of Philip Massinger,ed.P.Edwards,and C.Glbson,5 vols(Oxford:Clarendon,1976),vol.1,201-202页。)福斯沙吻妻子有毒的嘴唇而亡这一情节大概来源于《第二个少女的悲剧》,托马斯·狄德的《索利曼》和《波赛达》,以及杜赫拿的《复仇者的悲剧》。(注:Cyril Tourn-eur(1575-1626),英国剧作家。他的著名悲剧是于1606年至1607年所著的《复仇者的悲剧》(The Revenger's Tragedy),男主人公是温狄吉。)
一些戏剧评论家认为,以爱情和欺诈为主线的《米兰公爵》被麦辛哲加进了弗朗西斯科的复仇情节,结果使该剧结构松散。赫拉德·布拉那姆认为,作为复仇者,弗朗西斯科的人物塑造存在缺陷,他的行动“延迟了三年,然后先是错杀一人,最后虽然完成复仇,但已失去意义。”(注:参见Charold Frank Branam,"Neo-stoicism in Philip Mas-
singer's Tragedies,"Dissertation(Temple University,1972),166页。)但是我认为麦辛哲刻意表现爱情和复仇为人性的统一体。内心世界的堕落将斯福沙和弗朗西斯科紧密相连,遥相呼应。前者表现出疯狂的爱,后者为贪婪的欲。在詹姆士一世时代的复仇悲剧中,复仇者常常进行血腥的报复。而弗朗西斯科正是这样的典型形象。查尔斯·海利特则认为这种血腥暴力是“复仇者为达到目的,必须改变他的理智文明的人性,完成精神上从清醒到疯狂的过渡”。(注:参见Charles A.Hallet and Elaine S.Hallet,The Revenger's Madness:A Study of Revenger
Tragedy Motifs(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0),5页。)麦辛哲剧中的弗朗西斯科扭曲的个性,在制造骇人听闻的暴力上有所表示。但与他同时代的剧作家相比较,麦辛哲并非简单关注复仇行为,他对复仇悲剧中复杂人性的洞察是深刻细腻的。
二
麦辛哲在《米兰公爵》中对斯福沙的塑造是理解该剧的关键。全剧围绕着斯福沙—玛赛丽亚—弗朗西斯科的三角关系展开。这种关系展示了绝对背叛的模式,即绝对对立模式,也就是最信任的往往是最危险的这样的信条。按照文艺复兴悲剧传统,斯福沙是正面悲剧英雄,但麦辛哲笔下的米兰公爵并非如此。斯福沙从对妻子疯狂的溺爱到谋杀,而弗朗西斯科则从斯福沙最信赖的宠臣发展为最凶恶的敌人。麦辛哲充分注意到了主要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即性格中冲突的成分。在剧中,斯福沙利欲熏心的本性不容质疑;但作者也展示了他在与西班牙国王短暂的对话中表现的高贵的风度。作者这种对人性冲突性格深刻的观察使读者能够对悲剧发展的不可抗拒性与人物主要性格和生活偶然性的联系有所了解。首先,斯福沙溺爱妻子达到非理性的境界,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爱情的背叛。《米兰公爵》以在公爵夫人玛赛丽亚的生日时全国上下举行庆典开始。这一庆祝活动已经举行三年了,但今年却不同。米兰公爵斯福沙支持法国皇帝与西班牙国王正在进行的战争。而当前西班牙军队风卷残云,横扫法军,并威逼米兰。在国家处于累卵倒悬之中,斯福沙一意孤行,命令人民举国欢庆,显示了他的昏庸无道。格雷克是玛丽安娜的仆人,而玛丽安娜则是斯福沙的妹妹,也是弗朗西斯科的夫人。此时格雷克正在执行公爵的命令,
大家都要开怀痛饮;告诉所有你们见到的人,我的誓言是:今天我是国家领头的醉鬼(当然我并非出于自愿);如果你们发现有人在晚上十点还没有醉,他就是国家的叛徒;你们要执行我的命令将他逮捕。
(第1幕,第1场,第1-4行)
这是一个黑暗的时刻,米兰全城乌烟瘴气,神智颠倒:举杯痛饮成为正道,而清醒理智变成邪恶。格雷克认为,如果教堂的击钟司事打钟走了调,“好像街道起了火”(第1幕,第1场,第7行),那么证明一切正常,因为“他喝多了”(同场,第9行)。如果一个牧师在庄重地传道,他应当被吊起来接受惩罚。麦辛哲让这些话出自格雷克之口,让这个蠢钝、无知、趋炎附势的宫侍代表斯福沙的外在昏庸。
然而,斯福沙的过去并非如此。麦辛哲意图描绘他的个性的发展。通过大臣狄贝里欧的话,读者可以了解到斯福沙曾经是“一个虔诚基督徒,一个为荣誉而战的战士”(第1幕,第1场,第47-48行)。他过去的“睿智果断”(第1幕,第1场,第49行)与今日的昏蒙蠢钝形成鲜明的对比。事实上,在三年前剧还未开始时,斯福沙诱奸了弗朗西斯科的妹妹尤金尼亚,娶了玛赛丽亚后就开始失去理智。疯狂的情欲使他不能容忍与妻子须臾分离。这种情欲不是建立在对妻子爱的基础上,而是夫权至上的集中表现。他唯我独尊,无视妻子的价值。他对妻子的专横是尤金尼亚被摧残后他的欲念发泄的继续。在玛赛丽亚的生日庆典上,他对妻子外在形象的表白陈示了他用情虚浮浅泛。在他眼里,玛赛丽亚是绝代佳人,她的美貌超越了“斯巴达人吹嘘的贵夫人;她的雍容华贵,会使罗马感到荣幸”(第1幕,第3场,第23-24行);“她若遥望天穹,轻动朱唇,天使都会欲言而羞愧”(第1幕,第3场,第35-37行)。斯福沙的反常引起了他母亲的疑虑,“你还在追求她,她就像你的情人,而不是你的妻子”(第1幕,第3场,第37-38行)。的确,玛赛丽亚不过是丈夫的锦衣玉食。也许,斯福沙的这一偏执的欲望最突出地表现在他渴望永远生活在新婚之夜的狂喜中,
此夜难眠,
良宵之时,婚姻之神点起火把,
新的火把:那无穷的喜悦,
不要让那清脆的声音所扰乱,
在满足,欲望,激情,
和无限兴奋的气氛中,你给我
处女的欢乐;天赐之夜,但愿
成为生命中最欢快的时刻,那是
由万星允诺,降福人类的瞬间。
(第1幕,第3场,第42-50)
这段道白充满激情,但展示的仅仅是欲望,充分表现了斯福沙对玛赛丽亚人格、尊严和感情的无视。他的这一心态最终导致了他在赴西班牙帕维尔城之前炮制的罪恶计划。这是危险的出使,因为西班牙国王作为“意大利各国中最强大的君主”(第1幕,第1场,第67-71行),不但无视西法战争中西班牙向他发出出兵援西的呼吁,反而驰兵救法而大怒。斯福沙密令弗朗西斯科在获悉自己死亡以后处死他的妻子。斯福沙明白,自己的所为实乃人神同嫉天地难容的罪恶,
你必须这样做,
如此丧尽天良的行为,天上罪恶的星宿
将闭目自惭;为此人类将同声谴责,
你助纣为虐;我是主谋,
福音天使将弃我而去;如同黑夜般的罪恶啊,
弗朗西斯科,这就是你要去执行的任务,
人们将很快忘记我们所有善良的行为;
如果我们的名字能够长留人间,
我们的后代将为我们的罪恶不寒而栗;
这罪恶将使有史以来所有的恶棍相形见绌;
未来的罪孽,即便是在地狱里传授邪术,
也将望尘莫及。
(第1幕,第3场,第308-20行)
斯福沙的精神状态与麦克白在夜幕中谋杀邓肯一幕遥相呼应。不过,麦克白受麦克白夫人唆使,行凶后倍感内疚和恐怖。而斯福沙则是在个人欲念下所为,事后也未受良心谴责。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中有一些杀妻的类似场景,如奥赛罗将苔思台蒙娜窒息而亡,以及麦辛哲《致命的嫁妆》中查瓦罗斯刺杀妻子一幕。不过这两例略有区别。奥赛罗怀疑苔思台蒙娜不忠,愤怒之下失手将其杀害;查瓦罗斯深知妻子的通奸行为,为此伸张正义;而斯福沙则是在策划一起最狠毒的行动。不过,读者可以从斯福沙与弗朗西斯科的对话中窥见他企图终生占有玛赛丽亚的邪念,甚至她死后的灵魂,是对爱情的完全背叛,
我对她的要求不过是我所努力要获得的,
从她无暇的身体上获取她的灵魂,
就像她死于疾病或其他偶然事件。
那些富有的印度君主们,他们死后,
妻子和奴隶愉快地被当作殉葬品
被送进火堆里;他们最渴望的是
在来世仍能得到侍奉;
我所需要的礼遇应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1幕,第3场,第357-65行)
大多数戏剧评论家在处理《米兰公爵》时认为斯福沙的爱情和妒嫉
受影响于莎士比亚,(注:莫里和赫根详细谈到这个问题。参见Mark
Zeno Muggle,"Philip Massinger's Tragedies and Their Dramatur-gical Context",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78),
193-195页;Alice,P.Hogan,"Theme and Structure in Massinger's
Plays",The School of Shakespeare,ed.David Frost。)但在麦辛哲
剧中,假相掩盖事实,疯狂取代真情。在奥赛罗—苔思台蒙娜悲剧中,爱情是真挚感情的流泻:奥赛罗相信苔思台蒙娜的诚恳和忠实,而苔思台蒙娜崇拜奥赛罗的勇敢和自信。在斯福沙—玛赛丽亚悲剧中,婚姻的基础建立在丈夫的绝对主导地位上。
在对斯福沙性格的复杂化塑造上,麦辛哲还表现了主人公可敬的一面。与之比较,莎士比亚时代的悲剧作家们强调主人公性格的一致性。在他们的作品里,尽管灾难起于天赋特性的不足,但主角们的弱点并非让人憎恶:读者们喜爱奥赛罗、李尔王和安东尼,同情布瑟·丹伯华(《布瑟·丹伯华》)、维多利亚(《白妖》和马尔菲公爵夫人(《马尔菲公爵夫人》)。(注:莎士比亚的悲剧《安东尼和克莱尔巴特拉的悲剧》,作于1606至1607年;乔治·查普曼(1560-1634)于1600至1604年所著的悲剧《布赛·丹伯》(Bussy D'Ambois);约翰·韦伯斯特(1575?-1634或1638)于1609至1613年所著的悲剧《白妖》(The White Devil)和于1612至1614年所著的悲剧《马尔菲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因为这些人物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得到理解。相反,斯福沙在西班牙宫廷上的光彩表现却背离他的真实个性和全剧发展。在这里斯福沙使西班牙人看到了他的勇敢、忠诚和智慧。他的宫廷演说与勃特多的宫廷演说遥相呼应。在麦辛哲的《荣名女》中,勃特多在自己的国家中为富国强兵呼吁;斯福沙则在敌人的国家里表白对朋友的忠诚。面对西班牙国王,斯福沙勇敢坚毅,不卑不亢,诚恳坦率,直抒胸臆。
文艺复兴时代悲剧的一个传统就是通过宫廷争辩来塑造人物突出、一致的鲜明形象。在《白妖》中,维多利亚在审判她的法庭上,用充满勇气和蔑视的申辩反驳对她“行为堕落”的指责,同时表现了她具有“抱负”和“理想”的独立自主和叛逆的个性,在悲剧里树立起一个高大的女性形象。同样,奥赛罗在他的宫廷申辩中,言词坦诚朴素,反驳伯拉邦迪罗对夺走他女儿的指责。他的表白折射出他单纯的个性。艾力尔特认为斯福沙的宫廷争辩“仅仅使剧中的行为延迟,或者中断了感情节奏。”(注:T.S.Eliot,"Philip Massinger,"Elizabethan Drama:Modern Essays in Criticism,ed.R.J.Kaufman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他的评论本身能够说明问题。但是过于着眼于剧的结构,而对人物内在复杂世界的分析略显柔弱。
我认为斯福沙宫廷争辩的重要性在于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腐朽社会和人物个性的复杂性上。西班牙国王出人意料地将斯福沙释放是剧情的转折点。的确,斯福沙—玛赛丽亚悲剧建立在斯福沙自私的狂欲和弗朗西斯科的复仇并行发展的基础上的。处于第三幕开始时的斯福沙宫廷申辩一场,不仅长,比重也大,完全改变了全剧的节奏。这一场开始时有迈迪拿、赫纳多和埃尔佛苏三人的一段对话。他们都是渴望建立功勋荣获奖励的西班牙将军。他们的对话并非要表现士兵的散漫,而是展示社会底层普遍存在的腐败和堕落,以及战争中士兵的不幸状况。西班牙国王查尔斯敬佩斯福沙不畏强权,不苟且偷生。他未谈斯福沙的表现和战争的关系,但他的判断出于虚荣心。事实上,西班牙国王的行为远不能令人称颂。因而他的将军们在剧开始的时候抱怨他在战争中不光彩的行为和牺牲原则、沽名钓誉的处世哲学。换言之,查尔斯释放斯福沙的决定——“我们应捐弃前嫌”——并非深思熟虑、而是随机任性之举。但是这一决定使斯福沙、玛赛丽亚和弗朗西斯科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斯福沙意外的安全回国打乱了弗朗西斯科的计划,他的情欲和野心暴露之后被迫铤而走险。全剧的下半部分转而描写弗朗西斯科的复仇。斯福沙的宫廷争辩也许是一个偶然安排。但斯福沙的冲突个性,西班牙国王的虚荣和他们戏剧性会面的确对整个剧情举足轻重。
三
弗朗西斯科是《米兰公爵》中的反面英雄。但麦辛哲对他的塑造与斯福沙的形象平分秋色,使得他的情欲和野心在剧中与主线并行发展。弗朗西斯科是《米兰公爵》中邪恶势力的代表。与典型的文艺复兴时代悲剧反角英雄不同,如巴拉巴和伊阿格的狡黠诡诈,温狄吉和安东尼坚定的复仇决心,弗朗西斯科则两者兼得。(注:Cyril Tourneur(1575-1626),英国剧作家。他的著名悲剧是于1606年至1607年所著的《复仇者的悲剧》(The Revenger's Tragedy),男主人公是温狄吉。)读者从《米兰公爵》的前三场看到弗朗西斯科利用福斯沙的信任满足私欲。弗朗西斯科成为斯福沙的宠臣是以交换为代价的,“荣誉来自缄默不语”(第2幕,第1场,第26行)。他对斯福沙诱奸自己妹妹一事保持沉默以换取当前的地位,但弗朗西斯科首先是满腹情欲的复仇者。他垂涎玛赛丽亚的美貌,伺机在斯福沙不在时诱奸她。他软硬兼施,先赞美,后出示斯福沙的密令,力图控制她。为了取宠于玛赛丽亚,他软禁了伊莎白拉和玛丽安娜,并将格雷克毒打一顿,原因是他们对公爵夫人不敬。他的献媚获得了一次与玛赛丽亚约会的机会,然后向他的目标前进,他赞美公爵夫人说,“你无与伦比,举世无双;在纯洁的石壁上高高耸立,邪恶只能望而生畏,这个大自然建造的近乎完美的词坛”(第2幕,第1场,第260-63行)。看到对方迷惑不解,弗朗西斯科将他的欲念一展无余,“我像男人一样爱你,并希望像男人一样从你那儿得到欢乐”(第2幕,第1场,第282-83行)。接着他诋毁公爵夫人的丈夫,“他早有恶心,盼你死去”(第2幕,第1场,第343行)。但是,丽赛丽亚对丈夫的忠诚坚信不疑,“假如你希冀我在婚姻上用情不专,有机可乘,那你就是让我相信,地球转动,而太阳和星辰伫立不动;大洋无力驱动风暴和波澜”(第2幕,第1场,第334-36行)。看到一无所成后,弗朗西斯科拿出最后的王牌,斯福沙的密令。玛赛丽亚立即昏厥过去。尽管在后面的剧情发展中,弗朗西斯科告诉他的妹妹,他勾引斯福沙的夫人实乃复仇行为,他的表白难掩淫荡的本质。然而他仅仅展示了斯福沙密令中将玛塞丽亚处死的那一部分,而将执行这一命令的前提,“在得到斯福沙死讯以后”,掩藏起来。弗朗西斯科的行为显示至此他不过是满腹欲望,并非传统复仇悲剧中坚定的复仇者。在麦辛哲的另一悲剧《骨肉残杀》中,蒙特维尔玷污了老马尔福特的女儿赛奥克琳娜。(注:《骨肉残杀》(The Unnatural Combat)写于1624至1625年。)需要指出的是,复仇是蒙特维尔暴力
的基本动力。弗朗西斯科则利用斯福沙赋予他的权力去满足自己的欲望。
虽然斯福沙和弗朗西斯科这两个悲剧英雄的个性特征决定了全剧的主要发展方向,格雷克的戏剧性表现对弗朗西斯科的复仇行动起了关键性扭转作用,再一次证明悲剧过程中的偶然因素。弗朗西斯科和格雷克的对白占据了全部第4幕第1场。他们两人关系非同寻常。格雷克实际上是为玛丽安娜服务的男性伴侣,正像他自己坦白的,“我可以随时出入她的卧室”(第2幕,第1场,第63行)。但弗朗西斯科并非因格雷克与自己的妻子有染而在第1幕第1场中惩罚他。的确,弗朗西斯科的婚姻蹊跷可疑。玛丽安娜对丈夫的行动不但一无所知,而且给他引起麻烦。格雷克对他的女主人忠心耿耿。他愚蠢地相信斯福沙远行在外,玛丽安娜便是米兰的主宰。在丽赛丽亚与玛丽安娜争吵一场中他大肆嘲弄斯塔法罗和狄贝里欧,“我已被授权大肆奏乐;坦率地说,在我面前你们最好表示友善些”(第2幕,第1场,第77-78行)。而惹怒弗朗西斯科的是格雷克忠诚于玛丽安娜。所以在剧开始的时候,弗朗西斯科将这个会给自己制造麻烦的家伙毒打了一顿。
斯福沙的意外回国破坏了弗朗西斯科的计划,他不得不重新考虑与格雷克的关系。他打算利用这个蠢货去挑动玛丽安娜女人的妒嫉心,使他在斯福沙面前诬蔑玛赛丽亚。当然,这也并非易事。因为格雷克效忠玛丽安娜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弗朗西斯科不久前刚刚错误地惩罚了他。格雷克一生愚钝,但多少明白在这个浑沌的社会应该保护自己。所以,弗朗西斯科和格雷克的对话暗伏恐吓和欺诈,充满杀机,再次显示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社会形态和他们之间的微妙往来对全剧结构的影响。
他们的谈话开始时,弗朗西斯科为缓和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试探性的问道:“你是否能捐弃我对你的错怪,考虑一下我的处境和愿望?”(第4幕,第1场,第1-2行)格雷克的回答则是虚伪的阿谀,“受到像您这样高尚人的惩罚,我明悉大理,获益非浅”(第4幕,第1场,第6-7行)。他甚至对此表示感谢,“受辱于外,但受惠于内”(第4幕,第1场,第13-14行)。弗朗西斯科不以为然,并开始吹嘘他是如何命途多福,直步青云,从一个青衣小人一夜间大权炙手可热,“集美德于一身,我做梦也没想到”(第4幕,第1场,第23-24行)。他虽说自己是被过蒙拔擢,授以大任,实为暗示他有神明护佑,安然无恙。格雷克被震吓了,马上回答说,“都是上天的安排”(第4幕,第1场,第37行)。他似乎对这位公爵宠臣深信不疑,并忖度自己该如何行事,“难道因为一次错误的责打,我就该与手握命运转轮的人分道扬镳吗?”(第4幕,第1场,第37-39行)。尽管还不清楚弗朗西斯科的真正动机,格雷克还是继续恭维他,“虽然我疼爱我的身体就像我疼爱他人一样,如果您现在有兴致蹬我一脚,命令我去干某件事,难道我会坐视不动,难道我不该俯身叩首,亲吻您踢我的那只脚,一表谢意吗?”(第4幕,第1场,第42-46行)。
当他们开始讨论正事时,弗朗西斯科向格雷克透露他与玛赛丽亚的亲密关系,他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他要表明他已得到的“权力”和“荣誉”,以此向格雷克施加压力。格雷克得到玛丽安娜授意,前来打探弗朗西斯科与玛丽赛丽亚的关系。此时,弗朗西斯科要求格雷克挑动玛丽安娜,迫使她在斯福沙面前诬蔑玛赛丽亚。虽然弗朗西斯科坦率表明,“无论如何,有负于一人个人以后,再有求于他,是靠不住的;我想你缺乏诚意”(第4幕,第1场,第83行),他把希望寄托在后面的威胁上,“还是放明白点儿吧,笨蛋,上次是我的命令,你挨了鞭挞;今后任何一天对我的命令若有半点儿怠慢,我会让你再尝尝鞭子的滋味”(第4幕,第1场,第89-92行)。他重申公爵赋予他的权力,“我一言九鼎……不容质疑”(第4幕,第1场,第95-97行)。格雷克处于审时度势的关键时刻,他忖度该效忠哪一边,“我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第4幕,第1场,第102行)。一个绳枢氓隶之徒,格雷克对忠诚的理解不过是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他弱智浅识,但明白苟全性命的重要,“对他,我必须恭敬服从。我才疏学浅,不得不做个随风倒的村野小人”(第4幕,第1场,第115-16行)。格雷克的才疏学浅不过是他的智力低下。弗朗西斯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麦辛哲精心设计的这段对话突出了这两个人物的关系在向悲剧高潮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格雷克突然倒戈转向弗朗西斯科使剧情急转直下。他关于玛赛丽亚有奸情的挑唆使本来就十分挑剔、心怀恶意的玛丽安娜平添嫉妒。斯福沙平安回来后,玛赛丽亚表情冷淡,但他则认为这不过是一时的情绪变化。玛丽安娜对玛赛丽亚的诋毁使斯福沙确信妻子的“罪行”。没有清晰的证据,斯福沙无法摆脱谣言的困惑,进而重新获得对妻子的信任。悲剧一步步逼近了。
四
与斯福沙和弗朗西斯科相比,玛赛丽亚是一个位居边缘的从属角色,但在她身上也可窥见一种对道德的背弃。她在夫权桎梏的有限空间中谋求生存,而不是苔思台蒙娜式完美的女性。她比苔思台蒙娜更坚强,但缺乏麦辛哲的《荣名女》中卡米欧拉实现生活目标的坚定信心。首先,她陶醉于丈夫对她美貌的神志颠倒般的赞扬中。她重申她的忠诚和服从,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我对苍天发誓和祈祷,祝你,我的主公,事业昌盛,一生平安,”(第1幕,第3场,第60-63行)。她乞求他的理解,她只盼望自己“不会愧对他的厚爱”(第1幕,第3场,第64行),那种以“拥抱”和“亲吻”表达的厚爱。
如果苔思台蒙娜的俯首遵从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奥赛罗的疑心,玛赛丽亚的表白忠心只能使斯福沙疯狂欲望滑向灾难的深渊。与此相比,《荣名女》中的卡米欧拉更令人赞赏,她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自己完整的形象。公爵夫妇相互恭维和许诺,在声色犬马的物欲中越陷越深。在剧开始的合唱中,大臣狄贝里欧描述了公爵夫人的高傲,
高贵的夫人,绝代容貌,财富连城,
在连绵不绝的阿谀奉承中,
很少不露傲慢的举止;
在这方面,她也不例外。依仗
公爵独一无二的宠爱,
她昂首阔步,傲视群臣……
(第1幕,第1场,第198-117行)
狄贝里欧一针见血,看到了玛赛丽亚在浮夸吹捧的污浊并不能如秋芙出水,一身清洁。她与斯福沙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她的消极附庸的形象上。
在文艺复兴悲剧中,生活在夫权至上社会中的女主角,一般表现为三种特征:被动和纯洁的,志高和阴险的,放荡和不检的。第一种形象的女主角,如朱丽叶、拉维尼亚、奥菲丽亚和苔思台蒙娜,一般形象光彩完美,多出现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她们一般行为端正,但生不逢时,最终成为环境因素的牺牲品。第二种形象的代表人物,如麦克白夫人、宫达维尔和里根,多出于莎士比亚的詹姆士时代悲剧中。她们扭曲的人格不过是男人肆虐的社会中悲剧的殉葬品。像安妮·弗兰克福特(《死于善良谋杀的女人》)、毕尔阿特丽丝·琼(《双形》)、维多利亚(《白妖》)和伊万蒂(《少女的悲剧》)等大多数詹姆士时代女性角色属于第三类。(注:托马斯·米德尔顿(1580-1627)和威廉·罗雷(?-1626)于1622年合著The Changeling;托马斯·哈伍德(Thomas Heywood,1573?-1641)于1603年所著的悲剧A Woman Killed With Kindness;弗朗西斯·伯曼(1584-1616)和约翰·费莱彻(1579-1625)于1608至1611年合著的悲剧The Maid's Tragedy。)她们追求自由和自主,性格趋向复杂但充满生机。但麦辛哲的玛赛丽亚并不属于任何一种模式。尽管她是无辜的,但在斯福沙的疯狂欲望中,她的作用不能说是被动接受的。弗朗西斯科对此有明确的描述,“她要承担责任的,问题出在她的动机上”(第4幕,第3场,第251行)。社会缺乏理性,家庭沉溺情欲,公爵夫妇难以自拔。
如果说玛赛丽亚对于斯福沙的痴情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她的骄矜自负则不断引发斯福沙母亲伊莎拜拉和玛丽安娜的指责,进一步玷污了她的形象。狄贝里欧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伊莎拜拉和玛丽安娜对公爵夫妇婚姻的潜在破坏因素,“无论怎样她们的怨言被暂时压抑下去,可怕的事远不只眼前;它终究会爆发出来”(第1幕,第1场,第121-22行)。事实证明米兰的家庭和婚姻、社会一样充斥着怀疑冲突的因素。
正是在斯福沙出使西班牙的过程中,伊莎拜拉和玛丽安娜寻衅搅乱玛赛丽亚的心情。她们指使格雷克和一个小提琴师在公爵夫人的宫门外喧闹。三个女人间的矛盾终于演变成公开的对骂。玛赛丽亚毫不留情地显示了她尊贵和凌人的气势。她称斯福沙的母亲为“仆人”,“愚蠢的家伙,酒囊饭袋”(第2幕,第1场,第153-54行),称斯福沙的妹妹“无用蠢笨的傀儡”(第2幕,第1场,第157-59行)。她还神气十足地显示公爵夫人的地位,“……公爵完全和我在一起,他的权力和荣誉就是我的;你们对我就像对他一样需要绝对忠诚”(第2幕,第1场,第160-62行)。她进一步提醒她们,“不要忘记我与你们之间的君臣关系;你们应绝对服从,否则我会使用我的权力,像王后一样严惩不怠”(第2幕,第1场,第163-66行)。玛赛丽亚在斯福沙面前纵容他的偏执,在他不在的时候未能调解冲突,反而使其激化。伊莎拜拉和玛丽安娜难抑怒火,正如前者称玛赛丽亚“这个傲慢的东西”。她们在斯福沙面前挑拨是非,最终把公爵夫妇的婚姻推向了死亡。玛赛丽亚宽容不足,世俗有加,在自己不幸的天平上添加了一个砝码。
第4幕第3场是全剧的高潮:玛赛丽亚被杀,斯福沙发现弗朗西斯科的阴谋,弗朗西斯科逃离米兰。以后的剧情发展则是弗朗西斯科的复仇。但是麦辛哲强化公爵夫人之死的渲染,力图在戏剧技巧和情感上震撼读者。在第3幕第3场中,斯福沙回国后发现夫人冷若冰霜,便拒绝与她再见面。然而他仍然期待她回心转意。一直受命服侍玛赛丽亚左右的斯塔法罗忠告斯福沙,“弗朗西斯科大人虽然受您之命关照夫人,但他有过近之嫌”(第4幕,第3场,第85-86行)。斯福沙不能接受对宠臣的指责,“此言不实,我不能相信”(第4幕,第3场,第89-90行)。对玛赛丽亚的诬陷直接来自伊莎拜拉和玛丽安娜。斯福沙的目光首次落到妻子身上:“请拿证据来。”由于玛丽安娜只是从格雷克那儿听到了只言片语,并无证据,斯福沙只当她们的话是“无聊女人的嫉妒”。可是,他对妻子的信任却因此经历了剧烈的震荡。我认为不能否认麦辛哲描写斯福沙的心理冲突是受莎士比亚的影响。在《奥赛罗》第3幕第3场中,伊阿古的挑拨使奥赛罗顿生疑窦,他对苔丝台蒙娜的爱情出现裂痕。但是他不能接受她有淫荡行为这一事实,因此他向伊阿古索要证据,
恶棍,你必须设法证明我的心上人是婊子;(掐住他的脖子。)
一定要证明。给我可视的证据,
否则我就永恒的灵魂而言,
你就去做一个赖皮狗,
也平息不了我胸中怒火!
(第3幕,第3场,第358-63行)
奥赛罗的话显示他此时的心情爱恨交加,悬于“可视证据”之上。伊阿古的奸诈和奥赛罗的率直堆起了悲剧的干柴,丢掉的手帕作为奸情的证据成为引爆的火种。奥赛罗在第5幕第2场将苔丝台蒙娜窒息而死前与她的争执围绕着手帕展开。苔丝台蒙娜坚决否认与卡西欧有染。而奥赛罗则认为卡西欧手中有苔丝台蒙娜的手帕是不可抵赖的事实。这与《米兰公爵》中斯福沙游离于听信和爱情之间的困惑有异曲同工之妙。
斯福沙带着这种心情与弗朗西斯科见面。这个宠臣想通过坦承他与公爵夫人关系过密来达到激怒斯福沙的目的。斯福沙马上相信了他的话并接受他阴险的建议,告诉玛赛丽亚弗朗西斯科已被公爵处死了来检验她的态度。在这关键时刻,斯福沙,粗率莽撞,一个心思要得到证据。他下令将玛赛丽亚拖至面前,在短短的二十五行对白后便将她刺死。这一场面双方都义愤填膺,玛赛丽亚称斯福沙为“妖魔”,“嫉妒蠢笨,如移动的枯树”,“做白日梦的人”,“头顶生角的野兽”(第4幕,第3场,第261-62行)这与苔丝台蒙娜向奥赛罗乞求“可怜可怜我吧”的哀鸣截然不同。斯福沙的用词同样尖刻,“轻率的家伙,你看你原来是如此下贱!一心要当个浪荡女人……”(第4幕,第3场,第270-72行)。愤怒中的玛赛丽亚不慎失言,默认自己行为不检,“即便我与每个恶棍同流合污,你的行为更应受到谴责”(第4幕,第3场,第274-76行)。
和奥赛罗—苔丝台蒙娜的最后对白不同,斯福沙与玛赛丽亚相互指责咒骂。斯福沙的大男子主义迅速膨胀,而玛赛丽亚并不示弱。但她从未质问丈夫下达的导致关系恶化的密令。当斯福沙试探性地说出弗朗西斯科刚被他亲手杀死时,玛赛丽亚失去控制。她草率地回应不仅肯定了她与弗朗西斯科的私情,而且表示出这个阴险之徒在她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然而,这也她的真实心情完全相悖,
你是个十恶不赦的屠夫,
十分明显,你没有一丝一毫的爱。
你杀死的人,我承认我爱着他,
他是一个值得千万位女王仰幕的男子。
(第4幕,第3场,第279-84行)
玛赛丽亚的过失为斯福沙提供了所需要的证据,灾难不可避免。斯福沙一剑向她刺去,说道,“我现在行使我的正义行动”(第4幕,第3场,第287行)。临死前虽然玛赛丽亚说出了弗朗西斯科的恶行,但为时已晚。比较《奥赛罗》和《米兰公爵》结尾的杀戮情节,苔丝台蒙娜承认丢失手帕显示了对一个确凿真实的诚恳态度,尽管她对潜在的阴谋一无所知;而玛赛丽亚失口承认她与弗朗西斯科的私情,使诬告成为现实,紧张的情绪如火山爆发出来。由于米兰宫廷灾难不过是斯福沙的唯我独尊、弗朗西斯科的复仇意志和玛赛丽亚行为缺陷的函数,即随这些基本因素变化而变化,玛赛丽亚难度劫波只是时间的问题。
第5幕全部描写弗朗西斯科策划斯福沙的死,完成戏剧性的复仇结局。玛赛丽亚的死使斯福沙失去理智,这符合文艺复兴时期复仇悲剧中疯狂行为的模式。但是纵观全剧,这样的处理似乎有些思路模糊,结构松散。斯福沙吻玛赛丽亚中毒而亡的确有些离奇耸听,具有典型的詹姆士一世时代的悲剧特色。布拉那姆认为,“从戏剧技巧角度来看,整个第五幕和前面四幕还是融为一体的。”(注:参见Charold Frank Branam,"Neo-stoicism in Philip Massinger's Tragedies,"Dissertation(Temple University,1972),159页。)我也基本同意这种看法。第五幕是重要的,但麦辛哲为表现他的悲剧观念,把全剧的重点无疑放在了前四幕。
《米兰公爵》中悲剧的关键和重要因素表现在人性的欺诈和事件的偶然性。麦辛哲的悲剧观念与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传统有着明显的不同。广泛存在的背叛、奸诈、嫉妒的仇恨动摇了保障社稷安定的婚姻、家庭、爱情和忠诚等传统观念,缩小了人们争取完美生活的自由空间。在悲剧技巧上的创新表现在英雄与反英雄趋于接近,双主题结构并行发展。虽然评论家们始终认为麦辛哲在悲剧创作上热衷于对离奇、血腥的故事情节的描写,缺乏艺术的严肃性,但他对复杂人生的观察在《米兰公爵》和后来的创作中逐渐地更加仔细和多方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