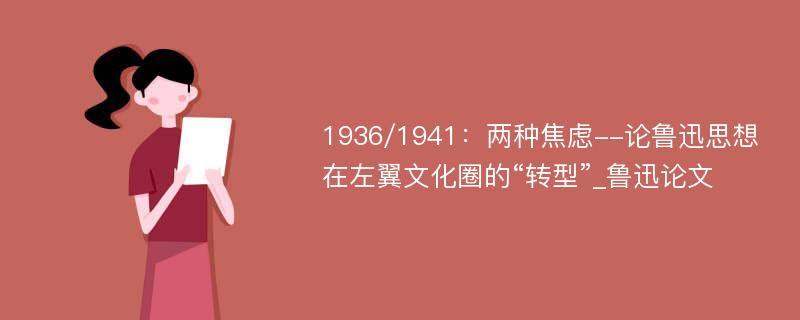
1936~1941:两种焦虑——左翼文化界关于鲁迅思想“转变”讨论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文化界论文,两种论文,左翼论文,焦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瞿秋白之前,左翼文化阵营尚没有人能够解释鲁迅“向左转”的思想基础。当上海滩小报惊呼鲁迅“转向”“投降”时,左翼内部的“创、太情结”也暗含着某种“受降者”心态。直到瞿秋白于1933年发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前后,两本持有左翼立场的文学史读物(注:这两本读物是: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新兴文学研究会1933年1月版;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北新书局1933年8月版。),仍然坚持认为“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点”上的鲁迅,“被时代的洪流所摧残,终于身受创痛,开始认识到了革命的到来和旧世界的崩溃,1930年以后,他要追上时代的洪流,……他不愿做一个时代的落伍者”[1](P138~139)云云。瞿秋白序言的发表,基本上中止了这类似是而非的拟断之正当性,也纠正了不少左翼人士类似的“定见”。同时,他文中的“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2],也成为左翼文化界、进而成为共和国文学史言说鲁迅思想“飞跃”的“定则”。
但在这之后,尤其是鲁迅逝世后,左翼文化阵营如何对待鲁迅思想“飞跃”前后的连续性,则成为左翼文化界面对鲁迅思想遗产的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用“从……到……”的公式来概括鲁迅思想变化的简易性和人们阅读鲁迅作品时的复杂感受之间的反差,越来越为敏感的人们所注意。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直至1949年后,论述鲁迅前后期思想连续性的文章一直持续不断,但其间的情形却颇为复杂。而在1936年至1941年之间,围绕着如何解释鲁迅思想的“转变”,两种不同的潜在焦虑正在左翼文化界暗暗滋长。
鲁迅逝世后不久,围绕这一问题就有过一次小小的争论。从《申报》的一则《北平文化界悼念鲁迅》的报道可以看出事情的端倪。这篇报道把涉及到鲁迅的“‘转变’问题”概述为如下中性的文字:
鲁迅于民国十六年后之二三年内,曾因创作态度问题,与当时属于前进分子之创造社、太阳社等人物,从事笔战。其后民国十八年左右,氏之态度变更,左翼作家大同盟成立,前进文人,纷纷加入。宣言发表时,署名其首者,赫然为鲁迅者。此后,即一贯的社会主义立场,发表言论,文坛上谓氏此时期态度之变更,为“转变”。[3](P148)
记者接着报道了“北平文化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称“根本上为前进,为一贯,并非转变也”。然后特别举出“北大前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氏,……于一班企借此‘转变’说法,以达私人目的之人,尤致以无限之愤慨”。[3](P148)马裕藻并非左翼中人,仅为鲁迅故交,为什么言及鲁迅“转变”会使他如此“愤慨”?后来参与争论的雪苇曾出示了令人“愤慨”的语义背景:“‘转变’、‘突变’这些名词,是早给中国的市侩投机家们糟蹋利用坏了,有了不洁的印象,由此生出反感。”[4](P334)如果仔细阅读《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就会注意到,瞿秋白在文中也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着“转变”一词,他宁愿使用“飞跃”、“走到”、“进到”。由此透露出了中国现代社会中某种情绪性的社会氛围,即一个事件的意义还没有敞开,各种私见就已本能地“登堂入室”,“反客为主”,个个榨取着于己有利的一份,满足着自己那从未清理过的“意欲”,从而继续维系着自身的非理性和封闭性。而恰恰是这种非理性和封闭性,常常压倒一切,成为主宰多数人意识和感觉的不容分辩的力量。
在哀悼鲁迅的那些日子里,“转变”一词变得有点敏感。因为这个词之于鲁迅,曾经和“投降”粘合在一起。这种“粘合”不仅来自各种传布流言的小报和“反动者的造谣中伤”(王淑明语),也来自隐约存在于左翼内部的某种久已有之的“受降者”心理。这种心理自然受制于情感的亲疏,但更取决于一种至深的感觉方式和思维逻辑。所以,当郭沫若的一篇悼念文章在《东京帝国大学新闻》上发表后,其中一段话的微妙之义便被敏锐的读者捕捉到了:“一九二七年与一九二八年之间,和我关系很深的创造社同人,跟他争论着‘意特奥罗基’上的问题,相当地激烈了。可是,那件事成了他底方向转换的契机,我以为宁可是一件很可纪念的事情。”[5](P608)这段话本只是解释创造社同人对鲁迅从不抱敌意,不管态度真诚与否,对已故者的不敬是丝毫没有的。但郭沫若所涉及的鲁迅“转向”以及也许连作者自己都难以觉察的微妙之义,还是成为王任叔随后予以评论的依据。王从雪苇刚刚发表的《导师的丧失》中也捕捉到“仿佛也隐隐承认鲁迅先生这一‘转变’”的信息。在刊发于《中流》杂志的《鲁迅先生的“转变”》一文中,王任叔认为:“‘转变’两字,有当于进化论上的‘突变’。是自量到质的变化。所谓前后判若两人的意思。绝不是进化论上那种渐进的意思。日本把这种‘转变’叫做‘转向’,倒更来得明白确定些。”王断然否定鲁迅有过这种“转向”或“突变”,认为“他自从发表《狂人日记》起,一向就是以现实主义者的姿态出现的,而且他始终站在历史的现实主义的土台上。始终随着历史的进化的法则,走着他的路”。对于“现实主义”,作者给出的解释是:既具有人类“伟大的理想”,又“注重实做”。而“实做”在作者那里,似乎不仅指埋头实干,也包含着“动态”之义,即一方面随着“历史的进展”而进展,另一方面又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都着手解决这个时代或时期的问题,既不滞后,也不超越之。作为这种“现实主义”的具体例证,作者列举了鲁迅与左联“领导者们”的两次冲突——关于以“作品”为标志和作家飞行集会的冲突;关于“两个口号”的冲突,以证那些“领导者们”从左到右的“突变”和鲁迅基于“现实主义”的“不变”。对于“进化论与阶层论”(原文如此),“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与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作者也认为“绝无冲突之处”,“更有共通之处”。文章最后的结论是,由于“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个历史的现实主义者,一九二七年以后与一九二七年以前,他并没有什么‘转变’,或‘转变’的‘迟缓’。自然,随着历史的进展,鲁迅先生也迈进了,但那不是一般意义上说来的‘转变’”。[6]
对于王任叔的批评,雪苇迅速写出了回应文章。他解释说,《导师的丧失》一文只是举例说明鲁迅具有“彻底的自我批判精神”,并没有论及鲁迅的“‘转变’或‘转变’的迟缓”问题,因为他知道“转变”、“突变”这些词,“早给中国的市侩投机家们糟蹋利用坏了”。但鲁迅的思想是发展的却是事实,“从进化论到阶级论,就不是用‘渐变’、‘渐进’解决得了的”。雪苇认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各阶段发展的特征”,均“反映在鲁迅先生思想发展的过程上”。“因鲁迅先生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唯物主义)者,而且是个缺点很少的现实主义者的缘故,所以他的思想发展过程,自始就带着一种一贯发展的特征,很相似于马、恩的发展过程”。所以,不必忌讳“转向”一词,因为“真实的‘转向’,是绝对不能拿与中国一般市侩投机分子相提并论的”。[4](P332~334)雪苇的中心意思是鲁迅的思想是发展的,这种发展是可以用“转向”或“突变”来形容的,但鲁迅的“突变”是鲁迅意义上的“突变”,鲁迅的“转向”也非“革命文学家”式的脚踏“两只靠近的船”(鲁迅语),而“发展”则是鲁迅思想的一贯性特征。
王任叔承认鲁迅“迈进”却拒绝承认“转变”的奇特观点,也招来第三方的批评。王淑明在《一个伟大作家的历程》中,论证了鲁迅“在思想上的转向”与辩证法“自量到质的变化”法则相“吻合”。针对王任叔“始终的现实主义”论,他指出:“无论先生有着怎样的现实主义的精神,这只是一个内在的契机,由于这,我们才看出先生在一九二八年的转变,并不是一种偶发的现象,一种从观念的立场出发的突发性运动,相反的,乃是在思想和精神的素质上,有其本来的根源。”这本来的根源“经过社会的养育,历史的进展,逐渐的将先生推送到正确之路上来”。作者显然是以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的辩证法,以证王任叔观点的生硬与悖谬,显示了作者的逻辑自洽和“理论正确”。但正是在这篇逻辑自洽和“理论正确”的文章里,作者几次使用“正确之路”、“最后的道路”、“终极点”[7](P714~716)这类富有终极性价值色彩的用语。他当然是在真诚地颂扬鲁迅的伟大,但这种伟大却是“先生”今是而昨非的“伟大”,是克服了“旧有的残存意识”的“伟大”,是“终于决定走上最后的道路”的“伟大”。
富有意味的是,这个随后介入的第三方批评,却成为我们解读王任叔奇特观点的一把钥匙。在与雪苇的论争中,表面上看起来,王任叔是在做一种无谓的批评,因为不管是他本人,还是雪苇,都承认鲁迅思想的“现实主义”特征,他们所针对的事实也几乎是同类的——王针对左联中后期的“领导者们”的易变,雪苇针对的则是“革命文学家”脚踏两只船的易变,所争仅限于“名词”。但在这些表面之下,却表现着某种深深的焦虑。王任叔的反应自然基于“转变”一词在当时语境中的含义,但当他认为瞿秋白“从……到……”命题的两组对立项之间“绝无冲突之处”、“更有共通之处”时,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瞿秋白《序言》以相知者身份大篇幅地肯定了鲁迅前期的思想和写作,其所针对的恰恰是某种溢于言表的等级观,即以“革命文学”发起者的身份,把鲁迅的既往业绩等而下之,把鲁迅的“向左转”视为“投降”,而“飞跃”一词在这样一种连接鲁迅一生的上下文里,并无“转变”、“突变”在当时语境中的贬义(他也的确避开了“转变”之类的词)。但当“从……到……”的“飞跃”离开了瞿序的上下文,而被嵌入左翼文化阵营中普遍存在、且一如既往的绝对主义思维逻辑中时,同样的等级观又以新的形式悄然滋长,那就是鲁迅的“后期”在等级上高于其“前期”。与“创、太”集团给予鲁迅前后“转向”之等级观不同,这是一种没有明说、也无法明说的情形,是一种明显存在而又好像根本不存在的状态,所以,王任叔的“挑战”才显得那么“笨拙”,以找错了对象显示着他的无以对象。正是从王任叔这种“笨拙”中,我们才得以窥见左翼文化阵营内部赋予鲁迅思想以独立性的艰难努力和表述困境。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
胡风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曾撰文指出:“他(鲁迅)从来没有打过进化论者或阶级论者的大旗,只是把这些智慧吸收到他的神经纤维里面,一步也不肯放松地和旧势力作你一枪我一刀的白刃血战。”[8]如果不细辨这段话,就会把胡风感觉到的鲁迅精神中的一种决定性特征,淹没在他和别人并无不同的左翼话语方式之中。这一决定性特征,不在于鲁迅使用的是什么武器,而在于他使用武器的方式——这一方式使武器“智慧”化,化进“神经纤维里面”,武器是什么反而并不显得头等重要了,至少不比化进“神经纤维里面”更重要了。这解释了胡风在40余年后像化石一样复出时,坚持说鲁迅五四时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9](P3~9),而在30年代后半期人们纷纷言说鲁迅思想构成时,他反而不以为然,直接接受了瞿秋白“从……到……”的命题。在他的意识和潜意识里,鲁迅属于世界,但也始终属于鲁迅自己。
鲁迅去世所引发的“哀悼的狂潮”(胡风语),使关于鲁迅思想的讨论持续了好几年。其中对鲁迅思想“转变”的问题,由于左翼哲学社会科学家的介入,在保留瞿秋白命题基本框架的同时,也使这一命题得以拓展。艾思奇发表于1937年6月的《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一文中,便把瞿秋白的命题修正为:从个人主义到集团主义;从人道主义到社会主义;从进化论到历史的唯物论。[10](P781)这个判断在瞿氏命题的基本框架上虽无改变,但语义上却有拓展,也使得原有“从……到……”的对立项在对应上更为规范。翌年10月根据鲁迅思想座谈会发言而李平心改写、署名“鲁座”的《思想家的鲁迅》,刊登在当年出版的《公论丛书》第三辑上。这篇论证严谨、分析细密的近三万字的长文,在论及鲁迅思想“转变”时,直接吸收了艾思奇的说法,但语义上同样做了拓展。他的表述为:由进化论进一步走向史的唯物论;由人道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由反对压制个性发展的个性主义走向争取大众解放的集团主义;由“为人生”的启蒙主义走向改革世界的国际主义。[11](P1041)与《思想家的鲁迅》出版同时,远在延安的周扬在《解放》周刊也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路》。关于鲁迅思想的“转变”,周扬在文中的一个比较新颖的提法可以概括为:从彻底的民主主义“走向无产阶级”。[12](P1019)这离茅盾等1949年后的提法“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13](P256)已经不远了。
但构成要素的增加和阐释概念的丰富,并不一定意味着被阐释出的精神的丰富和充盈。在鲁迅被热烈地纪念、尊崇和阐释时,那种取代“创、太”模式的潜在“等级观”并不因为王任叔的“焦虑”而有丝毫减少。鲁迅思想遗产在中国现代特有的历史情景中,不仅为整个右翼文化界所拒绝,在左翼文化阵营内也陷入了不可避免的两难之境。这个两难之境是:人们一旦做出了历史的选择,就情不自禁地倾向于将之终极化;鲁迅也同样做出了这种选择,但其思想的根底里却拒绝任何终极化。于是,那些将历史选择终极化了的人们,便感到了鲁迅与自己一致而又不一致的某种潜在焦虑。他们通过把鲁迅也纳入终极化的理解中,来削平自己的那种不一致感。而这种“削平”过程便转化为对鲁迅前后期“连续”和“断裂”的处理过程,其方式有二:一是赋予鲁迅前期以更多的“后期性”;二是在无法赋予之处,让那潜在的“等级观”浮出水面,用以说明那只属于鲁迅前期的局限。
在上述列举的文章中,艾思奇明确提出鲁迅思想是一贯的,但他解释说,这个“一贯,是发展的一贯,不是静止的一贯”。艾文的立意在于谈鲁迅的民族主义,并将民族主义区分为“最勇敢”的和“较勇敢”的,而像鲁迅这种“最勇敢的民族主义者”的标志,则是“和物质生活要求最切近的人民一致”。除了在鲁迅前期思想中寻找唯物主义因素外,艾文也寻找辩证法,认为鲁迅杂文在“巧妙地暴露事实的矛盾”时,“虽然没有有意地在讲辩证法,但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地在随时应用”。作者显然是想以他驾轻就熟的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来解读鲁迅,但面对这个王任叔曾“笨拙”地加以捍卫其“独立性”的复杂的存在,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哲学家也不免时而精彩辟透,时而拘泥生硬。而下述对鲁迅的判断自然为王任叔式的“焦虑”再次提供了“依据”:“他也曾蹉跌,走上歧路。他曾失望,感到虚无,……然而他……从反对精神胜利的旧唯物论思想,终于达到了科学的唯物论的境地。”[10](P782-783)
周扬用以证明鲁迅从彻底的民主主义“走向无产阶级”的方法很有意思,他引用列宁在《论民族自决》里的一段话作为起始时,暗示了他所言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但在比附“鲁迅的民族思想就是反对压迫的民主主义的内容”时,却巧妙地回避了以这种阶级论直接为鲁迅定性,从而使之出现了一个在逻辑上具“有”而词句上却“无”的话语空白。这一空白在诸多真诚肯定和赞颂鲁迅的话语中又极易被淹没,但这一空白在逻辑上的“有”却始终存在着,所以他才真诚而含蓄地批评鲁迅作品没有表现“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的斗争转到‘自为的阶级’的斗争”,但也紧接着给予了真诚地谅解:“由于这种时代的限制和他个人生活的特殊性的结果,现实主义者的鲁迅没有能够创造出积极的形象,正是很自然的事。”文中另一处的文字也显示了周扬像艾思奇一样对鲁迅20年代中早期内在思想和情绪的不理解,他写道:“这个忠实的民主主义者,目睹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屡次地横遭蹂躏,确曾有过怀疑失望的时候,但那是并不长久的。”[12](P1019~1023)他把鲁迅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怀疑失望”的一面,当作了应该加以克服的缺点以及后人(比如他本人)应该予以辩护的东西。
比艾、周和鲁座文章晚几年发表的洪亮的《鲁迅思想的蜕变》(1941年),则非常详细地对比了鲁迅在与创造社、尤其是与成仿吾论争时前后语气、态度,甚至“意见”之间的差别,从中寻觅鲁迅思想在那个时候“蜕变”的踪迹。虽然作者对鲁迅敬爱有加,但其“创、太情结”在文中还是不时有所流露的。通过列举,他认为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对人和事的态度是发展的,由“多少带有些意气”到“比较客观、中肯”,由“站在整个革命阵营之外,但却巴望革命文学能更完美无缺陷的立场上来指摘革命文学的某些坏倾向”,到“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站在革命文学之内执行自我批判或提供意见以便进行”。洪文还以很多笔墨论述鲁迅思想“蜕变”前后的一贯性,根据斯大林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四大基本法则”,一一对照、寻找鲁迅前期思想中“所孕育”的“许多唯物辩证法的个别因素”,这些因素在他遭遇了新的现实境遇后,便“很快地抛弃了进化论,而接受了阶级论的思想哲学”。[14](P452-455)这里“抛弃了进化论”与鲁座几年前“进一步走向史的唯物论”的表述适成鲜明对比。
尽管不同的观点、指向之间并没有形成正面交锋,但鲁座的《思想家的鲁迅》显然与艾、周和洪亮文章不同。鲁文虽然亦在同一话语系统内,但却竭力以“同情的理解”走入对象的复杂性,接近对象自有的逻辑,以揭示鲁迅思想的丰富性。作者认为在鲁迅“前期思想和后期思想之间,并没有横着一道鸿沟”,而是始终有着“它的一贯性和统一性的”。“个性主义和集体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进化论和历史唯物论在他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可以表示不同的阶段,然而他们并非前后脱节的”。作者提供的理由是:“鲁迅思想的发展诸阶段只是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诸阶段之反映。如果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它的前后连续性,那么鲁迅思想发展的诸阶段当然也有他的前后连续性,作为连贯他前后思想发展的主要脊骨的,就是他始终抱定的现实主义。”[11](P1019)
以“现实主义”概括鲁迅思想在当时几乎成为定则,但相互之间却歧异很大。鲁座的“现实主义”与前述王任叔的表述在精神上相通,但表述和解释得却较为清楚有力。这种“现实主义”当然不是通常所说的艺术创作方法,而是一种始终充盈着“生活实感”的思维和实践的能力。这种能力保证了当事者“从生动而丰富的现实中”、“在勇猛而不息的战斗中”,而不是在“书本”里、在权威理论和时尚思潮的追慕中“发掘真理”。作者意欲概括的是一种存在于鲁迅身上的非常独特的东西,这种东西被感觉到了,只是被装进了一个现成的、似是而非的、缺少更为深邃的揭示力的术语里。但可以说,这是当时左翼文化界所可利用的理论资源中最为准确的用语,因为通过具体的阐释,在由瞿秋白开启的既有叙述框架里,“两个鲁迅”正是由其所阐释的“现实主义”一词而被粘合为“一个鲁迅”,粘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使作者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鲁迅思想“差别”这个最为棘手的问题,他这样比喻道:“当然,我们同时不能否认鲁迅思想前后的差异性,正如不能否认中国革命各阶段的差异性一样……”[11](P1019)把各个时期的鲁迅给予历史化和境遇化,正显示着作者对鲁迅的理解并给鲁迅思想以独立性的努力。
不仅如此,对围绕鲁迅而发出的各种声音,包括敌对的右翼及其他各种诽谤者,鲁座也将其主体化,看成自有价值的存在,认为:“当它们从不同的嘴巴里喊出来或者从不同的笔底下写出来的时候,其中的任何一个其实都代表一定人群对于鲁迅的看法,并且多少是带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不论它们是从哪一方面发出来,也不论其发出时的动机怎样,决不能简单地看作一种私自的感情冲动”。[11](P1025)显然,《思想家的鲁迅》一文反映了当时左翼文化界中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其表现就是在坚持自身理论立场时,也给对象以主体性,而不是予以随心所欲的客体化。这是不同于绝对主义的另一种思维逻辑,也呈现了中国左翼文化在发展趋势上的多重可能性。
1936年至1941年,左翼阵营内部关于鲁迅思想“转变”的公开争论和潜在分歧,并未在现代思想史、甚至鲁迅研究中留下深刻的痕迹,但其中所暗含的两种不同的潜在焦虑,却已经预示了稍后几年左翼内部围绕同样问题的公开冲突,也留下了潜藏于左翼文化内部的两种不同发展脉络的蛛丝马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