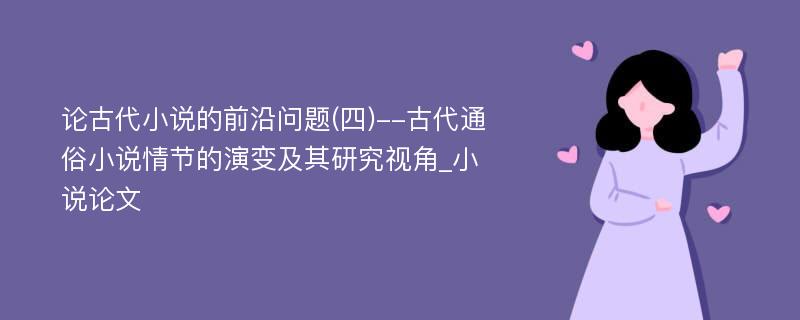
古代小说前沿问题丛谈(之四)——古代通俗小说情节衍变及其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丛谈论文,古代论文,小说论文,通俗论文,之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常来说,小说情节衍变乃源自作家本人的艺术修改,包括增、删、调、改等等,研究者通过不同版本的文本比较,可以探知小说家在思想情感、创作水平及文学观念诸方面的变化轨迹,这在西方小说或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均不乏其例。但是,古代通俗小说的情况则有些特殊。一方面,相当数量古代通俗小说文本的生成,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创作,而是对“本事”或旧作的演绎改编,且整体上处于较为仓促、草率的状态,商业化色彩甚是浓厚,往往未经作者认真修改,即匆忙刊刻行世,清代小说戏曲家李渔曾云:“予终岁饥驱,杜门日少,每有所作,率多草草成篇,章名急就,非不欲删,非不欲改,无可删可改之时也。每成一剧,才落毫端,即为坊人攫去,下半犹未脱稿,上半业已灾梨”(《闲情偶寄》卷二《词曲部》下),其创作状态便颇具代表性。另一方面,即使有部分小说家的“创作”较为精心,也曾进行过一定程度的修改,然因年代久远,再加上古代小说始终处于不登大雅之堂的地位,文献保存情况相对较差,故迄今已难找到诸如“初稿本”、“第一次修改本”、“第二次修改本”、“定稿本”等可供比对且成系列的版本资料,此类研究自亦无法有效地开展。
当然,例外总是存在的。譬如清代小说《红楼梦》,仅目前已知的早期抄本就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本”、“舒本”、“列藏本”、“梦本”、“郑本”、“杨本”、“蒙本”及近年发现的所谓“卞藏本”等十余种,它们传抄于不同时期,保留着《红楼梦》在曹雪芹创作修改的不同阶段的某些文貌。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就曾通过上述抄本的比对,发现了不少有意思的现象,颇具学术启发性。《红楼梦》第三十四回叙宝玉挨打后,宝钗前来探望,袭人告诉她被打原因,其中涉及薛蟠,宝玉怕宝钗担心,忙止住袭人,接着有一段宝钗的心理活动:“但你固然怕我沉心,所以拦袭人的话,难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恣心纵欲,毫无防范的那种心性。当日为一个秦钟,还闹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厉害了。”这段文字诸本均同,审其文意,则小说在第三十四回之前应当有描述薛蟠因秦钟而大闹的情节。然而,现存《红楼梦》诸版本均无此情节,秦钟始出于第七回,死于第十六回,他与薛蟠最近的关系,也不过是在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中一前一后、同回出场而已。那么,宝钗的心理活动岂非落空了?刘世德在“舒本”第九回找到了解开疑问的线索:“舒本”第九回末尾文字与其它诸本皆不同,叙贾瑞在宝玉压制下,被迫向秦钟认错,但心中“遂立意要去调拨薛蟠来报仇,与金荣计议已定。一时散学,各自回家。不知他怎么去调拨薛蟠?且看下回分解”,据此可以推知,曹雪芹初稿第十回的情节,应是叙述薛蟠“为一个秦钟,还闹的天翻地覆”,但这一情节在后来“增删”时被删去了,却又因一时疏忽,没有对第三十四回中的宝钗心事做出相应的修改,遂造成了一个小小的情节漏洞。事实上,薛蟠、秦钟皆属次要人物,如果对他们着墨过多,将会造成对中心人物及小说主线的干扰,曹雪芹的删改无疑是高明的;而研究者借助版本比勘,得窥小说名著生成、修润的若干细节,又是何等幸事!只可惜这样的例证,在古代小说研究史中实在太少了。换言之,因小说作者修改而造成的情节衍变,实际上并非古代通俗小说情节衍变的主体。
资料显示:古代通俗小说的情节衍变,主要产生于作品编撰阶段的“改编”环节以及传播阶段的“翻刻”环节。先来看前者。如上文所述,古代通俗小说文本的编撰,大多带有鲜明的改编色彩:或是小说对笔记杂著所载“本事”的演绎,或是白话小说对文言小说的扩写,或是文人拟话本对“宋元旧种”的新编,或是章回体小说对戏曲、弹词、宝卷、唱本及道情等其他俗文学作品的改造,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改编过程中,由于受到文本体制、作家文学趣味和道德观念、读者欣赏口味以及时代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新编撰的小说文本与被改编对象之间,往往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情节衍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节衍变乃伴随着作品之编撰而不是修改或流传而产生,具有某种“先天性”,与西方小说或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情况大不相同,蕴含着独特而又丰富的学术信息。
古代通俗小说“改编”环节的情节衍变,表现形式颇为多样,其中最为常见者则有以下两种:其一,增饰新人物,引出新情节。譬如明嘉靖洪楩清平山堂刊本《六十家小说》所收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叙宋代词人柳永在京风流倜傥,后就任余杭县令,筑玩江楼以自取乐,欲与妓女周月仙交好,遭到拒绝,遂暗遣舟人强奸月仙并以此相要挟,最终“两情笃爱”云云。拟话本《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收录于《古今小说》第十三卷)乃据《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改写而成,作者冯梦龙先后增添了四位人物,引出一系列相应情节:首先是“黄秀才”与“刘二员外”,叙周月仙与黄秀才两情相悦,刘二员外欲与月仙欢会,遭到拒绝,遂暗遣舟人强奸月仙,以为要挟,柳永闻之,出资替月仙赎身,并撮合其与黄秀才的婚姻;第三位是歌姬“谢玉英”,作为柳永之红颜知己,贯穿小说始终,叙述谢氏因喜爱柳词而与柳永相遇相知,历经相约失约,最后重逢京师的爱情故事;第四位是权相“吕夷简”,叙柳永外任期满返京,遭吕氏排斥而被罢官。上述增饰的人物情节,彻底颠覆了柳永的文学形象,他已从旧作中“才子”加“流氓”的形象,转化为集风流、才华、情义及气节于一身的文人典型,这些情节衍变,既是拟话本小说篇幅扩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也寄托着小说作者——与柳永同属风流落魄文人之冯梦龙的自我欣赏与身世慨叹。再譬如晚明西湖渔隐编撰的拟话本集《欢喜冤家》,其第七回《陈之美巧计骗多娇》与第二十回《杨玉京假恤孤怜寡》,分别根据万历张应俞所撰文言小说集《杜骗新书》卷三“婚娶骗”《因蛙露出谋娶情》、卷二“盗劫骗”之《公子租屋劫寡妇》改写而成(参拙文《〈欢喜冤家〉小说素材来源考》,收录于拙著《古代小说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58页),仔细比对文本,《欢喜冤家》所增主要就是叙述男女主人公“云雨偷欢”、“兰汤午战”等细节,此类情节衍变亦多见于其他明清艳情小说,显示了编撰者对市民阶层阅读口味的商业迎合。
其二,调整情节重心,改写故事结局。譬如明代拟话本小说《郑节使立功神臂弓》(收录于《醒世恒言》第三十一卷)乃据元代话本《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改写而成,《新编红白蜘蛛小说》属于“烟粉灵怪”类,其情节重心在于郑信与红白蜘蛛精怪的遇合故事,故人精离别之后的文字仅有两百余字,只是对郑信的结局略作交代便匆匆告止。而冯梦龙改编后的《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其情节重心已转移至凡人发迹变泰故事,故人精留别之后尚有大量文字,详细叙述了郑信依靠“神臂弓”建功立业的全过程。如果说《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与《新编红白蜘蛛小说》之间的情节衍变,乃体现了小说作者文学趣味的变化的话,那么,清代小说《桃花扇》与戏曲《桃花扇》之间的情节衍变,则完全受制于文学之外的因素。《桃花扇》传奇创作于清康熙中期,其时反清复明思潮虽已不像康熙初期那样风起云涌,但仍未彻底平息,部分汉族文人开始反思明朝覆灭的历史原因,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动机是:“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孔尚任《桃花扇小引》)故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只是传奇《桃花扇》情节结构的一个部分,其它诸如福王朱由崧的昏庸荒佚,马士英、阮大铖的结党营私、倒行逆施,江北四镇的跋扈不驯、互相倾轧,复社文人的孤芳自赏,史可法的才能短绌、优柔寡断,左良玉的心胸狭窄、意气用事,皆是孔尚任精心设计、着意展开的情节;为了凸显国破家亡的历史主题,作者甚至不惜撕裂作为爱情信物的“桃花扇”,让劫后重逢的侯李两人再度分离,双双醒悟入道。然至乾隆时期,社会国富民安,易代伤痛早已抚平,因此,在翰香楼刊本《桃花扇》小说的编撰者看来,文学作品已无须承载历史的伤痕,他调整了桃花扇故事的情节结构,将侯李爱情确立为《桃花扇》小说的唯一重心,删去《桃花扇》传奇中与爱情无关的“哭主”、“争位”、“和战”、“移防”、“闲话”、“孤吟”、“归山”、“会狱”、“劫宝”等出情节,小说结局也改写为:侯李两人破镜重圆,“一家完聚。朝宗也无意功名,因香君生子三人,只在家中教训儿子,后来俱各自成名,书香不绝。朝宗与香君俱各寿至八旬有余而终。”很显然,正是不同时期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和差异,才导致《桃花扇》小说与被改编对象——《桃花扇》传奇之间产生了令人注目的情节衍变。
再来看“翻刻”环节的小说情节衍变。由于古代中国缺乏版权意识和保护版权的法律,通俗小说文本刊行之后,时常会遭遇其它坊肆的盗印翻刻,而坊肆为了应对商业竞争——这种竞争既发生于区域之间,譬如明代的福建建阳地区与江南地区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地区的众多书坊之间;为了能给自己出版的小说找到刺激销售的“卖点”,他们一方面在书籍形式上(包括图像、注音、释义、圈点、评林等)费尽心思,标新立异;另一方面则运用“插增”手段,改变小说文本的情节内容,使之区别于其他众多版本,并借“全本”之名吸引读者眼球。这已经成为明清时期通俗文学出版的惯常现象,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及《西游记》等小说名著的早期流传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譬如现存《三国志演义》刊本有数十种之多,其间的学术关系颇难梳理,后经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终于找到了若干划分版本系统的参照标准,包括刊刻区域、周静轩诗及史书故事的插入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是属于情节衍变性质的“花关索”及“关索”故事,日本学者金文京将现存《三国志演义》版本划分为六大系统:“没有花关索、关索故事的版本”、“有花关索故事的建阳刊本”、“有关索故事的建阳刊本”、“有关索故事的江南本”、“有花关索、关索故事的版本”以及“毛宗岗本”(参金文京所撰《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三国志演义》,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308页);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花关索”、“关索”故事,非《三国志演义》祖本所原有,乃属坊肆“插增”所致,故目前所知刊印时间最早的嘉靖元年(1522)张尚德序刊本及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刊本,均无“花关索”、“关索”之名。再譬如万历时期出版的《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水浒全传》,也以“插增”田虎、王庆故事为卖点,以区别于其他众多的、没有这一情节的《水浒传》版本;而且,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藏插增本残本卷二十一书名题作“新刊全相淮西王庆出身水浒传”来看(参马幼垣《现存最早的简本〈水浒传〉——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收入其《水浒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1—88页),或许,田虎与王庆故事情节乃先后“插增”至《水浒传》之中也未可知。此外,《西游记》第三十六至三十九回的“乌鸡国故事”、第五十回至五十二回的“莲花洞”故事等情节,也有后来“插增”的痕迹(参侯会《从“乌鸡国”的插增看〈西游记〉早期刊本的演变》、《试论〈西游记〉“莲花洞”故事之晚起》等文,收入其《〈水浒〉〈西游〉探源》,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190、209—218页)。
“插增”之外,书坊基于节约成本、追求速刊的考虑,对情节文字进行不同程度的删削,也会导致同一部小说的不同版本之间产生情节衍变。古代通俗小说版本有“繁本”与“简本”之分,在一般情况下,“简本”乃据某一“繁本”删削而成,但是,由于文献传承的偶然性,现存“简本”与现存“繁本”之间,未必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这无疑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譬如《西游记》的两个明刊简本——朱鼎臣编《西游释厄传》及杨致和编《唐三藏出身全传》与今存繁本明世德堂刊本之间、《水浒传》今存简本与繁本之间的学术关系,便是古代小说研究中迄无定论的疑难问题。至于“唐僧出身故事”在世德堂刊百回本《西游记》中缺失的具体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它显然与上述书坊为节约成本而施加的删削不同,究竟是因底本残缺,还是书版毁失?或许是出于《西游记》文学重心转移的需要,因为,如果小说从以唐三藏为中心转向以孙悟空为中心的话,那么花费数回笔墨来详细介绍唐僧的出身及家世,就不是必需的了。
“插增”或“删削”小说情节的行为,多数情况下乃由书坊策划组织实施,其内在驱动力则源自对商业利益的追逐。不过,坊肆有时也会为了某些非商业原因,对小说现有人物情节进行改造。譬如明万历时期建阳书坊三台馆(又名“双峰堂”)主人余象斗,在推出《京本增补校正全像水浒志传评林》时,出于维护同宗人物的私心,竟将底本中一笔带过的配角“余呈”,大加改写,插入了包括余呈临阵斩将、失手被俘、不肯跪降、英勇就义、宋江哭祭等情节(参马幼垣《牛津大学所藏明代简本〈水浒〉残叶书后》,收入其《水浒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12页),读来令人哑然失笑。究其动机或在于:余象斗曾因科举落第而无奈从事出版业,光宗耀祖的梦想无法实现,遂借《水浒传》中“余呈”的英勇事迹,聊抒胸中磊块,联想到他还曾在所刊书籍内(譬如《万锦情林》内封页),刻印上自己端坐于类似衙门的“三台馆”中、童子执帚、婢女献茶的图像,这位编撰出版了多种通俗小说的书商型小说家,虽有些自恋,倒也不失个性。有意思的是,余象斗对“余呈”的增改文字,成为《京本增补校正全像水浒志传评林》版本的特殊标记,凭借这一标记,可以核查出诸如“映雪草堂本”、“藜光堂本”、“刘兴我本”、“李渔序刊本”、“《二刻英雄谱》本”、“《汉宋奇书》本”等多种《水浒传》简本,实皆源自余氏《水浒志传评林》(参马幼垣《现存最早的简本〈水浒传〉——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第86页)。此恰如“花关索”、“关索”故事成为梳理《三国志演义》版本系统的标记一样,因坊肆“翻刻”而产生的情节衍变,既造成了小说文本的某种混乱,但如果运用得当,也可转化为小说成书过程以及版本传承研究的有效的辅助手段。
此外,关于古代通俗小说的情节衍变及其研究,尚有几点值得关注:
首先,古代通俗小说的编撰方式与传播过程,均有不同于西方小说及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特殊之处;其情节衍变的产生,与小说作品的题材来源、成书过程、编撰者之文学及道德观念、文本体制、时代文化背景、出版商业竞争、刊刻者趣味、阅读者口味等文学内外因素密切相关。故借助对于古代通俗小说情节衍变的深入考察,事实上可以展开多项学术课题的研究。
其次,倘若将视野略加扩展的话,中国俗文学品种丰富,除小说戏曲之外,尚有弹词、宝卷、鼓词、唱本、道情、子弟书、木鱼书、二人转等类,遗留下数量可观的俗文学作品,它们彼此之间曾经发生过复杂的交叉影响,既有小说对其它文体文本情节的改编利用,也有其它文体对小说文本情节的改编利用(需加说明的是,这种“改编”实际上也会产生情节衍变,但对于小说来说,只是一种被动形成的衍变,故本文未予展述);同一个故事、尤其是那些起源较早的故事(譬如宋人《醉翁谈录》、《青琐高议》等书所载各篇故事),在不同的俗文学作品中留有形式多样、繁简不一的文学表现。因此,追踪这些故事的渊源流变,比较不同文体在演绎同一故事时存在的种种差异,无疑可以带给小说研究者十分丰富的学术思考,开启颇为广阔的学术空间。
最后,毋庸赘言,关于古代通俗小说情节衍变的考察,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版本及文本比对基础上,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足够的耐心和细心。目前古代小说研究正面临若干困境:新文献的发现越来越难,新理论的探索不尽顺利;文化研究多流于空疏,艺术赏鉴则颇乏新意;名著研究举步维艰,非名著研究的价值又似乎未获学界公认。有鉴于此,进一步拓展、加强包括情节衍变在内的古代小说版本及文本之细致研究,或许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学术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