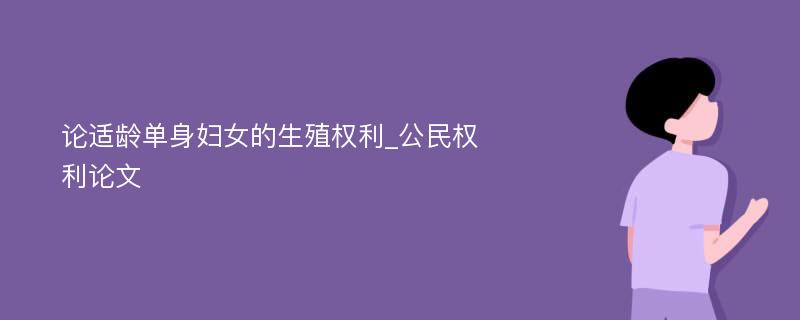
论适龄独身女性生育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11月1日,吉林省人大通过了该省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吉林省《条例》),该条例第30条第2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根据我国目前宪政体制安排,笔者认为此款规定属于广义违宪,也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1 违宪性审查:生育权权利主体认定
我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法律制度方面表现为,只有一部宪法,只有一套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维护宪法的权威和法制的统一是国家的基本职能。
生育权是公民最重要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对任何一项公民权利而言,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是其重要的构成性部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于生育权而言,权利主体一直是明确的,即:“夫妻”或者“作为夫妻的公民个人”是缔结婚姻的男女,同时双方在决定生育的权利上处于平等的地位。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在中国,所谓“生育”就是计划生育,法律不认可任何形式的非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属于国家强行法范畴,夫妻是生育权的权利主体,也是计划生育的义务主体。
在立法惯例上,1982年计划生育被写入现行宪法以后,在没有人口与计划生育基本法律的情况下,为规范公民生育行为,根据宪法的原则规定与国家的政策要求,国家计生委推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通过地方立法,制定了适用于本行政区域的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其中,新疆、西藏是以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这些地方法规(规章)结合本地实际有很多因地制宜的变通规定,但也都有一个底线,就是禁止非婚生育,违反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各地的变通规定主要针对二孩(多孩)生育的条件、生育数量、生育间隔等方面,不涉及生育权权利主体,这可以说是计划生育地方立法的“陈规”。所以,在中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将生育——计划生育的主体限于作为夫妻的公民个人,是中国宪政体制的要求,是授权立法的惯例,也是计划生育工作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经验。
2001年12月29日,根据《宪法》的规定并总结了各地计划生育地方立法的经验,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对我国多年计划生育地方立法经验予以肯定,特别在生育权的界定、生育政策的宏观调控方面既没有放宽,也没有收紧。根据法律解释的一般原理和规则,相关条款确认了生育权的权利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只能是夫妻:既然“夫妻”在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那么他们同时也就共同享有相应的权利,而且这样的权利还只能共同共有,不能按份共有。一方在行使权利时应当取得对方的同意或认可,才可以视为共同行使了该项权利。如果适龄独身女性可以单独享有生育权,根据公民享有平等民事权利的宪政精神,适龄独身男性是否也可以单独享有生育权?如何保证生育权的行使?是否也应当在该条例中予以规范?
根据我国的宪政体制安排,在国家制定一个基本法律以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上位法的授权,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的地方性法规。我国的宪法实践、立法惯例和立法法的授权条款规定,授权立法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其中包括尊重立法惯例、自律立法和审慎立法。任何一级地方权力机关根据上位法的授权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应当遵循宪法和上位法的基本原则。同时,还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被授权机关要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它机关。地方立法机关应该明确其立法适用范围的限制。省级人大作为次级国家权力机关,无权就某些特殊法律事项进行立法。我国《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对于“民事基本制度”这样的法律事项只能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在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地方权力机关不能越权立法。而适龄独身女性的生育权问题,无疑属于“民事基本制度”范畴。
所以,吉林省《条例》第30条第2款的违宪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违反上位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于2002年9月1日施行以后,根据其授权条款(第18条),地方权力机关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地方性法规。同时,地方性法规的主要功能在于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从《宪法》、《婚姻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相关行政法规分析,有一点非常明确,即婚姻是生育的前提条件,生育权的权利主体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就一直被限定为“夫妻”或者“作为夫妻的公民个人”。吉林省《条例》赋予适龄独身女性生育权,在权利主体的认定上突破上位法的规定,其性质超越了“执行与解释上位法”的授权立法范畴,是超越权限的实质性修改。
其次,违反立法惯例。吉林省《条例》违反了1982年宪法实施到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以来,各地根据上位法授权条款制定地方性法规所遵循的立法惯例。需要强调一点,在法治国家,立法惯例具有上位法的法律地位,被授权立法机关应当予以尊重。同时,该《条例》直接违反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关于“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原则规定,将部分非婚生育行为合法化,属于明显的立法不审慎。
再次,越权立法。适龄独身女性的生育权问题是“民事基本制度”中的重要范畴,属于不应搞地方特色的全国统一制度领域。对于这样重要的法律事务,没有宪法与基本法律的明确授权,任何地方权力机关均不能越权立法。否则,有权机关必然会依据立法法第88条的规定,通过违宪审查机制以超越权限的原由予以改变或者撤消。
2 权利与权利的行使:论生育权的社会负担
吉林省《条例》颁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适龄独身女性生育权问题的讨论。一些同志认为,生育权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民事权利,从民法学角度讲,包括公民生育权在内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对于这样的权利要求国家法律应该认可。有的同志认为,现代法制社会的一个原则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
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适龄独身女性享有生育权不难获得激情的辩护与同情式的理解。然而,权利是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应然与实然、权利与权利的行使等同起来。从权利的构造看,存在着权利与权利行使之间的差别。很多权利只是公民从事某项活动的机会或可能。比如,就业权是公民的一项权利,某公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实现了就业权。如果他没有找到工作,是不是就没有享受就业权呢?这不一定。假如他谋职过程中,因性别、民族、种族等问题,受到歧视,他的就业权可以被认为受到了侵犯。如果只是因专业不对口、薪水不满意等方面原因而未能成功就业,就不能说他没有享受就业权。对于现在的问题而言,如果国家法律在生育权权利主体上做出修改,明确规定适龄独身女性有生育权,但是其行使应当具备其它的法定条件,这矛盾吗?笔者认为,这并不矛盾。问题的实质涉及权利行使的条件与后果问题。在现代社会,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权利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条件、范围和程序。通常情况下,生育权的行使必须以满足某些法定条件为前提,如果条件不满足,虽没有导致生育权的丧失,但却限制了其生育权的行使。在我国,生育权的实际行使往往是与公民的精神健康状况、身体状况、婚姻以及社会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等紧密联系。就生育权而论,一个人只有具备了法定的结婚条件并结婚,其与配偶就生育问题达成合议并实施,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生育权行使过程。事实上,许多意外怀孕的夫妇从知晓受孕到顺利产子过程中,也是一个不断产生分歧、协商合议,再反复,再合议的过程。而每一次协商的失败,都可能导致生育过程中断,而这并不能否认当事人不享有生育权。
其次,从社会伦理的角度看,如果适龄独身女性的生育权获得承认或批准,在现在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公众舆论环境下,她与其将来的孩子将面临的社会、生活压力以及对孩子健康成长的负面影响是难以想象的。社会学实证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从统计学的角度,单亲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是相当不利的。对于这种环境,未出生的孩子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儿童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享受正常的父爱与家庭生活是最基本的权利要求;作为母亲,不能忽略和侵犯未出生孩子的正当权益。在人的生长过程中,家庭承担着重要的抚养、教育功能,作为个人的夫妻或父母必须承担特定的社会义务。1994年9月联合国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与其他联合国法律文件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因此应当予以加强。它有权得到全面的保护和支持。在不同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制度中,存在各种形式的家庭(国际社会对此应予以尊重)”。“所有国家和家庭都应给予儿童以最优先的重视”。一方面,权利是个别化的现象,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适龄独身女性主张自己的生育权是无可厚非的;另一方面,权利又是社会化的,权利不能超越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的制约,同时,社会也要承担公民权利的负担,这也正是国家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对个体权利施以平等而公正限制的理由。
吉林省《条例》颁布以后,该款规定的实施也存在法律障碍。例如,根据国家卫生部门的规定,公民(现在限于适龄女性)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必须三证(身份证、婚姻证、生育证)齐全,未婚者不得接受该技术。同时,截止到2002年11月1日吉林省《条例》生效之日,吉林全省并没有一家医疗机构获得国家卫生部的许可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根据笔者的了解,国家许可8家医疗机构开展此项技术,这些医疗机构分布在江苏、江西、浙江、湖南、湖北、重庆、海南7省(市),这些省(市)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均禁止非婚生育。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假如一个有吉林省户籍的适龄独身女性取得吉林计划生育部门的行政许可到一个禁止非婚生育省(市)的医疗机构接受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所在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该如何判断该行为的法律性质。是适用行为地法(lex loci actus)判其无效,还是适用“属人法”(lex personalis)默许这样的行为。如果是前者,那么吉林省《条例》的该款规定是一个现在“不可能实施的条款”,适龄独身女性的生育梦想是一个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是后者,公民在生育权的享有与行使上会因她们户籍的不同而呈现事实的不平等,从而对宣示自由、平等、公正的宪政体制提出挑战。
3 结语:权利,真正的宪政精神?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已经写入我国宪法。但一般认为,法律的稳定和法制统一是衡量一国法治水平的重要维度。“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单纯地追求所谓的权利本位而漠视具体权利的历史与社会条件制约,或者仅仅为了学术研究范式转换的需要而忽略宪政体制统一与稳定的无上地位,笔者认为这不是“认真对待权利”的负责任的行为。
因为宪政制度是作为人治体制中统治者独断意志的对立面出现的。为了防止立法专权,宪政文本自诞生之日就有独立于立法者意志的内涵和解释空间,公民权利也受宪法文本文意空间的限制而有具体的内容。在宪政国家,人民普遍尊重宪法(法律),推崇宪法,甚至迷信宪法。如果要发展或拓宽公民权利或公共权力,必须根据法定的程序修改宪法或法律,在上位法修改之前,任何公民和机关都可以呼吁权利、评论自己认为不合理的法律条款,但是,这些行为都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这才是真正“认真对待权利”的负责任的现代宪政精神与法治意识。
许多时候,权利无须辩护。但是,在现代法治国家,合法权利只存在于特定的法制体系之中。我们不能通过违反宪政的方法、特别是通过越权立法这种违反程序正义的方法追求所谓的实质正义,这会对一个国家的宪政体制与宪政精神造成颠覆性的损害。
同美国历经200多年发展的成熟宪政体制相比,中国的宪政进化好比正处于幼年期,从1982年《宪法》实施到今天也不过短短20余年的时间。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在这样的时期,对宪政体制建设的最大挑战就是法治意识的淡漠和违宪审查机制的缺位。一个不被最大多数人信奉、没有强力保障的宪法是不可能成为法治国家的制度根基,这可能是吉林省《条例》对中国宪政建设的一点启示。
也许,我们应该把法国哲学家哈耶克的领悟赠与审慎的立法者:“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根据我们的计划行事,是因为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文明社会中的成员都遵循一些并非有意构建的行为模式,从而在我们的行为中表现出某种常规性(regularity),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行动的常规性并不是命令或强制的结果,甚至常常也不是有意识地遵循众所周知的规则的结果,而是牢固确立的习惯和传统所导致的结果。对这类惯例的普遍遵守,乃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得以有序的必要条件,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惯例的重要性,或者对这些惯例的存在可能不具有很明确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