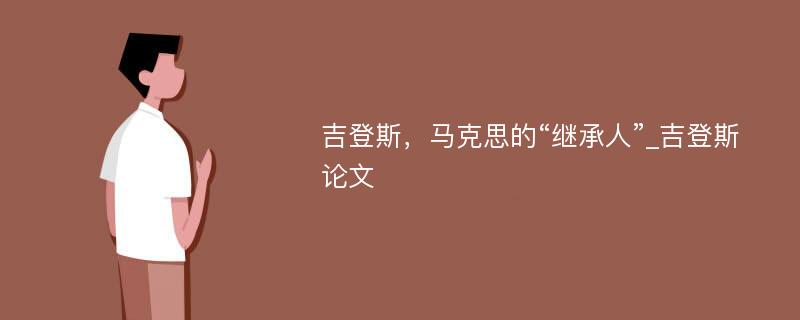
作为马克思“继承人”的吉登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继承人论文,吉登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如德里达所言:“全世界的男男女女们,不论愿意与否,甚至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①在非马克思主义传统出身的当代西方理论家中,或许没有谁能比安东尼·吉登斯更能称得上是马克思的“继承人”:他不仅系统研究过马克思的理论,而且选择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建构了自己的社会理论,并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保持着长期的对话关系。套用德里达的修辞,马克思犹如一个时隐时现的幽灵,始终以某种方式游荡在吉登斯的学术历程中。也因为如此,国内学界颇为热衷于吉登斯和马克思的比较研究。不过,抽象的比较至多只能发现外在的异同,只有回到吉登斯的学术历程中去,他之于马克思的“继承”关系才能得到真实的呈现。
吉登斯反思性批判视域中的马克思
吉登斯的学术历程以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反思性批判为真实起点。在这一工作中,马克思占据了毋庸置疑的中心地位。因为吉登斯认为,正是在与马克思的批评性对话中,涂尔干和韦伯分别阐发和建立了各自的社会理论,从而和马克思一起为现代社会理论奠定了基础。吉登斯的这种观点现在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接受。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英国,它的提出多少有些石破天惊的意味。那时候,英国社会学不仅深受帕森斯传统的影响,而且还保持着帝国主义的“英国特色”,缺乏社会学想象力以及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能力②,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被当做一种无足轻重的异端传统而遭到漠视。
按照吉登斯的自述,他之所以能够超越已然陈腐的“英国特色”来再发现马克思,主要得益于1968-1969年间他在北美度过了意义非凡的两年。③当时,美国新左派运动正值高潮,各种激动人心的革命性事件不断发生。面对这一切,作为当时社会学主流的帕森斯传统却无法给予有说服力的解释。这在让吉登斯感受到强烈困惑的同时,于新左派运动的漩涡中心发现了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影,促使他开始关注、思考社会理论的起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亲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社会学家汤姆·巴特莫尔的工作发挥了一种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巴特莫尔是最早关注、研究马克思社会学遗产的英国社会学家。1956年,他和法国“马克思学”家吕贝尔合作编辑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文选》,向英语世界读者第一次系统展现了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1963年,他独立编译出版了影响巨大的《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使英语世界的一般读者了解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成为可能。1969年,他出版《卡尔·马克思》一书,以社会学思想为主线对马克思进行了传记描述。1968年,当吉登斯前往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时,巴特莫尔已经辞去该系的系主任(1964-1967年)职务返回英国。尽管如此,吉登斯还是强烈感受到了巴特莫尔的存在,并从后者的工作中得到了直接的启迪。
虽然吉登斯直接受益于巴特莫尔,不过,他在197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阐发,显然要比巴特莫尔的类似工作(即1975年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1985年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④)更加成功。这种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吉登斯展现出了更强的理论化意愿。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后,随着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和现象学等欧陆哲学思潮的大举进入,英国的学术文化发生了显著转变。在不完全放弃经验主义传统的同时,人们也开始追求更高程度的理论化。这种需求在年轻一代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如果说巴特莫尔坚守“英国特色”,努力把马克思诠释为一个实证的“社会学家”,那么,吉登斯则顺应潮流变迁,成功建构出一个更加符合时代期待的“社会理论家”马克思。其次,吉登斯更加成功地勾画出了其他社会理论家与马克思之间的对话—“继承”关系。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看来,涂尔干、韦伯等人力图否定或取代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但实质上不过是以资产阶级的方式回应了马克思,并被马克思驳斥或同化。对于这个问题,吉登斯既没有像巴特莫尔那样直接予以肯定,也没有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是在一种开放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图景上进行批判的再诠释,从而比较客观、完整地揭示出了双方的对话—“继承”关系。最后,吉登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一种能够得到更多人认同的中间化立场。吉登斯力图同情地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但又坚决拒绝“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既肯定马克思的学说仍然具有当代相关性,但又始终强调它根本上是一种19世纪思想,因而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他这种比较超越的中间化立场得到了同时代人的共鸣。
历史地看,《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有效地颠覆了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圭臬的帕森斯传统的社会学史叙事,将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确立为社会理论的三大经典传统,同时也将自身确立为人们了解这三大经典社会理论的标准读物。一开始,该书获得的巨大成功还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学术上的成功。不过,随着吉登斯现代性理论体系的建构完成及为人所知,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学术成功所具有的思想性质:该书不仅成功追寻了“巨人的足迹”,而且在事实上帮助吉登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不想超越前人的学者也不是一个好学者。但是,在追寻“巨人的足迹”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人最终都不得不依旧生活在“巨人的阴影”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攀上“巨人的肩膀”。吉登斯何以能够幸运地做到这一点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不仅倾听巨人的“言”,而且关注巨人所走的“路”,从而使得他有可能像巨人那样并接着巨人“往下说”。因此,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吉登斯非常注意总结、反思马克思的理论道路,这促成他后来事实上选择了和马克思一样的创新道路。
在吉登斯看来,理论与实践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最根本特点。“马克思构思自己的著作,是旨在建立一个实现特定实践的平台,而不仅仅是对社会进行学术研究。”⑤对马克思来说,所谓“特定实践”就是1848年之前在西欧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德国的革命问题。这个“特定实践”从两个方面影响了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一方面,“德国的‘落后’成为马克思早年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性问题”⑥。马克思的著作为什么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核心?又为什么不遗余力地揭示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及其内在崩溃规律?说到底,因为马克思是以当时德国的落后性为自己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另一方面,西欧资本主义成为马克思建构社会形态(社会类型)理论所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这正可以解释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描述为什么并不具有普适性,以及他为什么更关心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非封建主义的性质本身。
吉登斯还发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是马克思理论研究最具魅力和当代价值的地方。借助于同时代人研究马克思的杰出成果,吉登斯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其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时期所确立的那些哲学主题,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发展而来的人类渐进性的“自我创造”观念。⑦从一个令人振奋的观念到一个令人震撼的理论体系,吉登斯注意到,马克思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同时代西欧的思想文化成果进行了“强有力的综合”,“从而以一种连贯的方式将英、法、德三国的不同经验和认识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又为从理论上解释这些国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上的差异提供了基础”。⑧一句话,吉登斯近似于认识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是马克思所开辟的理论创新道路。⑨
再思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
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之后,吉登斯对涂尔干、韦伯等其他古典社会理论家以及作为社会学方法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同样深入地展开了反思性批判。在此基础上,他建构出了作为方法的结构化理论,并初步划定了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认识框架。由于相信“对于任何试图理解18世纪以来横扫整个世界的大规模变迁的人来说,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仍然是一个必要的核心”,吉登斯决定通过批判历史唯物主义来呈现自己的“历史解释的某些替代性因素”即结构化理论⑩,继而建构出自己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三部曲陆续出版后,吉登斯得到了西方主流学术界的高度赞誉。按常理,吉登斯的这种成功应当遭到欧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激烈批判才对。可实际情况是,当时欧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反应不仅相当平和,而且比较积极。例如,主要致力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问题研究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赖特认为,这种批判属于严肃的学术交锋,值得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认真研究。(11)在具有托派背景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柯林尼库斯看来,吉登斯的批判与超越尽管本质上是失败的,但它却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置之不理的。(12)这说明,吉登斯的批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得到了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尊重。那么,吉登斯的批判何以能够受到理论界的普遍尊重呢?
首先,这是因为吉登斯的批判具有相当坚实的实践基础。吉登斯是一个修辞学大师,擅长用复杂的新名词来描述简单的事实。不过,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全部力量来源还是在于他力图让同时代人去承认的事实本身,即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变化,以至于历史唯物主义更多地展现出自身不能直接适用于当代的“19世纪时期的思想特征”。具体地说,吉登斯认为,第一,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变得空前复杂,经济、政治、军事、监控以及认识、情感、心理等诸多宏观、微观因素都参与其中,并且都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发挥决定作用;第二,随着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变化,社会变迁具有了更强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它们“都取决于不同的环境因素和事件的关联,这种关联的性质因各种具体情境而异”(13);第三,普普通通的个人的主体性日益增强,他们对社会再生产过程和社会变迁的影响也日益增强,以至于他们的理想性追求似乎具有可以左右社会发展前途的能力。不管马克思主义者是否愿意承认,这些变化都客观地存在着,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一种不容忽视的挑战或者期待。
其次,这是因为吉登斯的批判包含许多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也都认同的观点。“滤合式建构”是吉登斯自身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14)其实,这种“滤合式建构”同样也存在于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中相当数量的批判观点都可以从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找到某种形式的来源或灵感。在这个方面,吉登斯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吸收尤其容易得到指认。择其易发现者说,第一,1956年以后,汤普森、威廉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前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中的经济还原论倾向,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仅仅是一种隐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因素都有可能发挥客观决定作用,这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了长期而持久的影响(15);第二,在1974年出版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16),安德森通过类型学的分析比较,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具体化,有效地纠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中的目的论倾向;第三,在1978年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中,柯恩从功能解释的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当代阐发(17),有力地增进了人们的理解;第四,20世纪60年末至70年代末,影响巨大的“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的焦点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及其自主性问题。(18)
最后,这是因为吉登斯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建设性。与许多非(反)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吉登斯的批判是以建设为目的的,即在批判、“扬弃”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他还力图提供一种新的方法用于认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结构化理论。关于结构化理论,学术界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不能否认的是,它终究为理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图式,尽管这种图式本身并不完美。
承认吉登斯的批判值得尊重,并不意味着他的批判就是正确的,更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被动接受他提供的替代性方案。事实上,多年以来,吉登斯的批判之所以能够基本保持未经触碰的状况,归根结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像吉登斯一样,在观念上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束缚,以至于无法自信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作为后现代主义风行的一个历史见证人,伊格尔顿指出,作为一种思想风格,后现代主义“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换句话说,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做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者释义,这些文化和释义孕育了对于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份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怀疑”(19)。这种看似非常激进的认识论,实际上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政治退却。(20)它的盛行以及经典思想的崩溃,主要是1968年学生运动“政治失败的后果”(21)。
透过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鞭辟入里的剖析,回过头再看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就比较容易发现其中过犹不及、似是而非之处。首先,就本质主义的还原论思维确实存在着把事物的某一种性质永恒化和绝对化的倾向而言,吉登斯反对(生产力、经济、阶级)还原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为了肯定其他因素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迁中所具有的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否定生产力、经济、阶级所具有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或者说本质地位,从而在事实上滑向了否定本质的客观存在的极端。(22)其次,就其抵制历史目的论而言,吉登斯反对进化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当他因此否定历史发展中的连续性时,就倾向于“把历史视为一件具有持续变动性、极为多样和开放的事物,一系列事态或者不连续体,只有使用某种理论暴力才能将其锤打成为一个单一叙事的整体”,这样一来,真实的历史过程被解构,“变成了一个当前事态的星系,一个永恒在场的群组,它根本就不能叫做历史”。(23)最后,吉登斯反对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捍卫人类作为理性行为者的主体地位(24),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主义缺陷特别容易把行为者理解为社会系统总体的被动产物,可这很有一点掩耳盗铃的意思,因为“虽然我们可以忘掉总体性,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它不会忘掉我们”(25)。
吉登斯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
尽管吉登斯坚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显著的“19世纪时期的思想特征”,因而不能直接适用于当代,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事实上选择了和马克思一样的理论发展道路,力图通过“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来达成自己的理论创新。应当讲,《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之后,吉登斯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的理解日益深刻,践行也日益自觉,“联盟”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结出的理论成果也随之不断丰富。最终,他跻身现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之列。然而,无论怎样高度评价吉登斯的成就,都必须看到:吉登斯始终没有达到马克思那样的高度,为当代思想提供出真正不可超越的东西;不仅如此,与同样关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变迁、同样践行“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的哈贝马斯相比,吉登斯理论成果的持久影响力也要逊色不少。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过,吉登斯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本身存在的缺陷是不应忽视的。
首先,吉登斯的“联盟”缺乏真正的哲学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它必须能够发挥引领世界发展的作用,使“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26)。只有与这种真正的哲学“联盟”,社会科学才能参与到塑造时代精神的伟大事业当中,做出符合历史期待、具有持久价值的理论创新成果。与当代西方其他社会学家相比,吉登斯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社会理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哲学基础,即从马克思那里继承、“改造”而来的“人类创造历史”命题。在《社会的构成》的序言中,他明确指出:“本书其实是对马克思那里时常被引用的一段名言的深切反省。他指出,‘人们(或者让我们直接用“人类”这个词)创造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这话说得不错,他们就是这样创造着的。”不过,他同时认为:“可当我们把这些表面上没有什么毛病的见解运用到社会研究中去时,引发出的问题又是多么的纷繁复杂!”(27)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对马克思的命题进行了当代“改造”:第一,用抽象的“行动者”取代具有阶级色彩的“群众”;第二,以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把现代性(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确立为历史发展的实际终结之处;第三,用“行动”与“结构”的相互作用“更新”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一句话,吉登斯对马克思的命题进行了犬儒主义的改造,其实质是否定根本性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以诉诸恐惧的方式诱导人们认同、接受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放弃改变世界的尝试甚至是想象。正因为如此,他明确表示:“今天,我们必须与天命论决裂,不论它采用的是什么方式。我们不接受资本主义孕育着社会主义的观点,也不接受有可以拯救我们的历史能动者的观点,不论它是无产阶级的还是其他阶级的,更不接受‘历史’有任何必然方向的观点。我们必须承认风险就是风险。……我们必须承认从人为风险到外部风险没有回头路可走。”(28)试想,以这样的哲学观念为基础,吉登斯怎么可能为已经迷失航向的时代重新确定正确的方向呢?
其次,吉登斯的“联盟”在学科结构上存在缺陷。吉登斯的理论视野非常开阔,广泛涉猎并汲取了当代很多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成果。这使得他能游刃有余地发现并言说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很多新变化,有效满足人们的知识需求。不过,由于最初的学术路径依赖,吉登斯显然更关注并愿意吸收那些与个体、心理、微观有关的理论成果,而对某些宏观的社会科学成果特别是经济学成果关注不够。正是这种结构性的缺陷导致他在事实上未能对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变革及其社会效应形成完整准确的理解,容易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仅仅在此时此地才具有重要性的社会因素所吸引,从而忽略被这些因素所覆盖、遮蔽起来的生产力、经济基础之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而马克思以降的思想史表明,经济学在研究、把握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具有无可取代的基础性地位。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经济基础对社会历史发展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9)这意味着,如果不弄清楚现实在经济层面所发生的变化,就不可能真正弄清楚现实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乃至个体心理等其他层面的变化。
最后,吉登斯的“联盟”成果未能获得充分的哲学提升。由于吉登斯以后现代主义的方式看待“理论”,否定“理论”“必须能够用可以通过演绎而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法则或概括来表述”(30),因此,他拒绝像同时代绝大多数有世界性影响的社会理论家那样,对自己的研究结论进行高度抽象化的理论概括和论述,以使之更具哲学意味。结果,在建构、表述自己的理论成果时,他倾向于以折中主义的方式对各种因素、各种维度或各种可能性进行面面俱到的阐述,而不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也就是说,为了规避本质主义的危险,他矫枉过正地牺牲了理论的明晰性、深刻性和普遍性。最终,人们不再或者不愿像对待哲学那样严肃、认真地对待他的理论。对于吉登斯本人而言,这或许算得上是求仁得仁;但对于其理论的传播和接受而言,则肯定不是一件好事。
①Jacques Derrida,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New York:Routledge,1994,p.91.
②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111页。
③Anthony Giddens and Christopher Pierson,Conservation with Anthony Giddens: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40~43.
④参见巴特莫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卢汉龙等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巴特莫尔《现代资本主义理论》,顾海良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⑤⑥⑦⑧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忠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3、23、4页。
⑨参见张亮《“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开辟的道路》,《江海学刊》2009年第2期。
⑩(24)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6页。
(11)E.O.Wright,"Giddens's Critique of Marxism",New Left Review,138,1983.
(12)Alex Callinicos,"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 Critique",Theory and Society,14,1985.
(13)(27)(30)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2、40~41、37页。
(14)“所谓滤合式建构,就是在反思现存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吸收符合自身理论需要的因素,服务于自身理论建构的目的。”参见郭忠华《现代性理论脉络中的社会与政治:吉登斯思想地形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15)参见张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哲学研究》2012年第6期。
(16)参见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7)参见柯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18)参见刘力永《“普兰查斯和密里本德之争”的历史真相及其价值》,《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5期。
(19)(20)(21)(22)(23)(25)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8~19、28、119~120、56、14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28)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标签:吉登斯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