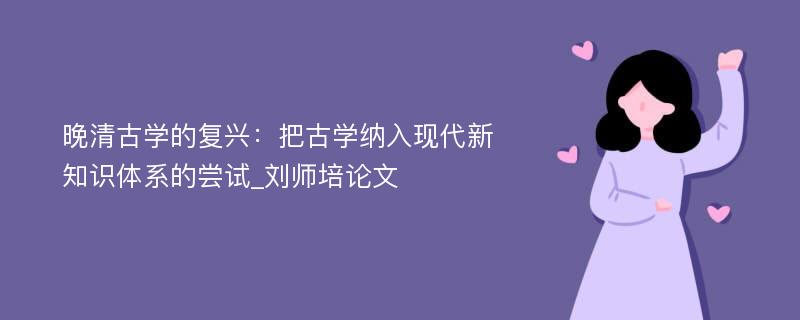
晚清“古学复兴”:中国旧学纳入近代新知体系之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旧学论文,晚清论文,新知论文,中国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9-0062-10
中国学术纳入近代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是很复杂的过程。接纳西方学科体制,仅仅是将中学纳入近代学术体系的开始;按照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编目中外典籍,也是中学纳入西方近代知识系统之初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及其知识系统,要完全纳入近代西方分科式之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中,必须用近代分科原则及知识分类系统,对中国学术进行重新整合。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国粹”、“复兴古学”过程中,开始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初步整理,尝试用近代学科体系界定“国学”,实际上肇始了对中国学术遗产进行发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正是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不断进行整理和整合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其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之新知体系中(注:本课题已有之成果,参见姜义华:《章太炎评传》,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李帆:《刘师培与中西学术》;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争论》等。这些著作重点讨论了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的历史轨迹,并对晚清古学复兴之背景作了深刻揭示。然而,从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之角度看,晚清古学复兴是中国学术转型之关键所在,尤其是清末民初之“整理国故”运动,对近代中国学术转型起了决定性作用。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点对晚清“整理国故”情况作深入而详细之分析,从“以中学比附西学”、“以西学框定中学”两条线索,探讨中国传统学术纳入近代新知体系的历史轨迹。)。本文仅限于对晚清学者整理中国旧学之情况略作梳理与分析,以揭示中国学术纳入近代西方新知体系之历程,而对五四时期“整理国故”运动则留待他文专论。
一 以西方新理新法治旧学
西学输入中国后,许多有识之士将研究兴趣从中国经史之学转移到西方近代新学上,接受了西方近代新知、新理、新法。以刚刚接受之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以适应近代学术演进之大势,成为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林白水定《杭州白话报》宗旨曰:“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1]故在晚清许多学者看来,中国传统学术是“一半断烂,一半庞杂”,主张用西方近代学科分类体系来分割和重新整理古代学术,即将原来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框架之分类体系彻底抛弃,转而按照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近代学科分类体系来分割和重新归类。
严复以西学为坐标来评判中学,对中国学术批评较为严厉。在他看来,若以近代西学之标准审视中学,则中国学问不称其为“学”:“‘学’者所以务民义,明民以所可知者也,明民以所可知,故求之吾心而有是非,考之外物而有离合,无所苟焉而已矣。……是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2](P45)既然中国传统学术仅仅是“阅历知解而存”之“散钱”、“委积”,则有必要“取西学之规矩法戒”,对之进行整理加工,使其演变为近代意义上真正的“学”。这项工作,便是“整理国故”。
提起整理国故,自然会想到五四时期胡适发起之“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广义上之“整理国故”,或者说以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研习中国旧学(国学、国粹)之工作,从清末即已开始。国粹派提出“保存国粹”、“古学复兴”及“昌明国学”之时,中国学术界实际上已经开始大规模之“整理国故”运动。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云:“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此黎明运动在当时之学术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面广博,波澜壮阔,沾溉来学,实无穷极。”[3](p28)钱氏将“国故研究之新运动”溯至晚清,称其为“黎明运动”,颇有卓识。
西方近代学术知识输入后,崇尚西学、新学之风日盛,中国传统学术面临着生存问题。既然旧学面临生死存亡之危机,故有学者思谋保存与发扬之道。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之国粹派对当时学术界之状况作了这样的概述:“今后生小子,入学肄业,辄束书不观,日惟骛于功令利禄之途,卤莽灭裂,浅尝辄止。致士风日趋于浅陋,毋有好古博学,通今知时,而务为特立有用之学者。”[4]正是有鉴于此,以章太炎、邓实等国粹派提出了“保存国粹”主张。
何谓国学?何谓国粹?《礼记》载:“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专指国家兴办之学校,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一国特有的学术”。近代意义之“国学”一词,是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的。国粹派所谓“国学”,是中国学术文化之总称;其所谓国粹,是指国学所含之精华:“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则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5]故保存国粹,就是保存与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为保存国粹,邓实等人主张“古学复兴”。其所谓“古学”,是指先秦学术,即君主专制建立及“异族”入主之前,未受“君学”、“异学”浸染之“汉族的民主的国家”之学术,即先秦诸子学。章太炎称:“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固。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6](p285)以“保存国粹”、“复兴古学”为宗旨,国粹派发表了许多研究中国旧学之论文,编写《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著,掀起了一个以西方新理新法研习中国古学之热潮,产生了诸如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齐物论释》、《新方言》、《小学答问》、《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国故论衡》,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古学出于官守论》、《中国哲学起源考》、《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孔学真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邓实的《古学复兴论》,黄节的《黄史》等二批学术研究成果。正是在用西学重新研究中国旧学的过程中,中国旧学逐渐被纳入到近代西方学术体系中,中国学术逐步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变。
借西学发明古学,是晚清中国有识之士研究中国旧学的基本思路。1902年5月,孙宝瑄云:“余数年来,专以新理新法治旧学,故能破除旧时一切科臼障碍。”[7](p530)《国粹学报》亦宜称:“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以阐发。”并云:“士生今日不能藉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8]主张应该用西方之“新理精识”,来“证明中学”,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
章太炎自幼“一意治经,文必法古”,后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经学大师俞樾,接受古文经学派的严格训练。在俞樾指点下,章氏致力于“稽古之学”,撰写了《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著。《膏兰室札记》,乃为其用格致新理阐发旧学之最初尝试。他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疏证《庄子·天下》篇及《淮南子》中《天文训》、《地形训》、《览冥训》等条目。他撰著《儒术真论》,以疏证和解释《墨子·公孟》篇之方式,发掘儒学中长期为人忽视之无神论思想;他依据近代进化论及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撰著《菌说》,均为“援西入中”尝试之明证。
甲午战后,章太炎广泛阅读西书,先后翻译《斯宾塞尔文集》、岸本能武太《社会学》,并采用西学新理新法,研究中国传统学术,颇多创获。章太炎在《訄书》中,所引证之西学知识随处可见。《公言》、《天论》、《原变》、《原人》、《族制》等篇,充满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进化论思想;《尊荀》、《儒墨》、《儒道》、《儒法》、《儒侠》、《儒兵》和《独圣》等篇,为打破儒家思想独尊地位、倡导复兴诸子学之名作;《平等难》、《喻侈靡》、《明群》、《播种》、《东方盛衰》、《蒙古盛衰》、《东鉴》等,则是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之佳作。这些篇章,开辟了以西学新理新法研究诸子学之新天地,对清末民初学术界影响甚大。1903年后,章氏阅读《因明入正理论》、《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佛学典籍,发现其哲理,开始以之阐释诸子学。“援佛入子”成为章氏研究诸子学之新法。梁启超曾云:“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9](p78)王伯祥等人亦云:“最早要推章炳麟的以佛理及西学阐发诸子,拿佛学来解老、庄,研究《易》象、《论语》,又拿《庄》来证孔,都有发明。”[10](p136)
章太炎尽管接受了西方近代学术,但其学问根柢及治学兴趣仍在中国经史之学:“学术万端,不如说经之乐,心所系著,已成染相。”[11]章氏谙熟朴学家考证方法,对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有很高造诣:“弟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于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12]接触西方新学理后,章氏更能“以新知附益旧学”,发明古学新义:“今既摭拾诸子,旁采远西,用相研究,以明微旨,其诸君子亦犹乐乎此欤?”[13](p118)《订孔》、《清儒》诸篇,将孔子置于诸子平等地位,作客观之历史考察,既肯定孔子对中国学术文化之功绩,也不赞同对孔子之顶礼膜拜:“《论语》者腌昧,《三朝记》与诸告饬、通论,多自触击也。”[14](p179)他以近代理性眼光,以历史进化观论孔子之功绩:“盖孔子之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14](p180)
章氏以西方新知,研究中国古文字学,撰著《文学说例》,对时人影响甚大。孙宝瑄云:“今览《新民报》所登《文学说例》一篇,知太炎于文学,新有进步。”正因如此,孙氏赞曰:“太炎以新理言旧学,精矣。”[7](p566)对于章氏“整理国故”之贡献,侯外庐评道:“太炎对于诸子学术的研究,堪称近代科学整理的导师。其文如《原儒》、《原道》、《原名》、《原墨》、《明见》、《订孔》、《原法》,都是参伍以法相宗而义征严密地分析诸于思想的。他的解析思维力,独立而无援附,故能把一个中国古代的学库,第一步打开了被中古传袭所封闭的神秘堡垒,第二步拆散了被中古偶像所崇拜着的奥堂,第三步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力,重建了一个近代人眼光之下所看见的古代思维世界。太炎在第一、二步打破传统、拆散偶像上,功绩至大,而在第三步建立系统上,只有偶得的天才洞见或断片的理性闪光。”[15](p158)
接受西方新知之晚清学者,当其再用新眼光看待中国旧学,自然会产生一些新见解:“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7](p526)正是在这种“以新眼读旧书”、以新理研旧学而不断产生“新见”过程中,中国旧学发生着微妙的嬗变。在此,不妨以孙宝瑄对中国史学之编撰为例,略作说明。
孙氏曰:“居今日而欲谈名理,以多读新译书为要。盖新书言理善于剖析,剖析愈精,条理愈密。若旧书,非不能说理,但能包含,不能剖析,故常病其粗。”[7](p755)因此,他格外强调研读新译西书,并将这些“新理”运用到史学研习中。1902年5月,孙氏与人谈论编史法云:“史有二类:曰事史,治乱兴衰是也;曰政史,典章制度是也。事史详于《通鉴》,政史详于《通典》,皆学者所当知也。”[7](p528)孙氏显然继承了传统之编史法,注重地理和职官,但也同样接受了近代西方编史法,以进化论探究中国之“治乱兴衰”。其所云“地图、职官表之前,复宜增一帝王年表,即仿纪元编例,专列纪元及甲子,使读者醒目”[7](p528),乃其接受西方新史书编撰法之明证。为此,他将编撰史书之体裁列为四种:年史、事史、政史、人史,并按照西洋编撰史书惯用之历史分期法,将所编撰之中国“事迹”分为10期:自伏羲起,讫秦为第一期;两汉为第二期;三国为第三期;两晋为第四期;南北朝至隋为第五期;唐一代为第六期;后五代为第七期;宋、辽、金为第八期;元为第九期;明为第十期[7](p533)孙宝瑄融合新旧史法编撰新史之例,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史学向近代形态演化之轨迹。
二 以近代学科框定中国旧学
相对于西方近代学科分类体系而言,中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学术分类体系及知识系统。中西学术分属两种形态迥异之知识系统。在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体系中,有经学、诸子学、文学、小学、理学、心学、禅学、道学、格物之学、训诂之学、心性之学、义理之学等名目,但却缺乏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近代西方学科门类。当近代西方学科体系为代表之新知识系统输入中国后,势必使“四部之学”知识系统面临分化与解体之境。
在西潮澎湃之强势影响下,抛弃“中学”所特有的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之学”为框架的知识分类体系,而采用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近代西方学科分类体系,并将经、史、子、集典籍分类体系及其包含之知识系统拆散,按照近代西方学科分类系统所划定的领域,将其重新归类,纳入到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教育等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中,成为清末学术演进之大势。这既是清末以来“整理国故运动”之主要任务,也是晚清许多学者努力的方向。
孙宝瑄接受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后,尝试将“经学”归并到近代西方学科体系之中。他自称:“余数年来,专以新理新法治旧学,故能破除旧时一切科臼障碍。”[7](p530)正因如此,他对中国旧学典籍之阐释颇具新意:“今于经,又别为二类:一曰哲学类,一曰史学类。《尚书》载言,《春秋》(三传附)载事,《周礼》载制度,《仪礼》载典礼,《毛诗》载乐章,皆史学也。《周易》发明阴阳消息,刚柔进退存亡原理,为哲学正宗。《论》、《孟》、《孝经》乃圣贤语录,其于人伦道德及治国平天下之术,三致意焉,故亦为哲学。《礼记》,丛书也,半哲半史,析而分之,各有附丽,若《大学》、《中庸》、《礼运》及《内则》、《曲礼》等篇,皆哲学也;其他《王制》、《玉藻》、《丧大记》之类,乃史学中典制一门,宜附于《周礼》、《仪礼》。此外尚有《尔雅》一书,古训诂也,学者通是,乃可以读群经;顾其释语言,释名称,释规制、器物,皆三代以前者,考古家有所取资,当附于史学焉。”[16](p1107)这是将“经部”分解开来,分别归并到“哲学”与“史学”两大学科门类中。
马叙伦根据近代分科原则及学科体系,提出“析史”主张。他认为,史乃群籍之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之开拓:“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文者文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他指出:“有政治史,而复析为法律史、理财史;有学术史,而复析为哲学史、科学史;美词有史,修文有史,盖骎骎乎能析史而万其名矣。”[17]故当以西方近代史学分类法,将中国史学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析之以政治史、法律史、理财史、学术史、哲学史、科学史等门类,重建中国近代新史学体系。持同样主张者,尚有宋恕:“史为记事之书,经、子、集虽杂记事,而要皆为论事之书。……今海外望国莫不注重史学,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有一史必有一史之学,数万里之原案咸被调查,数千年之各断悉加研究,史学极盛,而经、子、集中之精理名言亦大发其光矣严!”[18](p380)
1907年,国学保存会拟设国粹学堂,并草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课程表)。该学堂章程规定:“略仿各国文科大学及优级师范之例,分科讲授,惟均以国学为主。”[4]学堂课程分经学、文字学、社会学、实业学、博物学、经学、哲学、伦理学、考古学、史学、宗教学、译学等21门学科,各学科又分为若干种课程,如“社会学”分古代社会状态、中古社会状态、近代社会状态;“哲学”分古代哲学、佛教哲学、宋明哲学、近儒哲学;“史学”分年代学、历代兴亡史、外患史、政体史、外交史、内乱史、史学研究法等;“典制学”分历代行政之机关、官制、法制、典礼、兵制、田制等。此21门学科及其所属之具体课程,总数达百门之多。这既是国粹派接受西方近代“学科”体系之明证,也是其以近代“学科”界定中国旧学之尝试。
刘师培自幼受经史之学之严格训练,接受西学新知后,着力以西学新知发明旧学新理。其所著《经学教科书》,即是根据近代学科体系对“经学”加以整理与解释之作。其云:“盖六经之中,或为讲义,或为课本。《易经》者,哲理之讲义也;《诗经》者,唱歌之课本也;《书经》者,国文之课本也(兼政治学);《春秋》者,本国近世史之课本也;《礼经》者,修身之课本也;《乐经》者,唱歌歌本以及体操之模范也。”他认为,“特孔门之授六经,以诗、书、礼、乐为寻常学科;以易、春秋为特别学科。”[19](p4)这是以近代“学科”范畴来界定“六经”之必然结果。
刘师培认为,《易经》是中国古代学术之宝库,从中可以发掘古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找到“社会进化之秩序,与野蛮进于文明之状态”。故刘氏对《易经》作了详细研究。《经学教科书》第二册《弁言》云:“《易经》一书,所该之学最广,惟必明其例,然后于所该之学,分类以求,则知《易经》非仅空言,实古代致用之学。惜汉儒言象、言数,宋儒言理,均得易学之一端。若观其会通,其惟近儒焦氏之书乎?故今编此书,多用焦氏之说刺旧说者十之二,参臆解者十之三。如《易》于象传之外,兼有象经,则系前人所未言。”[20](弁言)可见,刘师培撰著该书,意在“发明《易》例”。而其发明之法,就是以近代学科体系来界定《易经》,将其蕴涵之知识,分门别类地归并到近代学科体系中。
《经学教科书》中最值得注意者,当数第二册之第22至29课。其第22课,刘氏专论“易经与古文字之关系”。他大胆断定《易经》乃上古时代之字典:“一曰入卦为象形文字之鼻祖”;“二曰卦名之字仅有右旁之声,为字母之鼻祖”;“三曰字义寓于卦名,即以卦名代字义,为后世训诂学之鼻祖。”[20](p33)其第23课,刘氏专论“易学与数学之关系”。他认为,“易经为数学所从生,上古之时数学未明,即以卦爻代数学之用,如卦有阳爻阴爻,阳卦为奇,阴卦为偶,易爻之分阴阳,犹代数之分正数负数也。”[20](p37)接着,刘氏便以近代数学来反观《易经》,寻找出《易经》之中有言加法、减法、乘除各法之例证,从而得出结论:“此皆数学出于周易之义,实与数学相通矣。”[20](p37~38)
其第24课,刘氏专论“易学与科学之关系”。他认为《易经》阐明“物理大旨”有二:一曰有裨于化学,二曰有裨于博物。“有裨于化学者,盖以地气水火为四行,即化学所谓元素。”“有裨于博物者,盖于众物之繁,悉该以阴阳二大类,以立其纲。”他所得出之结论为:《周易》之言科学,非仅裨研究学术之用也。盖以科学为实业之基因,以备物利用,故《系辞》言以制器者尚其象,又言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此皆研究科学之功也。则《周易》一书,非仅蹈空之学矣。”[20](p39)
其第25课,刘氏专论“易学与史学之关系”。他继承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将《易经》视为周公之旧典,有裨考史之用者有四:一曰周代之政多记于《易经》,故《易经》可以考周代之制度;一曰古代之事多存于《易经》,故《易经》可以补古史之缺遗;三曰古代之礼俗多见于《易经》,故《易经》可以考宗法社会之状态;四曰社会进化之秩序,事物发明之次第,多见于《易经》,故《易经》可以考古代社会之变迁。
其第26课,刘师培专论“易学与政治学之关系”。他断言,《易经》论政治,均为古代圣贤之微言,其“大义”有三:一曰内中国而外夷狄,二曰进君子而退小人,三曰损君主益人民。他断言:“《易经》之论政治,均就立国之本以立言,则《易经》兼为道政事之书矣。”[20](p42)
其第27课,刘氏专论“易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他以《周易》来“比附”近代社会学,视《周易》为中国社会学之祖:“今即《周易》全书观之,则《周易》之有象辞,即所谓现象也。”在刘氏看来,《周易·系辞》“均言社会学之作用”。其解释曰:“一曰藏往察来,《系辞》曰‘藏往而来’,又曰‘往来不穷谓之通’,又曰‘神以察来,智以藏往’。焦循《易话》曰:学易者,必先知伏羲作八卦前,是何世界。一曰探赜索隐,《系辞》又言极深研几钩深致远,均即‘索隐’二字之义也。藏往基于探赜,以事为主;察来基于索隐,以心为主。以事为主,即西人之动社会;以理为主,即西人之静社会学。”[20](p42)可见,刘氏将《周易》视之为社会学著作,并用近代社会学对《周易》作了“类比式”研究:“吾观《周易》各卦,首列彖象,继列爻词。彖训为材(材料),即事物也。象训为像,即现象也。爻训为效,即条例也。今西儒社会学必搜集人世之现象,发见人群之秩序,以求事物之总归。……而《大易》之道,不外藏往察来,探赜索隐。”[21]
其第28课,专论“易学与伦理学之关系”。他断言:“周易为古代伦理之书,其言伦理也,一曰寡过,二曰恒德。”其解释云:“《易·象传》所言之君子,即言君子当法易道,以作事耳。故所言之伦理,有对于个人者,有对于家族者,有对于社会者,有对于国家者。观于《易经》之彖传,而伦理之学备乎此矣。”[20](p43)
其第29课,专论“易经与哲学之关系”。他指出:“易经又为言哲理之书。其言哲理也,大抵谓太古之初,万物同出于一源,由一本而万殊,是为哲学一元论。”通过分析《易经》中之“隐”、“微”、“潜”、“几”、“深”、“远”等字义,断定“此皆《易经》形容道体之词,所以形容道体浑沌未分前之情状也。故知《易经》所言之哲理,皆从一元论而生,此即中国玄学滥觞也。一元者,即《易经》所谓太极纬书,所谓太易、太初、太始也。”[20](p45~46)他还强调:“《易经》之言哲理也,首持一元论,复由二元论之说,易为二元论。”这是以西方哲学观念来考察《易经》之结论。他指出:“易经之言哲理也,其最精之义蕴犹有三端,均至高至尚之哲理也。”即:一为不生不灭之说;二为效实储能之说;三为进化之说。[20](p48~49)
刘师培将《易经》视为“易学”,并与近代“学科”体系中之数学、物理学、化学、博物学、文字学、哲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对应起来,逐次发掘其中所包含之学科门类,虽然有明显的比附倾向,但其将《易经》所包含之思想,归并到近代学科体系中之意向则是非常明显的。
用近代学科界定中国传统学术,乃刘师培“类比式”研究的一大特征。如果将刘氏文著略加分析,便会发现,《古政原论》、《古政原始论》是其阐述古代社会学之作,《两汉学术发微论》是其阐述汉代政治学、民族学和伦理学之作,《伦理教科书》是其阐述中国古代伦理学之作,《中国地理教科书》是其阐述中国古代地理学之作,《中国文字教科书》是其阐述中国文字学之作,《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是其阐述汉魏南北朝文学史之作,《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其阐述中国古代历史之作,这些论著,均是按照近代“学科”观念及学科体系,界定、阐释与整理中国旧学之作,亦可视为创建近代意义之中国“学科化”学术体系之尝试。
以“人”为本位,以“人”为分类标准,是中国传统学术之重要特征。而近代西方学术则是以“学科”为分类标准,晚清学者在接受西方分科观念及学科体系后,便开始在研究和撰著中国学术史时,打破传统“学案体”,尝试用“学科”来框定中国传统学术。皮锡瑞之《经学历史》、章太炎之《訄书》、梁启超之《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均作了有益尝试。而完全以西方近代“学科”分类体系界定中国传统学术,当以刘师培为代表。
刘师培认为,以“人”为标准类分学术之“学案体”,难以对中国学术进行义理分析,故在其研习学术史之文著中,“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之体,拟以学为主,义主分析,故稍变前人著作之体也)。”[21]故其所撰著之《周末学术史叙》、《两汉学术发微论》等,即改变此种体裁,以近代西方学科体系来框定中国古代学术,力争将中国旧学纳入到近代学科体系中。
《周末学术史叙》乃刘师培拟著之《周末学术史》序目。全书将周末学术史分为16类: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逻辑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史(财政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刑法等)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它突破了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完全按近代西方学科门类重组和分类,既是一种是以西方学科概念界定中国传统学术的代表作,也是将以“人”为主撰写学术史之旧例改为以“学科”为主分类撰著新体裁的尝试之作,体现了近代西方学术专门化特色。刘氏之意图是非常显明的:将中国旧学纳入近代学科体系。
在《周末学术史叙》中,刘师培试图从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名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经济学)、兵学(军事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等各个方面加以条分缕析,对先秦诸子进行分类整理、诠释和评价。在这种分类整理过程中,“比附式”理解与“类比式”研究的倾向格外明显。如刘氏《心理学史叙》云:“吾尝观泰西学术史矣。泰西古国以十计,以希腊为最著。希腊古初有爱阿尼学派,立论皆基于物理(以形而下为主),及伊大利学派兴,立说始基于心理(以形而上为主),此学术变迁之秩序也。(见西人《学术沿革史》及日本人《哲学大观》、《哲学要领》诸书)吾观炎黄之时,学术渐备,然趋重实际,崇尚实行,殆与爱阿尼学派相近。夏商以还,学者始言心理。”[21]刘师培所撰著之《两汉学术发微论》,也采取了同样做法。该文以西方政治学、种族学、伦理学概念,来界定两汉学术,并分科论述,同样是以近代学科观念及学科体系框定中国旧学之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当晚清学者接受西方学科体系后,力图在这种学科体系中找到自己所研究的学问的位置,西方“哲学”与中国“义理之学”相通,因而孙宝瑄很快便找到了自己在近代学科体系中的位置:“余平素治各种学问,皆深究其原理,则余所治实哲学也,西人谓哲学与理学有别。理学是实验有形质者,哲学是论究无形质者。理学为事物中一部分之学,哲学为事物中全体之学。”[7](p744)宋恕在近代学科体系中,对自己之定位为:“最精古今中外哲学、古今中外史学、古今中外政治学、古今中外法律学、周汉唐宋词章学、古音学,次则演说学、教育学、理财学、日本文学、地理学,粗涉物理学、博物学、几何学,此外未学。”[18](p417)这种以近代学科为标准,对自己所研习之学问重新定位的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方学科体系对晚清学者影响之深刻。
三 对中西学术之比附式会通
中国近代学术及知识系统,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具有明显的“移植”特征。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的过程,既是中学如何吸纳西学而发生嬗变的过程,也是如何将中学纳入近代西方学术体系的过程。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既是学术体系之转型,也是知识系统之转型,是旧的“四部”知识系统瓦解与新的近代知识系统重建之过程。这样两个过程,其表现集中于近代学科化体系的引入与中西学术的会通。
晚清学者在吸纳西学、研习中国旧学之时,多以中学“比附”西学,对中国旧学进行“类比式”研究,并以此会通中西学术。所谓类比式研究,指在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时,以近代西方学科概念与学术体系为参照,找出中国传统学术中与西方近代学术类似之思想。这种类比式研究,是中西学术交流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其附会肤浅之弊端显而易见,但对于中西学术的接轨,是有益的。究其动机,是借助中西学术之类比,寻求中西学术会通之道,从而将中国旧学纳入西学新知系统之中。
这种“类比式”研究之体现,是晚清学者多强调中国旧学渊博高深,包含着西方近代学术,并认为周末诸子颇与西方学术相符:“墨荀之名学,管商之法学,老庄之神学,计然、白圭之计学,扁鹊之医学,孙吴之兵学,皆卓然自成一家之言,可与西方哲儒并驾齐驱者也。”“诸子之旧书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化光电之学,无所不包。”[22]他们甚至把荀子、孟子、子思、邓析等人说成是中国之卢梭、苏格拉底、孟德斯鸠、斯宾塞,比附之意甚为明显。至于其盛赞孔子是学习外来文化之楷模,程朱是吸收佛学之典范,更属牵强附会,其意在证明中学是可以用“西学”阐释的。
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发掘适合近代新学之义理,并对其作“比附式”理解,是晚清许多学者会通中西学术时采用的方法。1901年9月,吴汝纶致函陆伯奎:“求政治之学,无过《通鉴》。……其政治之学当以国朝为主,国家纪载流传者稀,无已,则于皇朝‘三通’择用其一,使习国家掌故,庶亦可也。”[23](p255)这显然是将《通鉴》视为中国“政治之学”,是用西方“政治学”学科观念,从中国典籍中寻找学术资源之努力。蔡元培在解释斯宾塞社会学时,大量引用中国典籍加以“比附式”理解。他认为群学上之“合其力艺抵自然之压力,而无不胜,于是灾疠不作,民无夭折,则《孟子》所谓性善,而《春秋》所谓大一统、所谓太平,而《礼运》所谓大同者也。”[24](p394)他在解释“群之分合,视爱之厚薄”时,将其视为《孟子》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比附之意甚明。不仅如此,蔡氏以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比附斯宾塞“人各自由,而易他人之自由为界”;以墨子所谓“养老之政”、“穷民无告之政”,比附西方近代之“慈善事业”;以孔子“杀身成仁”,孟子“舍生取义”,比附斯宾塞所谓“群已并重,舍已为群”[24](p397)。
梁启超采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及观念,对中国旧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其中对《墨经》之研究颇有新意,也最具“比附”特色。《墨子》是先秦时期包蕴逻辑思想最为丰富的典籍,长期以来受到冷落。晚清大儒孙诒让不仅傅采清中叶以来诸家之长,撰著《墨子间诂》,而且用他所接受之西方逻辑学“复事审校”,认为《墨经》中之“微言大义”有如“亚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25]受孙氏启发,梁启超着力研究《墨经》中之思想,先后撰写了《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墨子校释》等著。其所用方法即为“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以西方近代学术“比附”先秦墨学。其曰:“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又云:“《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至专言其法则之所以成立者,则惟《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非命》诸篇为特详。今引而释之,与泰西治此学者相印证焉。”这显然是梁氏研究《墨子》之指导思想。其释《墨经》,“引申触类,借材于域外之学以相发,亦可有意外创获。”梁氏列举先秦所论之范畴,用西方近代逻辑术语对比解释。其云:“墨子所谓辩者,即论理学也。”“墨子所谓名者,即论理学所谓名词也。”“西语的逻辑,墨家叫做‘辩’”。“‘墨辩’两字,用现在的通行语翻出来,就是‘墨家论理学’。”梁氏将“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分别解释为西方逻辑之概念、判断、推论。他用“论理学”译Logic,认为“辩”即“论理学”,“名”即“名词”,“辞”即“命题”;“名”是概念,“实”是对境(对象),“意”含判断之意。[26]
梁氏将《墨经》逻辑义理与西方逻辑学“类比”后断定:“《墨经》论理学的特长,在于发明原理及法则,若论到方式,自不能如西洋和印度的精密。但相同之处亦甚多。”《墨经》之推论方式,与印度之“因明”也有相类似处。在梁氏看来,《墨经》之演绎论证式,相当于因明三支式、亚氏三段论之省略式。故其称墨子为“东方之培根”、全世界论理学一大祖师”。梁氏以西学为比照,潜心发掘中国古代逻辑之近代价值,对晚清“墨学”复兴起了重要作用。但其解读《墨经》时以中学附会西学之倾向还是较为明显的,梁氏自称“每一复阅,觉武断凿解”[26],即为其真实体悟。
刘师培是清末以西学阐释中国旧学,并用旧学“比附”西学以“发明”新理之典型代表。以新知阐释旧学,以中学比附西方,是刘氏研究中国旧学的基本思路。从1903年开始,刘师培将所接受的西学新知,引入中国旧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主要体现在《小学发微》、《中国民约精义》、《中国民族志》、《攘书》、《新史篇》、《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论文杂记》、《南北学派不同论》、《古政原始论》、《汉宋学术异同论》、《两汉学术发微论》、《中国哲学起原考》、《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论著中。
刘师培认为,《论语》所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最能体现近代“天择物竞之精理”。松柏后凋,说明“存其最宜”;但这并非得天独厚,而在松柏本身具有“傲岁寒之能力”[21]。这种对《论语》词句之新解,旨在论证《论语》中暗含“进化之理”。刘氏还认为,《山海经》所记之时代,人兽之争未息,后来奇禽怪兽灭于无形,而人类得以繁衍,即是“优胜劣败之公例”[27],这显然也是以进化论“比附”中国上古社会所得之结论。刘氏自称“予于社会学研究最深”,用社会学阐释中国旧学亦颇多心得。其作诗云:“西藉东来迹已陈,年来穷理倍翻新,只缘未识佉卢字,绝学何由作解人。道教阴阳学派异,彰往察来理不殊,试证西方社会学,胪陈事物信非诬。”[28]故刘氏对西方社会学作了较为详细之介绍:“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即墨守故俗之风,气数循环之说,亦失其依据,不复为学者所尊,可谓精微之学矣。”[29]
刘师培以此种“精微之学”分析中国文字,从中国文字由简趋繁之变化轨迹中,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演化之历程:“予旧作《小学发微》,以为文字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之文,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故治小学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将西方社会学引入“文字学”,开辟了传统“小学”研究之新天地。刘氏将社会学引入小学研究,其动机在于通过对中国文字之研究,昌明近代社会学:“故欲社会学之昌明,必以中土之文为左验。”其研究思路为:“然欲治斯学,厥有数例:察文字所从之形,一也;穷文字得训之始二也;一字数义,求其引伸之故,三也。三例既明,而中土文字,古谊毕呈,用以证明社会学,则言皆有物,迥异蹈虚。此则中土学术之有益于世者也。”[29]
1904年11月,刘师培在《警钟日报》上发表《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尝试用西方近代社会学的理论及方法,“考中国造字之原”[30]。刘氏考证了舅、姑、妇、赋、君、林、田、尊、酉、社、牧、民等33则字义,对这些字义作了近代意义的阐释。他不仅通过阐发《社会通诠》、《群学肄言》有关社会进化之理,探讨中国文字之来源及引申之义,而且运用《泰西新史揽要》、《希腊志略》等书提供之史学,佐证中国文字演化之迹。
在《理学字义通释》中,刘师培进一步以西方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所述之理,对中国传统学术范畴之“理”、“性”、“情”、“志”、“意”、“欲”、“仁”、“惠”、“恕”、“命”、“心”、“德”、“义”、“敬”等字义,重新作了诠释。按照西方学科理念,刘氏将传统之“理”分为心理与物理,并在先秦思想中寻找相似之点:“故皙种析心理物理为二科。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又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有是非之心,则理即具于人心中可知矣)。此就在心之理言之也。”[31](p618)刘师培对用西方社会学治“小学”之成绩颇为自信:“余著《小学发微》,以文字证明社会进化之理,又拟编《中国文典》,以探古人造字之原。”并作诗云:“古人制字寓精义,周秦而降渺不存,试从苍颉溯初祖,卓识能穷文字原。”[28]
不仅如此,刘师培还以西方近代理论学与心理学之关系,阐释汉宋诸儒所言之义理:“西人伦理学多与心理学相辅,心理学者,就思之作用而求其原理者也;伦理学者,论思之作用而使之守一定之轨范者也。”[32](p535)他进而说明中国所谓之“心理”与西方知识系统对应范畴之关系:“盖中国之言心理也,咸分体用为二端。《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此指心之体言之也;又言发而皆中节,此就心之用言之也。……应万事之说,近于西人之效实(所谓辟以出力也),所谓拓而充之也。”[31](p634)比附之意较为明显。他还认为:“西汉之时,凡国有大政大狱,必下博士等官会议,此即上议院之制度也。”[32](p530)这显然是以两汉政治“比附”西方政治学。至于他所强调之汉儒伦理学“与西洋伦理学其秩序大约相符”[32](p535),更是以汉儒所云伦理附会西方伦理学之明证。
刘氏阐述《古政原始论》撰写旨趣云:“造字之初,始于苍颉。然文字之繁简,足窥治化浅深(中国形声各字,观其偏旁,可以知古代人群之情况,予旧著《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即本此义者也)。……惜中国不知掘地之学,使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之遗物。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迂诞之辞所能拟哉!此《古政原始论》所由作也。”[33]故《古政原始论》乃刘氏以近代社会学研究中国古史之力作。如果说《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是运用社会学考察中国文字变迁,进而阐述中国古代社会进化的话,那么《古政原始论》则是用社会学阐述古代中国社会起源与演进的典范。
刘师培对西方逻辑学有所涉猎,并将其引入中国传统之“小学”研究中。其介绍云:“论理学即名学,西人视为求真理之要法,所谓科学之科学也,而其法有二:一为归纳法,即由万殊求一本之法也;一为演绎法,即由一本赅万殊之法也。其书之传入中土者,有《名理探》、《辨学启蒙》诸书,而以穆勒《名学》为最要。”[34](p110)刘氏撰著《国文问答》、《国文杂记》、《正名篇》及《中国文字流弊论》等文,便是用西方逻辑学研究先秦“名学”之成果。对于自己在这些论著中发掘出之“新理”新义,他作诗赞云:“正名次义无人识,俗训流传故训湮,析字我师荀子说,新名制作旧名循……试证西方名理学,训辞显著则余休。”[28]
1903年,刘师培编撰《国文典问答》,其附录《国文杂记》颇具新意:“中国国文所以无规则者,由于不明论理学故也。论理学之用始于正名,终于推定,盖于字类之分析,文辞之缀系,非此不能明也。吾中国之儒但有兴始论理学之思想,未有用论理学之实际。……今欲正中国国文,宜先修中国固有之伦理学而以西国之伦理学参益之,亦循名责实之一道也。”[35](p10)这是用西方逻辑学改造中国文法之较早尝试,也是用西方文法检视中国语言文字之初步结论。其所云“先修中国固有之论理学而以西国之论理学参益之”,将以“比附式”理解来沟通中西学术的意向,表述得格外清晰。
刘氏还用西方逻辑学来说明中国“名学”之发源:“黄帝名百物(见《礼记》,又《聘礼》云百物以上,《国语·楚辞》云,陈百物以献败于寡君。),大禹名山川(见《书·吕刑》及《尔雅·释水》)是也。”[34](p106)在用西学阐释中国旧学之时,刘氏往往以中学来“比附”西学,认为中学有与西学所言之理相合者。以西方之心理学、社会学,来重新解释中国传统“心体”,即为典型一例:“春秋以降名之不正也久矣!惟《荀子·正名》一篇,由命物之初推而至于心体之感觉。”他断言《荀子》之说合乎西方逻辑学,“与穆勒《名学》合。名理精诣,赖此仅存。”对先秦逻辑学,他同样作了“比附式”理解:“盖周末之名家最与西人诡辩之学近。”[34](p109)较早看到先秦诸子中暗含有与西方逻辑学相似的观念。
《中国民约精义》,是刘师培以卢梭《民约论》思想阐释中国典籍之作。他从《周易》、《诗经》等先秦典籍直至清人文集中,辑录出与“民约之义”相关文字,加以案语,力图发掘中国典籍中之“民约精义”。在释《春秋谷梁传》时,刘氏案曰:“《谷梁》以称魏人立晋为得众之辞,得众者,即众意佥同之谓也,此民约遗意仅见于周代者。”[36](p14)他在释《扬子》时云:“杨子此说,近于卢氏之平等,而其实不同。”认为《墨子》之说,“最近于西人之神权,而著书之旨则在于称天制君”;认为《管子》所行之政治,“以立宪为主”;许行之说“近于民权,亦近于平等”。他断定《民约论》与王阳明之良知说同样有相似之处:“皆以自由为秉于生初。盖自由权秉于天,良知亦秉于天;自由无所凭借。良知亦无所凭借,则谓良知即自由权可也。印明著书,虽未发明民权之理,然即良知之说推之,可得平等自由之精理。今欲振中国之学风,其惟发明良知之说乎。”[36](p48)诸如此类的案语,既可视为刘氏以《民约论》思想解释中国旧籍之作,也可视为以中国思想附会卢梭“民约经义”之作。这种“援西入经”的解读方式,固属牵强附会,与中国典籍的本义有相当差距,但刘师培这种“比附”式努力的基本点,在于使中国旧典籍能够表达出近代学术的观念,从中国旧典籍中找到与西方近代学术的相似处,既便于西学在中国思想土壤中扎根,又促使中国传统学术取得近代形态。
刘师培以西学阐释诸子学,以诸子学比附西学,牵强附会之处甚多,既开启了诸子学研究的新思路,也使西学在中国旧学中找到了某些根基。刘师培以西学阐释中国旧学的尝试,力争将中国旧学纳入到西方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中的尝试,牵强附会的“比附”倾向是明显的,但其所取得的成绩与功绩并不因此而抹杀。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中国旧学研究中的“比附”现象作了揭示和批评:“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9](p72)章太炎亦批评道:“今乃远引泰西以征经说,宁异宋人之以禅学说经耶!夫验实则西长而中短,谈理则佛是而孔非。九流诸子自名其家,无妨随义抑扬,以意取舍。若以疏证《六经》之作,而强相比傅,以为调人,则只形其穿凿耳。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上。使立者倚,则失矣,使倚者立,亦未得也。”[37]
应该看到,对西学之“比附式”理解、“附会式”会通及“类比式”研究,虽非科学,却是中西学术交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对于“比附式”理解盛行的原因,姜义华之论颇具慧眼:“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没有来得及从其自身内部生长出批判和创新的力量,来独立地进行疏浚清理、发展转化;对于西方新学,也没有足够的基础与时间去加以咀嚼、消化、吸收。急迫的形势,驱使他们中间许多人匆匆地将两者简单地加以比附、粘合,结果,造成传统的旧学和舶来的新学双双变了形。”[38](p19)
传统之旧学与舶来之新学,“双双变了形”,乃为晚清时期中西学术交流的必然趋势。正是在这种不断“变形”过程中,中国旧学向西方学术体系转轨,逐渐取得了近代形态;正是在这种不断“变形”过程中,输入中国的西学开始其“中国化”历程,逐渐取得了中国的民族形态。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正是在这种“变形”中开始、演进并逐步完成的。
标签:刘师培论文; 社会学论文; 国学论文; 章太炎论文; 周易八卦论文; 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晚清论文; 读书论文; 易经论文; 古中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