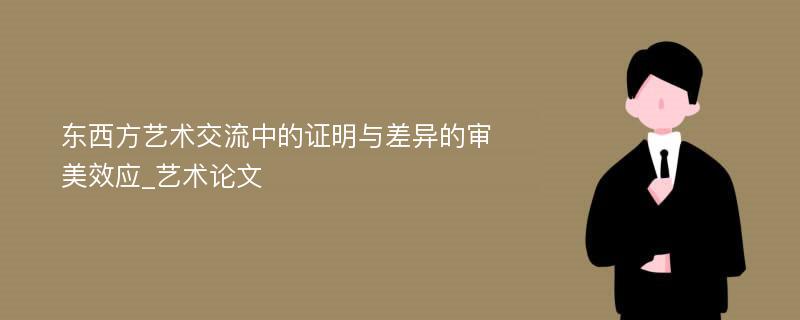
东西方艺术交流中的证异审美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方论文,效应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西方民族在源远流长的文化艺术交流史中,产生了诸多积极的审美效应,因而构成了令世人瞩目的两种文化上的互补。但是,既然东西方文化具有巨大的差异,那也就意味着这种跨文化交流所呈现的,不可能总是一种相互接受、相互吸引中的顺畅交流。事实上,在这种交流过程中,既有沟通与吸纳,又有冲突与碰撞,既有相互的吸引与借鉴,又不乏相互的排斥与抵御。如此看来,这种审美交流既可产生积极的审美效应形态,又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消极的审美效应形态。其中,证异效应就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消极性审美效应。
一、证异效应的发生
所谓证异效应,是指人们在进行跨文化艺术交流中,异域作品在审美主体心中所引起的一种否定性、批判性的审美效果。也就是说,有些作品,它在本民族欣赏者中本来产生了肯定性的审美效应,但在其他民族中却不被接受,引起了与之相反的审美效果。这时,审美主体往往通过对异域作品的否定和批评来排斥他者,从中证明他文化的与己之异,进而认同自我,维系本民族文化。
证异效应的产生原因,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审美主客体所存在的差异性。如前所说,东西方文化无论在文化观念、风俗习惯和审美趣味等方面都存在着各自独特的价值取向,它必然表现在各自的艺术作品中,于是人们在接受异域的文化艺术作品时,也最容易产生不同文化之间通约上的障碍。这里的所谓通约(commensurable),指的是不同文化之间可以互相理解,相互阐发。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尤其在两种文化出现明显矛盾和对立的时候,很难在一种文化系统中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来阐述另一种文化系统中的不同内容。美国学者约翰·波宁就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译性和不可通约性①,而文化的误读恰好就在这时产生了。
在进行跨文化艺术交流时,当异域作品中的价值观念、审美追求与本土文化发生明显的对立时,接受主体往往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审美心理的不适,甚至还会出现审美的反感(关于审美的反感,马克思曾有过论述,不过他主要是从审美对象的道德低俗角度来谈的,其实,当人们在接触到异域艺术中与本族文化精神完全对立的内容时,也容易出现这种审美的反感)。于是,审美主体也就采取了抵御和否定的审美态度。
在跨文化艺术接受中,异域作品所表现的文化内容和形式与接受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越大,就越容易引起主体对审美对象的否定,从而产生证异效应。董乐山先生在谈到对于美国文学的理解时就曾这样写道:“有些美国文学界认为非常优秀的作家作品翻译到中国来了,我看原文,老实讲也看不懂,不知所云,不知道他讲的什么,因为他讲的是美国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心理,我们和美国人的距离还是太远了,他们的心理有的地方我们想象不到。所以有一次张洁就讲美国作家都是神经病。她认为他们写的人物都是精神有毛病的。我也有这种感觉,所以老实讲,美国小说这么多,我看得很少。”②这里所表现的,就是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所造成的接受障碍所引起的接受者对于异族艺术的否定。
证异审美效应的发生,不仅仅来自于两种文化上的差异,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东西方民族之间在过去所形成的民族偏见。也就是说,无论是东方人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还是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解读,都有着极大的主观性和排他性。以至于使东方人眼中的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化都曾经被“妖魔化”和“类型化”。在这一点上,美籍阿裔学者爱德华·赛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中就给予了深刻的总结和剖析。他尤其对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东方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一个民族在审视其他民族的文化时,其民族偏见往往是一种习惯性的东西。赛义德说:“人们是如何表述其他文化的?什么是另一种文化?文化(或种族、宗教、文明)差异这一概念是否行之有效?或者,它总是与沾沾自喜(当谈到自己文化的时候)或敌视或侵犯(当谈到其他文化时)难解难分?”③他还指出:“文化常常咄咄逼人地与民族与国家绑在一起,把‘我们’与‘他们’加以区分。几乎永远伴随某种仇视他国的情绪。在这种意义上而言,文化是民族同一性的根源。正如我们从新近对文化和传统的‘回归’中看到的。与这些‘回归’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思想和道德行为规则,这些规则与多元文化观和合成文化观这样一些比较开明的哲学与体现的宽容精神水火不相容。”④
如此看来,一个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民族偏见的生成。在这一点上,东西方都毫无例外。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史上,各自都一度用民族的有色眼镜去建构对方的形象,并形成了歪曲对方的过滤框架和“前结构”、话语体系和想象视野。我们清楚地看到,近代以来在欧洲人与中国人的交往中,产生过许许多多冲突,双方都把对方指责为“野蛮人”。拿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来看,西方列强不仅以其优越感蔑视中国文化,而且认为中国人不可理解,还视中国人为“东亚病夫”,甚至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直至20世纪20年代,西方仍存在着对中国的荒谬无稽之谈。人类学家吴泽霖曾列举过美国公众对于中国人的偏见,“包括所有的中国人都狡诈奸猾”,中国人没有灵魂,“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所有的中国人都恨水,因为他们从来不洗澡”,⑤等等。同样,中国人也曾把西方人视为不可理喻的“蛮夷”。直到近代,中国人对西方仍是一无所知,而且夜郎自大,认为西方人是伦理沦丧、凶恶成性、攻击性极强的食肉动物;西洋人膝盖不会弯曲,故不能行跪拜礼。甚至连林则徐也认为西方人离开了茶叶就活不了,等等。
把本民族所居地看作是世界的核心,把自己的文化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之文化,视本族为人类,乃至优秀人类,而视异族为“野蛮人”乃至非人类,这是典型的民族中心主义。而且许多民族都难免存有这种民族中心主义。但是,东西方民族(这里主要指中国和欧美民族)在这方面似乎表现得更加明显而强烈。这也是引起东西方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既然东西方在审视自我与异族文化的时候都存在着这种既定的民族偏见,都是在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中去看待异域文化,那么,他们在接受异域的艺术作品时,对其进行否定和指责,也就在所难免了。这就是说,一个民族对于另一民族文化愈是歧视和否定,也就愈容易出现对其艺术作品的否定和鄙视,从而导致证异审美效应的产生。例如,西方人就曾十分轻蔑地看待过中国的戏剧艺术。在《中国比较文学通讯》中就有这样一段令人不解的文字:“1886年法国人彼勒梯在《中国戏剧》一书中说‘我觉得在中国戏剧与我们的戏剧之间唯一的不同……是婴儿的呀呀学语与成年人言语之间的区别’。1929年,世界戏剧史家英国的谢欧顿·契尼(对中国戏剧的)评价也不高:‘中国戏剧还只能跻身于通俗剧、老套的报道剧,或歌剧唱文之列。’19世纪中叶,曾任法国公使的德·布尔布隆公然声称中国戏剧的唱法是‘猫叫’,他在《关于中国的戏剧演出》中甚至妄断‘中国人没有艺术感’。”⑥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西方一些人对于中国戏剧艺术形式的偏见之大,误读之深,已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对于这样一种单边性的武断而带有歧视性的艺术评价,中国人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同样,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许多艺术也曾有过极大的偏见和蔑视,中国人过去不是也曾把西方一些音乐说成是靡靡之音,把西方的一些舞蹈斥之为群魔乱舞吗?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产生证异效应的某些政治因素。也就是说,当两大民族不仅在文化上存在着差异,而且还存在着政治分歧的时候,尤其这种分歧处在相当严重的时期时,接受国对于对立民族的文化艺术的排斥就会更为强烈,文化偏见也随之增多。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西方几乎完全断绝了文化艺术上的往来,而且都把对方的艺术骂得一无是处。这种对于对方文化艺术的先入为主的认识方式,当然也就直接导致了证异效应的产生。
顺便还需要说明的是,证异审美效应是与证同审美效应相对而存在的。如果说,证同效应是审美主体从审美对象中发现了与本民族文化相一致的相符点,产生了先得我心的证我之同,那么,证异效应则是主体从审美对象中发现了与本民族文化相悖的不同点、矛盾点,产生了证它之异。如果说,证同效应是主体通过对审美对象的肯定、欣赏来认同自我、确认自我,进一步发现了自我,从而从正面维系本民族的文化,那么,证异效应则是主体通过对异质文化艺术的否定和排斥来从反面确认自我,寻找自我,维系本民族的文化。
二、证异效应的表现
证异效应的表现形态虽然比较复杂,但它还是要从审美主体对于异族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等方面的否定和排斥中表现出来。
其一,表现在审美主体对于异域作品的艺术形式的否定方面。
也就是说,当异域艺术的外在表现形式不适应主体的民族审美趣味,甚至与主体的民族文化艺术趣味相悖的时候,就会引起主体的否定和抵御。如在绘画方面,中国古代画家颇重笔法、韵味,所以对讲求解剖、透视、光线和色彩的西洋画就极不习惯,他们看到西方的一些绘画艺术常常就有审美的不适感,而加以否定,指摘它们是“笔法全无、虽工亦匠”,“不入画品”⑦,而讲究解剖和透视的西方人看到了中国画后同样加以反对和指摘。比如他们在观看中国画中的鱼的时候,发现画中只有鱼而看不到水,就自然地会感到这种创作明显地违反了西方艺术创作法则,就要批评中国画中的鱼为什么不在水中游却在空气中游。而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中国画是不讲究透视,不讲究“图和底”的关系。两种文化艺术形式法则的对立与冲突,使得接受者不仅无法认同异域作品中特殊的审美趣味,反而出现了对于异域审美对象的批判。
再如在对于音乐的感受方面,东西方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汉民族所经历的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生活所形成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生产特点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封闭性生活方式,使之更亲近自然,更重情感,渐渐形成了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格以及凝重沉实的艺术气质。这使中国人习惯于欣赏缓慢而舒展的韵律和节奏,在艺术趣味方面,更偏向于对于优美风格的追求。于是,中国人对于那些急如风雨、旋律激昂的西方音乐便常常难以接受。
可见,东西方民族在艺术形式上的矛盾和对立,往往使各自在接受对方艺术时首先对其外在形式加以否定和抵御。这便成了东西方跨文化艺术交流时的首要障碍。这种接受障碍使得东西方都不可能顺利地理解对方文化艺术的精神主旨,更不可能从中获得美感。
其二,证异效应还表现在审美主体对异域作品中的深层文化观念和情感内容的否定方面。
我们知道,不同民族的艺术作品,在其深层结构——观念情感层总是蕴藏着各自的文化价值观念、情感方式、审美趣味等内容,它属于文化心理结构的范畴,这些内容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根本文化精神,也最能表现该民族的文化底蕴,它也是最能决定文艺作品感染力的层面。而这一层面也很容易在跨文化艺术交流中造成不同民族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法国学者伊夫·谢弗雷尔在谈到对于戏剧的接受时就曾这样说:“戏剧的语言和行为在本国文化中并不难懂,却与接受国文化的最深层传统发生冲突,致使观众感到不适,而作为社会艺术,戏剧迫使我们面对这一问题。”⑧谢弗雷尔看到了这一深层内容对于文化交流的影响,认为它们是最容易产生交流的障碍,它们也是引起证异效应的重要原因。在接受异域作品时,一旦这些深层文化内容与接受国的深层文化精神相矛盾,就会造成接受者审美心理的不快和对抗,从而引起主体对作品这一层面内容的否定,产生证异效应。
1904年,近代翻译家林纾与魏易曾把英国作家哈葛德的小说《迦茵小传》进行了全译,忠实地介绍给当时的中国读者。而这个反映迦茵与亨利不顾父母之命,进行自由恋爱并未婚私孕的故事,一经进入当时中国人的审美视野,就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道学家大声质问:“未嫁之女儿?有私孕,其人为足重乎?不足重乎!”有的则忧虑,如果把这类“女子怀春”的故事一并译入,“贞操可以立破矣!”“西人临文不讳,然为中国社会计,正宜删去为是”。
显然,这部小说所反映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恰恰与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特别是与传统的封建礼教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迦茵这一形象及其行为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她不仅不能使人们产生情感共鸣与美感,反而会出现反感,并引起一种抵制情绪。这个本来在西方读者中得到认同的,进而也能从中获得美感的作品,在中国读者中间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接受效果。
再如,中国古代文化要求妇女缠足,许多中国古代文艺作品还把这种缠足现象视为一种美来加以欣赏,而这一文化习俗所体现的深层内容便是传统的封建礼教对于中国妇女的束缚和禁锢。这恰好与当时就已经主张妇女解放、张扬个性的西方文化观念相对立,因此当西方人接触到中国旧时代作品中对于妇女的“三寸金莲”描写时,同样会感到不舒服,感到不可思议,并加以指责,并对此进行文化批判。
在这一接受过程中,人们一方面对于对立的异质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加以排斥,同时又在这种排斥中维系和强化着本土文化。
其三,证异效应还表现在审美主体对于异域作品中一些审美意象的否定方面。
我们知道,文艺作品中的审美意象往往又是表现和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的特殊形式和手段。对于同一审美意象,东西方民族往往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其感受也会大相径庭。比如,在中国人眼中,龙是和威猛、雄奇连在一起的,它甚至被看成是中国的象征。但在西方人眼中,龙则是邪恶的象征,它常与凶残,肆虐连在一起,在取材于公元700年左右的盎格鲁·萨克逊英雄传说的叙事诗《贝奥武甫》中,主人公与恶龙搏斗,同归于尽。这在中国人看来,就觉得难以接受,并引起质疑;狗在西方是极为受宠的动物,西方人甚至常用它来表示快乐、亲切、幸运等意义,而中国人却视狗为极下贱的动物,用狗来骂人的话也是不一而足;在色彩上,白色在中国常用来做孝服,而在西方则用来表达纯洁的爱情;黄色在古代的中国是神圣皇权的象征,而在西方则是身穿黄服的叛徒犹大所代表的低级色相;在植物方面,柏树在中国文化中常用来象征不屈的力量和高洁的人格,而在古希腊和罗马神话中,它却是阴间的树,坟场的树。
就连东风与西风这两种意象,在东西方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中也有完全不同的感情色彩。东风在中国人眼里是温暖的、和煦的,因此它往往代表着富有生机的和美好的事物,我国古代诗歌中就常把东风比作春风。而在西方人眼中,东风则是寒冷而刺骨的,毫无暖意可言,西风才是充满了暖意的。于是,当西方人读到朱熹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和宋代王令的“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等诗句时,就会产生相反或困惑的心理反应,他们会质疑:为什么要用寒冷的东风来表示春天?为什么要一味地唤回那并无暖意的东风呢?
东西方民族对于这些审美意象的完全相反的解读,必然会使人们在接受对方的文化艺术时产生否定性的审美评价。也就是说,当审美主体看到异域作品中表现的审美意象之意义与本土的文化意义截然相反和对立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对异质文化审美趣味的否定。
可见,证异效应不仅受制于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它所带来的文化误读,而且还显示出东西方民族在艺术交流中对于异质文化的排斥和抵御心理。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审美主体不理解、不熟悉异域文化艺术而出现的对于异域审美信息的忽略以及感觉上的麻木,与主体对于异域艺术的否定和排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审美效应形态。
前者属于一种无睹效应,后者为证异效应。无睹效应是审美主体对于审美信息的遗漏和忽略。它往往表现为主体对于审美对象的熟视无睹和心不在焉,它首先缺乏的是主体对于审美信息的关注和兴趣,缺乏一种对于对象的积极体验和审视,不属于对审美对象的否定和排斥。因为主体对当下的审美信息尚未真正的接受过来,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审美,因此也就没有获得什么审美感受。而证异效应则是审美主体关注并接受、体验了审美信息,但由于审美对象所呈现的内容与主体本土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矛盾,从而产生了对当下审美对象的快速否定和批判。例如:我们听不懂西方音乐,于是心不在焉,使我们没能获得什么审美感受,这是无睹效应。但假如我们认真接受了这一审美信息,但产生了不适和反感,并对之给予了否定,这便是证异效应了。
三、对策与征服
如上所说,这种对于异质文化的否定与指责所表现出的证异审美效应,是跨文化艺术交流中的负效应。它使得东西方民族都不能客观而准确地解读异质文化,因此也就不能使人们获得应有的审美效果。基于此,在接受和引进外来文化艺术时,为了避免这种证异效应的产生,变消极接受为积极接受,提高审美效应的质量,东西方艺术家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积极的相应对策,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通常我们会看到以下对策:
(一)改编异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
为使本民族能更好地接受异域作品,东西方艺术家在引进外来作品时,一旦发现了与本民族文化相对立的难以接受的内容与形式,就往往要对它们进行适应本民族口味的改编。甚至有时会对原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动。就拿我国的《木兰辞》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花木兰的主要性格突出的是忠孝两全一面。而被美国改编后的动画片,为了适应西方文化的审美趣味,花木兰的形象完全改变了,她成了一个不事脂粉、不合流俗的女子,是一个在世俗生活中自我价值得不到体现的孤独女子,而在后来的替父从军、上阵杀敌中才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显然,这是一个充满了西方文化精神的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的花木兰。甚至我们还可以从中察觉到当代女性主义的味道。显而易见,美国人之所以把中国古代的《木兰辞》改编到在中国人看来近似荒诞的程度,为的就是能使本民族观众更易接受,从而减少证异效应。然而,当这种完全被西方化了的《木兰辞》动画片再重返中国本土时,又难免出现另一种证异效应,中国人难以接受早已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木兰辞》,在注入了西方文化观念之后,变得面目全非。
1983年北京人艺曾把《推销员之死》搬上中国舞台,但是由于当时中国人对于推销员这个职业还不了解,很容易产生对整部戏剧的误读和排斥,因此当时亲自担任该剧制作的英若诚与导演阿瑟·米勒便采取了灵活的方法,他们淡化了推销员这个职业,而把重心放到了中国人熟悉的家庭问题上。正如阿瑟·米勒所说:“中国人似乎最了解家庭,家庭是该剧的中心,社会与家庭冲突的关系早就是中国生活的构成部分。”⑨经过这一处理,该剧在中国的上演很快获得了成功。
为了对于异质文化作更直接的民族化的处理,有时翻译者在介绍异域作品时常常会对其进行随心所欲的改写。昆德拉曾经发现他的小说《玩笑》的法译者“没有翻译小说,而是把它改写了”,并指责译者从三个方面作了“再创造”。如果说《玩笑》法译本的改动尚属“技术性”操作,那么它的英译本则不仅其“章节的数目改变了,章节的顺序也改变了”(昆德拉)。其实,他没有注意到,这种改写,对于接受者来说,又往往是不得已的,或是自然而然的事。
改写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也表现在体裁上。当初林纾就将莎士比亚的几个剧本和易卜生的《梅孽》(即《群鬼》)译成了小说的形式。
(二)删除难以接受的内容和形式
如前所述,那些蕴含着与本土文化相对立的文化观念的作品,最容易引起接受者对作品的反感,从而产生证异效应。所以在引进异域作品时,介绍者对于那些感到不适的和本民族难以接受的一些内容和形式,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作删除处理。而这种删除常常是大刀阔斧的,毫不留情的。
近代翻译家苏曼殊就把雨果的《悲惨世界》)译成了仅仅数十回的故事,而删掉了大部分不易被接受的内容。前文提到的曾受到中国人指责的英国小说《迦茵小传》,其实在被林纾全文翻译之前,已经被蟠溪子(杨紫麟)翻译出版过一次。不过那一次的出版,没引起什么波澜。那是因为译者恰恰考虑到由于两种文化存在着差异和矛盾,如全文译出,可能会引起讲究“男女授受不亲”而不允许女子越雷池半步的国人的反感,所以刻意删去了迦茵与亨利相遇登塔取雏的浪漫故事,删削了迦茵与亨利相爱私孕的情节;把亨利为了爱情,不顾父母之命而与迦茵自由恋爱的内容也全部删掉了。而恰恰是这种删略,满足了当时读者群的期待视野,使该作得以顺利地被接受,没有出现明显的证异效应。而后来该作被林纾全部译出的风波,也正好证实了这种删除在当时的必要性。
证异效应不仅表现在对于异域作品中有些内容的排斥方面,也表现在对于某些表达手段和方式的拒收,所以为能适应本民族接受者的审美习惯,在翻译和处理异域作品时,译者们往往还对那些异质的表达形式进行删略。如西方文学作品习惯于对于自然景物和人物心理做大段大段的细致描写,这对于注重情节的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读起来常常感到厌倦,往往是个累赘,于是译者便将原文中有关自然环境的大段描写、人物心理描写删去,所译的主要是原文中的故事情节。伍光建在翻译小说《三个火枪手》(《侠隐记》)时,对原作表现人物性格的地方便采用了直译的方法,而对于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则压缩或节略,与故事情节及人物性格无关的议论,乃至西洋典故也删掉了。
无论是林纾翻译的《块肉余生述》,还是罗新璋翻译的《红与黑》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作品,都毫无例外地将他们认为“过于繁冗”、“无关宏旨的枝枝叶叶”的部分大刀阔斧地删除了。其实与其说他们删除的是所谓“繁冗”的部分,还不如说是本族接受者所不适应的异质而特殊的表现手段。这种在异族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并能产生特殊美感的表达过程,在中国人看来则成了影响审美效果的累赘,不删除则难以顺利接受。因此,删除和压缩便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民族化处理工作。
(三)增加注释
为减少接受者对于异域艺术的误读以及排斥,在翻译和介绍的过程中,增加注释不失为又一有效的办法。如伊夫·谢弗雷尔所说:“处理这个微妙问题的最佳办法,莫过于增加注释。最好朝着淡化处理甚至略加删节的方向改编”。①施咸荣的中译本《等待戈多》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让一个人物对着另一个人物窃窃私语,观众听不见人物的话,肯定会刺伤他们,但是却能理解人物之间的反映。显然,注释对于理解作品原作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同时这也是一个民族化处理的过程,更是一个使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过程。
中西方在相互翻译和介绍对方的艺术作品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比较详细的注释。如A.C.格雷厄姆英译的《庄子》就既有选译本,又有注释本两种。杜布里奇的《李娃传》和海陶伟的《庾信的〈拟咏怀〉》(载于《哈佛亚洲研究》第43卷第1期)其注文广涉先秦、汉魏古籍以及西方汉学界文史名著。注释又不限于对于一些典故的探本溯源,同时还对我国的时令、地理、科举、官职、习俗、礼仪等也作了较详细的说明。另外,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多不胜数的《诗经》选译和全译本中,有许多西方译者都有意识地增加了姊妹篇注释本。尤其是高本汉的《诗经》英译和《诗经注释》不仅趋向于雅致化,而且注释力求精确化,被认为是《诗经》西播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2)。这种翻译和介绍显然会增加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减少误读。
总之,为避免证异效应的产生,为征服这种消极性审美效应,以便更好地接受异域文化艺术,东西方民族都采用了多种办法,进行了有意义的实践和尝试,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四)扩大民族审美心理结构
显而易见,对于证异效应的征服和对策,仅仅靠以上方法显然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看到,证异效应的出现,不仅来自于文化的差异以及民族文化的偏见,还来自于不同民族长期形成的审美趣味的保守性和狭隘性。也就是说,一个民族越是不去接受新鲜、多元的异质文化和审美信息,而只是习惯于欣赏本土的文化艺术,只满足于对本土文化和审美趣味的认同,就越是容易排斥和否定异质文化艺术,从而产生证异效应。而仅靠删除和改编异域作品等办法来适应本民族的欣赏习惯,来避免证异效应,终非最佳选择。
其实,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观点来看,文艺接受过程,既是一个同化过程,也应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同化就是主体纳入和改造了他所能够接受的那部分信息的过程,而摒弃了不能接受的“异己”部分。但是,对于客体刺激仅有同化作用还不够,为了能接受新内容,主体还须改变原有的结构,建立新的结构,使之更好地适应客体,以期达到相对的平衡,这就是结构的调节作用。这种旧结构不断被新结构所取代的过程,皮亚杰称之为建构。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只有有意识地接受更多的异质文化和审美信息,从而扩大和改变自己的民族审美心理结构,才能高质量地接受异域文化艺术。更重要的是,这不仅可以减少证异效应,更可以在丰富民族审美趣味,扩展民族审美视野的同时,不断获得新的灵感和艺术启迪,吸纳到有益的多元文化营养。其实,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既是一个相互误读的过程,又是一个相互启迪的历史。而更多的是相互间的文化视野和文化心理结构的不断扩大,以及对于异质有益文化的不断吸纳。显然,只有摒弃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偏见,才能更好地接受异域文化艺术,不断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艺术。
四、结语
以上我们分析并阐述了证异效应的发生规律及对策,但毫无疑问,证异效应并非一成不变,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势必要发生嬗变。
我们知道,证异效应主要是来自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误读,来自于东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偏见。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同民族的跨文化交流愈加频繁和深入,随着东西方民族相互了解的增多,两大民族的文化误读也将不断减少。如此一来,在继续接受相互的文化艺术时,必将出现审美效应的不同程度的嬗变。证异效应也会随之转为其他效应。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东西方过去曾相互排斥和否定的许多艺术作品,现在都转而成了受人喜爱的被广泛接受的审美对象了。
综上所述,当一个民族对于另一民族还缺乏了解,甚至是陌生的时候,当一个民族对于另一民族的偏见过多、误解过多,甚至积怨过多的时候,也往往是证异审美效应产生最多的时候。文化的对立和差异,往往使人们不能以宽容、公正的态度去审视和接受异质文明的丰富的文化艺术,因此也就不能够获得应有的美感。而对于异域文化的武断指责和否定,显然是不可取的。在这种误读与偏见之下,许多美的艺术被亵渎,应有的美感被扼杀,人们的审美判断将偏离方向。在这种时候,无论人们怎样评价异域的文化艺术,都容易有失偏颇。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相互了解与沟通,就是不断交流和对话,就是相互尊重与珍视,就是不断有意识地扩大和丰富自己的文化和审美心理结构。要看到,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别种文化所无法替代的长处和优势,因此,它们也就理应受到尊重。更重要的是,恰恰是有了多民族、多文化的存在,我们的世界才会如此的丰富多彩和美丽动人,我们才有机会不断地被他者启迪着和鞭策着,从而获得自我发展的意外灵感和动力,我们有什么理由对一些异质文化进行鄙视呢!
证异效应的出现,似乎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但无疑它又是暂时的,它只能是一个过程。不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仍不会永远的消失。因为东西方文化都太悠久而博大了,它们都不会在文化交流中丧失自己的民族性,而总是在不断地发展着。东西方既要进行文化上的互补和借鉴乃至融合,又会下意识地守住自己的特质,这是文化传统性和民族性使然。所以过去的误读消失了,可能还会有新的误读发生。
不过,只要我们用宽容的文化态度去面对另一种民族文化和艺术,就会走出低层面的文化误读的误区,就将获得更多的令人惊喜的收获,这时,一个民族才真正走向成熟。
注释:
①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1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②董乐山:《文化的误读》,1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③[美]赛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14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
④[美]赛义德著,谢少波、韩刚等译《赛义德自选集》,164~16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⑤吴泽霖著《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163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⑥转引自滕守尧《对话与比较文化》,见乐黛云、勒·比雄主编《独角兽与龙》,9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⑦[清]邹一桂:《山水画谱·西洋画》。
⑧(11)[法]伊夫·谢弗雷尔:《戏剧:文化碰撞与多元文化主义之症结》,《文学评论》,139、139页,2000(3)。
⑨N.张:《中国对西方戏剧的引进,西方的另一意义(1978-1989)》,196页,巴黎,阿尔玛唐出版社,1998。
⑩见前引著作38页注释4。译注《哈姆雷特》的中文译名系根据法文译出。
(12)周发祥:《〈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71页,《文学评论》,19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