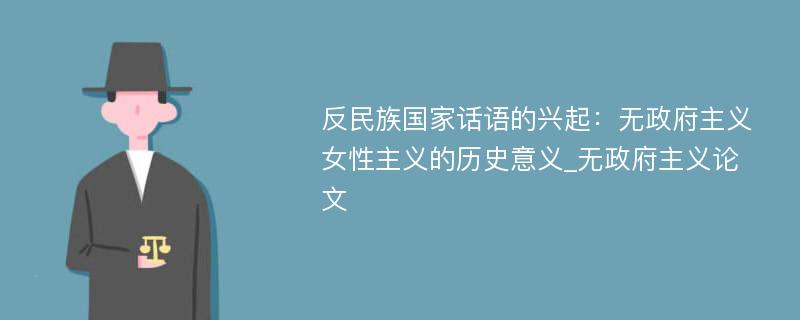
反民族国家的话语的崛起——无政府女权主义的历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无政府论文,历史意义论文,话语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里所论述的无政府女权主义,指的是1907至1909年间以《天义》和《新世纪》为中心,宣扬妇女解放的观点和言论,同时还涉及民国前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婚姻家庭观和妇女观。西方和海外的一些学者因为20世纪初中国的安那其主义者曾以《天义》、《新世纪》为阵地,发表过不少具有女权主义倾向的主张,因此将他们称为无政府女权主义①。在此笔者借用这一名称,但又不得不对此持一定的保留态度——笔者将在以下篇幅中作详细阐释。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20世纪初在中国所传播的无政府主义,从一开始就高举男女平等的旗帜,“男女革命”成为它的全面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重新打开那些被封存和悬置了上百年的历史,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在中国现代女权启蒙中如此强调民族国家话语的语境里,无政府女权主义却独树一帜地反其道而行之,这当然直接源自于无政府主义反民族国家的政治立场,但在整个女权启蒙的场景中却显得别具一格。
一、全面平等的基本立场——无政府主义对妇女问题的关注
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革命史的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曾在他的《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中强调指出,中国无政府主义自始至终注力于道德革命,向人民传播无政府主义关于个人、婚姻、家庭的观念,而“没有明确表达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独特的、全面的社会和政治哲学的观点”②,这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特征,从无政府主义早期的传播者“天义派”和“新世纪派”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安那其主义者们,出于无政府主义全面平等的基本立场,他们更多地致力于对个人、婚姻、家庭,甚至是妇女解放观念的阐释,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妇女解放的积极倡导者或鼓吹者,而且他们中的不少人早年还是这方面的实践者,例如,刘师培在接受无政府主义之前所作的《伦理教科书》(1905年),不仅阐释了父权社会产生的根源和批评了男女不平等的传统,而且提出了家庭改造的初步设想: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民国初年的两位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江亢虎、师复都曾身体力行地办过女学,1904年江亢虎在北京创办“女学讲习所”,培养女学教师,不久女学讲习所增至4所,前后延续了5年时间;1906年师复在从事暗杀活动的同时,也曾与朋友一起在广东香山创办过女子学校。
与中国现代早期一味企求富强的主流话语不同,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目标和理想是希望人类社会进入无剥削、无压迫的全面平等境界,所以妇女解放的话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纳入他们的视野。他们在抨击人类种种不平等时,对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也投入了较多的关注,这在《天义》和《新世纪》所刊登的一些非专门谈论妇女问题的文章中都可见一二。与《天义》不同的《新世纪》是一份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刊物,但在它的前期不仅登载过不少专门谈论妇女问题的文章,而且在一些专门论述无政府主义的“主干”性著述中(这些文章的主要特征:一是篇幅“宏大”;二是对无政府主义学说的介绍和阐释包罗万象)也有相当篇幅涉及妇女的现状或前景,例如较早在《新世纪》上发表的《革命原理》③和《无政府说》④,虽然《革命原理》所署是一篇翻译文章,但它的立论和阐述都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生活在欧洲的中国无政府传播者的立场,在阐述革命的理由时作者对现存的妇女及婚姻状态进行了抨击。《无政府说》则是紧接着《革命原理》在《新世纪》上登场亮相的“巨篇”,它同样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男轻女的现象予以批判:
今之重男轻女者,以男为尊,女为卑,男为贵,女为贱,男为强,女为弱,男为智,女为愚,一若女子为社会之赘物,此甚背万物自然之组织,而逆其发达之机体也。夫男女同为人,固无尊卑、贵贱、强弱、智愚之可分。脑力相等,惟昔之不教育女子,故女子之知识不能同于男子,此智愚之所由分也。男女身体之结构同,所异者,惟生育之机体耳,每月二三日不能动作过劳,受孕必有三四月不得畅快,分娩必有半月一月之休养,乳儿必有一年半载之牵累,此女子之弱于男子之点也。野蛮时代,俱以力争,适女子于月经或受胎或分娩时不能力战也,则女子为男子所征服,或男子为女子而战胜他人也,则女子为男子所保护。征服者尊,被征服者卑,保护者贵,被保护者贱,此女子生理上弱于男子,而尊卑贵贱遂由此定矣……
刘师培在《天义》较早时候发表的文章中也涉及妇女问题,例如长文《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在罗列人类不平等现象时曾详细分析了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指出男女不平等起源于私有制,并对西方现实中的妇女处境予以否定:
今耶教诸国,虽行一夫一妻之制,然服官之权、议政之权、近日女子间有获此权者服兵之权,均为女子所无,与以平等之空名,而不复与以实权。又既嫁之后,均改以夫姓自标,岂非确认女子为附属物耶,岂非夺其实权而使之永为男子所制耶。又西人初婚之后,必夫妇旅行,社会学家,以为古代劫女必谋遁避,今之旅行,即沿此俗。此亦女子为男子所劫之一证也。故今日之世界,仍为男子之世界,今日之社会,仍为男子之社会,安得谓之男女平等乎?③
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一样,中国无政府主义也都相信父权制社会之前曾存在过较为平等的、尊重女性的母系社会,他们也以此来抵御和反抗现存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基于对私有制的彻底否定和对平等的追求,无政府主义者们在对未来人类公平合理的生活设想中,屡屡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有制社会应考虑开设孕妇胎教室、乳母育婴室、男女配合室(有称为“士女行乐所”)、幼稚舍、学校、养老室等等⑥,主张彻底取消婚姻和家庭:“人人终其身处公共社会,无夫妇,故无父子兄弟,无家庭,故无继续法,生时所蓄余资,死则收入公中,教养诸费资焉。”⑦甚至提倡“男女杂交”,这些论点被当时及后来的人们称之为“公产公妻”。
从何震在《天义》上发表的文章来看,她明确表示接受无政府主义是在第三卷上为刘师培《人类均力说》一文所写的按语。刘师培在那篇文章中曾设想建立“栖息所”:“人民自初生以后,无论男女,均入栖息所,老者年逾五十,亦入栖息所,以养育稚子为职务。”这大概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对从育婴室到养老院这一大套社会福利和保障系统的最初设想。何震作为《天义》的编者则在刘师培这篇文章的文末写按语“欢呼雀跃”:
此论所言甚善,今之倡重男轻女之说者,均以女子所尽职务,不及男子,若行此法,则男女所尽职务,无复差别。男子不以家政倚其女,女子不以衣食仰其男,而相倚相役之风,可以尽革。况所生子女,均入栖息所,则女子无养育稚子之劳,所尽职务,自可与男相等。职务既平,则重男轻女之说,无自而生。⑧
从何震的这些议论看,她之所以倾向或接受无政府主义,是因为无政府主义对私有制的彻底否定和对平等的追求,这与她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相吻合。而对许多男性无政府主义者而言,他们也高喊男女平等的口号,提出了不少惊世骇俗或耸人听闻的见解和口号,他们更强调两性关系的自由,而忽视两性间的平等和社会道德责任。这多半出自他们要铲除私有制的信念,而不是从女性本位出发,设身处地为女性着想⑨。
在无政府主义(包括其它的社会主义)看来,人类的不平等起始于国家、政府以及家庭,而所有这一切又均根源于私有制。他们把由私有制而产生的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混为一谈,认为只要消灭了私有制就能达到全面平等(包括性别平等),因而也就能解决性别问题。所以,20世纪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家庭和婚姻:“自有家而后各私其妻,于是有夫权。”⑩他们纷纷喊出了“毁家”“废家”的口号:“自家破,而后男子无所凭借以欺凌女子,则欲开社会革命之幕,必自废家始矣。”(11)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集大成者师复在辛亥革命以后不久也曾专门著文《废婚姻主义》和《废家族主义》,他指出:“婚姻制度无非强者欺压弱者之具而已。女子以生育之痛苦,影响及于生理,且累及于经济,此为女子被欺之原因。”(12)“世界进化,国界种界,不久将归于消灭,故家庭必废。”(13)无政府主义对家庭全面彻底的否定就如它对民族国家的批判一样有其犀利和深刻的一面,但同时又给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尤其是妇女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包括何震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在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之后,她对究竟以性别平等为女权主义的纲领,还是以消灭私有制为首要任务,也开始变得模棱两可了。
其实,将性别压迫归根于私有制并非仅仅是无政府主义,国际社会主义思潮中涌现出来的“早期社会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波伏瓦都将妇女在承担体力劳动中处于劣势而受压迫与私有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14)。有关性别压迫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后来的西方女权主义者有着独到而深刻的阐释:早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人类社会就存在着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有自身运作机制的一种人类社会制度——“性/社会性别制度”(15),也就是说,性别压迫虽然与私有制密切相关,但却是由有着自身运作的一种制度而导致的,因而无法将二者混为一谈。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人们的思想框架中却还无法看清这一点,因此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和混乱是在所难免的。
《新世纪》与《天义》被并称为20世纪初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性期刊,而且它们都同样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但在有关如何平等和如何解放的问题上,男性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与以何震为代表的无政府女权主义却不能同日而语。何震与绝大多数的男性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更多地站在历史和现实的女性处境和立场上说话,而一些男性无政府主义者则更多地从无政府的信念或原则出发,有意或无意地主张实行一种放纵自由的两性关系,甚至为达到耸人听闻而制造一些哗众取宠的言论和口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何震是与他们泾渭分明的。以《新世纪》为代表的男性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设男子另有所爱,则可娶妾嫖娼,女子则不能,其不公之至,人人得而见之。设男子得御他女,则女子亦应御他男,始合于公理也。”(16)在这些男性无政府主义看来,男女要取得完全平等,女性就要像男性一样,男人可以嫖娼,女人也可嫖男人,男人可以一夫多妻,女人也可多夫。而何震最初发表在《天义》上的文章中早已对这样的观点作了痛斥:“男子多妻,男子之大失也,今女子亦举而效之,何以塞男子之口乎?况女子多夫,若莫娼妓,今倡多夫之说者,名为抵制男子,实则便其私欲,以蹈娼妓之所为,此则女界之贼也。”(17)
何震更多地立足于一种自然的女性立场来理解无政府主义的有关学说,尤其是她对传统婚姻家庭的否定和批评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天然女权主义的立场上。实际上,在当时某些中国男性无政府主义者的眼里,消灭家庭婚姻与其说是为了解放妇女,还不如说是在旧的伦理纲常分崩离析之际为男人自己及时行乐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和自由,他们主张消灭家庭的动机直接来自于他们企图摆脱现实生活中、尤其在家庭生活中(包括对妇女)的责任——他们将此视为拖累、障碍等等。只要回顾一下蔡元培等人分别于民国初年和1918年先后发起成立“进德会”或“社会改良会”以及1912年师复组织的“心社”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男性娶妾、狎妓成风,而与此为伍者有不少是“先进”男性,使得那些稍有道德感或廉耻感的男性不能不痛心疾首而发起改良“社会之腐败”的运动(18),这些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成立意味着“它把改变成员的道德看作社团的工作重点”(19),它们的成立被后人视为“一种道德启蒙运动”(20),实际上它又与女权启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中“社会改良会”明确规定的入会条件除了“不狎妓”、“不置婢妾”之外,尚有“实行男女平等,提倡废止早婚,提倡自由结婚,承认离婚自由,承认再嫁之自由,废缠足、穿耳、敷脂粉之习等等”(21)。
也许在今人看来,何震有关男女平等的思想不仅毫无新意,而且还趋于传统保守,例如她在《女子宣布书》中对一夫一妻制的维护,而且强调夫妇关系不合可以离婚,但在离婚之前双方都不能以任何形式与第三者结合,否则就是违反一夫一妻制。在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看来,婚姻家庭都被列入要消灭的对象,一夫一妻制则更不在话下。而何震却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甚至提出要以初婚之男配初婚之女,凡是离过婚的男性只能与离过婚的女子结合,这样才能达到男女或夫妻之间的真正平等和公正。这一点在当时就遭到日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的异议。当幸德秋水读到《天义》上何震的这些文字时曾写信说:“夫妇关系之第一要件,在于男女相恋相爱之情。纵令初婚之夫妇心中,无相恋相爱之情,则固有妨于夫妇之道。又令再婚之男与初婚之女,真克爱恋和谐,何害其为夫妇乎?”(22)很显然,何震在这里是要强调男女结合的神圣以及由这种结合而带来的对他人和社会的道德责任感,虽然它在表述的时候不免显得有些教条。何震还曾应幸德秋水之邀,与他和堺利彦一起讨论过妇女问题。事后,何震在《天义》上直截了当地指出:“盖幸德君及堺君之意,在于实行人类完全之自由。而震意,则在人类完全之平等。立说之点,稍有不同。”(23)男女之间对婚姻关系看法的分歧也许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平等与自由的分歧,五四之后的一个例子可能也能说明一点问题,据周建人在《妇女杂志》上所述:
去年本志征求对于不合意的旧妻可否离婚的意见,答者差不多是可否参半。对于结婚仪式应否废止一个问题,则男子大半主张撤废,而女子多半主张保存。再就近来所常见的已婚男子恋爱别的女子的问题而言,有的以为非和前妻已经离婚,不得和别的女子发生恋爱,或既和别的女子恋爱便当和前妻离婚;有些以为既和妻感情不和,不妨另行组织新家庭,或者即和前妻并不伤感情只要与别人是真实的恋爱也是无妨的。各人的意见的不同如此,至于女子的意见,在已结婚的常常说已婚男子决不能再和别的女子恋爱,女子也决不可以恋爱有妇的男子;未婚的则是说如男子恋爱别的女子时,必须立刻和前妻离婚。(24)
从字面上读来,似乎女性显得保守而落后,但实际上在一个男女不平等、女性没有安全感的社会体系内,女性有这样的看法和主张是非常合理的——她们只能诉求于制度而得以受到庇护或保障。
无政府主义全面平等的基本立场使得中国早期的接受者们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现存社会体制的否定,毫无疑问,中国无政府主义又是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投入最大关注的一种社会思潮。但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谈论妇女问题时,因为受到种种传统观念和思想的制约,对妇女的关注不是出于自身的切肤之痛,而是出于一种对主义的真诚信仰——为铲除私有制,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从而提倡取消家庭、婚姻,让女性实现彻底的“解放”(在他们看来的解放),最后将妇女解放引向一种歧途。
二、无政府主义反民族国家立场对女权启蒙的矫正
无政府主义是在20世纪初由政治上比较敏感的保皇派传播到中国的,一系列介绍俄国虚无党的翻译著作都是由具有保皇派背景的广智书局出版的,保皇派对其暗杀手段有兴趣,而对其主义本身则多保留和批评。为《天义》所推崇备至的法国女无政府主义者露易斯·米歇尔在1903年间就被《世界十二女杰》和《世界十女杰》大书特书过(25),同样,保皇派背景的女权启蒙对无政府女英雄采取的态度也同样是不太过问她们所信仰的“主义”,而看重她们为主义赴汤蹈火的精神。对“主义”本身的忽略和模糊不清,也许是导致无政府主义在译介成中文时很大程度上被歪曲的重要原因之一。
安那其主义(Anarchism)在译介到中国的过程中被曲解为“无政府主义”,其中主要是因为作为中介的日译从一开始就铸成了曲解,而中国社会的接受背景也对这种歪曲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Anarchism词源为An(=无)+archi(=支配、权力、暴力、压抑)。当它被译为“无政府主义”以后,便成为否定合法政府和一切组织的混乱和暴力的代名词(26)。也就是说,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它所否定和批判的是一切强权(包括国家和政府)。毫无疑问,对国家和政府的否定只是它的一个侧面,然而在以民族国家为主流话语的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里却成为无政府主义一个夺目的主题和特征,从而迅速地形成了一股反民族国家的“逆流”。从正式接受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派知识分子来看,无论是天义派、新世纪派,还是后来的中国社会党和民声派的核心成员——刘师培、张继、李石曾、吴稚晖、江亢虎、师复等等,早年都从事过排满活动,在不同程度上都属于民族主义者,当他们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之后,不论是在政治革命领域还是在文化革命领域,几乎无一例外地从反清革命论者走向社会革命论者。仅就《天义》和《新世纪》上所发表的一些文章来看,他们不仅批判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同时也批判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他们在中国最早公开打出了取消国界和种界的旗帜,也就是说要取消民族国家的存在,在他们看来政府是万恶之源,无论是专制还是共和民主的国家制度都是不可取的。
刘师培发表于《衡报》创刊号上的《论国家之利与人民之利成一相反之比例》一文,可以被看成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反民族国家的代表作。它上溯秦始皇下述近代西方各国列强,集中论述了国家图强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宁所发生的尖锐冲突和对立,他指出:“考之中国历史,国力有一次之扩张即生民罹一次之劫掠,凡四方之乱均生于国力扩张之后,且非惟国力扩张之病民也,即以国力扩张为目的,其结果亦莫不病民……凡有利于国者均不利于民,凡在平民慎勿以国家一时之虚荣引为己身之利益也。”他还阐释了国家并非是一种“实有”而是虚构,就如同宗教和迷信一样,是统治者为了更方便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而制造和植入广大平民内心的一种自圆其说。文章的最后他呼吁人们认清国家的本质从而颠覆和取消国家的存在,消灭国界种界及国际间的战争,使广大平民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27)。
“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也持同一种立场,他们对祖国、种族等概念大加讨伐:
爱种与爱国,同一癖也。爱国即爱种,爱种即爱国。所差异者,不过随历史之感情,与国际之交涉耳,前者由于恩仇,后者由于利害。苟有世仇,国同而种异者,则趋于民族主义(如满汉等);种同而国异者,则趋于国家主义(如中日英美等)。有世恩,种异而国同,则祖国观念生;国异而种同,则种族感情起。至于利害,则有异乎斯。同利害则相爱,不同利害则相妒,今日唇齿,明日吴越,同国而异种,同种而异国,皆不问也。(28)
无政府主义对国家种族利益的否定可谓全面彻底,这一基本立场极深刻和有力地影响着他们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问题的阐释。“天义派”无政府主义者出于这样的政治立场,既反对现代意义上的女子参政,也不主张女性就业。他们认为,“以议会政策为目的者,无论出何党派,决无有利平民之一日”(29),况且绝大多数妇女不仅受到男性的民族国家制度的压迫,同时也遭到富贵女性的奴役,所以他们反对妇女参政:“妇人参政为近日一大问题。然其争参政之权,即系承认有国家有政府也。故本社之志在于灭绝人治、消弭男子之特权。使男女归于平等,不仅以妇人参政为目的也。”(30)何震认为:“以少数参政之女子,处于主治之位,使多数无权之女子,受其统治,不独男女不平等,即女界之中,亦生不平等之阶级。”(31)他们甚至也不赞成妇女就业,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前后所提出的“分利说”,实际上包含着号召妇女为国家富强而投身社会劳动,并争取经济上的自立。“天义派”认为这种资产阶级的富强学说产生了“劳动买卖之奴婢制度”,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只能“使女子日趋于劳苦”(32)。就像他们认为女子参政会被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所利用,女性就业同样也会受到资本家乃至国家体制的剥削和压榨,都是妇女解放不可取的方式方法。在他们看来女性要实行彻底解放只有等到全社会都实行了全面平等的无政府主义之时。
无政府主义比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更早地关注到女性群体中的阶级差异,何震等人更多地关注女工、奴婢、娼妓、农妇等等下层妇女的苦难和利益,在考虑到她们受男人统治和压迫的同时,还指出她们受到富贵阶层妇女的奴役和剥削(33)。这是中国女权启蒙中其它群体未能也无力作出的关注。从中国女权启蒙的整个过程来看,注重女性这一被压抑群体内部的阶级分层,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传播者之外,是极少被人问津的,而无政府女权主义则是少数在这方面有专门论述者之一。总之,无政府女权主义与以富国强民为主题的女权启蒙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反对女性效忠于任何形式和任何内容的民族国家。
志达是一个在《天义》上发表有关妇女问题的重要作家,他/她出现的比例之高仅次于何震。针对20世纪初中国女子教育中以效忠民族国家为宗旨或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的现象,志达阐述道:
……汇集古女子之言行,取其关于忠孝节烈及明智贤达者,以为准鹄,推其意旨,无非使女子从事于家庭伦理,以尽其殉父殉夫之节或相夫教子,以使之作国家纯全奴隶耳……又杂伺以军国主义,以小戎无衣之风,提倡于女界,夫因此主义以激发女子革命之心,此固至良之教法,若仅勉女子以爱国,则是导女子于国家奴隶耳,故今日中国女校,其伦理一科,非迫女子为家庭奴隶,即迫女子为国家奴隶,其立意虽殊异,而其为奴隶教育则同。(34)
无政府女权主义基于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强权的政治立场,将中国妇女问题的重心移到了男女平等这一点上,在他们看来,妇女解放的前提是男女平等,而不是女权启蒙主流话语所强调的——小至当一个家庭的贤妻良母,大至做一个救国救民的“女豪杰”。民国前后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江亢虎曾一再批评这样一种妇女教育的思路和框架:
中国女子教育完全一家庭教育而已。近来虽有学校教育,然亦完全一家庭主义之教育而已,故其恒言曰良母贤妻,曰相夫教子,盖所谓女子教育者,并不以教育女子自身为目的,特为夫与子造成适当之补助人格而已。其后国家主义之教育大盛,其影响旁及于女学,于是女子教育似亦由家庭主义进于国家主义,故又有恒言曰,女子者国民之母也。然细绎其意,亦不以教育女子自身为目的,特为国家造成产出国民适当的补助人格而已。故上两者表面所称道虽各不同,而其实皆可名为补助人格之教育,余尝于演说场痛斥之,以为果采用国家主义之女子教育,则当曰男子国民也,女子亦国民也,今男子不曰国民之父,而女子独曰国民之母,是明明不视女子为国民矣。盖余对于女子教育之意见,自初讫今断然排斥家庭主义与国家主义,而主张世界的个人主义,即以造成世界上自动的个人为宗旨者是也,余一方面承认女子与男子各具特殊之天才,一方面承认女子与男子同处平等之地位。(35)
虽然江亢虎被不少人认为是一个非无政府主义者或假社会主义者,但我认为他在民国前后基本持无政府主义立场,尤其是在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和主张方面,他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在谈到无政府主义有关男女平等方面的思想和言论时,不能不提到他。上面的这段文字也体现了无政府主义在妇女与民族国家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他们反对现代的女子教育引导女性从顺从婚姻家庭到效忠民族国家这一整体性思路,而从男女平等原则出发倡导女性成为与男性一样的人。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时刻打出反民族国家的旗帜,令人有标新立异甚至离经叛道之感。《天义》曾以《石破天惊谈》为题,直接揭示了以民族国家利益取代和遮蔽妇女权利的实质:
男子曰,满洲吾仇也,是当攘;女子也从而和之曰,满洲吾仇也,是当攘。夫男子之仇,尤重于满洲之仇,今也助仇人以攻其所仇,转置切身之仇于不顾。或者曰,男倡女随古礼也,今女子执排满之说,附和男子,吾无以名之,则名之曰真倡随。(36)
它明确指出,排满是男人们发明的口号,现在女人被动员起来也高喊排满,实在是为男人所利用,女人忘记了自身一直受着男人的歧视和压迫,却去为男人们的民族国家效力。这直接点破了女权启蒙与夫唱妇随传统的一脉相承之处,对无政府女权主义来说,无论是贤妻良母还是“女豪杰”,都是受制于男性中心文化传统的“奴隶”,因此女性要获得彻底的解放,就必须摆脱奴性或隶属关系——不仅不做男人的奴隶,也不做国家或民族的奴隶,当然更不做专制君主或异族统治者的奴隶。
三、与民族国家话语的缠绕和混淆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无政府主义如此风光,与民族国家的主流话语形成了巨大反差和对比,从更为广阔和深远的时空来看,反民族国家话语毕竟是一种“弱势”话语,从它如此迅猛的发生和发展到如此急剧地衰竭和消失,强大的民族国家话语无疑是其重要的催化剂。而且即使是在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受民族国家主流话语的干扰也是显而易见的——某些无政府主义者在否定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的同时,又沉迷于“强种”“强国”的学说。在此笔者打算详细地分析一下《男女杂交说》——这是一个貌似极端偏激而实际则囿于“强种”学说浑然不觉的个案。
在无政府主义大量反民族国家的言论中,虽然大多数在政治上具有鲜明的反民族国家立场,然而,他们中的某些人却囿于强大的富国强民话语而“无以自拔”。鞠普的《男女杂交说》一直被认为是一篇非常偏激的无政府主义关于废除婚姻家庭的文字,仅从作者开篇所表明的主要观点就可一睹它的“激进”:
人群之不进化,爱情之不普及,实婚姻之未废也。今欲人群进,爱情普,必自废婚姻始,必自男女杂交始……(37)
与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尤其是后来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是,鞠普倡导的“男女杂交”或者自由的不确定的两性关系并不是出于当事人的利益和意愿。作者的意图似乎很明确:彻底地否定传统的婚姻家庭和民族国家。然而,在具体阐述“男女杂交”这一“公理”时却借助了“强种”这一深入人心的普遍真理,从而走向了自己立论的反面。众所周知,“强种”是整个现代中国民族国家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富国”一同构成了一种特定的话语形态。这篇以“男女杂交”为主题的文章很少涉及男女婚姻(无政府主义不承认以法律为形式的婚姻)和恋爱自由,也回避两性关系对当事者的愉悦意义,却从四个方面阐释了男女杂交对人种进化的益处:一、不杂交者种不进;二、不杂交者种不强;三、不杂交者种不智;四、不杂交者种不良。总之,杂交能够增进人种的强盛、聪慧和优秀等等。作者急切地呼吁“男女杂交”的立论是建立在强种强国这一主流话语的基础之上。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如此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建立他们新的伦理观念时依然难以逃脱民族国家话语这一巨大的“掌心”。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既然一切国家形式都是不可取的,既然中国有史以来的民族文化传统也都是与无政府主义的信条相抵触的,作者为何还要以维护这个种和这个国为基本出发点呢?这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就如上述民《无政府说》一文已强调的“爱种即爱国”,也就是说,对无政府主义而言,“种族”的概念是民族国家范畴内的概念,是为无政府主义信念和原则所反对和否定的。
鞠普在这篇短文中使用了大量表达强大的词汇,诸如横行一世、强盛、雄武、魁梧雄伟……等等,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强”的认同——他/她缺乏无政府主义起码的与强势抗衡的平等意识与立场,怪不得文末所附署名“燃”(此为吴稚晖之笔名)的批评对此极不以为然,但“燃”只是批评了鞠普过于强调人种进化而忘却了无政府主义的爱情观或世界观,并未指出鞠普心系强国强种这一与无政府主义基本原则相抵牾的根本性错误。而且不论编者按语如何批评鞠普的观点,《新世纪》发表这篇文章本身则导致了它自身在立场和信念上的混乱。
鞠普认为中国从宋代以后衰败了,究其缘由只是因为宋儒“……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由是女子遂永堕十八层地狱,鲜能遂其爱情者矣。故怨旷之气,上于天地之和,困郁之余,遂传愚弱之种,人群退化,至是极矣。彼他族之不重名节者,遂日强盛,凭陵侵侮,入居中国矣”。作者进一步作了血气方刚的追问和责难:“今使我神洲人种,气息恹恹,形容枯槁,弱不胜衣,血不华色,无论与西方人立,与东方人立,皆觉自惭弱秽者,是谁之罪耶?”不仅表露出极为强烈的民族意识,而且还深深地沉缅于男权谱系而毫不知觉——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实际上是以男权谱系为主体的一种盛衰史,作者对此的眷恋表露了他/她对民族国家这一根深蒂固观念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同。
另一方面,作者也流露出对传统和世俗观念的抗拒和颠覆,与传统的男女关系的井然有序相悖,鞠普不仅宣扬废除婚姻,还主张杂交和乱交,并以中西文化传统创始人的生平为例进行“现身说法”。为了充分证实“惟女子杂交,故进化最速,所生之人亦最良”这一论点,他/她以孔子、耶稣和传说中感天而生的聪明强武的古代帝皇等等的神话故事或历史传说为例,作出“皆女子杂交,故产奇杰也”这样牵强的判断。同时还将当时西方各国的强大也说成是“男女之界不严,故其人种,亦英武多姿,横行一世。”更令人咋舌的是作者将日本的“传种改良”归功于“娼妓四出”,这令同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编辑吴稚晖大不以为然:“尤似太附会而失其实。日本社会陈旧,至今贵族士族平民新平民,阶级分明,作者所谓今之壮佼颀硕之日本人,谁则可确指为娼妓所生……”(38)吴稚晖的这种不满似乎很意犹未尽,因此又在第五十六号的《新世纪》上提出质疑:“杂交之名词,若以为惊世骇俗,则世俗自惊骇耳,谈主义者,可不必以本报小人之腹,度天下君子之心也。惟在术语上,自与自由配耦,其义互有不同。杂交者即异种交合所生良,同种不良之说。此科学之定理,不可破也。自由则推而又进,虽交合既能异种,(交合必异种,乃交合者应当自守之真理公道,并不需他人强之)。而又任两异种以爱情自相配耦,绝不许第三人之干涉,如婚律之与婚礼,皆无理之干涉也。……娼妓以饥寒求得钱,强与人交,最为不自由,又与自由之意不合也。”(39)吴稚晖在这段话中还是重复了附于《男女杂交》文末的按语,无非是更强调男女两性的自由结合,而仍然没有触及鞠普在民族国家这一问题上似是而非的立场。
鞠普的这些立论和论述使我们看到了当时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及东洋诸多列强时,深深地自惭形秽,以致形成与这种“强势”相认同的巨大情结。有趣的是,20世纪初的梁启超也曾呼唤过类似人种杂交的向往,而且也是以科学或“生理学之公例”的名义:
种植家常以梨接杏以李接桃,畜牧家常以亚美利加之牡马交欧亚之牝驹,皆利用此例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两纬度不同之男女相配所生子必较聪慧,皆缘此理。(40)
梁启超还由此推及世界各大文明的兴盛,他认为无论是欧洲文明还是中国战国时期的文明或后来的隋唐文明都是在两种文明的碰撞或“交媾”中产生的,所以他大声疾呼:
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41)
女性主义对其背后的欲望想象以及异性恋父权婚姻关系已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42),笔者在此就不多言了,只是想强调一点:梁启超如此论述完全是出于他急切的富国强民立场——他通过对西方“美人”的想象或欲望对象,给中华民族注入一份强健和娇好,而鞠普的立场又何在呢?我们以“混乱”和“杂芜”来形容当时某些无政府主义者在男女两性问题上的论述和认识水平,不仅是指他们的一些刻意惊世骇俗的表述,更是指他们那些变化莫测而又昙花一现的观点。就是这位名为鞠普的作者,在发表于《男女杂交说》之前一个月的《〈礼运〉大同释义》(43)一文中曾提倡“使男子知有分际而不妄交,女子知应归宿而不乱合”,而时隔一月却公然打出“男女杂交”的旗号,且不论它是否过于偏激,这种变化本身实在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不明白作者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表述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他/她在《〈礼运〉大同释义》一文中振振有词地论述道:“人类之争,起于男女,妍媸不同,苦乐或异,一也。男女之数,势难相等,供求不给,匹配难均,二也。女子有天癸之期,有孕育之期,不予维持,实碍卫生,三也。女子阴绝早,男子阳绝迟,生华生稊,人情不乐,四也。男女相合,不宜太杂,纵欲过甚,生齿不繁,五也。故是时必有一公认之规则,使男女之合,必有其地,必有其时,必有其数,必有其类,于自由之中有限制之法。”(44)而到了《男女杂交说》中,除了为“种”强弱这一至关重大的利害权衡之外,这些“限制”似乎都不存在了,值得肯定的男女关系只剩下了“杂交”一种形式了。
现在几乎已无法确定鞠普是借强种话语作为手段而达到改善两性关系的目的呢,还是以“杂交”为振聋发聩的幌子来宣扬强种。无论两者孰因孰果,总之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上登载了如此一篇以宣扬强种的文字,这确实体现了一个时代与一种“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与矛盾。
正如笔者已反复论述的,中国现代的民族救亡话语是统驭一切的主导话语。无论是正面的民族动员,还是形形色色反传统、反民族或反国家的主张和言论,无不是依附于它,或由它分化、演变而来。即使是自称为“激烈派第一人”的刘师培,在1903年至1904年间曾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而到了1907年则迅速“转变”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而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刘师培,也依然夹杂着民族主义的“尾巴”。兴国强种的理念和情感纠葛对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无论是何震还是其他的无政府女权主义者宣扬女权主张的日子或篇章都屈指可数,而以振兴民族国家为主题的女权启蒙却贯穿了半个多世纪,甚至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以后。
注释:
①Peter Zarrow(沙培德):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该著以“妇女解放与无政府女权主义”为一章专门论述了无政府女权主义。日本学者小野和子(Ono Kazuko)在其著《革命世纪中的中国妇女》(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也以“无政府女权主义”来指称何震等人。
②参见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学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③革新之一人:《革命原理》,真(李石曾)译,《新世纪》第22—30号,1907年11月16日-1908年1月18日。
④民(褚民谊):《无政府说》,《新世纪》第31-36、第38、40、41、43、46、47、60号,1908年1月25日-1908年8月15日。
⑤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连载于《天义》第4、5、7卷,1907年7月25日、8月10日、9月15日。
⑥参见《与人书》,载《新世纪》第13号,1907年9月14日;X与X:《谈无政府之闲天》,《新世纪》第49号,1908年5月30日;高亚宾:《废纲篇》,载《天义》第11、12卷合册,1907年11月30日。
⑦徐安诚(江亢虎):《无家庭主义》,载《新世纪》第93号,1909年4月17日。
⑧申叔:《人类均力说》,《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⑨有关何震与《天义》的关系,参见拙作《从女权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何震的隐现与〈天义〉的变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2期),此处不再赘言。
⑩鞠普:《毁家谭》,《新世纪》第49号,1908年5月30日。
(11)汉一:《毁家论》,《天义》第4卷,1907年7月25日。
(12)师复:《废婚姻主义》,《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第107页。
(13)师复:《废家族主义》,《师复文存》,第115页。
(14)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6页。
(15)盖尔·卢宾(Gayle Rubin):《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4页。
(16)真(李石曾):《男女之革命》,《新世纪》第7号,1907年8月3日。
(17)震述:《女子宣布书》,《天义》第1卷,1907年6月10日。
(18)李石曾、汪精卫、张继、吴稚晖等人于1912年发起成立“进德会”,见《进德会会约》,《民立报》1912年2月26日;蔡元培:《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19日。这些组织都将“不嫖”(或“不狎妓”)、“不娶妾”(或“不置婢妾”)写入会约。
(19)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118页。
(20)曹世铉:《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
(21)曹世铉:《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第232页。
(22)《幸德秋水来函》,《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23)《幸德秋水来函》(震附记),《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24)建人:《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妇女杂志》第十一卷第一号,1925年11月。
(25)《世界十二女杰》,上海:广智书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发行;《世界十女杰》,无作者署名,无版权页,据编者序言似应为上海苏报馆于1903年所印。
(26)曹世铉:《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第3页。
(27)申叔:《论国家之利与人民之利成一相反之比例》,《衡报》第1号,1908年4月28日。
(28)民:《无政府说》,转引自胡庆云、高军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9页。
(29)申叔:《社会主义与国会政策》,《天义》第13、14卷命册,1907年12月30日。
(30)独应:《妇女选举权问题·案语》,《天义》第7卷,1907年9月15日。
(31)震述:《妇人解放问题》,《天义》第8、9、10卷合册,1907年10月30日。
(32)畏公《论女子劳动问题》,《天义》第5卷,1907年8月10日。
(33)畏公:《女子劳动问题》,《天义》第5、6卷,1907年8月10日、1907年9月1日;震述:《论中国女子所受之惨毒》,《天义》第15卷,1908年1月15日;志达:《女界吁天录》等等。
(34)志达:《女子教育问题》,《天义》第13、14卷合册,1907年12月30日。
(35)江亢虎:《中国女学古今谭》,《江亢虎文存》初编,上海、南京:现代印书馆,1944年,第141页。
(36)此文未署作者名,载《天义》第8、9、10卷合册,1907年10月30日。
(37)鞠普:《男女杂交说》,载《新世纪》第42号,1908年4月11日。鞠普被Peter Zarrow认为有可能是蔡元培的笔名,见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p.291,注47。但据蔡元培《复吴敬恒函(一九○八年)》中的一段文字:“近日《新世纪》所载荷兰来稿,未知何人所为?其引证虽多刺谬(先生所驳,弟皆表同情),而其笃信社会主义,殊为难得也。”(见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似乎又可证明:最初注有“荷兰来稿”的作者鞠普并非蔡元培。
(38)鞠普:《男女杂交说》,载《新世纪》第42号,1908年4月11日。
(39)燃:《答某君》,载《新世纪》第56号,1908年7月18日。
(40)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页。
(4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七》,第4页。
(42)刘人鹏:《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一书中“强权欲望里的西方美人与杂种宁馨儿”一节,台北:学生书局,2000年,第137-154页。
(43)《新世纪》第38号,1908年3月14日。
(44)《新世纪》第38号,1908年3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