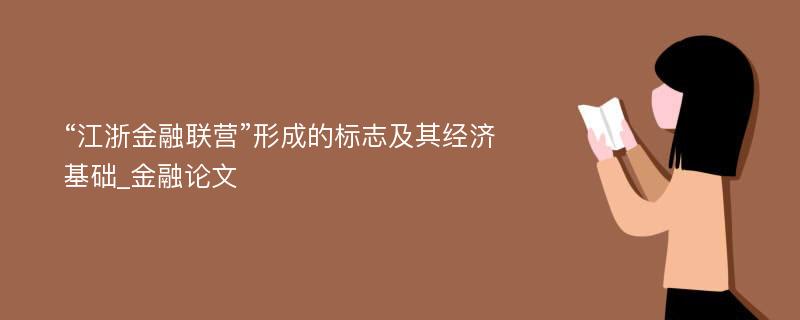
“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标志及其经济、社会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团论文,江浙论文,标志论文,基础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江浙财团”、“江浙财阀”和“江浙金融财团”
“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是中国金融资产阶级最为成熟的典型形态,也是其最有经济实力的组成部分。对于它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能正确了解和认识江浙金融资产阶级乃至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资产阶级。对江浙金融资产阶级传统的看法是“1927年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以后并依靠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来获取暴利”(《辞海》语),其实,事情远非这样简单,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活动也决不止此。它曾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广泛参预了中国近代社会,除开体现其阶级利益的政治活动外,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对于近代上海和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比寻常的巨大作用,尤其须加注意的是,这种“作用”还由上海幅射全国;第二,江浙金融资产阶级二十世纪前半期所走的路也是中国资本主义所走之路,研究它有利于人们认识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寻求、奋斗、挫折。从而准确认识新中国史前国情;第三,研究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有历史的启迪作用,使人们正确了解和认识今日金融并努力造就和发挥金融企业的集团优势。
但是,由于对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研究尚待深入,至今,学术界对于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称谓尚未有较为科学、明确的说法。到目前为止,涉及到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称谓有“江浙财团”、“江浙财阀”、“上海财团”等多种。这些称谓大都带有非严密性和不确定性。如,“江浙财团”一词有时被用来说指以上海为基地以江浙籍资本为主体的大资本集团,它不仅包括金融资本集团,还包括工商资本集团;它不只是单纯的银行资本,而是银行资本、钱庄资本、商业资本、工业资本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资本集团。因为“江浙财团”以上海为基地,支配着上海钱庄业、商业团体和各大商号、多数工业企业及主要航运公司、商业银行及各类买办和经纪人,成为影响上海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因素,人们有时也将“江浙财团”称作“上海财团”。“江浙财团”一词有时又被用来专指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有的金融史著述中将“江浙财团”与华北、华南、华西财团并称为旧中国四大财团便是一例。在这里,华北财团是指对华北金融有一定影响力和操纵力的以“北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为主体的银行资本集团;华南财团主要是指设立并活动于广州、香港的一批广东省地方银行及侨商银行,侨商银行中又以工商银行、广东银行、东亚银行、华商银行、国民商业储蓄银行为主;华西财团是指活动于四川一带的银行资本集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银行是聚兴诚银行,聚兴诚银行有“川帮银行首脑”〔1〕之美誉。在中国金融史上是否客观存在着华南财团和华西财团乃至“四大财团”,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姑且不论。但人们将”江浙财团”与华北、华南、华西财团并列在一起时,“江浙财团”所指的又显然只是江浙金融资本而不包括其它类型的资本。“江浙财团”这样一个名词一忽儿被用来泛指以上海为活动基地的以江浙籍为主体的大资本集团,一忽儿又被用来专指江浙金融资产阶级以及他所把持掌握的江浙金融资本,这不能不给人以一种该名词内涵不确定的混乱之感,缺乏学术的严谨性。
在有的著述之中,“江浙财团”又被称之为“江浙财阀”。“财阀”一词是从日本借用来的。一般理解,它是对那些控制着大银行和工商垄断组织的金融告寡头的通称,如日本的三井财阀、三菱财团等。而从江浙金融资本及其主体“南三行”(上海商业、浙江实业、浙江兴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们都属于上升中的私人金融资本,在30年代以前,业务发展迅速,资本规模日趋扩大,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也日益增涨,但它们远未达到“金融寡头”的垄断程度,因此,称他们为“江浙财阀”似乎欠准确,也不科学。
为了摆脱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及江浙金融资本称谓的混乱,也为了对之研究的方便,我们以为将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称为“江浙金融财团”较好。“江浙金融财团”与“江浙财团”是两个互相联系的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江浙财团”是指以上海为基地并以江浙籍资本为主体的大资本集团、包括金融资本及工商业资本。从地域范围看,“以上海为基地”并不意味着该财团的所有企业资本都集中于上海,也可能分布于邻近上海的其它江浙地区。诸如,张謇所创办并直接领导的大生企业系统、其主要部分设于江苏南通、海门而非上海,但它同上海有密切联系故尔同样是江浙财团的构成部分;从财团成员的籍贯组成来看,江浙财团不仅包括了江浙籍资本家,也包括了一切以上海为活动基地的其他籍资本家,但是,在财团内地位突出、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江浙籍资本家;从江浙财团的整合度看,其内部的结合与联合时而紧密、时而松散,入民国后,逐渐形成代表江浙资产阶级利益的紧密型代表人物层。“江浙金融财团”并不等于江浙财团,但它与江浙财团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江浙财团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江浙财团的核心和灵魂,是它决定着江浙财团的总体性质。本文所要研究的是“江浙金融财团”而非整个“江浙财团”。
二、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三大标志
在辛亥革命之前,虽有一批江浙籍官僚、买办、旧式商人转化而来的资本家如叶澄衷、朱志尧、祝大椿、严信厚、张謇等参预工业企业或近代银行的创办与投资,但那时,并未形成一个江浙金融财团。
江浙金融财团逐渐形成的时间是在北京政府统治时期。之所以如此判定,是因为江浙金融财团的主要标志都是在这一时期显露端倪的。这些主要标志有三:(1)是江浙地区商业银行趋于集团化,江浙金融财团有了实体依托;(2)是金融实力增加,江浙金融财团有了不受政府支配的独立发展要求;(3)是涌现出本集团的优秀代表和有影响的代言人。
1、私人金融资本发展迅速,江浙商业银行趋于集团化,江浙金融财团有了“物化”实体。当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寿终正寝之后,中国出现了有利于私营银行发展的诸条件。这些条件是,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某些政治制度方面的有利因素。如,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刘揆一当上工商总长后多方奔走,联络工商,做过一些利于民族资本发展的事情。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工商部之计划》,召开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他聘请了上海求新机器厂朱志尧、桓丰纺织新局聂云台等人担任工商部顾问,在全国极力造成“务以剔除官习,融洽商情为主”〔2〕的发展实业氛围。1913年9月11日,继刘揆一之后,张謇任农林工商部长,他进一步确定对工商实业“扶植之、防维之、涵濡而发育之”的方针,提出国家应积极为发展工商做好的四条,一要发挥法律保护作用;二要搞好金融;三要搞好税则;四要奖励工商。一时,国中掀起前所未有的创办实业、研究实业、振兴实业的热潮。1912-1914年的3年中,全国新设工厂115家,仅上海一地就有40家,占35%。〔3〕第二,北洋军阀争斗、干戈不断,从未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局混乱,各派纷立,哪一派都难于操纵政治、经济局面。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反而减弱了官权对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窒碍。没有哪届官府的控制与操纵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倒是不插手时情况要好得多。官权的减弱使工商企业与银行的发展较清末时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军阀间纷争开仗要消耗大量军费,为筹措军费北京政府发行巨额公债。两亿五千万元公债〔4〕经各个军阀之手有很大部分转化为银行资本或工业1资本,是有利于银行及某些工业部门发展的。第三、1914—1918年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欧洲大花园里打斗争夺。帝国主义因为忙于世界大战而难于顾及中国,缓和了中国民族资本所承受的压力;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这些因素使中国民族资本工商、金融业在国际大环境中的处境相对宽松,出现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第四、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因为暂时失去本国经济力量的后盾,在华的金融活动出现一些困难,尤其是资金周转方面的困难,甚至“连一度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素有资金、实力雄厚著称的汇丰银行此时也向中国同行求援通融”。〔5〕在中国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德华银行在中国的营业被迫停止;华俄道胜银行在“十月革命”后,更是如丧家之犬,成为“流亡银行”。外国在华银行的上述种种“被动态”是有利于中国民族金融资本的扩展与壮大的。第五、在此期间,官办银行经营不善,有的陷入窘境。一些军阀、官僚投资的“官僚银行”也逐步转化为较为典型的商办银行,金城银行便是一例。该行1917年投资创立时,主要的投资者是军阀、官僚、当年,该行实收资本50万元,其中军阀、官僚的投资占90.4%,1919年,此类投资的比例已降到82.1%〔6〕。到20年代后,军阀官僚以外的普通商股所占比重大幅析上升,到1927年时达25%。辛亥革命以后,官办和官商合办的银行占华资银行的数量比重逐年下降,1912年为65%,1915年为47%,1925年为18%,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的实收资本也从原先的75%降至1925年的45%。〔7〕官办银行及官商合办银行的特点之一是在银行界凭“官权”享有垄断地位,控制货币发行,操纵金融市场,对普通商业银行有很大的压迫性。而官办银行和官商合办银行势力的减退,客观上造成利于私营商业银行发展的金融形势。
上述已谈及或未谈及的种种条件和因素,恰如忽来的“一夜春风”,催开了中国民族金融资本的“千树万树梨花”,中国的私营银行出现了较快发展。从速度来看呈现一种超常速发展。1912年1年之中,就有14家私营银行成立。1911年—1925年,全国银行家数由12家增加到141家,〔8〕其中多数是私营商业银行。1911年到1920年间,平均每年的银行增加率为13.6%;1920年到1925年间每年的增加率亦为8.9%。〔9〕虽然因许多复杂因素所致,有一些私营银行倒闭关停,1927年时仍有51家银行继续营业,这一数字比1911年实存的7家商业银行增加了7倍之多。从营业状况看,私营银行存、贷款数额直线上升,资本力量猛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初创时,只有8万元资本,1921年时,该行资本总额已扩至250万元之多。从1930-1954年,该行的存款总额“一直居于全国银行一、二位宝座”。〔10〕
在私营银行迅猛发展势头中,一些银行通过相互代理、联合放款、联合清算、互相开户、相互投资、人事渗透等加强彼此联系,形成渐有垄断色彩的银行集团。江浙上海的商业银行也以“南三行”为核心骨干联合起来,沆瀣一气。所谓“南三行”是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浙江兴业银行的银行集团。三行的主要投资者是江、浙籍资本家。“南三行”大体形成的时间是1915年以后。“南三行”的出现标志着江浙金融财团的初步形成及其金融实力的日渐壮大。“南三行”中浙江兴业银行创设于1905年,它是浙江人民“保路运动”的直接产物。浙江省各阶层民众为了反对清朝政府出卖苏杭甬铁路筑路权,自发集资成立民间的浙江省全省铁路公司,并设立了配台铁路建设、管理铁路股金的浙江兴业银行。1914年,该行总行由杭州迁至上海。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下浙江兴业银行的发展很快,1928—1936年,该行的存款业务居于全国银行排名的第四位或第六位(存款数额1928—1931年居第四位,1932-1936年居第六位)。浙江实业银行创设于1909年,原名为浙江银行,系官商合办。1915年7月该行改名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1923年,官商股分离,官股部分改为浙江地方银行,总行在杭州,商股部分改设浙江实业银行,总行在上海。从此,“浙实银行”摆脱了先前“官股”的羁绊,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直到1936年,该行的存款数额一直稳居于全国银行界排名的第七、八位。〔11〕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于1915年,初创时只有8万元资本、七、八个工作人员,由于管理得法、用人得当及善于抓住并利用经济及金融机会,发展神速,1913年时资本总额已增至500万元。除银行间日益频繁的相互代理、联合放款、联合清算、互相开户之外,“南三行”及江浙金融资本的集中还表现在金融业内部相互投资上,甲银行或甲银行的董事长投资于乙银行,并在乙银行的董事会中占有席位,乙银行或乙银行的经理在甲银行投资,并在甲银行的董事会中占有席位,这甚至成为上海与江浙地区私营银行和商业银行中的一种时代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会里有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薪,李还兼中国恳业银行的董事;〔12〕浙江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信孚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会里有四明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衡甫,该行的董事长王芗泉又兼浙江典业银行的董事长、总经理;〔13〕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董事长是中国银行的张嘉璈,董事中还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1931年时,有6位上海银行家每人参加了5家以上的上海各银行的董事会,有15位银行家每人同时在3家以上的银行中兼任重要职务。〔1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之初时,张嘉璈投入长期存款5000元,成为该行的强有力后盾;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投资两万元成为股东,贝淞荪稍后些时也向该行投入5000元。〔15〕“南三行”乃至江浙金融资本的银行就是这样被连锁董事会及相互间的业务联合、资金彼此挹注而牢牢地联结在一起了。
2、随着金融实力增加,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步入有独立发展要求的成熟阶段,有了观念、灵魂且有了与北京政府抗争的实力与行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与江浙金融资产阶级通力合作,坚决而有力地抵制了北京政府的“停兑令”是一个较典型的证明实例。入民国以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继续保持国家银行的性质,与此同时,两行的商业性也日渐明显,尤其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更是如此。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是:首先,当时上海分行的领导权掌握在江浙银行家宋汉章和张嘉璈手中,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实际上已与江浙金融资本打成一片;其次上海分行虽是中国银行的分行,但却在中行系统中拥有举足轻重地位,对于总行有尾大不掉之势。到20年代中期后,中行上海分行的钞券发行数额始终占中行系统发行总额的60%以上,这种优势地位和雄厚实力使上海分行通常不受总行挟制、对总行少有依赖性。再次,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成立的时间早于北京总行,〔16〕也许正因为如此,中行上海分行历来对总行保有相对的独立性。
1916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与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团结在一起,抗命于北京政府、抵制“停兑令”,表现了江浙金融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官权控制、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倾向性。辛亥革命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被迫大量为北京政府垫款并引起滥事发行钞票。1916年止,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向北京政府贷款额多达6000万元左右,发行钞票多达8300万元左右,〔17〕两行大量垫款和发钞的同时,却无必要准备金,矛盾终于在1916年3月后暴露。3月2日袁氏虽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已无可挽回颓势,财政罗掘俱穷,国用捉襟见肘、政府信用扫地,致使济南、北京、天津等地发生中、高两行提存挤兑风潮。为遏止风潮扩大,北京政府府于1916年5月12日通令全国中、高两行停止兑现付现,此即“停兑令”。“停兑令”发出后,两行的天津、济南、重庆、成都、广州、张家口等多处分支行是遵令执行的。唯上海分行进行了不妥协的坚决抵制。
时任上海分行经理和副理的宋汉章、张嘉璈等人接到“停兑令”后立即紧急磋商,得到“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银行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要“维护中国金融之生命”“寄希望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银行”〔18〕的共识。为了表明银行不受政府“支配”的独立发展要求;为了“维护中国金融之生命”,他们公开表明拒绝接受北京政府“停兑令”的立场。宋汉章、张嘉璈等中行上海分行领导人采取了多方面的步骤和措施。一、先发制人,串联“南三行”主要头面人物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人以中行上海分行股东、存户、持券人的身仿向上海租界当局会审公廨提出起诉,以法律为武器与北京政府对簿公堂,以争取社会舆论的理解和支持。〔19〕二,动员江、浙两首中行上海分行股东,在“保护商股利益”的旗帜下组织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该会由张謇任会长、叶揆初(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任副会长、银行家钱新之任秘书长。由此将中行上海分行抵制“停兑令”的行动变为更大规模、更有气势、更名正言顺的社会集团的抗争,并争取整个江浙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实力为其后盾。三、公请师代表股东主持上海分行事务,管理上海分行资产,照旧兑付上海分行所发行的钞券并支付各项到期存款。县体确定5条办法:“(1),上海中国银行由股东联合会举定监察员二人,到行监督,全行事务悉归股东联合会主持,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一切适照普通银行营业办理;(2)本行所有财产负债,已移交外国律师代表股东管理一切并随时有查帐之权;(3)上海分行钞票,将准备金备足,移交外国律保管,随时兑现,不得停付,即中央有令他处停止总付,惟上海仍照章办理;(4)所有存款,均到期立兑;(5)将来如商家设有损失,悉归服东联合会负责,向南北政府交涉,归正式政府承认。”〔20〕四、取得外资银行的支持并借用外资银行力量。5月15目宋汉章往访汇丰和正金两外资银行,当日中午,外资银行经理开会,“赞成协助上海中行至必要限度”,共同承担对中行上海分行200万元透支借款(汇丰40万元、麦加利、华俄道胜、东方汇理、横滨正金各25万元、花旗、荷兰银行各15万元、华比、有利。台湾银行各10万万元)。16目,各国驻京公使团纷纷复电各国在沪银行,赞同“协助”上海分行之举。五、力争上海总商会等有影响的社会各界同情、理解和支持。上海总商会在北京政府“停兑令”下达之初,态度暧昧,“绝无一语敢请伪政府(指北京政府)收回成命。”〔21〕之后,明确表示支持中行上海分行为其大造舆论,并积极协助维持市面。
当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与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抵制“停兑令”的行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这里,我们不是研究抵制“停兑令”的细微过程。只是想通过上面所述去证明,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一种集团、这集团已经达到具有与北京政府作某种抗争的经济和金融实力。
从抵制“停兑令”,到1916年底1917年初抵制调动张嘉璈离沪,再到维护中国银行1917年新则例的抗争,所有这些,都绝非一个个孤立的偶发事件。它们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而联系它们的便是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渐趋明朗的团体意识及摆脱官权控制、谋求独立发展的要求。换个说法即是,民初江浙上海金融业大发展;而辛亥革命后,“共和”“民主”意识渐力传播;与清朝统治及后继的南京政府相较,北京政府的软弱无力、鞭长莫及等条件和社会氛围,从不同方面起作用促进该时期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崛起与趋向成熟。上述相联的事件,既是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意识的外在表现,又是江浙金融财团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3、有了本集团的优秀代表和有影响的代言人,一批,而不是个别的江浙金融英才崭露头角迅速崛起。诸如钱庄业改革派代表秦润卿(宁波籍)、上海交易所最早的创办人虞洽卿(浙江镇海)、同情并襄助过辛亥革命的银行家沈漫云(无锡)、敢于同北京政府坚决抗争的宋汉章(浙江余姚)和张嘉璈(上海宝山)、许多海外学成归来的学者银行家陈光甫(镇江)、李铭(绍兴)、钱新之(浙江吴县)、徐新庆(浙江余姚)等等。这批金融英才具有明显的特点:第一,他们籍贯多是江苏、浙江(其中又以宁波为多)。从历史上看,两者历来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旧式金融机构钱庄业早已在这里打下深厚基础;从地理位置看,浙江、江苏地区内连中国腹地面向辽阔海洋、这里的人民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商品意识、金融意识都远胜于中国其他地区。历史的熔铸和地理条件上的独特,使这一地区的人们较多开放意识,较强探索精神,他们“本能地热心外资和外国思想观念并与大陆后方那种根深蒂固的乡村和官僚正统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个中国”。〔22〕第二,他们大多受过较高层次的专门教育,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其中去国外深造留学的人占相当大比例。受有系统高等教育的人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资源,何况他们是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更能最大限度发挥潜能。他们进入银行企业后一般是担任较低级管理职务,经过一段实践和再学习,他们循阶梯式过程晋升到高级管理岗位。既便是没有去国外留学银行专业的,也往往在经营实践中与在华外国资本家及管理人员有密切往来和频繁接触。虞洽卿就属于这类人物。虞洽卿早年(1904)曾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第二年,他又充任荷兰银行上海分行买办。在充当买办为外国老板效力中,一方面他积累起最初的资本(在荷兰银行当买办时“他每月月薪是800两很子,加上年终分红和佣金结算,年收入约在两三万两之谱”〔23〕,另方面,他也广泛地接触外国人士,观念上受到他们的影响,增长了银行管理方面的业务能力和经营才干。为日后兴办实业、振兴国家的抱负奠定了基础。第三他们大多有强烈的献身精神。陈光甫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初创条件艰苦,环境险恶之时,毫不气馁、满怀信心,努力奋斗,为了行务的拓展与发达,他既是总经理,又是行员,常亲自上街拉存款、跑工厂、搞放款、联络社会、调查宣传,并且不以为苦,不以为累,常以“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并且成功”〔24〕自勉并激励行内同仁。第四,许多银行家少年时家境贫困,较早地步入社会。虞洽卿6岁时父亲病故,靠其母做针线活抚养;银行家王志莘因父早逝不得不辍学进钱庄学徒:企业家兼银行家朱葆三13岁时父亲患重病家境日贫;银行家陈光甫幼年做学徒时,“凡添饭斟茶,以及早晚开门上锁之役,无不为之。晚间卧于地板之上,热天则露宿凉台,饭时常不得饱。”〔25〕因为他们大都经艰苦生活的砥砺,便有强烈的创业和敬业精神。他们肯于下苦功夫学习,朱葆三当年在上海“协记”当学徒时,除勤奋学习珠算、记帐等业务外,还想方设法学习英语。邻近一家商店学徒每天夜里自费去补习学校学习英语,朱葆三因付不出学费不能去。他便将每月店中所发的5角津贴节省下来送给那位学徒,拜其为英语“小先生”。〔26〕第五,都在年富力强时担负了银行的主要领导职务,精力充沛、思路敏捷、对新鲜事物反映快,富于开拓创新精神,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出身经历,但在创办银行、发达中国金融事业方面却有着近乎于共同的志向和认识,实际经营活动、经营作风有着“不谋而合”的一致性。这种‘不谋而合”,实是因他们同属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所使然!第六,他们大多既与历届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又不大愿弃业做官,力图保持与政府间的一定距离。1927年时南京政府曾邀陈光甫出任财政部次长以做为其积极合作的回报,竞被其拒绝:张嘉璈、徐新云等人也多次婉拒到政府中任职。他们广泛结交,注重扩展社会联系网络包括结交达官显贵,着眼点不在做官当政客,而是为发展金融业、经营银行业务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
一批江浙金融英才和银行家出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源于不同的方面,汇聚于世纪之初江浙金融业迅猛发展的大潮中,做起了时代弄潮儿,他们似灿烂的群星,一时将江浙金融资产阶级辉映的熠熠闪光。应该说,是江浙金融资产阶级造就了他们这批金融英才,而他们的倔起又为时代托起了江浙金融财团。
三、近代金融资本——江浙金融财团的经济基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钱庄开始向近代金融资本演化。所谓中国近代金融资本,是指完全不同于旧式典当、钱庄、票号资本,其经营活动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密不可分,本身即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机构成部分的金融资本。中国近代金融资本与“江浙金融财团”有天然的联系,前者是后者得以形成的经济、物质基础,后者的逐渐形成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发展。
考察中国金融发展演变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出现和形成,大致有两种渠道,一是上个世纪末旧式钱庄的资本主义化;二是世纪之交近代银行的出现两渠交汇,便涌流出中国近代金融资本。
1、在1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里,钱庄资本逐渐向资本主义金融资本转化,并成为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以后,旧式钱庄染上了买办色彩。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实施经济掠夺与侵略时,钱庄与商界的传统联系为外国资本所利用和控制,钱庄的种种信用工具和信用手段转入了为扩大销售洋货服务的轨道。但,钱庆资本毕竟与买办资本有着质的差别。首先,钱庄资资本并非由外国资本的入侵而造就,它是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产生了的金融资本;其次,在“买办”性的程度上,钱庄远不如外国资本所豢养和造就的买办资本强烈;与封建政权和官吏的瓜葛,也不如买办及买办资本。钱庄资本与买办资本的这种区别,决定了它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作用和影响不同,这是钱庄业及钱庄资本向近代金融资本转化的内在条件。
钱庄资本在19世纪后期向近代金融资本转化并最终成为近代金融资本的过程,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钱庄业对资本主义银行的依赖和联系越来越密切。在上海,由于买办的穿针引线,从中斡旋,外商银行早就对上海钱庄进行放款(此种放款常被称之为chop Ioan),19世纪70年代外商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放额一般为三百万两左右,〔27〕到90年代,拆放额达七、八百万两已“习以为常”。〔28〕钱庄在资金周转上对外商银行的依赖必然越来越重。除外商银行外,本国近代银行产生以后,钱庄也与它们保持密切的业务往来,从本国银行那里得到资金融通。仅1897年5月至11月,中国通商银行每月拆放款额达到了三百万两左右,占该行拆放款总额的96-100%。之后,中国通商银行对钱庄的拆放款额虽有减少,但仍保有较大的数字和较高的比例。到1911年时,拆放总额为289.6万两,占该行对外放款总额的36%。〔29〕第二,钱庄的业务经营手段趋于资本主义化。如引进了近代的汇划制度,洋行开出的支票和华商发出的庄票均可在外商银行直接轧抵冲销,从而大大节省了时间、简化了手续;再如,1890年前后上海钱庄业首创了“公单制度”,每天下午各汇划庄将其应收之庄票送到原出票钱庄换取公单,然后交钱庄业汇划总会“汇总”并互相轧抵(也代理非会员钱庄和外商银行的清算业务)。〔30〕钱庄的“公单制度”方便了彼此的清算业务,避免了大量的现金搬运,开创了我国票据交换的雏形。另外,除继续把持操纵传统的洋厘、银拆行市〔31〕之外,钱庄越来越重视注入较大资金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股票买卖、房地产经营。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钱庄“以股份票互相买卖”〔32〕牟利已渐成时尚。第三,钱庄资本开始与近代工商业资本相互溶合,共同发展。“相互溶合”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钱庄开始并越来越多地向工商企业放款,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汉口福圣,协和机器轧油厂、毛业制造所、机器米厂以及炭山湾煤矿、江西铜矿等都曾得到过钱庄的放款,〔33〕上海更是如此;二方面,一些钱庄老板在经营钱庄业的同时,开始涉足创办工商企业。在上海最典型的例子是荣氏兄弟,荣氏兄弟以开设钱庄做为事业的起步,1900年,基于“钱庄放帐,博取微利,不如自己投资经营利益较大”〔34〕的想法,大力投资机器面粉业、棉纺织业、终于发展成为闻名海内外的荣家企业集团。汉口,“三怡”钱庄的股东黄兰生也曾投资设立“汉丰面粉厂”。〔35〕三方面,一些近代工商业企业主在经营工商的同时投资于钱庄业,为钱庄资本注入了新鲜血液。钱庄对近代工商业的放款以及两者间的相互投资必须使它们更为密切和融合。
19世纪下半期钱庄这种转化,使旧式钱庄资本成为近代金融资本的一部分,并产生了一批象秦润聊那样的优秀钱庄资本家(他们已完全不同于旧式钱庄老板)。秦润卿,浙江宁波慈溪人,15岁时走上了钱庄学徒之路。30岁以后,他当上了上海豫源钱庄经理,从1917年起历任上海钱业公会副会长、会长、总董、主席等职。在他的经营下,豫源钱庄的放款对象转向工业,尤以缫丝厂、丝织厂、棉纺织厂为主要对象,大力扶植上海机器工业的发展;在他的主持下,福源钱庄对存款、放款及帐房管理业务进行了改革,增设储蓄存款的种类,适当提高存款利率以广招客户存款;改传统的信用放款为抵押放款;公布营业报告、提取公积金。秦润卿在长期担任上海钱业领袖时,为维持和稳定钱庄业的信用以补钱庄资金薄弱之短,曾倡设上海钱业联合准备库;他还倡导成立上海钱业业务研究会,以“提倡改革与钱庄业务之扩张”为宗旨,研究改革钱庄备项业务,以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加强与新式银行的竞争力量。很显然,在历史动力的作用下,秦润卿这样的钱庄老板正不自觉地转变为金融资本家,钱庄资本正转化为近代的金融资本。
2、国内银行业的产生是形成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主要渠道和途径。中国近代银行主要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外国金融资本在中国的活动所诱发,没有这种“诱发”,国内银行业在19世纪末的出现是不可能的。当然,中国银行业的产生也有重要的内在因素:一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产生并发展,这种情况呼唤并催生了“国内银行”;二是清政府财政上的需要。近代,中国自然经济逐渐分解,商品经济与内外贸易长足发展使政府财政收支的货币部分比重日增,需要有银行机构为之代理;而通过银行进行纸币发行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的收入不足。三是政府以设立银行做为倡行“新政”的标榜。
中国通商银行是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嚆矢,它成立并正式营业于1897年5月。成立时资本额定为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在经营管理上,中国通商银行完全有别于旧式金融资本的钱庄、票号等。它学习和借鉴外商银行的管现制度和方法,“用人办事,以汇丰为准”并聘用英国人美德伦、马歇尔等来行担任“洋大班”;它的内部规章制度依照英资汇丰银行的章程拟订。〔36〕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最早银行,又因为它的创办人是盛宣怀而受到世人所瞩目。中国通商银行以自己的新式制度、新式管理、新式业务在中国金融业发展史上划开了一个新时代。较中国通商银行晚些设立的银行还有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应该说,银行是资本主义的金融信用机构,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儿。但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却既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如机构的股份公司性质、某种程度上的近代化管理制度与方法等),又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金融机构,勿宁说它们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交配出来的“混血儿”。从资本构成看,上述三行都吸收了商股参加,其中,中国通商、户部银行开办时都是官、商各半,交通银行甚至达到商六官四的程度;从经营方式看,中国通商银行号称商办,户部银行与交通银行均为官商合办,即三家银行或商办或官商合办,都招有商股,都与“商”有关;从管理大权看,名为“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实际是官掌实权,该行成立时总行的9位总董,都不是由股东选举产生而是由盛宣怀指派;该行下属各分行设有分董也都由盛加以委派,以致于早期香港、九江、天津、镇江、汕头、北京、汉口等地分行的分董全部是清一色的封建官僚。〔37〕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尚且如此,“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便可想而知了;从银行资力和势力看,中国银行业产生之初,官办、官商合办的银行在资力及社会势力方面明显过于商办银行,表现出银行机构对清朝封建统治政权的依附性。上述中国通商、户部银行、交通银行之间也是“官”压“商”的关系。户部银行成立较中国通商银行晚,但在地位和营业方面很快压过后者,以吸收的存款余额做比较,中国通商银行的存款余额1906年为194万两,1907年为224万两,1908年为194万两,1909年为200万两,而户部银行相同年份的存款余额则为1056万两、2208万两、3526万两、4381万两,两者相较相差竟至10倍到20倍。数额庞大的户部银行存款中必有大宗官款及政府财政存款。交通银行的存款余额虽不及户部银行,但也远过于中国通商银行(交通银行1909年的存款余额为1384万两)。〔38〕
由上,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因中国“向无银行”,〔39〕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出现,但是,前面分析的其资本主义的“不纯粹”性,又决定了它们难以成为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主体。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主体应是私营银行出现之后,即信成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等成立后逐渐形成的。
信成银行是由无锡籍实业家周延弼(字舜卿)和沈缦云(名懋昭、以字行)在1906年开办的,由周任总理、沈任协理。银行开办时集股50万元。总行设在上海南市,在上海租界内以及北京、天津、汉口、南京、无锡等地都设有分行。信成银行是中国较早的较典型商办银行(相对于中国通商银行),它的业务主要包括商业往来和储蓄两大部分。信成银行重视向近代工商企业放款、扶持民族资本的发展。荣家在创办振新纱厂和茂新面粉厂时,信成银行给预过抵押贷款;无锡业勤纱厂因为得该行贷款而几次度过难关。由于该行采用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对当地的企业进行详细的调查摸底,并分析它们的发展前途”,“所以年终结帐,很少吃倒帐”,〔40〕银行存款额很快高达700余万元,1907年,信成银行获准发行钞票,流通市面额达110万元。〔41〕浙江兴业银行的成立直接得力于世纪之初“保路运动”和不断高涨的“实业救国”热情。为了反对清政府出卖苏(州)杭(州)甬(宁波)铁路权益,1905年、浙江省各阶层人民集股成立浙江铁路公司,因民办铁路筹集保管股款的业务量巨大,旧式钱庄资本薄弱,规模狭小,无法满足需要,铁路公司1906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设浙江铁路兴业银行,后又改为浙江兴业银行,专营收存股款。该行总行初设杭州,1915年迁至上海,成立初资本额为100万元。该行全面经营商业银行业务,除存款、储蓄,发行等业务外,还在上海、天津等处建造仓库以扩大抵押放款业务。从该行资本构成看,浙路公司和工商企业家的投资占84.41%,这决定了该行与民族资本工商业有天然的密切联系、1919年、1922年、1923年、1924年、1925年、1926年该行对工商业的放款占总放款额的比列都在40%以上(分别为61.9;44.8;40.5;44.4;44.3;51.9)。〔42〕四明银行成立于1908年,它是由虞治卿、朱葆三等上十位宁波籍的实业家和商人投资开设的,其开办资本为150万两,实收半数。
上述三家银行有共同的特点:第一,开办资本中少有或完全没有清王朝各级政府府投入的官股,它们的主要创办人和主要投资者当时的身份不是官僚而是实业家、商人、钱庄股东老板等。第二,银行的主要资本来源一是商业和钱庄业的积累;二是产业资本。如:四明银行的资金主要来自宁波籍的商业资本家钱业资本家;浙江兴业银行的资金主要来自浙江铁路公司。第三,都注重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放款,支持和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银行经营有成效,发展比较明显,如浙江兴业银行1915年时吸收存款438万元,1926年存款额增加到3312万元,实力有很大增强,〔43〕表现出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的优越性与进步性。第五、这些银行有明显的进步倾向,都曾以一定数额的资金襄助过革命,尤其是信成银行和四明银行,《民立报》就曾说过:“光复前后九月十三四日所发之军饷,大半由该两行所输出”。〔44〕
上述商业银行的种种特点表明,它们才是中国近代典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银行的诞生,它们的出现标明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正式产生。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并溶入钱庄资本的近代金融资本的出现,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此,原来较为分散的、小额的商业资本和社会游资才有可能汇聚成相对集中的、巨额的资本去适应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交通运输业发展的资金需要。
这些江浙商业银行的出现与稳定发展,为“江浙金融财团”的形成积聚了最初的资本,而江浙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逐渐形成和壮大给“江浙金融财团”的出现与生成提供了历史舞台和经济基础,也为江浙金融财团造就了人才,培养了一批创设、管理商办银行的金融家、银行家。
四、“江浙金融财团”的社会基础
如果说,近代金融资本是“江浙金融财团”的经济基础,那末“江浙金融财团”的社会基础便是闻名遐迩,历史悠久的“宁波帮”。
“宁波帮”源于宁波而成于上湖。宁波在鸦片战争之前曾是盛于上海的东方大港。西方人早就描绘了她当年的繁荣,“其房屋建筑的整齐华丽,以及商业名声的无与伦比,在中国可称首屈一指”,称她为“令人神往的获利源泉”〔45〕。鸦片战争后宁波的外贸地位急剧下降。宁波开埠后的头5年中,其对外贸易额由50万元下降到此数的十分之一弱。〔46〕宁波做为外贸港口的衰落,主要是由于上海贸易口岸的崛起,鸦片战争后,上海的对外贸易额在短短的六、七年内超过了广州,居全国第一位。上海的崛起,宁波的相对衰落以及彼此地域上的相近,使得具有冒险开拓精神〔47〕和商业敏感性的宁波人开始向上海进军,在上海造成“宁波帮”。
所谓“宁波帮”是在上海进行经济活动的浙江省宁波及其周围几个县的商人及钱庄老板长期、自然形成的同乡性商业团体。
宁波人到上海后最初主要从事商业、沙船运输业后渐向钱庄业集中。贸易的发达带动了沙船运输业的发展。但船运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一艘沙船价值约为7000—8000两银,〔48〕而一般商人及沙船业主通常又缺乏相当数额的自有资金,这就创造了频繁的资金筹措及借贷方面的社会需求并推动某些积累了相当数量资金的商人投身于金融业。宁波人在这种经济感召下投资开设钱庄,将资本集中于钱庄业。镇海的方家与李家就是典型例子。19世纪30年代方家从镇海到上海经商,不久方润斋在上海南市开设兼营土布、杂货的覆和钱庄(后改名号为安康钱庄)〔49〕后,方家资力渐盛,除陆续在上海增设允康、寿康、同裕、尔康、安康、延康、五康、安裕、钧康、承裕、和康、汇康、赓裕、庶康、元康、乾康、夏康等十余家钱庄外,还在汉口、杭州等地开设了7家饯庄,〔50〕成为世人瞩目的钱庄家族。李氏家族的李也亭十几岁时在黄埔江上为沙船船员送酒以资糊口,之后自己成为船员并开设船行当上老板。在经营中,他遇到调剂资金的需要,这促使他在经营沙船贸易的同时,自投资本开设3家钱庄〔51〕。逐渐地,上海钱庄多为宁波籍老板投资开设。清末时,在上海宁波秦家、镇海方家、李家和叶家、慈溪董家、湖州许家、洞庭山严家和万家、苏州程家9大钱庄家族中,宁波籍(含镇海、慈溪)就占了5家,,以宁波人为主开设的上海钱庄逐渐成立了同业性团体——钱业公会(所)。由此,“宁波帮”自成势力,在上海钱业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
“宁波帮”在上海商界与钱庄业中的这种地位,使上海金融界中之人常以自己为宁波籍而引为自豪与荣耀,中国垦业银行创办人王伯元,祖籍浙江慈溪,其母是苏州人,王亦生于苏州。他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代理会长时,讲话中常露苏州口音,有人奇怪苏州人为何担任宁波同乡会会长?王则严肃声称自己是地道宁波人,而且是宁波慈溪王氏二十二世孙,有宗谱为证!
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宁波帮”在上海的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钱庄业,开始以钱业为基础向国内外发展。向外的发展是凭借雄厚的财力和广泛的商业渠道货币金融知识,与外商广泛接触,造就大量“买办、”和“后备买办、”。向内发展则是向近代工业企业和新式银行扩展。在这一过程中,“宁波帮”逐步扩大,——既扩展经营对象活动领域,又扩展该帮成员,其联络对象由宁波籍扩大到浙江籍、江苏籍,甚至包括安徽籍。宁波帮经营的成功和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使人们对其越来越另眼看待,宁波籍以外的一些商人与资本家出于各自的目的,愿意与宁波帮建立并发展经济等多方面和联系,并逐渐成为非宁波籍的“宁波帮”成员。随着宁波帮的财富和集团实力、经验的迅速增长和积累,19世纪末,它已发展成为上海最重要的经济力量,20世纪初宁波帮演变扩大为“大宁波帮”。除了掌握上海的经济、金融外,这一“大宁波帮”既是上海各种商业经济组织的基础,又是上海各种商业经济组织的驾驭者。1923年,上海总商会86%的席位浙江籍资本家所占据。〔52〕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是总商会的分会,它们在上海总商会内县有关键性地位,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许多重要人物秦润卿、虞洽卿、朱葆三等都长期在其中担任领袖人物。
综上所述,“江浙金融财团”在近代中国并非凭空出现,它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它的产生自有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近代金融资本做为其经济基础决定了“江浙金融财团”主导方面的资本主义属性,也决定了“江浙金融财团”必然伴随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而壮大;“宁波帮”做为其社会基础,则决定了“江浙金融财团”与封建经济即传统商业旧式金融的历史渊源关系,决定了“江浙金融财团”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封建色彩。这封建色彩的一面使“江浙金融财团”在金融界乃至延伸到政治领域中的活动带有明显的集团、派系性;而其主导方面的资本主义性质则决定“江浙金融财团”一有机会便要顽强地体现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企图得到或分享政治权力。北京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抵制停兑令”事件和“江浙金融财团”支持1927年的“四一二”证明了这点。“抵兑”的行动表现出“江浙金融财团”摆脱北京政府严密控制、独立发展的要求;而支持“四一二”不仅仅反映出江浙金融财团选择了蒋介石和对国民党右派的支持,还体现出江浙财团以此为筹码去影响南京政府乃至在这个政权中分润权力的企图。至于江浙财团的这种企图实现与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而应在另文中研究和探讨了。
注释:
〔1〕《聚星》,第2卷第5、6期,1948年11、12月。
〔2〕《实业杂志》,第1期,“政令章牍”。
〔3〕沈家五编:《北洋时期工商企业统计表》,附表二,《近代史资料》,总58号。
〔4〕《财政部整理国债办法分析》,《独立评论》,1932年5月29日。
〔5〕张虎婴:《厉史的转迹),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8月,第89页。
〔6〕《金城银行史料》。前言,第7页,正文,第243-245页。
〔7〕《历史的轨迹》,第91页。
〔8〕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1993年版,第66页。
〔9〕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1993年版,第66页。
〔10〕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1993年版,第67页。
〔11〕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1993年版,第67页。
〔12〕《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页B39、108页。
〔13〕《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页B87、217、196。
〔14〕《中国评论周刊》,1933年6月8日,第566页。
〔15〕《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页。
〔16〕《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经济科学出版社,第67页。
〔17〕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第70页。
〔18〕《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67页。
〔19〕《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版,第27页。
〔20〕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4页。
〔21〕《民国日报》1916年5月15日。
〔22〕《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6页。
〔23〕《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下)山东人民出版社,第524页。
〔24〕《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性,第138页。
〔25〕《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陈光甫先生简介“。
〔26〕《金融家的足迹》,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第65页。
〔27〕《申报》,1878年8月28日,1897年1月30日。
〔28〕《申报》,1878年8月28日,1897年1月30日。
〔29〕《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142、143页。
〔30〕《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页,53页,493—495页。
〔31〕洋厘:1933年废两改元以前,上海金融市场上银元折合规元银的行情,即银元1元拆合规元的数额,如,洋厘=7.225钱,意即银元1元可折合规元银7钱2分2厘半:银拆:废两改元以前,上海钱庄同业之间以银两为单位的互相借贷,期限一般为一、二天,分别称为“独天拆票”、“两皮拆票”。
〔32〕《字林沪报》,1883年10月18日。
〔33〕武汉市档案馆:全宗119,目录130,卷号113。
〔34〕《荣家企业史料》(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9页。
〔35〕《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142页。
〔36〕《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2页。
〔37〕《中国第一家银行》11,12页。
〔38〕洪葭管:《金融话旧》,中国金融出版社,第47页。
〔39〕《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1964年,第1037页。
〔40〕《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下)山东人民出版社,第84页。
〔41〕《旧上海风云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42〕《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下),山东人民出版社.第395页,附表2。
〔43〕《学术月利》,1983年,第3期,第75页。
〔44〕《金融话旧)中国金融出版社.第52页。
〔45〕《经济学术资料》,1983年第10期,第49页。
〔46〕《经济学术资料》,1983年第10期,第49页。
〔47〕《定海县志》:“冒险之性”为宁波人所特具,他们处在“饥驱寒袭,迫而之外、”的环境中,吃苦耐劳。能够“航海梯山,视若户庭”。
〔48〕《经济学术资料》,1982年,第4期,第50页。
〔49〕《经济学术资料》,1983年,第10期,第49页。
〔50〕《上海金融》,1989年,第8期,第43页。
〔51〕《经济学术资料》,1982年,第4期,第50页。
〔52〕(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5页。
标签:金融论文; 银行资本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论文; 银行论文; 工商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 商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