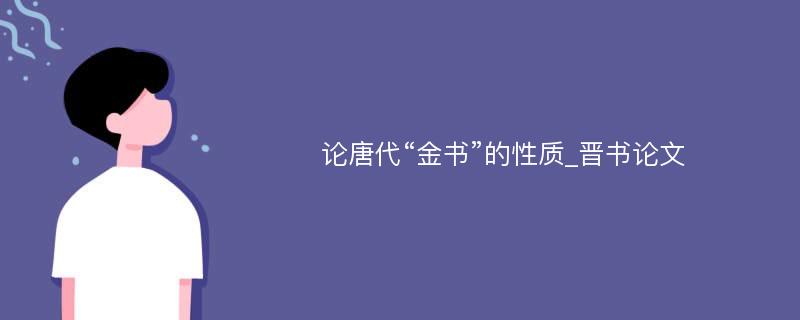
论唐修《晋书》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晋书论文,性质论文,论唐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汉学研究
序
从秦始皇以来,中国历代杰出的为政者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即使在社会、文化领域,也都想用自己信从的“善”、“美”标准来加以规范,并妄图以此来统治世界。但是,由于他们过于执信自己所信奉的“善”、“美”的绝对“正确性”,就很容易无视“真”的存在,从而具有极大的偏激性。
在今天,当我们研究这些为政者统治下的时代,并以他们下令编纂的文献为依据,来考察当时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情况时,就必须充分考虑到上述事实,从而对文献加以慎重的甄别与判断。
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一位杰出的为政者,为了唐王朝的安定,或许只是为了满足嗜好欲望,他也企图以个人确信的“善”、“美”,对唐代的各方面加以规定,并作出了种种实施。比如从《五经正义》中,我们能看到对经义事业的统制;从《南史》、《北史》、《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隋书》中能看到对史书编纂事业的统制等,这些均属上述企图中的一环。这其中,唐修《晋书》(以下简称《晋书》)是在原已存在多数晋代史书的基础上又特意加以改修而成的,从这一过程中,可更进一层体现出太宗的心理意图。
原来对《晋书》的评价,如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记》,都是通过对各种版本的校勘、或综合其它史书的比较,来详细修订载文内容的误谬、文字表现的异同等,而对《晋书》是“据太宗意图而有意识被改修”这一重要观点,几乎都未加考虑。不仅如此,直到今天,一般的看法仍然是:它是取在它以前各类晋代史的长处、避免了短处,从而被认为是最“标准的晋代史”。
当然,由于传存至今的完整晋代史只有《晋书》,所以在研究晋代诸问题时,不言而喻,仍然有必要把它作为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来加以采用,但是,这并非说它就是“标准的晋代史”了,而必须把“它是按李世民意图改修的”这点考虑进去,从而分析所载的真伪,这已成为当今考察晋代史实上重大的、且不可缺少的环节。
以下,笔者就《晋书》具体是以怎样的意图来进行改修这一点,先以晋代文人传记为中心加以论述。
(一)有关《陶潜传》的改修
陶渊明的生平事迹,在刘宋·颜延之《陶徵士诔》、梁·沈约《宋书·隐逸传》、昭明太子《陶渊明传》及《莲社高贤传》中均有记载。读《晋书·隐逸传》中的《陶潜传》便可知,它基本上是蹈袭《宋书·隐逸传》。本来,《晋书》只是晋朝的断代史,收录活到刘宋间的陶渊明的事迹对《晋书》来说是一种破例。尽管如此,此事也许如赵翼所说:“其列传编订,亦有斟酌。如陶潜,已在《宋书》隐逸之首。潜本晋完节之臣,应入晋史。故仍列其传于晋隐逸之内”(《二十二史记》),是《晋书》编者把渊明判定为“晋完节之臣”的结果吧。总之,这事本身就已明确说明,编者加以“斟酌”的意图来编订《晋书》的情况是存在的。
同时,只要阅读《晋书·陶潜传》,就可发现:它所蹈袭的《宋书·陶潜传》中能见到的“潜弱年薄宦”以下的文字,在《晋书》中却断然地被删掉了。正如以下引录所示,本来,这段文字是记述了陶潜是“晋完节之臣”的理由,作为把活到刘宋时代的陶潜收入《晋书》的依据来说,无论如何是必要的,是不应该被删除的。
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省略)。又为《命子诗》贻之(省略)。
为什么《晋书》在其它部分几乎基本上把《宋书》记载照原样抄袭了,但却特地消除了以上这一段文字?这其中一定是存在着相当理由的。如果只以于史实有误为理由而加以削删的话,那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晋书》的编者之一李延寿在编纂《南史》陶潜传时,以上的引文大体上照原样被记载了。而且,也完全不能说明确实是陶潜所作的《与子俨等书》(《陶渊明集》载为《与子俨等疏》)、《命子诗》也被删去的原因。
在这里,我想分析一下与《晋书》一样是受太宗敕命、在真观年间经李延寿手编纂的《南史》陶潜传,通过与《晋书》相比较,试着来说明其中的原由。可以说,在这两书中,都同样有李世民的史书编纂意图在起着作用。
《南史》陶潜传,也是据《宋书》陶潜传编写的,改修点也大致与《晋书》同样是后半部分。但《南史》陶潜传并没有象《晋书》那样,把后半部分断然地全部削除,只是删了《与子俨等书》“序”的部分与《命子诗》。而《晋书》的削除,就如下文所述那样,从表面上看只不过沿着《南史》删除的方向更扩大化、整理更极端化,但实际上,在《南史》、《晋书》共同被删除的部分里,“按李世民政权需要改修”这一最重大原因却被隐藏起来了。首先,我们看到《南史》把《与子俨等书》“序”的部分被删除了,(此《书》无可怀疑是陶渊明的作品),《南史》编者为什么这样不自然地进行部分的削除呢?下面列出被削除的原文,并加以讨论。
天地赋命,生往必终,自古贤圣,谁能独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岂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邪。
以上引用的内容说的都是“死生”、“富贵”等天命观念,这与坚持用儒教治世观的太宗李世民及他的重臣、亲信们在思想上没有任何的龃龉,很难想像有什么必须要删除的理由。但是,如果对这部分仔细地分析,在“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地方,却隐藏着与太宗有关系的重大问题。这《与子俨等书》中的“子夏之言”,实际上是引自《论语·颜渊》: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在唐初,《论语》已是士大夫所必读之书,当然《颜渊》的文字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当时的士大夫在读《宋书》陶潜传“子夏言曰”这部分时,必然在心中会浮现上记的《论语·颜渊》章句全文。这子夏的话,是针对司马牛所发出的“人皆有兄弟,我独亡”的感慨进行慰抚的。
这个司马牛,就是在《论语·述而》中企图杀害孔子的有名的桓魋之弟。在《论语·颜渊》中也有较详细的介绍:
(注)郑曰:“牛兄桓魋行恶死亡无日,我为无兄弟。”(省略)正义曰:云牛兄桓魋行恶死亡无日者,案:哀公十四年《左传》云,宋桓魋之宠害于公。公将讨之,未及,魋先谋公。公知之,召皇司马子仲及左师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于曹以叛。民叛之而奔卫,遂奔齐,是其行恶死亡之事也。桓氏即向魋也,又谓之桓司马,即此桓魋也。
据注记所说的《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宋国司马桓魋(向魋)受景公宠爱而日益骄盈,有害公之意,景公数请享饮,欲因请讨之。桓魋察觉此情,抢先设计谋,即以接受增加领地答谢景公为由请公享宴。以日中为期,桓魋招集家兵企图谋杀景公。此计被景公识破后,桓魋反过来攻打受景公之命的兄长向巢,并据曹地反叛。但曹地不能久留,在窘境中接连奔卫、齐。其结局是向巢也离宋奔鲁。因这事件,司马牛还领邑于君,奔齐、吴,最后客死于鲁国郭门外。司马牛兄弟五人,(据《左传》有兄巢、桓魋、弟子颀、子车。)都各自亡命他国,走向客死的命运。这就是司马牛慨叹“人皆有兄弟,我独亡”的背景。
以上大略说了桓魋谋叛事件,不管在细节上有相当的不同,但大体上,这是与兄长隐太子建成企图谋反,太宗李世民先下手在玄武门把建成、元吉(太宗弟巢王)杀死一事相仿佛的。因此,唐初的士大夫一见“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记述,必然会想起桓魋谋反一事,继而联想起新近太宗李世民谋杀兄弟的玄武门事件,这对太宗来说是一件很不利且令他讨厌的事情。不管李世民一方强辩说这一事件是建成、元吉先动手,以使玄武门行动正当化,但就谋杀兄弟这一点而言,决不是简单地就可被免罪。因此,要尽可能地避免触及这一事件,回避属于可能引起联想的一切。李世民的近臣李延寿当然对这样的情况是相当清楚的,可以推断,当他接受太宗敕命编《南史》时,必忖度太宗之意,考虑到这一部分是必须削除的,并强行这样做了。这一结果,造成了稍显不自然的部分性削除。
又,《命子诗》是陶潜在长男俨出生时表述对儿子期待的诗。一般说来,对表现这种人之常情的诗是没有理由必须把它删掉的。但是,据新、旧《唐书》记载,李世民的杀戮不仅是涉及了激烈相争中的兄弟,还波及了从长子恒山王承乾开始,因相互争夺太子位的不肖不孝的皇子们,从而使太宗陷入了整个家族性的不幸状态中。因此,与其说李世民不喜欢陶潜以写家族爱(兄弟爱、父子爱)为主题的诗文,不如说他必须回避这些的存在。就李世民来说,对下面所引的《命子诗》怀有嫌恶感,想敬而远之是必然的。
卜云嘉日,占尔良时。名尔曰俨,字尔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沟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爰待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日居月诸,渐免于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李延寿熟知太宗的这种心思与嗜好,于是删去了《宋书》载有的《命子诗》原诗,而只写“又写《命子诗》以贻之”。
另一方面,《晋书》陶潜传如前所述,不但不言及《命子诗》,甚至连“潜弱年薄宦”以下部分也全部删去,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让我们先从对陶渊明的名字记载方法上所表现出的象征性谈起。
陶潜的名字,《宋书》记有“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昭明太子《陶渊明传》作“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承继这些,《南史》记为“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南史》沿用《宋书》,可以推断原本是写作“陶潜,字深明,或云深明,字元亮”的,后来因版本误刻或有衍字,就变成了目前《南史》所载状态。有关陶渊明的名字,在很早即产生了混乱,是非如何一时难以判定,但只要是见到“潜”、“渊明”(深明)、“元亮”,谁都明白这是指那位,至于哪个是本名又另当别论。但陶是确实也被呼作“渊明”的。而《晋书》却非常干脆地把“渊明”说舍去,只记“陶潜,字元亮”。这不是有什么根据才这样做的,它比《南史》为避高祖(李渊)讳,用“深明”的作法更彻底,这暗示了《晋书》的编纂方针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晋书》完成于《南史》)后,和太宗对文化领域统制权的进一步强化,《晋书》在改修中将适应唐王朝最新现实需要放在比“实事求是”更优先的地位来考虑。李延寿编《南史》时虽把不适于太宗的箇所加了删除,但至少还残留着作为史家的“实事求是”精神,对于在陶渊明生平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及有“言其志并为训戒”内容的《与子俨等书》未加削除,而《晋书》编者却急切地对不适合李世民的箇所大加改修,不惜牺牲了“实事求是”。《与子俨等书》中“吾年过五十”至“自恐大分将有限也”部分是陶对自己品德及情志进行真挚述说的文字,对描绘陶渊明身世及形象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因此,《南史》也只是删到易引起联想的《序》为止。但《晋书》却因下面所引的《与子俨等书》后半部分中强调了兄弟之间的情义,顾虑到有伤于经历了兄弟、皇子们不和、相互残杀的太宗的感情,不仅止于像《南史》那样进行一部分削除,而与对待陶的名字那样,干脆全部削掉。
恨汝辈稚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敬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颖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汜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晋书》比《南史》更加肆无忌惮的削除,或许如新、旧《唐书》所说明的,与存在着为了迎合太宗之意,不惜歪曲历史的许敬宗(作为《晋书》的监修)有很大的关系。
以上仅限于陶潜传,可知《晋书》的改修确实是基于李世民政权的某些关系,可以说看不到在实录陶渊明的真实形象,因而,无论怎么说也难以称得上是“标准的晋代史”。
(二)《晋书·陆机传》的改修
据《旧唐书·房玄龄传》,唐修《晋书》是以臧荣绪《晋书》(以下简称“臧《晋书》”)为底本,又参考了笔记小说、诸家晋史编成的。
寻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
但是,令人注目的是《陆机传》与《宣帝纪》、《武帝纪》、《王羲之传》等四篇都有太宗亲撰的论赞(即“制曰”),可以设想,《陆机传》等很有可能更明确、直接地反映了李世民的某些意念。下面先将现残存的臧《晋书》与《晋书·陆机传》作比较。
《晋书》:收录了陆机的《辩亡论》、《豪士赋序》、《五等论》,以此为轴心,配以前后官历,构成了传记。
臧《晋书》:按汤球辑《九家旧晋书辑本》,收录了《文赋》、《豪士赋序》、《谢平原内史表》。
以上五篇文章全是陆机的代表作,都被《文选》收录并由初唐的李善加注:
①《文选·文赋》 臧荣绪晋书曰:“机字士衡,吴郡人。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机少袭领父兵,为牙门将军。年二十而吴灭,退临旧里,与弟云勤学,积十一年,誉流京华,声溢四表,被徵为太子洗马。与弟云俱入洛,司徒张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以文华(录)呈。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张、蔡。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
②《文选·谢平原内史表》 臧荣绪晋书曰:“成都王表理机,起为平原内史。到官上表。”“太熙末,太傅杨骏辟机为祭酒。骏诛,徵为太子洗马。吴王出镇淮南,以机为郎中令。迁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又为著作郎。”
③《文选·豪士赋序》 臧荣绪晋书曰:“机恶齐王矜功自伐,受爵不让,及齐亡,作《豪士赋》。”
④《文选·辩亡论》 孙盛曰:“陆机著《辩亡论》,言吴之所以亡也。”
⑤《文选·五等论》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圣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汉封树,不依古制。乃作此论。
李善在《辩亡论》、《五等论》中并未引臧《晋书》作注文。《文赋》、《豪士赋序》、《谢平原内史表》则明确记有引自臧《晋书》陆机传。从以上事实看,似乎可以判定臧《晋书》原不录《辩亡论》、《五等论》,而只收了《文赋》、《豪士赋序》、《谢平原内史表》。
以上五篇均为陆机代表作,因此,在构写《陆机传》中收录什么样作品来构成传记与历史史实正误是无关系的,但是它却关系到编者的意图是一心想描绘出一个什么样的陆机形象来。而《晋书》把由《文赋》、《豪士赋序》、《谢平原内史表》构成的臧《晋书》特意换成以《辩亡论》、《豪士赋序》、《五等论》来重构《陆机传》,说明这是有“意图性”的改修。下面先简述各篇内容。
1.《文赋》,它是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文艺理论专著。陆机精心的艺术构思,卓越的文学见解,使《文赋》成为划时代的巨篇。
如众所周知的,陆机用“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说明文学来源于人对生活的感动。这伟大理论启发了锺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其词也完全如出一辙。论及文体,《文赋》上承曹丕《典论》中所划分的:“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等四科八体,但更有发展,认为可作十体分类,并写下了著名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深刻揭示了诗、赋的艺术本质与基本特征。在论语言方面,《文赋》既反对以辞害意“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又重视“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这一理论也为《诗品》所继承,《诗品·序》在言“古今胜语”时,列出了“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清晨登陇首”等“警策”之句,而唐、宋人所谓“诗眼”也得益于《文赋》。对文学的意义,《文赋》也上承《典论》说出了“通载而为津”、“被金石而德广”的不朽意义。
可以说,《文赋》对《诗品》、《文心雕龙》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故章学诚云:“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文心’。”(《文史通义》)
显然,臧《晋书》录《文赋》是反映了历史上真实的以文学名世的陆机。张华曾言“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文章》曰:“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大治,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陆云也云:“兄文章已自行天下。”(见《与兄平原书》)
以上均说明,陆机是作为六朝最杰出的文人之一而存在的,因此,不采录《文赋》的《陆机传》必然是失真的。
Ⅱ.《谢平原内史表》是陆机写给成都王颖,就自己任平原内史一事表示感激的心意。陆机虽出身吴国,但已仕晋九载,今受陛下恩赐得以高官,值国遭颠沛,无节可纪之际,诚惶诚恐,深感忧愧。接着《表》说明自己受齐王陷害,被诬告在赵王伦篡位起草了“禅让文”,虽幸遇陛下恩赦,但也希望在朝廷中雪冤,以绝众人诽谤。最后身忝大命的陆机表示:即刻驱至宫殿叩头谢恩尚有困难,而自己的心却天子骖驰,难捺畏慕仰望之情。《谢平原内史表》写出了陆机个人经历中的一个重要转契点。陆机自入洛后,仕途风顺,但因卷入“八王之乱”而被齐王收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救而免死,竟又意外地被封“平原内史”,这种戏剧性的突变,当然最好以《表》来说明。臧《晋书》舍许多名篇不录而选此《表》,正是为了写出在人生转折期间中陆机活生生的心情。
Ⅲ.《辩亡论》(上.下)是述说吴的兴隆与衰亡一事。上篇先述吴从兴到亡的经过。在汉末群雄割据中,荆吴之地起兵的孙坚勇气出色,后继者孙策得张昭、周瑜等贤臣,安定了江东,欲迎接汉天子,但大业未半而崩。孙权继承父兄事业,招用贤士,据荆吴之地而与魏、蜀争衡天下霸权,成天下三分大业,修礼乐,祭天地,治化远及四方,渐渐使吴国政权巩固。继孙权的幼主孙亮,守王业政无大阙。继亮的孙休,受虽老犹存的旧臣支持。孙皓即位,旧臣们多亡故,吴王室随之衰落,被晋军轻易击败而灭国。陆机回顾了这一段亡国史,以为:昔日魏、蜀之军比今日之晋军要强大,地形、战略与昔日无变化,而今昔结果却相反,说明吴灭亡在于任人不当。下篇分析吴兴亡的原因。孙权导致吴的隆盛在于举贤人、爱民,持有统一天下的大度。爰及中叶,天人之分已定,百度亦备,即使是中庸君主,只要能遵循法典也不会有危亡之患。所以陆机认为,吴亡的原因,是因陆抗这样的良将亡故。即吴亡的真正原因在于君主不识贤臣,在人才录用上有失误。
Ⅳ.《五等论》是说治理天下时,五等封建制比郡县制优越。天下之大,帝业至重,昔日许多圣君无法一人独治,为了维固王室以安天下,圣君建立了封五等爵、分封领地的五等诸侯制。其结果是诸侯们亦以此心务各国之政,普天下之民,也知感恩于圣君,天下无暴逆谋反、永葆安泰。陆机认为:天下安定是因诸侯思治,立天子之尊是保诸侯自身。但物事有盛衰,治化的废兴在于实行之人。故桀、纣、幽王时出现了诸侯权力过大而王室衰弱的缺点;在商汤、周公之时却呈现了定礼乐、封土之制兴隆的美点。
陆机认为:当国有忧患、王室衰弱时,社稷所以能续存者,还是因为仰仗有藩卫王室的诸侯。秦抓住五等制的缺点,忘记了诸侯拱卫王室的作用,以富国强兵来治天下,因此在国忧之际,瞬间即陷入孤立无援而灭亡。相反,周代因无明君而衰弱,但有诸侯制而使皇统存续了很久。有人说诸侯制属世袭,往往产生谙主暴君,郡县长采用察举,适当人才去适当场所,故郡县制较易治理。陆机在《论》中反驳道,郡县长为自身利益而考虑,好为名利而奔走,而诸侯因封国的治政直接牵扯到家族利益,故会加以谨慎地对待。
Ⅴ.《豪士赋序》是刺齐王矜夸自己的才能与偶然的成功,受爵不知辞让的作品。陆机认为,功业并非一定是由个人能力大小决定的,多因合时运而成功。因徼幸的一时成功,往往有人就夸耀个人力量与功勋。身居下位而替君王下命令操纵天下者,必树敌怨而身受害,甚至连具有崇高品德的周公、怀忠义的霍光也因亲身治政,使天子只主持社稷、宗庙的祭礼,终被君主怀疑,人人诽谤。所以圣人忌过分的功名,功业、权势、欲望各应到一定程度为止,当知道无可进展、无法长保盈满状态时,如能超然离开世俗、引退高位,则盛德将凌驾于古之圣人,高风亮节会炳于史册,如能这样,身安泰而名声愈高。
综上所述,从臧《晋书》与《晋书》所收录的陆机文章内容来看,其共同点是对陆机文章的文学性方面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两书在描绘的陆机形象及评价陆机文章之间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
臧《晋书》中所采用的《文赋》是以修辞主义美学创作论贯穿始终的“赋”。《谢平原内史表》是有关陆机个人在被授官后表感谢之表,这些都没有论述到天下国家、经世济民的内容。与此相对,《晋书》收《辩亡论》是分析吴国兴隆与衰亡原因的;《五等诸侯论》是借鉴历代治世,这两论内容都清晰显示了它是立足陆机的儒教的天下国家观、经世济民观的。即与臧《晋书》采录陆机个人生活有关联内容文章,偏重于陆文学修辞方面相对照,《晋书》在改修时主要采录有关陆机的经世济民观内容的文章,而重视陆文的儒教治世方面。
从《晋书》所收两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陆机所追求的太平盛世是:治世要重视人才,只有君臣相互尊重、相互受益才能使天下国家安定。这与新、旧《唐书》、《贞观政要》等论述的李世民政权的统治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李世民才对与自己儒教治世观相接近的陆机的这方面观点有强烈的共鸣,在改修《晋书》时,特意为陆机亲撰论赞,并称赞他是“百代文宗,一人而已”。从《全唐诗》收录的太宗作品来看,也与名臣魏徵等一样,太宗在诗歌的表现形式上有敬慕南朝艳丽雕琢性美文的倾向,但其核心部分是持有文章应寄托治国平天下的儒教文学观。太宗把陆机评为“百代文宗”,决不只是注目于陆文的华丽的表现形式,而主要是为陆机文章的内容所吸引,所以在称赞陆机时,与对形式的评价如:“文藻宏丽、独步当时”、“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一绪连文,则珠联璧合”、“其词深而雅”相对照:一定要附加上如:“言论慷慨,冠乎终古”、“叠意,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其义博而显”之类对内容舒面的评价,并认为陆机的文章远远地超出在内容、形式上谐和并留下了优秀诗文的枚乘、司马相如、王粲、刘桢。
“制曰”更认为:陆机在吴时是“廊庙”、“瑚琏”之才,“奉佐时之业”,但正遇到吴之亡国,不得已向北仕晋后,如鱼失鳍、如鸟失翼,怎么期望“翔跃”也已不可能。尽管陆机自认为才智可安时、堪佐命,在晋庶可保名位,但终究办不到。陆机在世运闭塞时,不知已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在后半生“奋力危邦,竭心庸主”,但其“忠”、“实”不被承认,反而受到诽谤,终于落得个“卒令覆宗绝祀”的悲惨结局。
从以上所说的“制曰”内容来看,论赞的整体思想几乎都是注目于陆机的治世才能的。这样的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太宗的“制曰”,除了充分显示了他的独裁性及以自我审美标准来强行改变历史人物面目的狂妄外,对全面认识陆机形象及评价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毫无价值可言。很明显,历史上真实的陆机并非以杰出的治世才能或政治家而名扬史册的。封五等与郡县制的优劣问题,吴灭亡的复杂原因及必然趋势,也均非中世纪的陆机所能够正确、科学地判断的,还有,陆机虽以诗闻名于当世,但亦决非“百代文宗”。唐太宗以文学的“门外汉”硬要干预史学、文学范畴,以“制曰”这种“万岁”金口玉言所规范下的谬论,因它的“绝对的”政治权威性而遗毒于后世并开启了历代统治者强行干预文学的先河。总之,李世民用称赞创作了与自己统治思想一致的经世济民内容美文的陆机,来暗示了陆机文章是世上文章的典范。这一圣意在当时是奏效的,在整个唐代,除了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外,如上述陆文章那样的美文占了绝大多数。
下面本当论及同样由太宗写了论赞的《晋书·王羲之传》,以讨论那又是在什么意图下、具体又是怎样改修的问题,但限于本文篇幅,只能另稿详论了。
标签:晋书论文; 宋书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唐朝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陶渊明论文; 李世民论文; 陶潜传论文; 论语·颜渊论文; 突厥论文; 玄武门之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