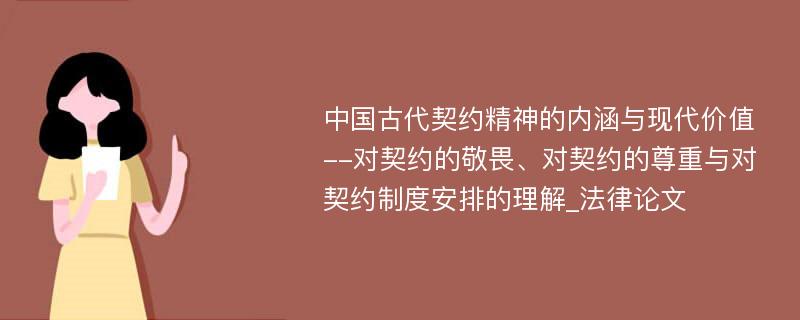
中国古代契约精神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敬畏契约、尊重契约与对契约的制度性安排之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契约论文,敬畏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内涵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一直有广泛而频繁的契约实践,传世的大量实契可为证明①;中国也一直有契约知识的传承,起源于唐朝后期的契约样文,其后绵延不绝,是订立契约的参照或遵循;中国古法典尽管留存不完整,但仍能看到其中有关契约制度的大量规定。这三个方面的事实表明:中国存在着契约制度,存在着相应的契约意识和契约观念,有特定的契约文化。那么,中国是否是一个契约社会?有没有契约精神?
我的意见是肯定的。古代中国虽采取的是等级的社会与国家的结构方式,但政治等级上的君臣、官吏、官民之分,社会等级上的良贱之别,家族家庭内部等级上的亲疏、尊卑、长幼之异,并没能消灭经济生活中的契约的平等,缘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庭伦理生活与经济生活不同,在朝、在家、在外不同,古代的中国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契约本身也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人的契约意识和契约观念,一直是视契约为确定权利义务的,尤其债权契约是持有财富的象征;中国人有关契约的概念,也一直在突出契约内容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性质②,“约束”二字,比较传神,与古罗马法的“债为法锁”之意相同③;中国人也有契约精神,这其中,既有他们对契约的敬畏,将约定等同于法律,也有他们对契约的尊重,视约定优先于规定,更主要也更为基础性的是,中国人对契约的理解,是将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以为契约是“立信”、“结信”、“征信”的。这后一点,是所有一切的基础性认识和基本前提。
一、约定等同于法律的精神:对契约的敬畏
敬畏契约,西方尤然,故人们常将其与法律相比拟。在西方法谚中,“合意生法律(Consent makes the law)”[1]119[2]150,“合意成契约为法律(Agreements constitute the law of the con tract)”[1]145,或“当事人的协议使契约具备了法律效力(The stipulations of parties constitute the law to the contract)”[2]151,“契约因当事人协议一致而具有法律效力(Contracts take their law from the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2]151,都强调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契约,即为当事人的立法。这是西方私法自治(意思自治)原则承认私人事务的处理,应当听任其自由意思为之的精神。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这样一种契约精神,在古代的中国并不缺乏,甚至还很浓厚。中国的契约语言,早期的三个发展阶段有三种说法,但无一例外地都表现了对这种合意的敬畏。
(一)汉以来的“民有私约如律令”
将契约的约定比拟为律令——“民有私约,如律令”或“有私约者当律令”,即契约具有与律令一样必得遵行的效力,是汉代以来契约的常用语。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7云:“汉时行下诏书,或曰‘如诏书’,或曰‘如律令’。苟一事为律令所未具而以诏书定之者,则曰‘如诏书’”;“苟为律令所已定而但以诏书督促之者,则曰‘如律令’”。“‘如律令’一语,不独诏书,凡上告下之文,皆得用之”,“其后民间契约,道家符咒,亦皆用之”。[3]845-846确如王国维所言,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汉代契约,在“买地券”这种为死者虚拟的买卖土地的契约中,可以看到频繁使用“如律令”一类句式的情形;后世同汉。
据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从东汉开始历三国、两晋、南朝宋齐梁直到唐五代、北宋、金、元、明的39件买地券中,分别使用了“如律令”、“以为析(律)令”、“这以为析(律)令”、“一如律令”、“有私约者当律令”、“民有私约,如律令”等20种套语。其中,充斥了夸张性语言的、道教色彩浓厚的地契也有许多,如“急急如律令”、“如天帝律令”、“急急如太上律令”、“急急如五帝女清律令”、“急急如五常使者女青律令”、“一如奉……太上老君陛下之青诏书律令”等,但在强调“如律令”这一点上,是相同的。[4]50-1016
买地券中的“如律令”等说法,学者以为是模仿实契而来的。这种说法,可以从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契约中得到印证。敦煌有5个便麦契,使用了“仍任将契为领六(令律)”、“仍任将此契为令六(律)”、“仍任将契为领(令)[律]”、“仍任将[契][为]领六(令律)”等套语[4]362-403,意即:该契的所有约定,都与律令效力相同。此外,敦煌还有2个契约有“仍任不著领六(令律)”、“其[车]请不著领六(令律)”的套语[4]362-404,意即不依照法律规定而依照本约定,通过具体的契约约定与国家法律相对抗,类似下述的“约定优先于规定”的契约精神。两种套语的意指虽不同,但都在张大契内约定的效力,以示其不可移易。这表明这种视契约如法律的意识,在契约生活中是一种实际的存在,并影响着民间契约生活。
(二)北凉、高昌的“民有私要,要行二主”
北凉时期的吐鲁番契约中,有“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套语。至高昌,这一套语几乎是每契必具。比如,高昌13件卖买田园、卖薪、买作人、买舍地等契券中,共11件有该套语;30件租佃契(即夏田、夏树、赁舍券)中20件有,18件借贷契约(举锦、举麦、举钱券)中17件有,无者皆属于残契,可能也存有这样的语句;4件雇佣契约(雇放羊、雇岁作券)中全部有。在具体表述上,一般都采用“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4]86-293;在时间上,唐初也沿用了高昌时期的该套语,太宗贞观、高宗永徽、乾封时仍在使用。
“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强调私人间的约定应该也必须得到双方当事人的遵从,类似西方“契约是当事人的法律”的说法,所以一旦有约定,必须通“行”于双方当事人之间。与汉以来的前述套语相比,它没有与律令相比类,而是更着眼于其纯粹的民间性。
(三)唐代的“官有政法,人从私契”
唐代吐鲁番契约,对此套语略作改造,形成了“官有政法,民从私契”,增加了“官”及“政法”的对照。这一过程,从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开始,高宗以后沿袭了这个改变。同时,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起,开始避太宗李世民讳,“民从私契”变成了“人从私契”。而在敦煌,受唐风的影响,在吐蕃占领时期及以后的契约中,也能见到“官有政法,人从私契”套语。后一句,有时也作“人从私断”、“人从此契”,意思未变。
在唐代,举凡买卖、租佃、借贷、博易、雇佣、伤害赔偿等契约,都有“官有政法,人从私契”套语出现;甚至契约样文如《放良文书格式》中,也有使用者。仅张传玺所收录就有14例。[4]194-661这一习俗,延续到了五代时期的敦煌。我们只在《北宋太平兴国九年(九八四年)安喜县马隐父子卖坟地券》这个虚拟的契约中,看到了“官有政法,不取私约为定”的说法[4]606,与此不同。或许,这来源于宋初的法律规定。
“官有政法,人从私契”套语,在“官、民”对举中,着眼于契约与官法的相同性或类似性,强调私契与官法一样的必得遵从的特性。即是说:凡事皆有约束,做官服从政令、法律,为民遵从契、券约定;“人从私契”保留了此前的“私”的民间性内容,以示其与国家法律的“公”意不同,因而在其后埋伏了抵抗国家法律的意蕴,这是当时契约中出现对抗国家赦免私债效力的抵赦条款的意识原因。这意味着:尽管“官有政法”,但民还是要“人从私契”的,私人服从的是私契的约定。
总之,汉以来“有私约者当律令”、“民有私约,如律令”,唐代的“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等套语,视契约如法律,显示了当时契约的特殊地位,以及中国古来即有的契约意识,在中国契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虽然,宋元以后的契约中不再有这类表述,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的中国就丧失了这样的契约精神。我们强调的是,通过这些套语,民间或立契人表达的是一种非常正式而郑重的对契约约定的正视,一种通过比类法律之必得遵从,而希望获得的对约定条款的敬畏。在古代中国,律令是国家正式制度的代表,将契约比类为法律,民间私人间的合议获得了“准法律”的地位。北凉、高昌的“民有私要,要行二主”,也是明显的私法自治的意识。由此两方面,中国人建立起了他们的敬畏契约的基本精神。
二、约定优先于规定的精神:对契约的尊重
西方法谚,主张“习惯与合意排除法律之适用”(Custom and agreement overrule law)[1]144[2]150,契约精神最终形成了“约定优先于规定”原则。类似的法谚有“契约胜法律”或“当事人的协议高于法律的规定”(The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overrides the law)[5]59,“当事人明示的协议胜过法律”(The express agreement of parties prevails against the law)[2]151,意指个人的意思,法律应当尊重,私法自治(或意思自治)要求对当事人私事的解决,首先应以其所订立的契约内容为准,即原则上契约应先于法律而适用。因之,法条中常有“契约另有订定者,不在此限”的规定。
在中国,这样一种契约精神也是存在的。这种精神,究其实是一种生自民间的纯粹个人意向、生根于利益考量的愿望表达。中国似乎缺乏“私约不损公法”(Private contracts cannot derogate from the public law)[5]59之类的法谚。这里的公法是指强行法而言的,而“契约胜法律”的所谓法律是指任意法而言的。任意法可以以契约排除其适用,而强行法则不可。因之,在西方,法律中常有“法律行为违背强制或禁止性规定者,无效”的规定,作为对“约定优先于规定”的限制。但在中国,“约定优先于规定”的精神是通过扭曲的方式展示出来的;其发生作用的方式也是特别的。
一方面,在“家资尽者,役身折酬”等以“家资”作为出举(有息借贷)之债的履行方式的场合,契约中例有“听掣家资杂物”的约定,但也不乏反制度的、违法的约定。比如,契约中可以约定,“牵掣家资牛畜,有剩不追”、“掣夺房资什物,用充麦直。有剩不[在]论限”等[4]356-404,这些契约约定,属于唐《杂令》中所谓“契外掣夺”,明显违背《唐律疏议·杂律》禁止“强牵掣财物过本契”的规定精神[6]485,民间显然是在与法律强行规定相对抗。如果说这种约定涉嫌违背“私约不损公法”理念,那么,我们就应关注另一种“预防性”的约定——旨在抵抗国家临时发布的私债赦免令、以求取得“约定优先于规定”效果的情形。
在这方面,这种契约精神自始就是国家强权的对立物,是对国家过度干预民间契约的一种强烈回应。比如,契约约定,“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4]340、“如后有恩赦,不在免限”[4]364-370,契约中的这类抵赦条款,与国家的大赦令屡屡赦免民间债负相对抗。笔者曾撰文讨论过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抵制赦免条款问题,就其与当时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问题进行了分析,基本的结论是:契约中的这种抵赦条款,是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7]我现在仍坚持这一基本结论,但这里更强调前述资料中所反映的“民间意识”及其细节问题。因为债负赦免问题是复杂的,不仅包括高利贷,而且涉及其他借贷并波及到了其他契约形式,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
(一)高利贷债负赦免的初衷及其带来的问题
按《魏书·释老志》记载,国家最初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及“翻改券契”等两种民间高利贷行为,前者因其违背了“一本一利”的收利不过本的规则,后者则是禁止“回利为本”的复利行为(“翻改初券”即将原本与利息重新计作本钱而生利)。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基本延续了这个传统。从现有资料看,这一干预过程,自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元初。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抵赦条款,处于这一时期的中段,它是民间高利贷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到明清时期,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
赦免私债的初衷,在执行中经常变味,正常的契约约定得不到尊重,债权人的正当利益经常受到损失。比如北魏,《魏书·孝庄帝纪》永安二年(529年)八月诏:“诸有公私债负,一钱以上、巨万以还,悉皆禁断,不得征责。”公债负先不论,私债负不论数额大小,一律不允许征偿,问题颇多。因本利征偿情况,每一宗债负会有不同:既可能有征利过本的,也可能有本钱都没有征回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免征,殊不合理。而这种极端情形,在古代一再出现。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光宗《登极赦》文云:“凡民间所欠债负,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该赦文发布后,“遂有方出钱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尽失之者”的情形。[8]412对此,沈家本评论曰:“民间债负乃私有之权,本不应在赦中。赦本非美事,此尤为失之甚者。”[9]773-774沈氏此论,是出自西风东渐之后的私权神圣观念的评价。
因而,我们说古代国家赦免私债,表明国家权力一度对纯粹民间事务的干预范围大、程度深、力量强。这里更应强调的是,这种干预惯性所造成的深层次问题。
(二)合法有息借贷、无息借贷中出现抵赦条款的意味
就此而言,抵赦条款应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违背法定利率的高利贷是应该被禁止的,因为它违背了强行法的要求。唐代《杂令》“公私以财物出举”条,比较全面地规定了有息借贷契约(出举)的利息禁制等:
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又不得回利为本(其放财物为粟麦者,亦不得回利为本及过一倍)。若违法积利、契外掣夺及非出息之债者,官为理。[10]412-413
这里有三个限定条件,一是最高利息率的限制,“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二是利息的总量控制,“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即利息总量不得超过本金;三是复利的禁制问题,“不得回利为本”即不得将利息作为本钱重复生利。按“法律行为违背强制或禁止性规定者,无效”的原理,国家对高利贷的任何一项违规行为所造成的债负进行赦免,是符合法理的。
另一方面,债负赦免如果针对了未违背法定利率的出举(有息借贷)债负而进行,就有问题了,因为这里不存在违背强行法的情事。我们现在注意到的是,国家对有息借贷(出举)高利盘剥的赦免初衷,不仅涉及到未违背法定利率的出举(有息借贷)债负,甚至最后竟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在可以考定为无息借贷的唐及吐蕃3个借贷契约中,也出现了“中间如有恩赦,不在免限”、“如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的抵赦条款。[4]368,370[11]154这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在强化,希望通过抵赦条款取得主动,得到“约定优先于规定”的效果。赦免债负波及无息借贷,与国家倡导民间相互抚恤以及无息借贷的互助功能、缺乏图利意识的道德指向,出现了严重冲突,并不合算。
(三)买卖契约中出现抵赦条款的问题
高利贷债负的赦免是欲解小民重困④,但那本来是借贷领域的事情。问题是国家赦令也牵涉到其他契约形式,比如买卖关系,致使民间在买卖时也担心国家大赦令的突然出现,故而买卖契约中也出现了抵赦条款。
我们注意到,唐五代时期的敦煌买卖契约中,有11个具有抵赦条款,包括3个卖地契,5个卖(宅)舍契,1个换舍地契,1个卖儿契,1个买舍契。除《吐蕃未年(八二七年?)敦煌安环清卖地契》中约定“已后若恩敕,安清罚金伍两,纳入官”外,其余10件大抵均写明“或遇恩敕大赦流行,亦不在论理之限”、“中间或有恩赦流行,亦不在论理之限”等。[4]216-247
无疑,这是民间社会被国家赦令逼出来的举动。但其中包含的意义却是:民间希望自己的契约受到保护——既得不到国家的强有力、始终一贯的严格保护,那就来个自我保护——以当事人双方合意的形式堵塞国家随时可能发布的大赦令免除债务的意图。因此“后有恩赦,不在免限”,是民间努力争取先机,时间上来个“约定先于规定”,以取得“约定优先于规定”的效果。国家有时不尊重我,我就来个自尊、自重。
三、立信、结信、征信精神:对契约作为制度安排的理解
西谚谓:“契约应严守”(Vertrāge sind zu halten)[5]59,“诚信原则之要求,在乎依约履行”(Good faith demands that what is agreed upon shall be done)[1]133,甚至强调“订约在己,解约不在己”(It is mine to promise,not to discharge)[5]82,这都是突出诚信、守信、践约。
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道德原则与伦理秩序;但在普遍的重人伦道德、重人生义务的大氛围中,中国人除了强调君子之道德上的“信”“义”外,也能将契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理解。在这种理解中,契约是一种制度性安排,从而形成道德诚信之外的“立公信”机制。
(一)立信、征信:对契约作为制度安排的总体理解
《慎子》曰:“折券契,属符节,贤不肖用之。”[12]556慎到注意到了“券契”作为制度被普遍使用的事实:无论是有道德、有才能的人,还是缺乏道德、才能的人,大家都在使用“券契”、“符节”,这是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呢?
《太平御览》摘录《慎子》时,将其纳入“信”之下。可见,《御览》的作者认为慎子的说法,体现的是一种取“信”的制度与机制。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也云:“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朝”指国家政治、军事,“市”指市场、民间日用,公私都免不了用“符、契、券、疏”去“征”信。
符节、券契可以“征信”,不是说符节、券契这些契约本身就是“信”。《太平御览》一本注云:“券契不为人信,人自用之”,这与《慎子·君人》的说法一致,慎子云:“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于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13]即券契、钩策本身是超不过人智的,但人们还是寄托于它们,因为它们可以“去私”、“塞怨”。《文子》曰:“使信士分财,不如探筹;使廉士守财,不如闭户。”[14]729用抓阄、锁门的办法,可以保证守信的“信士”、清廉的“廉士”不致出现定力不足而发生分财不均或监守自盗的情事,这是“去私”;而这样一来,也就杜绝了人们的无端怀疑,这是“塞怨”。至于有德者是否靠得住,都无关系,重要的是离开道德、别寻出路。这里指明了一个道理:制度、机制高于道德,对制度的信赖要优于对有德者的信任。
慎到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讲出这一道理的。《慎子》云:
夫投钩分财,投策分马,非以钩、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恶者,不知所以怨。故蓍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12]549
这是说,用投钩(拈阄)来分配财物,用投策(拈阄、抽签)来分配马匹,不是因为“钩”、“策”本身能够做到均平,而是为了使得得到美物、好马者,不因此而去感激什么人;得到恶物、劣马者,不因此而去抱怨什么人。目的是杜绝怨望,也杜绝感恩戴德。同理,用蓍草、龟甲兽骨来占卜,是求得“公识”;用秤锤和秤来称量物品重量,是为了求得“公正”;用契约、文书凭证来记录交易、记录出入取受,是为了求得“公信”;用尺子、斗斛来丈度、称量物品长度、体积,是为了求得“公审”;用法制、礼籍来定立规范、给予约束,是为了求得“公义”;而诸项“公”的建立,就是为了抛弃“私”情、“私”义的。
在慎到眼里,被看成制度性安排的,不仅是契约,还有耆龟、权衡、度量、法制礼籍以及符节、钩策等具有客观性的“物”件及相应的“投钩”、“投策”(探筹)、“闭户”等机制。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他“书契所以立公信”的说法,即使用文书契约得到的是皆无异言的公信。
坚持对契约作制度安排理解的,都是法家或具有法家倾向的人,这是法家对中国思想的贡献之一。
(二)结信:契约的制度性质
慎到云“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周礼·地官·司市》又载:“以质剂结信而止讼”,是说契约是遵循市场道德的,而不是一般道德。“公”的道德,是双方的合意,而不是单方之“私”;“信”的道德,是双方的在合意基础上的“确定性”,一旦做出,就不得反悔。在这里,契约精神表现为一个“公信”。
作为契约制度性质的“结信”,首先是取信于双方当事人。取信的方式一是书面契约。中国契约基本上排斥口头契约,采取书面形式,这可以克服口头语言之无法保存、无法再现的性质。契约中常说:“恐空口无凭,立此为据”,即指此。二是双契。将“券”分为两半,由双方当事人各执一半,作为凭证。“券”字就由“半”和“分”两个字组成。后世契约中说:“今恐无凭,立此文契为用者”[4]578,586,“今恐人心无信,故立文契为照者”[4]638,“恐后无信,故立此契,用为后凭”[4]628,640,券契能取信于人,即其所具有的“凭”、“信”性质。
作为契约制度性质的“结信”,其次是取信于他人,故中保证见画押等也具有制度安排性质。在实践中,“两无中据,难定曲直”[15]1064,被认为是不合此前的设计的,被理解为无法操作。当事人不会打到官府那里去,即便告到官府也不会受理。所以,中人、保人,在中国契约实践历史上,起源甚早。西汉契约中的中人,称“在旁”[4]33-34;保人,称“任知者”、“任者”[4]27-28。
(三)止讼:契约的机制价值
中国契约,自其第一种记述形式(竹木简牍)开始,就注意到了其遏制、杜绝争讼的机制,并在程序上注意发挥其诉讼证据功能。
契约的止讼机制,《周礼·地官·司市》讲“以质剂结信而止讼”。这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止讼”,具有事先的防遏和杜绝意味。在具体操作上,《周礼·秋官·朝士》云:“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判书”即契券,在司法上,无契券就“不听”即不予受理。东汉郑众在解释《周礼·天官·小宰》“听称责以傅别”时说:“‘称责’,谓贷予;‘傅别’,谓券书也。‘听’讼‘责’者,以券书决之。”也指听讼以“券书”为据。又,《周礼·秋官·大司寇》云:“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注:“狱,谓相告以罪名者。剂,今券书也。使狱者各赍券书,既两券书,使入钧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书,不入金,则是亦自服不直者也。”讼者提供不出券书,就等于“自服不直”,就得输官司。
《左传·文公六年》载赵盾“始为国政”,采取了“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由质要”等一系列新政。其中“由质要”,“由,用也;质要,券契也”,所谓“‘由质要’者,谓断争财之狱,用券契正定之也”,则不过是《周礼》所载的以契约为证据的制度,在春秋时期的实践情形,不过是申明旧制。
后来的中国,在制度上都是将契约作为财产法或诉讼法上的主要证据的。
唐宋法律承认“私契”的效力,民间借贷、租赁、卖买、雇佣等契约,都是确认产权的依据。比如,遇到国家罚没罪人财产,遇到财产权纠纷时,契约的证明作用就显露出来了。“券证分明”是绝对的要求。
基本沿袭了唐令的宋仁宗天圣《狱官令》规定:“诸犯罪资财入官者,……若受人寄借及质钱之属,当时即有言请,券证分明者,皆不在录限。其有兢(竞)财,官司未决者,权行检校。”[16]338就是说,对犯罪人没收财物时,如有与他人发生寄托、借贷、质押等契约关系者,只要当时声明在案,有契券能够充分证明,就不应被籍录没收;对存在财产权纠纷(竞物归属)等问题者,则官府应予以登记,以备将来断定。对后一款,承袭了唐令的日本《狱令》的资财入官条,作了如下注释:“谓假有竞财,判决之日,应罪人得者,随即没入;若应入他人者,依法还之。”[17]331即对财产权争执,判决竞物归犯罪人的,没官;归他人的,还主。前者反映的正是契约对财产权的证明力。
契约的这种证明力,在国家得到遗失物而需要给还主人的时候,也是有效的。沿袭了唐令的日本《捕亡令》规定:“凡亡失家人奴婢、杂畜、货物,皆申官司案记(……其虽未有案记,而券契及证据,足可验者亦还。故云券证分明)。若获物之日,券证分明,皆还本主。”[17]304即是说,有“券契及证据”证明遗失物是该主人的,即使没有在官府登记,在获得该物时也应还主。
在实践中,契约在司法上也是有证明力的。盖法律承认契约等书证的证明力,无则不受理,即使受理也会败诉。契约成为诉讼之基本证据。
首先,赎金凭证为证据。在抵押借贷中,质契和赎金凭证等书证,是法官审理争讼时必须调取的证据,无则败诉。因不动产抵押,往往以土地或房屋买契为质。质契要由承押人收执,以备出押人取赎。唐代有个“智断隐钱”的著名案例,因出押人缺乏先期交付的赎金文据,淮阴县和州府都不予受理,不得已越诉至邻县。江阴县令赵和,以诈术得到承押人实际拥有出押人先期赎质财产的实情,搞清了底里,遂断给还。[18]66
其次,租契也为证据。宋代有一人租牛于邻县的姻家,后“窃券而逃”。牛主征租,不仅得不到租金,牛也被卖掉了。累年打官司,“无券可质”,邻县又以管辖问题不予受理。泰兴县令刘宰,用诡诈方法得到被盗之租契,断令租牛者归还其牛与租金。[19]234
再次,婚书也为证据。清代周庆云聘郝延龄女,因家道中落,“婚书又失”,欲娶郝女,郝延龄拒绝之。河间府陈崇砥判曰:“婚书虽失,有媒妁可证”,终于通过第二证据判决此案。[20]445
最后,买契与借契等为基本证据,若无法查证,法官会设法依照租赋记录、财产清单为佐证断案。清代杨寡妇被族人诬以不洁,“夺其田产契券”,逐出家门。但杨氏颇有心计,在棉衣中密藏了丈夫所记的自家“租赋出入”清单,廖冀亨核查租赋记录与财产相符,遂将田产断与杨氏。[20]120
这些还只是当时案例的一鳞半爪。在古代中国,契约在制度及实践中均有证明力。契约即是当事人的法律,法官就要以之作为审判依据,这是西方的原理;在中国,契约同样被比类为法律,也得遵照执行。就此而言,中国人的契约精神,既是一种法律精神,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它完全可以与西方法律精神相衔接,成为构建新型法治的“中国元素”。
注释:
①杨国桢先生曾估计:“中外学术机关搜集入藏的明清契约文书的总和,保守的估计,也当在1000万件以上。”见杨国祯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②东汉郑众解释《周礼·天官·小宰》“听称责以傅别”时说:“‘傅’,傅著约束于文书。‘别’,别为两,两家各得一也。”“别”,指其形式;“傅”则是其内容,“傅”为将双方共同议定的“约束”事项“著”于“文书”。《释名》曰:“券,绻也,相约束绻,绻为限以别也;大书中央破别之。”刘勰曰:“券者,束也,明白约束,以备情伪,字形‘半’、‘分’,故周称‘判书’。”(《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
③周枏先生云:“优帝《法学纲要》称:‘债是依国法使他人为一定给付的法锁。’所谓法锁或法律上的锁链,即指特定的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见周枏:《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版,第628页。
④我们曾指出:国家对放免民间债务的认识,出发点在于嫉富怜贫意识、“父家长”意识、清静官府意识,并夹杂了对放债造成社会问题的清醒认识。比如唐宪宗赦文云:“京城内私债,本因富饶之家,乘人急切,终令贫乏之辈,陷死逃亡。主保既无,资产亦竭,徒扰公府,无益私家。”后晋高祖天福五年诏也云“宜蠲宿负,以惠黎元”。这都是意欲解除受困于高利盘剥下的穷苦百姓,缓解社会矛盾的不得不尔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