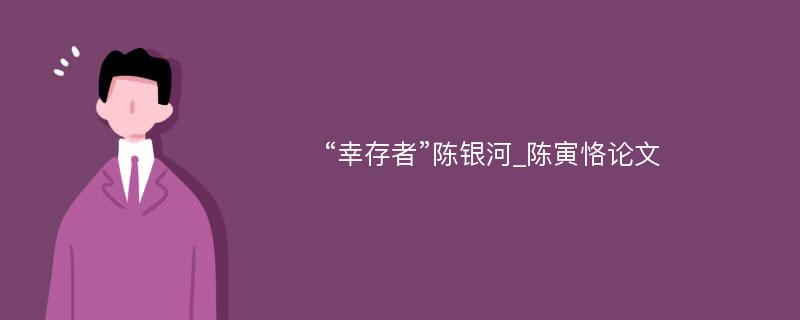
“遗民”陈寅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民论文,陈寅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我在《“遗民心态”与“角色化”》一文中曾说:
谈明、清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现象是很值得研究的,这便是“遗民心态”。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王国维、陈寅恪,几百年间,文人多讲“气节”,有趣的故事不知流传了多少。“气节”当然可做分析。明末清初的“遗民”反抗外族入侵,是一种“气节”;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能不能也算品性高洁?这些人都生于两个朝代之间,也都是新王朝的不合作者。因为失望于新朝,便不免留念旧朝。失望之中也常常寄情于旧朝文化,以往昔的时光驻足生命。陈寅恪或许例外,他比顾炎武、王国维还是进化了。这里颇有点儒家“杀身成仁”之态,细说起来,是民族的良知,其态颇为感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宝贵的精神,常常在这种心态中闪烁着。
但“遗民心态”有一个问题,一是为旧的主子守节,今人看来,便不免迂。王国维算是懂尼采、康德的人,偏偏在生存信念上,摆脱不了皇权的影子,便显得可笑。顾炎武到明陵拜谒亡灵,悲慨之气撼天动地,不免还是有点文人的奴气。这都是旧式文人,用今人的尺度去量,有苛刻之嫌。超历史地看古人,自然有距离感。但“遗民心态”,对后代知识分子,也曾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便是“清谈”精神。“清谈”好不好?这要做分析。好的一面是在俗界中多了一片净土,是民族文化精神尚未堕落的表现之一。但历代“清谈”者,拒不入世,对当时社会的文化建设,是个不小的损失。于是文人越来越边缘化,鲜于直接影响社会进程。而支撑社会文化旋转的,大多是品学较逊于“遗民”的人。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分离,不能说是好事。责任不能都在“遗民”那里,但“遗民”精神延伸的结果,却是更大的文化萧条,民风的积重难返,便一清二楚了。
鲁迅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才出现了真正意义的现代人格。顾炎武、王夫之、王国维等人与他相比,都要大为逊色的。“五四”个性文化,是对“遗民”心绪的巨大冲击。在鲁迅那里,人本的东西,入世的东西,特别是反抗绝望的东西,是极其深刻的。所以,谈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社会角色,我以为鲁迅是很好的参照。“遗民”式的“清谈”固然不可缺少,但我以为更需要的是参与现实变革的务实的人。现实不都是净土,但没有人去改良现状,净土从何而来?倘没有务实者的出现,改造国民性,便是一句空话。
这常令我想起当下知识分子的“角色化”问题。孤芳自赏地躲在象牙塔里,把自己看成圣人,这便又犯了旧“遗民”的老病。是虚幻的道德感在作怪。倘若是真正面壁做学问,那又当另说。述而不作,或不述不作,均不好。文人固然有社会良知这一“角色化”问题,但“角色化”一旦把己身凌驾于社会之上,民众之上,而缺少“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殉道感和平民化精神。我以为知识分子要真正确立自己的价值意义,是殊难之事。
由“遗民心态”,想到当前文人的“角色化”问题,觉得可总结的事情很多。这是一个棘手的文化难题,涉及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信念问题。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以期文人们在此话题下,更深入地谈论下去。
写作此文时,我正在读陈寅恪的著作。坦率说,依我这样的知识阅力,评价这位国学大师,自己也觉得好笑。但既然在谈二十世纪的文人,无论如何,他都是个值得思考的人物。对我来说,陈氏更多给人留下的是一种敬重,仿佛一座难以攀援的高山,他矗立在那儿,以自己的博大、伟岸而显示着价值。但另一方面他与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气质,似乎太远了。无论是其学识与品格,都不像胡适、周氏兄弟那样与我们这样亲近。似乎可以说,他是现代中国最后一位“遗民”,同王国维一样,在创造了辉煌的学术殿堂之后,便消失在黑暗之中。而那巨大的精神存在,后人要继续复制,已不再可能。
无疑,陈寅恪的一生是个悲剧。他的渊博的学识,独立的品格,与他所处的时代都严重地对立着。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处于时代主流思潮的边缘,从域外求学,到治学于清华国学院;从战乱流亡,到困居岭南,乱世之苦,一直干扰着他的生活。他差不多经历了从辛亥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各个历史风潮。在这样的岁月里,他与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胡适诸种文人,走的完全是两条道路。他没有发起过一次社会文化运动,也没有参与诸种所谓变革的思潮。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之中,几乎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他的名字。除了在史学界有限的圈子之外,他的名字是寂寞的。
从1890年诞生起,到1969年含冤而死,他的生命恰恰与中国的文化悲剧那么深重地搅在一起。以至在死后,他给人间留下了那么多的遗憾。1902年,十三岁时便东渡日本求学;1905年,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后,分别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读书;1913年,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1918年,去美国哈佛大学;1921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这些经历使他在学术领域,具有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知识储备。他精通的语言之多,范围之广,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而他在史学、考古学、文学诸方面的贡献,也令后人企羡不已。作为一代史学大师,他给人留下的,是说不尽的文化话题。
但另一方面,他的个人情绪的极其私人化以及与现实拒不合作的态度,使他渐渐远离着民众。我读他晚年写下的《柳如是别传》等个人情绪较强的学术巨著,一方面惊叹于他博大的学识,严谨的精神,而另一方面,似乎觉得,其独立的品格背后,好像缺少些什么。那种“遗民”式的老态,那种与某些旧儒学之风颇为合一的美学情调,似乎在把人引向一种沉寂、衰朽。所以,我暗暗地想:当他告诫弟子,不要被“俗谛”所扰,要有独立的治学精神时,他是何等的伟大啊!可当看到他那么热衷于古戏,和儒雅的名士之风,又觉得与现实的人生远远地离开。我这种感觉,不是在强迫老人去做一些趋时的事业,对他而言,除了那样,还会有什么?我以为陈寅恪的复杂性在于,其渊博的学识与现代人的观念、生活,是背离的。或许,他评价王国维时那种为自由和独立意志而死的精神,更合适于他?在王国维的遗绪里,是不是也可以看见陈氏的影子?
生于乱世的陈寅恪,除了在学术的跋涉中耗费自己的生命外,不再会有什么企盼。读他的诗文,就能感受到他的脆弱,感伤,乃至深切的绝望。在这个意义上,他与王国维的心,是相通的。不要以为那些考据学的文字、文史探索的论著,都是些闲适化或过于职业化的东西。在那些严谨、流畅、博识的文字间,难道读不出他的无奈?陈寅恪的苦闷、求索之情,都外化于那些枯燥的文字间了。他似乎本身就属于远古,属于昨天,除了在历史的长影中上溯人类的脉息,他不再会做些什么。他永远不会像梁漱溟,冯友兰那样,把自己的热情,一度外化于这个世界。陈寅恪大概是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共和国中的一个“遗民”,沉默的时光是如此之长,离着文化的中心是如此的遥远。作为一种价值的选择,他是独一无二的失败的英雄。
2
1926年,陈寅恪应聘到清华大学任教。那时与他在一起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陈寅恪正值青年时代,但学术上已造诣不凡了。在北京的十年执教生涯里,正是中国政局动荡、社会危机四伏的时期。新与旧,中与外,诸种思潮交织于社会。作为一个学人,虽也关注时局的变化,但在根本点上,他还是沉浸于纯粹的学术思考里。他似乎与梁启超、王国维有着某种相通的东西,虽然在骨子里,他们并不一致。这种相通的东西是什么呢?请看他的自白:
纵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多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艳诗及悼亡诗》
陈寅恪到清华后,与王国维等人相处很好,王氏那时自称是“遗民”的,其国学根底与生活情趣,均不同于他人。陈寅恪与王氏在清华只相处一年,王氏便投昆明湖自杀了。这事对国人震动很大,世人一直将王国维的死,看成一个谜。但陈寅恪眼里的王国维先生,是别于他人的。他似乎从心灵深处,感受到自己与王氏相通的地方。同处于乱世,思想不合于俗谛,这是他们同样感到孤独的地方。另一方面,因为太钟情于古东方文化,而眼看这古老的遗韵几成绝响,也有悲伤绝望的心境吧?我一直觉得,王国维之死,对他一生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为一种文化而死也好,因绝望于生命之苦路也好,陈寅恪从王氏的生命路向中,好似感悟到了什么。他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
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狱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综览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之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
写此文时,陈寅恪已值中年,距王国维之死恰好七周年。在这里,多少可以看到独行者的悲哀。这种既决绝又无奈的精神意象,一直延续到他的死。独立于学术之中,不为外事所动,便成了他生命的信条。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他于学术研究上,创造了奇迹。他精通数国语言,对佛教文化、中国中古以来的历史,殊为熟悉,其考据、史论、诗论等学术研究,均做出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因体弱多病,加之性情的孤僻,他的思想,与现实完全处于冲撞的现状。这使他,差不多沿续了王国维的道路。虽然他并不像王氏皈依于哪一个政权,但在心灵上与现政权拒不合作的态度,显示了他的耿介、孤傲的个性。
他对辛亥革命后的历届政权,均无什么好感。1948年底,当大批知识分子逃离北平,后来转向台湾的时候,他并没有走,而是留在了大陆。因为他已看出国民党的统治,不会给中国带来多少光明。但对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共产党人,他同样采取了疏离的态度。他心目中所有的,乃评价王国维时用的那句话“独立自由之意志”。1953年,中共中央设立的历史委员会决定,希望陈寅恪由广州的岭南大学赴京,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那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已开始普及了全国,知识分子正面临全面改造的时期。在史学界担任领导的郭沫若、范文澜都是出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陈寅恪在中古史上的权威地位是勿庸置疑的,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知道自己不属于时代的合作者,他果断地拒绝了中央的任命。《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曾录有陈氏对科学院的答复记录,兹引如下: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的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这种答复,在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是绝无仅有的。试看贺麟、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不是都曾经妥协过么?但陈寅恪不会。看他的答复,便可见出他不凡的气节。不管这气节的内涵如何,它自身的意义如何,仅这种果敢、坚毅的态度而言,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缺少的,大概便是这一点吧。
陈寅恪死后赢得的广泛的赞誉和同情,与其说是学术上的令人高山仰止,不如说这种甘作“遗民”的骨气。撇开他气质中的迂腐点不谈,就他执著于人生信念,和学术独立精神而言,确令人赞佩不已。一个奇特的现象是,那些口口声声自誉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古文化学家们,后来的学术,并未超出陈寅恪,先生的广博、深远,一直是那些趋时的人所弗及。这个道理告诉后人,理论并不是最主要的,学术之路,有不同的走法,这正如基督教文化下的史学,不能代替伊斯兰教文化中的史学一样,陈寅恪自然会坚定地相信,他自己的路,别人无法代替。
3
五四以后的中国学人,分化成几种势力。读书不忘救国,治学乃为启蒙,陈独秀、鲁迅等人,走的是这条路。为学术而学术,以求知为目的,王国维、周作人后来便选择了此径。陈寅恪是远离政治的人,自然在心态上与王国维等有相近的一面。在他眼里,社会固然离不开政治、军事,但作为学人,以独立思考而求知益智,是本职份内的事情,并不该和世俗社会搅在一起。看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表达的意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生活、治学状态,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陈寅恪是以治史学而闻名于世的。但其实他在诗赋、文化学、艺术等领域,均有很高的建树。治史学者,大多为爱国者,而此点,陈氏尤甚。他在1930年所作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说:“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汙,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夫吾国学术之现状如此,全国大学皆有责焉,而清华为全国所最瞩望,以谓大可有为之大学,故其职责尤独重,因于其二十周年纪念时,直质不讳,拈出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与清华及全国学术有关诸君试一参究之。”这段话可看出他对史学独立精神的忠贞不二的态度,可以说,他从一开始,就把史学与时下的流行思潮,分离开来。历史学是超过一切意识形态的纯粹的静观,倘杂以后人俗谛,便常混淆了认知的视线。应当说,这个看法是相当深刻的。这样,他便把学人的价值,与世俗价值分离开来,历史精神与现实精神分离开来,自我的追求与世俗法则分离开来。历史常常是被观念所遮蔽的,史学家的目的,在于以求实的精神,广博的学识,清除通往已逝岁月道路上的杂尘。这个工作,显得异常艰巨、繁杂。陈寅恪一生所做的,便是这个艰巨、繁杂的工作。
胡守为先生在为《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所作的序言里,详尽地概括了陈氏史学成绩。他认为,陈氏批判地继承了乾嘉史学的方法,力求通过考证来说明历史事实及其内在联系,找出事物发展全部过程。同时,他还吸收了西方比较语言学方法,并在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上,殊多贡献。这个评价是正确的。我读陈氏的史学论文集,最惊异的便是此几点。如《元代汉人译名考》、《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知识之广博,求真之仔细,论证之严谨,确可称史学中的奇观。中古史,是汉文化与西域诸国文化融合、交流的历史。因为历史久远,有许多史实,已模糊不清了。尤其是佛教的传来,使中国人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渐次发生了变化。陈寅恪的伟大在于,他从某些角度,还原了历史的旧貌,使我们终于晓得诸种文化碰撞时的后果。例如,武则天为何信仰佛教,后人多语焉不详。陈氏以详尽的史实,纵横开阔的视野,论证了武则天利用宗教,为自己做女皇寻找证据。宗教的功利化,自中古以来,就一直未中断过,但世人并不知之。陈寅恪独具慧眼,一下看穿了其中的把戏,让我们是感叹不已的。读此文时,我想,作者后来拒绝议政,少与世人往来,也是对时下社会思潮的实用性之失望吧?明古的人,常常是会察今的。陈氏一生注重“气节”,恐怕正是治学悟道所致。在他的看似枯燥的文字里,还是可以看出一种人生的激情的。
陈氏有一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我以为很好。考据、论证之精到且不说,仅作者从中所悟出的人生观感,与他的人生态度,何尝不是一致的?魏晋之际,士大夫阶层处于困境,其进退之苦难为世人所道,于是纸上玄言,口中讥语,均不绝于缕。陶渊明后来隐居山林,当然与此有关。陈寅恪发现,陶渊明思想的形成,是有其重要背景的。故他叹道:“古今论陶渊明之文学者甚众,论其思想者较少。至于魏晋两朝清谈内容之演变与陶氏族类及家传之信仰两点以立论者,则浅陋寡闻如寅恪,尚未之见。”何以从“家传之信仰”入手,去考察陶氏精神的形成?这或许与陈寅恪“遗民心态”有关亦未可知。我从他的感触中,好像感受到了一丝与古人共鸣的地方。此文结尾时对陶氏思想的概括,我总觉得,也看到了陈寅恪自己的影子,虽然在骨子里,他和陶渊明区别很大。那结尾说:
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重点号系引者所加),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推其造诣所极,殆与千年后之道教采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者,颇有近似之处。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
看重陶渊明思想上的特质,这是陈氏高明的地方。创一新说,开辟一个与世俗不伍的境界,那才是陈寅恪最感兴趣的东西。我读此篇文章,似乎悟出作者思想上的一个源头。史学家的道德激情,常常就是隐含在这类总结性的文字里。这篇从考证为主的文章,实可以当成诗和哲理来读。
4
陈寅恪注重“气节”,“道德操节”,其实是恪守古汉文明的心态使然。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陈氏的这一感叹,不像林纾那代人那般老朽,他确是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生出的结论。早在1919年,陈寅恪与吴宓在哈佛大学读书之余作的交谈,也涉及了这一问题。吴宓的日记记载了他们这样一段话:“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载《吴宓与陈寅恪》)谈话涉及的内容,与章太炎、梁启超、鲁迅那代人当年的话题,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看到了解决中国人灵魂的重要性,从精神的角度上来重振国民性,应当说,其思路是很有意义的。但他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者们不同,不是通过否定儒学而重塑国民精神,而是在儒学的基础上,小心地调整,或者说是恢复到旧文明的基础上。他说自己“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讥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这是理解他思想的一个入口,把握了这一点,就可见出他的基本面貌。陈氏看重曾国藩、张之洞,说明其意识是相当本土化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云“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可以说,这有些类似新儒学的精神了。但新儒学是要积极用世的,而陈氏则以文化为情趣,并不注重布道、议政之类。这就有些将自己封闭起来。1926年6月29日的吴宓日记载:“夕,陈寅恪来。谈大局改变后一身之计划。寅恪赞成宓之前议,力劝宓勿任学校教员。隐居读书,以作文售稿自活,肆力于学,谢绝人事,专心致志若干年。不以应酬及杂务扰其心,乱其思,费其时,则进益必多而功效殊大云。又与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在这个角度看,陈氏的独立的秉性,是牢固的,他的一切,都在自己的学业里。陈氏既不像胡适那样热衷于政治,另一方面,也不像鲁迅那样抨击时弊。陈寅恪几乎把自己的一切,都融于知识世界里,在古中国文化中的游历,那才是他的梦想。读陈氏的诗文,尽管常可以看出他悲观的一面,沉郁的一面,但也常常可以感到他在寻找着什么、寄托着什么。季羡林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讲演中指出:
陈先生在给王观堂所撰的挽词前的短序中讲了这么一个想法:中华文化是三纲六纪。据我的体会,里面就包括了爱国主义精神。如“君为臣纲”,说君臣这一纲,陈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意思就是,人君的贤与否,无关重要。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国家。陈先生又讲,三纲六纪是抽象理想。文化是抽象的,抽象的东西必然有所寄托,陈先生原文作“依托”。一个是依托者,一个是被依托者。作为文化的三纲六纪是抽象的,抽象的本身表现不出来,它必然要依托它物,依托什么呢?陈先生讲的是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总起来就是国家。文化必然依托国家,然后才能表现,依托者没有被依托者不能表现,因此,文化与国家成了同义词。[1]
陈寅恪的寄托,是三纲六纪的社会,这对生活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问题是,当陈氏全力去救古老的文明时,那古老的文明,能否救活他?当惊叹他的超凡的才气和渊博的知识时,我不禁也为他的迂拙而甚感可惜。历史是进化的,古文明许多东西,是窒息人的生命意志的。看一看战乱频仍的中国史,便也证明了旧文明自身的脆弱。所以,说陈寅恪是爱国主义,不如说是趋古主义。当他以精湛的学识去解释历史原态时,他是何等的伟岸、洒脱啊,可一旦把目光投向现实,总觉得在与实实在在的人生分开,与鲜活的生命意志离开。实际上,和他终生保持友谊的诤友吴宓,在对待生活本身,就不同于他。1928年11月,吴宓已决定与妻子离婚,寻找别样的生活,他把此事告诉陈氏,陈氏大为反对,吴宓日记载:陈氏云“无论如何错误失悔,对正式之妻不能脱离背弃或丝毫蔑视。应严持道德,悬崖勒马,勿存他想。又谓宓此时已堕入情网,遂致盲目,感情所激,理性全无。他日回思,所见必异。”陈氏在婚恋观上的保守,也正是其文化观上的趋古所使然吧?我们无论从价值观,社会观,还是审美观上看,陈氏都不能说是属于二十世纪新文化中人。我在他一生的挣扎、苦痛的命运中,好像看到了新旧文化分离,旧的文明猛然断裂之时,那些为昔日的文明而守节者的大悲苦。陈寅恪是悲壮的,明明知道这是一个绝路,但还要执意走下去,这比那些茫然随波逐流的人比,多了一份令人反省的文化课题。或许,二十世纪中国最令人困惑的文化迷津,便是与这类牺牲者的挣扎的足迹,交织在一起的。
5
我常常想,晚年,当他双目失明之后,为什么选择了柳如是、钱谦益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他的学识,为何不去勾勒一个系统的史学理论,或写一部完成的断代史?他的惊人的学识未能辗转到东方文明的核心领域,而偏偏选择了一对明代“遗民”?读《柳如是别传》,不能不震惊于作者那样广博的学识,扎实的考据功底。但按严格的版本目录学观点看,也不无可挑剔之处。黄裳在《钱牧斋》一文中,就指出过陈氏在版本引用上的缺憾。细想起来,陈氏倒未必想以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对他而言,柳如是这类聪颖、正义、美丽的女子身上,正寄托了自己的某种情感。这是一切细心的读者,都可以感受到的。或许正是共有的“遗民心态”,构成了他晚年学术的一个奇观,史学多诗学,以史写诗,以史鉴己,这大概便是他的精神原态吧?
一般史学家对柳如是这类人物,不会有那么浓厚的兴趣。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柳如是、钱谦益,实在算不上令人仰慕的旷世英杰。但陈寅恪似乎有另一种看法,恰恰在这种满蕴中国古文化丰姿的生命形象里,他找到了一种中国士大夫阶层,或说中国文化人心理的原型。儒家正统的东西,在危机中不怕死灭而力主抗争的精神,这才是陈氏以为弥为珍贵的精神源泉。《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说:
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疑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从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读这一段话,对他的世界,或许可以理解三分。有人说《柳如是别传》是“心史”与“伤心史”,这是很对的。他在柳如是、钱谦益等人的世界里,大概也看到自己的历史。所以他叹道:“噫!吾人今日追思崔(莺莺)、张(生)、柳(柳如是)、陈(陈子龙)悲欢离合之往事,益信社会制度与个人情感之冲突,诚如卢梭王国维之所言者矣。”陈寅恪在明末清初的历史里,看到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人深切的无奈,而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又何尝不是如此?对他来说,社会的转型,朝代的更迭,都算不上进化,而恰恰是对固有文明的偏离。清代的历史如斯,民国如斯,新中国亦如斯。对巨大的历史之力,能说什么?又能怎么说?当他困居岭南,双目失明之际,饱经忧患的身躯,已无法抵御外来震荡的袭扰。他渐渐放弃了历史学核心的劳作,而选择了颇有精神意绪,又充满艺术悲剧的研究对象。这里,便有他的哲学与精神的归宿。《柳如是别传》无论在诠释学、考据学,还是在以诗证史、艺术鉴赏方面,都堪称前无古人的巨著。但对我来说,却更加关注他治学时的所有的心态,那种呼应,那种移情,那种孤寂的生命形态。我从不相信有为史学而史学的人,倘有的话,大约也未必出现陈寅恪式的境界。在陈氏的劳作中,难道读不出一种生命的欲求,和不与世俗相伴的超然?我以为,在这个孤苦的智者那里,看到了中国史学中最迷人的东西,它至少告诉后人,昨日如斯,今日如斯,明日或者依然如斯。记得鲁迅、周作人都说过这样的话。但只有在伴着古人重温那已逝的长梦时,才可以最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陈寅恪生命中最诱人的一面,大约就在这里。
其实陈寅恪是一位感情很丰富的文人。撇开他的史学著作不谈,仅他的诗文而言,都是不可多得的。阅读他的遗稿,实觉得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他太敏感,太感伤,这一点,与王国维颇为相近。王国维以词胜,陈寅恪因诗名。二者审美情调、意象取舍的方式,均很相同,恍若出自一人之手。造成两人诗词韵致相当的原因,一是“遗民”情结,另一方面,便是悲观哲学。陈氏中年目盲,晚年骨折,这都是个人身世的不幸。就大的方面而言,历经战乱,久在漂流,生活动荡,也是一个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旧文化日趋衰亡,所钟情的精神之山屡遭劫难所致吧。1927年,北伐前夕,陈寅恪独自游玉泉静明园,看到清代遗迹物是人非,不禁咏道:
犹记红墙出柳根,十年重到亦无存。
园林故国春芜早,景物空山夕照昏。
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
人间不曾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
很有点遗老气,也有些绝望的叹息。但那感慨确是真挚的。当社会遭变革之际,要么随波,要么往旧,中间的路,是难寻的,陈氏自然选择了后者。他为文化而哭,为古有之儒士之气节日损而哭。和左翼作家对比一下,陈氏的优劣,短长,便一清二楚了。
陈寅恪拒绝新文化,拒绝流行色,恐怕还与他的悲观的人生哲学,即佛家式的苦难意识有关。他在诗里,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这种情感。1931年,曾有“空文自古无长策,大患吾今有此身”句;1933年,曾叹“隔世相怜弥怅惘,平生自恨多缠绵”;1939年曾云“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的诗这类意象,几成自然之念,悲慨感伤之情,满布其间。生的现实,对他已缺少意义,他不止一次地流露出绝望的感情。1953年他写下《癸已秋日病中作》,诗中咏道:
不生不死度残年,竟日沈沈寤寐间。
夜半虫声忽惊觉,魂归何处瘴江边。
那时他的心境是极苦的,我在他的吟咏里,好似看到了他消瘦、哀怨的苦态。倘若他像一般文人那样投入新社会建设中,至少情感上不会那么消沉。但他偏偏拒绝了外面的世界,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承受着巨大的折磨。自明清、民国乃至现在,历代“遗民”所受之苦,无陈氏更深者。这是王夫之、王国维那几代人,均无法相比的。
这样的时候,他便只有沉浸到古代,沉浸到明末“遗民”的世界里。除此,还会有什么选择?一个不相信古文化可以更新再造的人,一个对时代失去兴趣的人,那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我不相信,陈氏的这一选择是最好的归宿!世上的路有千万条,自沉苦海,总不能说是对得起生命价值吧?但在大变革,大动荡,大劫难的岁月里,陈寅恪自身的形象所折射的文化寓义,是深广的。我们毁灭了一个旧世界,但问题是能否建立一个更新的、合理的世界?能否把旧的文明在新的社会形态里,创造性地转化成新的文明?只要想起陈寅恪,这一类的思考,便会不断地继续着。
1997年3月于北京
注释:
[1]引自《〈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标签:陈寅恪论文; 王国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清谈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