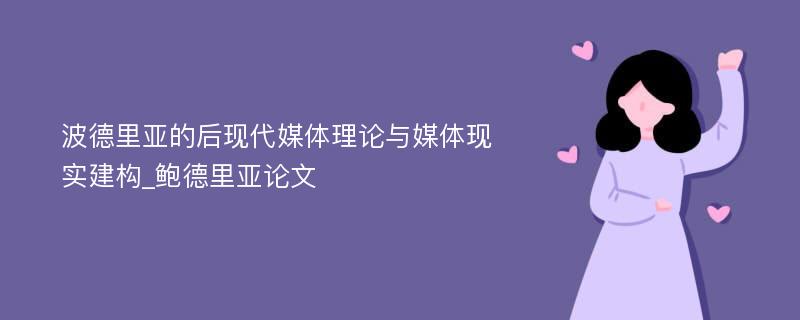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理论与媒介现实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里论文,后现代论文,媒介论文,现实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思潮,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传入中国,至今在思想、学术、文化领域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传媒领域也开始关注后现代理论,但相对于哲学、文艺学等领域,中国传播和传媒研究学科中的后现代理论研究尚未深入。本文就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对传播学影响最大的鲍德里亚的观点作一初步分析,以期引发更深入广泛的探讨。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理论对西方跨国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西方媒体霸权与消费文化提出了深刻批判,但我们必须质疑其激进理论所蕴涵的虚无主义倾向,以有助于进一步思考中国传媒改革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神圣的三位一体与媒介现实的构建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理论的三个关键概念是类像、内爆与超现实,是电视媒体构建模拟现实的主要手段。
(一)内爆——媒介现实表现的形式
内爆概念是鲍德里亚后现代社会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它原本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最初由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引进传播学领域,鲍德里亚对其含义做了进一步的扩展,把它应用于对后现代社会状况的描述。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外爆”,即商品生产、资本、国界、科技的不断向外扩张以及社会领域、话语和价值的不断分化,那么鲍德里亚的内爆理论所描绘的则是一种导致各种界限崩溃的社会熵增加过程。鲍德里亚将内爆界定为“相互收缩,一种奇异(巨大)的互相套叠、传统的两极坍塌进另一极”;(注:[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第139、142、153页,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这种爆炸意味着“每一种意义差异系统内部界限的消失瓦解,它原有的两极合成一极,造成意义差异的短路,并抹消术语、对立概念以及媒体和真实之间的一应区别”。(注: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词典》第47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政治、资本、娱乐、广告等混为一体,成了一个无差别性的仿真流变。
(二)类像与仿真——媒介现实塑造的手段
类像原意指没有现实根据的、非真实的影像或幻觉;而鲍德里亚将类像描述成用“虚构的”或模仿的事物代替“真实”的过程,也就是将电子或数字化的影像、符号或景观替代“真实生活”和在真实世界中的客体的过程,(注: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12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这是一种可以以假乱真的东西。在仿真社会里,模式和信码构成了经验并且消蚀了模式和实在之间的界限,即类像模型形成幻象,作为真实世界的替代它无所不在以至于因此无法分辨真实和幻象。与此相伴随,人们从前对“真实”的那种体验以及真实的基础也随之消逝。“水门事件”被描述为媒体“对一件丑闻的一个模拟”,而海湾战争则被视为是从未发生的美国和前苏联的核战争的一种模拟。
大众媒介特别是当今飞速发展的电子媒介凭借其先进的技术手段构建了一个几乎以假乱真或真伪难变的影像符号世界,它们的表现有如下特征:
1.传播模式的单向性
鲍德里亚早期的媒介观认为,大众媒介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统治讯息生产的各种权力关系,而在于媒介的“单向特性”。这是由媒介技术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在大众传媒成为高利润产业的同时也限定了它的准入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高技术设备的购买,优秀人才聘请,高质量的电视节目的制作都需耗费巨资。普通民众缺乏这种媒体接近权,因而不能参与电视媒体节目的制作与播放,所以无形之中媒体与大众之间便形成了一种简单的传播与接受、单向的播放与单向被动的接受的关系。实质上这是一种不平等、不平衡的信息流通关系,而并非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理论中所指出的双方基于一种互惠意义上的交换与交流。因此,鲍德里亚认为传播系统的技术能力始终是单方发言的,媒介不能被民主化,它也无须应答与回应受众。(注: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249、245、260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
2.能指与所指的断裂
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需求从生产转向了消费以及60年代电视的普及,对电视媒体特别是电视广告的分析成为鲍德里亚媒体技术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将语言分为两部分:能指与所指。能指表现为声音或形象,是符号的物质形式,所指是指由这种声音或形象在人心理所引发的概念,是符号的内容,两者的关系是完全任意的、非自然的、习惯的和约定俗成的。而在传播技术手段日益更新的当代,鲍德里亚认为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已分离,形式与内容游离,造成了“浮游的能指”与意义的丧失这一现象。这是一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言,即表征和意义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和理性的逻辑推理关系,而这正是鲍德里亚所分析的后现代社会电视媒体的广告特征。
3.电视融入生活,生活融入电视
鲍德里亚认为,既然在当前的模拟世界中,所有的事物都正在内爆,所有的事物都是模拟,那么所有的事物就都能融解成一个单一的巨大的模拟团块。譬如,以当前电视里的谈话节目为例,电视正融入生活,生活也正融入电视。(注:[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第139、142、153页,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在电视节目中所发生的事情显然是一种模拟,但生活自身也已经常常成为一种对发生在电视节目中的那些情节或画面的模拟。例如,电视剧中医生、律师和侦探的扮演者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会收到咨询、请求建议和得到帮助的来信;而在英国诺森伯兰郡莫尔佩斯镇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张贴着马龙·白兰度扮演的“教父”的肖像,以此作为这家意大利餐馆的正宗标志。(注: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25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三)超真实——媒介现实呈现的幻影
超真实是指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区分已变得日益模糊不清。按照鲍德里亚的观点,超真实是完全的模拟,它不仅仅是被生产出来的,而且“始终是一种已经被再生产出来的东西”,即此时真实不再单纯是一些现成之物(如风景或海洋),而是人为地生产(或再生产)出来的“真实”(例如模拟环境),它不是变得不真实或荒诞了,而是比真实更真实,成了一种在“幻境式的(自我)相似”中被精心雕琢过的真实。(注: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第143、15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超真实或超现实与真实或现实本身是什么样的关系,大众媒体在其中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对鲍德里亚而言,既然超真实是一种以模型取代真实的状态,那么模型就成了真实的决定因素:电视剧中的理想爱情成了人们现实生活的择偶选择标准,商品的电视广告宣传成为人们超市与商场购物的理想首选目标,时尚杂志或其他生活类杂志中所宣扬鼓吹的家居成为人们理想的居家模式;此外,伴随着超真实的来临,类像也开始构造现实本身,而且模拟出来的东西成了真实本身的判定准则:《现代启示录》就已经成为判断有关美国越南战争描写的真实标准,如果有人问“像《现代启示录》那样的吗?”,实际上就等于在问“是真的吗?”。(注: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25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相对于西方传统的现实、真实的观念,超真实是后现代主义的激进理论,试图釜底抽薪地把现实、真实这个传媒和文化所再现的对象转换成为虚构的类像。后现代主义解构传统现实观念的目的,本来是想颠覆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而鲍德里亚的理论更为极端,他把目标从思想领域转移到传媒这个与现实社会极为密切的公共领域,使其理论带上了更强烈的现实感。然而讽刺的是他的这种现实意义很强的理论,目的却在于否定现实的真实性。新闻传媒领域里的现实与真实性问题,具有强烈的社会与政治实践性,跟哲学的抽象理论思辨、文艺学领域里的虚构想象问题性质不同,我们在理解鲍德里亚理论时,应该对此抱有较清醒的认识。
媒介现实构建所导致的后果
(一)信息的迷狂与窥淫癖者的产生
鲍德里亚将现实世界视为一个“迷狂”的世界。这是一种失去控制直至丧失所有感觉的持续的自旋过程,这个失控的系统最终会显露出它的空泛和无意义,“在其纯粹和空泛的形式上散发出光彩”。时尚被视为“围绕着本身自旋的纯粹的和空泛的审美形式”,广告被描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纯粹和空泛的品牌形式遁入湮灭的自旋”,最重要的是,大众被看成是“对社会的迷狂,社会的迷狂形式”。(注:[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第139、142、153页,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大众对信息有着强烈的迷恋,大众俨然已成为当代社会堂而皇之的“窥淫癖者”,迷恋着我们这个社会自身,而当代媒体则为大众“信息窥淫欲”的满足提供了技术手段。
鲍德里亚将传媒看作是淫秽、透明和迷狂的工具,通讯技术的发展已使一切都变得公然、清晰和猥亵;传统的那种隐秘的、被压抑、被禁止和模糊意义上的淫秽变成了完全可视的淫秽;猥亵的出现也成了很正常的事情。(注: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249、245、260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我们各种最隐秘的事情通过媒介技术像举行仪式一般被公之于众,不再存在涉及禁忌的主题:每一件事情都被曝光,而且每一件事情都被议论,不论这些事情是多么繁琐。(注:[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第139、142、153页,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在以透明、曝光和猥亵为特征的后现代传媒社会,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拍成电影电视、在广播中播出、制成录像磁带等等;民意测验、脱口秀以及更一般性的媒体都在迫使我们说出我们的秘密,即使当你已无话可说之时亦是如此。(注:[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第139、142、153页,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这显然已成为后现代社会一道奇特的媒介景观。
(二)主体性的丧失
大众媒介出现后,人同时具有“生产者”与“受众”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在实践场域中被塑造为有行动能力的理性(实践理性)主体,一方面又在实践场域之外被塑造为心理退化、无需负责的“大众”。这一双重身份的冲突,造成了当代社会道德丧失、功能化、冷漠化,这已经不仅仅是工业社会早期“工人”劳动的异化,或霍克海默等人指出的理性丧失的问题了。鲍德里亚同时审视了当代社会人在这两种身份下所处的“不自由”与“过度自由”的悖反情境,在试图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他遭遇了启蒙理性在“类”的立场上与实践理性无法统合、但也无法放弃任何一方的困扰。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在实践场域(人与人的交往媒介)中,个体的自由意志与实践法则之悖反。当鲍德里亚试图批判造成人的悖反式存在根源——实践场域本身时,他发现,构建出整个悖反场域的“类主体中心主义”,既不是外在于“我”的“他者”,也不是“我”自身,因此,既不能现实地将之推翻,也不能靠个体的反思消除。
晚期的鲍德里亚一方面对“控制体系”(实际上就是已经扩展到全球化的资本体系)进行了反讽式的批判,另一方面又认为,在现实层面上,对于不可逆转的资本体系,只能持一种无为的态度。在晚期鲍德里亚看来,我们对于世界进程能够起推动作用的乐观信念,其实是幻想,就像当电梯门自动关上时,我们以为这是人按了关门的按钮的缘故。与早期对消费社会的激进批判相比,后期鲍德里亚倾向于相信,历史发展是“无主体的过程”,人类所能做的,就是静观其变和顺势而为,以及在思想上发出反讽的嘲笑。后期鲍德里亚对理性不信任,倾向虚无主义。启蒙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后期鲍德里亚的著作中是相互缠绕,纠葛不清的,这使他陷入理性的悖反之中,不断自我指涉和自我否认。
(三)对符号价值的膜拜
鲍德里亚将符号学的观点引入消费社会的研究当中,发展了一种商品—符号理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二重价值”观点进行了补充,在马克思所区分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外,引入了商品的另外一层价值属性——符号价值。这是当代社会中能给消费者带来身份感、地位感与满足感的一种特性。鲍德里亚认为,商品在得到消费之前首先必须要成为符号,这是一种索绪尔意义上的包括能指与所指的符号。商品符号的意义可以任意的由它在自我参考系统中的位置来确定,成为一种自我指涉体系。商品意义的建立是借助于符号组织为代码而完成的,这不是普通的代码,而是按一定的次序有序排列的符码;它起到了一定的“区分”作用,通过区分符码消费者的风格、个性、品味从而标识他们在社会中的阶层、地位和声望;因而我们在消费物品时也就是在消费符号,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区分我们和他人的社会差异从而界定自我。
19世纪70年代以后,鲍德里亚把传媒解释为“关键性的仿真机器”,它再生产影像、符号、代码。(注: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第16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其中,电视是最主要的仿真手段,因为它可以促使生成的“拟像”与“符码”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迅速传播和在消费者群体中的广泛普及。电视在商品符号的消费中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电视广告的优越性和有效性是其他媒体广告所羡慕的。电视利用技术仿真形成超真实的“类像”,以隐喻和神话作为修辞手段,成功地创造出一种乌托邦的广告话语;不断刺激和制造人们的虚假需求,使人们违背“消费伦理”,忽视物品的纯粹的功用价值而产生对符号价值消费的膜拜,享受这种盲目的购买所带来的空洞的快乐感与自由感——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认为的消费社会的内在逻辑。
传媒与受众的态度
在信息臃肿的社会,人们获得的有用信息远远少于垃圾信息。符号信息的大量生产超过了人们的接受、理解、阐释分析与判断能力。大众每天被来自媒体的信息流所淹没,“被活埋在信息地底下”,这些非互惠意义上的繁冗信息让大众疲惫不堪、感到厌倦、产生不满。
鲍德里亚认为受众对整天喋喋不休的媒介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对抗策略:冷漠与拒绝。要么对大众媒介置之不理,要么拒绝接受它们的意义以抵抗不平等的单向信息传递。鲍德里亚晚期企图发展一种不同的策略。他对民意测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认为民意测验“是一种混合体、是两种异质体系的糅合,这两种体系的数据不可能相互转换。一个统计的、基于信息的、仿拟性的操作体系被投映到一个表征、意志与舆论的体系上。(注: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第2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这样矛盾就产生了:基于技术手段的民意数据预测并不是真正的民意,不能代表公众的观点;因为它只是传统的表征、意志与舆论的体系的仿真与拟像。这种真实性与仿真性导致了意义的混乱;而这种差异的出现是由于大众新的反抗形式所造成的。在鲍德里亚的眼中,大众不再是那种束手无策,消极反抗的受众了;他们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报复对抗行动,那就是沉默与游戏。
大众在投票选举过程中不是积极的参与,而是表现出沉默的姿态。鲍德里亚认为,大众的沉默并不是他们异化的标志,而是他们权力的标志。因此,沉默是一种力量,一种答复,一种宿命性的策略;它是终结庞大的政治和信息操纵制度的一条途径,(注: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249、245、260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抵消着全部的政治景观和话语。大众的力量在于他们对意义和参与的拒绝:在选举投票和民意测验中,大众采取不合作、观望、弃权与沉默来“游戏”、“调侃”和“报复”媒体,以此来对抗媒体对他们的“政治敲诈”,媒体虽然有着先进的技术手段与合理的计算公式,但大众的“恶作剧”行为与“捣乱”却让媒体机关算尽,到头来却无从获得准确的数据,达不到预期的期望值。(注:孔明安:《从媒体的象征交换到“游戏”的大众》,《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2期。)
结语
鲍德里亚从后现代理论出发,提出了由“类像”、“符码”、“内爆”与“超真实”概念所构成的后现代传媒“仿真”理论。他的理论夸大当代传媒技术对社会和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的影响。他认为媒介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二元决定论,工业社会的所有界限、范畴和价值在后工业社会被抹煞——意义内爆于媒体,媒体与社会内爆于大众之中;大众对信息的迷狂以及媒体作为淫秽、透明的工具特性使社会的“道德感”与“羞耻感”丧失;而不具备表征意义的“浮游能指”则削弱了意识形态的认同性与社会次序的稳定性;四处泛滥的信息、类像、符码已全面主宰社会,导致了主客体逻辑的颠倒,大众丧失了主体性,沦为符号的“奴隶”,进而对于单向特性的媒体和符号的“反抗”也只能基于一种“宿命的消极策略”,那就是“沉默、拒绝与调侃”。基于鲍德里亚对当代大众媒体的技术特性所持有的过于“消极”、“悲观”、“命定”与“虚无”的态度,有学者将他的媒体思想定义为一种“传媒恐惧论”。(注:季桂保:《让-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文化观》,《电影艺术》2000年第4期。)但鲍德里亚提出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中期著作中谈论的有关类像、内爆以及超真实的论述,包含着对当代媒体与消费文化的深刻批判。
然而在解读鲍德里亚及其他后现代传媒理论时,我们应当质疑其激进背后的虚无主义倾向。在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与强权政治构成新的“帝国”,它们利用政治、经济、文化与传媒资源控制世界。全球化过程中,传媒资源的影响巨大,尤其在传媒多元化、民主化、服务公众等重大领域,传媒发展的方向和策略有着强烈的现实与实践意义。应当看到,以鲍德里亚为典型的后现代传媒理论立足点在批判、颠覆和结构,破有余而立不足,缺少建设性见解。其理论往往混淆不同领域的问题,把抽象哲学思辨和文艺学中的现实、真实、虚构以及主体性问题,跟传媒涉及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现实领域,统统归结于什么“仿真”、“内爆”、“超真实”。鲍德里亚提出的所谓受众策略无非是消极无为、宿命地接受新的传媒霸权的支配。对于社会正在发生重大转型,传媒也在经历最深刻的改革的中国来说,后现代传媒理论有哪些积极意义,则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的。
注释:
①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第143、15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