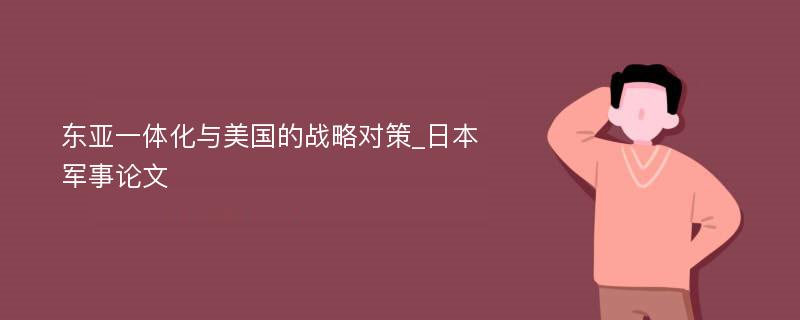
东亚一体化与美国的战略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美国论文,化与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9550(2009)06-0047-09
冷战结束后,东亚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引发了全球越来越多的关注。早在1990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就提出了建立“东亚经济圈”的构想。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东亚各国深切地认识到加强合作互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东亚各国开始积极寻求建立新的区域性经济/金融合作机制。① 其中包括日本提出的创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倡议、2000年5月《清迈倡议》的签署以及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提出的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等,均体现了东亚各国试图通过区域合作对抗经济/金融风险,提升共同福祉的政策意图。
近年来,东亚一体化进程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就,其中尤以经济一体化成果最为显著。例如,1997年12月,首届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标志着以“10+3”为主体的东亚合作机制的产生。2003年,东盟领导人在东盟峰会上倡议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在金融合作领域,2003年6月,东亚及太平洋央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发行了首期十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2007年5月初,“10+3”财长会议原则上同意建立一个共同的外汇储备库,以防止重蹈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即便是在一向极为敏感且鲜有建树的安全合作领域,围绕着朝核问题而展开的六方会谈也被很多人视为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雏形和曙光。
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以及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迅速提升,为东亚一体化的不断深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尽管东亚一体化在过去的20年间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较之于北美和欧盟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东亚一体化的发展程度依然严重滞后。究其原因,固然有东亚各国自身的因素,② 但是美国对东亚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疑虑及其在冷战后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战略布局和政策应对,也对东亚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造成了重要的制约。那么美国对东亚一体化的战略认知是什么?其基本的利益诉求是什么?又出台了哪些具体的政策加以应对?本文将对上述这些问题予以解答。
一 霸权护持:“三位一体”的美国东亚战略
针对美国如何应对东亚一体化这一问题,学者有不同的诠释,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观点主要关注美国在双边层次上的安全、经济政策应对,例如,美国与该地区盟国安全关系的巩固和扩展以及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推动等。③ 第二种观点则主要关注美国对亚太多边机制的政策演化,例如,美国对泛太平洋一体化组织的态度和政策变化,美国与亚太经合组织关系的演变过程等。④ 然而,通过对美国近年来相关政策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应对东亚一体化的战略经历了全面而深刻的调整,其中不仅仅包括安全战略的整合和经济关系的巩固,还包含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强化,从而构筑起了一个系统的战略应对框架。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独霸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如何运用美国的超强国力以长期保持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以及制定对外战略的基点。⑤ 例如,在1994年初,克林顿政府在其发布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便声称:“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⑥ 美国要努力确保“21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⑦ 小布什总统在其2006年国情咨文中也明确指出:美国必须“通过领导世界来建设我们的繁荣”。⑧ 2008年11月4日,赢得总统选战的奥巴马发表胜选演说,宣称“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新曙光即将来临”,并一再强调要重振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⑨
作为当今霸权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和最大的受益者,如何维系自身霸权领导地位及其所建立的霸权体系,是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念兹在兹的“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目标”。⑩ 为了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美国不仅要致力于“利用美国的优势地位建立和巩固美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单极霸权世界”,同时也要坚决“抑制其他国家试图谋求霸权的挑战倾向”。(11) 例如,美国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便明确指出,美国绝不容许欧洲、东北亚、中东和西南亚等“关键地区落入与美为敌的国家控制之中”,从而意味着美国会竭尽全力防止出现一个足以对美国区域乃至全球霸权发起挑战的新兴地缘政治强国,以避免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出现不利于美国的根本性改变。
就东亚地区而言,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崛起以及东亚诸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东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尽管自冷战爆发以来直至今天,美国始终是主导该地区安全、政治、经济格局的“领导国家”,其地位和影响力亦非东亚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可以比拟。然而,面对东亚各国加强区域内自主合作意愿的持续增强以及中日两国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尤其是建设“东亚共同体”这一目标的提出,则引发了美国对东亚一体化发展方向及其结果的疑虑。面对方兴未艾的东亚一体化进程,美国所关切的是这一进程将对其在东亚的利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是否会有一个地区大国依托东亚一体化进程强势崛起,挑战美国在东亚的领导权?其次,东亚一体化是否会改变和破坏既有的、由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格局?最后,美国是否会被排斥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之外,或是被边缘化,进而损害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利益?(12) 而其中的关键则在于,美国绝不希望看到有任何一个地区强国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进而削弱甚至颠覆美国在东亚的区域霸权地位。
东亚一体化至今缺乏一个公认的“盟主”或者“领导者”,可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制约一体化得到迅速推进的重要因素。放眼整个东亚地区,有资格挑战甚至取代美国“东亚霸主”地位的“领袖国家”无外乎中、日两国。但是从美国历届政府的政策行为来看,显然美国对于日本的疑虑并不十分严重。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点:首先,由于美日同盟的存在,使得美国对于日本的国家决策拥有无可争议的影响力,美国有足够的信心确保日本不会过度偏离美国的政策轨道。其次,尽管日本是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体,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以来,日本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实力也随之大打折扣。最后,由于日本与东亚诸国在历史问题上的纠葛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东亚各国对于日本的战略意图存有严重的戒心,进而严重束缚了日本影响力的扩张。
而相较于日本,美国对中国的疑惧和防范意识则不可同日而语。早在冷战结束之初,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便不时在美国朝野各界引发喧嚣。在美国部分高层决策人士看来,在后冷战时代,能够有条件和潜力在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屈指可数,而中国不仅拥有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资源禀赋,更“顽固”奉行与美国迥异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美国对中国必须严加防范。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崛起,军事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从而导致美国对中国的疑惧日益加深。例如,美国1997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便曾明确指出:“在2015年以后,将有可能出现一个地区性大国或全球匹敌的竞争对手。……俄罗斯和中国有潜力成为这样的竞争对手。”(13) 而于2002年出台的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正在寻求可以威胁到亚太邻国的军事力量”,并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竞争对手”。(14) 甚至连曾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的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也毫不讳言:中国崛起是美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美国为此必须做好两手准备,甚至进行必要的遏制。(15)
正是基于上述战略认知,面对蓬勃发展的东亚一体化进程,如何防止任一国家(尤其是中国)借助东亚一体化的发展迅速崛起,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和既得利益,遂成为美国制定和推行其东亚政治、安全、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为此,美国在三个方面展开了相应的战略部署和政策调整。首先是在安全领域,美国在维持和强化原有双边军事同盟的同时,通过与部分东亚国家拓展安全合作,进一步巩固以美国为核心的“轴辐安全结构”。其次是在经济领域,美国开始加强双边贸易协商,积极谋求与东亚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以防止美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被边缘化。最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大力鼓吹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外交”,试图构建符合美国政治规范和价值理念的“价值观同盟”。由此构成了美国以“霸权护持”为主旨的“三位一体”的东亚战略框架。
二 强化“轴辐结构”: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
在冷战期间,尽管东亚地区始终是美苏争霸的前沿阵地之一,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东亚始终没有形成类似于北约和华约组织的集体安全机制,取而代之的则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进而形成了以所谓的“轴辐结构(hub and spokes)”为特征的亚太安全格局。冷战结束后,美国依靠超群的军事实力,在东亚地区庞大的前沿军事存在及其所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在亚太安全问题上始终握有特殊的话语权,并对东亚地缘安全格局的演变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长期以来,美国将其在东亚地区的双边军事同盟视为地区安全政策的支柱,也是美国维护其战略利益,影响地区安全事务的重要途径。为此,美国始终对维护同盟体系给予高度关注。例如在2005年3月美国防部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中,便将“增强联盟和伙伴关系”列为新世纪美国四大战略目标之一。(16) 2006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明确指出:拥有众多盟国是美国最大的优势和资源之一。而为了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设想,就必须保持与欧洲以及亚太地区长期盟友的密切合作关系。(17) 冷战结束后,为了巩固美国在亚太地缘安全格局中的霸主地位,美国确立了“以前沿存在为基石,以双边同盟为支柱,以多边安全机制为补充”的亚太安全战略,(18) 以进一步强化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轴辐结构”,同时牵制东亚各国建立地区合作安全机制的努力。
(一)加强和巩固原有双边军事同盟
在冷战期间,为了在亚太地区建立遏制中苏两国的“反共防波堤”,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菲律宾等国缔结了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在上述诸多同盟关系中,尤以美日同盟最为重要,被美国视为“支柱中的支柱”,“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19)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指导方针、功能定位和战略重心进行了重大调整,以使该同盟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新形势下美国的战略需求。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加强美日同盟既可以确保美国在东亚的前沿军事存在,而且可以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进而确保美国在东亚的安全霸权。其次,利用同盟体制,美国可以限制和防止日本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发展成为“自行其是”的军事强国。最后,借助美日同盟,美国可以有效牵制和平衡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对抗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
基于上述考虑,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大力强化美日同盟。例如,1995年美日两国建立了防长和外长“2+2”安全保障协商机制;1996年4月,美日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将同盟的功能定位由单纯的防御转变为对地区乃至全球事务进行干预。1997年9月,两国发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再次扩大了美日同盟的活动范围和职能,建立了相互协同和联合作战的安全保障体制。(20)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又积极鼓励日本调整“专守防卫”的军事行动原则,力求将美日同盟缔造为全球性同盟,以更有效地配合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21)
在强化美日同盟的同时,美国还调整和加强了与澳大利亚、韩国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例如,1996年美澳两国通过了《澳美安全联合宣言》;1998年,美韩修订并续签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2001年7月30日,美澳两国防长举行会晤,提出建立美、澳、日、韩“四国安全磋商机制”,以应对“地区潜在威胁”。(22) 在美国的支持下,2007年3月,日澳两国签署了《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称将在涉及共同战略利益的事务上加强合作与磋商,从而标志着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地区三方安全同盟的形成。
(二)拓展与东亚诸国的军事安全合作
为了应对未来在东亚地区可能面临的挑战,美国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依靠既有的军事同盟之外,还“必须透过加强合作及强调共同安全利益的方式”,大力加强与该地区非盟国的安全合作,以建构起一个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网络。(23) 为此,美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拓展美国与东亚国家的军事交流与合作。
首先是通过大规模军售和军援提升军事合作。例如,在1992年美国向新加坡出售价值近3.5亿美元的12架F-16战斗机,随即又向印度尼西亚出售了2架E-2C“鹰眼”预警机和警戒雷达。其次,美国频繁与东亚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数量与规模均呈现上升趋势。例如,仅在1999年美国与东南亚各国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便达14次之多。而美菲“肩并肩”军演、“平衡活塞”军演以及美、泰、新三国“金色眼镜蛇”军演等系列联合军事演习甚至已成为年度“必修科目”。再次,开展多边军事外交活动,积极筹划建立“亚太版”北约。即以调整后的美日同盟为核心,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等盟国,并着力加强美国与印度的战略合作,以“遏制中国势力的扩张”。例如,借反恐之机,美国在2002年8月与东盟签署了《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联合宣言》,与后者在情报互享、武器销售、军事培训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此外,美国也对东亚目前唯一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和合作机制——东盟地区论坛(ARF)表现出浓厚兴趣,2002年和2003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两次参加ARF的相关会议。最后,通过签署双边协议获得对东亚地区的“军事准入权”。1998年2月,美国与菲律宾签署《关于访菲美军待遇协议》,菲律宾苏比克海军基地和马尼拉港重新对美开放;1999年11月,美国获得了租用新加坡樟宜基地的许可;2003年,美国与马来西亚达成了“开放天空”协议,随后又与文莱达成“允许美军舰机进入辖区”的协议。与此同时,美国还积极改善与越南的双边关系,并提出了租借金兰湾的设想。(24) 如此种种,均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东亚安全格局的主导权。
三 “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先导”:美国的东亚经济战略
美国历来将“拥有进入关键市场与战略资源产地的权利”界定为“永恒的国家利益”。(25) 近年来东亚经济的强劲增长势头以及巨大的人口规模所蕴涵的庞大潜在市场,自然引起了美国强烈的关注。早在1993年初,克林顿政府便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倡议,随即又发起召开了首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积极参与和领导东亚乃至太平洋地区经济的发展,创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而就美国的东亚经贸政策而言,则经历了一个由强调“多边主义”向注重“双边主义”转变的过程。
(一)从“多边”迈向“双边”:美国的政策转折
为了参与和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美国曾一度对以APEC为代表的亚太多边机制寄予厚望,但是事实证明却成效不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多边机制往往更为强调成员间的共识和最低共同标准,而亚太地区各国由于彼此国情和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太大,加之各种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盘根错节,很难达成广为各方所接受的政策共识。其次则是由于多边协调涉及多个行为体,其协商交易成本必然远远高于双边机制,由此导致包括APEC在内的多边机制很难解决诸多迫切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26)
而相较于多边机制运作的软弱乏力,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双边经济合作以及互惠安排则受到了广泛青睐。(27)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东亚地区也出现了新一轮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浪潮。2004年10月7日,温家宝总理在第七次“10+3”领导人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研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的建议。在中国的影响下,日本也与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先后签署了类似于FTA的“经济伙伴协定(EPA)”。目前,中、韩、日三国已分别同东盟确定了建立双边FTA的基本框架,中韩、日韩也各自开始了双边FTA的谈判,中日之间FTA的谈判也正在酝酿之中。(28) 以FTA为代表形式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得到了迅猛发展。
面对东亚地区层出不穷的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之美国所极力倡导的APEC多边机制成效乏善可陈,导致美国开始逐渐将政策重点转向双边协商和双边机制的建构,其中尤以美国对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积极推动最具代表性。
(二)以双边FTA为先导:美国的经济参与战略
为了防止在不断深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美国在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等亚太国家协商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也在着力加强同东亚国家的双边经贸合作。2003年5月6日,美国与新加坡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美国由此迈出了与东亚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第一步。2007年4月2日,美国与韩国正式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被认为是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美国与外国达成的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标志着美国长期置身于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之外的局面从此改变。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也一直在积极推动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而备受瞩目的美国与日本的相关协定也正在讨论之中。(29)
对于在东亚区域整合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东盟集团,美国不仅与东盟部分成员国加强了经贸往来,例如,在2006年5月和7月美国分别与柬埔寨和越南签署了《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和《双边市场准入协议》,而且美国也在不断深入与东盟整体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05年11月,布什总统与东盟七国领导人发表了《关于增进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试图推动美国-东盟关系的进一步机制化。2006年7月,国务卿赖斯与东盟十国外长共同签署了《实施增进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一个月后,美国又与东盟围绕简化办事程序、鼓励贸易流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达成《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为双方达成全面自由贸易协定奠定了基础。(30) 为了能够更为深入地参与东亚经济合作,影响东亚经济整合的未来,维护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经济秩序,美国甚至在2006年11月的APEC会议上提出了建立由21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俨然成为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新一轮FTA浪潮的领导者。
(三)争夺主导权:美国推动FTA的动因分析
由于担心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持怀疑甚至是反对的态度。例如,2004年7月14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提出,东亚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不应破坏美国同亚洲朋友之间良好而且稳固的关系”。而针对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10+3”),鲍威尔则明确表示美国“至今不相信有必要达成新的协议”。(31) 但是,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已然认识到地区整合的必要性,在东盟倡导下,“10+1”、“10+3”和部长级会议等多层次合作框架纷纷建立,东亚合作迅猛推进。美国被迫开始逐渐调整政策,通过签署双边FTA等方式大力拓展与东亚各国的经贸合作,以积极介入东亚经济整合进程。美国政策的明显转变,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多重动因。
第一,防止东亚经济发展被中日两国主导,威胁美国的区域经济霸权。日本对东亚经济整合的大力推动,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日两国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加深,导致美国日益担心东亚形成一个由中国或日本主导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集团,从而使其对东亚的经济主导权受到严峻挑战。(32)
第二,防止东亚形成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集团。美国在东亚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东亚诸国不仅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公债拥有者。仅以2007年为例,美国与东亚的贸易额约为9 600亿美元,约占美对外贸易总额的24%。(33) 在美国十大贸易伙伴国中,东亚国家占据了4席位置。(34) 美国公债持有者的前5名全在东亚,共计11750亿美元,是美国自己所持的15倍。(35) 鉴于美国与东亚紧密的经济联系,历来将自由贸易视为经济发展引擎的美国希望借助双边FTA的签订,融入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进而构建一个对美国全面开放的东亚市场网络。
第三,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地缘/安全战略。美国对FTA伙伴的选择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全球地缘战略的考量。正如美国前贸易代表佐利克所指出的:美国之所以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就是因为它有助于“将商务、经济改革、发展、安全和自由社会有力地联系起来”。(36) 利用双边FTA,美国不仅“可以惠顾其忠诚的盟友”,或是“惩罚其薄情的朋友”,也可以借此加强与签约国的政治、安全和外交联系,进而以之为杠杆影响和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地缘战略格局。(37)
美韩、美新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标志着美国政策调整迈出了成功的一步。而事实上,美国的FTA政策也得到了东亚各国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对美国的严重依赖。大多数的东亚国家均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而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以及最主要的最终产品消费国,美国也始终是东亚各国最主要的出口市场,扮演着“最后买家”的角色。(38) 如果能够与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无疑将为签约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助力。其次,“多米诺”效应。即在竞争极为激烈的全球贸易体系中,一个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或现有自由贸易区成员的增加,将刺激那些非成员与某些成员建立新的自由贸易区,以获得成员的利益,避免被排除在外而造成福利损失。(39)最后,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经研究证实,经济大国与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将给后者带来显著的福利增加。(40) 就东亚地区而言,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与美国相比均相差甚远,即便是日本也相形见绌,因此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必然将会给签约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四 构建“价值观同盟”:美国的意识形态战略
在冷战爆发伊始,美国为了配合其遏制苏联、争霸全球的基本战略,便不停地鼓吹要在全球推进民主、自由,以“抵制暴政”和“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被很多美国决策精英归功于“美国价值观的胜利”,也激发了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由民主制度的热情,以建构和巩固符合美国价值观念的“市场民主国家共同体”,从而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被抹上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一)推广自由与民主: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
自老布什于1990年9月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构想以来,如何拓展美国的价值观,最终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个政治经济自由、人权和民主盛行”的国际体系,便成为美国核心战略目标之一。(41) 例如在克林顿政府制定的“参与和拓展战略”中,便公开声称要在“全球范围内保卫自由和促进民主”,并将推进民主与拓展美国经济、维护美国安全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42) 而“人权外交”、“人道主义干预”则成为美国在全球推广美式民主价值观念,培植“世界自由民主力量”的重要手段。
继克林顿之后,奉行新保守主义理念的小布什政府则更加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2002年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在21世纪,美国握有把自由对所有仇敌的胜利发扬光大的机会。美国愿意承担领导这一伟大使命的重任,努力把民主和自由拓展到世界各个角落。”(43) 不仅如此,小布什政府还明确地将意识形态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鼓吹要抓住冷战后美国独霸全球的历史时机,把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推向全球,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强加”给他国,以此来加强和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全球霸主地位。(44) 诚如国务卿赖斯所言:“我们的政策不仅被我们的实力所支撑,也被我们的价值观所延续。美国历来就是让实力和原则联姻,把务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配对。……只有构建一个反映我们价值观的国际秩序,才是维护国家长久利益的最佳保证。”(45) 正是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美国在2003年才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公然出兵伊拉克,其战略意图就是要在伊拉克复制一个奉行美式民主制度的新伊拉克,重塑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
(二)以意识形态画线:美国与东亚“价值观同盟”的构建
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的意识形态战略在其东亚政策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其具体表现便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积极推行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外交”。美国一方面强调“自由和开放的价值观”对维系美国与亚洲盟国关系的重要性,并成功促成了美日、美韩、美菲、美泰同盟关系的调整和加强;另一方面则通过鼓吹“与我们有着共同价值观的亚洲国家可以成为我们的伙伴,与我们一起巩固该地区的新民主政体和推进民主改革”,(46) 借机拓展与东亚地区“民主伙伴”的关系,其中包括改善与“亚洲新兴民主国家”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双边关系、强化与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军事安全合作、与韩国和新加坡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在传统的东亚地理范围之外,美国还大幅加强了与印度和蒙古的关系,甚至提出了“以促进民主价值观和民主机制为目标的亚太民主伙伴关系计划”,(47) 以确保东亚乃至亚太合作的制度建设不会有悖于美国的价值和利益。
毋庸讳言,在美国上述种种政策行为背后,也隐含着以推广民主、自由为名孤立和打压中国的深刻意图。在美国看来,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仅是一个与美式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异类”,更是对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秩序的重大威胁。首先,近30年来中国在保障政治、社会稳定的同时,顺利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东亚乃至全球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成功的范例,甚至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激辩和质疑。其次,中国积极推行多边主义的务实外交路线,不仅大大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也在世界舞台上建构起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尤其是与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在历史上中国便一直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领导者,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导致中国再度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无疑也是美国所严重关切和全力提防的一个问题。美国之所以大力鼓吹和推动以意识形态画线的“价值观外交”,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要借此拉拢“民主伙伴”,孤立中国,以遏制中国影响力在东亚地区的不断扩展。
(三)东亚各国的政策应对
无论是对“有原则的多边主义”的倡导,抑或是对“价值观同盟”的鼓吹,美国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影响东亚合作的日程和价值规范”,(48) 以防止东亚经济一体化背离美国的价值理念“脱序发展”,损及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基于各自国家现实利益的考虑,美国的上述主张也得到了部分东亚国家尤其是日、韩等盟国的积极响应。例如,早在2005年8月,日本便提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需要“理念上的方向性”,日本必须推动“自由、民主、人权”价值在共同体的实现。(49) 在当年12月召开的首届东亚国家领导人峰会上,日本明确提出须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共同体的价值观。随后,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极力要求下,峰会后发表的《吉隆坡宣言》中声称东亚峰会“将是一个开放、包容、透明和外向型的论坛”,并将“推动加强全球性的规范和国际公认的价值观”。(50) 2006年11月,时任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又提出了构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方针,将开展“价值观外交”、倡导建立“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列为日本外交的三大基轴之一。与近年来美国不断改善和强化与印度的合作相呼应,2008年10月22日,日印两国首脑在东京签署了《安保联合宣言》,并宣称未来两国将以“共同的价值与利益”为基础,围绕打击海盗、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反恐以及防灾等议题在亚洲地区展开广泛合作。
无独有偶,2008年4月,韩国总统李明博在访美时也提出了新时期“美韩同盟三原则”,即所谓的“价值同盟、互信同盟和构建和平同盟”,并鼓吹由于美、韩两国共享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价值,因此两国应制定新的战略总体规划,建立更为成熟的“价值同盟”,因为“只有拥有同样的价值和理想,同盟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51) 如此种种,均反映出美国所鼓吹和推动的“价值观外交”策略在东亚部分国家的确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五 结语
面对冷战后东亚一体化进程的蓬勃发展,美国在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制定了“三位一体”的一整套应对策略。其目的不仅是为了防止美国在该进程中被边缘化,更重要的则是为了遏止任何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成为该进程的主导者,从而威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由于美国同东亚诸多国家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双边关系,加之美国所拥有的超群的综合国力,因此美国的态度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势必会对东亚一体化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52) 然而,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使得东亚各国通过开展区域合作以谋求共同发展成为大势所趋。近日来愈演愈烈的金融风暴不仅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也再次为东亚各国加强金融/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2008年10月24日,中、日、韩三国和东盟在北京达成协议,决定于2009年6月前共同出资建立一项8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并设立一个独立的地区金融市场监管组织,以“加强地区合作和政策配合”。(53) 2009年3月1日,第14届东盟峰会郑重宣布要在2015年将东盟建成“第二个欧盟”。事实证明,继续深化和拓展东亚一体化进程是增进区域内各国切实利益的明智之选,也必将不断得到提升和深化。
[收稿日期:2008-12-25]
[修回日期:2009-03-28]
注释:
① Lowell Dittmer,“East Asia in the‘New Era’in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Vol.55,No.1,2002,pp.38-65.
② 可参见段霞、姜建新:《东亚安全共同体路径探讨》,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6期,第7~12页;王联合:《东亚共同体:构想、机遇、挑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第76~81页。
③ 可参见吴心伯:《美国与东亚一体化》,载《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5期,第49~51页;马荣升:《美国在东亚一体化中的角色扮演》,载《国际论坛》,2007年第3期,第20~25页;吴金平:《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与美国因素》,载《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4期,第15~18页。
④ 可参见林立民:《美国与东亚一体化的关系析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1期,第2~5页;陈奕平:《美国与东亚一体化》,载《暨南学报》,2007年第3期,第6~14页;韩志强:《东亚区域合作中的美国因素》,载《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3期,第36~39页;秦亚青:《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和美国的作用》,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第27~29页。
⑤ [美]约瑟夫·奈:《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利益》,载胡鞍钢、门洪华编:《解读美国大战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⑥ 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July 1994,p.2.
⑦ “Remarks to Diplomats in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IA Wireless File,January20,1993,p.7.
⑧ 《布什国情咨文强调美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http://news.sina.com.cn/w/2006-02-01/17218113679s.shtml.
⑨ “President- Elect Barack Obama Victory Speech,”http:// bbs.elzg.en/redirect.php? tid =74250&goto = newpost.
⑩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11) 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i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Vol.81,No.4,2002,pp.20-33.
(12) 吴心伯:《美国与东亚一体化》,第48页。
(13) Section Ⅱ,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May 1997,http ://www.defenselink.mil/qdr/archive/sec2.html.
(14)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2006/nss2006.pdf.p.30.
(15) 《主要挑战是如何对付中国的崛起》,载[新加坡]《海峡时报》,2007年2月10日。
(16) 美国国防战略所列出的四大目标分别为确保美国免遭直接攻击、确保战略进入和保持全球行动自由、增强联盟和伙伴关系、建立有利的安全条件。具体可参见张双鹏:《美国防务报告显困境:单边主义+武力≠绝对安全》,http://news.sohu.com/20060209/n241747512.shtml.
(17)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2006,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pdfs/QDR20060203.pdf.
(18) 陈峰君主编:《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19) Department of Defense,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 Pacific Region,” February 1995.
(20) 陈效卫:《合作与冲突:战后美国军事联盟的系统考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21) 王淑梅:《四场战争与美国新军事战略》,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240页。
(22) 李学江、黄山:《美在中国边上拉联盟》,载《环球时报》,2001年8月7日第8版。
(23)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February 2006,http ://www.defenselink.mil/pubs/pdfs/QDR20060203.pdf.p.32.
(24) 陈效卫:《合作与冲突:战后美国军事联盟的系统考察》,第141页。
(25)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September 2001,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pdfs/qdr2001.pdf.p.10.
(26) 可参见陆建人:《亚太经合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其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2期,第60~61页;郭定平主编:《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314页。
(27) 据统计,截至2007年6月,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之间已经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共27项,成员与非成员之间达成33项;此外,正在谈判中的有42项,正在构想中的有6项。具体可参见宋玉华、李锋:《亚太区域内自由贸易协定的“轴心-辐条”格局解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2期,第69页。
(28) 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13页。
(29) Richard L.Armitage and Joseph S.Nye,Jr.,The U.S.- Japan Alliance: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CSIS,Washing,D.C.,February 2007,p.18.
(30) 杨天欣:《美国热衷张罗亚太FTA背后:深入东亚 保主导地位》, http://intl.ce.cn/sjjj/gb/200704/24/t0070424_11144
148.shtml.
(31) Colin Powell,“Roundtable with Japanese Journalists,” Washington,D.C.,August 12,2004,http://www.state.gov/secretary/former/powell/remarks/35204.htm.
(32) 王嵎生:《亲历APEC:一个中国高官的体察》,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33) 具体数据源自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报告《美国首要贸易伙伴》(Top US Trade Partners),http://ita.doc.gov/td/industry/otea/ttp/Top_Trade_Partners.pdf.
(34) 具体数据源自WTO公布的报告《世界贸易发展》(World Trade Developments),可参见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08_e/its08_world_trade_dev_e.pdf.P.17.
(35) 杨天欣:《美国热衷张罗亚太FTA背后:深入东亚保主导地位》,可参见http://intl.ce.cn/sjjj/gb/200704/24/t20070424_
11144148.shtml.
(36) http://usinfo.state.gov/journals/itps/0803/ijpe/pj81zoellick.htm.
(37) 以美国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美以FTA——为例,1985年美国对以色列贸易顺差高达405亿美元,但是在2002年则逆转为对以外贸逆差54亿美元,2007年则为77.7亿美元。美以FTA给美国带来的经济收益其实为负效应,但却使美以本已十分密切的政治、外交、军事联盟关系更趋紧密。参见信强:《试论美台“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及可能性》,载《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3期,第31页。
(38) Robert Lieber,ed.,Eagle Rules :Foreign Policy and American Primacy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2002,p.306.
(39) Richard Baldwin,“A Domino Theory of Regionalism,”NBER Working Paper,No.4465,September 1993.
(40) Robert Scollay,“New Zealand and the Evolution of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in the Asia - Pacific Region :A Stocktake,”October 1,2003.转引自宋玉华、李锋:《亚太区域内自由贸易协定的“轴心-辐条”格局解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2期,第71页。
(41)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2,1990,A20.
(42) Anthony Lake,“From Engagement to Enlargement,”Address at th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John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Vol.4,No.39,September 27,1993,pp.658 -660.
(43)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转引自王公龙:《保守主义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44)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Foreign Policy and the Republican Future,” The Weekly Standard,September 7,1998.
(45) Condoleezza Rice,“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American Realism for a New World,”Foreign Affairs,Vol.87,No.4,2008,pp.2,26.
(46) Ralph Cossa,“US View: One Step Forward,Two Steps Back?”Conference Paper for“The Japan -Asia Dialogue,” Tokyo,June 22,2006,http ://www.ceac.jp/e/pdf/060622prog.pdf.p.44.
(47) 张学刚:《布什东亚政策演讲意图何在?》,http://dzrb.dzwww.com/dzzb/dzzb-gjxw/200808/t20080815_3832867.htm.
(48) 吴心伯:《美国与东亚一体化》,第51页。
(49) 吴怀中:《评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战略”》,http://www.cass.net.cn/file/2005102550098.html.
(50) 周永生:《21世纪初日本对外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第73页。可参见《关于东亚峰会的吉隆坡宣言》,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zgeydyhz/9thdmzrh/t230070.htm.
(51) 《李明博提新韩美同盟三原则 想搞“价值观”外交?》,载《东方早报》,2008年4月17日第8版。
(52) 马荣升:《美国在东亚一体化中的角色扮演》,第23页。
(53) 《中日韩东盟就建共同外汇储备基金达成一致》, http://
news.sina.com.cn/c/2008-10-24/154916519150.shtml.
标签:日本军事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同盟论文; 贸易协定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