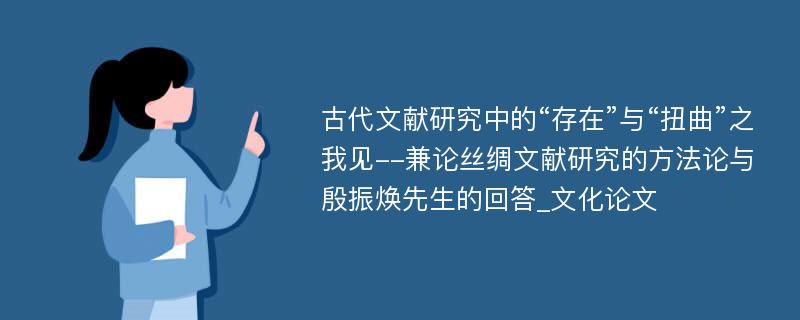
关于古文献研究中的“存真”与“失真”之我见——再谈研究简帛文献的方法论问题兼答尹振环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文献论文,我见论文,再谈论文,兼答尹振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4期刊出了尹振环先生《也谈帛、简〈老子〉之研究》(以下简称“尹文”)一文。该文对拙文《关于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思考——回顾简帛〈老子〉研究有感》(见《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以下简称《思考》)和拙著《帛书〈老子〉校注析》(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以下简称《校注析》)提出了批评意见。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提出意见进行切磋,是正常现象,本人表示欢迎。只是,尹文不能以礼待人,它对拙文特别是拙著,提出种种责难,戴了许多帽子:什么“框套今本”呀,“篇名失真”呀,“篇次颠倒”呀,“肢解帛书”呀,“改正为误,完全失真”呀,“违背古籍整理的基本规则”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他的眼里,拙文和拙著简直一无是处。为此,不能不对之作出回答,并就教于海内外研究《老子》的大方之家。由于拙作《思考》发表于本刊,境内同仁都可读到,是非自有公论;拙著《校注析》则出版于海峡彼岸,大陆同仁很难读到。为了向学界阐明真相,有必要在这里针对尹文对拙著提出的批评,多说几句话。
尹文一再批评拙著存在“完全失真”的严重问题,这很有必要讨论清楚。什么叫做“真”?笔者以为,“真”是相对的,它是与“假”对立统一的产物。由于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真”与“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真”的可变成“假”的,“假”的也可变成“真”的。例如,文物学家所理解的“真”,就同校注学家所理解的“真”有别。文物学家在整理文物时,要求完全符合文物客体的原貌。他们认为,符合原貌的,就是“存真”,不合原貌的,就是“失真”。而校注学家所理解的“真”,则不一样。他们在整理古籍时,不是简单地顺从客体本有的真迹,而是将研究对象与同类古籍进行比较研究,择善而从。这“择善”的过程,就是“去伪存真”的过程。一旦发现研究对象原有的“真”不可靠,就需要据他本予以改正。如此做,非但未“失真”,而且恰恰是“存真”。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这才是历史记录的实相,也是考据家所最应用心的地方。……抱着真则全真,假则全假的……观点的人,我觉得他根本不能……做考订工作。”(注:《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274页。)这是说得很中肯的,值得我们三思。在尹氏看来,帛书《老子》全是“真”的,而今本《老子》全是假的、不可靠的,谁要依据今本《老子》改正帛书《老子》某些东西,谁就是“曲古就今”,就是“失真”。显然,这种真假观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尹氏根据他的真假观,指责拙著存在内容“失真”、“篇名失真”、“篇序失真”、“‘肯定帛书不分章’失真”、“将错就错”的“章序失真”等严重问题。这些所谓“失真”,能够成立吗?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讨论。
一、关于内容“失真”的问题
尹文认为,拙著在校勘帛书内容方面,“改正为误,完全失真”。他列举了几例,并附有一张表,以说明“失真”的严重程度。然而,判断校注《老子》中的“正”与“误”,不能凭自己的主观臆恻,而必须以是否符合老子本旨为标尺。简帛《老子》和今本《老子》,都是发源于原本《老子》。今本《老子》在流传中难免造成讹误,但并非全属讹误;同理,简帛《老子》比较近古,其中保存了《老子》的某些真迹,但也并非字字正确。因为,它们也非《老子》原本,而是一般的手抄本。既是手抄本,就难免出现误字、漏字、衍字的情况,这就有对之进行辨正的必要。在辨正的过程中,择善而从,就需要对帛书的讹误之处予以改动。这种改动,非但不是“改正为误”或曰“失真”,而恰恰是还《老子》之本旨,“改误为正”或曰“存真”。从尹文所列的几例来看,正属如此类。
其一,关于帛书甲本“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句,此句乙本作“水善利万物而有争”,而传世今本此句多同王弼本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里“有静”、“有争”、“不争”三个概念殊异,究竟如何取舍?拙著认为,从《老子》之本旨看,似以今本“不争”一语为当。本章先言“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继言“夫唯不争,故无尤”,前呼后应,逻辑谨严,且与《老子》一贯思想相合。人所共知,《老子》中多次出现“不争”一语,如,二十二章:“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等,均凸现了“不争”之意。研究道教的著名学者王明先生也认为“《老子》书中的‘不争’思想有大量表现,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注:《道家和道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10页。)因此,帛书把“不争”写作“有争”或“有静”(按:“有静”实为“有争”之声假),实属误抄,应当据通行本改正。对于这一看法,尹文提出异议,认为应从帛书甲本作“水善利万物而有静”,释曰:“水善于滋润万物而又静默无声”。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说得通的。但综合全章来看,则下文“夫唯不争,故无尤”一语,就语无伦次了;而且,同《老子》一贯提倡“不争”的思想不相吻合。显然,作“不争”是,作“有争”或“有静”非。据此,拙著依今本取“不争”一语,似乎并未失真。
其二,今本第十四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帛书甲、乙本“古”字均作“今”字。究竟应取“古”字还是取“今”字?愚意以为,当从今本,作“执古之道”是。因为,从《老子》总体思想看,一贯强调“古道”。例如,笫十五章帛书乙本有“古之善为道者”(甲本此句脱损)第六十五章帛书乙本又有“古之为道者”。可见,《老子》重视“古道”。在《老子》中,还多次引用古圣人的格言(据统计,全书“圣人”一语有29见),也是重视“古道”的表现。此外,第三十八章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里讲的是古道每况愈下,不断退化的情况。显然,《老子》是在怀念“古道”。此外,孔子曾评价老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也从侧面证明老子要执的是“古道”。所以,老子是主张用“古道”来治理当时的天下国家。那么,为什么帛书将“古”字写作“今”字呢?愚意认为,“古人有反义通假的习惯,《尔雅·释诂》中就有‘故,今也’之说。可见帛书之‘今’乃为‘古’之假借字”。据此,该文应作“执古之道”。对此,尹文也提出异议,认为是“改正为误”,并反驳曰:“《尔雅》说的是‘故’,而不是‘古’,何以能证‘今’即‘古’呢?”这样的发问,未免有失身价:稍有训诂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古”与“故”可以通假。尹文还引《淮南·汜论》曰:“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其意在于说明“执古之道”不合老子本意。然而,这不是以《老》解《老》,而是以《淮》解《老》。须知,《淮》著属汉初黄老新道家著作,其思想体系同《老》有所区别。
其三,今本第三十七章首句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此句帛书甲、乙本并作“道恒无名”。拙著在校勘此句时,认为通行今本此句优,当作“道恒无为而无不为”(唯“恒”字从帛书)。又,本章末二句,今河上公本作“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此二句中的“不欲”,帛书甲乙本均作“不辱”。比较二者,余以为帛书之“辱”字乃“欲”之声假,当从今本作“不欲”。对此,尹文也提出批评,说什么“这一来,《老子》劝导侯王勿求取名辱不见?……掩盖了《老子》说教中心”云云。本来,校勘者将帛书与今本对校,有自己取舍的权利,只要不是无据改经,就无可非议。拙著关于本章的两处校文,都有通行今本为据,用“道恒无为而无不为”代替“道恒无名”;用“不欲”代替“不辱”,怎么就“掩盖了《老子》说教中心”呢?实质上“无为而无不为”、“不欲”都属于《老子》的基本思想。
关于“无为而无不为”句,今本《老子》先后出现三次,即三十七章、三十八章、四十八章;帛书甲乙本从已存文字看,未见此句。有人据此认为帛书无“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愚以为此说值得推敲。因为与今本第四十八章对应的帛书甲、乙本,此句均脱损,我们还不能肯定帛书该章无“无为而无不为”句。而且“无为而无不为”,从《老子》中还可以找到类似其意的文句。如第六十四章:“无为故无败”。这是说,做到了“无为”,就不会有失败。第四十七章:圣人“不为而成”。其意是说,圣人不用作为,就能成就一切事业。不难看出,其意都与“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相通。又,第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文中的“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等用语,都同“无为”相近,其意是说,君主做到了“无为”,就可以使众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显然,这里也透露了“无为而无不为”的观念。以《老》解《老》,可知“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观念。韩非《解老篇》及诸今本保存了《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句,是值得特别珍惜的,拙著依从今本改正帛书之误,还原《老子》之本旨,又怎么会“掩盖了《老子》说教中心”呢?难道一切依从帛书(按:况且我们还不能肯定帛书无“无为而无不为”句),才是正确的吗?果真如此,那又会重蹈“以帛书之是非为是非”的覆辙啊!
另外,拙著用今本“不欲”取代帛本“不辱”,也非毫无根据的妄动。今本此语概作“不欲”或“无欲”,从文意上看,当以今本为优。“不欲”或“无欲”,是《老子》的基本思想之一,书中多次出现。且“不欲”与“以静”相连,符合《老子》的一贯思想。而“不辱以静”,是很牵强的。需要说明的是,以今本之“不欲”,校正帛书之“不辱”,并非黄某一人如是作。近日重读张松如、张舜徽、陈鼓应、高明诸先生校注《老子》之作,发现他们均取今本之“不欲”。是不是别人都错了呢?奉劝尹先生不要陶醉于“众人皆醉我独醒”啊!
其四,与今本第二十五章对应的帛书“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一段文字,拙著在校勘中,将“王”正为“人”,“国”校为“域”。并附有一段按语:
“王”当作“人”。吴承志曰:“据《说文·大部》:‘天大、地大、人亦大焉,故大象人形。’则许所据本‘王’作‘人’,证以下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作‘人’是矣。‘人’,古作‘三’,是以读者或误为‘王’。”其说有理,检范应元本正作“人”。又,“域”,帛书作“国”,但通行各本并作“域”,按:“域”、“国”古通,《广雅释诂》:“‘域’,‘国’也。”今从众本作“域”。
上段文字,应当说已把道理讲清楚了,可是尹氏却批评说:“黄著却依据唐宋本,改帛本之‘王’、‘国’为‘人’、‘域’。这种违背古籍整理原则的作法,令人吃惊!”看来,这个“吃惊”,似乎有点过敏。人所共知,《说文》的作者许慎是东汉人而非唐宋人,怎么是“依据唐宋本”呢?退一步说,即使是“唐宋本”,只要持之有故,也无可非议。因为,到目前为止,谁也证明不了“唐宋本”都不可靠。所以,尹先生之“吃惊”,似超乎寻常。此外,尹文还说:“楚简《老子》不仅证明‘王’、‘国’二字正确无误,而且是‘国中有四大安,而王居一安’,比帛本多了两个‘安’字。这一来,老子尊王的政治哲学更为凸现。……解放前后,几乎所有人户堂屋中都有‘天地君亲师之位’的牌位,其实就是,‘家中有五大安’的祈盼。”这段话有两点明显失误:一是把简本中两个“安”字,当作实词“平安”之“安”。须知此“安”通“焉”,属语尾虚词,与今本或帛书“居一焉”之“焉”同义。尹文不明此义,将此“安”看作实词,作如此这般的一番解说,实在白费心血!二是用《老子》之“四大”来比附“天地君亲师”之“五大”,是不当的。因为前者属道家观念,后者属儒家传统,两者不应混为一谈。再者,尹文谓简本的“王”,“国”二字,证明帛书无误,亦恐非是。因为,从《老子》整体思想看,“王大”不合其本旨。我们知道,《老子》强调“侯王”要以卑贱自处,第三十九章:“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第六十三章:“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这都说明,“王大”不合乎老子的本意,当从今本作“人大”。“人”误为“王”,当自稷下道家始。稷下道家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维护封建王权的要求,讲“王大”,就是他们急于掌权的心理反映。竹简《老子》是稷下道家的摘抄本,突出“王大”,就是很自然的了。以之为据来证明《老子》原本为“王大”,是不当的。
还需说明的是,尹文为了向世人公布拙著“改正为误”,专门列出一张表。由于该表多属断章取义,笔者不拟在此为之费笔墨,只好持保留意见,相信读者自能辨别是非。
二、关于“篇名失真”的问题
尹文言:“《史记》只是说‘老子修道德,著书上下篇’,所以如用‘道’、‘德’二字命名《老子》这部书,还不能说走调;但用《道经》、《德经》来命名上下篇,则未免名不符实了。”这里涉及的问题是:《老子》的篇名能否以《道经》、《德经》名之?愚意以为完全可以,理由如下:
人所共知,《老子》自古称《道德经》,与此相对应,以“道”字起始之篇,称为《道经》,以“德”字起始之篇,称为《德经》,这已经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共识。尹文以帛书乙本篇末只有“德”、“道”二字,甲本篇末连“德”、“道”二字也没有为由,判定将《老子》篇名定为《道经》、《德经》为“失真”。显然,这是以帛书之“真”为“真”。事实上,帛书也只是一种手抄本,我们没有必要完全照搬帛书。凭实而论,今本在不少地方也保存了真迹。就篇名而言,今存传世本,概称《道经》、《德经》,愚以为未必不真。《老子》称“经”,当不晚于汉代。《汉书·艺文志》载有《〈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可见,早在班固著《汉书》以前,《老子》就已称“经”。邻氏、傅氏、徐氏三家之书,同帛书下葬时代相比,恐不会晚多少。又,据牟子言:“吾览佛经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经》亦三十七篇”(《理惑论》)牟子其人生活于东汉灵帝之时,他所言的《道经》,当是今本《老子》上篇。由此可知,与之相对应的下篇,当是《德经》无疑。这说明《老子》上下篇分别称《道经》、《德经》至迟在牟子著《理惑论》之前就已定型。故帛书之篇名虽无“经”字,但据上述情况,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上下篇分别称为《道经》、《德经》。这样作,既考虑了历史传统和有诸今本作依据,又考虑了继承前人已经约定俗成的文化成果的必要性,似乎没有什么不妥。还需要指出的是,把帛书篇名称为《道经》、《德经》,并非鄙人的发明。自帛书《老子》出土以来,已有许多专家如是作。例如,参加过帛书考古与整理工作的晓菡先生,在其所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中就有“《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注:见《文物》杂志1974年第9期第41页。)之语;又,高亨、池曦朝先生所著的《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一文第二部分的标题就是:“《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注:见《文物》杂志1974年第11期第1页。)。此外,张松如先生的《〈老子〉说解》、高明先生的《帛书〈老子〉校注》等,也都用《道经》、《德经》作篇名。可见,将帛书《老子》篇名称为《道经》、《德经》,许多学者都是这样做的,这并非不尊重帛书,而是沿袭已经约定俗成的文化传统。
三、关于“篇序失真”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篇序”,指的是《道经》、《德经》孰先孰后的问题。关于“篇序”,拙著曾作过说明:
帛书《老子》甲乙本上篇为《德经》,下篇为《道经》;但流传今本上篇概为《道经》,下篇概为《德经》。《老子》原本究竟是《道经》事前,还是《德经》在前?学术界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以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符合《老子》“道生德”的思想,也符合古往今来人们称老子学派为“道德家”的历史传统,不应该轻易改移。因此,本书仍按流传令本分篇之贯例,将《道经》列为上篇,《德经》列为下篇。
应当说,这里已把笔者的观点说清楚了,可是尹氏感到极不满意,仍指责拙著“从篇次排列上曲古就今……改正为误,完全失真。”对此,也有必要提出驳辩。
(一)尹文以若干古本证明《老子》篇序《德》上《道》下,证据不足。
尹文言:“韩非的《解老》、《喻老》据本以及严遵本(乃至王弼古本)也是《德》上《道》下的。”必须指出,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关于韩非的《解老》、《喻老》二书所涉《老子》文次序,并非《德》上《道》下,拙作《思考》已作论证,在此似不必多费笔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近读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书〈马王堆老子写本〉后》一文,发现他也指出过:“韩非《解老》,非论列全经,其先解《德经》首章,自是随手摘举,不足援之以证《老子》全书之先德而后道也。”其所见,与鄙人之论不谋而合。
其二,说严遵本也是“《德》上《道》下的”,同样经不起推敲。我们知道,关于严氏《指归》,今存有两种本子:一为《秘册汇函》本,题名为《道德指归论》,《津逮秘书》、《学津讨原》、《丛书集成初编》等,均收入此本(以下简称《函本》);二为《道藏》本,题名为《道德真经指归》,《怡兰堂丛书》亦收入此本(以下简称《藏本》)。这两种本子相较,有如下几点特色:
(1)《函本》为六卷本,列卷之一至卷之六,内容从《上德不德》章至“民不畏死”章,共34章,每章前未附经文;而《藏本》则为七卷本,列卷之七至卷之十三,内容从《上德不德》章至《信言不美》章,比前者多出六章,每章前均附有经文。
(2)《函本》附有谷神子《序》(全文124字),言及该书“陈隋之际巳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论德篇》,因猎其讹舛,定为六卷”;而《藏本》则无该《序》,但有说明从《上德不德》章至“民不畏死”章互相串联关系的序文一篇,姑称为《总序》。
(3)《函本》之《指》文中,无谷神子注释文字,而《藏本》则在相关的经文与《指》文下,插有谷神子注释文字。
(4)两本均附有严氏《说目》一篇。该《说目》从阴阳说立论,言及全书共72章以及上、下经所囊括章数的基本情况。
关于这部书,尚存不少历史悬案(因篇幅所限,不拟在此展开论述),过去曾有人怀疑是后人伪造(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即持此论),后经学者反复考证,肯定该书所涉《指归》之文,乃为严氏原作,但认为附于《函本》中的谷神子《序》及附于《藏本》中的《总序》,乃后人伪托,不可信。虽然学界有此共识,但关于该书篇序问题,至今尚未统一认识。这是由于历史资料扑朔迷离,疑点尚多。近年有人根据《说目》“上经四十而更始”、“下经三十有二而终”之语,对照《藏本》保存的《德篇》之章数刚好四十,便肯定《德篇》为上经。但这个结论是值得推敲的,它至少对以下问题难以解释:
问题之一:《藏本》原整理者无疑熟知《说目》“上经四十而更始”之语,亦当更熟知该本刚好40章(符合《说目》所言“上经四十”之旨)。令人费解的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却仍将该七卷列卷之七至卷之十三,即将《德篇》视为下经。这恐非简单从事所致,当有其所持依据。对此,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
问题之二:从《说目》所涉有关思想看,可以推知上经为《道篇》,下经为《德篇》。首先,《说目》明确指出:“变化所由,道德为母”。这“道德为母”一语,表明《指归》作者是把“道”置于“德”之上的,肯定“道”统帅“德”。这种情况,在《指归》正文中,亦时有所见。如:《上德不德》章言:“道为之元,德为之始”、“大道未分,醇德未剖”、“被道合德,恬淡无欲”、“体道抱德”等,都表达了“道”先于“德”之意。据此,似乎严氏不应当在篇序上来个颠倒,将《德篇》置于前,《道篇》置于后。其次,《说目》又曰:“《老子》之作也,……上经配天,下经配地。……天地之数,阴阳之纪,夫妇之配,父子之亲,君臣之仪,万物敷矣。”不难看出,作者在此是用天地、阴阳、夫妇、父子、君臣等关系来比附上、下经的关系(亦即道与德的关系),据此可知,严本应是上经为《道篇》,下经为《德篇》。因为只有“道”才可能与“天”、“阳”、“夫”、“父”、“君”等相匹配,从而符合其“道”统帅“德”的思想。可见,依据《说目》本意,该书上经应为《道篇》,而非相反。
问题之三:从《说目》得以保存的情况推知,《德篇》不可能为上经。因为《说目》实为该书之《序》,如唐鸿学在《指归跋》中所言,汉人著书之例,往往将序言置于书后,“如《法言》、《史记》、《汉书》、《说文》”等,均是如此。如果《德篇》为上经,那么按照以上排《序》贯例,《说目》应当在《道篇》之后。既然《道篇》早已佚失,则《说目》也不可能保存。今实际的情况是:《说目》确已保存。这种情况的出现,只有《说目》附于《德篇》之后才有可能,这就证明原书《德篇》为下经,而非上经。
总之,说严遵本也是“《德》上《道》下的”,亦难以成立。
其三,说“王弼古本”也是“《德》上《道》下”,更不可信。尹氏大著《帛书老子与老子术》(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此下简称《尹著》)中,有一段关键的论证。为了讨论问题,我们不妨将之摘录如下:“宋晁说之跋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犹近于古。’熊克说得更明白:‘不分道德而上下之,亦无篇目。’即也不辩析道经、德经,而颠倒上下篇的篇次,且无篇目。”上段所引晁、熊二人之言,含义一致(晁文的“析”字与熊文的“分”字同义),其义可以概括为:古《老子》不分道篇、德篇,而只分上下篇,且无篇目。如此而巳,没有别的意思。可是尹文却借题发挥。他首先将“析”字曲解为“辩析”,然后概括其义曰:“也不辩析道经、德经,而颠倒上下篇的篇次”之意。其中“颠倒”一词,原文中找不出对应词语,因而属于“添字解经”的作法,完全违背训诂学的法则。用这种曲解文意的作法来证明“王弼古本”也是“《德》上《道》下”,又怎么能令人信服呢?
总之,韩非本、严遵本以及所谓“王弼古本”均为“《德》上《道》下”之说,全都不能成立!则尹氏之论,失其依矣!
(二)尹文所谓“《德》上《道》下”之“自证”,亦不能令人信服。
为了证明《老子》原本是“《德》上《道》下”,尹氏还在“考证《老子》之自证”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并且提出了四点理由。为了讨论问题,我们不得不一一分别予以辩析。
其理由之一曰:“从行文看,应该由浅入深,从易到难。《德》上则是从‘上德不德’较为浅显的地方入手,如果《道》上则是从‘道可道,非常道’艰深的认识论开始。显然《德》上合理。”这个论证实在太牵强。说“上德不德”较“道可道,非常道”浅显,实质上很难找到客观依据。愚意以为,“上德不德”包涵着极深奥的哲理,在当时是对传统观念的猛烈冲击,其理并不“浅显”。因为在常人看来,“上德”应当是最有德的,而《老子》却说“上德不德”,这就同常人的思维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要突破常人的这一传统思维方式,其难度恐不亚于帮助人们认识“道可道,非常道”的哲理。今读王弼《老子注》,其“道可道”章,注文仅用了290余字(据楼宇烈《王弼集校释》本,下同》,而“上德不德”章注文,则用了1050余字,是首章用字的三倍多。这也从侧面说明“上德不德”章并不比“道可道”章浅显。附带说一句,尹文谓“道可道”章讲的是“认识论”问题,也不确。实事上该章的重点讲的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以及“众妙之门”,属于本体论问题。如果说本体论问题是最难的问题,应当放到最后讲;那么《老子》第四十二章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更是艰深的本体论问题,为什么又要放到《德》篇较前的位置,而不放到《道》篇较后的位置呢?显然,用文意的“浅”与“深”来解释《老子》的篇序结构,是不恰当的。
其理由之二曰:“先秦两汉的序言置于书后,如《庄子》、《史记》、《淮南子》等。《老子》的《序》看来不是内容驳杂的八十一章,而是三十七章。由此看,《德经》为上篇。”这段论述,更有臆测之失。请问:把《老子》三十七章看作全书的《序》,根据何在呢?作为一篇《序言》,它不能不讲一下写作动机、宗旨、过程之类的东西吧?今读该章,王本仅50字(帛书48字),其内容既未涉及写作动机、过程之类的东西,亦未能综括全书的基本思想,说它是全书的《序言》,确实太离谱了。须知,《老子》是一部内容独特的哲理诗,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序》之类的东西。尹文在此把《老子》与《庄子》、《史记》、《淮南子》等书相比附,把三十七章确定为该书的《序》,实在过于牵强。
其理由之三曰:“《老子》说教的中心与重头部分在‘德’,也可证《德》为上篇。”这个结论,显然又失之偏颇。人所共知,《老子》一贯“尊道贵德”。在老子那里,“道”与“德”一方面是不可分的统一体;另方面,就二者的地位来看,“道”又重于“德”。第一,“道”是产生世界万物的最后本体。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既然万物皆由道生,则“德”亦由“道”生。显然,“道”决定“德”,没有“道”就没有“德”。第二,“道”是最高法则的体现,人们只有“唯道是从”,才能使法则为己所用。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就从特定的角度揭示了“道”具有法则的权威。第三,“道”是侯王治国的根本依据。“道常无为”,侯王只有遵循无为之道,才能实现天下大治。第四,“道”是人们立身做人的保障。所谓“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即寓此意。第五,“道”是人们实现“长生久视”的法宝。所谓“治人事天莫若啬。……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五十九章),就表达了这一思想。以上五点,集中说明了《老子》的核心思想与重头部分在“道”而不是“德”。正如王弼所言:“《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不难看出,王氏所讲的“宗”或“主”,乃是“道”的代名词。故楼宇烈先生《王弼集校释》注释该句曰:“此句意为,言论、行事都不能离开道。”可见,王氏也是把“道”视为《老子》全书的支撑点。在他看来,“道”重于“德”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据统计,《老子》全文“道”字76见,而“德”字仅44见(据世界书局《十子全书·老子》),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道”重于“德”。令人惊奇的是,尹氏却说什么“《老子》说教的中心与重头部分在‘德’”。这一观点新则新矣,但却离《老子》主旨相差甚远,更不能证明《老子》原本为《德》上《道》下。
其理由之四曰:“从唐玄宗用圣旨统一篇章的史实看,《老子》古貌必为《德》上《道》下。”其所谓“史实”,指的是两段史料:一是《唐玄宗道德真经疏·外传》中所记的事:“道分上下者,开元二十一年,颁下所分,别上卷四九三十六章,法春夏秋冬;下卷五九四十五章,法金木水火土。”二是《全唐文》卷三十一所载唐玄宗《分道德为上下经诏》中所载“其《道经》为上经,《德经》为下经,庶乎尊道贵德,是崇是奉”等语。尹氏据这两段资料,判定今本《道》上《德》下的篇序,是由唐玄宗“划一并正式固定”下来的。这个说法,很难成立。如前引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援《七略》之言,可知早在唐以前,汉代思想家刘向校勘《老子》,曾“定著二篇,八十一章”,则其总章数在汉代就已基本定型;又据前引牟氏《理惑论》所言“《道经》三十七”,结合上述《七略》所载“八十一章”之数,可以推知《德经》四十四,则今本《道经》、《德经》之章数,早在汉代就已定型。今存《〈老子〉河上公章句》成于汉代,全书八十一章,每一章都有章题,如“体道第一”、“养生第二”、“安民第三”等,这些章题当是该书原本所有,亦可证《老子》总章数及上下篇章数,定型于汉,并非唐玄宗独出心裁、利用权力“划定”。唐玄宗的《诏书》只是为了兜售其《御注道德真经》,以表达其崇“道”的大政方针。至于他的《诏书》,是否在当时产生过“统一篇章”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比如照他的分章法,上篇三十六章,下篇四十五章;而今本多为上篇三十七章,下篇四十四章。此外,还有五十五章本、六十四章本、六十八章本、七十二章本等不同章数的本子,在世间流传。这些情况都说明,人们并未照唐玄宗的圣旨办。可见,以唐玄宗《诏书》为据,来证明《老子》原本是《德》上《道》下,仍然不可信。
以上说明,尹氏提出的所谓“考证《老子》之自证”的四点理由,全都站不住脚。
或者辩方会提出:即使韩非本、严遵本、王弼古本不能证明《老子》原本《德》上《道》下,那么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本子《德》上《道》下总是千真万确的吧,为什么也可置之不顾呢?是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本子的确是《德》上《道》下,但它是否真的保存了《老子》原貌,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道,《老子》的基本思想是强调“道”生“德”。“道”先于“德”,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西汉著名学者司马谈把《老子》所创立的学派,称之为“道德家”,这也从特定角度反映了《老子》原本《道》上《德》下这一客观情况。司马谈生活的年代与帛书乙本下葬时间相近,他的作法也应成为我们确定《老子》篇序的一个重要依据。另外,还需要考虑的是,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本子,均为殉葬品,是供在阴间的人享用的。楚地有一民风:凡供阴间之人享用之物,恰好与阳间顺序相反。如:过去农村为死去的亲人所设灵堂,在灵台下面摆放的死者的鞋子,左、右恰好颠倒:左脚鞋放在右边,右脚鞋放在左边;又,阳间的人穿的衣服,纽扣在右边。而给死者穿的寿衣,则纽扣在左边;又,民间抬活人,头在后、脚朝前。而抬死人,恰好相反,是头朝前、脚在后。如此等等,都说明对待阴间之人,与阳间正好相反的情况。此外,楚地传统风俗,左为大,《左传·桓公八年》:“季梁曰:楚人上左”,讲的就是这种情况。同时,楚地民间又有“亡人为大”之说。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本子,出在楚地,其篇序颠倒,可能与楚地民风有关:活人用的本子,是《道》上《德》下;死人用的本子,则是《德》上《道》下。这既体现了“楚人上左”,又符合“亡人为大”的民风。帛书《德》上《道》下,其次序正是《道》左《德》右。基于这些考虑,笔者以为帛书《德》上《道》下之篇序,乃是事出有因,并非《老子》本来面貌,不应当以它为据,确定《老子》之篇序。
综上所述,尹氏所要论证的《老子》古本应为《德》上《道》下的种种观点,完全不能成立。既然《老子》古本并非《德》上《道》下,则拙著依据传世今本,按《道》上、《德》下安排篇序,何谈“失真”之有?须知此种篇序,并非黄某伪造啊!
四、关于“‘肯定帛书《老子》不分章’失真”的问题
拙著《校注析》曾肯定帛书《老子》不分章,对此,尹氏也提出批评,指出:“如果只说乙本不分章,还差强人意,而说甲本也不分章,就不对了。这岂不否定帛书整理者所认定的‘帛书《老子》甲本用圆点作分章符号’的结论?……帛书《老子》甲本残留十九个分章圆点和十三个可证分章的勾勾点点,……黄著……连提都不屑一提,岂不又是违背古籍整理的基本规则的吗?”“可见,否定帛书甲本之分章,不校订帛本的分章,是太不应有的忽略吧!”这些批评,耸人听闻,不能不加辩驳。
首先,尹氏认为,拙著肯定帛书不分章是“否定帛书整理者所认定的‘帛书《老子》甲本用圆点作分章符号’的结论”。这个批评,实在不尽情理。须知,帛书整理者所讲的“帛书《老子》甲本用圆点作分章符号”的说法,也只是他们的一种推测,或曰一家之言,并未取得学界共识。事实上,当代不少研究《老子》的著名学者,大多认定帛书《老子》不分章。如,著名学者高亨先生曾明确指出:“帛书《老子》不分章”(注:《文物》1974年11期3页。);著名史学专家张舜徽先生亦说:“帛书甲、乙本《老子》都没有分章”(《周秦道论发微》第97页》;被张岱年先生称为“考古学专家”的高明先生,在其《帛书〈老子〉校注》中也说:“帛书《老子》甲、乙本皆不分章”。这都说明所谓“帛书整理者所认定的‘帛书《老子》甲本用圆点作分章符号’的结论”,并非金科玉律,不可移易。鄙人没有提及那个结论,怎么就是“否定”谁的什么呢?退一步说,即使有“否定”之实,从学术探讨的角度来看,也是正常现象,用不着大惊小怪。
其次,肯定帛书《老子》不分章,完全符合客观存在的事实:乙本未分章,自不用说;甲本本来也未分章,因为其中存留有一些圆点,整理者据之推测其可能为“分章符号”。仔细研读,愚意以为将之看作“分章符号”,理由不太充足。
其一,如果圆点是分章符号,那么,由它所划定的内容总应该相对集中、完整吧?但细读其文,并非如此。例如,与今本第五十一章相对应的甲本原文,有三个圆点。为了讨论问题,不妨照录如下:
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
不难看出,这里三个圆点,把今本第五十一章分为两部分。这两部分,本来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前面“道生之而德畜之”等语是后文“生之、畜之、长之、遂之”等推衍的前提,两者不应当分割开来。如果此圆点是分章符号,那么,就得把这两段本来相联而完整的文字,切割开来,使其各自独立成章。这又怎么能符合分章的基本原则呢?
其二,如果圆点是分章符号,那么,它应当表现出某些规则性。但是,从其分布情况看,却很不规则。有的地方仅十几个字,前后却有两个圆点;有的地方很长一段文字,却未见到那些符号。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随意性。此种无规则的符号,我们又怎么能将之作为分章的标志来看待呢?尹氏言:“十三个勾勾点点”也是分章符号,就更难讲得通。
其三,凭实而论,把那些圆点或“勾勾点点”看作分章符号,很难自圆其说,尹氏自己也感不踏实,只好解释说:“正像标点符号的概念尚未形成那样,分章的概念也是十分模糊的刍形”。这里“分章的概念也是十分模糊的刍形”一语,说明对于那些所谓“分章符号”,他们自己也感到不怎么踏实。
以上三点说明,把那些圆点或“勾勾点点”看作分章符号,理由并不充足。令人惊奇的是,尹氏却以此“十分模糊的刍形’,为立足点,要求所有研究者都要为之研究一番,谁如果对之持保留意见或不公开表示自己的看法,谁就是“违背古籍整理的基本规则”、就是“太不应有的忽略”,一顶顶帽子飞来,然而却不能令人信服。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古籍,各人有不同角度,研究什么与不研究什么,对哪些问题发言或对哪些问题不发言,作者都有自己的考虑。比如,对于那些尚研究不够或条件不太成熟的问题,作者可以暂时保持沉默或曰:“存疑”,这样作非但未“违背古籍整理的基本规则”,而且恰恰是严谨求是的需要。尹先生自己对帛书《老子》中的那些“勾勾点点”感兴趣,作了一番研究(这里姑且不评价其研究成果的价值),要求别人也象他那样去做;谁如果不像他那样去做,谁就是“违背古籍整理的基本规则”、就是“太不应有的忽略”。这种以己为是、强加于人的作法,实在不合乎学术讨论的应有宽容。
五、关于“‘将错就错’的‘章序失真’”问题
拙著《校注析》在《说明》中说:“帛书《老子》甲乙本均不分章。为校、注、析以及研究的方便,本书仍按今王本之次序,分章进行校注和简析。”应当说,这里已把宗旨交待清楚了。可是,尹氏却又借题发挥,大作文章。他以“将错就错的章序”作为小标题,批评拙著“章序失真”,指出:
黄著……将今本颠倒的篇次,错乱的章序,正确的或错误的分章,全部保留,然后肢解帛本,一一放入于今本框架中。这与其说是校注帛书,不如说是在肢解帛书。
这里又用一些耸人听闻的诛语强加于拙著,然而又有几点能站住脚呢?
首先,帛书本来就不分章,它的内容除篇序与今本有别外,在两篇文字顺序方面,大体与今本一致(只有少数几处文序与今本有别,关于这一点,拙著在《代序》中已作说明,并主张今本参阅帛书文序,改正几处章序:如今本第二十二章应放在第二十四章之下;第四十二章应放在第四十章之下等。)基于这一情况,亦为了“研究的方便”,拙著采用了今本的章序。笔者认为,今本的章序虽然亦有几处需要参阅帛本予以调节(如上所述),但从总体上看,基本上是可取的。而且,它已经过历史的检验,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成果,为人们广为接受。在学界未取得对之作修改的共识以前,不应轻易改变它。如果校注家都各持己见,自以为是地拿出一个章序,那只能造成新的混乱。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拙著沿用了今本的章序,并在《代序》中作了说明,这怎么就是“将错就错”、“肢解帛书”呢?
其次,最近笔者再次拜读了尹氏大著,领教了他的关于帛书分章的独见:“我们初步考证的结果是:帛书《老子》分章符号当在一百一十四个左右,或者说它是由一百一十二个左右的‘章’所组成。”尹文曾指出:“甲本残留十九个分章圆点,和十三个可证分章的勾勾点点。”即使他所说的那些都是所谓的“分章符号”,其总和也仅三十二,而经他的“初步考证”,竟变成了“一百一十四个左右”,比帛书真迹多出八十二。不知这八十二个新的“分章符号”究竟是从何地蹦出来的?如果无帛书真迹作依据,那就是出于臆测。尹氏以这种臆侧的分章符号数为立足点,把帛书分为“一百一十二章”。这确实创造出了一个关于帛书《老子》分章的“新体系”,它没有“将错就错”,然而它是否科学,是大可怀疑的。拙著的章序虽然有所谓的“将错就错”问题,但它至少有传世今本作依据;而尹氏提出的“一百一十二章”之说,历代从未见过,纯属“无据改经”之失。如果拙著仿效尹氏之研究方法,也搞所谓“重新排列章序”,并把帛书分为“一百一十二章”,必将带来更大的弊端,导致真正的“肢解帛书”,并给《老子》研究造成重大混乱。所以尹氏抛出的“章序失真”、“肢解帛书”等帽子,留给他自己用,倒比较合适。
以上我们从五个方面,说明尹文关于拙著的所谓“内容失真”、“篇名失真”、“篇序失真”、“章序失真”以及“‘肯定帛书不分章’失真”的评论,均有失客观、公允。与上述评判情况相联系,尹氏对我国学界研究简帛《老子》的评论也有偏激之嫌,他曾抱怨说:“从已出版帛本的注译看,框套今本者多,订正讹误者少;以古从今者众,用古正今者寡;谨慎保守有余,信古从真不足。对帛书《老子》的研究、开发、利用极为不够。”(黑体字为尹文原有)了了数语,将我国学界研究帛书《老子》的成绩一笔勾销。这些评论,只能说明尹先生过于自负、自信。无须讳言,他以这种过于自负、自信的心理来评判他人的成果,是很难得出中肯的结论的。奉劝尹先生不妨坐下来调适一下自己的心绪,以免参与争鸣时感情过于冲动、偏激。毛泽东诗曰:“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愿我们共同保持道家宽容心境,坐下来心平气和地相互切磋琢磨、研讨学术,千万勿过于骄躁。若先生还有未尽之言要发,鄙人愿意奉陪,共同切磋。真理愈辩愈明,相信读者自能明辨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