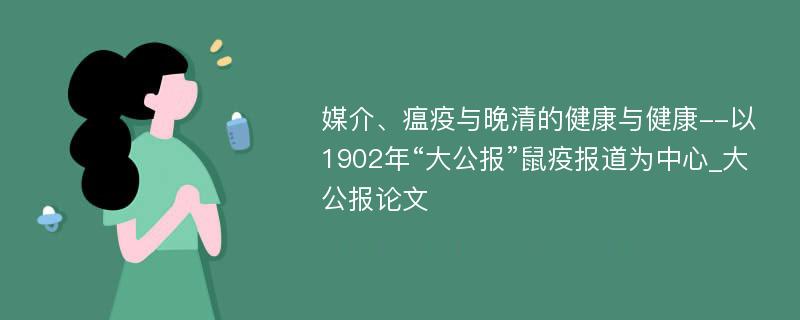
媒体、瘟疫与清末的健康卫生观念——以《大公报》对1902年瘟疫的报道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瘟疫论文,大公报论文,清末论文,观念论文,卫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R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 (2006)06—0096—08
疾病一直是人类健康的大敌,特别是危害较大的传染性疾病,例如瘟疫①,带给人类的痛苦和灾难更是巨大,甚至有时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都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② 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之后,对瘟疫的报道一直是媒体报道的重点。 在对瘟疫的报道过程中,媒体实际上也参与到瘟疫从发生到结束的整个进程中。在媒体与瘟疫的互动中,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思想观念尤其是在关乎人类身体健康的卫生观念上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1902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灾难结束才一年,一场可怕的瘟疫便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对于这场瘟疫,创刊于1902年6月17日的《大公报》给予了极大关注。从创刊之日起,到瘟疫结束,《大公报》对瘟疫进行了连续、详细、多角度和多侧面的报道。本文拟通过《大公报》对1902年瘟疫的报道,对清末普通民众的健康卫生观念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媒体话语下的瘟疫概况
从现代传播学理论来看,瘟疫是典型的灾难性事件。③ 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一直是新闻媒体报道的重点。西方新闻界有句名言:不是好消息就是好消息。《大公报》在对1902年瘟疫的报道中也遵循了这一新闻报道原则,对其进行了十分详尽的报道。从《大公报》的报道中,我们可以对1902年瘟疫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1902年瘟疫主要是指霍乱,患者“得病后下泻如白冻者即不可救”,但各地患者病情并非完全相同。④ 预防和治疗之法有:用“磺强水”“灭微生物以绝其源”;“远避染病之人及其人所使用之器物”,并用火烧或沸水来消毒;慎饮食,“凡食物之含水愈多者愈益留心,如鲜果、生菜、鱼肉之类”;染患霍乱者,当感觉“身体不舒,四肢乏力,口苦失味,胃不思食,大便或结或微泻”等情况时,宜急服用磺强香水及鸦片质或吗啡或服樟脑鸦片酒等,皆可治之。⑤ 上述预防和治疗霍乱的方法主要是以近代西方的医学知识和卫生学知识作为理论基础提出来的。
引发瘟疫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饮食不洁。“上海西医官来函云,此次致疫之故,以饮食不洁之物为最要端。”⑥ 其次是居民生活环境的恶劣,“省城街道湫隘,人烟稠密,居民每以秽物任意堆积门首,以致秽气熏蒸,酿成瘟疫之症。”⑦ 第三是气候异常,“今春桃汛未见,春雨又稀,河浅溜迟, 秽水入河不能畅流而下,故食之致病也。”⑧ 第四则是1899年至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即所谓“大兵之后,继以大疫”。⑨ 此外, 还有人开始从微生物学角度对病因进行解释:“泰西生物学家用极大显微镜察出一种尾点微生物,为最害人最毒人之物,此病之起,实由微生物之作祟。”⑩
从空间上的分布情况来看,1902年瘟疫是一场遍布全国的瘟疫(11);同时,在东亚和世界其它许多地方也出现了瘟疫。(12) 从持续的时间来看,瘟疫爆发于《大公报》创刊之前(13),至1902年10月开始逐渐消失(14),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四五个月之久。
瘟疫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首先是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从瘟疫开始之日到1902年7月初,天津因疫而死者共620人,(15) 且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天津的周围地区。浙江至1902年8月底,因疫致死者达16300多人。(16) 而江西至1902年8月上旬,因疫死亡人数便达二三万。(17) 瘟疫患者的范围很广泛,并不只是贫民、乞丐等生活条件很差的人群,还包括不少官绅阶层的人士及其在华的外国人。天津名绅严修之子严智庸,本欲出洋留学,“不意偶患瘟疹,医治无效,遂于上月底逝世。”(18) “英国驻津某武弁,年仅二十六岁,……已于六月三十号染疫殒命,殊为可惜。”(19) 甚至连皇宫内的嫔妃们也难逃此劫,“京津瘟疫盛行,近闻大内嫔妃中亦屡染时病且患目疾者尤多。太后慈躬亦连日进药饵以防疫气,故太医院各官每日皆有宣召云。”(20) 这场瘟疫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生命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其次,这场瘟疫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在瘟疫泛滥的情况下,一些准备回国或南下避暑的外国妇女和小孩都不得不延期而行,因为当时“烟台、威海卫及日本各埠均须验病,殊多不便也。”(21) 再则,瘟疫影响了国内各省市之间以及对外经济交往。瘟疫发生之时,有一轮船在由上海到天津的途中,病死搭客一人,“为大沽口西人查知该船带有疫气,饬令停泊大沽口外,一礼拜内不准上下,故邮便箱亦不能到津,而该船吃亏尤巨,每日须耗费五百元云。”(22)“本年三月以前,日本轮船来往此间者曾有多只,近来因查疫过严、利益太少,船来者因而大减。”(23)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了解到1902年瘟疫主要是指肠道传染病霍乱的大规模流行。它表现出三个比较鲜明的特点:一是流行区域广,不仅遍布中国的大多数省市,而且在东亚和世界其它许多地方都同时出现瘟疫;二是流行时间长,达四五个月之久;三是危害特别严重,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而在防治这场瘟疫时,出现了新的因素,即近代西方医学和卫生学知识。时人开始用这些近代科学知识分析病因,并提出预防和治疗办法,表明近代西方的医学和卫生学知识已经传入中国,并逐渐传播开来。
二 《大公报》的价值倾向(24):宣扬科学的健康卫生观
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认为:“新闻本身不局限于对真实的判断,它也包含了价值观,或者说,关于倾向性的声明。”(25) 沃伦·布里德也指出,无论承认与否,每家报纸都有自己的政策原则。(26)《大公报》在创刊号中即公开声明:“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以开我民智,化我陋俗而入文明。”(27) 在1902年瘟疫报道中,《大公报》认真实践了自己的办报理念。因为瘟疫主要是与人的身体健康相关联,故《大公报》在对瘟疫的持续报道中,极力宣扬科学的健康卫生观,而这实际上也是《大公报》自身办报理念的一次展示,自身价值观的一种宣传。
《大公报》发表评论主要是采取“论说”和“附件”两种形式。“论说”一般刊登在《大公报》的首页,是表明报纸政治态度、思想观点等基本价值观的评论,一般由报馆创办人英敛之撰写。(28) 但有时, 报馆也会将与《大公报》价值观相似或相近的来稿作为“论说”刊登。“附件”则固定在《大公报》最后的广告栏目前,它主要是就社会上或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阐发一些浅显易懂的道理,以达到“化俗美意”(29),通篇采用白话写作,“为便文理不深之人观看”。很显然,其实质还是为了宣扬《大公报》自身的价值观。
据初步统计,在1902年瘟疫时期,《大公报》上所刊登的专门介绍瘟疫和卫生知识的“论说”有2篇:《霍乱症预防法》、《时疫缘起治法说》;“附件”4篇:其中3篇都是以“讲卫生学”作为标题。(30) 此外,并非专门发表评论的“译件”栏目和“来函”栏目也刊登了不少关于瘟疫和卫生的稿件。其中,“译件”2篇, 题目均为《霍乱考》;“来函”11篇,题目有:《疫症杂说备志》、《用痧药宜先辨痧症说》、《霍乱考书后》、《中西医药论》等等。
两篇关于瘟疫的“论说”都不是《大公报》报馆中人所作。《霍乱症预防法》在报纸上的署名是“北京李萌斋”(31),《时疫缘起治法说》署名“征信堂郭方斋”(32)。两文从微生物学的角度对瘟疫致病之因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符合西方近代卫生观念的预防和治疗瘟疫之法。
在这两篇“论说”之后,《大公报》通过“本馆附识”表达了其登录这些“论说”的用意:“谨各录原稿,公之世人,倘未病者,照各法得以预防,已病者,按各法得以获愈,斯以济世利人之一端也。”(33) 由此可见, 《大公报》宣扬近代西方的医学知识和卫生学知识,最初的目的是在瘟疫中济世救人。
“附件”因为采用白话形式写作,通俗易懂,深受普通民众的欢迎。而《大公报》也利用这一点,大力宣扬近代西方的健康卫生观念,如《讲卫生学当知》(34) 一文中写道:
我们中国人,在养生的道理上,多是不肯讲究的,……如今,我把西洋至浅的卫生学,稍说一说,请大家留心,也是大有益处的事情。卫生学是什么呢?就是讲保养身体的法子。……人的心是总管血脉的,一呼一吸,循环周转,日夜不息的。凡是人,过于劳苦,血脉就消耗,必须用饮食赔补他。人的这出入气,顶是要紧的,比方地方脏污,房屋窄小,那些浊气最容易伤人。每天必须走个圈子,活动活动,换换清气,与人大有益处。睡觉的地方,必须要合外头通气,不然紧紧的关在一个小屋子里,那浊气一会功夫都满了,与人大有妨碍。
此外,该文还介绍了许多外国医学书籍,如《全体通考》、《全体阐微》、《医理略述》等。从上文叙述中,可以看出该文作者对“卫生”一词的理解与中国传统的“养生学”思想比较接近,或者说是在“养生学”思想的基础上来理解近代西方的卫生学。在养生学中,人与环境的关系主要讲调适而非控制和改变,与现代卫生观念强调对人们生活和劳动环境的管理和改造等内容并不相关。(35) 但是, 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该文作者已经了解到许多近代西方的生理学和医学知识,并根据这些知识,认识到生活环境对于人的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如对居住环境、空气清洁、居室通气的要求。
可见,作者对“卫生”概念的认识虽然还较多地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养生学”思想上,但是,关于“卫生”的具体内容已经加入了很多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对于这一点,文章作者有很明确的认识:“如今讲养生的道理,先要明白点格物、化学。”(36) 由此可知,中国卫生观念的现代化,并不是缺乏内在传承的西化, 而是在中国传统“卫生”观念的基础上,为适应环境的变迁,在借鉴了近代西方医学、生理学、卫生学和化学等科学知识后,逐渐形成的。
此文之后,《大公报》又以白话“附件”的形式刊登了《再讲卫生学》、《续讲卫生学》等文章,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宣传介绍近代西方在健康卫生方面的科学知识,以期改变国人根深蒂固的已经不适应环境变化的传统卫生观念和卫生习惯。这是《大公报》宣扬科学的健康卫生观更深一层的目的。
《大公报》宣扬科学的健康卫生观的价值取向,除了在“论说”和“附件”中得到直接的表现之外,还在《大公报》对“驱避疫鬼”(37) 的防疫方式的批判性报道中得到体现。
瘟疫期间,全国各地,主要是南方,较多使用“驱避疫鬼”的方式防治瘟疫。在苏州,当瘟疫发生后,“居民遂终日以禳醮符箓为事,好事者抬神游行街市,装神饰鬼,恐吓小儿。家家门首俱贴黄符,画钢叉官长,形同聋瞽,亦不知清街道污秽”(38);“继乃有所谓春申君会者、温天君会者、姜太公会、泰伯会者,自五月中旬至今无日无之,亦不能枚举。遂有青面赤发牛鬼蛇神,装出许多鬼脸,争奇斗巧,异想天开,令人发噱……”(39) 在杭州,当举行瘟元帅会时, “倾城士女扰扰攘攘,汗流浃背,人气熏蒸业已不堪触鼻,犹复兴高采烈趾踵相错,真所谓举国若狂矣。是役也,劳民伤财,百无一是。”(40)
《大公报》在报道上述新闻时,带有很强的价值倾向。这些价值倾向通过报道时所使用的词语,很明显地体现出来。对积极参加赛会的人,称作“好事者”、“青面赤发牛鬼蛇神”;描述赛会是“装神饰鬼,恐吓小儿”、“装出许多鬼脸,争奇斗巧,异想天开”;对赛会的作用评价是“劳民伤财,百无一是”。在否定“驱避疫鬼”这种防疫行为的同时,《大公报》还极力宣扬新的更科学的防疫措施。在报道中,《大公报》多次指责官府和民众“不知清街道污秽”,这实际上是在宣扬“清街道污秽”这种更符合科学的防疫措施。(41)
《大公报》否定“驱避疫鬼”的防疫方式是与它的办报理念相一致的。《大公报》以开民智为办报宗旨,而民智不开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相信异端邪说。“中国贫穷软弱,不足为忧,可忧的就是糊涂,没有真见识,专信那异端邪说,牢不可破,这就是大阻挡长进的一个关口。”(42) 《大公报》认为“驱避疫鬼”正是异端邪说的一种形式:“前几天我讲的,我们中国人妄信异端邪说,就是最阻挠我们长进的一个大关口。……这几天更听见新鲜事了:有瘟气,不知道想正经法子躲避,搭着个姜太公像,满街游。在他们想,这是很大的聪明人出的主意,因为有一句话说,‘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43) 由此可知,《大公报》对科学的健康卫生观的宣扬,最终的目的在于通过它对“驱避疫鬼”的否定和取代,以达到“开民智”的目的,而这也正是《大公报》办报宗旨之所在。
《大公报》以近代西方的健康卫生观念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的宗教背景有关。英敛之是一个天主教徒,因而对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采取了完全批判的态度。实际上,“驱避疫鬼”的防疫传统对传统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这一点,范行准和余新忠在自己的专著里都有阐述。(44) 任何一种观念和行为,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历史和现实的印痕。中国传统的卫生观念和行为缺乏对环境的改造和管理等现代卫生观念所包括的内容,很大程度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环境的破坏程度并不足以使世人感到管理和改造外在环境是极其必要的。
三 在新闻报道中彰显科学的健康卫生观
沃伦·布里德认为,媒体的价值取向一般是通过对新闻的“省略、有差别的选择,带有偏好的安排”表现出来的。(45) 《大公报》在对1902 年瘟疫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对科学的防疫行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报道。这些报道主要集中于公共卫生方面,对于控制瘟疫这样的传染病,公共卫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大公报》通过报道这类新闻,大力宣传科学的健康卫生观念,“以开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46)。
实际上,在分析瘟疫发生的原因时,《大公报》特意强调“饮食不洁”和居民生活环境的恶劣,正是为宣传科学的公共卫生观念和行为作铺垫。
在饮食卫生方面,《大公报》报道了官府对食品卫生的稽查:“以鱼虾等类其味腥臭,易召时疫,乃出示禁止市中不得售卖鱼虾等鲜物,而业渔者亦遵谕歇业矣。”(47)
饮食卫生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自来水的设置,它不但对防疫有重要作用,更可以改变城市居民的饮水习惯,有助于民众形成现代的健康卫生观。《大公报》对各省市关于自来水的新闻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报道。“厦门向无泉水,一遭亢旱,取汲维艰。日前延少山观察特请日本技师在厦丈量地道远近,以便安设自来水管。闻已筹银二十余万,饬人在上海购办水管机器云。”(48) 瘟疫期间,当时天津最大的自来水厂——济安自来水公司正在兴建之中,《大公报》其进行了报道:“西头芥园迤东原有大坑一段,兹经工匠多人铺垫洼处,修筑房间,落成在即,闻系安设自来水公司之用。”(49) 之后,又连续报道自来水管被运到天津(50),及其安设的进展情况(51)。由于瘟疫带给人们的巨大痛苦和灾难,也由于《大公报》的极力宣传,民众慢慢形成了饮食讲究卫生的观念。天津英租界的鸿兴荷兰水(即汽水)公司,最初因都统衙门禁止售卖生冷物及各种汽水而停业。后来,该公司改用开水制造汽水,请各捕房验明,准其售卖,并在水瓶上贴一红纸条,印有英国武官所签洋字,以声明此水清净,实为开水制造。(52) 为了招徕顾客,鸿兴荷兰水公司还专门制作广告,特别声明汽水“蒙都署梅大人(53) 莅验,许以做法精良,与卫生局章程相合,特给执照,以广销售”。(54) 广告宣传中,经常使用“转移法”来有效增加某一产品的销量。“转移法”是指“将某种权威、约束力,某一令人尊敬和崇拜的事物的威信转移到其它事物上使后者更可被接受。”(55) 汽水公司做广告时特意强调汽水经过了医生的化验和卫生局官员的批准,正是想通过掌握了现代医学卫生知识的“医生”和“卫生局官员”的威信来增加汽水在民众中的信任度。而掌握现代医学卫生知识的“医生”和“卫生局官员”在民众中拥有崇高的威信,这一现象本身即说明了卫生观念的日渐普及。
在环境卫生方面,《大公报》着重报道了清道排污、对粪便的管理及对尸体的埋葬和处理这三方面。《大公报》一方面报道并指责一些官府和民众采用“驱避疫鬼”的方式来防疫,而“不知清街道污秽”;一方面又大力报道天津巡捕局对于环境卫生一向很重视,“每日稽查居民门首街心有无污秽”(56),如有则对其处以严厉惩罚。天津某堂因为在门首任意污秽,其堂主则被带到巡捕房鞭责,并罚洋三元。(57) 通过两方面报道的强烈对比,可以看出《大公报》试图向民众表明,清洁卫生的重要性。
粪便管理不善是导致居民生活环境恶劣的一个重要因素,“每有粪厂,秽气熏蒸,实非居民所宜。”(58) 《大公报》对于粪厂和官厕有相当细致的报道,这种报道主要集中在天津新闻里。当时,经都统衙门卫生局(59) 查明,天津境内应立官厕150处。(60) 而粪便又可以作为肥料借以取利,因此对于粪便的管理,一般带有商业性质。卫生局先是将官厕承包给邱应运、冯天锡,但是二人违背规则,与民人私订合同以获取钱财,被卫生局发现,取消其承办资格。(61) 之后, 卫生局又将官厕承包给李润章等人,强调不准借端舞弊。(62) 粪厂和官厕的设置,不仅是一项重要的防疫措施,更由于其关系到城市里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其对人们的生活习惯,乃至卫生观念的改变都将起到巨大的作用。而《大公报》对粪厂和官厕的报道,推动了人们对粪厂和官厕的认识和接受。
再则是对尸体的埋葬和处理。《大公报》在这方面的报道主要侧重于以下几点:首先是关于报丧制度的建立。报死者必须由绅董查明开单,而死者家属也须赴保卫医院呈报病死之因,才能“酌发执照”,得以安葬。(63) 其次, 对于一些无力掩埋或者无人掩埋的尸体,官府或民间都会设法加以掩埋。如某地有一人患疫身亡,但因家贫无以殓葬,最后由官医院给棺材一具,葬于义地。(64) 有乞丐因疫死亡之后,附近居民便自动出钱雇人抬埋之。(65) 另外, 《大公报》还报道了不少绅董或者公司捐献土地作为义地以供掩埋尸棺的善举。比如天津善绅王树泉自愿将一块二十多亩的土地以其原价的一半卖给保卫医院,作为埋葬无主棺材的义地。(66) 瘟疫结束之后,《大公报》还后续报道了天津卫生局发出的告示,本年染疫尸棺,停放时间不过一年不准迁葬。(67)
注重对尸体的埋葬,其实是中国一项非常悠久的传统。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尸气是造成瘟疫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大灾或者大战之后,会有专门的组织来处理遗骸,这一方面是出于人道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疫。(68) 例如天津的掩骨会, 专门将无茔地棺木者埋入义地,每年春秋两季,还会派人到各处拾取暴露骨骸,所以也叫拾骨会。(69) 《大公报》对尸体埋葬的报道,强化了这一传统。 传播理论家约瑟夫·克拉珀认为,大众传播的总体效果是态度强化。(70) 注重对尸体的埋葬,是符合科学的公共卫生态度,《大公报》以宣传科学的健康卫生观为己任,便对中国的这一优良传统进行了强化宣传。
四 结语:科学的健康卫生观在防治瘟疫中得到了广泛传播
宣传的目的在于重塑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态度。大众传媒在宣传方面具有巨大的威力。由于长时间的接触媒体,人们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媒体表达的角色模式,使得自己讲话的方式、穿着的方式、思考的方式和行为,以及反应的方式都趋向于媒体的价值倾向。(71)
《大公报》在1902年瘟疫报道中,或通过对开设自来水厂、官厕等科学的公共卫生行为进行大量而详细的正面报道,或通过对“驱避疫鬼”等不太科学的防疫行为进行批判性的报道,或通过“论说”和白话“附件”等形式直接介绍近代西方的卫生学知识,来大力宣传科学的健康卫生观,并期望以之取代民众根深蒂固的不太科学的传统卫生观。这种宣传有力地推动了科学的健康卫生观在民众中的传播。
首先,自来水厂和官厕等现代公共卫生设施的大量建立,表明公共卫生至少在官方层面成为一种共识。同时由于自来水和官厕直接关系到大部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所以这些公共卫生设施在投入实际运作之后,都对普通民众的卫生习惯和卫生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其次,掌握近代西方医学和卫生学知识的医生和卫生局官员成为普通民众信任的权威,说明民众对近代西方的医学和卫生学知识产生了信任感。伴随着这种信任感而来的是民众对自身固有的卫生习惯和卫生观念的怀疑,这为科学的健康卫生观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再则,从社会各界人士寄给《大公报》的“论说”、“来函”和“附件”等稿件中出现“微生物”等词语,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近代西方的医学和卫生学知识已经开始在普通民众中传播和普及。1902年12月16日的《大公报》上有一则“来函”,讲道:
某君来函云窃查泰西卫生之道,精益求精,其保卫之有方,盖以民生为至重耳。自天津设立都署以来,即安设卫生总局以除污秽,以洁街衢,法至良,意至美也。今夏疫气盛行,朝不保夕,而卫生局竭力保护,讲究卫生。凡有益于民者,莫不剀切而晓谕之;凡有害于民者,莫不出示以严禁之,卫生有术,故能疠疫潜销焉。
从来函中所表示出来的对“泰西卫生之道”的由衷钦佩,我们可以看出,1902年瘟疫中,近代西方的科学的健康卫生观念和行为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注释: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对“瘟疫”的解释是:“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2页。
② 曹树基认为:“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见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32页。
③ 从传播学理论的角度来考察,灾难性事件表现为自然界、社会、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的恒常性的断裂或破坏,这种断裂或破坏使人类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一定的可知性基础上建立的对自然界、社会、人类文化或价值观念的认知的确定性降低,破坏了社会群体或个人与其生活环境已有的和谐,使整个社会、社会中的个人对灾难性事件的表层信息(即发生了什么事)和深层信息(即为什么或有什么样的影响)产生强烈的需求,以便调整原有的认知结构,最大限度地消除认知不确定性,实现与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价值环境的重新整合。
④ 《疫气北来》,《大公报》,1902年7月1日。
⑤ 《霍乱症预防法》,《大公报》,1902年7月12日,论说。
⑥ 《大公报》,1902年6月22日,译件。
⑦ 《清理街道》,《大公报》,1902年7月1日。
⑧ 《麦黄水涨》,《大公报》,1902年6月28日。
⑨ 《依然守旧》,《大公报》,1902年7月11日。
⑩ 《霍乱症预防法》,《大公报》1902年7月12日,论说。
(11) 《大公报》在1902年期间的新闻编排,是分省市进行的。如果某省市新闻里有关于瘟疫的报道,即可表明该省市有瘟疫。由此可知,全国有北京、天津、保定、营口、张家口、上海、桂林、山东、东三省、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河南等地发生了瘟疫。在对各省市瘟疫的报道中,尤以天津、北京、营口、东三省、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关于瘟疫的报道最多。需要注意的是,对瘟疫报道的多少,与瘟疫严重程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大公报》对天津瘟疫的状况报道最为详细,但从瘟疫死亡人数来看,天津并不是1902年瘟疫中最严重的地方,浙江瘟疫致死人数远远超过天津。天津瘟疫之所以报道最为详细,是因为《大公报》开设于天津。
(12) 从《大公报》在1902年期间的报道来看,除了中国之外,日本、韩国、意大利也发生了瘟疫,其中以对日本的报道最为详细。
(13) 因为1902年9月4日《大公报》上有一则《保卫医院广告》,其中讲到“暂行保卫医院总局由五月初十日入局”。《大公报》上使用的都是农历,“五月初十日”推算为公历,应该是6月15日。这说明专门为防治瘟疫而建立的保卫医院是在1902年6月15日建立,而《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6月17日。
(14) 《大公报》上并没有明确的瘟疫结束时间, 该时间是根据《大公报》对瘟疫的报道情况得出的。从1902年10月初开始,《大公报》对瘟疫在全国范围内的报道逐渐减少,由此推知瘟疫从1902年10月开始逐渐消失。当然,也不排除《大公报》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再从各省市获得关于瘟疫的信息,或者《大公报》不愿意再报道瘟疫方面的新闻。这些情况,本文无法进行讨论。
(15) 《大公报》,1902年7月3日,译件。
(16) 《疫死记数》,《大公报》,1902年8月31日。
(17) 《疫气未已》,《大公报》,1902年8月11日。
(18) 《赍志以移》,《大公报》1902年8月7日。
(19) 《大公报》,1902年7月3日,译件。
(20) 《大公报》,1902年6月29日,录件。
(21) 《大公报》,1902年7月1日,译件。
(22) 《禁船进口》,《大公报》,1902年6月21日。
(23) 《大公报》,1902年7月22日,译件。
(24) 这里主要指《大公报》在对1902年瘟疫进行报道时的价值倾向。
(25)(26) 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第361页。
(27) 《大公报序》,《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
(28) 《大公报》早期“论说”不署名者,多为英敛之撰写。参见何炳然:《辛亥革命前〈大公报〉的评论探究》,载《新闻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总26辑,第51页。
(29) 《附件:讲看报的好处》,《大公报》,1902年6月22日。
(30) 《讲卫生学当知》,《大公报》,1902年7月12日,附件;《再讲卫生学》,《大公报》,1902年7月14日,附件;《续讲卫生学》,《大公报》,1902年7月19日,附件。
(31) 《霍乱症预防法》,《大公报》1902年7月12日,论说。
(32)(33) 《时疫缘起治法说》,《大公报》1902年7月13日,论说。
(34) 《讲卫生学当知》,《大公报》,1902年7月12日,附件。
(35)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36) 《再讲卫生学》,《大公报》,1902年7月14日。
(37) “驱避疫鬼”的防疫方式来源于中国传统的鬼神致疫的观念,中国的许多传统节日,如春节、上元、立夏、端午、立秋、重阳、除夕等都与驱避疫鬼的观念有关。参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93页。“驱避疫鬼”的防疫行为,在1902年瘟疫中,主要以各种赛会的形式出现。
(38) 《瘟疫流行》,《大公报》,1902年7月5日。
(39) 《吴中醮会志盛》,《大公报》,1902年7月22日。
(40) 《举国若狂》,《大公报》,1902年8月8日。
(41) “驱避疫鬼”的防疫方式能延续千年,本身即说明其含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不能认为这种防疫行为是完全不科学的。但是,在举行赛会时,“倾城士女扰扰攘攘,汗流浃背,人气熏蒸业已不堪触鼻,犹复兴高采烈趾踵相错”,这种人群的聚集无疑是有助于瘟疫的传播,所以对于举行大规模的赛会来防疫,的确是不科学,不可取的。
(42) 《讲妄信风水有益无害》,《大公报》,1902年7月1日,附件。
(43) 《不嫌琐渎再贡愚言》,《大公报》,1902年7月11日,附件。
(44)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上海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版;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5)(55) 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61页、第116页。
(46) 《大公报序》,《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
(47) 《禁卖鱼虾》,《大公报》,1902年7月13日。
(48) 《兴自来水》,《大公报》,1902年11月25日。
(49) 《食德饮和》,《大公报》,1902年6月27日。
(50) 《水管到津》,《大公报》,1902年8月3日。
(51) 《安设水管》、《埋设水管》,《大公报》,1902年10月2日、11月14日。
(52) 《汽水复作》,《大公报》,1902年7月3日。
(53) 天津都统衙门卫生局委员,是一位法国医生,曾在北洋医学堂担任教习。在瘟疫期间,积极参与卫生局防治瘟疫的工作,并率同北洋医学堂学生在专门性的防疫医院保卫医院救治病人,“活人无算”。《大公报》1902年10月4 日的新闻“纪北洋医学堂”中对其有简单介绍。
(54) 《鸿兴荷兰水公司》,《大公报》,1902年7月21日,广告。
(56) 《稽查甚严》,《大公报》,1902年6月20日。
(57) 《污秽受惩》,《大公报》,1902年7月23日。
(58) 《府县告示》,《大公报》,1902年9月19日。
(59) 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后,组成都统衙门,对天津实施了长达两年的殖民统治(1900年8月—1902年8月15日)。都统衙门设立之后,便设置卫生局。1902年瘟疫主要发生于都统衙门统治天津时期,而都统衙门卫生局是天津防治1902年瘟疫的主要领导机构。
(60) 《更换粪头》,《大公报》,1902年6月30日。
(61) 《卫生局示》,《大公报》,1902年6月28日;《早出暮归》,《大公报》,1902年7月27日。
(62) 《卫生局示》,《大公报》,1902年6月28日。
(63) 《严查病死》,《大公报》,1902年7月11日。
(64) 《掩埋尸棺》,《大公报》,1902年7月15日。
(65) 《抬埋丐尸》,《大公报》,1902年7月28日。
(66) 《保卫医院广告》,《大公报》,1902年7月13日。
(67) 《严禁移坟》、《卫生局示》,《大公报》,1902年12月23日。
(68)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13页。
(69)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页、272页。
(70) 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71) 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3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