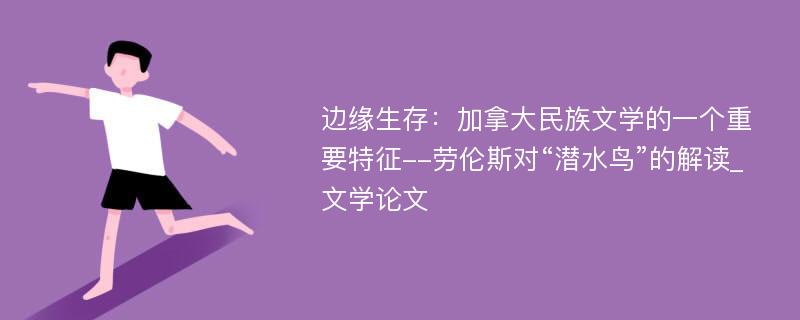
边缘生存:加拿大民族文学的重要特色——M#183;劳伦斯所著《潜鸟》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伦斯论文,加拿大论文,所著论文,边缘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加拿大民族文学根植于其多元文化。本文以玛格丽特·劳伦斯所著的《潜鸟》为例,通过对其民族的“根”、“身分”和“自尊”三方面的解读,剖析了加拿大文学所揭示的少数民族边缘生存的困境并试图阐释其民族文学的底蕴。
关键词 边缘 民族 生存 文化
加拿大当代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1926—)童年不幸,父母早逝,由继母和祖父抚养成人。她与工程师杰克·劳伦斯结婚后,去过非洲的索马里、加纳,也曾在英国生活过多年,直到1974年才回到故国定居。
玛格丽特·劳伦斯与绝大多数英美白人作家不同,她并不以白人的大文化圈为写作的中心,而以自己多年在别国文化圈中的生活体验,加上对加拿大多元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女性的细腻解读,在自己的创作中对处于边缘文化的人和民族的困境作出了自己的解读,其著名短篇小说《潜鸟》较深刻地揭示了边缘生存这一主题。
《潜鸟》写于1970年,〔1 〕讲述的是一位印地安姑娘皮佩特·托勒妮的一生。故事的情节主线很清晰:作者少年时认识了一位印地安姑娘,是作者的同班同学,九年后作者在一家咖啡馆又偶然见到托勒妮,得知她马上要与一位白人结婚了,四年后又得知她婚姻失败回到故乡,不久与自己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起烧死在失火的棚屋里了。这一貌似简单的婚姻悲剧蕴涵着深刻的哲理,作者通过文中不同身分的人物的视角,从深层次上提出了在多元文化冲击下少数民族的生存问题。
《潜鸟》一开始就介绍了托勒妮一家的背景:他们家虽有法国血统,但他们既不讲法语也不讲克里方言,而是讲其特有的土话。他们也讲英语,只是极不规范,因为“他们既不是北部加罗宾山区保留地的克里人,也不是马拉瓦卡流域的苏格兰—爱尔兰人或乌克兰人”,就像作者的祖母所说的,“他们非驴非马,无法界定”。
一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这常是一个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蕴涵着该民族历史上沉淀下来的大量文化信息。从语言习得的角度来看,托勒妮在儿童时期在习得母语时同时受到几种语言的影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她讲的语言有缺陷,但这绝不是其智力的缺陷,而在于其认知的途径方面,其影响更多的是来自于外来语言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如果说托勒妮所讲的土话是一言语共同体(因为这是他们社团中人们交流所使用的),那么该共同体也未形成完善的体系和自身明显的标记。他们语言中那不规范的英语、法语极好地象征了其边缘生存的特点,因为他们的出身和生活环境要求他们被迫作出语码混合以保持与别人的正常交流。
劳伦斯先用托勒妮的“失语症”来暗指一位土著姑娘的边缘生存困境。本来“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2 〕而托勒妮的民族文化背景使她使用的混合语言被排斥在大文化圈的正式语域之外,常使她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受阻。按照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深刻的文化内涵已不是普通的语义分析可解读的。沃尔夫在研究印地安语言的过程中,特别是通过对霍比语动词体系的内涵与霍比人的时空观的关系的研究,沃尔夫发现一个人的语言影响到他理解现实世界的思维模式和其行为方式,而萨丕尔也认为语言的物质反映了一个概念世界,语言决定了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一假说的重要贡献在于指出了语言与思维和文化的紧密联系,这也适用于对托勒妮在语言困境下的思维和文化困境的解读。印地安人本来有自己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而且他们世世代代都用自己的语言来理解自己周围的世界,但如今外来语的侵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影响更为深远的文化侵入,这些新的语言传输的信息不少与印地安人传统的对世界的理解相悖,这种撞击下产生的结果就可能是一种对世界扭曲的看法或是一种支离破碎的看法,既不属于印地安传统构建的模式,也不属于任何西方模式,因此托勒妮的“失语”的底蕴早已跃出了语言本身的层面。
《潜鸟》中的作者“我”与少年时代的托勒妮的关系是书中的主线之一。作为同学,作者所知道的托勒妮好像对读书不感兴趣,常缺课,患有骨结核,衣着不整,但作者当时对她谈不上“友好或不友好”。此时作者的父亲出现了,因为他是托勒妮的医生,对她的处境表示同情。为了帮助她,他主动提出夏天去钻石湖渡假时带上托勒妮。虽然作者的祖母极力反对,甚至威胁说如果这样她就不去了,但是作者的父亲还是坚持己见并要求作者与托勒妮友好相处并尽力帮助她,而其结果完全出人预料之外:来到钻石湖时,作者发现托勒妮脸上毫无表情,“似乎她已灵魂出窍,去了别处”,连作者主动邀请她玩也被断然拒绝了。作者之所以对托勒妮产生兴趣,是认为她“在一定程度上是森林的女儿”,能告诉她林中的秘密。但托勒妮几乎对任何事都持冷漠态度,特别令作者吃惊的是,当作者说她一定很了解林中的秘密时,托勒妮粗鲁地回绝了她。这实际上表明了托勒妮对外来者的抵制和还想以沉默来保留心灵中的最后一块净土。因为这儿森林实际上象征了印地安人世代相传之地,也是大自然的象征,而今天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不仅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且更重要的是造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毁灭。弱小民族在现代大工业文明与自然的冲突下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更易成为牺牲品,因为在挤压中变形的边缘人更难跨越时代和交流的鸿沟。
作者的父亲看来确是好人,但读者总感到他是她的医生和一位有钱人,他的视角是托勒妮患了骨结核,他应该帮助她。但他的帮助更像一种居高临下的恩惠,他并不能真正理解印地安人所处的文化边缘的困境。作者没有提及在钻石湖渡假时的治疗效果,这暗指印地安人的心灵创伤是无法治愈的。当年冬天作者的父亲因病去世更增添了一种无力回天的凄凉。
几年后当作者与托勒妮在一酒吧不期而遇时,她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会变化那么大,她从前那毫无表情的脸庞上呈现出一种可以算是极度的欢乐”,外貌也体现了她此时的心情,“她擦着鲜红的唇膏,头发剪短后烫成卷发,”虽然她不算漂亮,“但她那双黑色,稍稍斜视的眼睛却是美丽的;而且一条紧身裙和一件桔黄色套衫把她那柔软,苗条的身体衬得恰到好处,极令人羡慕”。读者不禁会问,既然托勒妮说她一生只碰上作者的父亲真正想帮助她,那么她如今的巨大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不容置疑,托勒妮少年时代的沉默多病更多的是源于被控制和压抑,更准确地说是源于一种边缘人的精神痛苦。而此时她就要嫁“一个英国小伙子,他不仅人长得帅,连名字都棒”。这是作者多年来唯一一次在“瞬间见到了她的真面目,她的目光中闪烁着一种令人害怕的渴望。”作者此时才能猜想到“她当年的需求一定是多么大呀!”此时的托勒妮似乎摆脱了过去,她那受压抑的心灵如飞向太空的云雀,尽情地享受着自由的空间。当然,这一自由实质上是一虚渺的海市蜃楼。当婚姻很快破裂后,托勒妮带着两个婴儿回到故乡。此时变得邋遢、酗酒的托勒妮实质上已是一具躯壳,她多年来的等待被证明只是一场梦幻,生命的意义已不可复得,精神已经消散,肉体还会久存吗?
传统文学中不乏描写少数民族妇女受压迫的情景,而劳伦斯跃出了这一传统描写重心的巢臼,突出了托勒妮在世代居住的土地上成了一个无法立足的边缘人的主题,其深刻含义可由几方面来解读。
首先是对“根”的理解。托勒妮的父辈们辛劳耕耘的土地上虽然没有西方文明的物质基础,但毕竟是世代相依繁衍的根基。当印地安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大民族文化的冲击下变得残缺不全而新的根基又无法构建时,作为边缘人怎样才能幸存下去成了托勒妮(这类人)难以回避的问题。少年时代的托勒妮先是以一种貌似冷漠的态度来对付外来文化的侵入。无论当作者是在赞美湖光美景时还是邀她同玩时,托勒妮总是漠然视之,甚至回答还带有敌意。这实质上体现了托勒妮失去“根”的恐惧感,因为此时的她太弱小,当传统的生命意义的座标已经消解时,剩下的似乎都是变幻的、流动的和难以捉摸的,她唯一的自我保护似乎只有像蜗牛一样龟缩在壳里,等待着那幻想中的解脱。
其次是有关“命运的主宰”的问题。在像《雾都孤儿》,《名利场》,《苔丝》这类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常由救世主般的好人或由魔鬼般的坏人所掌握,或由机缘和命运所规定。劳伦斯既批判了这类小说中截然分开的“好人”与“坏人”的不可信,也指出了个人的机缘和命运无法解读整个民族的命运。她从宏观上指出了西方文明构建的弊端,暗示了一个民族虽然牺牲了许多美好的东西,但还是可能无法摆脱其边缘困境,这实际上指出了整个西方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创伤:传统的中心的解构,整个世界的物化和人的异化处境。
第三是“身分”问题。托勒妮出身于处于边缘文化的印地安家庭,由于她希望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能得到主流文化的承认和接纳,她更渴望自己不明确的身分得到认同,因此她选择了一个女人似乎是最简单的途径——嫁人。她的丈夫是一个有工作,身分明确的英国人。劳伦斯完全抛弃了对托勒妮婚后生活的具体描写,而画龙点睛地由第三者讲出了其婚姻破裂这一结果。作者描述的托勒妮婚前和婚后外貌上的巨大反差是为了揭示当代西方文明对人的精神面貌的巨大影响,而不管托勒妮是美如天仙或丑如蛇蝎都是这种社会的产物,其外貌本身不应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
劳伦斯对妇女的从属地位体会很深,她认为传统的描述有太多的虚假成分和浪漫色彩,妇女以嫁人为出路实质上是不敢直面人生。在传统小说中,幸福的爱情或女性的平等多有虚幻或虚假的浪漫色彩,男女婚姻的美满与否多为社会地位和环境所左右。如受众人称赞的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就是一例:身为贵族时的罗契斯特向简·爱求婚失败,而当他身残破产后却赢得了简·爱的爱情。就这一点而论,19世纪的这类小说受到欢迎可以说是符合了读者的一种浪漫的心理需要。这种文本解读的印象是:女性在寻觅理想伴侣时,常关注其社会和心理需求,如果能获得一种成功和统治的地位(或这种地位的幻觉时),她们似乎就更有了吸引人的魅力。而劳伦斯深刻地指出,虽然托勒妮以嫁人跨入了白人文化圈,而且她的孩子已有了白人的血统,但这也不能表明她与白人文化的真正融合。已被异化的托勒妮虽然想永远地忘掉过去,但她毕竟部分保留了自己的种族记忆,文化积淀和反思能力。作为土生土长的印地安人,她曾生活在自己特定的文化氛围中,这种文化本身的积淀性是无法扬弃的,不存在颠覆性的逆转,因此她无法跨越历史和文化断裂的巨大鸿沟与白人文化同步。
第四是“自尊”的问题。作为一个民族生存的根基需要自尊,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兰顿的观点,〔3 〕人对自尊的渴望是一个基本需要,人对自己的评价具有生死存亡的重要性,而获取自尊就必须满足必要的条件。我们都体会到当一种身体的或心理的需要未被满足时,其结果对生物体有害。托勒妮特殊的处境也具有特殊的自尊心理需要。在学校读书时,托勒妮似乎并不是一个好学生。从她的出身来看,我们可以猜想她随白人孩子上学也算是政府给予印地安人的一种平等,而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很难考虑到印地安人的特殊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环境。托勒妮缺课的原因更多是出于心理上的而不是出于有残疾,因为她很难理解这种教育的价值。就如著名的美国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通过一位不识字的黑人母亲谈到她一位读过书的女儿时说:“那时她毫无怜悯地读书给我们听,把文字,谎言和其他人(指白人)的习惯和整个生活强加在我俩身上,而我和玛吉在她声音的控制下显得无知并处于被动。她灌输给我们的都是虚假谎言,以及大量我们不必了解的知识。她严肃地强迫我们听她读书,又正好在我俩像傻瓜一样,看上去似懂非懂时把我们挥之而去。”〔4〕这就是一位黑人母亲对白人教育“成果”的反应, 托勒妮的处境也是同样。接受教育按常规来看确是好事,但损害一个民族的自尊的教育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托勒妮的缺课是她心理上的第一次逃避,她想龟缩在壳里躲避可能面临的困境,实际上她是有意在压抑自己,禁止现实中的某些现象,观点和评价进入自己的知觉中。但逃避就是一种搅乱意识的恰当功能的行为,因为一个人越是回避他/她觉得想起来就痛苦的事实,他/她的心理障碍就越多。
当多年生活在自尊丧失的回避中之后,托勒妮真正的渴望终于展示出来了,这是她在认识了一个英国白人之后,她认为通过婚姻就可以摆脱困境获得自尊了。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另一次回避。因为人的自尊包括个人效力感和个人价值感。托勒妮满足自尊的方法不是去获得自我的效力或价值,也没有要求自己对自己的处境保持一种不屈不挠的理解愿望,她的结婚表面上是在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己处境的恐惧,实际上是在逃避现实,而对现实的回避最终可能导致死亡。
同样,真正的爱情也建立在自尊之上,在于双方的互敬、钦佩、看重,在于寻求精神上一致的人。人们发现跟价值和性格与自己相似的那些人交往更符合其利益。因此人对价值与他/她相同,行为方式对他/她的生存有利的那些人产生出亲切感或爱情,追求享受与另一个有生命的意识的相互影响、传情达意的感觉,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爱情的能见度的深度和广度。被爱的对象应体现自己高度评价的品质,是愉快的源泉。真诚的男女之爱是一个人所能贡献给另一个人最强烈的,积极的情感反映,其最重要的是能映射出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和最深层的自我观和生命现。由此可见,爱情的基础绝不能建立在依附上,可托勒妮嫁人的目的是出于摆脱自己身分不明的困境,而不是体现自身的价值。一位“金发”,“白皮肤”的丈夫使她脱离了世代相栖的土地,但又无法使她融汇于白人现代社会,即使她后来又到故乡,她已是一个失去了根基异化了的人。异化是劳伦斯涉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对托勒妮这个边缘人来说,世界和生命已双重异化,面对现实的裂变,她的精神走向偏移了传统轨迹,她已丧失了内在的自由和独立的生命意志,其意识已陷入迷乱。她嫁人的选择实质上指向了她的传统根基被连根拔起,她的归家也无法使她回复到其初始状态。
劳伦斯的文笔洗练浓缩,蕴藉含蓄,常借用恰当的象征物来烘托主题。她通过作者两次到钻石湖边的感受将一个民族的悲剧和人的生命的偶然性的一角向读者掀起。
“夜晚,月光在像黑色镜子一样的湖面上投下一条琥珀色光带,湖边密密地生长着高高的云杉,在寒空闪烁的星光下树枝投下清晰黑色的影子。此时,潜鸟开始鸣叫,它们从岸边的巢中像幻影般地飞起,向漆黑宁静的湖面飞去。没有人能够描述潜鸟的叫声,听见过这种叫声的人永远忘不了它。它们的叫声哀怨,还带有一种令人心寒的嘲讽,这种叫声属于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夏季别墅那整洁的天地和家里明亮的灯光有亿万年之遥……”。正如作者的父亲所说:“潜鸟一定在人类从未涉足此地时就是这样鸣叫的了”。在托勒妮去世后,作者又一次来到钻石湖边,“至少在晚上钻石湖看来与从前一样,它在黑暗中闪烁,在镜面般黑色的湖面上,月光投下了一条琥珀色的光带。今晚没有风,我周围是一片宁静,似乎太宁静了,然后我意识到潜鸟消失了。为了肯定了这一点,我又听了一会儿,但一点听不到那拖长了的,带有一些嘲讽和一些哀怨的叫声划破湖面的宁静。我不知道潜鸟的命运如何,或许它们已飞往某一遥远的归属之地,或许它们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已经死光了,不再关心生死问题了。我还记得当我和我父亲坐在湖边听着潜鸟的叫声时,托勒妮是怎样轻蔑地拒绝来湖边。现在我似乎意识到:以某种下意识和完全看不出来的方式,托勒妮毕竟可能是唯一的一位听见了潜鸟的哀鸣声的人。”
万籁俱寂,寒星横空,月光似水,万物似乎都在朦胧中凝固起来的景色给读者以丰富思维的空间,那琥珀色的月光千百万年来就一定是这样照耀着钻石湖面,它激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去思考过去自然状态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去体验一个遥远的,早已不属于我们的世界。此时,潜鸟开始鸣叫。那贯穿时空哀怨的叫声带有一种隐约可见的悲怆,更笼罩着一种浸人心灵的凄凉。这种令人战栗的鸣叫满载着业已逝去的远古时代的历史文化内涵并向读者暗示着一种文明的逐渐消亡。而最后潜鸟陨灭的轨迹是作为一种隐喻符号,暗合着托勒妮和印地安民族无法摆脱的命运。那消逝的潜鸟的鸣叫指向了一种生命,一种价值,一种文明从荣到枯直到消殒的底蕴。此时作者终于感受到当年托勒妮的一种本能的预见,这种本能超越了理性的表层而直透人的生命深处,是人性飘逝前最后的抗争。作者那心灵中难以忘却的潜鸟的叫声正如荒漠孤魂无望的呼喊,是对未来不幸的预感。读者在这种不可言说的静寂中总感到潜鸟那空谷足音般的鸣叫的余音依然不绝:文明不是没有代价的!
注释:
〔1〕《潜鸟》(The Loons)收在《诺顿短篇小说集》(英文版)1981年第二版,本文所有引文皆译自该书。
〔2〕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 (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二版第173页。
〔3〕Nathaniel Branden,The Psychology of Self-esteem,Nashedition 1969,Bantam edition,12th printing,1978.
〔4〕译自Alice Walker,Everyday Use,Norton Anthology ofShort Fiction,2nd edition,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