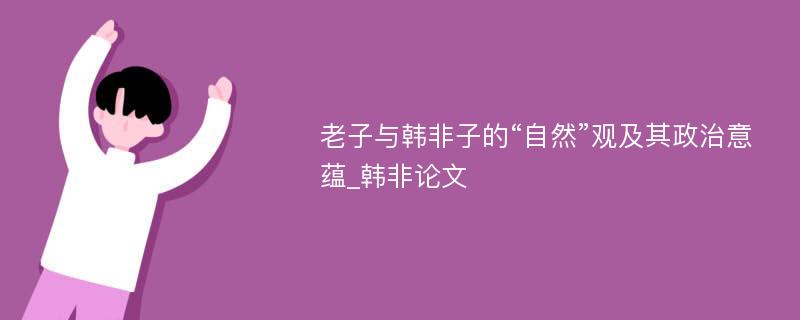
老子、韩非子的“自然”观念及其政治蕴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非子论文,老子论文,观念论文,自然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中图分类号:B223.1:B2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2-0080-007 韩非子之“自然”观念,不仅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存在深刻关联,而且与其人性论、政治观密不可分,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重视不足,张岱年先生所撰《中国古典哲学范畴要论》虽论及“自然”,但只论及老庄、汉儒及魏晋玄学,并未提及韩非子之观念。[1]534-537毋庸置疑,韩非子的思想深受老子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体现在“自然”观念层面又是怎样的呢?本文将在老子、韩非子思想之整体视野中考察“自然”观念的多重内涵,以期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和探讨。 一、老子“自然”观念及其政治寓意 “自然”一词,始见于《老子》,意为“自己如此”、“本来的情况”。现代汉语中以“自然”表示自然界广大的客观世界,源自魏晋时期的阮籍[1]534、536,而按照戴琏璋的说法,阮籍也“并非说自然是一至大的集合体”,进而认为“自然”指称自然界则更晚。[2]273刘笑敢进一步解释何谓“自己如此”,他说:“‘自己如此’的意思就是自然发生的,从事物本身的状态自然的延续、自然的变化。”并认为“先秦两汉,‘自然’从来没有指自然界。”[3]也有学者认为:“‘自然’讲的不过是宇宙万事万物原原本本的‘自己而然’、‘自身而然’罢了。”[4]日本学者认为:“不用借助他者的力量,而通过内在于其自身的活动,成为这样那样的情况,或者是这样那样的情况。”[5]542老子之“自然”观念,直接带来一个理论困惑:“自然”或“自己如此”背后潜藏之“第一推动力”又是什么呢?换言之,“自己如此”既是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起源追问(“自己”从哪里来),也是一种过程意义上的动态描述(“自己”如何按照自身的形态延续、变化),其背后都无法绕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自己如此”的动力何在?此动力究竟源自自身,还是源自外在之力?① 在老子那里,宇宙起源不成问题,万物起源也不成问题。《老子》第四十二章已说得很清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老子看来,万物皆起源于“道”,万物在起源问题上不能做到“自己如此”(“自然”),这与郭象“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的“独化”(《庄子·齐物论释》)理论相比,思路完全不同。②但是万物生成之后,是否就意味着万物脱离“道”而独立,其演变形态就完全取决于“自己”?“道”在“万物”的存在状态与演化过程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老子》第五十一章对此回答最为完整:“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一方面,“万物”之生育衣养有赖于“道”;另一方面,“道”对于自己所起之作用的态度却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第三十四章更直接点出“道”之所以成其为“道”的内在原因即在于虚怀若谷:“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因此,有学者将“道”与“万物”之关系描述为“动因的内在性与外因的间接性”,可谓精当:“道的概念所要求和保证的是大范围的整体的自然的和谐,即‘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而不是对行为个体的直接的强制的束缚,因此可以给每一个行为个体留下自由发展的空间。”[2]277、416需要特别强调者在于,老子“自然”之逻辑前提,实则离不开作为大环境、大背景的“道”之先在性。在此逻辑之下,“道”为“万物”之演化默默无闻地、不易察觉地提供着和谐完美的环境,以便“万物”能够以最佳状态向最佳方向演化。因此,万物“自己如此”的存在形态,其实是“道”之呵护(外)与“万物”之本性(内)之合力产物。“自然”在老子思想体系中始终存在两套话语,一方面,从实然视角观之,“道”生育衣养着世间万物,其先在性对于万物之演化具有根本性之决定作用,“万物”之和谐状态并非完全源自自身之“自然”;另一方面,从应然视角观之,“道”具有虚怀若谷之特性,主观上并不愿意夸大先在性之决定作用,而以一种谦逊之态度,将其归因于万物之“自然”。也就是说,万物背后不是没有一个动力源泉,只不过这个动力源泉比较谦虚、不愿居功而已。因此,老子对于万物之“自然”,与其说是一种事实,毋宁说是一种价值期待,犹如父母对于子女自立般的一种期待。 由此,可以看到老子思想中事实存在两种形态的“自然”,一种为“道”之“绝对自然”,一种为“万物”之“相对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表明,属于万物之“人”、“地”、“天”,最终都以效法“道”为依归,只有“道”才拥有自己作为自己依据的终极格位从而无所效法,“自然”是“道”的存在形态,只有“道”才不依赖任何外力而做到“绝对自然”。“万物”之“相对自然”,一方面固然与万物自身特性密切相关而“自己如此,另一方面这种“自己如此”又源自对“道”之“绝对自然”的模仿与效法。 老子之所以深究“自然”,其目的就在于阐述一种基本的政治原则:无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这说明老子的思想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清代学者魏源则直接点出《老子》经世、救世之用意:“《老子》,救世之书也。”[6]3按照老子的思路,体道之圣人,乃是“道”之代言人,能够洞彻“道”之“绝对自然”与“万物”之“相对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圣人治国时,一方面,为万民百姓的繁衍生息提供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又要效法“道”之谦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老子之无为,并非无所作为,乃是营造良好生存与发展环境之“无为”,承担呵护百姓之义务与责任,实则有为;主动放弃高高在上之权利意识与权力优越感(并非放弃实实在在的权力),实则无为。圣人的功能在于“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圣人在面对万物之生存形态时,只作为外因起辅助作用,而万物之所以如此的动力,应该来自自身特性,“相对自然”地变化发展。《老子》第二章明确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尤其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则完全依据“道”之原则来行事,始终作为一种最高的权威,犹如慈母一般,注视、呵护并辅助万物的演变。《老子》第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真正之“善治”或太上之治,乃是营造一种大环境,百姓自觉认可并且无法感知任何源自外在规则之约束和限制、充分享受秩序之内的自由。显然,此处之“自然”,亦非纯粹百姓完全自主之“绝对自然”,而是“道”辅助、关怀之下的“相对自然”。 老子之“自然”观念,其实隐含着一层未曾明言的逻辑:只有在“道”的辅助与呵护之下,“万物”之“相对自然”,才可能产生和谐、完美的结果,整个世间万物才会真正有序而自由地存在。问题在于,就社会治理领域而言,倘若失去“道”及“圣人”之辅助与呵护,完全按照百姓的意愿及潜质“绝对自然”,其结果将会怎样?人之“自然”,取决于人之特性。在老子眼里,人究竟具有怎样的特性?进一步的问题便是,人性倘若欲冲破“道”之自然秩序,“道”又该如何作为? 关于老子对人性的认识,徐复观说:“《老子》虽然没有性字,更没有性善的观念;但他所说的德,既等于后来所说的性;而德是道之一体;则他实际也认为人性是善的。”[7]314然而事实上老子对于人性的态度却并不乐观,他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老子》第五十三章)表明普通民众并不总是遵循理想化的基本准则,而是喜欢寻求更能满足自己需要的方法和途径。老子已经明确意识到,人类形形色色的欲望会导致丧失理智,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在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的同时,又不使人的心智成为物欲的奴隶。然而,普通百姓在面对欲望时根本无法淡定:“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既然人难以抵制“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田猎”、“难得之货”的诱惑,那么,百姓“自然”的结果,便是欲望的膨胀与泛滥,所谓“百姓皆注其耳目”(《老子》第四十九章),必然在欲望的驱使之下相互竞争、戕害以至于无序。 老子尽管认识到人若纯任“自然”的不良后果,但其处理方式却显得异常无力。《老子》第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净,天下将自定。”此处之“自化”即“自己如此”意义层面之“自然”。“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之观念,与《老子》第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思想是相通的。然而,“无为”似乎并不能直接导致“自化”之理想效果,相反,却呈“化而欲作”之趋势。之所以“欲作”,当然源自人之自身欲望驱使,其结果便是使得不依赖外在环境与规则的纯任“自化”或“自然”变得不再可能,放而强调“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问题在于,何谓“无名之朴”呢?刘笑敢的解释是:“‘镇之以无名之朴’是因为万物不满足于‘自化’,因而‘欲作’,即为更多的欲望驱使。一般的侯王就会用刑罚或兵刃镇压。但守无为之道的侯王则会用‘无名之朴’来‘镇’之,而无名之朴怎能真的有镇压的效果呢?无名之朴就是道,就是‘法自然’的原则的体现,所以,无名之朴的‘镇’实际是使人警醒,重新回到自然无为的立场上,化解大家的不满和过多的欲望。”[2]385如果“镇之以无名之朴”仅仅重复“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老子》第四十一章)、“我无为而民自化”(《老子》第五十七章)的思路,一味强调身教功效,希望借此引领人们领悟并模仿圣人,“使人警醒”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理想罢了,处理方式之无力,决定了结果之无效。 在如何“使人警醒”的问题上,老子除了“不言之教”外,亦时常依据人生体验,站在长者之立场对世人进行“言教”,告诫人们正确对待名利与生命的关系,要珍惜最本真的生命,不要为名利所惑,更不可因为名利而损坏自然生命:“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并谓欲望太多会给自己带来灾祸:“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 然而,潜移默化的“身教”也好,苦口婆心的“言教”也罢,老子基于长远视野而进行善恶祸福之因果推演及各种预言式的忠告,对于“人”受欲望作用之“自然”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对社会秩序的冲击、破坏,均无切实的效果。老子“辅万物之自然”的观念体现在政治领域,对于人类社会之秩序在“道”之辅助之下良性运行存在不切实际的理论期待,在如何有效应对人的欲望泛滥而破坏社会秩序问题上,承担“辅”之职责的“道”的监督及惩罚功能,探讨不足。当然,探讨不足,并不等于没有探讨。《老子》第七十四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司杀者,是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如何理解本章“大匠”之确指,历代注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天”,有人认为是“政府主管刑杀的部门”[2]697-698。但不管怎样,在老子思想体系之中,道及体道之圣人在“辅万物之自然”的同时,对于为“奇”者,对于规则与秩序的破坏者,的确具有某种惩戒的职责与义务,这也再次证明老子“百姓皆谓我自然”之“自然”,是“道”与“圣人”的一种不居功自傲的谦逊说法,而非实情。老子“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之政治理念以及“自然”理想,在韩非子那里得到了充分的继承与发扬。 二、韩非子之“自然”观念及其政治蕴含 老子以降,在“道法自然”层面,存在庄子与韩非子两个发展维度:一方面,庄子描述“吹万不同”时“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庄子·齐物论》)的观念被魏晋时期的郭象无限扩大为万物脱离“道”之主宰进而成为一种绝对自然③;另一方面,韩非子以道之权威性统摄万物,万物皆以道之法则为依归。近人陈柱说:“予以谓传老子之学者,莫善于庄周与韩非。”[8]1可谓一语中的。验之《韩非子》,《解老》、《喻老》诸篇实为最初注解《老子》之文本。就此而论,司马迁将老子与韩非子合传,并非没有道理。倘若立足“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之哲思,司马迁论及老韩关系时所谓“老子深远”的判断,或许有一定道理。然而,如果立足“如何辅万物之自然”之政治实践,韩非子跟老子比起来,则更显得切于实用与有效,并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这种复杂性表现在,韩非子赋予“自然”观念以“必然”的内涵,但同时又不忘情于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的“自然”价值,从而在“必然”的视野之中深化了“自然”的政治蕴含。 韩非子从发生学角度将人性基于生物属性之“自然”视为一种“必然”,同时,韩非子又在过程或趋势意义上力主外在力量对人性自然趋势及方向的干预。 就发生学角度而言,韩非子明确意识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为了生存,必然存在基本的生理需求,这既是人内在特性“自己如此”的结果,又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基本事实。韩非子指出:“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子·解老》),这种基于生理需求而产生的欲望,完全源自个体自身之“自然”,所以韩非子又将其视为“自为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显然,人对物欲的追求以及卑苦的规避,根源于阿伦特意义上的“肉体的绝对支配”,这是一种“必然性的绝对支配。每个人都能从他们最切身的体验中,不假思索地了解到”[9]48。由此,韩非子推导出人性趋利避害的特征:“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韩非子·难二》)“人情皆喜贵而恶贱”(《韩非子·难三》)。在韩非子看来,人趋利避害的生理欲望及心理特征,既是“自然”,又是“必然”。正因为韩非子将“自然”视为“必然”,所以他才深刻洞察到政治领域不可改变的必然法则,“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因技能则不急而自疾,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令,故曰明主。”(《韩非子·功名》)在此,所谓“天时”、“人心”、“技能”、“势位”,都是政治治理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而所谓“自然之道”,即为不得不如此的“必然之道”。 就过程或趋势角度来说,韩非子认为,除非像老聃那样的圣人一样自我约束内在的欲求从而“知足”,否则人的欲望无法真正得到满足。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百姓根本无法像老聃那样知足,因为人性根本就无法知足,“众人之所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韩非子·解老》)。既然如此,如果想以彻底满足民众欲望来实现社会治理,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身为君主,也未必能感到满足:“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韩非子·六反》)。人若凭借自身本性任其发展,势必导致欲望的膨胀与泛滥,从而导致社会失序与混乱。《韩非子·心度》篇谓:“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这与乃师荀子反对人性“自然”(即“顺是”)的思路(《荀子·性恶》)也是一脉相承的。职是之故,韩非子格外重视以“赏罚”为核心内涵的外在规则对于人性“自然”而形成的“必然”事实在趋势、方向上所具有的引导及惩戒功能。《韩非子·制分》说:“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八经》也谓:“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就发生学意义上的“自然”而论,韩非子将其视为一种必然如此的事实,认为这是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他主张“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的根本原因所在(《韩非子·显学》)。所谓“必然之道”之“必然”,亦即发生学意义上人性之“自然”。 不难发现,韩非子对“自然”内涵中“自己如此”的趋势预见,并未赋予老子意义上的价值,而是就事实而论,而“自己如此”之趋势,对社会来说亦具负面影响。因此,某种意义上说,韩非子具有“反自然”思想。熊十力就“因物自然”的观点对韩非子思想发表过一番议论:“圣人法天地自然之化,故不肯用私智而行独裁。其于万物也,有裁成,有辅相,皆因物而成之,因物而相之。倾者覆,栽者培,与夫并育、并行者,一皆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稍过。稍过,即将以己宰物,而物失其性矣。故不过。此圣人之所以为功于造化而使万物得所也。若乃乘几狂动者,不知法天地之化,将任己之偏见而固持之以统御万物,虽可制胜于一时,其害之中于无形而发于后者,将不可胜言。韩非、吕政是也。”[10]65-66从前文的分析来看,熊十力的判断似乎得到了印证,即韩非子具有明显的“反自然”思想。 然而,问题似乎并非如此简单。章太炎谓:“夫法家者,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与行己者绝异。”[11]535显然,在韩非子或法家是否强调“自然”的问题上,熊十力与章太炎的观点截然相反。那么,又该如何看待二人的观点分歧呢?笔者以为,二人观点均有可取之处,又各有不足。 首先,韩非子的“反自然”思想表明他并不认同“自己如此”意义上的“自然”。最典型的证据,就是《韩非子·难势篇》将“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相提并论,主张如果一味谈论势之“自然”,其实就没必要谈论“势”,因为只需全任“势”之自然演化即可:“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究竟何谓“自然之势”?韩非子有详细的阐述,他说:“今曰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吾非以尧、桀为不然也。虽然,非一人之所得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按照韩非子的理解,在人类治乱的趋势问题层面,圣贤在位,社会一定大治;暴君在位,社会必定大乱。这种体现在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上的“自己如此”,就是“自然之势”。熊十力将韩非子的“自然之势”解释为人力无法更改的“天下大势之所趋”,是非常有说服力的④。在此,“自然之势”,即为“必然之势”。趋势的必然性,一方面容易导致宿命,另一方面又因其固有的极端思维方式忽略了社会演变进程中的人为努力因素,因为真正主导人类社会演进的主体不在少数圣贤或暴君,而在“中人”(普通人)。韩非子的“中人”政治思维,开启了依靠制度与规则来进行社会治理的政治学思路。他说:“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韩非子·难势》)韩非子在社会治理层面并不措意于那些没有悬念的趋势或结果,他念兹在兹的,是如何通过人为的努力,在人类社会多种演变可能性中,用后天的干预去创造一个最佳可能,从而实现社会的秩序和谐。这就是他所谓“人设之势”,所谓“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就人性“自然”之趋势而言,韩非子并未主张人性千篇一律,而是强调绝大多数人如此。在韩非子看来,人群由“不可以赏劝”的太上之士如许由、尧、舜等圣贤,“不可以刑禁”的太下之士如盗跖和普通民众三部分组成。治国的基础,应该正视太上之士与太下之士均不占多数的事实,从而认定绝大多数人“劝之以赏然后可进”、“畏之以罚然后不敢退”。“太上之士”的自我克制与“太下之士”的绝对放任,都不在韩非子“人设之势”的考虑之内,“国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为量”。治国应该考虑人性趋利避害的恒常状态,“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韩非子·忠孝》)。毋庸置疑,在过程、趋势层面,韩非子力主干涉,具有强烈的“反自然”的思想特征。韩非子以“赏罚”为核心内涵的外在规则,亦即“抱法处势”之“人设之势”,主张以人为的主观努力引导人性“自然”的合理成分,规避其突破社会秩序的不合理因素。梁启超认为法家“政治论主张严格的干涉”[12]78,确有道理。 其次,韩非子“反自然”的“干涉”思想,与章太炎“夫法家者,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与行己者绝异”的判断亦不相矛盾。如此说的依据在于,韩非子强化了老子“道”对万物生衍的呵护功能,主张以强制性的规则和制度(“法”)来对人们的“自然”(自己如此)本性加以干预与引导,最终实现强制规则的内在化,形成一种“第二自然”的生存方式。唯有在理想化了的“第二自然”视域中,韩非子与老子才能在“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层面具有思想共通性。 《韩非子·安危》:“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尽力于权衡,以动则胜,以静则安。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国家久安。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今使人去饥寒,虽贲、育不能行;废自然,虽顺道而不立。”在此,韩非子描述了理想状态的“法”之性质,不使人感到约束与压迫,服从外在法则,就像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一样,就像服从自己内在真实意愿一样。之所以能够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法”满足了人们“乐生”、“爱身”的真实意愿。日本学者认为:“在这里所见的二例‘自然’,就是对于作为主体的‘上’也就是君主来说,作为客体的‘人’也就是民众的‘自然’,具体的是指被代表为‘饥而食,寒而衣’的‘民’的存在方式。”[5]541在此,韩非子显然呼应了老子“自己如此”的“自然”价值,并且在理想社会状态下予以认可。 《韩非子·说疑》亦谓:“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此处观念直接源自《老子》第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韩非子认为,禁奸的最高境界,就是让百姓在思想深处根本不产生任何奸邪的念头,完全按照制度规定的是非观念来为人处世。所谓“太上禁其心”,即是将外在的客观规范内在化,成为一种“日用而不知”的“自然”行为,亦即“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禁其心”的最终目的,实则“不治”,“不治”即老子之“下知有之”,亦即“百姓皆谓我自然”,这是一种以外在规则为基础的“自然”。这是一种政治理想和价值期待,君主存在,规则亦存在,但由于外在的规则已经完全内化为自身的实际意愿,故而可以实现“自然”的生活。显然,此处之“自然”,实则“第二自然”⑤。当然,按照福柯的“规训”理论,这毫无疑问属于一种压迫与洗脑。然而,正如福柯的理论虽具深刻的批判意识却无法完全“解构”现代社会一样,规训、内化某些外在规则,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无法避免的一个基本事实。也就是说,完全按照社会个体不加“熏染”的“绝对自然”意识行事,无论在事实与理论上均不可行。就此而论,韩非子从思想与观念层面入手,让百姓真正信仰具有是非、善恶价值的客观规范,并以此作为实现良好社会的最好方法,这个观点实则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刘笑敢在评论老子“自然”观念时说:“在现代社会,要维持自然的秩序,法律是绝不可少的,然而,法律的功能对多数人来说,可能只是虚悬一格。”[2]216其实,“虚悬一格”的法律功能,可能更符合韩非子的政治理想。 综上,韩非子的“自然”观念具有复杂的内涵。他将人性之“自然”视为一种“必然”,一种规律,一种无可回避的事实,据此主张治国应以此“必然性”为基础与前提。一方面要顺应并满足人们对于利益的需求和渴望,另一方面又对人性“自己如此”的欲望膨胀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主张以外在的强制性规则加以约束和规避,由此形成了“反自然”思想。同时,韩非子虽然不主张“尧舜”这样的圣贤在位而形成的“势治者不可乱”,但是他本身对于通过人为努力营造“大治之势”,进而不依靠圣贤亦能产生“势治者不可乱”之效果,充满了狂热的理论期待。他在理想社会中赋予了“自然”以“自己如此”的意味,强调规则治理之下理想状态中人们行为的自然,具有“消极自由”的意味。梁启超如此批评韩非子将“自然”转换为“必然”之观念:“彼宗最大目的,在‘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此误用自然界之理法以解人事也。‘必然’云者,谓有一成不变之因果律为之支配吾侪可以预料其将来,持左券以责后效。如一加一必为二,轻养二合必为水也。夫有‘必然’则无自由,有自由则无‘必然’。两者不并立也。物理为‘必然法则’之领土,人生为自由意志之领土,求‘必然’于人生,盖不可得,得之则戕人生亦甚矣。此义固非唯物观之法家所能梦见也。”[12]192倘若结合韩非子的“自然”思想来看,梁氏实则误会了韩非子在发生学意义上理解的作为治国基础的“自然”(必然)与理想社会状态中的“自然”(自己如此)的区分,尤其未能洞彻韩非子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始终存在的“道”与“法”对人们“自然”的呵护与观照。韩非子与老子不同之处在于,老子的“自然”体现了一种价值,而在韩非子那里,“自然”是一种治国必须尊重与遵循的事实。并且,韩非子在更高意义上回应了“自然”的价值,将老子“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政治理想加以了制度化的改造与创新。 ①刘笑敢认为:“自然的概念大体涉及行为主体(或存在主体)与外在环境、外在力量的关系问题,以及行为主体在时间、历史的演化中的状态问题。”参阅刘氏著:《老子古今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②有学者恰恰用郭象的“独化”理论来理解老子之“自然”观念:“‘自然’应当在‘本然’的意义上来理解。天地间万事万物,形形色色,仪态万千,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原原本本的生成方式和存在、发展的途径。……所以‘自然’作为‘自己而然’所强调的首先就是这种存在的独特性与无可替代性。”王庆节:《老子的自然观念:自我的自己而然与他者的自己而然》,《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 ③需要指出,庄子“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的相对主义观念依然受制于“道通为一”的思想,从而对普遍性亦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参阅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111页。 ④熊十力:《韩非子评论·与友人论张江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刘笑敢亦曾区分“自然”概念在时间序列上的稳定性:“自己如此”(原初状态)、“通常如此”(现在状态)、“势当如此”(未来趋势)。参阅刘氏著:《老子古今上卷》,第292页。 ⑤西方汉学家阿尔伯特·盖尔万尼《超越规则的统治:〈韩非子〉最高权力之基础》一文运用福柯的规训思想来解读《韩非子》,认为韩非子运用赏罚,其最终的理想就在于将各种规则由外在强制内化为人的自觉意识,并提出“第二自然”的概念来描述韩非子的法治理想。Albert Galvany,Beyond the Rule of Rules:The Foundations of Sovereign Power in the Han Feizi,Goldin,Paul R.(Ed.),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an Fei,Spriger,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