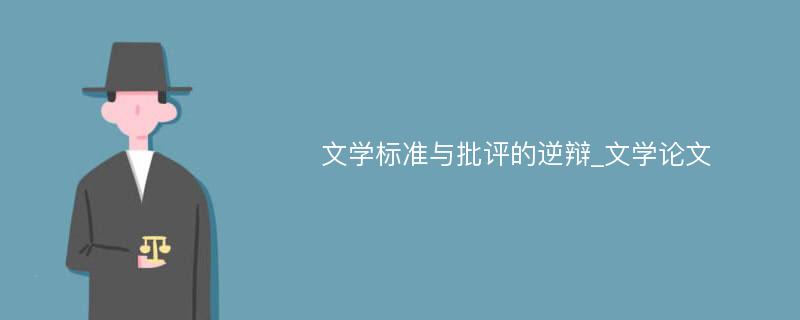
文学准则与批评的逆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准则论文,批评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钟山》今年第一期发表了一篇“对话录”,几位追逐热潮的作家、评论家谈“历史转型与知识分子定位”。迄今,在文坛引起众说纷纭。由此我想起爱尔兰诗人叶芝(W.B.Yeats)在“政治”(Politics )这首诗中引用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一句话:“当今, 对人存在的目的作意义的陈述时,常出之以政治性的语汇。”这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论断,但环顾时下论坛,对这位中国当代作家而言,苟同者恐怕寥寥无几,因为“对话录”中不少的话语,已臣属于政治之下进行“政治旋涡中的危险”的人身攻击了。
“对话录”恭维一陈刘心武为“‘伤痕文学’之父”后,便得利于收集有关旷野经验和各样散佚的传说,目的在于要征得政治光环。在这里,似乎批评的概念不属于文学的范畴,而是一种政治类别。对文学的准则,似乎要进行全新的、激进的诠释。在许多的论调里暗指文学准则若非不存在,便是相对的无关宏旨。“对话录”可能引起不同效果,自然持有特定的厉害考虑。他们在评价中各取所需,利害互见,认知本质、逻辑地位、美学判断都在所选择的政治观点中打转。他们全部拥护的批评信条是刻意使文学卷入“政治旋涡”,文学的准则变得子虚乌有,完全无视文学中的道德动机,这才是“危险”的。如果文学准则被这些作家、批评家所暗示的不过是一种幻影,当代理论、文评或隐或显,经常拥抱政治“炒作”,那才是“并不是在真正地从事文学”了。
“对话录”中说张承志扮的是“教主”、“教宗”,“一个大群体的发言人”,“向内寻求感情”“自我膜拜”,“皈依到宗教”,“原红旨”,终于找到“哲合忍那”,皈依“沙沟派”……这些所思所言,决非无涉于任何意识形态,也不是申扬一种特定的神学信念。所能传达和捍卫的是取代文学准则的“权利斗争”和“权利资本”,是用“历史转型与知识分子定位”而充分认定张承志那些“非文学性著作”。把这些定义不彰和无关宏旨的概念归纳于“直接为权利斗争服务”,这就一竿子打落了所有文学和美学准则的理念。
“对话录”接着说张承志是“红卫兵这个符码的发明者”,是“原旨红卫兵”、“对现实不满”,于是苦闷、孤独地走向“荒芜英雄路”(张文章的题目竟也可作为打击的目标!),“用文学创作来抒发他的焦虑和苦闷”。奚落了一番张承志在清华附中的经历之后颇带嘲讽地说:“把张承志他们‘凉拌’了”,“张承志他们早就被抛到边缘的边缘了”。任何理论或实践,最主要的危险莫过于在其所选择的或隐或显的立场上,企图把传闻和历史加诸于文学背后所持的理念,这大概就是“对话录”所说的“复杂的文化心态”吧?
我们何尝不需要从过去撷取相异的见识,以避免重复同样的愚顽?何况批评理论看来的确像是一部充满愚顽的历史,也是一部充满反讽的历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把思路引向当代的文学准则,寻找曾经用过的那种认知事物的理论。在杂乱无章的逆辩中,很多事物被强力压倒,有些竟全然被漠视或歪曲,像是必不可少的复光反照,在充满舞台趣味的政治攻击诱导原则中,虚拟新的批评支点。
进而说张举起了“清洁”的旗帜,“以笔为旗”,这是“‘一次性全盘解决’的乌托邦欲求”,是“产生极端主义的温床”,并说“清洁、污染的概念都是希特勒的东西”。一个文学座谈会上,由一个作家主讲另一个并不在场的作家这么多“问题”,实属非“伤痕”时期以来文坛所仅见!满怀抱负的批评家不妨看看,“对话录”令任何雄心万丈的人都会感到气馁。在激烈的专业竞争中为自己闯出一片天地,可行的途径之一似乎就,是把住一种逆辩的语言,把它运用到某一点小事上或是道听途说的传闻上,这样才能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尽管这个作家用来表达文学突现的歧异观念的语言是以新的“寓言”出现,但这似乎是一种讯号,表现某种对文学准则的修正即将发生。
我们再引用英国批评家波普(Alexander Pope)的话:“在别人身上褒扬自己,文人的党派常拌随着政治的派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