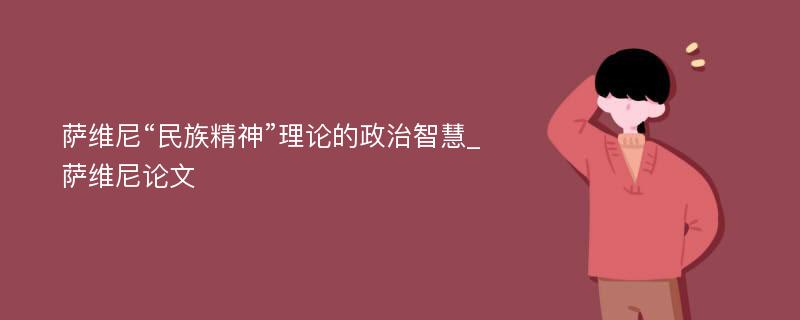
萨维尼“民族精神”说的政治智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精神论文,维尼论文,智慧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09)06-0042-07
一、传统误解:对萨维尼“民族精神”说缺乏政治考量
1814年,“作为自己祖国的一介热心竭诚之友”,在爱国热情的鼓动下,蒂堡奋笔疾书,14天内便写出了《论制定一部统一的德国民法典的必要性》一文(该文更为恰当的翻译应为《论制定一部统一的德意志民法典的必要性》,因为在1871年1月18日以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德国。不过,为了尊重译者,笔者在行文中,遇有类似情况,仍旧照抄为“德国”)。文中倡言仿照《法国民法典》,在三四年的时间内,经由“举国一致”的努力,为德国制定一部综合性的法典,并借由法制的统一,继而达成德国国族的统一乃至德意志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最终建立[1]80。
时执教柏林大学并担任普鲁士皇室王子罗马法、刑法与普鲁士法教师[1]308的萨维尼,同年10月[1]345以《论立法和法学的当代使命》一文批驳蒂堡,旗帜鲜明地反对在当时立法。萨维尼的主要观点是:法律如同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法律家是民族精神的反映机;立法需要很高的法学水平,而当时德意志还没有这样伟大的法学家堪此重任,所以制定一部伟大法典的时机尚不成熟。他的这本小书被认为是历史法学的起点[1]19,[2]。
就笔者的阅读范围观之,对萨维尼“民族精神”说的评论,皆是围绕法律到底是不是民族精神的争论,不够深入。
黑格尔认为:“否认一个国家的法学家有法典编纂的能力是对这一国家法学界的侮辱。”[1]176
马克思认为萨维尼的观点是为现存统治阶级张目。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将历史法学派批判为“用昨天的卑劣行径来证明今天的卑劣行径为合法的学说”。“一旦皮鞭被认为是世代相传的”,它就能够“将女奴对皮鞭的反抗称为背叛”。马克思对法律渊源的结论是:习惯法只能用于预知新的制定法,只能作为穷人和受压迫者反抗特权阶层制定的现行法的工具[3]。
在庞德看来,萨维尼的学说“主要还是在对立法化和法典化时期,也就是哲学统治趋于终结的时期的自然法学派的立法理论作出反叛”[4],[1]260。
博登海默在《法理学》中指出:“历史法学派的理论与古典的自然法哲学家的理论是尖锐对立的。后者认为,只要诉诸人的理性,人们就会发现法律规则,并能制定法典;而前者却厌恶制定法,强调非理性的根植于久远传统之中的几乎是神秘的‘民族精神’的法;前者认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同的,而后者却认为法律制度具有显著的民族特性(亦即非常强调法律的差异性——引者注);前者面向未来,而后者‘作为一种反对革命的理论’面向过去。”在政治上,博登海默还认为,“萨维尼是一个憎恨法国大革命平等理性主义的保守贵族”、“一个反对法兰西世界主义理论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1]229。
有的学者甚至用纳粹曾把“民族精神”作为法学理论的重要源泉之一,来批评萨维尼,认为正是他的遗毒“资助”了纳粹的歪理邪说[5]67。
也有学者用后来埃及、日本、土耳其直接移植外国民法典并在一定程度上还算成功的事例,来反驳萨维尼提出的“民族精神”说,认为萨维尼过高估计了习惯法的重要性以及铲除它的危险性;认为萨维尼的判断已经被后来的法律发展史证伪了[1]333-337。
当下中国学者一般比较认同萨维尼的观点,认为“民族精神”说很有见地,发现了法律的真正本质,而蒂堡则显得比较轻率[1]83;也有学者把萨维尼与蒂堡的争论放在整个德意志当时的思想源流中考虑,认为蒂堡代表了18世纪以来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理性主义思潮,而萨维尼代表了德意志崇尚精神意志的浪漫主义,“民族精神”概念的后面站着谢林、赫尔德、歌德等浪漫主义文化运动的天王[1]172-176。
笔者认为,以上学者大都就事论事,即把萨维尼的观点仅仅当作一种法学思想来对待,而较少顾及彼时彼地状况,未把萨维尼的观点放在当时的语境中作总体把握,当然也无从发现萨维尼这个提法的策略因素。如果把“民族精神”说的大致缘起与当时德国的总体状况综合起来考虑,就有可能发现新的东西。
二、蒂堡和萨维尼:一样的目的,不同的手段
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的颓势,以及1813年反法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给老德意志帝国注入了重新崛起的希望。拿破仑战争之后,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当时许多德意志人的愿望[6]。
蒂堡和萨维尼也热衷于这一理想。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萨维尼明确表示与蒂堡在运用立法手段促进德国统一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所追求的目的乃是一致的:我们都渴望拥有一个坚实的法律制度,以抵御任意专擅与伪善兮兮对于我们的伤害;再者,我们都寻求国族的统一与团结,专心致志于秉持统一目标的科学研究。”[7]121,[8]
作为法学家,对于他们而言,德意志的分裂特别刺眼地表现为法域过多。1907年,王宠惠论及这一问题(这一年,他英译了《德国民法典》,该译本在英语世界影响甚广,沿用至今):
根据德国司法部给国会提供的信息,从司法的角度德国可划分如下:
(1)在德国的中心,有一片极广大的区域,从阿尔卑斯山延伸到波罗的海,从威悉河到易北河,从德国西南部之山林地区到波西米亚,包括1650万人口。这个区域适用普通法(Gemeines Recht),也就是继受的罗马习惯法,以及大量古老的地方法、城市法、特权法与成文法。
(2)在普鲁士,有2120万人口,普遍适用1794年的普鲁士法典。
(3)在莱茵河省,有670万人口,适用1804年的拿破仑民法典,另有170万居民适用1809年的巴登法典。
(4)在萨克森,有350万人口,适用1863年的萨克森民法典。
(5)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有1.5万人口,适用1683年的丹麦法。
(6)在巴伐利亚的一小部分地区,有不到2500人,适用1811年的埃斯特帝国民法典。
上述这些法律分别用德文、法文、希腊文、拉丁文、丹麦文记录下来。更为复杂的是,每一种体系都随着各地的地方法和习惯法的变迁而变化[9]。
怎样从法学的角度对德意志的统一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萨维尼和蒂堡的共同之处;然而,他们的手段各不相同。
蒂堡认为编纂民法典能够促进德意志统一。在《论制定一部统一的德国民法典的必要性》一文中,蒂堡对德意志私法状况进行了批评,主张对当时德意志民法进行彻底变革,德意志各邦通力合作起草一部通行于德意志的法典,以取代现在各邦在这一领域自行其是的状况,使德意志人民享受幸福的市民生活。蒂堡批驳了支持罗马法的观点,认为罗马法在当时已经不能适应德意志的要求,有很多弊病;论证了一部简明法典的诸多优点,反驳了反对进行法典编撰的意见。在学术层面,蒂堡一一反驳了民族精神理论、强调法的差异性理论和崇拜传统的心理,并论述了当前编纂法典的诸多有利条件[10],[1]180-187。
萨维尼则针锋相对地认为暂时搁置立法才能促进德意志统一。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一文中,萨维尼分别对法的起源和法典的性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推动法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来自民族内部的、无声无息地在潜移默化之中发挥作用的力量;决定法的发展的内在力量是民族精神,立法者不能发号施令。一部普通的、一般化的法典将是以后的法的唯一的渊源,法典将取代在其之前有效的一切其他法的渊源。萨维尼大赞罗马法,认为罗马法是唯一的由一个伟大的古代民族在一千多年的进程中一直不断加以发展、完善和改进的法律。他认为,拿破仑民法典、奥地利民法典和普鲁士民法典这三部现有的法典都不具备一统天下的能力。萨维尼指出,德意志法学和立法的当代使命是“清算占据统治地位的理想主义法学思想”[7]188-189。
三、比较:萨维尼与蒂堡各自主张的可行性
十九世纪上半叶尚无统一的“德国”。明确地说,在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加冕为德国皇帝之前,并不存在一个在法权上统一的民族国家——德国;甚至连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也还是问题。当时各邦都是主权国家,没有谁的主权更高。1815年虽然成立了德意志联盟,但三十多个君主制的邦都拥有绝对的主权,其中最大的邦和最小的邦一样都是主权国家[11]。虽然联盟条例第19条规定各邦将来在贸易和交通方面“采取一致行动”,但实际上谁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独立的税收和商业政策[12]88-89。
1815年,在“荣誉、自由、祖国”的宗旨下,耶拿大学学生率先成立了“全德学生社团”,并迅即在其他大学得到仿效。当时耶拿学生社团的目标很明确,即“希望德意志能被视为一个国家,德意志民族能被视为一个民族”[12]88-89。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不但那时德意志不是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且连是不是同一个民族,也还是一件要有知识、有理想的热血青年倡议跟鼓动的事。
总之,当时德意志地区的现实是分裂,而人们希望统一,但还仅仅是希望。越是希望统一,就越是要珍视一切能够促进统一的因素,防范一切不利因素。
(一)蒂堡的仓促立法主张显然是热情有余而务实不足
蒂堡认为,出于利益考虑,反对在当时德意志编纂法典的意见有:①一部统一的法典将剥夺各邦王公的权力并限制其自由;②在这样复杂的时期应避免进行任何改革;③对于法律体系的改革会扰动人民、刺激舆论,导致在德国发生类似于法国的事情。蒂堡为了打消德国各邦统治阶层的疑虑,反复重申,这一法典编纂只限于民法领域,而不涉及公共法律领域,比如与财政、经济、警察有关的法律都不属于这一领域,因此很难说王公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同时,蒂堡为了否认在德意志可能发生法国式的革命,不惜笔墨地对德意志王公贵族、对人民对传统宪法(亦即君主制)的珍爱以及对王公的忠诚大唱赞歌[1]185。
笔者认为蒂堡列举的反对意见并不是当时编纂法典的最大困难,他的反驳和妥协亦未击中要害,因为在当时的德意志,如果仓促编纂法典更有可能催化分裂,而非助推统一。
1.国家尚未统一,遑论制定统一适用的法典
虽然德意志在当时还是一个地理概念,但蒂堡认为德意志人民当时的民族认同感空前强烈,相互之间充满友爱精神,没有敌对意识,十分有利于一部新法典的制定[1]187。显然,蒂堡的主张理想成份太重。立法,尤其是编纂意在代替罗马法传统的民法典,实际上是一个彰显政权实力的机会,而且带有很强的公共政策选择意味。立法没有公认的权威,仅仅靠某种心理状态,是很不稳妥的。甚至,蒂堡的立法蓝图隐含了危险,即把冷峻的现实过度理想化,不顾现实中力量对比的强弱,只片面强调希求的结果,没有看到可能出现的危险。立法,尤其是立关键的大法,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大事,更是政治上的大事,它要考虑的,首先是防止出现危险,而不是一味地往好处想。
立法活动一旦开始,权威便注入其中。立法活动不能像自然科学做试验那样,仅仅考虑物质损耗,遇到失败便随即停止,有时即使失败了,立法活动也不能随便停止,甚至明明失败了,还要说成功了,因为权威要表现得无往而不胜。对于权威而言,失败似乎从来都不可能限制在当权者划定的区域或范围。立法活动一旦启动,失败就会大幅度损害权威,进而波及政治。这就要求必须谨慎对待立法活动,假如没有十足的把握,就不能随便启动。在蒂堡的语境下,如果德意志人民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团结、那么友爱,而是同床异梦、各有所思,那么,他的过高估量,无异于为一次立法失败做好了铺垫。
2.新民法典的适用需要其他邦国放弃主权
实际上,并非蒂堡说的那样,如果一部法律仅仅关系到民法领域,不涉及公共法律领域,就不伤害一个法域中的主权者利益,主权者就可以不管。必须明确,立法和司法都是公权力天生的重要职能,司法中适用什么法律,从来就是国家主权的重要象征。只要主权还存在,它就要尽量在自己领有的空间中充塞自己的法律。如果随便同意使用其他公权力的立法,或者随便允许其他公权力在自己的领地内司法,其实就是向这个公权力割让自己的主权范围,甚至就是俯首称臣。在这种情况下,主权者是不可能放任不管的。因为对于任何当权者来说,适用什么法律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直接关涉公权力有无恪尽职守、有无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那里,再上溯,甚而至于会关系到一个政权有无合法性的问题。所以,任何公权力都不可能在适用异邦法这个关涉主权的问题上随便让步。
在主权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个统一的德国还不存在乃至于主权诸邦林立的情况下,仅仅信赖什么“民族认同感”就认为能够实现法律的统一,是很天真的。一个志在统一德意志的法律制定出来,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无论这部法律多么精湛完美,但如果诸邦各有私心,基于维护自己的主权而有意不予援引,又有什么力量可以强迫他们呢?这时候,“民族认同感”还能派上用场吗?
一部法的编纂和推行肯定要有一个背后的力量。在当时德意志的情况下,不能天真地设想会有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力量来编纂这部法并在司法中运用它。这恰好与有能力统一德意志的力量是一样的。
假设普鲁士编纂了志在通行德意志的法典,但由于当时德意志所处的分裂状况,便会出现有的邦选用而有的邦不用的状况,从而造成与其初衷大相径庭的后果,即这部法典意在统一德意志、意在表现普鲁士的力量,但却因为各个邦的不配合而分裂了德意志,让普鲁士显得外强中干,所以立法活动是很危险的。
3.新法典会破坏德意志地区的共同法——罗马法
萨维尼强调,一部普通的、一般化的法典将是以后的法的唯一渊源,法典将取代在其之前有效的一切其他法的渊源[1]191。法典在建设一个新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实际上也是它对旧世界的巨大破坏力。那么,在当时编纂德意志统一民法典会破坏些什么呢?
中世纪罗马法复兴以后,在德意志地区,罗马法渐渐成为普通法[1]180。虽然各邦的罗马法不尽相同,但都尊崇优士丁尼系列法典。这样,罗马法实际上成了凝聚德意志各地区的重要力量,成了能够促成德意志统一的重要力量。
而蒂堡建议的这部新法典,恰恰是要代替罗马法在德意志的地位。新法典的力量不那么可靠,却要德意志先脱离起到重要粘连作用的罗马法,弄不好会造成“法治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的弊端却先发生了”[13]的局面,这对于图谋统一的德意志是非常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加深理解萨维尼为什么会倾毕生心血研究罗马法。罗马法不仅仅是学术的古代源头,对于德意志而言,罗马法就意味着统一)。对于这种代价,蒂堡甚至完全没有看到,他就认为,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典对于德意志每个邦国所造成的花费不大可能高过供养几个女演员[5]72。
从当时德意志并不统一、甚至连有没有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也并不是一个定论的情况来看,这时贸然依靠理想编纂法典,显得很不务实;殊不知,这种对待立法的超越现实的浪漫态度,反而会破坏已有的统一因素,造成分裂。
(二)萨维尼的伟大之处在于阻止了浪漫而危险的法律实践
一般认为,在与蒂堡的论战中,萨维尼的贡献在于其提出了“民族精神”说,但略略考察之,就会发现“民族精神”说有两处软肋:一是萨维尼推崇的是罗马法。萨维尼提倡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但是德意志人是日耳曼人,按照他的说法,似乎更应该如艾希霍恩一样经由“民族精神”而推崇日耳曼法,而不是推崇从异族那里译介来的罗马法。萨维尼几乎不研究德意志本身的习惯法以及固有法传统,而以罗马法为唯一的研究对象,把罗马法当作了一个自足的完美整体。萨维尼之后的潘德克顿学派也有同样的倾向[1]178。通常认为这是萨维尼思想上的断裂[14]。二是其论述后继无人。令人奇怪的是,“随着182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的逝去,萨维尼对于他的信徒和弟子们的‘直接影响’,最晚终结于1890年前后”[1]359。后来德意志帝国统一以后,距离最初的辩论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而在实际进行德国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并没有听到什么反对的声音。发生的争论也主要是关于法典编纂的实际技术性问题[1]178。
如果认为萨维尼作为一位伟大的法学家,其伟大的成就之一就在于他论述了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发现了这个法律规则的普世真理的话,那么,上面这两点就很不好解释,似乎观点的提出者本人并没有尽力推进这个观点,而且在本国影响时间也比较短,仅此而已。
诚如上述,按照蒂堡的建议是很危险的,能阻止这种浪漫而危险的蓝图,本身就是伟大的。所以笔者认为“民族精神”说在后世的衰落,并不能证明萨维尼论说的价值就不高,他提出的“民族精神”说的客观价值要远远高于其学理上的价值。萨维尼的伟大并不是因为他提出了某个法律观点本身,而是他在恰当的时候,用一套说辞阻止了堂而皇之的激情,有效防止了一次不可逆转的立法实验的发生。
结合萨维尼的处境,人们或许更能理解这一点。1812年被普鲁士国王任命为柏林大学校长可以认为是萨维尼进入普鲁士王国话语精英阶层的标志,因为柏林大学由普鲁士国王全力支持并筹建,有很强的民族国家意蕴[15]。自此以后,萨维尼一边学术大进,一边平步青云历任要职。1814年著《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1815年与艾希霍恩、格舍恩合编的《历史法学杂志》创刊,使得柏林成为德国法学中心。1817年任普鲁士枢密院法律委员,1819年任莱茵州控诉法院兼上诉审核院的“枢密法律顾问”。1835年他开始着手撰写《当代罗马法体系》。1842年,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任命为国务兼司法大臣,承担立法审核的工作。任大臣期间,萨维尼在政治上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因为他是内阁中一个“优柔寡断的法比乌斯·库克塔托(库克塔托在战争中实施战略极其慎重,人们便用其名字讽刺那些优柔寡断的人。但事实上由于法比乌斯·库克塔托在战争中大智大勇、沉着应战连获成功,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1847年,萨维尼被任命为内阁主席,负责枢密院及行政厅。1848年3月大革命爆发,他与其他大臣一起辞职。1856年,被任命为皇家律师,1859年又被任命为贵族院议员[5]68,[1]294。因为萨维尼所处的位置,他不能随便说普鲁士立了法就万事大吉了,别的邦可能会不理会普鲁士的权威和引领。这等于在法权上折损普鲁士的豪气和“天命”,这不符合普鲁士王国自命德意志霸主的主流政治话语。如果注意到萨维尼后来的荣显,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或许正是因为他在论说上的巧妙、结论上的中庸并充满政治智慧,才使得他为普鲁士王国所看重。他的论说,适应了那个时代德意志的现状,但又没有打击普鲁士的憧憬,所以才能在争论中捞得政治资本,他1814年著《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之后的平步青云本身就证明了普鲁士高层看重的,不仅仅是他的学术实力,更是他的政治家才能(比如“国务兼司法大臣”一职可能就更需政治家才能)。
所以,笔者认为,和萨维尼争论法律到底是不是民族精神,其实并没有太理解他的处境,也没有理解他文字背后的深意。那种认为后来德国民法典的颁行证伪了萨维尼论说的观点更是马虎。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萨维尼反对在当时立法的前提是那时德意志没有统一;如果德意志已经统一,政治问题已经解决,萨维尼论说的境况已经发生改变,结论的不同就不能认为是萨维尼的失误。同样,拿后来埃及、日本、土耳其等国移植外国民法典基本成功的事例反诘萨维尼也是错误的,因为萨维尼的论说只是为了解决当时德意志的问题,“民族精神”说的发生本身只是一个地方性问题,不能轻易地就认为他是在论说一个普世的真理。
萨维尼不是一个光会啃罗马法的法律学究,更是一个深谙政治角力的政治家(甚至,他啃罗马法,就是因为他是政治家);他不是浪漫的空想家,而是实干的战略家(笔者不同意莫尔诺的看法,他认为,萨维尼的理论有很强的空想和神秘主义意蕴[8]937;当他说法律是什么时,可能连他自己都不信,他只不过借用了那一套法律话语来言说一个政治企图,如果被他误导,不从他的语境中去理解他的论说,而轻易相信他的命题,就会陷入“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概而言之,萨维尼作为一个法律人与政治家的伟大之处,就是他运用政治智慧阻止了一次浪漫而危险的法律实践。
四、贡献与借鉴:萨维尼观点对我国现阶段民法典立法的参考价值
综上可见,萨维尼的“民族精神”说并非他反对编纂民法典的真正最关键理论;抑或他的理论之所以能在当时阻止蒂堡建议的实行,也不是因为他的“民族精神”说使大家恍然大悟,而是他的法律论说实际上讲明了一个道理:在一个法域还没有真正形成的时候,如果草率立法、急于求成,并不能促使这个法域形成,反而会造成一个孕育中的法域的分裂。一个统一法域的形成,并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法律的任务,而是一个社会发展、政治角力的结果。法律在这时候显得无力乃是因为相对于政治和社会变迁而言,法律是一个太阳系中的地月系,是一个大公转里的小公转。法律是被社会生活所决定的,而不是相反。
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民法典在近年编纂成功,并真的像法学家们想象和期望的那样,能在全国统一适用,那肯定是一个奇迹。因为它将在世界范围创造至少两个民法典的第一:一是适用它的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最大;二是适用它的人口最多。可能还有其他的“名列前茅”:它所面临的全国市场变动很大;支持它的司法资源非常薄弱。这些情况都不能从德国、瑞士、日本以及台湾地区民法典的适用方面找到现成的答案。
萨维尼的智慧对于当下中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制定民法典会同时涉及两方面的统一,一是政治上的,二是经济上的。相应产生两个问题:如果没有前者,因立法和司法会涉及主权权威,故而会发生基于主权的不认同;如果没有后者,经济的地区差异会在法律的具体适用中虚置民法典,最终也会产生害及立法者权威的效果(经济实力的差距会引发一系列有关法律的差距,比如社会工商化程度的差距、社会陌生程度的差距、司法资源分配的差距、法律知识类型需求的差距等,这些又会造成法律适用的差距。发达地区制定的法律可能对于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的地区来说,不仅意义不大,而且硬性实施还会造成不良后果。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法典编纂的老路:基于城市生活制定的法律越完善,就越被虚置;法学家越满意,法统的整体合法性就越虚弱。一个被发达地区、城里人奉为圣典,而同时又被欠发达地区鄙视为“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的民法典,很难推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反而会增添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基于规则的隔阂,会损害立法机关在欠发达地区的形象)。德国在19世纪初立法,会更多面对第一个问题。中国大陆在今天立法,虽然政治统一,但全国统一大市场尚未最终形成,所以会更多面对第二个问题。我们今天思考经济差异对民法典的影响时,萨维尼处理政治统一的智慧仍然有借鉴意义,甚至今天的中国比那时德国更需要重视立法的风险和破坏作用。因为经济上的地区差异所带来的问题会弥散在社会间,而不像萨维尼遇到的主权不认同那样显露在外,立法和社会的错位会体现在一次次诉讼或者交易中,会长时间慢慢显现,一般不会集中在一时一地,矛盾不容易被立法者察知。况且,中国民主进程尚有较大发展空间,社会的声音还要较多期待公权力的倾听,如果立法者不积极主动地充分重视立法和社会的错位问题,而制定出一部同社会实际情况差距较大的民法典,很可能就制造了一张蓄积社会对公权力不满情绪的温床,这种蓄积会在特别情势下骤然爆发。所以今天中国和当时德国相比,可能更需要立法者动用政治智慧体察立法的负面效果。
笔者不是借此就反对民法典的编纂,只是想借对萨维尼的论述提醒,要注意分散立法风险。
(一)保守和现实的规则比“筑巢引凤”式规则好
那种打算先置办一个优越的制度、等着民众在未来的博弈中选用的立法计划,笔者权且称为“筑巢引凤”式。因为中国太大,各地发展不平衡,有的“凤”会来,有的“凤”不来;有的“凤”来得早,有的“凤”来得又太晚。所以这种制度设计实际会造成规则的差异,而不是统一。基于对立法风险的考虑,建议学习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比较稳重的风格,重在总成,而不是采用后进工业化国家一般选用的以法典来引领社会的模式,因为引领就意味着更大的风险。要充分估计法典的破坏力,建议在编纂的过程中强调立法的法律清理功能,多选用在全国已经能通行的办法、制度,而不是利用民法典编纂机会大规模创制新制度。把承认新制度的任务留给以后法典修订或者肯认有全国意义的判例。
(二)降低对民法典的期望值
对法典的期望值太高其实会加强一部法典的破坏力。只要能树立一个民法的总框架,能为后来补充和修正提供依托已经很不错了,没必要毕其功于一役,非要利用这次立法机会制定出一套特别详密完善的制度,没必要指望这部法典用上一百年,也没必要指望它“不朽”[16],更没必要像有些学者说的要创制一部超越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新法典[17]。中国还在快速成长中,全国统一大市场还没有完全形成,这样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基础,不可能支持过度详密的制度安排。
收稿日期:2009-07-16
标签:萨维尼论文; 民族精神论文; 德国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民法典论文; 罗马法论文; 法律论文; 罗马帝国论文; 外国法制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