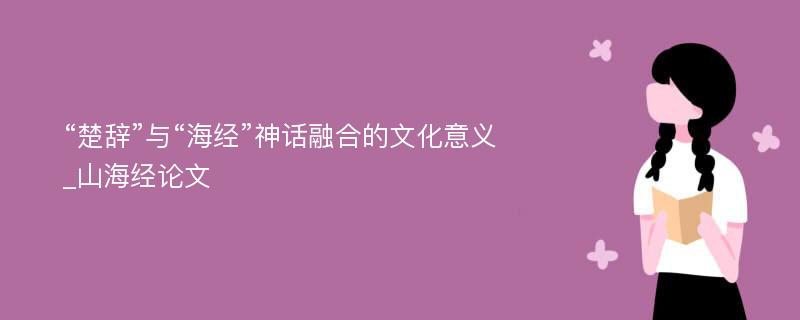
《楚辞》《山海经》神话趋同的文化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学论文,楚辞论文,山海经论文,意义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1)02-006-09
一、神话材料呈现趋同性特征
《山海经》和《楚辞》是我国现存先秦典籍中保存神话材料最丰富而又最具原生面貌的两部书。《山海经》“以山海之所经,历述怪兽异人的地域分布和由此而产生的神话和巫术幻想,进而成为百世神异思维的经典。”[1]“是一座神话学宝库和蕴藏量巨大的富矿。”[2](P264)而“在我们中华古国,神话也曾为文学的源泉,从几个天才手里发展成了新形式纯文艺作品,而为后人所楷式,这便是数千年来艳称的《楚辞》了。”“《楚辞》是研究中国神话时最重要的书籍”,“南方民族曾有不少神话靠《楚辞》保存至今。”[3]
《楚辞》、《山海经》中的神话材料既各具特色,又有明显的趋同性,即有着众多相同、相合、相似、相近之处,从而使它们能够相互印证、相互注释、相互补充。它们载有相同的神山圣水神树,相近的神异禽兽、神祇灵巫[4]、神乐神舞,相似的长生不死思想与娱神习俗。在鲧禹神话、夏启神话、后稷神话、后羿神话、王亥仆牛神话、离朱鲮鱼神话、幽冥世界等神话中都有可以相互解释、相互补充的材料片断。
《楚辞》、《山海经》中可以互证的神话材料甚多。仅在屈原的作品《离骚》、《天问》、《九歌》、《九章》、《远游》与《招魂》等篇中,就有诸多神话材料与《山海经》所记相合。其中自然神灵有帝、西皇(少昊、少暤)、伯强(禺彊)、应龙、烛龙、河伯、太皓(太暤)、冯夷、玄冥(禺彊)等;古史传说中的神话人物有高阳(颛顼)、伯庸(祝融)、高辛(帝喾)、后羿、女娲、成汤、后稷等等[5];地名如昆仑、苍梧、崦嵫、穷石、流沙、三危、南越等[6]。《楚辞》中神话故事及传说在《山海经》中能够对应起来的例子也非常之多。如《天问》中的“伯禹愎鲧”部分,就是《山海经》的“鲧腹生禹”一段;“雄虺九首”就是《海外北经》和《大荒北经》中所记的“九首人面”、“蛇身自环”的相柳(相鳐);“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就是《海内经》的“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该秉季德”一大段,就是《大荒东经》中的“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一段;“何兽能言”就是《海内南经》记载的“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按:《礼记·曲礼上》云:“猩猩能言”,猩猩即狌狌);“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就是《大荒西经》里记载的“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就是《中次十二经》中洞庭之山的“帝之二女”;河伯就是《海内北经》中的冯夷;山鬼的原型就是《中次三经》中神武罗;《远游》中所写的“降望大壑”就是《大荒东经》所写的“东海之外大壑”;“丹丘羽人”、“不死旧乡”也就是《海外南经》中的“羽民国”、“不死民”;[7]《招魂》中的“十日代出”也就是《海外东经》中的“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和《大荒东经》中的“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雷渊就是《海内东经》所记的“雷泽中有雷神”的雷泽;幽都就是《海内经》所记的“幽都之山”、“大幽之国”……
同时,二书中也有众多可以相互补正之神话材料。如多日神话。《大荒南经》云:“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楚辞·招魂》云:“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楚辞·天问》:“羿焉彃日,乌焉解羽?”这四个片断合起来刚好是一完整的后羿射十日神话。这个完整的神话见之于《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再如月亮神话。《山海经》仅有《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而《天问》中则有月有生死盈亏和月中有玉兔的神话(“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和嫦娥盗不死仙药神话(“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藏?”)。还有古史传说,如《天问》中的舜偏袒其弟象神话,禹和涂山女恋爱于台桑野合的神话,启取代伯益神话,羿射河伯、妻洛嫔而终为寒浞和纯狐勾结所害神话等等,都是对《山海经》中神话的阐释丰富和补充。“屈原在无意之中使《山海经》中许多看来不明不白,支离破碎的神话得到了复原,犹如我们通过对某种考古文物有了完整的认识一样,从而获得了对历史较为全面的理解,充满喜悦之情。”[8](P164-165)《山海经》中神话材料对《楚辞》起到补证作用的也很多。如,《天问》云:“何阖而晦,何开而明?”《海外东经》中“钟山之神,名为烛阴,视为昼,冥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大荒北经》中“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可以补之;《天问》中“伯强何处?”可用《大荒北经》中“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彊”补之;《天问》中“角宿之未旦,曜灵安藏”一句问太阳未升起之前的藏身之所。《海外东经》之“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可以补之。此外,“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昆仑悬圃,其居安在?”“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等等,均可在《山海经》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二、神话材料趋同原因的争鸣
对于《楚辞》、《山海经》之神话材料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性现象,早期的研究者一般仅仅以之互相解释或佐证。例如,郭璞注《山海经》多引《楚辞》;柳宗元《天对》引《山海经》材料答《天问》;洪兴祖《楚辞补注》引《山海经》材料达七十多次。然而,他们都没有从内容所反映文化源头这一更深的层面去探讨这种互证互补现象的成因。自宋朱熹起,不少学者开始探究《楚辞》(特别是神话材料最丰富的《天问》)与《山海经》神话材料趋同的原因,并作了一些探索性解释,但是仅仅局限在二书互为源头的狭窄视野内,均未能切中肯綮。
《山海经》源自《楚辞·天问》之说肇始于宋代朱熹。他在《楚辞辩证》中认为《山海经》、《淮南子》均是解《天问》之作。他说:
大抵古今说《天问》者,皆本此二书(《山海经》与《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本皆缘解此《问》而作。而此《问》之言,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如今世俗僧伽降之祈、许逊斩鲛蜃之类,本无稽局据,而好事者遂假托撰造以实之。[9](P192)
朱子此言是根据《楚辞》与《山海经》在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这则神话故事提出的。其实,《楚辞》和《山海经》在对鲧的态度上是不同的,《山海经》没有明显同情鲧窃息壤的描写,而在《楚辞》中屈原处处为鲧鸣不平,真切地反映了这则古史神话的原生面目。[10]此外,针对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多引《山海经》材料证《楚辞》,因此朱熹又说:“(洪兴祖)谓屈原多用《山海经》语,而不知《山海经》实因此书而作。”宋代陈振孙在《书录解题》中对朱熹的观点评价道:“谓《山海经》、《淮南子》殆因《天问》而著书,说者反取二者以证《天问》,可谓高世绝识,无遗恨者也。”体现了他对朱熹见解的极度推崇。
明代胡应麟的看法与朱熹颇为类似。他认为《山海经》是战国好奇之士采“《离骚》、《天问》之遐旨”及先秦诸书异闻而作。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侈大博极之,杂傅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问》之遐旨,《南华》《郑圃》之寓言,以成此书。”
上述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有二。其一,这些说法均只是由《楚辞》与《山海经》在神话材料上趋同的现象而产生的“猜想”,缺乏理论上的论证和考古学依据,因而颇欠说服力。其二,这些观点把《山海经》成书完全定在屈原作品产生之后,认为它是战国后期甚至秦汉间人所作,过分推迟了《山海经》的成书年代,隐匿了《山海经》神话的原生品质,因而很难令人信服,后世推崇发挥此说者甚少。
虽然刘秀《上〈山海经〉表》、王充《论衡·别通》中《山海经》出自伯益之手的观点、郦道元《水经注序》、刘知几《史通·杂述篇》中禹著《山海经》的观点、《隋书·经籍志》《颜氏家训·书证篇》中禹益共著《山海经》的观点均不为人们所普遍赞同,但《山海经》之主体的传述和成书早于《楚辞》却是不争的事实,因而由《楚辞》与《山海经》神话材料趋同而推出《楚辞》乃据《山海经》所作之学者甚众。由朱熹“大抵古今说《天问》者皆本此二书”可知此说自古流行甚广,后世持此观点的学者也不乏其人。
清人吴任臣《山海经广注·读山海经语》云:“周秦诸子,惟屈原最熟读此经。《天问》中如‘十日代出’、‘启棘宾商’、‘枲华安居’、‘烛龙何照’、‘应龙何画’、‘灵蛇吞象’、‘延年不死’,以至‘鲮鱼鬿堆’之名,皆原本斯经。”清人陈逢衡《山海经汇注·山海经是夷坚作》也认为是南人夷坚作了《山海经》,其书流传楚地,待至屈原作《天问》时,便多采其说而问之。吴任臣、陈逢衡等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今人陈子展先生亦赞同其说,认为《天问》可能是根据古本《山海经》或《山海经》的同类文献而作;[11]蒙文通先生则认为《天问》所依据的壁画就是《大荒经》之图;[12](P6)吕子方先生认为“是屈原的《天问》取材于《山海经》而不是‘《山海经》缘解《天问》而作’”,他也说《山海经》便是“楚国先王庙里壁画的脚本”。[13](P3)这些观点和《山海经》源自《楚辞》之说一样苦于证据不足,萧兵先生称之为“一个很难证明的假设”。[14](P455)
神话作为上古时代原始氏族生活和思想的产物,是原始先民信仰与生活状况的反映,因而神话与原始文化紧密相连,透过神话这枝绽放在原始文化肥沃土壤上的绚丽灿烂的花朵,我们可以追寻原始文化的踪迹。从文化学观点考察,《楚辞》与《山海经》在神话材料上的趋同性,反映了它们在文化的渊源上的同源关系。正如袁珂先生所言:“这种大同小异的现象,只能解释作二者是属于同一文化区的产物,并且产生年代也相差不远,由于都是根据当时当地的神话传说而作,故而才大体相同而又取舍详略各异。”[15](P8)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可以为此提供理论上的支持。荣格认为,相同民族在民族心理上有一种现象可以概括为“集体无意识”,它是由无数的同类经验在心理上长期积淀的产物,它反复出现在一些意象、故事情节中,在创造性幻想中自由表现。这种在创造性幻想中自由表现的形式就是一种神话。作家在创作时,借助神话(原始经验)来表达自己的经验——这种经验只能靠神话的想象赋予其形式。想象被用来表现幻想,集体无意识就在其中产生,其内容就是原型,它几乎是永恒的存在。[16]正是因为《楚辞》、《山海经》源于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中华远古氏族文化,这种氏族文化上潜在的集体无意识使它们具有相同相近的神话思维,使得这种以原型为内容的集体无意识借助于想象和幻想在作品中反复重现,因而产生相同或相近的神话情节和神话片断。
三、神话趋同的文化学考察
(一)《楚辞》《山海经》文化归属的学术悬案
“按文化学的观点,任何文献典籍均是特定文化的载体,均以某种特定的文化色彩占主导地位,并存在一个主要的隶属关系。”[17](P128)纵观《楚辞》《山海经》二千余年的研究历史,一直贯穿着对其文化渊源主要归属上的论证。王逸、朱熹等注家一方面揭示《楚辞》与楚地巫风宗教的密切关系,同时又从中原儒家思想本位出发,以《诗经》的讽谏、比兴来解释《楚辞》。他们过分强调屈原对巫风《九歌》的根本改造与提升,使这种粗朴的原始形态诗歌转化成寄寓诗人自我爱国情怀和讽谏之心的艺术形式,故而使《楚辞》的文化阐释呈现出“二元性倾向”[18]。王夫之、刘勰等过分强调地域环境、气候条件因素对楚辞文化生成的决定意义,把《楚辞》惊彩绝艳,奇诡浪漫的风格归因于南国“山川光怪之气”对诗人审美理想的感召。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云:“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迭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以崟嵚戎削之幽菀,故推岩无崖,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俯,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宋黄伯思“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19]之说,从楚语、楚声、楚地、楚物诸因素论证,把《楚辞》的南楚文化论观点推向极致。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随着楚地考古工作的逐步展开,楚墓出土了大量与中原风格异趣的文物,一时间,“南北文化不同”论似乎找到了新的佐证。一些学者由楚文化与湖北龙山、屈家岭文化之间的重叠关系而提出楚文化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一支所发展起来的,当其发展成为一个独特文化共同体时,又不断和周围其他文化相互作用的观点,一时间影响很大,赞同者甚众。
同样是考古学的成果使楚辞文化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随着东周楚墓年代学序列的排出,东周楚文化的考古特征大体得到了确认。学者们通过对考古发现的楚墓内含有不同文化因素的分析研究,得出楚文化多源之结论。因此,“西周楚文化不会是从某一新石器文化单线条的进化为青铜文化并直线发展来的。楚文化是由多支早期文化汇聚而成的。各个源头虽有主次之别,但绝不是从一个源头发展来的。”“而且自它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形成后,已经成为自身特征的面貌,又会随着生产能力的进步,生活方式的变动而变化,并且本身向四方扩展和其他文化也同样发生着的扩展,又会不断与新遇到的文化相互影响,产生新的因素,出现新的特征。”[20](P10-22)同时,考古发现还显示:春秋时期楚人的冠笄之饰,车马礼食之器,文字系统等作为文明程度标志的诸因素全盘袭自商周。因此,有关学者进又一步指出:“楚文化的形成,是在楚国形成了强大的国家之后,主要吸收了中原周文化,于春秋中期以后逐步形成的。”[21](P70)考古学者的发现及其对楚文化整合过程的分析,为我们探讨其背景和源流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在考古学成果的基础之上,学者对楚文化源流研究的结论渐趋一致。正如张正明教授指出的那样:“楚艺术的主源是中原艺术,说得更加明确一些是商周艺术。”“楚艺术的旁源是边裔艺术。边裔即楚人周围那些被统称为蛮夷的民族。分别说来,东南有扬越,中部有楚蛮,西南有巴人。”“楚艺术的本源,可以追溯到楚氏族始祖祝融时代崇火、拜日、尚赤、尊凤的原始巫风文化。”[22]
《山海经》的文化归属,有“南方说”、“北方说”和“域外说”三类。
只因《山海经》中有诸多内容与《楚辞》趋同,所以《山海经》被为数不少的学者认定是南方楚人的作品。朱熹称《山海经》乃解《天问》而作,明胡应麟认为《山海经》采《离骚》、《天问》之遐旨及先秦诸书异闻而作之说,清陈逢衡以《山海经》乃南人夷坚之作。今人陆侃如先生、吕子方先生、胡小石先生也均认为《山海经》是南方人作品。蒙文通先生更具体地说,《五藏山经》、《海外经》是楚国作品,《海内经》是古蜀国作品,《大荒经》是古巴国作品。[12](P76-78)具有“当代《山海经》研究第一人”之称的袁珂先生经过极其详尽地论证后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是楚人。袁珂先生在《〈山海经〉的写作时地及篇目考》中称《楚辞》和《山海经》乃“同一文化区的产物”,这里的“同一文化区”就是指南楚文化区。[15]
依据《山海经》与《楚辞》神话材料的趋同性和其中存在一些楚方言及楚人特有的修辞手法,把《山海经》文化之源归属于楚文化的论断显然很难站得住脚。学界多已公认,《山海经》的主体部分成书较《楚辞》稍早,而成书前辗转传述的时间可能更长,《山海经》初本传入楚国后经楚人之手转录、增饰,因而会在语言上留下痕迹。再者,在《楚辞》的文化渊源还没有辨清的情况下,仅根据它们之间的趋同就将《山海经》归于楚文化,未免失之草率。离开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古代华夏文化背景,单一的南楚文化说必然失去依赖和存在的基础。
与“南方说”相对,茅盾先生在《致大江编者论中国神话》中说:“《山海经》可信是北方人的作品。”他分析道:“在《山海经》中,虽然说昆仑是帝之下都,有神陆吾,又有若干奇树,有开明兽,又有许多猛兽怪鸟,并不是缥缈仙乡的样子。大概中国神话里的昆仑最初观念不过如此,正好代表了北方民族的严肃现实的气味。”[3]郑德坤先生与茅盾的观点极其相近。他也说:“《山海经》的神话最可代表北方民族严肃、现实、朴质的生活和理想。”[23]孙致中先生认为:“《山海经》最早的编著者是西周时的殷遗巫师。”[24]袁行霈由《山海经》中西北神话特富,而炎黄二族自西北入河洛,遂将《山海经》之主体归入炎黄二族。[25]主“北方说”的外国学者也不乏其人。如日本小川琢治认为《五藏山经》主要以洛阳为中心,遂将其定为东周洛阳人作品;[26]法国莱姆坎贝尔(Lamcanperi)认为《五藏山经》乃“商代山岳之记事”等等;张军《楚国神话原型研究》一书从《山海经》的原型、底本、素材与说本等诸多方面因素,结合周王室的文化机制和氛围,经过严密的论证,将《山海经》归属于北方的周文化。
“域外说”则认为《山海经》本来是外国人所作,或认为该书广泛地反映了西亚、南亚、俄罗斯、北美、欧洲等地的奇景异物。苏雪林认为:“此书为阿剌伯半岛之地理书,古巴比伦人所作,而由战国时波斯学者携来中国。”[27](P182)魏聚贤先生认为《山海经》是印度人“隋巢子所作”[28](P302)。美国学者李约瑟说西方学者认为《山海经》中的怪人可能“来自希腊”。[29](P582)荷兰学者希勒格认为《山海经》里写到远东库业岛、千岛群岛等岛屿情景。[30]美国学者还认为《山海经》相当精确地写到了北美大陆的地形、动物和特产,《大荒东经》中的“光华之国”就是科罗拉多大峡谷。(1980年第8期《科学画报》)这些观点无疑体现了学者们“大胆假设”的创新精神,但其科学性和可信性仍有待进一步“小心求证”。
此外,萧兵教授曾提出了兼容众家之说于一炉的“《山海经》:四方民俗文化交汇”[14]的观点,体现了《山海经》蕴涵中国古典文化的宏富与广博,确为一种创见,但是萧先生没有指出《山海经》之文化主源,甚为可惜。
(二)《楚辞》《山海经》同源于北方中原文化的神话学论证
1、《楚辞》《山海经》中的主神均与上古夏夷部族有过密切联系
从大量的文献记载看,楚民族与夏族本为同源。《史记·楚世家》开篇即言:“楚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氏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史记·夏本纪》亦云:“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由楚夏两族的世系可知,帝颛顼是楚夏两族的共同祖先,楚夏乃同源族无疑。楚夏族发祥以后,曾沿黄河东进,直至黄河中游。夏芈至鲧禹时,以山西、河南一带为活动中心,这在学界已成共识。以山西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东下冯文化和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的考古材料,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大约是到了黄河中下游时,颛顼族中的芈姓支族开始独立出来,并以荆楚灌木名为其族名。何光岳先生经过考证认为,荆楚植物盛产于黄河中下游,与新居在这里的芈姓族生活密切相关,芈姓族遂以其为族名。[31]根据《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族得姓于季连,出于祝融集团,祝融乃帝高阳颛顼之后。《离骚》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伯庸即楚先祝融是学界之共识。据《左传》所载,祝融、颛顼活动范围均在中原。《左传·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郑,祝融之虚也。”杜预注曰:“卫,今濮阳县,昔帝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郑即今河南新郑。《路史·国名记己》:“今郑州有祝融冢。”据考证,颛顼部落活动之范围,大体上在今河南临汝、嵩县、杞县、濮阳、内黄等地,即豫西、豫东和豫北一带等中原地区。[32]《国语·郑语》载祝融后人分为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即八个部落。“祝融八姓的早期分布,北起黄河中游,南至河南北部,可以说是环处中原。”“推本溯源,八姓原始分布都是中原及其周围。”[33]
楚人作为华夏族的一支,与东方夷人集团也有密切联系。东夷族发祥于渤海两岸,以凤鸟为图腾。楚文物里飞廉(风神鸟)造型之多见,鸷鸟践蛇、鹿角神凤御虎之类造像的繁美不能不说是夷文化浸润的结果。楚先人也以鸟为图腾。楚远祖祝融、重黎属东夷太阳鸟图腾。“祝融即朱明、昭明,本殷人东夷之日神、火神。楚本亦殷人东夷之族,及其南迁,遂自以火正祝融之后。”[34]何錡章先生就认为楚先祖祝融曾是鸟的化身。他说:“祝融亦朱鸟所演而出,朱鸟即南楚之图腾黧鸟,一作离……楚人先祖黎,亦火正,号祝融,或即由其图腾黧鸟之音而得名。后迁至南方,史称黧族。”[35]不难发现,楚人发祥于西北华夏族后沿黄河东进后长期活动于中原地带,而以殷商为代表的东方夷人集群及其文化也很早就渗入中原,与夏文化融合。因此,从文化渊源上讲看,楚人接受的主要夏夷族的原始文化。后来在武王克商后,周族东进使楚不断受到排挤,楚族便沿丹水南下,后融合了三苗云梦等氏族,最终发展成为以郢都为中心的“北接汝颖,南接衡湘,西连巴,东连吴”[36](P205)的横跨今十一省之地的战国时最大的国家。
在《山海经》神话体系中,最高祖先神有两位,即西北华夏族始祖黄帝和东夷祖先神帝俊。《山海经》中绝大多数神祇和英雄都能归入他们的世系,成为他们的子孙或部属。
黄帝是《山海经》中地位最显赫的祖先神。《山海经》中的黄帝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宙斯。据袁珂先生统计,《山海经》中记载黄帝事共十八处,为众神之最。黄帝家族在中国古神话体系中占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无怪乎司马迁《史记》开篇起自黄帝。
黄帝事迹遍布《山海经》,但其家族谱系主要集中在《大荒经》和《海内经》中。其子禺虢为东海之神,孙禺京为北海之神(《大荒东经》);孙始均生北狄而有北狄之国(《大荒西经》);子苗龙之后白犬有犬戎国,昌意之后颛顼为楚先祖,骆明之后鲧禹为夏祖。《山海经》中黄帝世系横跨西北南三方,且和东方帝俊有密切联系。因此,“如果要说《山海经》里有主神的话,黄帝和颛顼应该算是《山海经》的主神,尤其是黄帝,他的事迹遍布于《山海经》的各个部分,而帝俊事则仅见于《荒经》以下五篇。”[15]
在《山海经》中,颛顼是黄帝后裔中地位最显赫、世系最繁盛、神性最强的一个。《海内经》云:“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生、渠股、豚止,取淖子阿女,生帝颛顼。”颛顼的嫡系血统有伯服、淑士、老童、叔歇、中、騹头等,而老童后则是楚先祝融、重、黎、吴回等。在《山海经》中同样能发现楚先颛顼与东方的联系。如《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帝俊在《山海经》是东方大神或祖先神。《海内经》说他有子八人:中容、晏龙、帝鸿、黑齿、季厘、后稷、台玺、禺號,多为各氏族小国的创始者,后稷则是周族始祖。同时,帝俊妻羲和及常羲而生十日和十二月,因而他又是日月之神。长沙子弹库《楚十二月神帛书》有“日月夋生”和“帝夋乃为日月之行”之语,可与《山海经》内容互证。帝俊即帝舜,帝舜即《离骚》“就重华而陈辞”之“重华”。
可见,《山海经》中主神也同样出自上古夷夏族,亦即茅盾、郑德坤所说的北方民族。华夏、东夷族经过迁徙和融合而成为中原民族之主体,夏夷文化经过整合而成为中原文化的主流。
2、《楚辞》《山海经》古史神话人物和神祇多源于中原
在《楚辞》与《山海经》的神话材料中,有一大部分属于古史神话。如鲧禹治水神话,夏启《九歌》神话,殷高母简狄吞燕卵而生契神话,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周祖后稷神话,殷先公王亥与王恒传说神话等等。这些古史传说神话或见之于先秦之北方典籍,或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如,《尚书·洪范》、《国语·周语下》、《吕氏春秋·君守篇》、《吕氏春秋·行论篇》、《韩非子·外储说》等都有鲧治水及其被杀的记载。《国语·周语下》称鲧为“崇伯”,崇地即在今河南登封县嵩山附近。从神话历史化的角度看,鲧神话原型极可能是我国中原地区在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氏族间围绕争夺部落领导权而进行的一场激烈斗争的反映。至于治水无功,违背帝命等,仅仅是后世儒家思想对古史神话浸入和“润饰”的结果。
在洪水神话中,最能反映我国古代文化者当推大禹治水神话。关于大禹治水神话,虽在南北方均广为流传,但其起源当在黄河流域。在中原地区有着蔚为壮观的大禹治水神话,主要在河南、山西一带。如禹在崇(嵩山)周围中州腹地治理河水神话,在嵩岳、伊洛、禹县治理洪水神话,大禹桐柏导淮神话,大禹决济和导黄神话等等。[37]《吕氏春秋》、《孟子》等书均有洪水泛滥中原的记载。《吕氏春秋·爱类篇》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洪水,禹于是疏河决江……”《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中国……”这个大禹中原治理洪水神话系列全面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中原腹地开创华夏基业的精神面貌。
《楚辞·天问》用了六章二十四句的长篇写了商人先公王亥王恒兄弟二人到北方游牧民族狄人那里做买卖,并与狄人部落女子通婚,最终王亥被杀,王恒逃归之事。《大荒东经》亦有相关记载:“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兽方,食之,名曰摇民。”这一古史神话虽然不见于北方典籍,但在殷商卜辞中得到了印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确定了他们的殷先公身份,解决了《楚辞》研究的一个千古疑案。这些传说的源头当在北方无疑,因为殷先祖的神话传说绝不会出自战国楚人之口,王亥王恒传说必定是由中原流传到南方楚地的。[38](P200)
《楚辞》《山海经》所记大体一致的上古神话人物众多。像夏族的尧、共工、鲧、禹、皋陶,殷族的俊、喾、舜、季、亥、恒、昏为、成汤、伊尹,周族的稷等都有明显的北土流传源头。据统计,屈原作品中提到的历史传说人物有81人,其中真正属于南楚的只有接舆、堵敖、子文三人。[39]
在《楚辞》与《山海经》中,不仅古史神话人物有明显的北土源流特征,其中的各种神祇和神奇异物亦多属于北方。屈原作品中提到的神祇共有24名,其真正属于楚国“土生土长”的神祇竟无一个。拿《九歌》所祭祀的神灵来说,至尊之神东皇太一是“东皇”与“太一”的混合体。“东皇”则是东夷太阳神少暤。[40]云中君、东君为晋赵之神。《九歌·云中君》曰:“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冀州乃赵、晋境域之古称。又《史记·封禅书》曰:“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亦可证之。湘君、湘夫人旧称为沅湘土著神祇,但据传说又是尧之二女,舜之二妃娥皇、女英。因而就其内容看,无疑揉合进了商周之际南迁沅湘流域的殷民和或者是战国初年楚灭陈后南迁的陈国移民传述的尧女舜妃神话故事,当属复合型神祇。对于《九歌》中的大司命与少司命,《史记·封禅书》载晋荆之巫同祠司命。据齐鲁官书与周典编成的《周礼·大宗伯》云:“以樵燎祠司中、司命。”由此可知司命乃楚、齐、鲁三晋共尊的两位神祇。山鬼的原型乃《中次三经》中居“青要之山”的神武罗。[41]据徐旭生先生考证,《中次三经》之地望“盖西起今新安,东至今孟津”,故“青要之山”恰在东周王畿近北处,所以神武罗(山鬼)无疑当是周人敬祀的女山神。[42](P177-179)
又如,《海外北经》中有巨人夸父的描述:“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其中“饮于河渭”、“北饮大泽”等均显示出这则神话的北方特征。对此,郑德坤先生风趣的评论道:“假使《山海经》是南方的产物,夸父或要饮于江湘,江湘不足而饮洞庭了。”[22]
再如《楚辞》《山海经》中均提到的烛龙的原型是自然现象北极光。《河图稽命征》云:“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耀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于轩辕邱。”这就是附宝感神光有孕而生黄帝的神话。现代科学研究“长期观测统计结果表明,极光最经常出现的地方是南北磁纬度67度附近的两个环状区域内”。[43]可见,只有在我国北部地区才有机会观测到这种天文奇观,因此只有在北方才有可能产生解释这种自然现象的神话传说。
四、余论
《楚辞》与《山海经》神话材料的趋同性特点显示了两部典籍在文化渊源上的同源关系。它们的主源都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北方文化。《山海经》文化源于夏文化是因为《山海经》的原型是周王朝手中控制的“九鼎”。《汉书·郊祀志》云:“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像九州,皆尝鬺享上帝鬼神。”可见,九鼎所铸乃夏代山川鬼神,铸神目的是为了求祭。关于九鼎与《山海经》的继承关系,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云:“《山海经·海内经》四篇,《海外经》四篇,周秦所述也。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按其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际,是鼎所图也。鼎亡于秦,故其先时人犹能说其图以著于册。”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云:“今《山海经》‘海内’、‘大荒’等篇,即后人录夏鼎之文也。”沈钦韩《春秋左传补注》曰:“今《山海经》所说形状物色,殆鼎之所像也。”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山海经》是以“九鼎”为最初原型和模本不断增补、改铸、累积而成的。所以,《山海经》之文化主源应上溯至夏文化。《山海经》成书后在辗转传述流传过程中,经过不断增补减色,遂带上了诸如战国时楚文化等各种文化印记。
以“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浪漫风格著称的楚辞是南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其文化之根也应追溯到北方夏文化。与先楚同源的夏民族是黄河流域开化最早的民族,它发祥于西北后沿黄河东下入主中原,并在那里发展壮大。楚夏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图腾,它们在黄河流域融合了东夷文化后,楚从夏民族中分化出来南下长江流域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楚民族。从文化渊源上看,中原殷商文化在楚文化里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南楚信鬼好祀的浓烈巫风文化正是对殷商巫风基本内容的继承。由于地处中原,随着历史的嬗变,周代礼制政治型文化取代了殷商热烈浪漫充满幻想的原始巫风内容,而南下长江流域的楚人则成为这种巫风的唯一继承者,《楚辞》则是这种殷商巫风的活化石。
楚文化作为华夏文化中重要的一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融合了商周文化,在长江中下游吸收了吴越文化,同时又和其他同期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影响,最终得到了完美高度的发展,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在楚文化所包含的众多文化因素中,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北方中原文化,仍然是楚文化的根源之所在。
因此,我们从《楚辞》与《山海经》神话材料的互证补正中,所看到的不仅是神话材料上的相同、相似或相近的表面现象。透过这种表象,我们看到的是两者有着诸多共同的神话原型。它反映了同一源头民族的共同的原始神话思维。能够显示这种共同原始神话思维的原始文化就是环太平洋文化圈中最具特色的中华文化的代表——以夏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
标签:山海经论文; 楚辞论文; 文化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世界神话体系论文; 神话论文; 中国神话人物论文; 楚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离骚论文; 颛顼论文; 天问论文; 海内经论文; 淮南子论文; 九歌论文; 祝融论文; 中原论文; 黄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