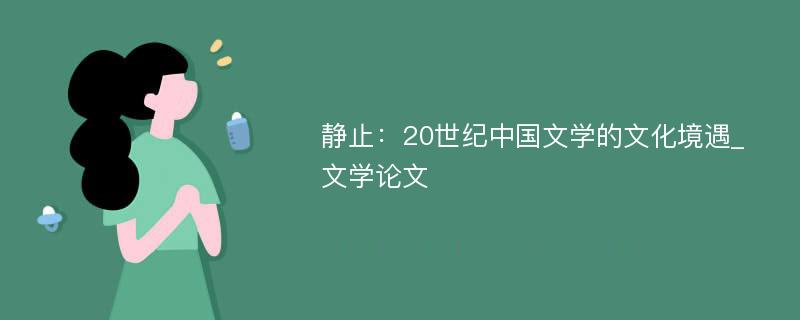
变动不居:20世纪华文文学的文化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动不居论文,态势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借用胡绳80寿辰时的《自寿铭》:“十五志而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七十八十初知天命”,颇能说明20世纪华文文学的某种变化历程。
“十五志而学”:晚清文学拉开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构建的序幕,但那时西风东渐尚未成大气候,翻译虽已大盛,但借“输入”来求新求变仍囿于传统之内自我改造。1915年,《新青年》的创办,至今仍可视作中国“人的觉醒”时代的启端。在此前后,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努力于以异域新说来探求国家、民族的出路,并将思想启蒙、个性解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此时的文学也唯西方新说为马首是瞻,广泛摄取,表现出强烈的于求新知中来实现根本性的蜕变的势头。“五四”文化思潮对“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的提倡,使五四新文学多义杂陈,众声喧哗。作家们虽大多以感时忧国的文人自居,但创新求变的文学意识仍有多个层面。
“三十而立”:30年代文学的成熟形态早已被载入各种文学史,但这文学而立之年却是被置于阶级对立而引发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异常激烈的社会环境中。王元化先生在《思考“五四”》(注:载《辞海新知》创刊号。)一文中指出的“五四”时期流行的4种观念, 即庸俗进化观点、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跟此时社会环境所容纳的文化气氛非常吻合,这使得此时作家对自己的身份、自己所从事文学的性质等的认定泾渭分明。许多作家在创作日趋圆熟之时,政治上的皈依也日益鲜明。恰如巴金当时所言的:“固然人说生活是短暂的,艺术是长久的,但我却始终相信着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舍弃文学生活,而没有一点留恋。”(注:巴金《我的写作生活回顾》。)巴金30年代并未加入左翼作家阵营,但他也宁愿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舍弃艺术。革命是构建现代性的最高形式,30年代的文学正是在革命文学运动中变得健壮,但自身独立的目的也开始变得模糊。
30年代,中国大陆新文学的辐射影响机制已形成并得到充分运作。“五四”新文学对台湾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都存在着时差,而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文艺大众化主张等对外产生了“即时效应”,台湾、东南亚等地区新文学同步呼应中国文学的格局在此时完全形成,一直延续到1937年至1941年间。
“四十而惑”:40年代华文文学“惑而分流”的态势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战争文化环境对作家创作心理的重大影响,战争之后中国大陆政治格局、社会体制的根本性变化,使“尊群体而斥个性,重功利而轻审美,扬理念而抑性情”(谢冕语)的价值取向完全主宰了文学,作家在虔诚的皈依中产生了重重困惑。同时,战争大大削弱了大陆文学对台湾地区、海外华人社会文学的影响。之后,海峡两岸的政治对峙逼使台湾文学进入自行其是的生存轨道。而中国政府对“双重国籍”不予承认的政策也迫使海外华侨社会仓促向华人社会过渡,海外华文文学脱出跟中国文学呼应的格局,而立足于居住国本土创作资源的开掘。在跟母体文化的联系削弱,乃至一度割断的情况下,作家们对自身身份的确认产生了种种认同危机。有一首诗《填表》令人心酸且心凉地抒写了在异国填写身份表格时的心情:表格“好像迷宫/难以着手”,而“我借助残黄风湿的资料/战战兢兢地逐项攀爬”,“末了/还逼我表白/肯定了四五十年的身份/我最不甘心/缩半截才塞进去的那一栏”。此诗的作者艾文是个出生于马来亚的华人,赤道异域生活了半个世纪,他依旧无法摆脱难以定位的矛盾心境。台湾文学中此时激荡相生的中国情结和台湾本土意识的矛盾,也集中反映了台湾文学定位自身的曲折艰难。
“七十八十初知天命”:70年代以来,各地区华文文学在文化中国的层面上出现整合趋势。1982年,中国大陆召开第一届台湾文学国际研讨会,后延伸成“台湾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1992年又定名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1999年召开了第十届会议,大规模而又持久地展开了跟其他地区华文文学的双向对话。几乎同时,台湾文学界也快速拓展着同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联系,协助成立了各大洲的华文作家组织,并先后召开了3届世界华文作家代表大会。 “内在中国”视域明显化解着各地区华文文学间原先的阻隔。
“初知天命”对于华文文学而言,应指自身定位的初步完成,其含义大致有两层,一是不要被政治、经济等属性遮没,而保持文学作为人类通过情感性想象去感悟生命之美的方式的独立品格,二是指不要被别种强势文化淹没,而保持自己族裔的、乡土的文学特性。这中间包含着作家个体角色的定位,但也有着不同地区华文文学整体角色的定位。七八十年代以来,正是由于各地区华文文学角色定位的适得其所,世界格局中的华文文学重新在各守其所、互相呼应中呈现旺盛之势。
在上述极简略的历史回顾中,浮现出了整合20世纪华文文学的一种文化视角,即从作家自我的文化身份和各地区华文文学的文化属性的变动不居上去构建一个开放意义上的华文文学生存体系。也许恰恰是变动性孕蓄着20世纪华文文学的生命活力。
“人类是不能离开身份生活的。”(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18页。)对自身身份的寻求和确认,是人类主体性的表现。但这种主体性理论在70年代以来也遭到了主体消解论的挑战。同时,一些只关注精神层面而忽视了从肉体(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性上来把握主体性的看法遭到质疑。这大致构成了20世纪华文文学文化身份定位的理论背景。
20世纪华文文学的文化定位一直徘徊于一种身份的确认和几种身份的适应之间。而在20世纪华文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种种因素,影响、促使着作家确认明晰、单一的群体归属。五四时期,社团蜂起,流派纷出,外来文化影响上各自沟通于欧美文化、苏俄文化、东亚文化,文学趣味上或张扬知识精英旗帜,或沉潜自由平民意识,或走向民间大众文化。(注:此种分类可参阅杨洪承《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版。但杨著分类是就整个现代文学时期而言,本文的表述有所不同。)各群体的文化成规本来就迥然相异(自然也不排斥相通相合之处),又整体分化于新和旧、改革和保守、传统和现代的对峙中,所以虽也有作家或迎合、奔走于不同群体之间或从一种文化成规转向另一种文化成规,但大多数作家的群体归属是较为明确的。之后,以文学社团为基础的群体生存空间逐渐缩小,代之以政治分野为主的组织、派别。上海、北平的情况自不必说,即以台湾文学而言,三四十年代也是以台湾艺术研究会(1931)、台湾文艺协会(1933)、台湾文艺联盟(1934)、台湾文艺家协会(1940)、 台湾文学奉公会(1943 )等较为统一的组织(其中大多政治倾向明显)代替了原先散落零乱的社团。再后,纯然民间性的文学社团几乎不复存在,附属政府机构或官方赞助支持的“群众团体”成为作家唯一可选择的群体归属,如50年代台湾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1950)、中国青年写作协会(1953)、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1955)、中国文艺界联谊会(1957)等都是某一方面大一统的组织,这种明晰、单一的群体归属必然使得作家的角色被确定得划一无误,也使得真正的创作成为一种压抑机制下的写作。
黎湘萍在他的《台湾的忧郁》(注:三联书店1994年6月版。 )一书中曾引用罗兰·巴尔特的话:“一种写作的选择以及责任表示着一种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不具有相同的限制……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立的……”当群体的归属成为创作自由的限制时,作家对自己身份就会产生怀疑,甚至产生失落感。六七十年代后,自由撰稿人队伍的重新聚集和组合,台港地区和海外华人社会民间性文学团体的增多,正可视为作家们寻回自己身份的一种努力。
20世纪华文文学被分割成几大板块,作家们在不同板块间的政治放逐、文化迁徙、生活移居,使不少作家熟悉并接受了不同文化成规。特别是那些漂泊异域、定居海外的作家,当他们能出入于两种或更多种文化而且都感到从容、自在时,他们的文化身份虽有可能变得模棱两可,但他们的创作却由此趋于成熟。然而,更多的作家会因放逐、迁徙、漂泊、寓居而对自己的身份游移不定而焦灼不安。我在《华侨文学·华人文学·华文文学》一文中述及这3个概念的重合之处,意在说明这3种作家身份的交叉之处。但从实际情况看,作家们对这3个概念, 尤其是华侨文学和华人文学的文化定位是截然分明的。这也反映了作家们并不看重适应不同的文化成规的创作状态。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定存在着一个自足的、内外界定清楚的中国文学(或华文文学)的体系,使得作家们一旦放逐、漂泊于这一体系之外,哪怕只是暂时的,或在体系内不同区域间游移不定,就会责疑自己身份,甚至引起身份的失落?
个人身份可视作个人对其自身条件和他所接受的成规的把握。对于文学的审美的成规而言,它主要表现为“所有那些意欲把语言表层性文本实现为审美交往性文本的参与者都应当愿意而且应当能够”实践的“群体协议”。(注:西格弗莱德·施密特所言,转引自佛马克《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31页。)20世纪华文文学的审美成规一开始就从古典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的“真”、“善”体系中分离出来自主自立,以其“通过情感性想象来感悟生命之美”的方法原则独立于认识对象之真的科学思维,实施功利之善的实践精神、希冀灵魂之安的偶象崇拜之外。审美成规一方面呼应于种种外来思潮,一方面对应于作家的个性解放,衍生成多套“集体协议”,这些成规被抛撤、挟带到各个地区,那里相异的政治变动、社会转型、风情迁徙,又不时促使本地区作家改动互相之间认可、协作的审美成规。可以说,20世纪华文文学审美成规形态多元,变动频繁,并且整体上呈开放态势。
这里还可以借用西格弗莱德·施密特提出的一个概念“文学多价成规”,即“在我们的社会中,按照预设,所有意欲把一个表层文本实现为一个语言的、审美的交往性文本的参与者们都愿意而且能够通过多价而非一价来操作他们的加工处理过程”。(注:西格弗莱德·施密特所言,转引自佛马克《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34页。)自然,这里的“参与者”不仅指作家,也可以包括读者。20世纪华文文学面对的创作和阅读环境,多价成规的存在是明显的。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华文作家(华裔)们难于多价的生成,而易于多价的接受。这使得华文文学在雅和俗、传统和现代、乡土和西化、本土和异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方面都经历过严重、尖锐的对立。但也许正是严重的对峙形成的当道并立状态,使作家、读者对双方都同时认可,促使一方向对方松动并向对方渗透。这种在多价的生成和接受上的差异,实际上也包含有传统文化心理和外来文化冲击之间的挪移。愈到后来,作家的创作、读者的阐释愈具有“多栖性”。本来,审美成规的作用之一就是“使人们对文学中所表现的事态比对‘现实’中的事态怀有一种更大限度的宽容”(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 月版,第32页。),文学多元成规的存在和人们对它的接受,使得审美成规的作用真正得到发挥。
过去,我们常感到对一些作家难以定位,实际上是对20世纪华文文学审美成规的交织和作家们的多价成规状态考察得不够。白先勇、余光中、张爱玲,乃至金庸等实际上是在自身创作中进入了多价成规状态才有突破,甚至开一代创作风气的。
上述对审美成规的考察已大致呈现了20世纪华文文学并非一个界限了了分明,各种传承皆自成一脉的体系。下面来考察一下作家的人员流动对华文文学体系的影响。20世纪是中国人员流动最频繁的年代。“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文革结束、香港回归等变动,都引起作家一定规模,乃至大规模的外迁。海峡两岸的对峙、东南亚各国对华人政策的变动等,也都引起过当地作家的外流。20世纪,中华民族是接触国别文化、种族外来文化最多的民族。“中国人”衍生出了华侨、华族、华人等名称,又有了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等专称。这些称呼都有着对应类别的文化、文学。由于作家多次的自我放逐(从大陆“流亡”到台港再迁居海外的作家并不在个别),其创作适应着不同的文化成规,改变着原先的文化视野。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变化是,中国意识在不少作家创作中逐步被中华情结所取代。我在《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之一章《南来作家创作模式的转变》中述及那些在中国大陆完成了文学启蒙或已开始了创作生涯的南来作家在其创作模式的蜕变中,其中国意识逐步淡化,而中华情结趋浓的情况。中国意识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层面,是一种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它使得从“五四”至四十年代的海外华文文学一直同步呼应于中国大陆大学,甚至可视作中国文学的分支。而中华情结则表现为精神的、伦理的、审美情感的等文化层面的内容,它使得海外华文文学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跟世界文化对话、文汇、融合。这种变化在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中也是明显存在的。有意思的是,王一川在他的近著《中国形象诗学》(注: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版。)的最后一章,依据中国大陆文学80 年代后期以来的走势预示不久将来的中国大陆文学,其民族国家色彩会谈化,文化认同色彩会趋浓,“中国性中国形象”会被“中华性中国形象替代”。这似乎可以说,中国性和中华性之间的转换,是华文文学共有的一种现象。
立足于20世纪华文文学的整体性而言,上述变化确实主要是由人员的多向迁移造成的。当炎黄子孙无法共同认同于一种政体、一个权力集团,而互相间的血缘亲情又无法割舍时,中国性和中华性之间的转换就是自然的了。但其中的具体情况是复杂的。有的会经历游子、孤儿、“遗民”等种种痛苦状态,有的会在想象中构筑始终变动的“中国”形象,有的会徘徊于“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的抉择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人员的多向迁徙中,事实上存在着几个大的文化迁徙群体,比如闽粤——东南亚文化迁徙群体:东南亚的华文作家中,90%左右祖籍闽粤桂,其祖籍地域文化和居住国本土文学资源的交融,构成这一群体文化迁徙的基本走向;中原——台湾文化迁徙群体:40年代后被各种因素裹挟到台湾的中原文化人,对50年代后的台湾文学基本格局的构建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东南亚——台湾文化迁徙群体:60年代至今,东南亚华人的大批学子前往台湾、香港攻读高级学位,将一种华文非主流社会的华族文化同华文主流社会的文化交融,这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作家目前构成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新生代;台港——欧美文化迁徙群体:70年代以后,不少在台湾、香港文学中已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迁居欧美澳,有的是几度漂泊,出入于几种文化之间,面临自己拥有的母土文化几度异质的挑战;中国内地——欧美澳文化迁徙群体:80年代以后,华裔新移民中来自中国内地的占大多数,如今已成为新移民作家群的主体,呈现出一种压抑禁锢日久后的文化爆发景观……这些大的文化迁徙群体在构筑20世纪华文文学的大开放空间上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具体地辨析这些文化迁徙群体将自身原先拥有的文化资源迁移于现时文化时空时所发生的种种交融情况,将会清晰呈现出20世纪华文文学文化属性的开放性、变动性。
20世纪华文文学文化属性上的开放性、变动性首先表现在各地区文学的包容性越来越大。这里有一件刚刚发生的文学事件颇能说明这种包容性的含义,1999年3月19日至21日,由台湾文建会主办、 《联合报副刊》承办的“台湾文学经典研讨会”在台北举行。在此前不久,台湾多家机构参与评选的29位作家30部“台湾文学经典”揭晓。小说有张爱玲的《半生缘》、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白先勇的《台北人》、陈映真的《将军族》、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黄春明的《锣》、王文兴的《家变》、姜贵的《旋风》、七等生的《僵局》等;散文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杨牧的《传说》、王鼎钧的《开放的人生》、陈之藩的《剑河倒影》、简媜的《女儿红》、琦君的《烟愁》等;诗集有余光中的《与永恒拔河》、商禽的《梦或者黎明》、洛夫的《魔歌》、郑愁予的《郑愁予诗集》、痖弦的《深渊》、周梦蝶的《孤独国》、杨牧的《搜索者》等;戏剧有姚一苇的《姚一苇戏剧六种》、张晓风的《晓风戏剧集》、赖声川的《剧场》;评论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王梦鸥的《文艺美学》等。这里不吝篇幅列出了“台湾文学经典”的全部名单,意在展示台湾文学的包容性。无可讳言,在各地区的华文文学中,台湾文学是最极力熔铸其自立性的,它一直在努力构建自身的传承机制,“台湾文学经典”的筛选和确立就可视之为这样一种努力。然而,略为熟悉台湾文学的人就可以从“台湾文学经典”名单中感受到台湾文学极力延伸的空间和无力拒斥“异数”的生存机制。30部台湾文学经典的29位作家中,19位属所谓“外省作家”,10余位曾旅居海外或目前仍定居海外,有的作家还从事外文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用英文写成,而由他人译成中文)。20余部文学作品中,直接或间接写到大陆生活经验的有10部之多。近几十年来,台湾文学中本土意识昂扬,但上述经典作品作者出身及其生活经验的构成却说明台湾文学难以某一地域囿定了。再略微考察一下作品。就艺术延伸而言,“白先勇的《台北人》与王文兴的《家变》都承袭爱尔兰的乔伊斯,梁实秋的散文服膺英法传统,陈之藩的《剑河倒影》地理背景为英国,而王梦鸥的《文艺美学》多数篇幅处理的是西方文学概念。”而“《烟愁》的中国风和《嫁妆一牛车》的台湾味可以并陈”(注:李奭学《锣声若响》,载1979年3月15 日台湾《联合报》副刊《读书人》。)。就政治纠葛而言,陈映真的《将军族》一度是政治层面上的禁书,作者也因违背官方意识形态而身系囹圄,而出身苗裔的姜贵的《旋风》却属于五六十年代官方文学的正宗,至于白先勇、王文兴等的小说则是早年台湾当局高压专制政治下的一种对抗。余光中、郑愁予等的诗作孕成于政治放逐、文化流亡之中,其中国情结浓于作品各个层面;而王祯和、黄春明的乡土小说形成于70年代台湾的政治氛围中,成为“文学上的台湾中心论”的先声,乃至演化成台湾的“民族图腾”(注:李奭学《锣声若响》,载1979年3月15日台湾《联合报》副刊《读书人》。)。赖声川的京派相声,姚一苇的中国传统剧作,在今日台湾本土派眼中常被视为本土文化的对立面,但“‘经典’二话不说,照单全收,反映出今天‘台湾文学’的定义确非基要思想(即台湾本土意识——笔者)所能绳墨,早已超越族群与文化政治的轇輵。台湾既为移民之岛,强调文化‘固有’是固步自封”(注:李奭学《锣声若响》,载1979年3月15日台湾《联合报》副刊《读书人》。)。 至于就艺术流派而言,更以其宽泛性改写着以往的典律。张爱玲、梁实秋、余光中、白先勇、七等生、杨牧、陈映真、洛夫、琦君……几乎每个人都代表着一种艺术的价值走向,从政治依违到个人化,从现实到超现实……交织、化用,都给人一种感觉:书写完了,但其艺术探索方兴未艾。这样的“台湾文学经典”自然给人一种“有容乃大”的印象。
“台湾文学经典”作为台湾百年新文学的某种总结,多少表明了,文学可以超越政治思想的对峙、历史事件的阻隔,容纳下个体生命的创造。
20世纪华文文学文化属性上的开放性、变动性还在于它始终处于从一种纯然的思维框架向杂然的思维方式的变化之中,从而呈现出分合起伏的长久态势。我在《雅俗何以兼容,又如何整合》一文中述及雅俗两种艺术思维在20世纪华文文学中从了了分明的对峙、分流到兼容乃至某种程度的合流。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对话”确实可视作20世纪华文文学的一种趋势。20世纪华文文学始于“分”。例如,有学者指出,20世纪初中国文学已逐步分裂为两种不同流向:“一种是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由‘五四’文学革命催生的‘新文学’;一种是保留中国文学传统形式但富有新质的本土文学。”(注:刘再复《金庸小说在廿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载香港(明报)月刊1998年8月号。 )后来,华文文学发展中也确实存在着知识精英话语系统、民间大众文化话语系统、官制文化话语系统等,但这些“文化对话”系统都时而纯然、时而杂然,时而分流,时而有所汇合。有的作家可以作为某种纯然的话语方式的代表作家存在于文学史。例如,赵树理无论如何不应从我们的文学史中消失,因为他是纯然的民间大众话语方式的杰出代表者。但也有许多作家是作为某种“杂然”的话语方式的代表者出现于文学史。例如,台湾意识是台湾乡土文学系统的重要基石,然而,被视为台湾乡土文学大家的黄春明、王祯和在70年代创作中都力图跟“台湾意识”划清界线,这表明他们此时所坚持的正是一种非纯然的台湾乡土文学。充分注意到20世纪华文文学中“分久有合,合久有分”的势态,对于我们客观地审视作家自我的文化身份和华文文学的文化属性是有帮助的。我们既要看到一位作家、一种经典可能属于一种文化类型、文化系统,也要看到其可能具有的多栖性、“杂交”性。
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学主要提供了一种纯然的汉民族艺术思维方式,那么,20世纪华文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在纯然汉民族思维方式之外又提供了其他艺术思维方式。台湾原住民文学对台湾原有文学的冲击,海外华文文学在对当地文化的认同和对母体文化的归属之间所作的种种抉择,都提供了新的艺术审视、思考的角度。这使得20世纪华文文学的思维类型极其丰富多样。如果有可能大致梳理清楚20世纪华文文学文学思维的类型,我们可以看到,原先大一统的艺术思维体系被打破,一个虽斑驳杂然但无疑含有新的生命力的艺术思维体系在形成之中。例如,语言思维方式的变化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余华在他的《许三观卖血记》的《意大利文版自序》中曾谈及他“在中国的南方长大成人,然而却使用北方的语言写作”的困惑,清代前“权力向北方的倾斜使这一地区的语言成为了统治者,其他地区的语言则沦为方言俚话”。“五四”以后建立起来的白话文规范,也主要服从于政治、文化大一统的需要,强化了北方语言的支配地位。但许多作家从小所受却是家乡方言的熏陶,这就产生了余华所说的“口语与书面表达之间的差异让我的思维不知所措”的写作困惑。语言故乡的失落多少阻碍了作家用家乡方言中包含的特有的思维方式去呈现故乡人事的灵性神韵。但是,当华文文学被分割在几大块空间中时。政治大一统的影响力削弱了,汉语灵活性的空间增大了,这不仅使得作家增大了将故乡特异的氛围、节奏注入到原先的汉语系统中去的自由度,也使得地域语言思维方式有可能直接丰富汉语思维方式。时至今日,我们浏览一些台港或海外华文作品,往往很快从字里行间感觉到跟大陆文学作品的差异(此时我们还往往不了解作品内容),其中重要原因是我们最先感受到了语言层面上的差异。语言的民族文化之根是不会变的,但民族语言的现实思维形式需要在变动中不断丰富。如果对这种变动的丰富性有所揭示,20世纪华文文学史的构建可能又多了一块基石。
综上所述,从作家自我的文化身份和各地区华文文学的文化属性的变动不居上去构建一个开放意义上的华文文学生存体系,是一种值得展开的文学史思路。目前,以往近、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分期越来越遭到质疑。在淡化将鸦片战争、“五四”运动、大陆解放等重大政治事件及其相关意识形态的转变作为文学分期依据的作用后,不能用另一种意识形态替代原先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真切地去呈现20世纪华文文学起伏盛衰的面貌。也许没有必要硬性将某一事件视为某一时期文学的起终,大体描绘出文学的起伏启阖历史,文学分期就豁然可见。这正是我们从20世纪华文文学文化属性的变动不居中得到的启示。
当然,20世纪华文文学文化属性的变动不居也揭示了这一世纪文学的过渡性质。设想一下几个世纪后再来回首20世纪华文文学,其过渡时期的性质更不可置疑了吧。
收稿日期1999—0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