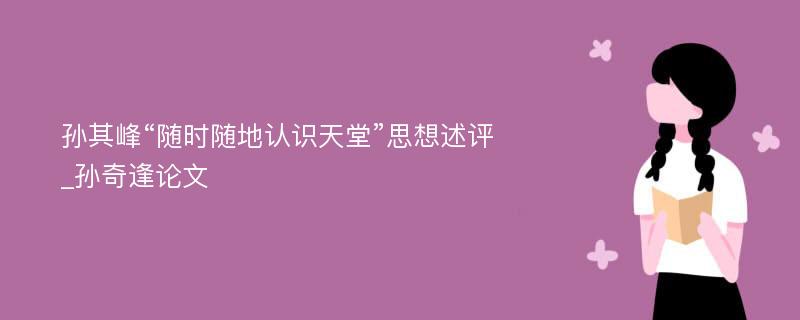
孙奇逢“随时随处体认天理”思想论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认论文,天理论文,思想论文,孙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3248.99 文献标识码:A
孙奇逢(1585-1675),字启泰,又字钟元,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道学家。因其身处新旧王朝更迭之际,田园被清贵族圈占,只得远徙他乡,到了河南辉县。由于他的特殊生活经历,使其思想具有不同于一般道学家的一面,即有着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内容。尤其他改造宋明理学意志性极强的“天理”的观念为客观世界固有的规律,它存在于自然和社会,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所以,他教人“随时随处体认天理”(《日谱》卷14)。试想,也的确是如此,人们欲成就一项事业,不都是随时随地想着怎样做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吗?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概莫能外,人人都必须如此。所以,“随时随处体认天理”的命题,是指导人生立世、指导治国安邦的一个不容动摇的根本原则。
一、“儒学本天”
作为历史悠久的儒学,孙奇逢认为它是建立在天本论之上的。基于这一认识,所以他很欣赏程颢如下的观点。他说:
程子曰:“圣学本天。”又曰:“余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己体贴出来。”(《理学宗传叙》)
这就是说“圣学本天”,也就是圣学本于“天理”。这也是孙奇逢明确讲了的。如其引录这句话之后,则眉批其上云:“圣学本天,故天理二字是先生宗旨。”(《理学宗传》卷2)这段话的原文则见于《程氏外书》,如说:“明道尝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集》,1981年中华书局版,第424页)其胞弟程颐基于这一观点说:“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二程集》第643页)是说孟轲殁后不传之学是他们兄弟俩予以继承和弘扬的,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道学之创立!然陆九渊则讲:“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事?”(《陆九渊集》,1980年中华书局版,第436页)于是乎他要全力弘扬道学了!
孙奇逢认为,就本质而言,道学是一样的。但每个人之侧重,却又不完全相同。如说:
周、程、张、朱本同也,而细论之,特以师生兄弟未分门户耳。(《孙夏峰年谱》第33页)
这说明一个问题,道学家内部在根本观点上,一开始就不是统一的。就是说二程兄弟不仅创立了道学,而且也创立了道学两派。冯友兰先生于《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论及道学时,持的就是这样的观点。且以程颢哲学“心是理,理是心”(《二程集》第139页)的根本命题为例,他不仅给心本论的主观唯心主义提供“心是理”的理论根据,而且也给理本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提供“理是心”的理论根据。理本论的朱熹不仅从说程颢“理是心”的理论,而且更打出程颐“天下只有一个理”(《二程集》第196页)的旗帜,从而直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朱子语类》,1986年中华书局版,第1页);心本论的陆九渊则从说于程颢“心是理”,直谓“心即理也”(《陆九渊集》第149页),这点则终其世而不移。他深深影响尔后明中叶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很显然,道学中见心见理之殊,则不能不说是从二程开始的。只是碍于师生兄弟情面,而未曾公开化罢了。这是二程尤其是大程的哲学特点所规定。所以,孙奇逢则直谓“于朱、陆之间见明道之学术!”(《理学宗传》卷24)
孙奇逢也是位重要的道学家。余以为他是道学发展中的否定之否定。其虽从说大程,但其思想则是在更高一个层面上的回复。他不像陆九渊那样恪守“心即理”,而容不得一点不同的观点,孙奇逢却能容得下理学一派的见解,认为“凡言天、言仁、言性、言诚、言未发、言主一者,皆我同堂共室之人,俱当浑尔我异同之见”(《夏峰集》,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52页),何必一定要于心于理争得个高低呢?“大道无南北,吾徒深异同。”(《夏峰集》第378页)其实呢,都不外乎是从出于孔门而犹未必能尽圣人之蕴罢了。比如,孙奇逢说:
夫学统于孔门,或具体而微,或名分一体,总之皆学孔子之学而识孔子之道者也,自颜、曾、思、孟以及周、程、张、朱,虽未必尽圣人之蕴,总是此一条路。路以同为异,以异为同,正不妨并存而互见之。建安亦无朱元晦,青田亦无陆子静,姚江亦无王伯安。明道云:“吾学虽有所本,天理二字是自己体贴出来。”儒学本天,天者,理也。(《日谱》卷17)
这就是说在他看来,程颢体贴出“天理”二字,正是学孔子之学的心得,而继千载之绝学也。“儒学本天,天者,理也。”儒学原本就是本天之学,就是本于天理之学。程颢度越千载,则直接把自己的学说同孔子的学说联系起来了。在孙氏看来,“自颜、曾、思、孟以及周、程、张、朱,虽未必尽圣人之蕴”,但“总是此一条路”而已。“路以同为异,以异为同,正不妨并存而互见之。建安亦无朱元晦,青田亦无陆子静,姚江亦无王伯安”,无不归本乎孔门,亦即无不归本乎天、归本乎天理!
二、“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
孙奇逢是以程颢“圣学本天”命题为是的思想家,从而提出“儒学本天”的命题,说“天者理也”。天也就是理,就是天理,它乃道学之所以为道学的根本观念。所以孙奇逢说:
何谓性学?天理而已。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非人之所能为,欲须臾离之而不得者也。佛氏于是非善恶归之平等无自别,心失天然自有之秩序,是谓无理,所以,乱教与圣人经世宰物,何啻千里!(《日谱》卷9)
这是说,性学也就是天理之学。孙奇逢说:“理者,性之理也,即天之所以为命也。”(《日谱》卷25)所以,天命、天理乃至天道,就是天地之性,就是客观世界之性,其存在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之于人,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人则离它不得。当然这不是说人们的主观于客观是毫无作为的,不是的,人们的主观有反作用于客观的能力,这就是自觉按照事物规律变革自然,变革社会。孙奇逢说:“见危授命,经世宰物,随地自见,总之一理而已。”(《日谱》卷17)即此意也。然而,佛氏则“心失天然自有之秩序,是谓无理”也。无理,他压根就不承认天理、天道或天命的客观存在,哪还谈得上什么按照规律办事而胜利地治国平天下呢?所以说“乱教与圣人经世宰物何啻千里”耶!
孙奇逢界定“天理”即“天然自有之理,非人之所能为,欲须臾离之而不可得”,则把个“天理”、“天道”或“天命”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确定了下来,说“理也者,天也”(《读易大旨》卷2。以下引此书仅注卷次),“道本于天”(《夏峰集》第457页)也。那么,天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孙奇逢肯定地说:
天者,时而已。(卷1)
时者,天时也。(卷1)
这就是说“时”或“天时”的一维性就是天,就是天理,也就是客观世界于一维性的时间里有规律地运动发展过程。子贡之所以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就是因为“性”或“天道”的存在就根本用不着说什么。比如孔子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百物生”,“四时行”,就是“天”,就是“天理”,就是“天道”,它就在百物生中,就在四时行中。这就是说“天”的根本特点就是“生”,就是“行”,万事万物一概都是不能例外的,无不是生与时生,行与时行,这就是生生灭灭的客观世界及其运动的规律性。孙奇逢说得好:
圣人未出,道在天地。天地泄其秘于未有文字之先,所以告也;圣人既出,道在圣人,圣人发其藏于既有《图》《书》之后,所以教也。(卷5)
这就是说先有天地泄其秘以告,方才有圣人发其藏以教。那么教什么呢?教天地之所告也;那么告什么呢?告天地之所生、之所行也。那么它究竟是怎样个生法、怎样个行法呢?也就是说推动其所生所行的力量是什么?是其所谓的“两”。那么“两”在哪里呢?就在天地自身所固有。比如孙奇逢曾以《易》卦六爻以象天地人之对立和统一,则是明确讲了的。如说:
天道两,则阴阳成象矣,五为阳,上为阴也;人道两,则仁义成德矣,三为仁,四为义也;地道两,则刚柔成质矣,初为刚,二为柔也;道本如是,故兼而两之,非圣人安排也。(卷3)
阴阳、刚柔、仁义,三者虽若不同,然仁者阳刚之理,义者阴柔之理,其实一也。分之以见两在之机,合之以见一原之妙。(卷4)
这两段话是说天地人原本就是一个矛盾对立统一体,这就是客观世界。“《易》模写天地间事理”(卷1)嘛。《易》卦六爻原本就是圣人主观对客观的形象写照。有客观世界运动发展泄其“生”、“行”之秘密以告天下,方有圣人发其“生”、“行”之藏以教天下。这是说先有客观的天地人一原之道,则后有圣人主观的《易》卦六爻之道。圣人《易》卦六爻之道则揭示了客观世界一原之妙。妙在哪里?妙在其自身固有“两在之机”上。这就是孙奇逢所说:
天地之道,莫善于相反而相交以为用。史则通,不交则携。天地且然,况于人乎!(卷1)
天道地道是“反交为用”的,交则通,不交则不通;人道也是“反交为用”的,交则通,不交则不通。这就是《易》道,就是圣人对天地人之道的主观摹写。人们以之为观察认识世界的方法,就能做到循理而前,按规律办事,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易》之道是打开世界之道的一把钥匙。《易》之道教人认识天道地道,其旨则在教人认识人道,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也是孙奇逢明确讲了的。如说:
言天道也,为人道榜样,总为尽人以合天。(《日谱》卷36)
天道,则涵括地道。这也就是说言天理也为人理榜样,总为尽人以合理。言天时也为人时榜样,总为尽人以合时。合时、合理、合天,则须尽人而已矣。尽人,则“须与天地合德”(《理学宗传》卷2)也。此则程颢之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孙氏正是于此眉批上道:“此句是一篇骨子。”(《理学宗传》卷2)“骨子”在哪里,就在“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即以人而合天也,也就是说主观与客观统一。孙奇逢之所以说“仁体即所谓天理也,实有诸己,须自体贴”(《理学宗传》卷2),道理也正坐于此。它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中,人们按不按天理办事,主不主动以人合天,是关键的,是之谓“实有诸己,须自体贴”!
三、“天理在日用动静上见”
程颢谓“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那么他是根据什么即根据哪件事体现出来天理的呢?不得而知。但他却有指摘旧党攻击王安石变法太过的说法。如云:“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二程集》第28页)是说王安石变法固然不对,但是,“吾党争之有太过”而激成“新政之改”,“涂炭天下”,也是不能辞其咎的。在程颢看来,这才符合实际,才是事情的全貌。这个观点倒有点列宁“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01页)的意味。否则,若或一切归过于王安石,那不公正,不实际,不能服人。这点正是孙奇逢从说于程颢的地方,即他具体地把程颢体贴天理同其谓旧党反对新法这件具体事直接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如说:
程明道曰:“新法之行,吾党激成之,当与分过。”此方是真实体贴天理。(《畿辅人物考》卷2)
所谓“此方是真实体贴天理”,是孙氏的点睛之笔。他认为程颢站在旧党立场指摘旧党在王安石变法运动中之失,才真正是具体地体贴天理。孙氏也同程颢一样作如是观,王安石变法有罪,旧党反对王安石变法太过也不能辞其咎。是之谓孙氏所云:“须要在应事接物上体贴天理。”(《畿辅人物考》卷5)天理在哪里?天理就在具体事物上。固然,“分过”则不是说的半斤八两,而是说要全面看待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他也同程颢一样,认为“涂炭天下”的责任主要应由王安石来负,但旧党也有责任。这样一来,且不说程颢“分过”之说如何,而孙氏的天理论中就具有了全面地、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新内涵。
孙奇逢于上面那段引文之前,也曾讲到明末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与反东林党的事,说“予谓东林未必皆贤,而贤者多;攻东林者未必皆不肖,而不肖者多。”(《畿辅人物考》卷2)就某种情况来说,这也同其对王安石变法与旧党反对变法的看法一样,认为这样看问题才是实事求是的。这就是说实事求是是不杂私念地看待问题,才算得上是“真实体贴天理”。于此可见,所谓“天理”就是事物自身固有的规律性,就是“天然自有之理”,它是本然的,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如孙奇逢说:
天理在日用动静上见。非谓日用动静即天理也。此处必须真实分明,方有工夫。(《日谱》卷18)
这是说“天理”是一回事,它是客观事物的规律;人们的日用动静,如王安石变法等,是人们的主观作用客观,是对是不对,则是另一回事。“天理在日用动静上见”,即天理在人们的主观作用客观的过程中反映出来。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孙奇逢看来,王安石变法是不对的,是违反天理的行为;至于“吾党争之有太过”,当然也不对,也是违反天理的行为,激成“新政之改”,“涂炭天下”,所以也难辞其咎。故而孙氏着重地提醒人们说:
日用食息间,每举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违天理拂人情处。(《夏峰集》第438页)
拂不拂人情,违不违天理,就反映在人们日用食息间一念之举,一事之行,一言之接有没有法则上,所以,则不能不慎之又慎。孙奇逢讲得好:
恐惧而无慢易之心,则日用之间举动自有
法则,一笑一言,皆哑哑然而自如矣。(卷2)
这就是说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可稍生懈怠之念。尤其当事人即“处其交履其会者,必尽变化持守之道”(《读易大旨总论》),方能于日用食息间举止有法则。这样,行动才会有自由。此仁也,亦智也。孙奇逢说:“既仁且智,何怒何惧。”(《理学宗传》卷2)恐惧之心亦自不存在矣!这说明一个重要问题,主观作用客观时,人们真能做到主观用客观统一,胆量才能够大,才能够不恐不惧,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这是由主、客观的本质关系决定的。这就是说有主观依赖客观的道理,而没有客观依赖主观的道理。且就客观而言,孙奇逢界定说:
凡不是人为处便是天。天与命总一样,在天为天,着落于人为命。(《四书近指》卷18)
又说:
自然之谓天,一定之谓命。(《四书近指》卷18)
所以说天也好,命也好,天命也好,天理也好,指的都是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它“不是人为处”。“人为处”,是就主观一方说的。主观可以认识客观,可以依规律而改造客观。但从根本上讲,客观是决定主观的,客观发展着,主观认识则必须因之而发展。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必须时刻增进认识事物的规律,服从事物的发展的自觉性,这是对主观一方的绝对要求。人生立世,无论做什么,都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天命、天理的发展是绝对的,所以,人们必须“是无一事一时可不戒惧。大人以身体之,圣贤以言传之,自尧竟舜业以至诸儒之居敬穷理,无非畏惧一念流行于无穷”(《夏峰集》第437页),从而贻害于天下后世,犹“从来不知学之人以无人管束,恣意纵情为快,不知此小人闲居为不善,自驱之陷阱之中也。”(《夏峰集》第437页)这样岂不是活该!这就告诉人们一个真理,治世者若欲立功天下,“举一念,行一事,接一言”,则不可稍违天理,忤天命,应该是身体而力行之;圣人若欲立言后世,“举一念,行一事,接一言”,同样也不可稍违天理,忤天命,必须是言传而身教之,这些都不可稍生慢易之心。“尧竟舜业以至诸儒之居敬穷理”,无不是即此旨趣。若或一念之失,而离开天理天命,则不能以人而合天,以人而合时,岂非违天理而忤天命也耶?孙奇逢说:
人为万物之灵,故贵;而不能与万物为一体,则自失其贵矣。(《理学宗传》卷5)
这话讲得很在理。本来嘛,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夏峰集》第437页)。然正因为人与禽兽有此“几希”之异,所以才把自己同万物区别开来。但是,人们若或失却警惕,不能尽变化持守之道,“不能与万物为一体”,“几希”岂不是要自己丢掉了吗?“几希”丢掉,人亦自混于禽兽矣,责任当然是自己负,是谓“自失其贵矣”,这样可又怨得了谁呢?所以说人们自觉地循天理,恪守“几希”之灵而不稍怠,则是最为重要的。实事求是地讲,这是个一步一个脚印的学问,是个真诚实践而不稍懈怠的学问,只有这样,方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君子之人也。如孙奇逢说:
君子不独畏大人,而匹夫匹妇不敢忽;不独畏圣言,而刍荛工瞽皆可采!皆所以畏此天命耳!天命在日用常行中。成汤顾諟天之明命,亦只在此处顾諟。(《夏峰集》第437页)
话说白了,若或君子单单畏大人,而不把匹夫匹妇放到眼里,那是不对的,不全面的,所以是反天命的;单单畏圣言,而把刍荛工瞽的话当成耳旁风,那也是不对的,不全面的,也是反天命的。其实,天理、天命则在人们日用常行中见,则在人们日用动静上见。孔子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话显然是不全面的,不说他把天命意志化,而且他言畏大人,显然没有把匹夫匹妇考虑进去;他言畏圣人之言,显然没有把刍荛工瞽的话考虑进去,这无疑是片面的。是犹谓旧党于王安石变法中只见王安石之失而不见自己之失的道理一样。殊不知,所谓“成汤顾諟天之明命,亦只在此顾諟”,这是主观正确面对客观的地方,则一定要慎之又慎也。既要有畏大人之心,更要有畏匹夫匹妇之心;既能畏圣人之言,更能畏刍荛工瞽之言,所谓“畏天命”,其实亦不外乎是“畏此天命耳”,岂有他哉!为治者若能畏此天命,博采众长,而时刻把百姓的力量、百姓的呼声放在心上,认识事物的规律、则必然会快一些;治国平天下的胜利把握,则必然会大一些。在孙奇逢看来,所谓“君子有三畏”,则不过是止此而已矣。这无疑是对孔子“三畏”思想的合理改造和发展。
总之,孙奇逢将宋明理学意志性极强的“天理”的观念,改造而成“天然自有之理”,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可以体贴其存在,可以遵循其发展。这样一来,孙氏便把人们的视线、人们的注意力,由天拉回到地,拉回到人们的日用食息间,拉回到人们的日用动静上,“须要在应事接物上体贴天理”,如此,人们方能相对自由地积极地立于天地之间,“随时随处,体认天理”,自觉“尽人以合天”(卷5),必能胜利地推动和平建设事业的前进和发展!
来稿日期:2000-0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