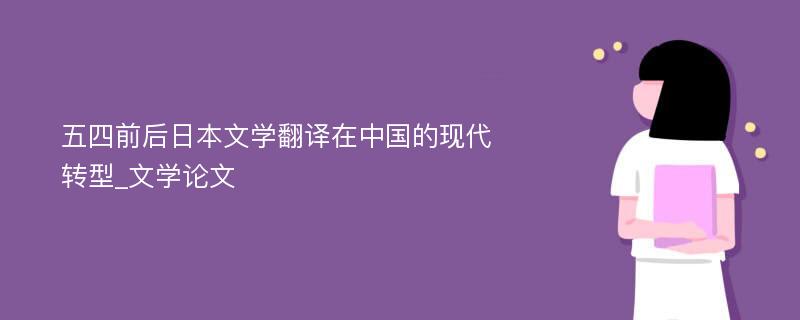
五四前后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1)01-0011-5
一、翻译选题的变化
五四前后,既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一个转折点。转折的最显著的标志,是翻译在选题上出现的明显的变化。
在五四之前,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具有浓厚的急功近利的色彩。在大多数翻译家们看来,文学翻译只是一种经世济民、开发民智或政治改良的手段。我们看中的不是文学本身的价值,而是文学所具有的功用价值。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翻译选题基本上不优先考虑文学价值,而是考虑其实用性。一方面为了宣扬维新政治,启发国民的政治意识而大量翻译日本的政治小说;一方面为了开发民智,向国民宣传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近代法律、司法制度、近代教育、军事而大量翻译日本的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冒险小说、军事小说等。而明治时代40多年间日本文坛出现的许多重要的文学家和大量优秀的作品,却大都在中国翻译选题的视野之外。如,日本近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二叶亭四迷的长篇小说《浮云》(1887-1890),直到1918年周作人于一次演讲中提到之外,此前甚至从来都没有被人提起,更不必说翻译了。这样的作品之所以没有翻译,恐怕是因为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与当时中国的需要不相适应。《浮云》所反映的是处在近代官僚制度压抑下的个人的苦恼和个性意识的觉醒,批判了当时的西化风气,而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拼命鼓吹的,却是如何培养个人的国家观念,如何引进西方文化。至于个性的觉醒与苦恼,是五四以后才被觉察并在文学作品中加以表现的。再如夏目漱石是明治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极有影响,他于1905年发表杰作《我是猫》,直到1916年去世,此后十几年间佳作不断。夏目漱石活跃的时期,正好是中国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的热潮时期,当时中国大批的留日学生,不可能对漱石一无所知,但是,漱石在那时却完全没有被译介。主要原因恐怕是夏目漱石作品所贯穿的对“文明开化”的怀疑与批判态度,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感与反思,与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文学界的主流文化不一致。上个时期得以译介的仅有一个日本大作家是尾崎德太郎(红叶)。尾崎红叶是明治文坛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文学团体“硕友社”的核心人物。当时有著名译者吴梼翻译了他的三部作品——《寒牡丹》、《侠黑奴》、《美人烟草》,但这些都不是他的代表作。这几个作品大都以异域故事为题材,之所以翻译它们,恐怕是为了迎合当时读者异域猎奇心理的需要。而尾崎红叶当时影响最大、最受迎欢的代表作《金色夜叉》,却并没有被翻译,原因恐怕也是因为该小说所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万能,与当时中国的时代主调不相协调。
还有一层原因,五四以前的中国翻译界,一方面非常重视、大力提倡或从事日本书籍的翻译,而另一方面又普遍认为日本的文化、文学比不上西方,因此翻译日本书籍只是一个方便的捷径,而不是最根本的目的。在这方面,梁启超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在《东籍月旦叙论》一文中说:“以求学之正格论之,必当于西而不于东;而急就之法,东固有未可厚非者矣。”在他看来,学问的“正格”当然应求诸西方,求诸日本只不过是“急就之法”。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有人认真地去研究日本文学,而往往只能是东鳞西爪,取己所用。所以,五四以前的20多年间,我们找不到一篇认真研究和介绍日本文学状况的文章,那些日本文学的翻译家们,包括其中的佼佼者如梁启超、吴梼、陈景韩等,对日本文学的状况都没有总体、全面、准确的了解和把握。这样,近代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选题,就不可能是以文学为本位,而常常是由非文学的因素决定着译题的选择。在译出的作品中,要么是文学与其它学科领域交叉产生的作品,如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之类;要么是通俗作品,如侦探小说、言情小说之类。而纯文学的翻译,则如凤毛鳞角,非常罕见。
而这种情况,在五四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这篇演讲系统全面地梳理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20年的文学发展情况。虽然谈的只是小说,但由于小说是日本近代文学压倒性的文学样式,因此并没有以偏概全之嫌。其中重点提到了“写实主义”的提倡者坪内逍遥及其文学理论著作《小说神髓》,“人生的艺术派”二叶亭四迷及其《浮云》,以尾崎红叶、幸田露伴为代表的“砚友社”的“艺术的艺术派”的文学,北村透谷的“主情的”、“理想的”文学,国木田独步等人的自然主义文学,夏目濑石的“有余裕”的文学与森鸥外的“遣兴文学”,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的“享乐主义”的文学,白桦派的理想主义文学,等等。当然,这篇演讲并不是没有缺憾,如对当时日本文坛崛起的以芥川龙之介、菊池宽为代表的“新思潮派”(又称“新理智派”、“新技巧派”)完全没有提到——但总体上看是抓住了日本近代文学之要领的。鉴于周作人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这篇演讲发表后,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特别是翻译选题所起的指导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重要的是,周作人的演讲开了中国研究日本文学的风气之先。五四以后,不少文学家、翻译家,都对日本文学做了认真的研究,至少是对所译的作家作品做了研究。大多数译本都是介绍作家作品的文字,而且所谈的,也大多准确可靠。有的译本还附了译者或专家撰写的上万字的序言,或者附了作家评传。这表明翻译者同时也是研究者。而在五四以前,日本作品译本中,很少有译者写的研究和介绍作家作品的“序言”或“后记”之类的文字,即便有,也只是借题发挥,而很少谈到作家作品本身。
好的翻译选题,是以全面了解被翻译国文学状况为前提条件的。它有助于译者克服选题上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由于五四以后翻译家们大都是日本文学的行家里手,因此在翻译选题上,显得既繁荣,又有序;既有重点,又比较全面。虽然五四前后乃至整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主导倾向还是主张文学为“人生”服务的,但这又不同于五四以前翻译文学中的功利主义。在他们看来,文学是手段,同时文学本身也是目的。他们对日本文学的选择还是以文学的本位的。加上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因此,在对日本文学的翻译选题上,标准与对象也非定于一尊,而是各有喜好。因此,日本文学的不同的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都有人译介,又都有各自的读者群。
在二三十年代,随着时代环境的推移,中国的日本文学的翻译在选题上也呈现出阶段性变化。五四时期,时代的主旋律是“人的觉醒”、“人的解放”和“个性的解放”。因此,最受欢迎的是像谢野晶子那样的关于向传统挑战的浪漫主义作家,译介最多的是日本的白桦派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文学。20年代中期以后,五四新文学阵营因思想分裂而崩溃,文学观念更趋多元化和复杂化。对日本文学的翻译也是如此。有人对日本的人道主义文学感兴趣,有人热衷译介日本的唯美主义文学,有人赞赏“新理智派”的小说艺术而翻译芥川龙之介和菊池宽的作品;有人受“革命文学”浪潮的影响,倾向于左翼无产阶级文学,大量翻译日本普罗作家的作品。而对于夏目漱石地样的超越流派的大家,则始终充满着译介的兴趣。
还应注意到的是,五四以前,对于日本的文学著作几乎没有译介,而五四以后,出于建设新文学的需要,对于日本近代文学理论的翻译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这也是日本文学翻译选题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对日本文学理论的译介,单从翻译的数量上看就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理论的译本占这一时期全部译作的三分之一以上,突出地表明了日本文学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文学的理论建设中对日本文学理论是如何的重视,如何地注意借鉴。因而,对日本文论的译介,应该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中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对日本现代名家名著的翻译,是日本文学翻译中最富有建设性的工作,也是最能体现翻译家的翻译艺术水平的领域。在那不到20年的时间里,日本文学中的许多中长篇名著都有了中译本,还编译出版了许多日本短篇小说名作的选本。这都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成绩,它表明我们的翻译家,在翻译的选题上已经具备了文学角度的、历史角度的敏锐眼光。越是水平高的翻译家,翻译的选题也越精到。因此,日本文学名家名著的翻译,一般都是由好的翻译家们来承担的。日本近现代的著名的作家,各种思潮、各种流派的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大都被翻译过来了。如,近代文坛的两位领袖人物——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作品,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等人的作品,自然主义作家田山花袋、岛崎藤村的作品,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的作品,新理智派作家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的作品,左翼作家叶山嘉树等人的作品,都在这时期的中国得到了译介。其中不少日本作家在中国有了自己的中文版的《选集》,重要的有《国木田独步集》、《夏目漱石选集》、《芥川龙之介选集》、《菊池宽集》、《有岛武郎集》、《谷崎润一郎集》、《佐藤春夫集》、《志贺直哉集》、《叶山嘉树集》、《藤森成吉集》,等等。
二、翻译方法的转换
五四以前的日本文学翻译,在翻译方法上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使用文言,一是在翻译时任意添削删改,截长补短,“豪杰译”盛行。
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文学,是五四以前翻译界的风尚。最为人所推崇的林纾的小说翻译,严复的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用的都是古文。在日本文学翻译界,最早翻译日本小说的梁启超,用的也是文言,后来是半文半白。本来,梁启超翻译的用意在于广为人读,以收启发民智之效,而使用文言,当然不如使用白话更有效。但梁启超还是使用了文言。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清末民初,发生了声势较大的“言文一致”运动,但是几千年形成的古文的势力更大,连一些提倡白话文的人,自己也不能经常使用白话。那时的文学家,翻译家们,受的都是古文的熏陶和教育,用惯了古文。对他们来说,使用古文写作或翻译,比使用白话文要容易的多,所以当时许多人,是先用古文来写,然后自己再“翻译”成白话文。对使用白话文的困难,梁启超有深刻的体会。他根据日本森田思轩的日文译本翻译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的时候,本来想用白话文来译,结果还是译成了文言。在《十五小豪杰·译后语》中,他交代说:“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载,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计前数回文体,每点钟仅能译千字,此次则译二千五百字。译者贪省时日,只得文俗并用,明知体例不符,俟全书杀青时,再改定耳。但因此亦可见语言文字分离,为中国文学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梁启超是嫌白话用起来不顺手,而当年的鲁迅用文言文翻译,则是嫌白话文太冗繁。鲁迅根据日文译本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时说过:“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月界旅行·辨言》)
五四以前,用文言翻译日本文学,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当时日本文学界,“言文一致”运动虽然在明治十年前后就有人提倡,但一直到了十多年以后的1887年,才出现了第一部用“言文一致”的文体写的作品——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从那以后,“言文一致”才逐渐普及。五四以前,中国翻译的日本文学文本或通过日文转译的西方文学文本,或是“汉文体”,或是“和文体”,或是“雅文体”,或是“和汉混淆体”,总之,大都不是“言文一致”的现代日本白话文体。这种情况对中国的日文翻译使用文言,是有一定影响的。当时的西方各种语言,无论是英语,还是法语,本身就没有“文言”和“白话”的纠葛。换言之,那些语种本身就是言文一致的“白话”。中文翻译以文言译西文,在文本的层面上就是对原作的不忠实;而中国以文言翻译日本的文言,起码在文体上是对等的。因此,在母语与日语的双重钳制中,五四以前中国普遍使用文言、或者半文半白的文体来翻译日本文学。用白话翻译的,只是少数作品,如吴梼根据日文译本转译的契诃夫的《黑衣教士》等俄国作品。而只有到了五四以后,白话文才完全取得了权威地位,普遍地用白话文来翻译才成为现实。
五四以前,在翻译方法上,忠实的翻译还很少见,普遍使用译述、演述、改译等方法,存在着“豪杰译”或者“乱译”的问题。这种翻译方法,不仅存在于文学翻译中,也存在于学术著作等所有领域的翻译中。如严复著名的译著《天演论》,所用的就是“达旨”(译述)的方法。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闻,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目达旨,不云笔译,即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严复后来的译著,如《原富》、《群学肄言》等,据说逐渐接近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目标,但是,用桐城派古文来译西方的言文本来一致的原作,又如何能够真正做到“信”呢?
在日本文学翻译,或根据日文译本转译的其它语种的文学作品中,这种不忠实的翻译,甚至乱译的现象普遍存在。清末民初我国所译日本的政治小说,使用的是“豪杰译”的方法。其实,在政治上说之外的翻译以及根据日文转译的外国文学译文中,情况也是如此。我国近代最早翻译的第一批欧洲国家文学作品,大都是通过日文转译的。在这批转译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豪杰译”现象。如戢翼翚根据高木治助的译本转译的普希金的《俄国情史》(今译《上帝的女儿》),不但大量删节,而且改变了原文的人称;包天笑根据日文译本转译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其实是翻译加自己的创作,连书名都按自己儿子的名字“馨儿”而改译的《馨儿就学记》。鲁迅根据日文译本翻译的几部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如《斯巴达之魂》、《地底旅行》等使用的也是译述的方法,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他在1934年写的《集外集·序言》中反省似地说:“……那时我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的很。而且文章又那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1934年5月15日在致杨霁云的一封信中又说:“青年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
总之,在五四以前的日本文学翻译,乃至所有语种的文学翻译中,在翻译方法上,大体存在三种情况。第一,在翻译“汉文体”的日文原作时,采用孙伏园所说的“勾乙”方法,“只将各种词类的序调换一下,用笔一勾就成,称为勾乙式”。(孙伏园.五四翻译笔谈[J].翻译通报,1951,(5):2.)这种情况在近代早期的日本政治小说的翻译中多见;第二,译文采用深奥难懂的文言,而且也不尊重原文,随意增删;第三,采用直译方法,对原文不作损益,但却使用文言来译,在文体上有悖原文;第四,译文使用了白话或浅近的文言,但却不是忠实的翻译。一句话,译文既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翻译时又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作品,是罕见的。
三、周氏兄弟对日本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所做的贡献及其影响
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对翻译方法上的这些问题最早做出反思和反拨的,是鲁迅、周作人兄弟两人。周氏兄弟在1909年合作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两册,选译了欧美各国16篇短篇小说。《域外小说集》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是对当时流行的乱译风气的反拨,开了五四以后新的译风之先河。但在当时,那样的“直译”却难以被读者认同和接受,出版的书只读出20来本,计划中的第三册也只好搁浅。而且,受当时时代风气的制约,译文所使用的仍然是文言文。
这种情形在五四前后得到了根本的转变。“既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又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作品”出现了,那就是周氏兄弟的翻译。
周氏兄弟在五四前后,就对文学翻译的方法问题发表了很有意义的意见。1918年4月周作人在北京大学的一次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中,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指导思想问题。他认为,以前我们之所以翻译别国作品——
便因为它有我的长处,因为他像我的缘故。所以司各特小说之可译者可读者,就因为他像史、汉的缘故;正与将赫胥黎《天演论》比周秦诸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着这样一个心思,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肯去学别人,只顾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了一点,便古今中外,扯作一团,来作他传奇主义的聊斋自然主义的《子不语》,这是不肯模仿不会模仿的必然的结果了。
我们想要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摹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特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照上文所说,中国现时小说情形,仿佛明治十七、八年的样子;所以目下切要办法,也像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
这个意见非常重要。他实际上是提出了此前中国翻译文学的本质上的问题及其根源:为什么没有出现真正尊重原文的翻译。这也是为以后提出“直译”设置了一个理论前提。同年11月,周作人在答张寿朋的信(原载《新青年》5卷6号)中说:“我以为此后译本,仍当杂入原文,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字的度量,不必多造怪字。又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后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到了1920年,周作人在他的译文集《点滴》的序中,明确说明他的翻译使用的是“直译的文体”;1924年,鲁迅在所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引言》中声明:“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1925年,鲁迅在所译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中又说:“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1925年,周作人《陀螺·序》中,进一步说明“直译”的含义:
我的翻译向来采用直译法,所以译文实在很不漂亮,——虽然我自由抒写的散文本来也就不漂亮。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近来似乎不免有人误会了直译的意思,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譬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一句,不译作“仰卧着”,而译作“卧着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反不词了。据我的意见,“仰卧着”是直译,也可以说是意译;将它略去不译,或译作“坦腹高卧”,以至“卧北窗下自以为羲皇上人”是“胡译”;“卧在他背上”,这一派乃是死译了。
周氏兄弟提出的“直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在理论与方法上,解决了近代文学翻译中存在的不尊重原作胡译乱译的问题,解决了用古文翻译外文所造成的将外国文学强行“归化”,从而失去的“模仿”价值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周氏兄弟的这些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以日文的翻译实践为基础的,因此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而且,他们在五四时期翻译并发表的日本小说、剧作和理论著作,都体现了这些理论主张,对日本文学翻译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在1920年发表的译作《一个青年的梦》,还有周氏兄弟在1920年前后翻译并陆续发表的一系列日本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在1923年以《现代日本小说集》的书名结集出版。作为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现代日本小说的选集,它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是一个开创性的贡献。《一个青年的梦》和《现代日本小说集》的出现,标志着日本文学翻译方法的转变,也象征着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的完成和崭新的时代的到来。
长期以来,周作人、鲁迅提出的“直译”法,作为在日本文学翻译中被绝大多数译者普遍遵守的一种翻译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欧美文学翻译比较而言,日本文学翻译中的“直译”更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日语中有大量汉字词汇,特别是日本近代翻译家和学者们用汉字译出的西语词汇,对于丰富现代汉语的词汇,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引进的必要性。鲁迅曾经感叹过汉语词汇的贫乏,说许多事物,汉语中都没有相应的名称。随着现代文明的输入,大量新事物的出现,汉语中的原有词汇显得不够用了,表示新事物的词汇,又不能无限制地采用“译犹不译”的音译方法来解决。而近现代日语中的新词汇,在这方面是足资借鉴的。清末民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第一代日本文学翻译家们,在翻译中引进日本新词,甚至引进日文的句法,作了开创性的努力。到了二三十年代,仍然需要做这样的努力。在此时期的日本文学译文中,我们随处都可以读到在当时、甚至在今天都感到有些陌生的日文词,和日文式的句法。现以夏丐尊译《国木出独步集》(开明书店1927年版)的译文为例。
(1)来信感谢地拜读了。(P61)
(2)村中的人们都这样自慢地批评她。(P104)
(3)平气地把烟吸着。(P117)
例(1),把“感谢”作为拜读的修饰词,在日文中常见。译者在这里是把日文的句法直译过来了;例(2)中的“自慢”是日文词,意为“自以为是”、“自满”、“自夸”等,例(3)中的“平气”也是个日文词,意为“不在乎”、“无动于衷”、“若无其事”、“平静”、“冷静”。这里举的这三个例句,无论是句法还是词汇,都是至今没有被现代汉语所接纳的。的确,我们在今天来读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文学的译文,不免会产生某些“生涩”、“不纯正”、“不流畅”、“不漂亮”之类的阅读感受。但是,当时翻译家们的良苦用心,却包含在其中。在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文学译文中,我们很难看到现在所要求的那种流畅、优美的文字,翻译家们不是不能把汉语说得更漂亮一点,而是宁愿译得生硬、拗口一些,也要把日文中可以借鉴的东西直接移译到汉语中来。上面举的至今没有被现代汉语所接纳的三个例句,毋宁说是少数,更多的是在当时看来译得别扭,而现在看来却已经符合现代汉语表述习惯。许多直接从日文中移译过来的日文词,当初曾遭到保守人士的讥笑,如“动员”、“取缔”、“经济”等,而现在,这些词早已经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了。翻译家们从日语中引进了上千个词汇,如“积极”、“消极”、“卫生”、“义务”、“具体”、“抽象”、“革命”、“干部”、“哲学”、“美学”、“目的”、“自由”、“封建”、“理论”、“漫画”、“杂志”、“剧场”、“关系”、“集中”、“经验”、“会谈”、“消化”、“动力”、“作用”、“克服”、“必要”、“申请”、“作风”等,已经是现代汉语中不可缺少的了。这就是日本文学翻译的“直译”为丰富我们的语言文字所做的特殊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0-07-01
标签:文学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日本文学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艺术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周作人论文; 浮云论文; 日语论文; 白话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