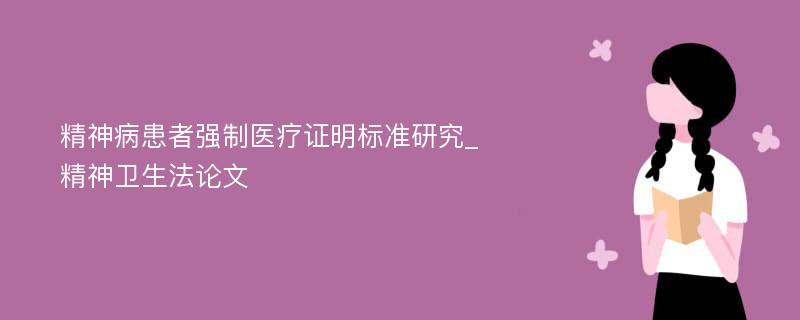
精神疾病患者强制医疗的证明标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患者论文,精神疾病论文,医疗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2014-04-20 [中图分类号]D91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226(2014)02-0208-12 强制医疗尽管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但本质上仍属于限制人身自由之措施。由于强制医疗对人身自由的剥夺并不受严格的司法程序的限制,且拘禁期限不确定,其对人身自由的剥夺程度并不亚于刑罚。同时,接受强制治疗的患者往往被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由此带来的“污名”与消极影响,可能损及精神疾病患者的人格尊严与名誉,并使其在工作、生活和学习中遭受各种歧视和排斥。因此,为保障精神疾病患者乃至正常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有必要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强制医疗设定严格的法律程序,使之符合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而“正当程序标准则意味着需采取充分严格的证明标准,以防止人身自由被错误剥夺。”①那么,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应采取何种证明标准以判断特定人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呢?这无疑是强制医疗决定程序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在我国《精神卫生法》和《刑事诉讼法》对此问题均未做出回应的情况下,有必要专门探讨之。 一、精神疾病患者强制医疗的要件及其证明 精神疾病患者强制医疗的要件直接决定着强制医疗的对象和适用范围,也实际决定着政府以强制医疗方式干预人身自由的限度。从历史发展来看,强制医疗的要件经历从宽泛到严格、从社会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发展过程,其集中体现便是强制医疗的标准从早期的“医学标准”向“危险性标准”的变迁。医学标准以患有精神疾病并需要治疗作为强制医疗的条件,医生根据其医学诊断即可将患者予以强制收治,其依据是医疗上的父权主义。但随着自主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权观念的勃兴,父权主义拘禁的正当性基础及其适用范围逐渐受到限制,需要治疗标准不再成为强制医疗的实体要件,②危险性标准逐渐取得支配地位。根据该标准,强制医疗仅限于对本人或他人具有危险性的精神疾病患者。换言之,“仅仅认定患有精神疾病并不能正当地将一个人违背其意愿予以拘禁,并将之无限期地给予监护性拘禁……州不能合宪地拘禁一个没有危险性且能够依靠本人或在亲友的帮助下自由生活的人。”③因此,对于没有危险性的精神疾病患者予以强制住院将违反宪法对人身自由的保护。尽管各国强制医疗的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普遍以个人患有精神疾病且具有人身危险性为要件。 (一)患有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 患有“精神疾病”是强制医疗的前提条件,如果某个人没有患有精神疾病或所患精神疾病已经治愈或康复,就不应该采取强制医疗措施。但“精神疾病”本身属于不确定之概念,很难对其做出精确的界定,以致有学者指出精神疾病的概念“如此模糊以致是一个无从讨论的问题。”④确实,精神疾病不仅是医学问题,还涉及文化、观念、传统、宗教、政治等因素,其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我们很难对其概念、范围、类型及其判定标准等做出一致的界定,而对于哪些类型的精神疾病可纳入强制医疗的范围更是众说纷纭,各国立法对此也存在巨大的分歧。有的国家和地区采用“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如挪威、美国、我国台湾地区等,从而将轻微、非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排除在强制治疗之外。我国《精神卫生法》亦采取该标准,将非自愿治疗的对象限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对严重精神障碍的概念做出了定义;相反,有的国家则采取更为宽泛的定义,如英国、日本等,从而授予医生十分宽泛的裁量空间以确定何种情形符合其范围。⑤各国立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明确哪些特定的状况应纳入或排除出非自愿入院。⑥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是精神发育迟滞、人格障碍和物质依赖等精神障碍可否纳入强制医疗的范围。精神发育迟滞、人格障碍等精神障碍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将这些患者非自愿收治于精神卫生机构将面临正当性质疑。因此,有的国家和地区明确将这类精神障碍排除出强制医疗的范围。例如,新西兰《精神卫生法》规定,不能仅仅以物质滥用、智障、性取向等作为强制评估和治疗的依据;我国台湾地区的《精神卫生法》亦规定,精神疾病不包括反社会人格违常者。同时,对酒精、药物等物质依赖者可否采取强制治疗则可能面临更大的争议,有的国家明确将其排除在精神障碍的范围之外。例如,英国《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酒精和药物依赖不属于精神障碍。 尽管对精神疾病的内涵和外延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对于特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离不开专业人员的判断。对此,各国法律都将精神医生的诊断作为强制医疗决定的重要依据,从而授予专家在强制医疗的启动程序中的关键角色。⑦精神疾病的诊断和认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因而有必要对诊断人员的资质和技能水平做出规定。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只有精神科医生才有资格承担诊断工作,而在其他国家,通科医生也被认为有作出诊断的资格。⑧欧洲人权委员会也认可精神障碍的医学证据可以来自于通科医生,而非只能来自于精神科医师。⑨同时,精神疾病的诊断离不开诊断依据和标准。对此,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这意味着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应以与精神健康状况无直接关系的其他任何理由为依据,包括政治、经济或社会地位,或是否属某个文化、种族或宗教团体等。此外,精神疾病的诊断应采取法定的诊断标准,在没有法定诊断标准的情况下,应以国际接受的医疗标准为依据。 (二)危险性 人身危险性是强制医疗的正当性基础,政府或精神卫生机构无权将没有危险性的精神疾病患者予以强制住院。但作为模糊与高度抽象的概念,“危险性”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需要谨慎厘定其内涵与外延。 1.危险性的概念 危险性是一个不确定性概念,作为强制医疗的标准,其适用取决于法律的解释。⑩在各国法律中,危险性概念并没由获得一致的界定。有的国家压根就没有对危险性做出任何界定,从而宽泛的授权拘禁那些符合法定条件的精神疾病患者,如英国《精神卫生法》。有的国家只规定对本人或他人的危险,而没有进一步界定什么是危险,如我国《精神卫生法》。也有国家的法律试图进一步界定危险性的类型、表现形式等,如美国一些州和判例要求危险性达到即刻危险的程度,(11)或将危险性界定为“造成本人或他人严重损害的可能性”。(12)但对危险性概念的抽象定义似乎也很难具有操作性,有学者试图从更为全面的视角检视这一概念。例如,Brooks教授将危险性概念拆分为四个构成要素:损害程度;损害发生的可能性;损害发生的频率;损害的紧迫性。(13)Hiday教授将危险性分为5个行为指标:行为类型;行为的频率;最近的行为;行为的严重性和行为的对象。(14)这为我们理解危险性概念提供新的视角,或许比抽象定义更为可行。 2.危险性的界定 针对危险标准的模糊性,有必要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该标准做出更为精确和可操作的界定。(1)危险性的程度。危险性一般表现为对本人或他人的损害风险,这种损害应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因此,有的国家要求损害必须是“严重的”,在美国少数州甚至规定损害危险必须是“即刻的”(imminent danger)。但多数州摒弃了这一过于严格的限定,规定只有精神疾病患者存在对本人或他人产生损害的合理可能性,即可违背其意愿予以拘禁。(15)堪萨斯州非自愿拘禁法代表这一模式:如果精神疾病患者在“合理可预见的将来”可能伤害自身或他人的,或造成“严重”财产损害的,可予以拘禁。同样,亚利桑那州将“危险性”界定为“根据充分的医学观点可以合理的预见精神疾病患者的行为将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然而,这一模式面临不精确的批评,但这种不精确却与其最大的优点——灵活性相联系。同时,对“危险性”概念采取更为灵活的界定,使得那些需要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能够获得适当的治疗,从而“凸显患者的医疗需求而不是武断的、弄巧成拙的强调‘权利’。”(16)(2)危险性的时间维度。特定患者的危险性只能依据其现有的精神健康状况和以往的行为予以判定,这就意味着危险性的认定是以现有和既往的行为预测其将来的危险可能性,这就给危险性的认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难度。那么,特定患者距离现在多久的行为可作为其具有实际或潜在危险性的“证据”呢?很明显,因果链条不应延伸过长,否则将导致危险性的过度预测而使患者被不当拘禁。因此,在美国很多州对危险性的认定都以被告的“最近行为”(recent act)或“明显行为”(“overt act”)作为前提条件。例如,宾夕法尼亚州规定,“对他人明显和已有的危险”限于有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精神障碍者“在过去的30天对他人造成或试图造成严重身体伤害,且有合理的可能性类似行为还将发生。”在Lessard v.Schmidt案中联邦地区法院亦持相同观点,认为危险性的认定以“试图或威胁实施严重损害本人或他人的最近的明显行为”为条件。(17)(3)危险性的类型。根据危险行为针对的对象,一般将危险性分为:对他人的危险和对本人的危险。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所有国家都允许拘禁对他人具有危险性的精神疾病患者,但对他人的危险是否仅限于暴力行为或犯罪行为则不无分歧。而基于对精神障碍者本人利益的保护,各国一般都允许拘禁对本人具有危险性的精神疾病患者,如实施或企图实施自杀或自残的患者。除了人身伤害之外,是否存在其他形式的损害(或危险)可以作为危险性的形态?如在美国,少数州规定造成他人精神损害或财产损害,可认定具有危险性予以强制住院。同时也有不少州将“严重残疾”、“需要治疗”、“不住院将导致状况恶化”或“不能满足基本需求”等作为对本人危险的表现形式。 我国《精神卫生法》对精神疾病患者的非自愿治疗也采取了单一的危险性标准,但何谓“伤害自身的危险”和“伤害他人安全的危险”却是模糊不清。例如“伤害自身”除了自杀或自伤(自残)之外,是否包括不予住院将导致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严重失能导致生活不能自理和满足基本需求等情形?如果对“伤害自身”作狭隘的理解,是否会导致急需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因不符合非自愿治疗的条件而被排除在强制治疗之外呢?同时,“伤害他人安全”是否仅限于对他人的人身危险?是否包括非人身的危险,如财产损害危险?这里所说“他人”是指特定的人,还是包括不特定的人,如公众?是否包括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的危险行为?这都有待于在实践中予以澄清。 (三)强制医疗的证明 强制医疗程序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由谁证明特定人是否符合强制医疗的要件?且应根据何种标准判定特定人已符合强制医疗的要件应接受强制治疗?这就涉及精神疾病患者强制医疗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 在美国,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强制医疗称为民事拘禁(civil commitment)或非自愿拘禁(involuntarily commitment),是指在犯罪矫正设施之外对精神障碍者的非自愿治疗或照护。(18)任何非自愿拘禁均构成对人身的限制与个人自由的剥夺,应受宪法和正当程序的严格约束。(19)因此,多数州规定,非紧急情况下的对精神疾病患者的非自愿拘禁必须取得法院的听证许可。如果精神卫生机构认为特定人应接受非自愿住院治疗的,应向法院提出拘禁申请,在听证中,精神卫生机构应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被申请人符合民事拘禁的条件。同时,法院在听证程序中应根据相关证明标准判定被申请人是否符合民事拘禁的条件,从而决定被申请人是否应接受非自愿住院。对此,多数州的民事拘禁法都规定了非自愿拘禁应采取的证明标准,从而为法院做出非自愿拘禁裁决提供标准,也为精神卫生机构提出非自愿拘禁听证的举证提供指引。 我国《精神卫生法》并未规定类似的强制医疗司法审查模式,而是由精神卫生机构行使强制医疗的决定权。《精神卫生法》第31条针对不同的危险性类型,规定了不同的非自愿治疗的决定模式。对本人具有危险性精神障碍患者的强制住院由监护人决定,而医疗机构可根据其诊断和评估将符合条件的对他人具有危险性的精神障碍患者采取非自愿住院治疗措施。同时,《精神卫生法》第32条进一步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强制住院诊断结论有异议,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对再次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主委托依法取得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可见,我国《精神卫生法》将精神疾病患者的强制医疗决定权授予给医疗机构及精神科执业医师,并建立起以医学专业为主导的强制医疗程序。相对于多数国家所采取的由法院或中立机构依据司法程序或准司法程序决定精神疾病患者的强制住院,我国《精神卫生法》所确立的强制医疗程序可称之为“医学模式”。这种模式充分发挥了医疗机构和精神科医师的专业优势,在人身自由、健康权益与公共利益的价值冲突中倾向于诊断治疗的效率和公共利益的保护。 就理解而言,既然由医疗机构行使强制医疗决定权,其就应向患者本人及其近亲属证明患者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精神卫生法》第30条第2款规定:“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本条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规定了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治疗的条件;二是规定了做出非自愿治疗决定的基本程序,即经“精神疾病诊断和病情评估”,认定就诊者符合非自愿治疗条件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精神疾病诊断”在于证明患者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系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病情评估”实际为危险性评估与预测,即证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对本人或他人实施了伤害行为或有伤害危险,其中还隐含因果关系的证明,即证明精神障碍患者对本人或他人的危险系因精神疾病所致。由此可见,就诊者是否符合非自愿治疗的条件,应由精神卫生机构承担证明责任,但应以何种标准判定精神卫生机构已充分证明就诊者符合非自愿治疗的条件呢?这就涉及强制医疗的证明标准问题。 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从而将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纳入刑事诉讼程序,并规定由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在强制医疗诉讼中,检察机关应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被申请人或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除非检察机关能够证明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的要件,否则其申请将可能被法院驳回。这一理解符合证据法的基本原理:“作为一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手段,强制治疗是国家加诸于被告人的法律负担。若使其具有合法性,检察机关就必须代表国家以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措施的正当性。”(20)因此,法院在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依据一定的证明标准认定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是否符合法定的强制医疗条件,并作出最终裁决。那么,在刑事强制医疗诉讼中应采取何种证明标准呢? 二、美国立法和判例中的强制医疗证明标准 (一)英美法中的证明标准及其类型 在英美法中,证明标准(standard of proof)是指“证明责任被卸除所要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它实际上是在事实裁判者的大脑中证据所产生的确定性或可能性程度的衡量标尺,也是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最终获得胜诉或所证明的争议事实获得有利的事实裁判结果之前,必须通过证据使事实裁判者形成信赖的标准。”(21)在诉讼中,证明标准不仅是程序问题,而且直接涉及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在涉及个人权利的案件中,“证明标准至少反映了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重视程度。”(22)在美国,各类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主要包括三个:优势证据标准(preponderance)、排除合理怀疑标准(beyond reasonable doubt)和中间标准(intermediate standard),即“清晰和令人信服”标准(“clear and convincing”)或“清晰、明确和令人信服”标准(“clear,unequivocal and convincing”)。 优势证据标准普遍适用于民事案件,这种证明标准“所具有的盖然性必须达到一种合理的程度,但不能像刑事案件要求的那样高。当法庭就举证这样说:‘我们认为其可能性大于不可能时’,此证明负担即可卸除,但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势均力敌时,证明负担则不能卸除。”(23)因此,优势证明标准的实质是要求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提出的证据的分量和证明力比反对该事实存在的证据更具说服力。(24)换言之,优势证据要求事实认定者认定“争议事实的存在比其不存在更由可能”,是事实认定者对“盖然性性优势的确信”。(25)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适用于刑事案件,在这些案件中被告的利益如此重大要求采取“尽可能排除错误判决的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予以保护。(26)在英美国家,“排除合理怀疑”是否应进行定义以及如何定义均存在激烈的争论,(27)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相反“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尽管受到种种质疑和挑战,仍然没有被其他标准所取代,并且为司法界和社会公众广泛认可,成为英美刑事诉讼和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28)对于何谓“合理怀疑”,英美判例中将其界定为“在日常生活中足以使人在决定重要事务时产生犹豫的不确定性”、“一种有理由的怀疑,不能是一种推测或猜疑”、“一种建立在共同意识基础上的怀疑”以及将“排除合理怀疑”界定为“一种对被告人有罪的内心的坚定相信”、“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等界定方式。(29)但无论如何,“排除合理怀疑”作为严格的证明标准,要求追诉方对被告人指控之证据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因为,“在刑事案件中,被告的利益如此重要,从而受到证明标准的严格保护,以最大可能排除错误判决的可能性。”(30) 中间标准——通常并列使用“清晰的”(clear)、“令人可信的”(cogent)、“明确的”(unequivocal)、“令人信服的”(convincing)等词语。这一标准最典型的是适用于涉及欺诈或其他准犯罪行为的民事案件,这些案件中所涉利益被视为比纯粹金钱损失的案件更为重要。此外,一些司法管辖区为了减轻被告无故受到名誉损害之风险,而增加了原告的举证负担,从而采取该证明标准。同样,一些法院使用了“清晰、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明标准以保护在各种民事案件中特定个人的重要利益。(31)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涉及个人权利剥夺但没有达到刑事控诉程度的各类案件中,包括送入精神疾病院、监护权的终止、国籍的剥夺和驱逐出境,联邦宪法或可适用的联邦制定法要求运用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证明标准或其他类似证明标准。(32) 尽管三个证明标准有着各自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但三者之间的界限并不并不十分清晰,尤其是“清晰和令人信服”标准与“优势证据”标准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之间的区别。对此,一些学者尝试运用量化方法解读证明标准,“优势证据”标准要求待证事实的证据精确度超过50%,“清晰和令人信服”要求争议事实的证据精确度至少超过70%,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要求证据的精确度超过95%。(33)尽管量化方法面临较多的批评,但也为证明标准的理解提供更为直观的视角。 (二)强制医疗诉讼中证明标准的选择 在诉讼中选择适当的证明标准主要考虑以下3个因素。(34)(1)司法成本或司法效益(Judicial Economy)。如,选择过高的证明标准是否会过度增加司法成本或降低司法的效率,这就涉及“司法效率是否比个人权利的保护更为重要”这一问题。(2)错误信息(Erroneous Information)。即,采取不当的证明标准将可能导致不当证据的采信,从而导致错误判决的发生。而“法律程序的功能就是要将错误判决的风险降至最低。”(35)(3)被告权利(自由)的性质及其重要性。正当程序的一项基本原理是权利越重要,程序保护程度和范围也随之增加。因此,当被告面临重大自由利益损害之时,正当程序要求给予更大力度的程序保护。(36) 具体到精神疾病患者非自愿拘禁决定程序中的证明标准问题,联邦最高法院曾在阿丁顿案中有过专门阐述,具体应考虑以下因素。(1)个人利益的保护及其平衡。尽管国家享有保护社会和为无自我照顾能力的人提供照护的重大利益,但这一利益并不必然优先于对个人自由的保护,民事拘禁程序中采取适当的证明标准必须合理平衡个人和州之间的利益。(37)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民事拘禁程序中的个人利益如此重要,正当程序要求州承担比优势证据更为严格的举证责任以证明拘禁的正当性。”而“‘清晰、明确、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能够平衡个人权利和州的合法利益。”(38)(2)纠正错误判决的可能性。刑事案件中适用严格证明标准的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避免错误判决的发生,“但这一理念并不适用于民事拘禁”,因为在民事拘禁中即便出现错误也能够在“第一时间予以纠正。”(39)(3)证明的可能性及其成本。精神医学诊断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使得很难“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个人患有精神疾病和危险性。如果采取刑事案件的严格证明标准,无疑将增加证明的难度和可能性,实际上并不符合精神疾病患者的利益。 (三)强制医疗证明标准的确立及其发展 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州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必须具有重大利益(compelling interest)方具有正当性。不管是出于国家监护权(parens patriae)还是警察权(police power),各州对精神疾病患者的非自愿拘禁都必须证明其符合法定的标准,而各州对此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及其程度则取决于非自愿拘禁所采用的证明标准。然而,在20世纪70年年代之前,法院几乎没有考虑民事拘禁所涉及到的证明标准问题。第一件广泛关注举证分配的案件是1972年的Lessard v.Schmidt案。(40)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民事拘禁所伴随的剥夺人身自由比驱逐出境更为严重。(41)因此,仅依“单纯的优势证据”作出判决将难以获得正当性,应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作为民事拘禁的证明标准。Lessard案被其他法院所遵从,但也有法院拒绝适用这一严格的证明标准,认为“非自愿拘禁听证的目的不仅仅是剥夺自由”,“治疗和帮助个人确诊患有精神疾病和对本人或他人具有即刻的危险性,是更重要的目的。”(42)从当时各州立法看,13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事拘禁法采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25个州只要求“明确和令人信服”标准。(43)可见,在20世纪70年代,各州立法和司法对民事拘禁的证明标准存在较大的分歧,直到1979年的Addington v.Texas案联邦最高法院才着手解决民事拘禁的证明标准问题。(44) 1.“清晰和令人信服”标准的确立:Addington V.Texas 在本案中,阿丁顿(Addington)系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被多次被拘禁于德克萨斯州的多家州立精神卫生机构。1975年12月18日,上诉人因“恐吓攻击”其母亲而被逮捕,之后其母亲根据德州法律提出不定期拘禁上诉人的申请。在初审中,阿丁顿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疾病,但认为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他对本人或他人具有危险性。初审法院根据“清晰、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明标准认定阿丁顿患有“精神疾病并需要住院治疗”。而德州民事上诉法院认为民事拘禁应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从而做出撤销了初审判决的裁决。 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本案后认为,证明标准的功能是“指导事实认定者”,并服务于诉讼当事人之间错误风险之分配。在诉讼领域主要有三种证明标准,分别是优势证据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中间标准,即“清晰和令人信服”或“清晰、明确和令人信服”。三种证明标准适用范围不同,且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民事拘禁程序应适用哪种标准,法院认为“必须评估个人不受非自愿不定期拘禁的利益与州在特定证明标准下拘禁精神疾病患者的利益”,并铭记“法律程序的功能是将错误判决的风险降至最低。”法院解释到,任何目的的民事拘禁均构成对自由的严重剥夺,从而应受到正当程序的保护;同时,非自愿拘禁将对个人产生不利的社会影响,应谨慎选择相关证明标准。 法院考虑到精神医学诊断的不确定性,如果适用过于严格的证明责任,将给州施加不合理的负担,并对需要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之治疗树立不合理的障碍,从而认为正当程序并不要求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作为民事拘禁程序的证明标准。同时,考虑到对人身自由的保护和当程序的要求,民事拘禁的证据标准应比优势证据标准更为严格,并认为“清晰、明确和令人信服”等中间标准能够平衡个人权利和州的合法利益。值得注意的事,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应采用何种层次的证明标准。因此,各州可以在立法和司法中自由选择“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清晰和令人信服”的标准,只要采用的证明标准比优势证据标准更为严格即可。结果是各州在认定个人对本人或社会是否具有危险性时,所采用证明标准并不完全相同。(45) 评论者普遍赞扬阿丁顿案是一个具有逻辑性和平衡性的裁决,“敏锐的满足了平衡个人自由利益和州政府为患者提供治疗的利益之间的冲突。”也有人批判该案“是将正当程序引入精神疾病领域的倒退”,(46)认为“联邦最高法院没有提供充分的程序权利保护,从而防止错误剥夺一个人的宪法权利。”(47)但无法否认的事,阿丁顿案对非自愿拘禁证明标准的解释对后续案件和各州的立法产生重大影响。为回应判决,许多州降低了证明标准,将“清晰和令人服”标准取而代之。(48)目前,只有少数州采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包括肯塔基州、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等。也有个别州采取更为复杂的证明标准,如蒙大拿州将证明标准一分为二:医疗事实的证明采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其他事项的证明采取“清晰和令人信服”标准(49)。而夏威夷州则根据不同的拘禁对象和条件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对本人或他人具有即刻危险或严重残疾或明显患病”的人的拘禁采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而对“需要治疗而又没有更小限制替代措施”患者的拘禁则采取“清晰和令人信服”标准。(50)可见,阿丁顿案只是确立了民事拘禁最低限制的证明标准,但并没有彻底解决非自愿拘禁的证明标准问题,各州仍可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清晰和令人信服”标准之间进行选择。 2.强制医疗证明标准的发展 从后续的判例看,联邦最高法院对非自愿拘禁的证明标准似乎并没有采取一致的观点。例如,在Heller v.Doe中,(51)肯塔基州的法律规定,对精神疾病非自愿拘禁的审查应采用严格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而对精神发育迟滞的拘禁采用更宽松的标准(明确、可信服标准)。联邦最高法院判定这一区分具有合宪性,且不违反平等保护条款。同样,在Jones v.United States案中,(52)联邦最高法院对因精神疾病而无罪释放者的民事拘禁适用优势证明标准,而没有适用Addington案的证明标准,理由是在刑事追诉中被告自己提出精神疾病抗辩,且在精神疾病无罪的认定中已对精神疾病和危险性做出了认定,从而已最大程度才降低了错误拘禁的风险。 2010年,United States v.Comstock案涉及对性暴力侵犯者非自愿拘禁的证明标准问题。(53)该案涉及5名联邦监狱局关押下的性暴力侵犯者,在被非自愿拘禁后,他们对根据《美国联邦儿童保护与安全法》(Adam Walsh Child Protection and Safety Act,简称“Adam Walsh”法案)的合宪性提出挑战。根据“Adam Walsh”法案的规定,政府对性暴力侵犯者的拘禁需有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一个人符合以下要件:(1)实施或试图实施性暴力行为或猥亵儿童;(2)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3)如果释放将难以抑制实施性暴力行为或猥亵儿童。联邦最高法院在撤销第四巡回法院的判决后将该案发回重审,第四巡回法院重新审理后认为,“Adam Walsh”法案所采取的证明标准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如果采用更为严格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造成政府在民事拘禁程序中难以克服的障碍,从而不利于防范性暴力行为和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和精神健康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54)在Comstock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将Addington案中的证明标准引入到性暴力侵犯者的拘禁案件中,尽管还无法确定“清晰和令人信服”标准是否将成为性暴力侵犯者法的证明基准,但至少给采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州发出“清晰和令人信服”具有合宪性的信号,并将促使各州降低性暴力案的证明标准。(55) (四)小结 根据联邦法院的判例和各州的立法,美国非自愿拘禁的证明标准始终游离于“清晰和令人信服”标准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之间,且以“清晰和令人信服”标准作为最低限度的证明标准,从而排除适用民事案件的“优势证据”标准。(1)在民事拘禁案件中,“清晰和令人信服”标准居于支配地位,这不仅获得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可,在各州立法中也占据主流,而只有少数州采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2)在精神疾病患者实施犯罪行为且提起精神疾病无罪抗辩的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降低了非自愿拘禁的证明标准,从而采取了优势证据标准。(3)对性暴力侵犯者非自愿拘禁案件中,联邦法律和判决倾向于采取“清晰和令人信服”标准。尽管仍有不少州对此类型案件适用刑事证明标准,但受Comstock案的影响,可以预见更多州将会采用中度证明标准。(56) 三、我国强制医疗的证明标准 (一)非刑事强制医疗的证明标准 如上所述,我国《精神卫生法》将强制医疗决定权授予给了医疗机构。由于精神疾病患者的非自愿治疗由医疗机构单方面决定,患者的陈述权、参与权、提交证据、质证、抗辩等程序性权利均未获得应有的重视,正当程序的缺失成为我国非自愿治疗制度的缺憾。同时,由于强制医疗欠缺司法机构或其他中立机构的审查或决定,强制医疗的诉讼程序或准诉讼程序也就无从构建,而强制医疗程序中所涉及的证明问题,如举证责任、证明内容与证明标准等均被淡化,甚至无从谈起。在医学模式下,医疗机构既是强制医疗关系的当事人,又是强制医疗的决定者;既由其承担就诊者符合强制治疗条件的举证责任,又由其单方面行使强制医疗的决定权。然而,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并不受任何程序的制约,在做出强制医疗决定时,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亦无从确定。毕竟证明标准作为诉讼程序中的证据法问题,在非诉讼程序中是否具有适用的余地和意义则不无疑义。当然,如果将精神卫生机构仍然视为依据专业知识作出强制医疗决定的中立裁决者,证明标准问题仍有探讨的余地。 应该说,我国强制医疗所采取的医学模式沿袭了以往由医疗机构决定强制住院的传统,符合现有的精神医疗模式和精神卫生体系的现状,且操作简便、运行成本低廉,在兼顾患者权利的同时,提高了强制住院决定的效率。然而,强制住院决定不仅涉及医学判断(是否患有严重精神障碍)还涉及法律判断(如危险性),而对于危险性的判定与预测,已不仅仅是医学问题,还涉及危险的范围、类型、判定方法等复杂法律问题。尤其是强制医疗关乎人身自由的剥夺与限制,涉及精神疾病患者的基本人权,已绝非纯粹的医学判断问题,由医疗机构和医生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是否合适则不无疑问。对此,不少学者提出强制医疗的决定权应由法院行使,通过司法程序决定精神疾病患者的人身自由限制问题。(57)纵观各国立法,由法院或中立机构行使强制医疗的决定权已成为各国普遍采取的模式,这也应成为我国《精神卫生法》和强制医疗法律制度从未来发展的趋势。 强制医疗的法治化进程关键在于程序构建,核心在于建立司法审查程序,以确保由中立的第三方对关乎公民自由的重大事项作出独立、公正的裁决。(58)而在构建强制医疗司法审查程序中,证明标准则是无法规避的关键问题之一。基于强制医疗决定的特殊性,精神疾病患者强制医疗的审理和裁决不应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而应适用民事诉讼特别程序。在特别程序中,强制医疗的证明标准适用普通诉讼的证明标准还是特别证明标准则值得特别探讨。我们认为,强制医疗证明标准的选择应考虑以下因素:(1)强制医疗的目的在于治疗而非惩罚,本质上符合患者本人的根本利益。因此,不应适用过于严格的证明标准,避免将应该接受治疗的患者排除于强制医疗之外。(2)强制医疗毕竟直接限制和剥夺了精神疾病患者的人身自由,而人身自由作为公民最重要的一项权利,是公民享有和行使其他权利和自由的前提,(59)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理应受到更为严格的程序制约,包括较高的证明标准。因此,为避免强制医疗的滥用和错误强制治疗的发生,强制医疗的证明标准不应采取较低的证明标准,如类似英美国家的优势证据标准。(3)强制医疗可否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则需考虑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性质。 我国《民事诉讼法》采取了“证据确实充分,事实清楚”这一“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明标准不仅高于前述英美法系国家的一般民事证明标准,而且高于这些国家的刑事证明标准,该标准因司法者及诉讼相关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和诉讼实际条件的限制而不具有现实性和可能性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60)2002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第1款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定。”根据该条规定,我国民事诉讼中正式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61)学界也普遍认为这是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我国的体现和法定化。(62)而我国民事诉讼所采取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是否等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则不无争议。(63)但是,由于我国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是指“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需“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它与美国的“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证明标准应相当或基本相当。就此而言,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强制医疗特别程序中的证明标准可采取类似美国的中度证明标准,即“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证明标准,而该证明标准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基本相当。 (二)刑事强制医疗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刑事强制医疗的证明标准,而第53条规定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是否能适用于强制医疗程序则值得深入探讨。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4条的规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包括三个条件:(1)实施暴力犯罪行为,即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2)患有精神疾病而无刑事责任能力,即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3)具有社会危险性,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基于上述3个要件不同属性和功能,本文认为应区别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前2项要件系犯罪构成要件,应适用刑事证明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而危险性要件应适用中度证明标准,即“清晰和令人信服”标准。理由如下: 首先,刑事强制医疗的适用以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为前提,而证实某人实施犯罪行为关系到其人格、尊严以及他人的评价,与个人的基本权利息息相关。因此,对于犯罪行为的证明,无论是在普通诉讼程序还是在特别程序中,都应实行最高的证明标准,也即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64)即便是对精神病人的犯罪行为的认定,也应与普通程序一样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不得因其精神状况而降低标准。 其次,刑事责任能力是刑事诉讼中定罪裁判的重要认定内容之一,其证明标准应统一适用刑事证明标准,即便是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亦不例外。一则防止正常人或应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藉由强制医疗程序逃避刑事制裁;二则避免不应接受强制医疗的人被强制治疗,防止“被精神病”的发生。毕竟强制医疗作为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其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不受期限限制,尤其是精神病和强制医疗所带来的污名和不利影响实际上可能比刑罚还更严重。因此,无论从追究犯罪、制裁违法,还是从保障人权、防止强制医疗的滥用,都应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明采取严格证明标准。 最后,精神病人危险性的认定应采取中度证明标准,而不应采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优势证据”标准。第一,对犯罪行为的证明属于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证明,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可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而对于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的证明在性质上是根据证据对将来事实的一种预测,(65)而“行为人有可能实施危险行为永远都不可能表现为‘排除合理怀疑’”(66)。事实上,法律和医学界对危险性预测的准确性从来都持怀疑态度,(67)美国精神卫生协会曾告知联邦最高法院精神医学专家做出的危险性预测三分之二都是错误的,(68)联邦最高法院亦认为“精神医学预测精神病人的未来风险行为并不准确”。(69)如此,由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法官对危险性做出“排除合理怀疑”的认定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必然增加强制医疗审理的成本和难度,并最终可能导致应该接受强制治疗的患者被排斥于医疗机构之外,从而损害精神疾病患者的健康利益。第二,强制医疗并不具有惩罚性,而是以治疗为目的,通过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以恢复健康并消除其社会危险性。如果设置过高的证明标准,将导致应该接受治疗的患者流落社会,不仅不利于本人健康,也可能增加再犯之危险,从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第三,由于强制医疗涉及人的自由的剥夺,其证明标准应高于一般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如类似英美国家的优势证据标准。 从美国经验看,联邦最高法院对因精神疾病而无罪释放者的民事拘禁也适用“优势证据”标准,而未适用更高的证明标准。但值得注意的,“优势证据”标准适用的前提是被申请人已被判决无刑事责任能力而被释放,且在诉讼中本人提出精神疾病无罪抗辩。因此,先前的判决中已证明被申请人患有精神疾病而刑事责任能力,法院在预测其危险性时,错误判断的可能性降低,故适用较为宽松的证明标。然而,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并不具备上述前提和条件,无论是在侦查阶段由公安机关移送检察院申请启动强制医疗,还是检察院依职权申请和法院依职权启动强制医疗审理程序,事先均未对被告人的是否构成犯罪及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做出认定。换言之,被告人或被申请人是否实施暴力犯罪行为和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都属于待证事实,不应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 综上,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应针对不同的证明内容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符合强制医疗的基本属性和特定,并具有理论上的合理依据。以“排除合理怀疑”和“清晰和令人信服”相结合的证明标准能够合理平衡了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健康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有利于实现强制医疗在维护健康、保障人权和防卫社会等方面的功能。 近5年相关研究文献精选: 1.陈学权:未实施犯罪的精神病人对强制医疗的司法救济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 2.纵博:论强制医疗程序的证明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3.周维平:对强制医疗条件的审查,《人民司法》,2013(6) 4.纵博,陈盛:强制医疗程序中的若干证据法问题解析,《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7) 5.朱晋峰,宫雪:强制医疗程序的诉讼化建构——基于强制医疗程序行政化色彩的分析,《证据科学》,2013(2) 6.倪润:强制医疗程序中“社会危险性”评价机制之细化,《法学》,2012(1) 7.陈绍辉: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研究,《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①Alexander Tsesis.Due Process in Civil Commitments.68 Washington & Lee L.Rev..,259(2011). ②Stuart A.Anfang and Paul S.Appelbaum.Civil Commitment—The American Experience,3 Isr J.Psychiatry Relat.Sci.,211(2006). ③O'Connor v.Donaldson,422 U.S.563(1975) ④Michael L.Perlin.Mental disability law:civil and criminal(volume 1),Matthew Bender & company,1998.p.62 ⑤Richard M.Jones M.A.Mental Health Act Manual.london.Sweet & Maxwell,2012,p.20 ⑥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人权与立法资源手册》,第68页。 ⑦David T.Simpson,JR.Involuntary Civil Commitment:The Dangerousness Staneard and its Problems.63 North Carolina L.Rev.,246(1984). ⑧前引⑥,第83页。 ⑨Schuurs v.the Netherlands,1985,10518/83 ⑩See supra note7,at246 (11)Lessard v.Schmidt,349 F.Supp.1078(E.D.Wis.1972). (12)马塞诸塞州民事拘禁法第1条。G.L.c.123第1条 (13)A.D.Brooks.Law,Psychiatry and The Mental Health System.1974,675; 转引自Michael L.Perlin.Mental disability law:civil and criminal(volume l).Matthew Bender & company,1998.p.99 (14)Hiday.Court Discretion:Application of the Dangerousness Standard in Civil Commitment,5 L.& Hum.Behav.,275-276(1981). (15)Collin Mickle.Safety or Freedom:Permissiveness vs.Paternalism in Involuntary Commitment Law.36 Law & Psychol.Rev.,303(2012). (16)Id.at 305 (17)See supra note 11 (18)Christoper Slobogin.Law and the Mental Health:Civil and Criminal Aspects,Thomson/West,2009.?p.701 (19)Grant H.Morris.Defining Dangerousness:Risking a Dangerous Definition.10 J.Contemporary Legal Issues,64(1999). (20)纵博、陈盛:《医疗程序中的若干证据法问题解析》,《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3期。 (21)Peter Murphy.Murphy on Evidence,Blackstone Press Limited,6th ed,1997,p.109;转引自牟军:《民事证明标准论纲——以刑事证明标准为对应的一种解析》,《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 (22)Addington v.Texas.441 U.S.418(1979). (23)Rosamund Reay.Evidence,OLD Bailey press,1999,p.89;转引自冷根源:《论英美证据法上的民事证明标准》,《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5期。 (24)冷根源:《论英美证据法上的民事证明标准》,《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5期。 (25)[美]约翰·W.斯特龙:《麦考密克论证据》,汤唯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页。 (26)See supra note22. (27)陈永生:《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在西方面临的挑战》,《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杨宇冠、孙军:《“排除合理怀疑”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证据科学》2011年第6期;赖早兴:《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法律科学》2008年第5期。 (28)余剑:《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运用》,《东方法学》2008年第5期。 (29)陈永生:《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在西方面临的挑战》,《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 (30)See supra note 22 (31)Id. (32)前引25,第658页。 (33)Scott M.Brennan.Due Process Comes Due:An Argument for the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tiary Standard in Sentencing Hearings.77 Iowa L.Rev.1804,(1992).. (34)Id,at1814-1817. (35)See supra note22. (36)Speiser v.Randall,357 U.S.513,520-21(1958). (37)Note."We're Only Trying to Help":The Burden and Standard of Proof in Short-Term Civil Cimmitment.31 Stanford L.Rev,439-442(1979). (38)Ssee supra note 22. (39)Id. (40)See supra note11. (41)最高法院已经在一件驱逐出境案中裁定,剥夺自由应比“纯粹过失案件”适用更高的举证责任。因此,在该案中应采信“清晰、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See Woodby v.Immigration & Naturalization SERV.358 U.S.276,(1966). (42)French v.Blackburn,428 F.supp.1351,(M.D.N.C),443 U.S.901(1977). (43)Alexander Tsesis.Due Process in Civil Commitments.68 Washington & Lee L.Rev.272(2011). (44)See supra note22 (45)Peter D.Keane.The Use of the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Standard in Civil Commitment Proceedings Pursuant to The Adam Walsh Act Does Not Violate Due Process.3 J.Health & Biomedical L.,673,(2012).. (46)See supra note4,p.399 (47)See supra note 43,p.263 (48)Id,at272 (49)MONT.CODE ANN.§ 53-21-126(2011) (50)HAW.REV.STAT.§ 334-60.2(2),334-60.5(i)(2010). (51)509 U.S.312(1993) (52)103 S.Ct.3043(1983). (53)627 F.3d 513(4th Cir.2010) (54)See supra note 45,p.679 (55)See supra note 43,p.279-282 (56)See supra note 45,p.679 (57)参见房国宾:《精神病强制医疗与人权保障的冲突与平衡》,《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7期;戴庆康、葛菊莲:《精神障碍患者保安性非自愿住院的主体与标准问题研究》,《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李筱永:《强制医疗制度中精神病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与保护》,《卫生软科学》2011年第7期。 (58)陈卫东、程雷:《司法精神病鉴定基本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 (59)周伟:《保护人身自由条款比较研究》,《法学评论》2004年第4期。 (60)牟军:《民事证明标准论纲——以刑事证明标准为对应的一种解析》,《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 (61)参见李国光:《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62页以下;黄松有:《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页。 (62)李浩:《证明标准新探》,《中国法学》2002年第4期。张家骥:《对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理论反思》,《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2期。 (63)有学者对我国民事诉讼法采取了大陆法系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证据规定》所指的“高度盖然性”不同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参加吴泽勇:《中国法上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清华法学》2013年第1期。 (64)前引20。 (65)同上。 (66)《哈佛法律评论》编辑部:《精神病人的民事收容:理论与程序》,朱江译,载《哈佛法律评论,刑法学精粹》,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67)Cocozza & Steadman,The Failure of Psychiatric Predictions of Dangerousness: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29Rutgers L.Rev.,1084,1085(1976). (68)Barefoot v.Estelle,463 U.S.880,(1993). (69)See supra note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