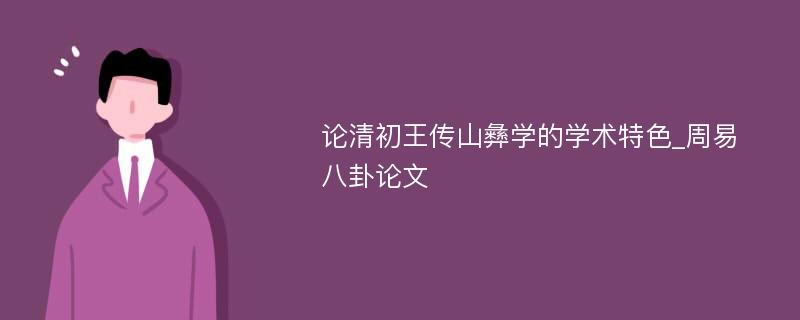
从清初学术看王船山易学的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易学论文,学术论文,特色论文,看王船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0)04-0083-07
王船山是清初著名的经学家、易学家。研究他的易学不能离开清初学术,因为易学作为学术的一个门类,不能超然于学术之外,而只能在一定的学术背景下进行。船山治《易》是在清初学术背景下进行的。清初学术承晚明而来,由于理学末流的空疏,以及时代的动荡,使这一时期的学术有别于先前,大有从理学回归于经学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则以反思与批判理学、博大宏伟、经世致用、回归经典等特征表现出来。清初学术的这些特征无疑对船山易学产生重要影响,大体决定其易学的基本特色。
一、修正和批判宋易
明清之际,理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由于其空谈虚理、不务实功而渐趋没落,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现实的要求,促使学术界对其进行修正与批判,表现在船山易学中则是对宋易的修正与批判。他之所以对宋易进行修正与批判,是因为宋易在具体事物之外设置了一个“虚悬孤致之道”,(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十一章。)此道是虚伪无实的。具体地说,包括对义理派和图书派批判两个方面。
对宋易义理派的修正和批判。船山易学虽倾向于义理派,但对宋易义理之学并不十分满意。他指出:“宋之言《易》者,虽与弼异,而所尚略同。苏氏轼出入于佛、老,敝与弼均,而间引之以言治理,则有合焉。程子之《传》,纯乎理事,固《易》大用之所以行,然有通志成务之理,而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张子略言之,象言不忘,而神化不遗,其体洁静精微之妙,以益广周子《通书》之蕴,允矣至矣,惜乎其言约,而未尝贯全《易》于一揆也。”(注:《周易内传发例》三。)在船山看来,就总体而言,宋易义理派重视义理,反对象数,符合圣人作《易》的宗旨,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义理派也存在着很多不足,主要是他们过分重视义理,而多少忽视了象数及其他,这一点与王弼有相似之处。苏轼《东坡易传》流于佛老方外,援佛老入《易》,这一点与王弼以玄学治《易》方法相同,皆有背离易学的倾向。程颐《伊川易传》讲理事,使《易》“通志成务”之大用得以施行,摆脱了释老虚无之学的束缚,是正确的,而继王弼黜象数而崇义理,以《序卦》为释卦之旨,纯乎讲事理而不与于筮占,以及否认“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即否认事物生化中的一种偶然性,则是错误的。张载既言义理又讲象数,发挥《易》阴阳刚柔之象,符合《易》旨,因为这揭示了《易》的神化之功,体帖事物发展的不测之神与精微之妙。但美中不足是过于简略,未能“贯全《易》于一揆。”船山修正宋易重视义理忽视象数的片面性,使两者统一起来。
船山对朱熹易学也提出批评。其原因是:“朱子学宗程氏,独于易焉尽废王弼以来引伸之理,而专言象占。”(注:《周易内传发例》三。)尤其不赞成朱熹把《易》视为卜筮之书,因为这否认了《易》作为人生哲理之书的特点。朱熹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提及《易》为卜之书,他曾说:“八卦之画,本为占筮。方伏羲画卦时,止有奇偶之画,何尝有许多说话!文王重卦作《繇辞》。周公作《爻辞》,亦只是为占筮设,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去。”(注:《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易二》纲领上之下。)朱嘉把《易》视为卜筮之书,是从其最初形成意义上讲的,他也承认,自孔子治《易》后,从中推出许多义理来,《易》在孔子那里已不是卜筮之书。船山对朱熹的批评也有偏激之处,但对宋易重视学忽视占的修正,是正确的。
船山集中批判了宋易中的图书派。他认为,邵雍把《易》归纳为整齐的次序与方位是错误的。君子有所作为,在于显天道,以昭人道,崇德而广业。而邵雍之图,“如织如绘。如饤如砌,以意计揣度,域大化于规圆矩方之中。”又“一切皆自然排比,乘除增减,不可推移,则亦何用勤勤于德业为耶?疏节阔目,一览而尽,天地之设施,圣人之所不敢言,而言之如数家珍,此术数家举万事万理而归之前定,使人无惧而听其自始自终之术也。将无为偷安而不知命者之劝耶?”(注:《周易内传发例》十三。)邵雍之图“域大化于规圆矩方之中”,且“一切皆自然排比,乘除增减,不可推移”,显然把丰富多彩,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归于机械的易图之中,这是一种僵化的思想模式。在船山看来,这陷入“术数家举万事万理而归之前定”的先验论泥坑。如果依着他的主张,人们便可以“端坐以俟祸福之至”,“无为偷安”了。这也背离了《易》不可为典要的宗旨。
船山集中批判了邵雍的卦序,邵雍说:“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上交于阴,阴下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迭用柔刚,《易》六位而成章也。”(注:邵雍:《皇极经世》卷七上,《观物外篇·先天象数二》。)意思是太极生阴阳两仪,两仪之上又各生一阴一阳,而为太阴、少阳、少阴、老阳四象;四象之上又各生一阴一阳,为坤、艮、坎、巽、震、离、兑、乾八卦;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阴一阳,为十六,十六之上各生一阴一阳为三十二,三十二之上各生一阴一阳为六十四卦。这是所谓的加一倍法,朱熹称其为“破作两片”。船山认为,这种方法与《易》中阴阳互蕴的思想相违背。“《皇极经世》之旨,尽于朱子破作两片之语,谓天下无不相对待者耳。乃阴阳之与刚柔,太之与少,岂相对待者乎!”正如“少即太之稚也,太即少之老也,将一人之生,老少称为二人乎?自稚至老,渐移而无分画之涯际,将以何一日焉为少之终而老之始乎?故两片四片之说,猜量比拟,非自然之理也。”(注:《思问录·外篇》。)阴与阳、刚与柔不是截然对立的,不可云二,而是合和统一的。如同一个人从少到老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但这种发展与变化是在人这个统一体中进行的,其前后相互关联,岂能截然分开?
可以看出,船山对宋易的基本态度是站在义理派立场,抨击邵雍先天图书象数易学,修正程颐、张载、朱熹义理之易。
二、以《易》统摄诸学科
清初学术的博大宏阔,是指批判理学独尊后,先秦诸子学、经学、史学、理学、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各门学科全面发展,王国维说:“国初之学大”(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概括了这一时期的学术特征。清初学术的博大在船山易学中也有所体现,因为《易》本身就是一个包括众多学科在内的百科全书。纪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注: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一·易类一》。)船山解《易》博大,指把多种学科纳入其易学体系中,并分别论述了它们与《易》的关系。
关于历法,船山认为,它只是“象数已然之迹,而非阴阳往来之神”。(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四章。)任何历法都有它的局限性,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天象的认识。而天象是在不断变化的,也即“日运刻移,东西循环,固无一定之方”,“自岁差之法明,尧时冬至日在虚,周、汉以后冬至日在斗,而今日在箕之度矣。”(注:《思问录·外篇》。)由于天象的变幻莫测,要了解天象就必须坚持灵活变通的原则,切不可拘泥于陈规陋法。与历法有所不同,《易》则是阴阳往来之神,象数已然之迹正是阴阳往来之神变化的具体显现。因此,他得出结论是:“犹《易》可以衍历,历不可以限《易》。”(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四章。)在《易》与历法的关系上,《易》可以衍历法是承认《易》比历法更根本,历法不可以限《易》,是说《易》比历法更博大。
关于地理,扬雄著《太玄》,把“太玄”视为宇宙之模型。船山指出:“其所仰观,《四分历》粗率之天文也;其所俯察,王莽所置方州部家之地理也。进退以为鬼神,而不知神短而鬼长;寒暑以为生死,而不知冬生而夏杀。方有定而定神于其方,体有限而限《易》以其体。”(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四章。)依扬雄之见,便把《易》限制在固定不变的范围之内。船山认为,“方圆整齐之象,皆立体以限《易》,而域于其方,虽亦一隅之理所或有,而求以肖无方之神,难矣哉!”(注:《周易内传》卷五上,《系辞上传》第四章。)这表明《易》道广大采备,不能限《易》于一隅一域。
对于律吕,船山认为,律历本于《易》才有变通。他说:“夫律者上生下生,诚肖乎七八九六之往来,而黄钟之数十一,则天五地六之一数也。数全而仅用其二,以之建方,以之立体,是拘守其一,而欲蔽其全矣。故《易》可以该律,律不可以尽《易》,犹《易》可以衍历,历不可以限《易》。”(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四章。)黄钟所用之数十一,其实是《系辞》中的天五地六一对数,其它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并没有涉及,只能是《易》的一个局部。以偏概全,以局部蔽整体,是片面的。因此,律不可以尽《易》、限《易》,律来源于《易》。对于数,船山认为,有象才有数,数因象而生。《河图》五十五之数是“纪天地之化”的,数只是《易》的一个组成部分,非《易》全体。如果仅以数来解释《易》,那么就会陷入数术之学。他说:“充邵康节、蔡西山之道,可勿仅以数学名也。始姑就之,天下趋焉;终遂耽之,大道隐焉。”(注:《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子产对黄熊》。)把《易》只归结为数,是以小术隐大道。
船山还以《易》来统摄其它经书,从常变、理事等角度解释《易》与诸经的关系。
关于常变关系,他指出:“礼之兴也于中古,《易》之兴也亦于中古。《易》与礼相得以章,而因《易》以生礼。故周以礼立国,而道肇于《易》。《易》全用而无择,礼慎用而有则。礼合天经地纬,以备人事之吉凶,而于《易》则不敢泰然尽用之,于是而九卦之德著焉。《易》兼常变,礼惟贞常。《易》道大而无惭,礼数约而守正。故《易》极变而礼惟居常。”(注:《周易外传》卷六,《系辞下传》第七章。)就时间而言,礼与《易》产生时代大体相同,就逻辑说,是礼生于《易》。另外,两者特征、功能不同,礼有据有则,贞常而不变,《易》则兼顾常变。又说:“是故圣人之教,有常有变。礼乐,道有常也,有善而无恶,矩度中和而形成不易,而一准之于《书》;《书》者,礼乐之宗也。《诗》、《春秋》兼其变者,《诗》之正变,《春秋》之是非,善不善俱存,而一准之于《易》;《易》者,正变、是非之宗也。(注:《周易外传》卷七,《说卦传》。)礼乐指社会伦理的法则、常规,《书》是先王的法典、告示、誓词等政治文献,是有典有要的法则,是礼乐之宗,具有不变性,均属常。《诗》以比兴而言志,有褒贬,《春秋》判定是非,权衡善恶,为变。把《易》以外的经书分为两类,各有常或变的特征,只有《易》才真正兼顾常变。“《诗》、《书》、《礼》、《乐》之教,博象以治其常;龟莛之设,穷数以测其变。合其象数,贞其常变,而《易》以兴焉。”(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三章。)其它诸经与龟莛各执象数一端,象至常有定,数极变无穷,《易》合象数,把常变统一起来。
关于理事关系,他认为,“《春秋》之记事也”,《春秋》为记事之作,应与《易》为表里,“故曰:‘《易》言其理,《春秋》见诸行事。’”(注:《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十一章。)《易》重在言理,而《春秋》为记事之作,它们之间的联系,可谓互为表里。他说:“天下之情,万变而无非实者。《诗》、《春秋》志之。天下之理,万变而无非实者,《易》志之,故曰:《易》言其理。《春秋》见诸行事。”(注:《周易外传》卷七,《说卦传》。)《诗》与《春秋》反映的是天下之情与事,《易》召示的是天下之理,圣人“本《易》以制礼,本礼以作《春秋》,所谓以礼存心而不忧横逆之至者也。”(注:《周易外传》卷六,《系辞下传》第七章。)《春秋》之作本于礼,制礼又本于《易》,《春秋》本于《易》。正如在理事关系上,事本于理一样,诸经皆本于《易》。
船山从常变、理事关系角度论述《易》与其它诸经的关系,旨在说明《易》是诸经的根本,其它诸经统一于它。他指出:“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注:《周易外传》卷六,《系辞下传》第三章。)他把其它诸经只当作反映天下之象,具体地说是天下之象的不同侧面,各有其特点,而《易》则统一其它诸经。基于这种认识,船山在自己非易学著作中也大量地运用易学观点,以此来说明、解释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就是说他的易学思想渗透到其它著作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易学也是博大的。
三、用《易》经世
清初学术上的经世致用是针对明末以来学术界空谈心性以及社会动荡而展开的一场学以经世、挽救社会的思潮。经世致用在船山易学中表现为用《易》经世,他治《易》不徒托空言,而把学《易》与运用《易》了解宇宙自然、立身、评说政事等结合起来。
船山说:“体三才之道,推性命之原,极物理人事之变,以明得失吉凶之故,而《易》作焉。”(注:《周易内传》卷一上,《上经乾坤》。)既然《易》的任务在“极物理人事之变”,就必须首先对宇宙自然有个基本观点。他把《易》运用于自然,解释自然现象,提出:“言天者征于人,言心者征于事,言古者征于今。”(注:《张子正蒙注》卷八,《乐器篇》。)这是由空谈转入实功,把理学蹈虚空谈的“格物穷理”变为探索质测之学的“实功”。本此,他对张载关于海水潮汐的假说提出批评:“不及专门之学以浑天质测及潮汐南北异候验之之为实也。”(注:《张子正蒙注》卷一,《参两篇》。)又指出朱熹关于自然现象的臆断:“朱子谓虹霓天之淫气,不知微雨漾日光而成虹。”(注:《张子正蒙注》卷八,《乐器篇》。)他还提出“延天祐人”的思想,说:“圣人与人为徒,与天通理。与人为徒,仁不遗遐;与天通理,知不昧初。将延天以祐人于既生之余。而《易》由此其兴焉。”(注:《周易内传》卷五,《系辞上传》第二章。)圣人对民行仁德,对天通晓其理,延长自然的功能,为人类服务。他借助《易》中的太极、阴阳、道器、理气、动静、有无等范畴对宇宙自然现象给予说明。
船山易学与其一生出处行谊、经历忧患有关。他远祧文王、周公、孔子,而近宗张载。文王、周公处忧患中而演《易》。《系辞》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子承其绪发挥“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晚年读易至韦编三绝。至于张载之学则无非《易》。船山深知易道出于忧患,自己又处于社会大变革时代,治《易》抒发忧患之情。他以易理出入于险阻,对《易》终生服膺不忘,每逢忧患之时,都从《易》中有所得,并凭此在忧患中仍然振奋。他处于亡国之秋,犹能发扬刚毅,不灰心丧气。他说:“明夷本以明而受伤,象大明为地所掩,”“然两间之启闭有象,则天下有其时;而君子即可体之以为德。夷者,时之变也,而君子之常也。故死生祸福皆天之道,即皆圣人之德,非穷神知化者,其孰能知之。”“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箕子“于艰难备极之日,彝攸叙之道未尝一日忘之,则迹自晦而道自明,是以利贞。然则箕子怀道以待武王之访乎?非也。箕子无待武王之心,而访不访,存乎人者不可期也。君子虽际大难,可辱可死,而学道自其本务,一日未死,则不可息于一日,为己非为人也。怀道以待访,则访不可必,而道息矣。志节之与学问,道合于一而事分为二。遇难而恣情旷废,无明道之心,志节虽立,独行之士耳,非君子之所谓贞也。”(注:《周易内传》卷三上,《明夷》。)是借箕子处忧患之世不辱身不降志,来抒发自己的气节与意志,虽然亡国,但士大夫的志节不可丢,表现了一种在逆境中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这是用《易》立身之实例。
船山总结历代君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是非得失,认为,君主经世必须用《易》。他说:“四时之将改,则必有疾风大雨居其间,而后寒暑温凉之候定。”“汤武体天之道,尽长人、合礼、利物、贞干之道以顺天,文明著而人皆悦,以应乎人,乃革前王之命。当革之时,行革之事,非甚盛德,谁能当此乎?”(注:《周易内传》卷四上,《革》。)“当革之时”,采取“疾风大雨”式的手段“行革之事”,是符合天道的行为。用疾风暴雨比拟汤武革命,是他对“革命”行为的赞颂,反映明末清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呼声。
清政权建立以后,船山看到反清复明已无希望,面对现实,他说:“君子以风行天上之理,自修明于上,而无为之化,不言之教,移风易俗,不待政教而成矣。”(注:《周易内传》卷一下,《小畜》。)他借风行天上来阐述开明政治的理想。统治者“自修明于上”,即以身作则,上行必然下效,社会风气就会好转,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又告诫统治者天下太平后,也应居安思危,时存戒惧之心。“天下晏定,各循其分,所虑者,人亡厝火积薪之忧而竟于仕进。”(注:《周易内传》卷二上,《蛊》。)安而忘危,趋于利禄之途是很危险的。他反对统治者为推护其统治,在经济上搞绝对平均,提出:“君子施惠于民,务大德,不市小惠。不知治道者,徇疲惰之贫民,而铲削富民,以快其妒忌,酿乱之道也。故求荒者,有蠲赈而无可平之粟价;定赋者,有宽贷而无可均之摇役。虽有不齐,亦物情之固然也。”(注:《周易内传》卷二上,《谦》。)社会上的贫富不均是正常的,正如物有不齐一样,硬要削富益贫,这是施小恩小惠,不是务大德。
船山用《易》解释安邦治国,主张德刑兼顾。释《损》卦时说:“内卦方生为德,外卦立制为刑。损民以养君,损质以尚文,损情以适事,损德以用刑。”又“《损》《益》者,阴阳交错以成化,自然之理,人心必有之几,《损》不必凶,而《益》不必吉也。”(注:《周易内传》卷三下,《损》。)他认为,正如《易》有损益相互补充一样,德刑也应兼顾。“君子为不可犯而乃以全天下之愚顽。不善用谦,以称兵制胜,是鸷鸟之将击戢翼,猛兽之将攫而卑伏,虽利亦险矣哉。”(注:《周易内传》卷二上,《谦》。)这要求统治者宽猛相济,刚柔并用,德威兼施,对被统治者应行“无为之化”,才能“端拱而治”。
四、重视对《易》本文的解释
清初学术回归经典指回到以通经学古为特色的经学。理学治经的特点是借经发挥己意,重道轻经,明末以来,此风愈演愈烈,忽视对经本文的解释,由此造成空谈性道。面对这种情况,学术界掀起了一场自救运动,转向古老务实的经学,以取代走向穷途的理学。回归经典,也即对经学的倡导,表现在船山易学上就是重视从《易》本身出发对其性质、原则进行诠释,即使对其义理的发挥也大体遵循《易》的内在逻辑。
对于《周易》的性质,《系辞》解释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是说言论效法卦爻辞,行动效法卦爻的变化,制造器物效法卦象,判断吉凶效法占法。君子要有所作为应先向《易》请教,《易》可告知努力的方向,它是天下最精妙的典籍。这四者前两者讲的是学《易》,后两者讲的是占《易》的问题,按《系辞》的解释,《易》是占与学的统一,不过占只是形式,学才是内容。船山对此评道:“夫子阐《易》之大用以诏后世,皎如日星,而说《易》者或徒究其辞与变以泛论事功学术,而不详筮者之占,固为未达;又或专取象占,而谓《易》之为书止以前知吉凶,又恶足与圣人垂教之精意!占也,言也,动也,制器也,用四而道合于一。道合于一,而必备四者之用以言《易》。”(注:《周易内传》卷五上,《系辞上传》第十章。)船山同样把这四者看成占与学的关系,他既反对后来说《易》者只讲辞与变的学《易》,也反对专讲象与占的占《易》,认为言、动、制器、占这四者,也即学与占是统一的,从他的易学看,占只是《易》的一种职能,而察言观变才是其主要任务。与《系辞》一样,把《易》视为充满宇宙、人生哲理的典籍。
船山治《易》十分重视解《易》诸原则体例。对于爻位说,他肯定“其例有阴有阳,有中有不中,有当位有不当位,有应有不应,有承有乘,有进有退。”(注:《周易内传》卷一上,《乾》。)并在解《易》中广泛地加以运用。
当位说,指一卦六爻各有其位,二、四、六为偶数阴位,一、三、五为奇数阳位,阳交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即当位或得位,阳爻居阴位、阴爻居阳位,即不当位或失位。一般说,当位吉,不当位凶。如既济卦,初九居阳位,六二居阴位,九三居阳位,六四居阴位,九五居阳位,上六居阴位,六爻当位。《象》说:“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以此释卦辞“亨小,利贞。”船山对此解释说:“以常理言之,则利贞。”(注:《周易内传》卷四下,《既济》。)又未济卦,六爻皆不当位。《小象》解此卦六三辞:“未济,征凶”说“未济,征凶,位不当也。”船山说:“位不当而欲上进则必凶。”(注:《周易内传》卷四下,《未济》。)
应位说,指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其位相应。应位分有应与无应。应位分有应与无应,阳爻和阴爻相应为有应,阳爻之间或阴爻之间无应。一般说,有应吉,无应凶。如大有卦五阳一阴,六五爻居于阳位,为不当位,不吉利,可六五卦辞说:“厥孚交如,威如,吉。”《彖》说:“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船山解释说:“居阳之中曰‘大中’。位尊,故上下皆应。”(注:《周易内传》卷二上,《大有》。)上下应指六五爻与九二爻有应,虽不当位,也吉。又如未济卦六爻皆不当位,可卦辞说“亨”。《彖》说:“虽不当位,刚柔应也。”船山解释说:“不当位而应以无疑。”指初与四、二与五、三与六皆有应,因此,亨。
中位说,指居上下卦之中,即二、五爻位。一般说,虽不当位,也吉。如噬嗑卦六五并不当位,但居上卦之中,《彖》说:“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船山释曰:“‘不当位’,谓六五也。变否塞之道,柔自初而上行以得中,其妄而治以刑,合于义,故‘利’。”(注:《周易内传》卷二下,《噬嗑》。)五爻应属阳位,六五居之,不当位,但六五居上卦之中,为中位,也吉利。
趋时说,指卦象之吉凶与所处的时机不同有关。如同居中位,不一定都是吉,适时吉,失时凶。节卦九二、九五居中。《彖》说:“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而九二爻辞说:“不出门庭,凶。”《小象》说:“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船山释曰:“‘极’,至也。时至事起而吝于出,则败而物怨之。”(注:《周易内传》卷四下,《节》。)九二虽居中位,但应出而不出,失去时机,所以凶。
承乘说,指一卦中临近两爻,下为承,上为乘。上爻为阳,下爻为阴,为阴承阳或阳乘阴,为顺、吉。上爻为阴,下爻为阳,为阴乘阳或阳承阴,为逆、凶。如归妹卦初九、九二、九四皆为阴所乘,《彖》说:“无攸利,柔乘刚也。”船山释曰:“外卦二阴乘一阳,内卦一阴乘二阳。阳妄动而为阴所乘,则败于家,凶于国。”(注:《周易内传》卷四上,《归妹》。)上卦六五乘九四,下卦六三乘九二,皆阴乘阳或阳承阴,六五虽居中位,也不吉利。
往来说,指卦中各爻可以上下往来,由上到下为来,由下至上为往,卦义及卦辞的吉凶可以用往来说明。如无妄卦,乾上震下,《彖》说:“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船山释曰:“外卦皆阳,阳与阳为类,而一阳离其群,间二阴而在下,以主阴而施化。”(注:《周易内传》卷二下。《无妄》。)上卦乾为刚,来到下卦之中,成为震卦初九爻,此爻又统率二阴,以此解释乾上震下,“动而建”。
船山也运用《易》中的取象说。《大象》是取象说,以八种自然现象解释八卦,进而解释卦象的义理。其对卦义的解释,先讲自然现象,后讲人事生活教训,可谓天道与人文合一。船山尤重视《大象》的研究,所撰《周易大象解》是专门诠释《大象》的著作。如师卦《大象》说:“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宽民畜众。”先讲“地中有水”,以自然现象解释师卦坎下(水)坤上(地)的特点,后则讲人事,君子应像土能盛水那样,容纳百姓,对百姓宽容。船山释曰:“地中之水,无见水也;君子有民,无见民也。君子观于地之容水,以静畜动,而得抚民之道焉。士安于塾,农安于亩,淳者漓者,强者弱者,因其固然,不争不扰而使之自辑。”(注:《周易大象解·师》。)君子像土容纳水一样,对百姓宽容,让他们修生养息,不要扰民,体现其兼容并包的品格。先讲自然现象,后讲人事,符合《大象》本义。他后来撰《周易内传》释师卦《大象》时也体现这一点。
船山治《易》时也如实解读其中的基本原理。如《易》中所包含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自然界生成图式;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变易思想;天道与人道相一致,人道必须效法天道的天人合一问题;以及天尊地卑,君臣、父子、主从、上下依附关系,等级观念等,船山都加以准确把握。
就学术内在的发展逻辑而言,清初学术由空谈性道的理学转向通经致用的经学。这一趋势是以修正和批判理学为先导的,批判理学独尊及空谈虚理,导致各门学科的发展、经世致用思潮的出现以及经学的复兴。但自康熙二十二年后,随着清廷对全国进行有效的统治,清廷逐步确立了以尊朱熹为特色的崇懦重道的文化政策,使理学日趋僵化,思想领域的专制开始。经学本来包含通经与致用两方面,由于当时政治思想的影响,通经代替致用,经世致用趋于消沉。这赋予理学转向经学另外的内涵,即理学转向通经学古,换言之,取代理学的经学实质上是经学考据学,这表明学术朝着通经学古的经学考据学的路子走去。这一趋势也反映在船山易学上。顺治十二年撰写的《周易外传》为他早年的代表作,此书是通经致用的著作,可以说是《易》的应用,康熙二十五年撰写的《周易内传》为他晚年代表作,此书为解经之作。从通经致用到解经的转变,大体与清初学术发展趋势一致。看来“退伏幽栖,俟曙而鸣”的船山,也没有囿于学术背景之外。
[收稿日期]1998—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