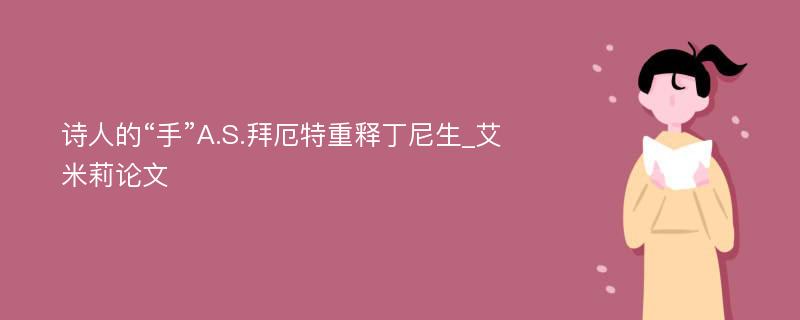
诗人之“手”——A.S.拜厄特重新解读丁尼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人论文,拜厄特论文,丁尼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当代女作家A.S.拜厄特在其创作的第二部“新维多利亚小说”《天使与昆虫》之《婚姻天使》篇中,①以虚构的形式重新讲述了19世纪桂冠诗人丁尼生和他的挚友亚瑟·哈勒姆及妹妹艾米莉·丁尼生的故事,描绘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丁尼生为悼念哈勒姆早逝而创作的悲悼诗《悼念集》以内文本的形式贯穿故事始终。小说围绕两场家庭降神会展开,通过虚构的灵媒莉莉斯·帕佩格(Lilias Papagay)和索菲·施克(Sophy Sheekhy)以及虚构化的真实历史人物,将历史与虚构融为一体。拜厄特通过人物内心独白将自己对于《悼念集》的理解和评述巧妙地融入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思想活动。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婚姻天使》是拜厄特以小说形式展开的丁尼生诗歌批评。她对丁尼生、艾米莉与哈勒姆故事的重构其实就是她与不同流派的丁尼生批评以及《悼念集》本身的一场对话。正是由于《婚姻天使》所具有的学术性和思辨性特点,批评家们将其称作“批评小说”(ficticism),即以小说形式展开的文学文化批评。②
T.S.艾略特在评价丁尼生时曾说:“偶尔,一个诗人由于某种奇特的巧合表达了一代人的情绪,与此同时他也表达了一种与同代人不同的个人情绪。这并不是缺乏诚挚,而是因为在意识的层面下服从与对抗相互融合。”③在《婚姻天使》中,拜厄特无疑强调了丁尼生思想中“个人”的一面。与我们所熟悉的维多利亚时代代言人的形象相比,拜厄特笔下的丁尼生表现出更多的内心矛盾以及大卫·肖所说的“有趣的不确定性”。④
作为与弥尔顿的《利西达斯》及雪莱的《阿多尼斯》齐名的悼亡诗,《悼念集》中的悲悼结构与丁尼生自身精神成长之间的联系一直为评论家所关注。对哈勒姆的悲悼无疑极大地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丁尼生的生命观、自我观以及精神和物质观。创作于1842的《悼念集》原标题为《心灵之路》(The Way of the Soul)。它通常被视为记录诗人心灵成长的精神自传,呈现了诗人从失去挚友后的悲伤、绝望、怀疑到重铸信心与希望的心灵轨迹。但拜厄特在《婚姻天使》中对丁尼生的重构却凸显了他在悲悼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物质性焦虑(anxieties about materiality),这种焦虑被批评家视为维多利亚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时代症候之一。正如达娜·席勒指出的那样,拜厄特笔下的丁尼生既对物质主义所描绘的冰冷冷的生命图景感到恐惧,又不由自主地为物质性所吸引。⑤
《悼念集》中反复出现的“手”的意象集中体现了丁尼生对生命物质性的思考。许多评论家都曾对诗中“手”的意象进行分析,但这些分析大多从丁尼生与哈勒姆之间情感关系的角度入手,重点论述《悼念集》中“手”以及与手相关的“触摸”、“拥抱”等意象所带有的情欲蕴涵(erotic charge)。拜厄特对丁尼生的重构同样围绕着“手”的意象展开,但她却赋予其更为深刻的文化寓意。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拜厄特在小说中对“手”这一意象的解读,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丁尼生物质观和生命观的重新阐释。
一、从欲望之“手”到救赎之“手”
批评家们很早就注意到物质性尤其是物质性肉身在《悼念集》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牛津大学教授A.C.布莱德里在其评述《悼念集》的专论中指出,诗人的悲悼最初始于对哈勒姆肉体复活的渴望:“来,显现我所熟悉的容貌/让我从你的同类中认出你的灵魂。”(2.5-6)⑥似乎脱离了具体可感的形象,诗人的悲悼便无以寄托。⑦第二首诗中,诗人表达了与哈勒姆墓旁的紫杉树融为一体的愿望。约翰·罗森伯格指出,紫杉树的意象无疑承载了诗人对哈勒姆肉体存在的欲望,与紫杉树融为一体,诗人便可拥抱咫尺之遥的哈勒姆。丁尼生希望、也愿意相信哈勒姆已经超越肉体的羁绊,融入自然和上帝永恒的怀抱,而他与哈勒姆的重逢将是彼此灵魂的交融:“我的灵魂缠在他的灵魂中/在思想的九天之高急转。”(95.37-38)但另一方面,他对哈勒姆的悲悼又表现出强烈的肉身依附性,他无法接受哈勒姆的身体也会慢慢腐烂、分解直至化为尘土的事实,他只有不断诉诸“触摸”、“拥抱”等可以感知的物质化方式,以抵御对哈勒姆肉体消亡的恐惧。⑧显然,这种恐惧不仅仅源于哈勒姆的死亡,它是一个越来越推崇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时代的精神产物。
罗森伯格认为,亚瑟·哈勒姆,尤其是丁尼生对哈勒姆的爱,是《悼念集》的首要主题。丁尼生对于永生的思考植根于他渴望看到并触摸哈勒姆的无尽欲念,因此才有那些无处不在的手的意象。⑨在《悼念集》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为罗森伯格的论断找到证据。第7首中,诗人用“手”来借代哈勒姆:
昏暗的屋边我再度站立,
站在这不可爱的长街上;
在这门前,往常我的心脏
为等待一只手总跳得急。
可这只手再也无从紧握——(7.1-5)
在第10首中,作者再次发出感叹,
那常常被我紧握的手,
竟然同水藻和贝壳纠结在一起。(10.19-20)
在第14首中,诗人希望哈勒姆“能够突然把手放在我的手中”,(14.11)而在第119首中,诗人故地重游,手的意象也再次出现:
这门前,我的心曾经猛跳,
如今我又来,但并不流泪;
祝福你,因为你双唇温柔,
明亮的两眼中充满友情;
于是我几乎没叹息一声,
就仿佛感到你握着的手。(119.1-2,9-12)⑩
在这些诗行中,“手”的意象无疑承载着诗人对哈勒姆的欲望。第13首诗中对“鳏夫的手”的描写在批评家眼中具有最为强烈的情欲色彩:
鳏夫在睡梦中看到
新近逝去的妻子的身形,
他满怀疑虑地伸出手,触摸到
一片空白,他的眼泪滚滚而下。
哭泣,丧亲之痛永生难忘。
心与心交叠的地方,如今一片虚空。
温暖的手掌紧紧握住的,如今已悄无声息,
直至有一天,我也变得无声无息。(13.1-8)(11)
克里斯托弗·克拉夫特指出,丁尼生运用异性爱欲和婚姻作为比喻,以表现自己对哈勒姆的热烈情感和欲望。(12)
关于丁尼生与哈勒姆之间情感关系的界定一直是丁尼生研究者们无法回避的话题。在《悼念集》第93首中,丁尼生祈求哈勒姆的亡灵:“下来,抚摸,进入;倾听/那个无法用言语命名的强烈愿望。”(93.13-14)杰夫·努诺加瓦指出,对于当代读者而言,这种无法命名的愿望不能不使人想起王尔德为同性恋辩护时所提到的“那种不敢说出名字的爱”。(13)但也有批评家认为:“维多利亚人对于同性之爱的观念无法被一个醉心于弗洛伊德的时代所正确理解。他们看到的只是纯粹的友谊,现代读者却认定为性反常。”(14)克里斯托弗·里克斯在他撰写的丁尼生评传中曾经指出,丁尼生对哈勒姆的爱并非同性恋之爱,但他仍然认为,对于《悼念集》中流露出来的同性情爱予以关注并非一种时代错误:“那些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感到不安的维多利亚人,对《悼念集》同样感到不安。”(15)
克拉夫特在《“下来,抚摸,进入”,丁尼生奇特的称呼方式》一文中详细记述了不同时期的评论者对《悼念集》所表现的同性爱欲的不同反应。(16)据该文记载,自1850年《悼念集》甫一问世,其中所蕴藏的欲望机制便引起评论家的关注。《泰晤士报》1851年11月28日刊登的一篇匿名评论对诗中的情欲比喻和“情人般温柔的语气”进行指责;查尔斯·金斯莱也曾撰文表示,他在《悼念集》中发现了一些古老的同性故事的影子;丁尼生的儿子哈勒姆·丁尼生在为父亲创作的传记中,谨慎地删除了任何可能引起“同性恋误解”的材料。克拉夫特指出,与这些惴惴不安的维多利亚人相比,现代批评家大多对诗中表现的情欲采取一种迂回的批评策略。哈罗德·布鲁姆在《丁尼生、哈勒姆与浪漫主义传统》(1966)一文中宣称:“丁尼生的缪斯是,并且一直都是哈勒姆,没有人需要再为此感到不安……一个诗人作为诗人(a poet qua poet)的性渴望与纯粹的经验没有关系。”里克斯则回避从文学角度对文本中的欲望进行分析,他认为应该由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对丁尼生的情感性质进行界定。对此,克拉夫特评价道,重要的不是如何描摹出一个饱受痛苦折磨的心灵潜在的病理轨迹,而是话语在表述欲望的同时如何作用于欲望本身。(17)克拉夫特的观点显然受到福柯有关性话语理论的影响。
克拉夫特认为,在《悼念集》中,丁尼生通过文本的形式使自己对哈勒姆不同寻常的欲望得到规诫和升华。对于哈勒姆的“抚摸”和“手”的欲念最终升华为对基督救赎之手的渴望。
那时我灵魂也可乔迁,
同你既共命运又共爱,
超越这痛苦的狭隘地带,
融合在一起后飞向彼岸;
最后到达那终点的洞天——
在那里,死于圣地的耶稣
会把他亮光光的手伸出,
把我们当一人接进里面。(84.37-44)
基督宽容的怀抱吸纳、消融了强烈的同性情欲,他像一个仁慈的父亲,“从黑暗中伸出手掌/穿越自然,塑造人类”。(124.23-24)基督的赐福将使诗人与哈勒姆的灵魂最终合而为一,并一同融入到自然和神的怀抱里。(18)
罗森伯格的观点与此相似。他指出,丁尼生笔下的哈勒姆与耶稣基督之间具有一种明显的类比关系,他是基督在人间的完美化身。诗中多处引用《圣经》对耶稣的描写以暗示这种类比关系。“情欲升华论”在丁尼生研究者中颇具代表性。约翰·亨特等人都曾撰文论述《悼念集》中欲望的净化和精神化过程,即从相握的手到相融的灵魂。但时至今日,关于丁尼生与哈勒姆之间究竟是否同性恋的讨论依然在继续。
二、诗人之“手”与道成肉身的艺术
《婚姻天使》中大量与《悼念集》相对应的“手”的意象表明,拜厄特没有回避丁尼生与哈勒姆情感关系中的情欲成分。小说中,在丁尼生的妹妹、老年艾米莉的回忆里,我们似乎捕捉到某些她不愿提及但又难以忘怀的感觉和画面:“如果她能完全坦诚地面对自己,她记得曾经看到两个男人的背影,两双腿,急切地爬上安放着白色床铺的阁楼,而她的感觉如同一个被关在天堂外面的人。”(226)(19)尽管艾米莉的叙述向我们表明,丁尼生和哈勒姆把自己关在阁楼上的目的只是为了不受打扰地讨论诗歌,但是,接受过弗洛伊德理论熏染的当代读者无法不去猜想那扇门把什么关在了我们(以及艾米莉)的视线之外。当然,拜厄特笔下的艾米莉似乎不会像我们一样浮想联翩:“并不是说她对阿尔弗雷德感到嫉妒——她怎么会?她,艾米莉,才是亚瑟要娶的人,是她的脚步令他屏住呼吸,是在她的唇上,他印下那些紧张而急迫的吻。”(260)然而,时隔40年之后,在艾米莉的意识屏幕上,哈勒姆与丁尼生亲密无间的情景依然清晰如昨日。透过老年艾米莉的回顾性眼光,我们看到,在丁尼生家屋外的草坪上,“在微微下陷的柳条椅的扶手中间,他们的两只手几乎触到地上的草皮,一只伸向另一只,一只是土棕色,另一只白皙并且保养良好”。(262)每当艾米莉想起萨默斯比的花园,那两只“无声地指向对方”(262)的手指便会出现在她的脑海之中。
这个与“手”有关的画面同样出现在老年丁尼生的回忆片断中:“他记得,有一次,他和亚瑟在萨默斯比的草坪上一整天都在讨论事物的性质、创造、爱和艺术、感觉和灵魂。在雏菊盛开的暖洋洋的草坪上,亚瑟的手离他自己的手只有几寸的距离。”(297)事实上,正是通过“手”的意象,我们得以进入老年丁尼生的意识世界。灵媒索菲在卧室中遭遇哈勒姆的亡灵后,恍惚中看到一个身穿睡衣的老人的形象:“他坐在床上,不停地转动他的手。他的神情有些困惑。他非常英俊。又有一点心不在焉。”(293)与此同时,老年丁尼生冥冥中也感到似乎有人在注意他的手,于是他联想起《李尔王》、《麦克白》以及济慈诗歌中对“手”的描写,还有《悼念集》中与“手”有关的意象:
亚瑟死后,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的手。四十多年过去了,与亚瑟握手的感觉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就像一支蜡烛,火苗渐趋微弱、摇曳不定……他记得亚瑟的手掌压在他手掌上时温热的感觉,亚瑟急切的一握。正是通过这种英国绅士式的握手,亚瑟与他相遇并短暂地交往。男人气的,有活力的,一种新生的触觉。相遇,分离。收到那封可怕的(告知亚瑟死讯的)来信之后,令他备受折磨的是,他的手仍然期待与亚瑟的手相握。(295)
如果说,艾米莉的回忆令我们对哈勒姆与丁尼生之间的亲密关系感到某种模糊的猜疑,那么,透过老年丁尼生的意识世界,拜厄特对他们之间的同性情感进行了更为直接的剖析:
米开朗基罗曾经爱慕过其他男子。他(丁尼生)自己不只一次看似开玩笑地告诉亚瑟,他爱他,就像莎士比亚热爱本·琼生,“在人世这叫偶像崇拜”。他们两人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找到一行又一行的诗句,可以用来作为礼物献给对方,表达善意,或是作为一种保证。他知道他们围绕没有意义的火焰飞舞,没有烧焦羽翼,也没有在火中枯萎。他也知道,他在悼念亚瑟的诗歌中对自己全部的悲伤和渴望细致的描述使他遭到世人可怕的误解。(298)
据史料记载,哈勒姆的父亲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感到不安,并因此销毁了丁尼生写给儿子的信件。(20)小说中,老年丁尼生回忆起这段往事,内心依然不能平静。他十分清楚亚瑟父亲害怕和怀疑的是什么,但一直以来他对此佯装不知,在言谈举止中从未流露出任何不安或慌张。(299)然而,在内心深处,老年丁尼生知道,与自己同妻子之间温馨平静的感情相比,
如果他讲真话,他和亚瑟手指之间的那段空隙,蕴含着更多令人激动的能量,那是一个灵魂向另一个灵魂发出耀眼的信号,那是心灵的呼应、思想的共鸣,那是他们感受到的一种共识,那就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一直以来就彼此相知,他们不必像陌生人那样去相互了解。(301)
在拜厄特笔下,老年丁尼生对哈勒姆的回忆显然带有克拉夫特所说的欲望蕴涵,但丁尼生的内心独白又似乎对这种欲望进行了消解和限定,他将自己与哈勒姆的关系更多地视为一种不同寻常的精神交谊,一种心灵契合而非肉体结合。对于《悼念集》在同时代人中引起的猜疑,小说中的丁尼生在内心为自己进行了辩解:“是的,是的,他一再将自己称作哈勒姆的未亡人,但那只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称谓,他的灵魂、他的生命遭受了丧亲之痛。”(299)在老年丁尼生对往日情感的回顾中,“亚瑟不是一个耽于肉欲的人。他的爱闪耀着浪漫的光彩”。(301)尽管他出众的才华和外表吸引了诸如理查德·米尔内斯(Richard Monckton Milnes)、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等文人政客的爱慕和追逐,但丁尼生相信:“如果亚瑟曾经,譬喻说,越过想像的门槛,参与到任何肉体行为中,他一定会知道。”(301)而且,老年丁尼生认为自己也不是“一个感情热烈的人,可以说,他的感官知觉散布在天地万物中并与之融合在一起,在刚刚绽放的娇小花蕾中,在大海滚动的波涛中”。(301)尽管拜厄特让小说中的丁尼生以一种诗意的语言为自己与哈勒姆的关系进行辩解,但拜厄特的整体评述显然更加倾向于克拉夫特的论断,即无论丁尼生如何分散、转移或升华他对哈勒姆的炽热情感,哈勒姆仍然是诗人欲望世界的中心。(21)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拜厄特意欲在作品中探讨的并非只是如何界定丁尼生与哈勒姆之间情感关系的性质,她对《悼念集》中“手”的意象以及与手相关的“触摸”(touch)、“把握”(hold),“塑造”或“铸造”(mould)等词语的重视更多是源于她对丁尼生诗歌的感性特征及物质性思考的关注。这种感性和物质性,在拜厄特看来,是思想得以触摸外部世界的保证;拜厄特以此抵制某些现代艺术流派纯粹以个人内心风景作为描写对象的创作倾向。(22)
小说中,老年丁尼生记得,他曾和哈勒姆讨论为什么但丁《神曲》中的《地狱》篇要比《天堂》篇更具吸引力,两人一致认定“原因在于语言、文字不可逃避的感性特征,就像是呼吸、舌头和牙齿,就像是留下温暖文字的这只手在白色的纸笺上移动,留下黑色的痕迹”。(309)这个有关作者之手的意象显然来自济慈。在其史诗片断《海庇里安之亡》(The Fall of Hyperion:A Dream,1857)开篇,济慈描写了一个诗人之梦:“当留下温暖文字的这只手已在墓中(when this warm scribe my hand is in the grave)/现在(我)意欲讲述的究竟是诗人之梦还是狂热者的迷梦,就会为世人所知。”(23)
吉莲·比尔对此曾评述道,济慈对“手”的描写消除了冰冷的铅字与身体之间的距离,作家之手存在于文本之中并从文本中伸出来,与读者之手相握,从而使读者意识到阅读以及写作过程中手的活动。作者逝去,但他的手能够以思想的形式存续下来,只要他的思想能够吸引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想像力。济慈将书写的手与带有体温的文字融为一体,这样就消解了思想与肉体间的二元对立。(24)
拜厄特同样试图通过“手”的意象消解思想、想像等精神活动与物质性肉身之间的对立。小说中的丁尼生同妹妹艾米莉一样,“通过想像去触摸(to touch)(哈勒姆)死去的肉体并停在那里……”尽管他愿意相信某种神秘的联系可能存在于他与哈勒姆之间,如同“光在光里,魂在魂里”,但是,“他的手将依然空空如也,盲目地摸索着那片空白”。(297)在此,“手”的意象表明,丁尼生与哈勒姆之间的精神联系一直包含有物质性的一面。
小说中,拜厄特通过老年艾米莉之口表述了自己对《悼念集》中所蕴含的物质性思考的解读:
在他(哈勒姆)离开的日子里,她曾经想像他归来的情景,伸出的双手,含笑的眼睛,浓密的眉毛,还有眼睛上方他引以为傲的米开朗基罗式的眉弓。在那些日子里她无法停止想像这一切将会变成什么样……阿尔弗雷德(丁尼生)也曾经体会过这一切。阿尔弗雷德也什么都没有说,但整部《悼念集》清楚地表明,他的想像曾经面对并探究过同样的问题,即那个深受热爱的身体最终有什么能够被保留下来(remains),或者说有什么不再能以我们可以辨认的形式保留下来。(254-255)
这里,remains一词显然蕴含双重含义,既指经由海上运回的哈勒姆的骨骸(remains),同时还暗指哈勒姆的遗著集Remains。拜厄特以双关语揭示出精神遗存与肉体遗骸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小说中的艾米莉而言,手的意象再次出现所要表达的就是:希望死者再次出现的愿望,可以相握的手,明亮的眼睛,声音,说出的和未说出的思想。拜厄特的描述使我们相信,如同济慈一样,尽管哈勒姆的肉体已经消亡,但通过《遗著集》,我们依然可以与他“伸出的双手”相握,诗人之“手”在文字中获得生命的延续。
与此同时,通过与“手”相关的“塑造”或“铸造”等意象,拜厄特强调了丁尼生对文字及语言物质性的自觉意识。小说中,老年丁尼生为《悼念集》中称语言为“物质铸成的话语形式”(matter-moulded forms of speech)的描述感到骄傲:“铸造(mould)是一个好词,它令你思考,令你想到肉体的死亡,想到上帝造人时所用的粘土,想到物质终究会腐烂分解(mouldering)。”(310)这段对铅印文字的描述使我们想起格瑞菲斯所说的“思维的体魄”(physique of intellection),(25)它再次消解了思想与物质之间的对立。
布莱德里等批评家认为,历史上的丁尼生在悲悼的过程中最终超越了对肉身的依附,并开始讴歌“具有无限价值的爱,当对象不再以物质化的形式在场,这种爱依然可以延续”。(26)然而,对于小说中的丁尼生而言,诉诸上帝并不能完全驱散科学所带来的疑虑,对精神世界的吁求也无法彻底放逐沉重的肉身。面对即将溺亡的苍蝇,拜厄特笔下的丁尼生无法消除内心的不安:“它们活着,它们挣扎、嗡嗡地飞过,它们死了。它们也有身体,生命一度蕴藏其中。它们绕着水罐的边缘飞舞,它们发出嗡嗡的声音,它们化为乌有。”(304)
在《悼念集》中,随着诗人对精神世界的信念渐渐复苏,他开始将死亡视作两种生命状态的交界:
切不要把人类的爱和真,
看作垂死自然界中的泥土和白垩。
请相信:我们称为死者的
是更为丰富的日子的生者
追求着更高的目的。(118.3-7)
但在小说中,老年丁尼生对永生的信念似乎不足以消除对肉体消亡的恐惧:
他正在走近死亡,一步又一步,不论他相信那是多么短暂的一个过渡,每走一步,他可怜的肉体在他眼中都好像另一个他需要为之负责的东西。每走一步,那种担心自己就像一个动物那样被扼杀的恐惧也更强烈一筹。当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在教堂中吟诵对肉体复活和生命不朽的颂扬……但现在那都过去了,人们开始害怕了。(303)
在《悼念集》中,丁尼生相信哈勒姆已经超越了肉体的羁绊,融入自然和上帝永恒的怀抱,而自己对他的爱有增无减:
我的爱包含了往日之恋,
如今变成更博大的神情;
你虽同上帝和自然相混,
我对你的爱像有增无减。
你虽远去却同我在一起;
我为仍能拥有你而高兴,
又因你话音缭绕而昌盛,
即使死去也不会失掉你。(130.9-16)
但在小说中,老年丁尼生回首往事时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如果,在他知道亚瑟活着的时候,他就知晓亚瑟的死,真正了解亚瑟肉体死亡的含义,他不可能爱上他,他们不可能彼此热爱。”(304)
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对比体现了拜厄特对丁尼生重构的用意所在。拜厄特对于物质性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她对基督教“道成肉身”思想的关注,其代表性文集《思想的激情》第二章的标题即为《维多利亚人:道成肉身与艺术》。拜厄特指出,道成肉身“确保了受难的肉身与超越的灵魂之间永恒的联结”,无限借此寓于有限之中。对于文学创作而言,那种能够通过感性和物质性对思想进行体悟从而将无限融于有限之中的艺术就是审美与叙述领域的“道成肉身”。(27)拜厄特笔下的丁尼生无疑就是这样一种“道成肉身”艺术的典范。小说中的丁尼生总是以一种具身化(embodied)的方式认知和观照物质世界。他对自己所写的有关哈勒姆的诗歌中的超验描写感到不满,因为它们没有使他产生一种恰如其分的感觉,这种感觉对他而言是同物质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三、物质的想像与想像的物质性
所谓“物质想像”(material imagination)最初由法国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加斯东·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提出,它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即我们以何种方式想像物质和物质世界以及这种想像本身所具有的物质性特征。一方面,物质世界必须经由语言、概念、类别(category)等媒介才能为我们所认知,但另一方面,巴舍拉指出,物质不只是我们思考的对象,事实上,我们“在物质中思考,通过物质进行思考从而使我们的想像物质化”。也就是说,想像总是被它所试图想像的世界“提前占有”(prepossessed)。(28)在此基础上,比尔·布朗等人提出“物论”(thing theory)用以阐述我们如何透过“物”来生成意义,建构自我以及规范情绪。受此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维多利亚研究领域出现一股“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物质性及物质想像迅速成为新的批评热点。文化批评家所讨论的物质性(materiality)通常包括四个层面,即客观实在的物质性(physical)、语言的物质性(linguistic)、身体的物质性(corporeal)以及经济活动的物质性(economic)。(29)
拜厄特创作《天使与昆虫》之时,批评领域的“物质转向”尚未形成规模,但作为一名具有敏锐批评嗅觉的学者型作家,拜厄特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在一系列批评论著中探讨了勃朗宁、丁尼生、乔治·艾略特等19世纪作家对物质性的思考及其在文本中的表现方式。此外,拜厄特十分推崇T.S.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思想,而集中体现这一思想的“客观对应物”原则与所谓的“物论”无疑具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
在《婚姻天使》中,拜厄特赋予丁尼生一种物质化的想像方式。据史料记载,丁尼生曾经对华莱士说:“我认为物质比精神更神秘。在某种程度上我能想像精神是什么,但无法想像物质是什么。”(30)这段话原本是丁尼生在谈及华莱士所著《热带自然》一书时所发出的感叹,他为书中对神秘热带雨林的描述感到惊奇,同时表示自己作为诗人对精神活动更为熟悉。拜厄特在小说中几乎原封不动地借用了这段话,但却对其进行了不同的解读:
当他的朋友们对这个时代粗俗、冷漠的物质主义大加斥责的时候,他总是点头附和,一付洞悉一切的样子。但是他的想像力却被物质所打动,被数量冗赘、具有灵性或不具灵性的肉体、土壤以及植被所具有的紧密坚实的物质性所打动。(306)
拜厄特的描述显然并非旨在挖苦丁尼生的言不由衷或典型的维多利亚式虚伪,而是为了表明物质性对诗性想像和思考的影响。
拜厄特在对丁尼生的重构中,强调了卢克莱修式的物质性世界观对诗人思想的影响。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一书中阐述了“万物有其诗”的哲学理念,同时也强调了人性自身的物质主义基础。赫胥黎曾经说过,丁尼生“是继卢克莱修之后第一个真正懂得科学要义的诗人”。(31)莱顿指出:“丁尼生从卢克莱修那里得到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一种物质化的或者说由物质铸成的(matter-moulded)看待世界的视角。”(32)小说中,老年丁尼生对自己诗歌创作的回顾与评价突出体现了这种物质观的影响。在他看来,《悼念集》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沉重的球体:
上面缀满宇宙间的一切。山峦和尘土,潮汐和树木,泥浆中的苍蝇、幼虫和龙蜥蜴,燕子、云雀和信鸽,乌鸦般黑暗的色泽和夏日的空气,人和母牛和婴儿和紫罗兰,全被如同结实的丝缆或光线一样的活生生的语言的经线编织在一起。世界是一大块(物质),而他的诗就是它闪光的映象。(312)
这里,拜厄特借人物的内心活动将《悼念集》中出现的物质性意象加以集中归纳,突出表现了丁尼生在心灵“内视”(inward-looking)的过程中对现实物质世界的“外观”(outward-looking)。
然而,拜厄特并没有忽略丁尼生对生命物质性的矛盾态度。丁尼生在《悼念集》中对生命的本质有过这样的疑问:“难道说,人——她最后最美的作品……难道他也将随风沙吹散/或被封存在铁山底层?从此消灭?”(56.9;59.19-21)他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完全由物质规律所统治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人只是“用粘土巧妙铸成的模子”,(120.5)而死后的世界“不过是骨殖和残灰”。(34.4)拜厄特显然体会到了丁尼生对纯粹唯物主义生命观和自然观的不安情绪,她通过小说中的丁尼生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人不是天使般智慧的生物,他自己的思想不过是一团苍白、粘滑、虫子般蠕动的肉体所发出的几缕电火而已。”(306)与其他人物一样,小说中的丁尼生迫切渴望确认个体灵魂能够永生:“我们无法忍受下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会化为乌有,像草蜢和肉牛一样。于是,我们向他们,我们的专属天使,寻求保证。”(196)正如拜厄特指出的那样,维多利亚时代人十分担心“我们只是我们的身体,死后所发生的一切就是自然腐烂”。(33)小说中丁尼生的一段内心独白生动地体现出这种矛盾的心绪:
你看到的是一种东西,牙齿和利爪滴着鲜血的自然,尘土,还是尘土,而你相信另一种东西,或者声称你相信,或者试图去相信。因为,如果你不相信,这一切的意义何在,生命、爱情或者美德?(303-304)
W.H.奥登在《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爵士诗歌选编》中断言,丁尼生“或许拥有英国诗人中最灵敏的耳朵,但也无疑是当中最愚蠢的一个。”(34)拜厄特对丁尼生的解读显然是对奥登所做评价的一种驳斥。拜厄特笔下的丁尼生不是奥登等现代评论者眼中那个语言优美但思想简单的桂冠诗人。她在小说中表现了丁尼生对于自我所处时代的一种历史性的眼光和洞见以及他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等古老命题的重新思考。小说中的丁尼生所表现出来的物质性焦虑无疑是马修·阿诺德笔下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不安的维多利亚人的精神写照。
迈克尔·莱文森指出,在拜厄特重构的维多利亚世界中,宗教感必须在令人炫目的物质主义中生存。(35)在一个宗教式微的年代,一个人仅凭心灵的内省和识见似乎已不足以抵抗世俗化宇宙观的冲击,人们只能在一个已没有“神圣穹幕”(sacred canopy)笼罩的赤裸的物质世界中寻找救赎。今天,在一个强调肉身安顿大于精神救赎的时代,深入体察维多利亚先辈面对信仰危机时体验到的物质性焦虑从而对当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精神文化困境进行历史性反思,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这正是拜厄特对诗人之“手”进行重构的用意所在。
注释:
①“新维多利亚小说”neo-Victorian novels有时也称作retro-Victorian novels,是指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描述对象或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故事背景的新历史小说。曾为拜厄特赢得布克奖的成名作《占有》(Possession,1990)是她创作的第一部“新维多利亚小说”,《天使与昆虫》由两部较长的中篇小说《尤金尼亚蝴蝶》(“Morpho Eugenia”)和《婚姻天使》(“The Conjugial Angel”)组成,分别以19世纪60年代早期与70年代中期的英格兰为时代背景,重构了19世纪达尔文主义者和唯灵论者的故事。
②Marilyn Butler,"The Moth and the Medium," rev.of Angels and Insects,by A.S.Byatt,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6 Oct.1992:22; Kelly,A.S.Byatt 114.“批评小说”(ficticism),即以小说形式展开的文学、文化批评。这种小说不以故事取胜,情节发展缓慢,具有较强的互文性特征,作家更加关注的是如何以故事为依托,通过人物之口,表达自己的文学、文化观念。
③John Dixon Hunt ed.,Tennyson's "In Memoriam":A Casebook,(London:Macmillan,1970)133.
④Qtd.in Dana Shiller,"Neo-Victorian Fiction:Reinventing the Victorians," diss.,U of Washington,2001,109.事实上,诗歌批评界也存在“两个丁尼生”之说,一个是“徘徊于林肯郡丘陵山地间、忧郁阴沉闷闷不乐的神秘主义者”,而另一个则是“怀特岛上功成名就,志满意得的维多利亚人”。David Ned Tobin,The Presence of the Past:T.S.Eliot's Victorian Inheritance(Michigan:UMI Research Press,1983)81.
⑤Dana Schiller,"Neo-Victorian Fiction:Reinventing the Victorians",104.
⑥《婚姻天使》中的人物常常引用丁尼生和其他诗人的作品,而我所引用的评论文章以及我本人的论述中也涉及到对丁尼生诗歌的引用。鉴于本文中诗歌被交叉引用的复杂性,我将采用不同的标示法以示差别。如果该诗歌在小说中出现,则用页码+分号+诗歌节码行码的方式,如果是本人直接引用或转引自其他批评家,则只标示诗歌节码行码。以下所有引用诗歌均按此方法标示。所引《悼念集》部分,如无特殊说明,均采用飞白译文。
⑦A.C.Bradley,A Commentary on Tennyson's In Memoriam(Hamden,CN:Archon,1966)41.
⑧John D.Rosenberg,"Stopping for Death:Tennyson's In Memoriam," Victorian Poetry 30.3(1992):296.
⑨John D.Rosenberg,"The Two Kingdoms of In Memoriam," in Tennyson’s "In Memoriam":A Casebook,204-205.
⑩关于《悼念集》中的各种意象(包括手,门,紫杉树,船等)参见布朗大学乔治·兰岛教授主办的维多利亚文化网页中的相关总结。
(11)本段诗行为笔者翻译,黑体亦是笔者所加。
(12)Christopher Craft,"'Descend,and Touch,and Enter':Tennyson's Strange Manner of Address," in Critical Essays on Alfred,Lord Tennyson,ed.Herbert F.Tucker(New York:Macmillan,1993)162.
(13)Jeff Nunokawa,"In Memoriam and the Extinction of the Homosexual," ELH(English Literary History)58.2(1991):427.
(14)Qtd.in Nunokawa,"In Memoriam and the Extinction of the Homosexual",427.
(15)Qtd.in "In Memoriam and the Extinction of the Homosexual",427.
(16)Christopher Craft,"'Descend,and Touch,and Enter':Tennyson's Strange Manner of Address",153-174.
(17)Qtd.in Craft,"'Descend,and Touch,and Enter':Tennyson's Strange Manner of Address",156.
(18)Craft,"'Descend,and Touch,and Enter':Tennyson's Strange Manner of Address",163-164.
(19)A.S.Byatt,Angels and Insects(New York:Vintage,1994).以后引自此书之处,一律随文注明页码,不再另外加注出版信息。《天使与昆虫》尚无中文译本,所有引文均为笔者所译。
(20)T.H.Vail Motter,rev.of Alfred Tennyson,by Charles Tennyson,Modern Language Notes 65.5(1950):357.
(21)Craft,"'Descend,and Touch,and Enter':Tennyson's Strange Manner of Address",170.
(22)在本文的论述中,对感性、物质性(包括语言的物质性)和肉身性的讨论常常交织在一起,因为这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在《肉身的放逐及其影响》一文中,作者指出,“肉身是一个交汇点,它是各种因素的汇聚之处,想像力和语言这两条线索都指向肉身,在肉身那里交织。经验是想像力的根源所在,而经验来源于肉身,身体的各种感官眼耳鼻舌等是一切经验对象的主体,是一切经验现象的感知者,因此,想像力与肉身或身体的感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至于语言与肉身的关系,我们至少可以这样来理解:语言系统中的绝大多数能指,其意义和所指需要直接通过感官来确定,而对另外一部分虚拟能指的理解也间接地来源于感官。压制肉身与对感性经验的排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感性经验是物质性肉身与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结。2008年1月2日
(23)诗学上,济慈有着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散见于他的书信和《睡眠与诗》等作品。首先,他强调感性,重视细腻的感觉,强烈地反对古典主义的理性主义。济慈认为诗的成熟不能依靠“法则与公式”,只能依靠“感受的敏感”本身,表示“我宁可要充满感觉的生活,而不要充满思索的生活。”Newell F.Ford,"Keats's 'O for a Life of Sensations..." Modern Language Notes 64.4(1949):229-234.
(24)Gillian Beer,Open Fields:Science in Cultural Encounter(Oxford:Oxford UP,1999),13-14.
(25)Eric Griffiths,"Tennyson's Breath," Critical Essays on Alfred,Lord Tennyson,ed.Tucker(New York,1993),36.
(26)A.C.Bradley,A Commentary on Tennyson's In Memoriam,42.
(27)Byatt,Passions of the Mind,48,59.“道成肉身”(incarnation)是指神的道降世为人,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之成为人乃是取了真实的身体和理性的灵魂,藉圣灵能力在童女马利亚的腹中怀孕而出生,但祂是无罪的。道成肉身是神爱世人的一个具体的行动,为了救赎,祂成血肉之体。这样,神对我们不再是一个抽象、虚幻的概念,而是一个实在、具体的存在。参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18节。
(28)Qtd.in Victoria Mills,"Introduction:Victorian Fiction and the Material Imagination",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6(2008),www.19.bbk.ac.uk.
(29)Mills,"Introduction:Victorian Fiction and the Material Imagination",www.19.bbk.ac.uk.
(30)Helen Allingham and Dollie Radford eds,William Allingham:A Diary,4 May,2007
(31)Leonard Huxley,Li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2 vols(New York:Appleton,1900),2:338.
(32)Leighton,"Touching Forms:Tennyson and Aestheticism",67.
(33)Byatt,On Histories and Stories,108.
(34)Qtd.in John D.Rosenberg,"The Two Kingdoms of In Memoriam",200.
(35)Michael Levenson,"Angels and Insects:Theory,Analogy,Metamorphosis," Essays on the Fiction of A.S.Byatt,eds.Alexa Alfer and Michael J.Noble(London:Greenwood,2001),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