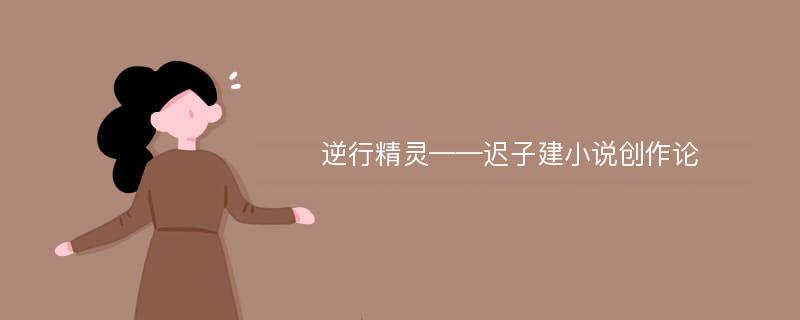
常暮晗[1]2012年在《理想·前景·希望》文中提出迟子建是当代作家群体中一位创作风独特格的作家。她以其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温情与现实关怀精神,关注并书写了平凡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同时,迟子建还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她洞悉人世间的悲欢善恶,执着地守护着人类善良的本性。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风云变幻,世间百态怎样的迷离混沌,她都用一种“背转身”的姿态,朝着理想中的北极村,用她女性的特有的温柔和宽宥,描写那寒冷的高纬度北极村的故事,以灵动的文字为疲惫的现代人开辟了一块精神的“伊甸园”,使平淡的生活在这种理想的照耀下充满了温暖和希望。本文将从文学理想与现实结合的维度切入迟子建的作品,探析迟子建对生活的热爱与理想的希冀以及由此所建立的属于她自己、亦属于对生活有着深刻的体悟与希望的读者的文学世界。第一章“迟子建文学世界里的人物形象”。迟子建始终关注着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的“小人物”。她摆脱了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与布道者的姿态,采用一种民间的视角,融入到“小人物”的凡俗生活中,用沉静而有韵味的笔触书写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迟子建表达了自己独特的两性观。在迟子建的笔下,无论是追求自由如逆行精灵般的女性,还是在婚姻中坚强妩媚的女性,亦或是那些经历了岁月洗练拥有大爱的老妇人,都是如此的思想独立、内心丰富、热爱生活。在迟子建塑造的人物形象系列中,还有对鄂伦春、鄂温克少数民族生活的独特描写。这些少数民族生活在大自然中,热爱大自然,崇尚万物平等。他们勇于担当,敢作敢为,拥有原始的生命张力,与在现代社会中日渐丧失激情的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第二章“迟子建文学世界的后花园”。北极村是迟子建从小生活的地方,这里有令她神往的神话传说,有她深刻体验的人与人之间的浓郁情感,亦使她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宽容,看到了动物的忠贞。北极村醇厚的民风、儒道互补的处世方式、人与人之间温暖的情谊、乃至充满灵性的自然风光,为迟子建的创作提供了生命的韵味与底色。可以说,北极村是迟子建艺术世界的后花园,是她的文学理想的源泉与寄托。第叁章“烛照生活的文学理想”。理想给现实生活以力量。人的生活中有着无数的残缺或阻断,有着难以逃避的无奈或苦难。迟子建的作品直面生活的现实,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心灵之窗,让我们在理想的寻觅中获得一种越过苦难的态度和姿态。生活或许是平凡的但却是奇特的,最平凡的生活场面其实都是富有生活意蕴的最美的风景。希望与理想生长于凡俗的生活中,成为照亮人们前行的一缕光明。
刘新锁[2]2003年在《逆行精灵》文中认为迟子建是中国当代文学界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独特存在。她的作品地域特色鲜明,个人风格显着,已日益引起更多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本文由对迟子建大量作品的细致解读获得的感性认识出发,借用中国传统的思想理论资源对其进行阐释,力求将感性体验与理性分析相互结合,从整体上把握迟子建独特的文学思维方式及审美理想。在此基础上以当代文学创作的现状为参照,对迟子建个性色彩强烈、民族风格突出的创作进行尽可能准确的评价与定位。 本文从叁个方面入手,由作品内容来探讨迟子建创作的独特内涵。 首先,一方面,迟子建在创作中时时显现出所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这体现了她对传统伦理道德理想的认识、继承和坚守;另一方面,迟子建在对其继承的基础上又对有悖人性、束缚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僵化伦理道德规范进行了个人化的重新审视和改造处理。迟子建作品独特的人物塑造和作品体现出的死亡观等都表现出她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这种特殊的关系。迟子建继承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符合人的真善美追求、有助于提升人的思想境界的精华部分,又借鉴了西方思想资源中对个体生命和人自由发展的尊重等内涵,在创作过程中将两者相互融会,使其作品具有了现代性追求的内质。迟子建作品中表现的以道德伦理化解现代人精神危机的价值取向、个人化叙事伦理与人的现代性追求的和谐并存,是其创作一个重要的内涵。 其次,迟子建的作品还体现出相当强烈的理想主义话语特征。她用自己洒脱不羁的想象力和独立于各种意识形态之外的理想主义话语建构了一个纸上的童话世界。她用万物有灵的自然观来观照作品中出现的事物,赋予它们以人的生命活力;同时,她还充分调动自己的飞腾起来的想象力,创造出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种种神奇美丽的意象。迟子建笔下的人物与自然界中的事物平等相处,他们将无生命的事物视为具有生命价值的应然存在,在并给予他们以充分的尊重。此外,迟于建对梦幻场景的描绘也表现出相当强烈的理想主义话语特征。这是迟于建的创作引人注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叁,迟子建的作品大都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氛围,她创作的悲剧故事却呈现出一种较为特殊的悲剧形态。她创作的悲剧性作品不像西方的悲剧,不是以悲剧冲突各方面的毁灭为结局,而是趋向于悲剧冲突的化解。以道德善的提升、人格美的转化来消解悲剧结局带给人的心灵上的痛苦和震撼。迟子建的很多作品在故事层面以悲剧结束,但内在蕴涵却往往以道德的善和人性的美为结晶,悲剧冲突往往消融在一片和谐之中。这种特殊的悲剧形态体现出中国传统“中和”文化精神的潜在影响。这是迟于建区别于其他作家的又一个特点。 迟于建既拥有独异于其他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审美理想,又有过人的文学天赋。作为一个蓬勃生长着的作家,她的发展前景值得我们予以期待。
李全慕[3]2008年在《理想的光辉》文中指出在喧嚣复杂的当下文坛,迟子建乃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以其女性特有的温婉细腻,用饱含诗意的笔触为大千世界的人们描绘了一幅幅温情恬静的图画,让读者被现实生活麻痹的心灵深深感动,从而恢复人对于大自然和诗意生活的感觉。在迟子建多姿多彩而又神奇瑰丽的文学世界中,渗透着自我坚定的文学与人生信仰,也正因如此,迟子建为自己打上了迥异于他人的烙印,疏离于各种思潮流派之外,成为一个逆行精灵。本文由对迟子建大量作品的细致解读出发,将感性认识与理性分析相结合,由作品营造的一个虚拟的理想化世界入手,立体地研究她的自然观、人性观、家园观,阐述迟子建创作的独特意蕴和审美价值。在此基础上,以当代文学创作现状为参照,进而对迟子建独具一格的创作尽可能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和定位。本文从叁个方面入手,力图从自然、人、家园叁个层次探讨其创作的独特内涵,勾勒出其理想化写作的方方面面。首先,在自然观上,迟子建秉持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在东北边地独特的萨满教文化熏染下,迟子建用万物有灵的自然观来观照世间的万事万物,赋予他们人的灵性和气息,从而勾勒出一幅人格化的自然世界。这主要通过众多的意象创造来展现,有动物意象、植物意象还有其他一些自然事物等等。同时,其笔下的人与自然万物是相互平等的,自然不再是人类的附属物和只供征服利用的物质资源;人们可以与自然万物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善待自然中的任何生命;每一种自然事物都有独特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甚至可以和人产生神秘不可知的感应;自然如果得到善待和有效的保护,就会成为人类的福音,如果人类不顾客观规律一味的掠夺攫取,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其次,迟子建通过对四类生命形态(疯癫者、儿童、“死魂灵”、鄂伦春人)的刻画,表达了自己对俗世人生的关照与救赎,阐述了自己独特的生命美学观,体现出她博大深厚的悲悯情怀和对人的理想化存在状态的开掘和探索。通过阐述疯癫的特质,她颠覆了现实社会中疯癫与正常分界的标准;通过儿童的话语举止,她告诫人们保持童心的可贵;通过生者与魂灵的对话,她表达出自己独特的死亡观;通过对比现代文明人颓靡的生存状态,她呼唤原始生命激情的喷薄。由这四类生命形态的言说,迟子建向现实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指引出一条通往人类本真存在状态的途径,这不失为一种人类超越自我的可能性。第叁,迟子建在对自然和人的整体观照的基础上为人们揭示出在既存现实的有限性、相对性之外人们应该仰望的无限、绝对的另一个精神世界,这就是她在原乡家园的基础上升华虚化出的人类诗意唯美的精神栖息地——“北极村”世界。面对浮躁的外在环境和苍凉的人生困境,迟子建在记忆和想象的基础上为现实人生划定了一个可以超越苦难的坐标。精神家园的存在是因为人类需要拒绝理想、情感、爱情、艺术、友谊等等生命特质不断被物化的命运,人需要有一个完美的象征超越丑恶和痛苦来寄托自己的希望和所认同的价值。精神家园的闪烁,就意味着精神力量在显示魅力,就意味着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正闪耀着眩目之光。这种理想情怀是一个作家艺术家不可或缺的审美内质,而迟子建就无可挑剔的具备了这种可贵的理想情怀。迟子建拥有独异于其他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审美眼光,迟子建的文学是形而下的俗世关爱与超越性精神相统一的文学。作为一个不断进步和创新的作家,她正韧性十足地行进在自己的文学之路上。
施一丁[4]2012年在《迟子建乡土小说论》文中研究表明大自然美丽风景及具有艺术魅力的自然意象是迟子建乡土小说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深刻地了解迟子建乡土小说宛如风景画的原因及这些自然美景对迟子建本人及其乡土小说的意义。迟子建在其乡土小说中的民间立场体现在对“胡子”、少数民族等群体的关注;体现在迟子建数十年如一日地将温情投向这些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的边缘小人物,并把这些人物中带有浓厚地域风情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其他民俗文化都一一呈现出来;体现在对乡土之子的温情关怀和宽容,对女性地位的诠释和认知等方面。迟子建乡土小说中的自然风景及民间立场,是其近叁十年的文学创作的恒定因素,但迟子建乡土小说创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迟子建乡土小说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作品氛围从单一化到多元化、迟子建对“爱与性”的新解读、作品的批判力度和历史感增强以及叙述视角的多元化。发生这些变化是由于迟子建本人知识的积淀、写作经验的丰富、不断突破自我和写作中反复出现的矛盾等因素造成的。迟子建乡土小说的变化对于其本人来说,是一种质的飞跃,因为她对故土有了更为理性的批判态度、更为深刻的关注视角、更为节制的情感抒发方式,从而也就使得作品的分量更加沉重。
马冬雪[5]2011年在《真善美的颂歌—迟子建小说创作论》文中研究说明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在内容、主题、形式上体现了真善美的特色,本篇论文分为叁个部分,分别探讨迟子建的小说创作所呈现出的生命之真、人性之善、灵性之美。第一部分生命之真是从关注日常生活和正视生命残缺这两个方面来解读。所谓关注日常生活是指迟子建在处理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这类历史题材时是站在民间立场,通过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反映出历史的大背景;而正视生命残缺是指迟子建对身体残疾、智力缺陷以及鳏寡孤独这类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的真实描写和平等关注。第二部分人性之善则是从人性的多面和本质的善良这两个方面来论述。迟子建相信人性本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迟子建有意忽视人性中的恶,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也有对于人性恶的揭示,也有亦善亦恶、善恶并存这样的人物形象,只是迟子建坚信博爱、宽容、忠贞这些善良美好的品格才是人性的本质。第叁部分灵性之美还是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评析:一是超自然,一是意象美。本篇论文中的超自然是指迟子建在小说中对灵魂、梦境、巫觋的特别书写;而意象美是指迟子建的小说中融入主观情思、具有特殊意味的艺术形象。
参考文献:
[1]. 理想·前景·希望[D]. 常暮晗. 河北师范大学. 2012
[2]. 逆行精灵[D]. 刘新锁. 山东师范大学. 2003
[3]. 理想的光辉[D]. 李全慕.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4]. 迟子建乡土小说论[D]. 施一丁. 云南大学. 2012
[5]. 真善美的颂歌—迟子建小说创作论[D]. 马冬雪. 辽宁师范大学.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