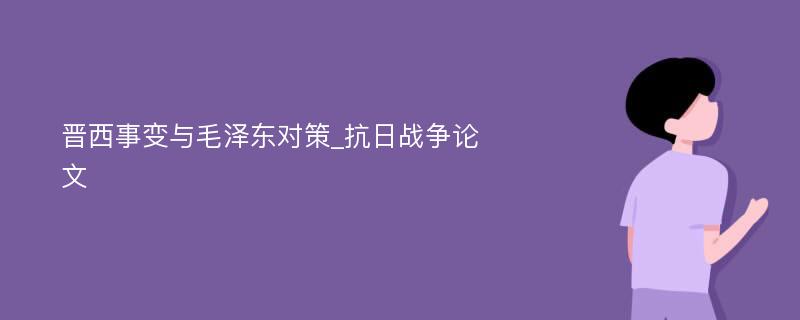
晋西事变与毛泽东的应对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变论文,应对策略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26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6)01-0075-09 1937年夏秋之际,中共领导的3.4万正规部队得以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含一个总部并三个师,编制人数4.5万人,并得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辖三省交界十余县范围。一年多之后,即到1938年年底,原第八路军增至16万人,军政实际控制范围扩展到山西、绥远、察哈尔交界地区,并发展至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横跨一、二、三、五4个战区,与各地原军政当局发生了颇多纠纷与摩擦①。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处根据五届五中全会代表的呼吁,拟定了一个《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并于会议结束后下发执行②。文件明确提出了“积极”和“消极”两种办法,要求其党政军随时得采取措施,对中共“非法”活动加以限制和取缔③。在此一方针影响下,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很快拟定并推出了一系列应对中共问题的秘密文件,两党关系亦因此开始全面紧张起来了。 与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比较而言,八路军在山西省一直与“山西王”阎锡山保持着较好的关系。自抗战以来,直至1939年国民党中央下达《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之际,双方之间从没有发生过军事摩擦,因行政管辖引发的矛盾冲突亦较少。这与阎锡山始终注意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之间保持微妙平衡关系,以维护其对山西的控制力的做法,明显有关。由于阎有意与国民党中央保持一定距离,《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下达后,山西省军政当局也没有像其他省那样,马上去制定一些防范或限制中共活动的秘密文件。但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这一方针及其文件,还是对阎锡山造成了相当的影响。从1939年春天开始,阎明显地对他所创立的,一直带有左倾色彩的牺盟会和决死队与八路军的关系,开始担心起来了。这一年3~4月间,他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的山西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首次批评了决死队中的政治工作和牺盟会的行政区专员随意撤换县长的做法。由于他越来越怀疑牺盟会和决死队有脱离其控制的严重危险,因此他亦很快采取措施,力图根本解决对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控制问题。考虑到八路军借助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这一在他批准下成立的合法的组织形式,直接介入到山西军政工作中来,对牺盟会、决死队和地方政权影响甚大,为了在不破坏与中共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名正言顺改变此种情况,他还想到了请重庆中央出面来帮助自己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为此,他暗中报请重庆政府,希望能让重庆下文取消这一组织形式④。 这些措施在事实上还是使阎锡山与中共的关系在1939年春夏之后也变得逐渐紧张起来。但是,不论是阎锡山,还是中共中央,显然都没有料到,半年之后双方竟会爆发一场史称“晋西事变”的严重军事冲突,不仅几乎彻底毁掉了双方此前几近两年之久的合作关系,而且打响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军事冲突的第一枪。 限于篇幅,本文这里主要仅尝试对中共方面,特别是毛泽东这一时期在阎锡山态度变化情况下的应对方针,和中共策略变动的复杂情况与背后的原因,略做一考察、梳理与说明。 一 秋林会议后中共方面的基本方针 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推动防共、限共政策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以及晋冀豫区委的基本应对策略就是要求针锋相对。刚一得知阎锡山秋林会议的内容,无论中共中央,还是中共中央北方局,都马上将两者联系起来,并一致提出:在全国、在山西,都“必须采取斗争,停止其上层分子动摇,促其继续进步。”⑤ 中共中央发出强硬指示,一个重要的政治背景,是这一年春天苏联联合英、法,防范德、意的欧洲政策发生了改变,苏联政府秘密与德国希特勒政府开始谈判协定互不侵犯条约,意图祸水西引。在此背景下,受到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当年5月底,即阎锡山秋林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得到共产国际指示:要警惕国民党积极反共包含投降的阴谋,因而认定“反共即准备投降”。因此,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开始积极准备应对以蒋介石、阎锡山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投降危险⑥。 不过,中共中央对阎锡山的策略,还是区别于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抗战爆发以来与阎锡山在山西合作的经历,让中共多数领导人对争取、利用阎锡山,一直颇有信心。特别是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加强统战的工作方针后,整个1938年,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都相当重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只不过,无论是中共中央也好,还是八路军也好,亦或中共地方组织也好,他们对统战策略的运用,都是建立在维护、巩固和发展自身这一基本利益诉求的基础上的,因此一有机会就会全力以赴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也正是这种情况,客观上造成了中共的统战政策事实上很难坚持到底。与阎锡山的关系,也很难不出问题。当发现阎锡山有可能将事实上大部控制在秘密的共产党人手中的牺盟会、决死队重新掌握到自己手中这一情况后,中共各级组织的态度都是可想而知的。不仅牺盟会及决死队中具有相当力量的共产党人,就是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包括八路军总部,都是一定要坚决抵制并与之斗争的。北方局8月6日即有指示强调“阎有继续向右动摇之可能”,“必须推动山西进步势力与之作适当的斗争”。中共中央也明确表态,赞同在“注意方式”的基础上,“给阎的进攻以反攻与抵抗”⑦。 1939年6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密电,要求各分局、各区委和各部队,严格注意巩固党在山西已取得的阵地,巩固牺盟会,加强对牺盟会干部的领导,反对一切反共限共的企图。北方局书记杨尚昆解释说,秋林会议后,山西已出现明显变化:“1.国民党部及所谓各专员区党务专员的出现;2.专员区域的缩小(第一区宋时昌处)与权限的限制(专员不能改变县长);3.决死队改编为独立旅,取消政委,政治工作人员服从同级军官,取消新的薪饷制度;4.旧派李冠洋、邱仰濬等之抬头;5.限制民众运动,民运工作人员今后将调往行营轮流受训,所谓组织百万群众,实际系变相的保甲制度;6.取消晋西北战地动委会,企图吞并战委会的武装力量(实际上这些武装都在我党领导之下,八路军干部创造起来的)。”“这些都说明了,今后山西的环境比以前是会更加复杂起来,新兴势力可能受到限制与压迫,顽固分子与旧势力将比从前活跃,我党我军今后可能受到部分的限制与打击中,摩擦与斗争可能更多”。对此,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⑧。 7月,日军向晋东南发动大举围攻,很快打通了白晋公路和长邯公路,再占长治等县城,并开始长期驻守。这种情况进一步引起了中共中央对阎锡山右转是否包含着投降阴谋的担心。 9月初,德国大举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不能不采取谨慎态度,开始要求各部政治上表现强硬,实际工作上则应收缩隐蔽以小心应对各种危险的情况。指示称:共产党八路军必须立即开展反对投降妥协的斗争,可公开指出反共反八路“就是投降妥协分裂的准备(不应指出阎锡山的名字)”。但“新军(即决死队——引者注)、牺盟及政权中的党的组织,必须严密紧缩,停止不可靠的分子的党员组织关系”,避免暴露而遭破坏⑨。 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1939年10月开始,中共在秋林牺盟、民青(民族青年革命团)及阎锡山属下各机关中有组织地陆续撤出了部分可能暴露和不便临时撤退的人员。身为中共秘密党员,主要负责与阎锡山打交道的决死一纵队政委薄一波,为免除后患,干脆于11月间,将他领导下的一纵队中上百名亲阎的旧军官集体缴械,然后解送到中共设在太行山的抗大分校去强制“学习”⑩。 二 晋西事变发生各方均感意外 尽管多少有所准备,从中共中央到八路军总部对随后事变的爆发,仍然估计不足。就在事变发生前几天,彭德怀还很乐观地在延安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报告称:从五台,到北当,到太行山南脉,除八路军外,有“友军”决死队5万人,游击队约5万人。同时县以下政权绝大部分都掌握在我手中或进步分子手中,加入各种群众团体的民众达250万人之多,相当于晋察冀边区的数量,因而是比较巩固的(11)。但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发生后,除了薄一波领导下的决死一纵队因预先清洗了亲阎的旧军官,同时又驻扎在八路军太北根据地附近,基本上没有遭受损失,晋西北四纵队事变后防范及时,损失较小外,二、三两个纵队,特别是它们活动区域内牺盟会左派控制的县区政权,都遭到沉重攻击,大部垮掉了。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还是北方局,或山西省委,都没有向决死队中的党组织发出过与阎锡山决裂的指示。这次事变的起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秋林会议后形势紧张,以致直接当事人高度敏感所致(12)。 综合已知资料,事情的由来首先触发于阎锡山的一纸电令。阎指示韩钧部与西路军各部一起,准备实施冬季攻势,要求韩部等于12月10日以前完成准备,15日肃清汾河右岸之敌,而后向汾河左岸进出(13)。韩得令后,分析阎之部署,严重怀疑阎是要将二纵队置于日军与晋绥军六十一军之间,“如顺其令,势必落入圈套,全军覆没;如不执行,阎必加以‘抗命’之罪,兴师讨伐”(14)。左右为难之下,基于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强调的斗争原则,韩选择了抗阎命不遵,率部脱离了原驻地,并于12月5日致电阎锡山,以“六十一军等欺我太甚”为由,说明他将率二纵队万余健儿单独行动,半月内不受任何命令(15)。韩此举不可避免地激怒了阎锡山。他接电后认定韩钧这是带头反叛,遂严令所属各部“迅速集结兵力,讨伐叛逆”,并要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消灭”之(16)。 12月上旬,阎部新旧两军很快陷入全面冲突之中。虽然韩部很快就得到了八路军晋西支队的支援,却还是勉强得以保存下少部分部队,而其原先控制的汾阳、交城、文水、离石等地区全部落入到旧军,即晋绥军手中去了。 损失最为惨重的,是驻扎在晋东南太南地区的三纵队及其所属政权。事变中,该部几乎全部被阎锡山的晋绥军所接管。其原先所在的太南地区,即第五专区下辖的12个县政府,将近10个都被晋绥军和国民党军摧毁和控制,只有专区保安司令部两个团,和游击十团的武装,大部保存了下来。该专区被捕、被俘和被害的牺盟会、决死队干部及中共党员,不少于150人,政委戎子和及纵队长颜天明等主要领导人,几乎是靠侥幸才得以脱逃的(17)。 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当时事变关系各方,无论阎锡山、国民党,还是牺盟会、共产党,都不能不顾及抗战大局,对事变采取了公开和秘密的两手策略。阎锡山于事变发生后即公开表示此系“平叛”,因而只是内部秘密通报重庆军令部,并小心请示应对八路军介入事变的处置方针。阎锡山当时提出两案:“(一)分汾东汾西,借剿叛军名义北上,肃清共党势力。(二)就事论事,用政治方法解决。”他亦深知事变不宜扩大化,因而表示称:“前者有扩大之虑,后者有养痈之虞,究以如何处理为宜,请核示”。显然,蒋介石对此如何应对也颇感犹豫,迟迟未予答复,更未公开向八路军方面施压(18)。在得不到重庆方面明确答复的情况下,阎锡山自然认为蒋尚无军事解决这类问题的打算,故不得不再电重庆,承诺称:在未得中央明令前,对八路军当“竭力避免冲突”,“决不以一区之事搅乱中央全盘计划”。(19) 三 毛泽东应对事变的态度变化 决死队,亦即新军方面的反应,从一开始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令行事的。而中央军委这时主要其实是毛泽东在负责,故对此一事变的处置经过,很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个人的应变指挥风格和政策策略考量的侧重所在。 毛泽东最初得到韩钧所部决死二纵队受袭,196旅旅长等军官叛变,晋西南永和、太宁等县政府被摧毁的消息时,虽然看到“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认为晋西南、晋西北作为陕甘宁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因而提出“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予以有力的还击”,但还并未估计到事变会发展到全面破裂的危险,还特别强调八路军形式上保持中立的重要性。他提出,应“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八路军“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在形式上应以调(解)方式出现,阻止旧军对新军进攻,八路军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口号”(20)。 毛泽东12月上旬对形势的估计也还比较乐观。他认为:“晋东南、晋东北两区,抗战派比投降派的实力大;晋西南、晋西北两区,投降派比抗战派实力大。”“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决不能让投降派胜利”。他相信旧军战斗力不强,新军有战胜的可能。故只是强调“必要时八路军应以适当力量支持新军”(21)。 到12月中旬末,晋西南的形势明显对二纵队不利,同时又有报告说晋西北决死四纵队因逮捕顽固军官,也出现严重情况。据说阎已命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率部以武力解决之(22)。到这时,毛泽东才下令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支队陈士渠部速向吕梁山增兵一团,“伪装或用一部伪装夹在决死队中”,协助韩钧部打击旧军。同时要求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或政委罗贵波以一人就近去帮助四纵队雷任民部掌握形势,如果新军确有失败危险时,可以有力一部伪装决死队参加战斗。但仍特别强调,“不给阎赵以口实,并在事后也不要承认我们参加了战斗”(23)。 毛泽东没有想到,从12月20日开始,晋东南决死三纵队在旧军孙楚部的压迫和引诱下,也接连发生了集体叛变的情况。决死三纵队的迅速瓦解,导致晋东南大部地区迅速陷于旧派之手(24),这让毛泽东一时极为震怒,以至于开始在电报中斥骂阎党旧军为“王八蛋”。得知八路军一部截击消灭孙楚部两营,他30日激奋回电彭德怀,果断指示:“望继续用此办法消灭一切叛军叛党,或全用我军伪装或一部伪装夹在决死队中。总之,不消灭这些王八蛋,不足以寒贼胆。”他并且还要求八路军对晋西南也要如此做,称:“吕梁山增兵一团望速来,非把吕梁山之逆军逆党全部消灭决不放手。”(25) 不过,毛泽东毕竟需要从政治的角度来衡量与阎锡山全面军事冲突的利弊得失问题。尤其是在晋东南方面发现有中央军大举介入的迹象,更让毛变得冷静下来了(26)。而与此同时,他亦得到了决死二纵队与陈支队被迫撤出晋西南的消息。因此,就在他异常激愤地发出要八路军参战,非把这些逆军逆党“全部消灭决不放手”的指示的第二天,他的心态就开始冷静下来了。 31日,毛泽东电告八路军总部称:决死二纵队已于27日被迫撤离晋西南,中央军在晋东南参战并准备随时增援晋西南,胡宗南一师已到宜川东南,蒋、阎有“转攻晋西北,隔断华北与边区以及华北各个区域的联系”的目的,此举“将牵动华北全局关系全党的重大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而此中关键,还是要确保晋西北不失。他要求,紧急出动贺龙所部两三个团,与决死四纵队及续范亭部联合作战,全力巩固晋西北的战略枢纽地位(27)。 对于总部就设在武乡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来等人来说,晋东南是八路军重点经营的另一个战略枢纽,也是创建另一个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因此,晋东南遭遇如此大的损失,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毛泽东12月30日的激愤情绪,其实也是朱、彭等人同样心理的反映。但是,毛泽东很快冷静了下来,朱、彭的想法却没有那么快转变过来。 彭德怀在1939年12月3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明确提出蒋、阎事实上已经转向反动,故应对晋绥军予以沉重打击,应有不惜与国民党撕破脸的准备。随即,朱、彭即部署八路军重回太南,并要求各部对那里的晋绥军还以颜色,用严厉手段予以打击(28)。然而,毛泽东对此却有不同意见。他再三告诉彭德怀说,“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彻底消灭阎锡山旧军也是长时间事,迅速解决不可能。目前,“晋西北有贺、关率两个团去,可以保障逐渐消灭旧军化为根据地”。但晋西南情况已转为复杂,必须重新布置。一个选择是派人回去打游击;另一个选择是让阎占吕梁山大部,“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当然,他同意,晋东南已失之七县可选择无中央军之几县,消灭孙楚,恢复政权(29)。 直到1940年1月16日,我们仍能看到毛泽东赞同朱、彭争取夺回晋东南的电文。这是因为他担心,由于八路军基本控制了晋西北之后,“阎与中央会更结合,以夺取晋东南”。因此,对晋东南国民党军的进犯不能不坚决抵抗,“否则势必丧失晋东南”(30)。但几乎与此同时,他却已经在考虑分化蒋、阎关系,以重回山西以往统战局面的需要了。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上就此解释说:“此次山西的摩擦,阎锡山在晋西南、晋东南获得两个胜利,占去十七个县,拉走决死队两个团。我们也取得两个胜利,取得晋西北七个县的全部政权,取得新军四十一团,(我们)这两个胜利比阎大。”因此,他明确主张要立即派人与阎锡山接触,争取妥协,和平解决事变(31)。 既然要争取与阎重建统战关系,对阎及其晋绥军的策略就必须要从武力反击,转回到协商妥协上去。因此,从1月下旬开始,毛泽东对打回吕梁山去的提议已开始表示异议,说:“反攻晋西南会使我们处于进攻者的地位,在武装摩擦中对于我们有利的是战争的局部性和防卫性,而不是战争的全面性及进攻性。”(32)同样,对夺回晋东南各县政权的方针,他也不很赞成了。他强调认为:“晋东南是持久斗争”,“该区有建立最大根据地之前途”,但目前只宜采取“巩固现有阵地,严阵以待,来者必拒”的态度,只宜做“防御的局部战争”(33)。他的理由是:“现在山西是八路军、阎锡山、中央军三大力量的斗争,我们的方针以保持原有力量(关系)为好。”对阎及其旧军,要使他们有些希望,不要说他们是汉奸。“我们去谈判的方针是新旧军互不处罚为好。”(34)他告诉朱、彭等军事将领,根据已了解到的情况,“在蒋介石的分化政策下,阎锡山可能与新军达成妥协”,故“新军也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的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国民党中央军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国民党中央指挥”(35)。 四 阎、共及国、共的划界谈判与妥协 1940年1月31日,毛泽东开始启动对阎锡山的“和平攻势”。他一面用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的名义致电二战区参谋长,表示愿意出面调停新旧两军冲突;一面亲自为薄一波起草致阎锡山电,表示愿意继续拥阎抗战。他紧接着又要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转告阎称:“八路军与晋绥军团结一致拥阎抗日到底,唯愿新旧两军重归于好,勿为阴谋家所算。”而“他们如不与新军妥协,他们是很危险的”。同时,他并指示山西八路军各部“到处发布”包括“拥护蒋委员长阎长官卫长官抗日到底”等统战口号,以造和平声势(36)。 2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与八路军代表肖劲光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秋林,与阎锡山会面并商谈解决冲突办法。王、肖提出了6点建议,即“(一)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停止政治攻击。(三)新军表示拥阎,不受某方改编;(四)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五)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领。(六)恢复与新军的电台往来,及人员往来。” 阎锡山表示,新军属晋绥军是其愿望,目前问题已交中央,不便说话,但他相信这件事可以“自然演变,不了自了”,新军会自动归他指挥,不致受中央收编。至于恢复八路军交通线,阎亦表示不是问题。据此,中共中央明确认为可以承诺与阎锡山“在晋西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在公路以南准备停止游击战争,党的工作转入秘密状态”;与卫立煌“在晋东南以临(汾)屯(留)公路为界,八路及新军不向路南发展”(37)。 毛泽东特别解释晋东南划界问题称:“此次反摩擦斗争中我们能够巩固临汾、屯留、平顺、漳河、大名之线,已算很大胜利。在此线以南,应与国民党休战,维持卫(立煌)之地位;在汾离公路以南则与阎锡山休战,维持阎之地位……这种休战现时是完全必要的。”他的基本设想是:在山西,“认真恢复我们与阎锡山的关系,寻找具体办法,建立新旧军的妥协,使新军牺盟重归阎锡山指挥”。同时,在晋东南,“争取使蒋、阎、卫承认,军渡、汾阳、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为双方作战地界,在此线以北之彼军如朱怀冰向南调,在此经南之我军向北调。我们只保留垣曲通太行山及永和通灵石两条兵站线”。“其重心之重心又在朱怀冰退出磁、武、涉三县及承认壶关、林县为我驻兵地区”(38)。 但是,想要以汾屯公路划线,这时却已经变得很难实现了。还在1月12日,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就去电军令部,要求将已在晋东南之庞炳勋、范汉杰两军归其指挥,并要求划白(圭)晋(城)公路以西、同蒲路以东、长治东阳关以南归第一战区(39)。蒋介石当即批准了卫的请求,并先后于1月17日和2月14日两令朱德将部队移至白长路以东、长(治)邯(郸)路以北地区。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命令,朱德、彭德怀强烈反对。1939年7月,日军大举进据白晋路和长邯路沿线之后,原晋冀豫区被切为四块:白晋路以东、长邯路以北为太北区;白晋路以东、长邯路以南为太南区;白晋路以西、中条山以北为太岳区;中条山及以南为晋豫区。创建晋冀豫根据地的计划已无从实现,如果连太南区也放弃的话,太岳、晋豫两区亦难接通,八路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将只剩下太北区了。故他们坚持认为:太行山南部的壶关、长治、潞城、黎城、平顺是我基本地区,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巩固,并尽可能争取巩固陵川以及高平至晋城大道以西地区。对高平、阳城、晋城、陵川地区的叛军和反动政权,应寻求机会打击消灭之。对中央军虽应尽力避免冲突,但其如果进犯我军,则应给予坚决打击,争取消灭其一部(40)。这一意见意味着,他们不仅对蒋令不以为然,就是对中共中央打算以汾屯公路与阎锡山划线的提议,也不很认同。 而毛泽东同样很坚持自己的意见。其1940年3月5日给朱、彭发去长电,力劝朱、彭将前伸至晋城、陵川、高平之部队撤回到长治以北来。为此,他委婉地提出,可以争取让对方“承认壶关、林县为我驻兵地区”。他很清楚,该两县是在蒋介石命令的北撤线长治、邯郸路以南,蒋必不接受此议。因此,他实际上的意见是请朱、彭考虑:“退出壶关、林县两县”,“承认平顺、磁县为两军境界”(41)。 这个时候八路军与中央军在晋东南的军事冲突已经箭在弦上。蒋于2月14日再令不见朱德回电后,于2月22日正式批准了军令部拟定的对太南地区八路军实施包围,必要时“断然歼之”的作战方案(42)。3月3日,蒋又以手令形式发出命令。3月12日,在仍没有收到朱德回复的情况下,蒋介石更进一步发出限期令:“严令第十八集团军所部,限本月十五日以前撤至长治、邯郸之线以北,该线上归中央军防守,如其不遵限撤去,应以违抗命令,破坏抗战之叛军论罪”。电报明令在山西的中央军,八路军过期不撤,即应“全力剿除之,勿稍犹豫,致误大局”(43)。 得知蒋限期令后,彭德怀电毛泽东,仍强硬表示对中央军的过分压迫应以防御姿态予以抵抗。毛复电再示不同意见,明确提出:“须避免在陵川、林县地域再与中央军冲突。如彼进迫,我应北退。”并告诫说:“蒋卫已下令庞炳勋、范汉杰、刘戡、陈铁各部主力集中于太南周围,并有从陇海路加调六个师渡河讯,请兄等密切注意此事之严重性。”“我们此时必须避免同中央军在该地域作大规模战斗,因此须准备让步,以便维持国共两党合作局面。”为此,“请你们考虑让出陵川、合涧、林县一线的问题”(44)。 慎重权衡利害并考虑中央的意见后,朱、彭终于不得不痛下决心放弃长治以南地区。他们于15日一面电嘱各部:“当前应以保障离汾、临屯两条公路和平顺及漳河以北地区的巩固为主,避免扩大摩擦及继续摩擦。”(45)一面电告蒋介石和卫立煌,说明已下令将晋东南平顺、陵川境内的八路军一律撤至平顺,将豫北辉县、林县境内的八路军各部,一律撤至漳河沿线(46)。 自3月15日起,晋东南八路军在长邯路以南的部队,陆续开始北撤,地方党政机构和群众组织骨干亦被迫随军全部北迁(47)。据统计,此次北撤八路军主力部队1.2万人,太南特委及所属17个县的党员约5000余人,牺盟会等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卫生队等约1万余人(48)。 五 结语 晋西事变发生的直接原因,明显与1939年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强化限制中共方针措施的出台这一大背景有关。但归根结底,它还是与抗战开始以来国共两党,也包括合作关系一直还不错的阎、共双方,基本利害冲突达到了相当程度,因而会一触即发这一深层背景有关。阎锡山生怕他一手创立的牺盟会和决死队被八路军控制了去,八路军又早就在相当程度上通过秘密的方式实际掌握着牺盟会和决死队。一旦阎锡山受到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防共限共警告的刺激,开始想要采取措施实际夺回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控制权,中共方面又绝不放弃这一权利时,双方之间就难免高度紧张,并可能因意外事件而爆发严重冲突。 只不过,在当时条件下,国共也好,晋阎与中共也好,最主要的敌人还是日本侵略者,因此三方至少在形式上都还力图维系合作关系。晋西事变不仅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的计划无关,也不在阎锡山的计划之内,也超出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预料。这也就决定了三方,特别是毛泽东和中共方面,在应对事变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相当复杂的情况,内部分歧及应对方针前后变化很大。 从事变的结果来看,中共和阎锡山都相信自己一方遭受了损失,蒋介石的中央军因之获益,一战区卫立煌乘势控制了晋东南大部地区。但在毛看来,能够取得在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控制权问题上与晋阎一分为二,特别是能够与阎、蒋在山西分界而治,从而取得军政地方控制的合法权力,无论如何都是一大收获。这也是毛泽东所以会力劝朱、彭等妥协退让,以息事宁人的办法了结了这一事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共、阎、国此番割袍,无异于破裂了此前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军政指挥体系和共、阎在山西的合作关系。自此之后,一方面中共相信各方活动范围已基本划定,自己已经独立自主;一方面国民党中央却仍旧坚持以政令军令限制防范中共,双方之间会更多爆发摩擦,甚或走向冲突对立。 ①八路军1937年9月出发时的确实人数约为3.4万人[见《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并见张廷贵、袁伟、陈浩良:《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503页;《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重庆签报蒋委员长提出扩张要求》(1939年12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5编(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印,第494页]。 ②《院长孔祥熙令》(1939年3月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号:特005-25.13。 ③《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社会部档案,档号:(京)53。 ④《王世英关于山西阎部情况的报告》(1939年5月11日);《杨尚昆关于山西时局与统战问题的一封信》(1939年6月7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1页。 ⑤转见《杨尚昆在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1939年9月28日),山西省档案馆等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587页。 ⑥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209页。 ⑦参见《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战的指示》(1939年8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阎锡山右转向我们对策的指示》(1939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202页;《中共中央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1939年9月21日);《朱德、杨尚昆、左权关于山西反妥协反投降及豫北工作的意见致彭德怀电》(1939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385、401~402页等。 ⑧《杨尚昆关于山西时局与统战问题的一封信》(1939年6月7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379~383页。 ⑨《中共中央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193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第384~385页。 ⑩凌云:《晋西事变前夕剑拔弩张的秋林》,《炎黄春秋》1999年第12期;安力夫:《与党和人民共命运》,《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离退休干部回忆录》第2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页。 (11)《彭德怀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39年11月下旬)。 (12)从韩钧后来被批评“破坏统一战线”,再未叙用,本人长期想不通,以至自杀而亡的情况,亦可看出晋西事变爆发不在中共计划之中,因而受到批评(参见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13)《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团报告书中所述共党煽动国军叛变情形》(1940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5编(3),第16页。 (14)转见山西省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山西新军概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 (15)《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团报告书中所述共党煽动国军叛变情形》(1940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5编(3),第24页。 (16)《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呈蒋委员长报告独二旅政治主任韩钧鼓动该旅一部在隰县附近叛变电》(1939年12月5日);《第二战区参谋长楚溪春致军令部徐永昌转呈蒋委员长报告韩钧等叛变情形并请示处置办法电》(1939年12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5编(3),第11~12页。并见山西省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山西新军概况》,第241页。 (17)参见杨献珍:《十二月政变前五专署的一些情况》,中共长治市委党史办公室编:《(长治)城区党史资料》第3辑,中共长治市委党史办公室1983年印,第39页;戎子和:《我在五专署时期的几点回忆》,中共长治市委党史办公室编:《长治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长治市委党史办公室1982年印,第37页;王培仁口述,程东明、王雷平整理:《我在长治工作时的片断回忆》,《长治党史资料》第2辑,中共长治市委党史办公室1983年印,第25页;戎子和口述,王雷平整理:《五专署工作情况粗忆》,《长治党史资料》第4辑,中共长治市委党史办公室1983年印,第44页;聂真:《在晋豫5059、太岳区的斗争历程》,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西革命回忆录》第4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18)蒋介石迟至1940年1月10日始有回电给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称:“查此次晋西部队叛变,共党否认系其策动,我为振肃纪纲,剿灭叛军,自属名正言顺。阎长官所拟一、二两案,以第一案为妥”[转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 (19)可参见《楚溪春致重庆军令部徐部长电》(1939年12月18、21、24日)等,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档号:特交文档(四),50591,50592,50593,50594等。并参见中研院近史所编:《徐永昌日记》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印,第248、249、251、254页。 (20)《军委毛、王关于晋西南新旧军冲突及我们的方针的指示》(1939年12月6日)。 (21)《毛、王关于晋西事件之估计及我之方针的指示》(1939年12月9日)。 (22)《罗贵波关于对二○五旅、独七旅事件发生后工作布置致中央电》(1939年12月20日),转见杨锡九:《与120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编者商榷——关于赵承绶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问题的考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45502a0100b9r1.html,2015-02-16。 (23)《军委毛、王致朱、彭、杨、贺、关关于援助新军击退旧军的指示》(1939年12月22日);《毛泽东关于对晋西南事变的方针》(1939年12月23日)。 (24)到1940年1月,牺盟会原先已经掌握和基本掌握的晋城、陵川、高平、长治、长子、壶关、阳城、沁水等10县,均被孙楚及国民政府军夺占,县以下干部损失超过200人[《关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晋东南杀害逮捕我干部的情况通报》(1940年1月6日),中国军事科学院编:《左权军事文集》,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412、414页;《薛迅关于晋豫工作的汇报》(1940年2月10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72页;《中共中央关于山西十二月事变经过及解释方针的指示》(1940年1月28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36~39页]。 (25)《毛、王关于非把吕梁山之逆军逆党全部消灭决不放手致德怀电》(1939年12月30日)。 (26)有关中央军在当地具体驻扎及介入事变的情况,可见《薛迅关于晋豫工作的汇报》(1940年2月10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65、69~71页。 (27)《毛、王致总部、一二○师关于晋西事变以及我军事部署电》(1939年12月31日)。 (28)《朱、杨、左致黄克诚并告彭德怀电》(1940年1月5日);《朱、彭致聂、吕、程等电》(1940年1月5日),中国军事博物馆编著:《朱德军事活动纪事(1886-1976)》,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521页,并转见《毛泽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对阎方针致彭德怀电》(1940年1月11日)。 (29)《毛、王致德怀同志电》(1940年1月5日),转见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92页,《毛泽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对阎锡山的方针给彭德怀的指示》(1940年1月11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30~31页。 (30)《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1940年1月16日)。 (31)《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山西问题的报告》(1940年1月18日)。 (32)《中央关于阎锡山继续反共情况下对山西工作的指示》(1940年1月25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22~23页。 (33)《中央关于阎锡山继续反共情况下对山西工作的指示》(1940年1月25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22~23页;《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 (34)《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40年2月)。 (35)《毛、王致朱、彭等电》(1940年2月11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86~87页。 (36)《毛、王关于山西新旧军冲突我之工作方针问题致朱德等同志电》(1940年1月31日);《毛泽东、王稼祥关于为新军代拟致阎锡山电稿及新军口号致朱德等同志电》(1940年2月11日);《毛、王致王世英电》(1940年2月7、11日);《毛、王致朱、彭电》(1940年2月14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86~87页。 (37)《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山西十二月事变后我之基本政策的指示》(1940年3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88~91页。 (38)《毛泽东、王稼祥关于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的方针与基本步骤给彭德怀的指示》(1940年3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92~94页。 (39)转见中研院近史所编:《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262页。 (40)《朱、彭、杨致黄克诚电》(1940年1月29日),转见中国军事博物馆编著:《朱德军事活动纪事》,第523页。 (41)《毛泽东、王稼祥关于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的方针与基本步骤给彭德怀的指示》(1940年3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93~94页。 (42)见《刘斐等关于鹿钟麟企图侵占陵川围歼八路军往来文电》(1940年2月19日);《蒋介石致鹿钟麟密电》(1940年2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第254页。 (43)《蒋中正致洛阳卫长官电》(1940年3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档号:特交文电,29061172。 (44)《毛泽东复彭德怀电》(1940年3月13日);《毛、王关于必须避免同中央军作大规模战斗致朱、彭并告贺关、刘邓、左黄、陈罗电》(1940年3月15日);《毛、王关于请考虑让出陵川、合涧、林县一线致朱、彭电》(1940年3月15日)。 (45)《朱、彭、杨致电左、黄、杨、程、宋、刘、邓等电》(1940年3月15日),转见中国军事博物馆编著:《朱德军事活动纪事》,第532页。 (46)《朱彭致重庆蒋委员长电》(1940年3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第243页。 (47)实际撤军界线似应在漳河以南的林县姚村以北和平顺、壶关以南的大井至郭家坨一线,即河南林县北部到平顺、壶关一带[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注16]。 (48)见焦书文:《华北抗日斗争史上的重要一笔——太南撤军》,《党史文汇》2002年第5期,第34~35页。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阎锡山论文; 八路军论文; 中央军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1939年论文; 历史论文; 国民革命军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