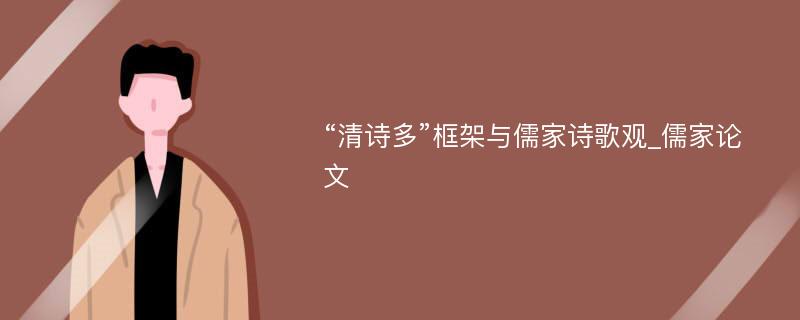
《清诗铎》的构架与儒家诗歌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构架论文,诗歌论文,清诗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诗铎》是清人张应昌耗费十多年时间精心编选的一部大型诗歌选本,所收诗作从明末清初至同治年间,但以清代中后期为多。前人也有认识到这是一部非凡诗歌选本的,但长期以来无人研究。我因见该书内容丰富,现实性极强,情调沉痛感人,艺术上有独到特色,文献价值亦高,总觉得这样的选本若受冷落是一大憾事,故撰文《〈清诗铎〉的社会视野初探》,该文于《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3期发表后, 已引起一些学者注意。笔者余兴未绝,又撰此文,对《清诗铎》的构架作些研究,以求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这本诗选。
一
《清诗铎》不仅凭内容扎实,情调忧患感人至深取胜,而且它还有很独特并自成体系的构架,构建出没落中的旧中国的社会群体框架,再以内容丰富繁多的、有血有肉的诗歌充填,展现出那一社会的立体画面,场面很为宏大。并且由于内容的丰富性,使得那一藏污纳垢的社会暴露无遗,令人一见惊心动魄,再见毛发耸然,直欲痛斥。本来,艺术家反映或再现社会群体面貌,因小诗很受限制,往往采用的是《清明上河图》那样的长卷大型绘画方式,或采用长篇小说塑造形形色色社会人物的方式刻画。张应昌却选择了短小精悍的小诗,但采取的是采花为蜜、集腋成裘的再加工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群体面貌,别具匠心地规范于他自己构建的社会框架之中。
《清诗铎》不象其他选本,不是按作品的创作时间编撰、不是按作者的生世先后编撰,不是按诗歌形式分卷编撰,不是兼收并蓄各种作品以诗取诗,不是以某种艺术风格统筹编撰,。《清诗铎》是以社会问题统诗,以社会观察、政治倾向、艺术特色来选诗。编撰的体例又巧妙地以社会问题为支架,以诗的内容为砖石,以思想倾向为色彩自成体式的构架。
《清诗铎》的构架是异常庞大的,又是有序渐进的,很见创造性和囊括一切的涵度。不难看出,编选者张应昌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思想,艺术思想是儒家诗歌观,编选过程是这种诗歌观的取舍实践,编排体例是这种取舍的条理化、规范化、系统化,故在思想上虽然受儒家思想牵制,诗歌观继承白居易及新乐府诗派的思想,但在选本的结构上却自成体系。
张应昌编选《清诗铎》,在指导思想方面,自己声称持儒家诗论为依据,这在《清诗铎》的《自序》中自有阐述。他说“孔子曰‘兴于诗’,晦翁以为兴起学者好善恶恶之心。取其为言易知而感人易人也。”但他又不完全赞同孔子的诗歌观,尤其认为孔子的“温柔敦厚”之道过于隐晦,“然解人默喻,而流俗未能明晓也”。强调“直言讽刺之作,其不必讳者”,从汉儒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见解中申发自己的见解,因而能够注意到那些痛斥黑暗现象的诗歌,从而与杜甫、白居易的诗论进步主张相通,能相当大胆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论唐诗,张应昌推崇“子美《潼关吏》,《石壕吏》诸篇及香山、文昌、仲初新乐府”(《自序》)。在《自题》中又说“乐府爱香山,陈事比贾谊。诗史称少陵,三别与三吏。文昌仲初俦,歌行亦其类”。这样的指导思想,就决定了唐代新乐府诗派;这样的指导思想,就决定了唐代新乐府诗派的诗歌观得到了继承,所选的诗能具有现实意义和大胆的揭露。
张应昌是清朝官吏,属统治阶级内部人物,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论诗自然也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但儒家的诗论自唐代起分为两派,共同的特点都关心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关心诗歌与社会的关系,主张诗歌要为政治服务。不同的是,一派比较保守,主张用诗歌维护封建礼教,为统治阶级粉饰太平,孔子有“事父事君”说,汉儒有“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说。另一派是以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儒家诗歌观,主张诗歌要反映社会问题,揭露社会矛盾,白居易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说法,又有“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但得天子知”的主张。张应昌接受了白居易的主张,《自题》中说“吾儒吐言辞,于世期有济,岂徒累篇牍,月露风云字。乐府爱香山,陈事比贾谊。诗史称少陵,三别与三吏。文昌仲初俦,歌行亦其贵。”持论同《与元九书》,又宣称自己是儒家,要继承杜甫、白居易作品中现实性强的那种精神。至于编选主张,则是“惜哉充栋编,纷若散珠碎,不免闻见遗,曷资韦弦佩。披拣集众益,民生及吏事。以充铭座词,以为采风备。”(《自题》)说得很明白,一是惋惜诗歌散失,二是为了“采风”。采风的目的,又是为“民生及吏事”,即为了反映民情,上达助皇帝确定论国之道。“采风”即“采诗”,周代有采诗之官,从民间采诗搞国情调察。但张应昌与一般的编选家不同,“专择其关于警觉之义者录于篇,名之曰铎,以宣民德,以资吏治,以厚风资吏治,以厚风俗,以清政原。”(《清诗铎·朱序》)至于“铎”,《朱序》有解释说“金铎通鼓”,又说“铎,度也”,作动词用,即击鸣之意,“清诗铎”即是以清诗鸣击报警之意,这就决定了必然选择现实性强烈的,暴露深刻尖锐的作品。但张应昌还有儒家忠君的一面,也决定了张应昌还今选择一些为皇帝歌功颂德的,甚至反对农民起义之类的作品。然而,由于白居易诗论的指导思想浓重,《清诗铎》还是“惟歌生民病”的作品为主导,决定了它的价值。
二
《清诗铎》共选诗二千首,规范为二十六卷,一五二类,每类都是一种至数种社会问题,每种都有若干现象,主题相当鲜明,仅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是当时较强烈的社会问题和现象。例如,卷一是气候交通及法制问题,分为《岁时》、《舆地》、《总论政术》、《善政》四卷。卷二是财务税收问题,分为《财赋》、《米谷》、《漕改》之类。而卷一至卷四实际都是经济建设问题。卷五至卷六是农桑经济问题。有的卷类列很多,如十二、十五、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等卷问题都多达十几类;涉及面相当广泛,很有社会百科全书的容量。且从名称上看,又可知编者的政治嗅觉相当敏感,对官吏的腐败、统治阶级的矛盾、国事的艰危、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外来侵略、腐败现象、民生艰难等都有精细的类别。例如卷十四《灾荒总》即收诗一百二十七首,总观灾荒危害,已够惊心动魄。卷十五又再立《水灾》、《旱灾》、《风灾》等十多类足见种种灾害雪上加霜似的危害情况,活现当时人民水深火热的处境和惨状,其中人吃人现象尤为令人悲愤欲绝。又如《催科》、《税敛》、《力役》、《扰累》、《捕捉》等,仅从名称上即可以看出编者在有意挖剥当时的社会疮疤。因这些问题都来至官府,来至封建统治阶级,故官吏的贪婪凶残、朝廷的腐败是无法掩饰的。
从卷目编次来看,张应昌对社会问题,早已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眼光,在他看来,社会黑暗处处皆是,社会问题来至各个方面,不再是孤立出现的,并且,有问题就有诗歌反映,有诗歌揭露就有社会问题。所以,他以社会问题的构架,选诗充填,整本《清诗铎》显得有巨型建筑的体式。对于社会问题,张应昌也不当作一团乱麻,而是有自己的权衡。《清诗铎》罗列的问题,不是其他选家喜欢选择的风花雪月、愁情别绪;不是凭栏怀古、官场失意;更不是声色犬马、花间月下之类,而是与国运民生有关的内容,如吃饭穿衣、灾荒人命、治国齐家、战火兵荒等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专卷,一般是不受诗家选家注意的,例如《查户口》、《吏胥差役》、《赌博》之类。类似的问题,其他选本罕有专卷,都足以看出张应昌执国民生计问题之网,要对社会问题进行一番大的揭示。故若研究《清诗铎》的类别编目(原书称为“分类目”),即可知张应昌眼中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什么样子,再考察所选诗歌,又可知这个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张应昌不可能认识到封建社会必然没落的命运,但已看到整个社会在腐败溃烂,这比当时仅在个别问题上认识到封建社会黑暗的人要高明得多。
这里似有必要从《清诗铎》类别的排列来考察张应昌对社会问题的系统观察,既可见《清诗铎》的构架之宏大,又可见其体式与社会的关系。《清诗铎》大体是以社会问题的大小与缓急来依次排列的(若小有混淆并不影响这一判断)。考察首起卷一至卷七,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其间出现的是经济基础的问题。第一卷至四卷是交通财务税收等问题。五至七卷是农业桑蚕问题,含《水利》、《农政》、《田家》、《树艺》、《蚕桑》、《木棉》、《纺织》七大类,是封建社会的经济支柱。在儒家看来,立国在于农桑、军队,《论语》记载“子贡向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食”、“兵”就是指农业和军队,这的确是封建社会的命根子。交通财税,对统治者的生存是最直接的,下达政令、调兵遣将和维护国家的开支、兵饷,无不赖此。所以把这些问题摆在各种社会问题的前列,是必认为至关重要的了。于此之后,八至十卷是《丈量》、《催科》、《税赋》、《力役》等十二类,全属国家政务,表明张应昌对政府职能的考察。从现代人来看,农业交通都是当时立国的基础,那么这些政务则是上层建筑的构属。是否可以说张应昌看到了什么样的基础有什么样的上层呢?即使不能说,那么指出基础破烂崩溃,国政流毒生瘤,客观上也就是这样的看法,总算是看到了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及症结。接着十一至十三卷,编排的是军政国防问题,是维护封建上层建筑之中的问题。如《盗贼》、《武功》、《兵卒》、《军器》等都是军事事务,这些问题,既有歌颂清王朝的武功又有咒骂农民起义军的内容,但也有一些揭露统治阶级的军队沦为匪徒烧杀摅掠危害社会的内容,当具体分析。即使清王朝的武功,也不全是镇压人民,也要加以区分。至此之后的问题,再无直接关系到封建社会命根子的问题,而是自然灾害、社会各阶层、封建道德及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在十四卷至十七卷都是自然灾害对社会危害的问题,其间有贪官污吏乘机敲诈勒索的内容。接着十八至十九卷,是吏治问题,官场人事问题,如《用人》、《察吏》、《仕宦》、《训士爱士》等都很直接。排于灾害问题之后,大概是认为人祸仅次于天灾。随之二十卷排列的是儒家重视的封建道德问题,对这些问题有揭露有礼赞,体现出张应昌的不彻底性。二十卷之后,更能见出张应昌对社会问题的权衡,愈往后愈是儒家认为次要、低下的问题。以民风民俗、社会下层居多。最后几卷全是奴仆、妇女、苦力、嫖赌之类的问题,如《淘金》、《采矿》、《采薪》、《采煤炭》等表现的都是社会苦力,《妇女》、《悯婢》、《娼优》、《驭仆》等,人物的社会地位更为低下,是孔子眼中的“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但张应昌对这些人很同情,选录的不是一些挖苦、嘲讽这类人的作品,而大多是为小人、女子鸣不平的作品,是一篇又一篇的血泪控诉和大声疾呼的作品,是白居易同情人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及全面化。为张应昌争得了光辉,也成为《清诗铎》的闪光点之一。
至此,可以作一个简略的综合,那就是:一至七卷为交通财务农业桑蚕经济的问题,八至十卷为行政管理问题,十一至十三卷为军事国防,十四至十七卷为天灾水害,十八至十九卷为吏治人事,二十卷为家庭伦理建设,二十一至二十二卷为道德修养,二十三至二十四卷为民间习俗,二十五至二十六卷为下层社会问题。由于类别繁多,涉及了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充分体现了编选者多方位的观察,多角度的揭示,体现出社会的立体框架和丰富的内容。
从以上综合就能直观地看到,《清诗铎》的体例是以社会结构印象为框架而以有关诗歌为砖石充填而成的。但张应昌是先以社会总体印象为框架再分门别类进行选诗入围呢?还是先行观诗选诗然后再分门别类根据社会观察而就范呢?不可得知,这不重要。然而张应昌持儒家诗观(白居易派)去读诗选诗这是无疑的,为此选录了大量的反映社会问题的诗歌与社会问题映照,二者必经过多次的互相协调、互相规范方能得出那样的体例。历来的诗歌选本很多,但能与社会结构映照的选本却很少见,构架成体系的更只此一家。《清诗铎》一方面系统地体现了儒家诗歌观积极的一面,体现了儒家的社会观念、忧患意识。另一方面,《清诗铎》又通过活生生的艺术作品,全面保存了那一时代的旧中国的社会现实状况,使得那一社会与艺术都存活一大部诗歌选本中,难度相当大。可见编选者的气概和本领及态度,成绩也是突出的,通过编选与社会问题映照的方式来体现整个社会面貌和思想观念,也是有创造性的。
三
从以上研究,可知《清诗铎》是以封建社会结构及相关的社会问题为框架,选诗暴露这个框架的实体及有关问题的组合体。这种框架结构对《清诗铎》的成就有什么关系呢?不妨设想,如若《清诗铎》不采取与社会问题映照的方式,而采取错杂罗列的方式或其他方式,会有什么效果呢?那就是,读来如同进入鬼域,呻吟此伏彼起,只闻哭声,不知问题;只见病态,不见症结,社会一片混乱,不知矛盾何在等感性认识居多。而《清诗铎》把若干诗歌纳入一定的框架,把一个问题从方方面面考察,则读者仿佛进入一个黑暗社会的实体参观,有路有径,有坎有门,有房有屋、有人有物,能观总体面貌,又能考察细部。并且,问题的分类使得矛盾尖锐突出,暴露更加强烈;集中暴露,控诉也强为有力。有关诗歌的集中,使得面上能展开广度,点上能进入深度,同一问题以诗歌连续暴露的方式出现,如一锤又一锤地鼓击,方能充分起到“铎”(警策)的作用。好比这里鼓一声锣那里擂一下鼓,总不及列阵分行响起来,相继不绝地响下去惊人得多。
针对一个问题,编选一大批暴露黑暗的诗歌,仿佛一针见血,产生一定的刺激,但如果《清诗铎》仅限于任意罗列社会问题,选择暴露黑暗的诗歌,力量也不会强烈,一针见血也只是见血而已。《清诗铎》通过有意识的成体系的组合,一大批又一大批的集中暴露却是形成一种连锁反应,掀起整个社会的波动,使人觉得整个封建社会的摇动,内部在流血,尽管还未能揭示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将要出现、壮大,但陈旧的正在没落与死亡已是昭然若揭了。封建社会的行将就木已十分可见了。例如,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盗贼”问题,《清诗铎》立有专类,但如果采取单篇的方式,即使出现杜甫诗“不过行检德,盗贼本王臣”那样的指责,也只是一个指责,一种揭示,未能深入。而《清诗铎》的《盗贼》专类,收诗几十首,不仅可以从活生生的例子中看到“盗贼本王臣”,还可以看到官兵做盗贼“弓箭在手刀在腰,门里劫商门外坐”,“人人知是食粮兵”。还可以看到被官兵掠夺后“报官知”反被“合门拷掠血淋漓”的事实(见《绿林豪》)。又可以看到官兵巡捕对真正的盗贼“口噤目眙不敢前”(《估客泣》)而“煌煌铁马四百骑,缚得倡家两博徒”(《鸡犬》)充数的闹剧。可以看到官方“捕人亦作贼”,“捕人安乐流民苦”(《警捕人之虐》)的颠倒世界,对官盗勾结问题,还有更令人惊讶的。例如《捕贼人》写不堪盗贼危害的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捉贼,等到抓住了贼送交官府,官府的“捕人”“公然下乡村”,“和钱还送胥吏门”。捕贼的官与做贼的又有何区别?更有甚者,写捕贼的官长,捉贼关起来后,晚上放贼出去搞盗窃,得脏物与官方瓜分,出现“贼充捕,捕养贼,衣贼衣,食贼食”的丑恶现象。如此,老百姓报官,“捕人”反而刁难声明贼已经捉来关在监房里怎么能出去偷盗呢?反诬来报案的老百姓作伪。而“失物之人语顿塞”,直到“咚咚鼓动贼四合”公开大干时才知道底细(《放鹁鸽》)。《盗贼》中的丑事是多方面的,不再一一例举,需要区分的是,有少数诗把农民起义军也当作盗贼则是反动的了,可具体分析。
如此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若干社会问题,单题单篇只能限于一隅之见。而一个问题从方方面进行揭露,若干问题也从方方面进行揭露,才能构成与社会形态相应的,从全方位反映问题的总体力量,留下历史长卷、文学群体形象。
张应昌之前,白居易新乐府诗派的诗歌观早已流行,元白张王也创作了几百首“惟歌生民病”的诗歌,历代诗歌选本也颇注意。然而,为什么在张应昌手上突然出现那么一部以社会问题为框架的,规模俱全的诗歌选本呢?而较早一些的诗歌选本却无类似的可以比较呢?是张应昌全凭个人兴趣、个人偏爱吗?也许这有一些原因,但更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社会原因。从张应昌生活的时代来看,正是清帝国从停滞到急剧下坡的时代。列强的侵略,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官吏的腐化、吸毒的严重,自然灾害的危害,贫民的困苦等都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远远超过了元白张王的时代。从诗歌发展来看,元白张王的乐府诗,是“惟歌生民病”的初期,尽管他们的艺术才能都很高,但社会矛盾暴露得还不充分。封建社会末期才出现的许多问题,那时还未出现,例如《清诗铎》中反映的人口与土地的问题,西方商品冲击的问题,吸食鸦片的问题,列强侵略问题,都是清代才出现的。旧的矛盾已经充分暴露,新的矛盾急剧升华,如干柴遇火,如火上加油,对社会形成比以往强烈得多的冲击波,促使有政治眼光的知识分子更关注社会问题。张应昌时代已陆续出现林则徐、龚自珍、魏源、洪秀全等那样对社会问题有深刻见解的知识分子。后来成为改良派的郭嵩焘、冯桂芬等人也在对现实思考,他们的观察都不再限于一人一事、一角一隅,而是试图对整个社会进行总的观察研究。就观察社会问题而言,张应昌也是敏感的一个。但他与思想家不同,他不是要从政治上、哲学上作出解释,而是以选诗的方式来对照各种问题加以反映暴露,来表现自己对社会的爱憎及忧虑。哲学家以思维的方式解释世界,政治家以行政手段改造世界,而艺术家诗人则以艺术形象来反映和表现世界,张应昌则是以选诗的方式来反映和表现世界及表现自己的爱憎,而以选诗可反映和表现世界,又做得那么系统,自有他的独创意义。
由于《清歌铎》是以社会来构建选本体例的,因而《清诗铎》也兼备两重性,既是社会的,又是艺术的;既是社会问题的总汇,又是艺术群体形象的组合;既有当时社会百科全书的含量,又有诗歌艺术宝库的本色;既是艺术的又是文献的。但不论从哪一方面着眼,《清歌铎》都是一部匠心独具的选本。张应昌活了八十四岁,《清诗铎》是在他的晚年(66—79岁)编选的,此时阅尽人世炎凉,眼光老辣,对社会才能看出那么多问题来,所选也就切中时弊,能透见内脏。书稿成时,当时人应宝时阅后即惊赞说“此天下不可无之书,非独为功于诗教也,而诗教亦莫善焉”。又把《清诗铎》与几部最著名的诗歌选本《楚辞》、《玉台新咏》等相提并论,说“是则历来选家莫之及也”。《应序》此非虚话,亦非吹捧。的确,比较起来,在诗歌选本中,有意识地从社会问题着眼的诗歌选本,论构架及规模及体系(不是指数量的多少而言),《清诗铎》不仅前无古人,即使后代也没有一部堪与匹敌,更没有一部超过它。因此,《清诗铎》一方面在文学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留下了许多艺术形象,一方面为文学和历史留下了很丰富的文献,为过去的时代摄录下足以长期留存的文字画卷。张应昌的创造性劳动是有价值的。
标签:儒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清诗铎论文; 诗歌论文; 封建社会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白居易论文; 张应昌论文; 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