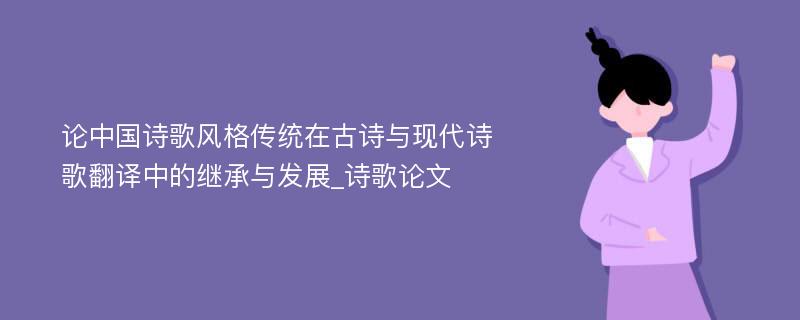
论古诗今译中汉语诗体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今译论文,诗体论文,汉语论文,古诗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3年郭沫若选译《诗经·国风》成《卷耳集》,做了古诗今译的首位“食螃蟹者”。这引发了关于诗是否可译的热烈讨论,并使古诗今译者接踵而起。至今古诗今译的成果之多已难统计,只是书的印量之大也远超一般的学术书籍。然而,就现在已发表和出版的古诗今译成果看,能接近原诗的情致韵味和艺术风貌的实属少见。这说明古诗今译不仅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也应从实践上做出尝试和提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对祖国传统诗性文化遗产的继承和推广,关系到新诗诗体的发展与建设。
现有的古诗今译质量普遍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译者之目的似乎只是疏通文字障碍,说明文本意思,而对如何复现原作的情绪、意象和意境等往往考虑不多,结果造成这样的现象:在语言上只将无严格语法规范的文言转成有严格语法规范的白话,而根本不顾古诗独特的点面感发式语言体系在今译中的转化问题;在形式上只把绝句、律诗、词和散曲小令一律转成大致押韵的自由体或半格律体,而根本不顾其特殊的音节设置、形态有别的格律在今译中的移植问题。而事实上,诗译与诗创作一样应有固定的判断标准。法国大诗人瓦莱里曾十分赞同马拉美的意见:“诗歌须予字意、字音甚至字形以同等价值。”这句话引起了中国当代一位诗歌翻译家的共鸣,认为在译诗时应考虑到“音美”、“形美”与“意美”同等重要,而不是诗歌可有可无的“装饰”。① 由此可见,古诗今译当然要把诗的意思转达出来,但诗中的“意思”只是所指,是通过能指活动体现出来的;而诗歌的能指活动是一个包括情绪、想象、意象等诸多方面围绕着意境而展开的多向交流系统,“意境至上”乃是中国古诗之所以能特立于世界诗歌之林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古诗今译者来说,首先是——或者说只能是忠实地传达原诗的意境才算是完成了今译的使命。而意境并非神秘抽象的存在,它的物化形态是意象及其组合体,所以意境实为对意象及其组合体具体而真切的体验。至于意象及其组合体,乃是情绪—想象的产物,它也有自己的物化形态,那就是情绪感兴的语言与声音象征的形式。有学者曾表示:“翻译外国诗歌用中国古典诗体,又用文言,很难成功。”② 同理,翻译中国古诗仅用西方的语法和现代白话也难以办到。古诗今译中语言的转换和形式的移植并不是只凭变文言为白话、再拿自由体凑上几个韵脚就能解决的,必须对之进行认真和深入的探讨。
古诗今译在语言的转化中首先应以继承古典汉诗语言的优良传统为原则,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点面感发式隐喻语言的保持,二是意境感兴化抒情特征的坚守。
中国古诗所采用的语言,是在神话思维的观物态度和天人感应的感物方式作用下的一个属于直觉世界的符号传达系统。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排斥分析演绎、逻辑推论,强调词法、句法对对象直接显示和直观感兴的作用;(二)淡化语法甚至不受语法规范;(三)按对等原则开展词法、句法和连续性的句法活动。这些特点是从古诗的下述反常语言现象中概括出来的:词性活用、人称不明、成分省略、词序错综、关联脱落等。这些反常语言现象说明古诗所属的语言体系不同于新诗的线性陈述,它是一种点面感发式的语言体系③。从这一语言体系出发,今译者对这些反常语言现象本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今译中也当尽量保持其“反常”的原貌,而事实上,今译者基本上都没有这一认识,他们通常采用新诗那种词法、句法,按照逻辑的推延关系,用严守语法规范的语言来译古诗。结果在这些今译文本中,原作的词性活用变得规范了;人称不明的,也代原作者使之明确了;成分省略的,全部给予补足;词序错综的,按语法规范序列的要求也理顺了;关联脱落的,全都给有机地连接起来了。总之,古诗中凡是按对等原则④ 进行的词法、句法活动,都遭到了破坏,一切全照现代语法规范处理。这样,今译文本力求“意思”明白的目的基本达到了,但原诗提供给读者的想象余地却所剩无几,意象及其组合体因趋向如实化而使得兴发感动的功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意境就更是随之变得淡薄。这方面的例子随处可见。如徐昌图《临江仙》词的下片:“今夜画船何处?潮平淮月朦胧。酒醒人静奈愁浓!残灯孤枕梦,轻浪五更风。”这里的最后两行,各由三个光秃秃的、不见关联的并置意象按对等原则组合成两个并置的意象群,用来作为“奈愁浓”的“浓缩象征”。两个诗行各自的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反映着对分析—演绎和关联性表达的摒弃,因此显得破碎与断裂。但正是这种破碎和断裂,却反倒能给读者以刺激,激活他们的记忆联想,让这些孤零零并列在一起的名词之间建起隐含的关联,形成一个富于兴感性的意境。因此,这两行诗反常的语言现象其实具有“浓缩象征”式的隐喻功能。可是今译者却看不到这种语言现象的重要性,有人就把这两句诗译成:“夜深灯残里醒了寒枕独梦,/伴随我的只有五更轻浪和寒风。”⑤ 显然,译者把这两行诗中的并列名词按分析—演绎的观物态度、逻辑推论的感物方式纳入语法序列了,以至于使原作藉对等原则获得的意境感兴变成了事物及其关系的陈述。这与原作是大相径庭的。当然,这不是译者的水平问题,而是他采用的语言体系和翻译原则问题。新诗的语言立足于分析演绎,合于语法规范,排斥对等原则,强调修饰成分,在词法、句法和连续性句法活动中遵守逻辑序列,重视相互关联,根据这类语言在新诗中的种种表现来看,它已发展成一个线性陈述式的语言体系。这两类语言体系和西方符号学者提出的隐喻的语言和分析的语言正相一致。雅各布森在《语言的两极与语言的失语症》中就曾以俄裔学者的身份指出:“在俄国抒情诗歌中”,以隐喻结构的语言处于优势,而“在英雄史诗中”,占优势的则是分析结构的语言。⑥ 既然抒情诗以采用隐喻的语言为主,而古诗的点面感发式语言体系与隐喻的语言非常一致,那么,从诗学的要求看,古诗今译者也应在白话即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尽可能让语言的转换工作保持古诗点面感发式语言,即隐喻结构语言的根本特色,以不连续、客观、直接诉于感觉并包含了绝对时空的特色。按照这一原则,我们将徐昌图《临江仙》中的“残灯孤枕梦,/轻浪五更风”译成下面句子也许更合适:“呵,残灯,孤枕,/怀人的幽梦;/轻浪,五更,/旷远的风……”比较而言,这样译与原诗语言那种“浓缩的象征性”更接近一些,因为它保持了不守语法规范、坚持对等原则构词组句的特质,也比较符合隐喻语言的基本要求,即不连续性、客观性和直接诉之于感觉性。但这样的语言却并不属于文言即古代汉语,而是白话即现代汉语。因为译文之基本词汇虽有直接沿袭,但对过分光秃的词已给予了必要的修饰,如用“怀人的”和“幽”去修饰“梦”,“旷远的”去修饰“风”,以强化“梦”与“风”这两个意象,使之具有适度定向的时空感受度,而古体诗用文言来完成的隐喻性语言结构则总是尽可能不用修饰成分。
古诗今译把原来的隐喻语言转化成分析语言派生出一个结果:把古诗所擅长的意境感兴化的抒情表现,改成了事理叙述性的说明。这是值得警惕的。如对李商隐的七律《锦瑟》,历来解说纷纭,以至于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也感叹“独恨无人作郑笺”。歧见主要出在颔联与颈联:“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两联四句诗,全凭四个意象群的兴发感动功能来进行抒情,而这四个意象群又是景象与典故很复杂的组合,它们之间的事理关系本来就搞不清楚,并且越想搞清楚就会越糊涂,所以后人大有欲作郑笺颇恨难之感。对它们的解释,我们很赞成台湾学者陈晓蔷先生的提示,他在《论“象外象景外景”兼谈晚唐二李诗》中提出应对它们作“综合的印象”⑦ 的把握。的确,这两联四行诗不能坐实,而应凭从意象群的兴发感动所得的“综合的印象”来理解,其中一联即是一个单元。按此思路我们认为:颔联给人的感受是,从梦的瞬间迷乱到心的永恒哀怨的综合印象;颈联给人的感受则是,从心的无边哀怨到梦的飘然消散的综合印象。颔联的综合印象是时间的,颈联则是空间的,二者属于不同的层次。不过这两个不同的层次的两联也可以合成一个更大的单元,给人以从时间上对虚无人生的执著到空间上对人生虚无的神往——这样更大的综合印象感受。要今译这首诗,必须对这两联具有一个比较近于诗学本质的认识思路——如同上述的综合印象才是,同时也必须明确这两联还具有一种堪称中国传统诗歌精华也很现代的艺术表现技巧:凭意象群兴发感动出来的意境来抒情。也就是说:所译对象是表现的、富于隐喻感发性的,而不是说明的、属于推论陈述性的。可是,不少《锦瑟》的今译,几乎都没考虑这些问题。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名译》为例,该诗颔联、颈联的译文是:“庄周不知自己是蝴蝶,蝴蝶是自己?/他在梦中,天亮也没有醒意,/在他的梦里,原没有醒的日子。/望帝死去化为杜鹃,/借杜鹃的鸣声,/诉说自己心的不死。/望帝是杜鹃,杜鹃是望帝!/他在永远追求,在永远悲啼。/海上的明月照见:/滴落眼泪化为珍珠的人鱼,/天空的太阳下射:/埋在蓝田生起轻烟的暖玉里。”四行诗放大成十二行,三倍。这里两个对子的今译语言容量很不匀称,颔联今译占了八行,全是事理的说明,并且添了不少内容。如果为使隐喻的表现发挥得更充分丰富一点,今译中适度添加意象倒是可以的,但添加说明性内容就是强化了分析和推论,乃抒情诗之大忌。所以推论“晓梦迷蝴蝶”的庄周“天亮也没有醒意”已是不当,但今译还进一步推论“在他的梦里,原没有醒的日子”,更不得要领了。在“望帝春心托杜鹃”的今译中,把“望帝死去化为杜鹃”的笺释硬塞进文本已是不当,而后面又推论说:“望帝是杜鹃,杜鹃是望帝”,更有画蛇添足之感。颈联四行,却一变主观分析、推论为客观转述,不过,不是用对等原则下的隐喻语言,而是采用分析语言紧紧扣住事理关系作线性陈述,原本须在今译中以客观表现的方式凸现意象和意象群的,在此也一笔勾销。所以此段译文显出了散文式的松松垮垮,外加颠三倒四和条理不清。不过,《锦瑟》今译本出现的类此问题并非“无人作郑笺”之故,恰恰相反,是好“作郑笺者”在今译中作得实在太多了,以致忽略了诗性语言的转化问题。因此,丢掉今译中好“作郑笺”的不良习惯,在语言转化中尽量保持传统的点面感发式隐喻语言体系的特色,才有可能译得好些。在此,我们试对《锦瑟》当中两联作这样的今译:
彩蝶恋花丛狂舞翩翩——
这庄生晓梦,瞬间的迷乱;
杜鹃啼残夜泣血点点——
这望帝春心,永恒的哀怨。
浩浩沧海呵,月白霜天,
鲛人的珠泪晶莹凄艳;
莽莽蓝田呵,日暖秦川,
良玉的浮烟飘忽灵幻……
我们无意于说这样的今译就成功了,但有几点语言转换上的问题倒值得一谈:(一)原诗两联四行,现在译成八行,扩大了一倍,但并没有稀释意象及意象群和冲淡意境,以至于化解了浓缩的象征,如“沧海月明珠有泪”的今译不仅没有把“沧海”、“月明”、“珠有泪”三个意象组合成的意象群稀释,且因采用了“月白霜天”、“鲛人的珠泪”这样的今译词语而使“月明”、“珠有泪”更具象化了,使这两个意象的质感(包括旷远的空间感和凄艳的情态感)更得以强化,从而深化了意境,浓缩的象征也发散出定向的感受力。(二)今译虽立足于白话,却又是白话与文言和合而成,如“杜鹃啼残夜泣血点点”,从词语到句式大有文言色彩,和下一行“这望帝春心,永恒的哀怨”杂凑,并不感到别扭;“浩浩沧海呵,月白霜天”则前是白话词语后是文言词语,杂凑在一起也还和谐。有学者指出:“翻译中所采取的一切手段”,“是服从于‘和谐’,即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和谐,以及译文本身的和谐。”⑧ 我们赞成这一见解。更何况像“凄艳”、“啼残夜”、“泣血点点”、“月白霜天”等,虽都有文言色彩,但由于它们在古体诗中常用,已有意象定位,能给接受者以特定的感兴,所以进入今译的文本中,也有利于在浓缩语言容量中凸现意象、强化意境。由此看来:新诗采用的白话诗性语言,在词语、句式上完全可以掺入古诗采用的文言诗性语言。(三)今译虽基本上采用具有语法规范的白话,而这样的白话在这个今译文本中也基本上是按语法序列展开词法、句法和连续性句法活动的,但也体现出一种超越,即为了使原诗的意象和意象群得到较好的转述,而使诗性白话所属分析的语言得以适度的改造,使之具有一定的隐喻功能,把对等原则引入诗性白话的词法、句法、连续性句法活动中,如“这庄生晓梦,瞬间的迷乱”,“良玉的浮烟飘忽灵幻”等都是如此。尤其是原诗颔联与颈联各是对句,是对等原则的体现;颔联、颈联之间也是对等原则的体现,今译也一律译成对句——为了体现对等原则。(四)古诗今译不能不采用线性陈述式分析的语言体系,但这很容易导致诗思分析化、对象陈述化。所以在《锦瑟》今译中尽力秉承对等原则来打破语法序列对词法、句法活动的干扰。但新诗的语言体系强调修饰成分,倒也可以对古诗点面感发式隐喻语言体系起一点矫正之功,使其光秃得像电报密码一样的词语句式所导致的过分扑朔迷离有所缓解,诗思也得以明朗些。因此,在这个试译中较多起用了修饰成分,如“沧海月明珠有泪”的“泪”前加上“鲛人的”、“珠(的)”两个定语,这就带出了南海鲛鱼对月泣泪、滴泪成珠的典故,强化了意境,并从而避免了上引今译中“珠也会流泪”的望文生义。
综上所述,古诗今译在语言的转化上给人这样的印象:新诗的语言建设,一面必须把古诗的点面感发式隐喻性语言体系作为一个根本传统来继承,并在继承中改造新诗现今通行的分析性语言体系,同时新诗线性陈述式分析性语言体系中某些策略(如强化修饰成分),也能给传统诗性语言体系提供新鲜的血液——使其功能机制更趋合理化,以适应和表现现代人的精神境界与生活情调。这就进一步涉及古诗今译中“文与白”的关系问题。
这里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古诗采用的点面感发式结构的隐喻语言和文言是不是一回事?新诗采用的线性陈述式结构的分析语言和白话是不是一回事?按照诗学原理来说都不是,因为诗性语言不能和日常交际语言划等号;但这和古诗、新诗的语言实况一结合,就显得比较复杂,所以不能简单化对待。文言是古代人的书面交际语言,古诗的语言是在文言的基础上形成的、以点面感发式结构为特征的诗性语言,但诗中纯粹用点面感发式结构的语言显然是不现实,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诗性语言也是出于交流的需要而确立的,它必须以日常交际的语言为基础。所以古诗语言从总体上说属于点面感发式结构、强调对等原则对词法、句法、连续性句法活动的控制,排斥语法序列的规范,但在过程性的叙述和说明性的传达中还得掺入日常的书面交际语言,即古诗也会出现接受文言语法序列规范的诗句,这些诗句有主谓宾的正常关系,也使用了关联性的虚词。这反映出古诗的语言只是尽可能(而不是完全)做到了从对等原则出发组织词法、句法和连续性句法的活动。白话是现代人的书面交际语言,新诗采用的那种以线性结构为标志的分析语言和现代人日常书面交际语言完全一致,因此从本质上说以白话为基础的这种新诗语言,只是白话而已,不能算是诗性语言。用现行的那套新诗语言来今译古诗,语言转化这一关首先就通不过,成绩不大也势在必然。因此,古诗今译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改造现行的新诗语言,使它的词法活动、句法活动、连续性句法活动最大可能地接受对等原则,尽可能少受语法序列的规范;当然,像古诗一样,面对过程性的叙述、说明性的传达也应允许适当保持白话的线性陈述式分析语言的存在,适度接受语法序列对词法、句法、连续性句法活动的规范。有鉴于此,在今译中还应该强调如下两项措施:
一是在古诗中有的诗句,其过程性叙述或说明性传达虽不显著,但在词法、句法、连续性句法活动中却受到语法序列的规范,这样,在今译中完全可以使它对等原则化。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后两行:“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有人这样译:“望着你坐的那只小船的帆影/一点一点地远了/直到碧空的尽处,/而我仍没有离去呢!/可是这时候/能看到的/却只有那浩荡的长江/——还在天边上奔流!”⑨ 今译的前三行对“孤帆远影碧空尽”的译法,完全改点面感发为线性陈述,改对等原则对句法和连续性句法活动的控制为语法序列的规范,这样做显然并不妥当。今译第四行凭空添入是废话。后面四行是对“唯见长江天际流”的今译。原句因“唯见”的存在,使它和上一行之间的连续性句法活动由原本完全可以用对等原则体现的点面感发结构,变成了受语法序列规范的线性陈述结构;也即使原本完全可以是隐喻的语言而有了分析意味。这可以说是大诗人李白的败笔。可是今译者却在败笔上进一步做文章,“可是”呀,“却只有”呀,“还在”呀,这些转折词使转折关联更为明确,从而使转化了的语言也更显出分析性。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按对等原则这样译:
孤帆,贴住江波的扁舟
远影,沉入碧空的哀愁
寂寞的人生路,迢迢遥遥
无言的长江水,天际奔流……
这样译,为的是推出几组语言意象的“蒙太奇”,使今译中语言的转化真正落实到隐喻上,这一效果大致是可以达到的。
二是古诗中有些带点说明性内容的诗句,其作用是对隐喻情境的点化,但语言表达却也按对等原则来展开句法活动,弄得需要意思明确处反而含混。为此,今译则可以按语法序列的规范来补足省略的词语,使之转化为线性陈述的分析语言。如李煜《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末两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前一句是三个词语按对等原则组合的隐喻语链,它们之间有内在的感兴联想关联,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它具有美的消逝这一浓重感伤情绪的兴发感动功能;后一句是两个词语按对等原则的组合,是按上一句的隐喻语境的推延作的点化。隐喻语境到一定时候是需要点化的,而点化必须明确,不可含混,所以这一句是以自己曾在“天上”现在已落“人间”的说法,对美好人生已逝作了点化,但“天上人间”的对等组合使欲点化之意含混了,于是歧义顿生,使今译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有人这样译:“流水漂走了落花,漂走了春天,/把一切都漂到了天上,只把我留在了人间!”这完全是从“流水”出发对两行诗中的意象“落花”、“春”、“天上”、“人间”作了逻辑串联,语言的转化完全陈述化、分析化了,这就很不正常。其实前一行必须维持点面感发结构、对等原则化的句法活动,后一行倒要改成线性陈述结构、语法序列化的句法活动。不妨这样译出:
我的存在:流水、落花,
消逝了阳春的残秋天。
呵,我曾在天上
却已落人间……
对“天上人间”作这样的今译足以表明:点面感发的隐喻语言被转化成线性陈述的分析语言有时也是必要的——为了点化前面一句的隐喻语境。
古诗今译在语言转化上的上述策略和途径启示我们:未来新诗的语言形态应是以白话为基础,以点面感发结构为本,让点面感发结构与线性陈述结构相结合、隐喻性语言与分析性语言相交融的诗性语言形态。
古诗今译在语言转化上之所以采取以上措施,究其根本原因是为了使诗歌语言充分凸现意象,藉语言意象的隐喻功能达到抒情的意境感兴化或氛围的象征化。而氛围象征才是抒情的最高追求。不过,这不只显示在语言也显示在体式形式上。
在中国诗学中,形式就是格律,就是节奏。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一文中就认为:“格律在这里是form(即形式)的意思”,“form和节奏是一种东西”,因此“格律就是节奏”。⑩ 有鉴于此,古诗今译中形式的转化,要按节奏—格律—形式这样的顺序来考虑。其中节奏问题是形式转化的核心内容,因为节奏是诗歌音乐性的具体体现。诗歌的音乐性是诗歌中的语音效果,而这就涉及声音象征的问题。凯塞尔·沃尔夫冈在《语言的艺术作品》一书中说:“发音本身以决定的方式呼唤出每一样客观的东西并且创造出客观的东西的灵魂的情调。客观的东西对于这种情调的关系比对于明显的存在和现实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在这个认识之下他提出了“声音的象征”的主张。(11) 这是很有见地的。因此在诗学中必须把节奏—格律—形式作为十分重要的方面予以考虑,这都是为了音乐性,为了可与氛围象征相对应的声音象征。因而在古诗今译中,节奏表现与格律形态——也即形式的转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工作。
在古诗今译中形式上比语言转化中存在的问题也许更大。这缘于今译者几乎都不考虑节奏、格律的相应转化。当然,认识古诗、新诗的形式特征以及把握古诗向新诗的形式转化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中国诗歌,无论古诗还是新诗,其鲜明的节奏显示总体上依赖的是不同型号的音组(即闻一多提出的“音尺”)的等时停逗(古诗还讲究平仄而新诗则不讲)。音组一般可分为性能不同的四种型号:单字音组,徐缓;二字音组,次徐缓;三字音组,次急逼;四字音组,急逼。其中四字音组除了在新诗的自由体中有较多使用外,一般新旧体格律诗中使用得并不多;此外,即使偶尔有使用三字以上音组的,在实际吟诵中也大多分裂为二。这些不同型号的音组在不同诗行长度上的有机组合,正是诗行节奏的显示。(12) 就近体诗来说,一般只使用单字、二字音组;有三个音组组合而成的诗行,即三顿体;也有四个音组组合而成的诗行,即四顿体。一般来说三顿体诗行是由两个二字音组和一个单字音组组合成的,如“床前/明月/光”;四顿体诗行由三个二字音组和一个单字音组组合成,如“风急/天高/猿啸/哀”;三顿体诗行的节奏急促,四顿体的舒徐。近体诗诗行煞尾的总是单字音组,使诗行节奏还具有吟唱的性能。近体诗就以这样的诗行节奏重复四次(绝句)或八次(律诗)而成富于吟唱味的均齐匀称型的诗篇节奏,因此而有了绝句、律诗这两大格律体。就词而言,一般使用单字、二字、三字音组,其诗行节奏借这几个音组的有机搭配得以体现,有一顿体、二顿体、三顿体、四顿体甚至五顿体的诗行根据循序渐进、两极对比等调节律有机搭配成诗节节奏或诗篇节奏,诗行煞尾的音组有单字的,也有二字的。单字尾的诗行既是吟唱味的,那么双字尾则是诉说味的,两者在词中也有机搭配,从而形成了旋律化的节奏:由多种节奏类型综合,以吟唱为主兼备诉说,并不均齐匀称而节奏起伏较大以至于往复回环,并且因此有了多种词牌的格律形态。至于新诗的形式,迄今也未定型。流行的自由体诗很难说有音乐性,更遑论声音的象征;新格律体诗也基本停留在新月诗派的“豆腐干”体,并未走上正规。不过,闻一多的《死水》和戴望舒的《雨巷》可能是个例外,它们继承了古诗传统节奏——格律的形式样板。《死水》是近体诗型的,属均齐匀称的节奏—格律形态;《雨巷》是词型的,属于复沓回环的节奏形态。
由此可见,在古诗今译中,节奏转化必须坚持以四类型号音组的有机组合作等时停逗来显示节奏的原则。据此,节奏的转化需要掌握一些操作要求:鉴于古诗中诗行节奏的显示以单字、二字音组的有机组合为本,今译为了适应白话比文言的容量要大的实际,音组也可以升格为以二字、三字音组为主的有机组合。不过,诗行以音组显出的相对长度(即三顿体和四顿体诗行)不能变。可变的是绝对长度,即原诗一行今译可扩大为两行,原诗一个三顿体或四顿体诗行可今译成两个三顿体或四顿体诗行,绝句四行可译成八行,律诗八行可译成十六行,《临江仙》十行可译成二十行,等等。这样做同样是为了使以白话代文言的古诗今译工作适应语言容量扩张的需要。鉴于古诗中的近体诗属吟唱调性,而新诗属诉说调性,故在形式转化中近体诗煞尾的单字音组今译时一律改成二字音组。词没有统一的节奏调性,在一行译成两行时,后一行煞尾音组型号今译可以不变,前一行煞尾可用与之相对立的型号音组。这就决定了古诗词今译中格律的转化:第一,五绝、七绝转化成三顿、四顿体,各八行,四行一节、译成两节;第二,五律、七律转化成三顿、四顿体,各十六行,四行一节,译成四节,至于它们的颈联、颔联也要相应地转化成双行对,不能改变对句形态;第三,各词牌的规定行数在转化中也应扩大一倍,原诗上下片若是对应匀称的,扩大一倍后对应的诗行也应一致,以保持其转化后上、下片的匀称格局。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今译者没有考虑这些形式转化的要求,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节奏转化不到位。
节奏转化不到位表现为丢弃了原诗的音乐美,以致削弱或根本消解了原诗的声音象征。
先看诗行节奏转化的不到位。温庭筠的五律《商山早行》前两行“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今有一译文是这样的:“黎明起来,车马的铃铎已丁当作响,/出门人踏上旅途,还一心想念故乡。”(13) 今译者把三顿体诗行转化成六顿体,结果原诗急促不宁的诗行节奏对早行人急促烦躁的心情所作的十分贴切的声音象征,被拖沓沉涩的今译诗行节奏消解了。我们试着这样译出:
微明里,车马,行装
铃铎声沉沉回荡
游子又一段苦旅
迢遥了,我的故乡
虽然原诗两行在今译中扩大成四行,但能保持原诗三顿体的节奏,并因今译中诗行扩大为两个三顿体诗行,急促不宁的诗行节奏复沓多了一次,强化了抒情主人公仓促烦躁的心绪,声音象征仍然凸显了出来。
再看诗节节奏转化的不到位。徐昌图《临江仙》下片说:“今夜画船何处?/潮平淮月朦胧。/酒醒人静奈愁浓!/残灯孤枕梦,/轻浪五更风。”诗行长度(即音组数)不同,诗行节奏感也不同,比较而言,愈短愈明快是“扬”的节奏感;愈长愈沉滞是“抑”的节奏感。这一节诗以三顿体、四顿体共五个诗行组合成诗节,诗节的节奏显示为“扬—扬—抑—扬—扬”,并靠这声音的象征传达出一股由旷放到沉郁再以旷放消解沉郁的情感流程。但有人这样译:“今天晚上船儿将要停泊在哪里呢?/淮水上风平浪静月色朦朦胧胧。/夜深人静酒醒人散时怎样排解这无穷的离恨?/孤灯下孤枕上又做起了思乡美梦。/五更时忽然一阵轻风拍打着浪潮把梦惊醒。”(14) 把三顿体、四顿体诗行混在一起毫无规律地转化为或六顿体或五顿体或八顿体,于是作为长短句组合的抑扬顿挫感悄然消失,声音象征也荡然无存。我们似乎可这样译:
夜重重,何处让画船
云帆落篷?
唯见淮水潮平
月色更朦胧。
酒醒,江天寂寂里,
愁情比酒浓。
呵,残灯,孤枕
怀人的幽梦;
轻浪,五更,
旷远的风。
应该说,长短句所特有的旋律化节奏感在此有了一定的显示,比较接近原诗声音象征的要求。
最后是诗篇节奏转化不到位的情况。诗篇节奏的音乐性更多情况下是以诗节匀称组合造成的复沓回环感体现出来的。在古诗今译中,对词的诗篇节奏进行转化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不少词的上下片往往就是节的匀称组合,复沓回环的诗篇节奏就更显著也更讲究。但词的今译对这一转化却最是薄弱。如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吴江冷。”这是两个匀称的诗节组合,据理说来,对应诗行都应该音组数(顿数)一致,音组型号也是对应一致。但几个今译文本不仅不能做到对长短句诗节的旋律化节奏进行转化,也不能达到词篇复沓回环的要求。根据上面提出的今译要求我们做这样的今译:
叶落尽,疏桐剩残柯
挂缺月一痕
梆声敲遍漏滴断
宵深梦初沉
可谁见神秘幽人
漫漫长夜独游行
呵,缥缈的孤鸿
黄州寂寞魂
心骤惊,展翅欲远行
又眷顾难腾
流徙生涯蹉跎年
向谁诉长恨
虽拣尽凝霜寒枝
茫茫远夜难栖身——
呵,飘零的丹枫
吴江冷艳魂
这种译法因诗节格式的重复而使诗篇节奏有了鲜明的回环性能,也许这样做才能让作者主体那一脉彷徨情绪的内在流程起到声音象征的效果。
总之,古诗今译在节奏转化方面的缺憾启示我们:新诗必须像古诗那样讲究形式的音乐性,重视声音的象征作用。
古诗今译格式转化不到位的情况,表现为丢弃原诗格律形态的精致严谨,成为蹩脚的自由体诗,甚至典型的分行散文。对古诗今译这一形式本不值得提倡,可是有人还在为今译者的“变形术”作经验推广。有学者在给《宋词三百首今译》作序中说:“在译诗的形式方面,(译者)则作了多种尝试,有的比较整齐,像格律体的新诗;有的更像民歌;也有类似自由诗的……这一切都说明他是化了心血的。”(15) 这种肯定显然是不够慎重的。写诗在形式上可以作多种追求,而古诗今译若在形式上去作“多种尝试”则断然不可,因为这是常识。可是不少今译者对这一常识不认账。人民日报出版社连续出版了几本徐放的古诗今译集,这位今译者是专写自由体诗的,于是他就全用自由体来今译绝句、律诗。李商隐的七绝《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竹,却话巴山夜雨时。”他竟然译成这样一首自由诗:“你问我归去的日期/我还未定归期,/今夜/一个人在这巴山驿馆的楼头看雨/雨呀/都涨满了秋天的水池。/怀念你,亲爱的。/可是/要到哪一天/我们才能够相依偎在西窗下/一起剪烛花儿?/那时候我当低低地对你说:/在巴山看雨的这夜晚/我是怎样的在相思着你!”这当然使这首传诵千百年的名篇变形了!诗歌译家许渊冲针对这种作风提出过诘问:“既然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割,那么原诗有韵有调的形式,译成无韵无调的自由诗体,不管诗句里的音响和节奏多么丰富,这种自由诗体能说是忠实于原文的吗?”(16) 其实,只要认真按上述形式转化的要求来译,还是可以较完好地保留原诗的形式美的。我们不妨这样译:
你若问归帆进港的日期
客舍的游子怎向你说呢
烛影摇曳里,这巴山夜雨
淋湿了怀念也涨满秋池
到何时能重叩故园门扉
剪烛在西窗下一起回忆
远方的人啊,那时我会说
这巴山夜雨伤感得美丽……
这是按照格律形态的要求,朝着尽可能保持原作形式本体特征的方向努力的。古诗今译界就是因为失去了固定的格律模式,所以古诗今译的形式转化相当混乱,以致许多今译文本在形式转化上给人失真之感。这里着重谈谈《唐诗名译》中诗人绿原对王翰《凉州词》的今译。这个今译文本很出名,《唐诗名译》在《编辑缘起》中对之首先作了推崇。的确,译者把握住了诗的“神”,但若以“信达雅”的标准来衡量,它既“达”又“雅”,却不太可“信”。为什么呢?因为原作是七绝,而绿原的今译使人无论如何联想不到它是七绝形式的转化,倒像是从词曲转化来的。所以,这仍然不值得大力提倡。当然,为古诗——特别是近体诗和词在今译的形式转化中相应地确立今译的格律模式颇有难度,但若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模式,而是失了原诗的形态,那就更趋向自己创造了。确立绝句的今译格律模式或许比较简单,难的是确立律诗与多种词牌的词的今译格律模式。
就律诗今译而言,形式转化中至关重要的是两副对子必须相应译出。可是今译者少有人这样做。如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焟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我们读到几个今译成自由体的文本,都根本不考虑对两个对子实行相应的转化,至于其他方面更不谈不上了。而律诗这种极严谨的格律形式里原本潜藏着多少浓缩的情感信息!轻易放弃格律形态的转化其害莫大!对此,我们尝试着这样译:
相见,又别了,时光短暂
聚难,散更难,能不心酸
三月的软风慵倦地吹来
惆怅的季节,惆怅花残
呵,万缕苦情已幻成春蚕
到死丝方尽,难续难断
呵,一颗痴心愿化为红烛
成灰泪始干,无悔无怨
深闺卷帘时,你盈泪低叹
画屏,晓镜,愁老了容颜
他乡漂泊中,我敛眉长吟
暮砧,月光,轻寒着诗篇
相信吧,你纵已身处蓬山
碧波的通途当并不遥远
我要让青鸟去殷勤探问
叼一粒相思子,向你呈献……
可见,此诗中两个对子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作为七律之格律形态极其重要的构成要素,这两个对子对全诗至少起着以下作用:第一,从结构关系看,近体诗都显示为起承转合的圆美组合关系,这首七律的一二句提出了全诗中这段爱得刻骨铭心的情感流程的引发性内容,这有着开启意义。三四句承接了首联,把抒情主人公满腔爱意的表达拉开了,围绕“春蚕”、“蜡烛”这两个中心意象形成两大意象群来隐喻爱情的至死不渝,而在这两大意象群之间,内外结合而生出复沓的情感效应,而这种复沓效应是依靠对句才体现出来的。五六句转,是至死不渝爱情别开生面的表现,即从直接抒发转为从生活场景中透现情意,这是经历激情后的深情表现,却通过两人不同时空中的生活实况交互映衬表现出来。这种时空意象的相互映衬,只有使用并列对照的对句才能产生更强烈的感应效果。所以,为加深至死不渝的爱恋表现而在转柁处使用对句,其功能意义不容忽略。七八句是“合”:从宿命的忧伤起,通过灵肉失衡的情绪大骚动而进入超凡脱俗的境界,完成了一个圆美结构。从这一结构关系可以看出,在律诗中承与转是结构核心,强化其功能十分重要,而这种强化通过颔联、颈联两组对句的形式方能收到超常效果,所以古诗今译必须重视对句的转化。第二,从旋律进程上看,律诗具有气势流转的特性,诗情表现的往复回环使它能以螺旋状的旋律进程诱导接受者进入使人沉静或兴奋的灵境,因此其旋律进程的构成颇值得研究。《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由于中间两联是激情与深情的表达,节奏感是升调,属于“扬”,第一组“起”的忧伤感与第四组“合”的超越感相应合的关系显出了降调,属于“抑”。因此,此诗是“抑扬扬抑”的旋律进程,显示着一场能使人沉静的心灵流转。不过,这“抑”——沉静人的节奏感由“扬”——持续鼓舞人的节奏感在对比中反衬出来、强化起来。使人沉静的心灵流转(其他律诗的旋律化进程也可显示为“扬抑抑扬”——能兴奋人的心灵流转)要得到充分体现,一个极重要的条件是当中两联是对句的设置。对句以其往复回旋的性能把兴奋人(在其他律诗中可能是沉静人)的节奏感应强化了,从而也以强有力的反衬张力,推进此诗沉静人的那种心灵旋律化流转进程。由此看来,颔联与颈联的对句在今译中的转化切不可随意丢弃。根据这些思考译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中,两联的今译也以扩大的对句形式出现,使这首七律的今译文本比较近似原诗的形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作为律诗今译格律模式的一个参考。
应该为古诗尤其是词中的特定格律在今译中的转化确立相应的模式。由于词有多种词牌,每一词牌就是一种特定的格律形态,所以有必要为一个个词牌确立相应的今译格律模式。然而,在对词的今译中要么被译成自由体诗,要么被译成节的匀称、句的均齐的现代格律体诗,鲜有考虑也将词的抑扬顿挫的旋律化节奏以相应的格律形态显示出来。我们认为非作节奏表现的移植不可。如皇甫松的《梦江南》:“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这首精美而富于梦幻情调的小令,我们可今译如下:
兰蕊儿似的灯花
快凋尽在残宵
画屏上,光影无力地摇淡
艳红的美人蕉
呵,我乃有闲情五月的江南梦
青梅熟了
船泊烟水迷濛里
笛迢迢,雨萧萧
人语驿馆外
在小桥……
这首先根据上文提及的一些形式转化原则,此外,词是长短句的组合,今译就还它一个长短句,有点像自由体诗,但实际上又不是。长短诗行的搭配是有机的,一要根据诗行节奏“抑扬”或“扬抑”相间的原则来组合,长诗行相对而言是“抑”,短诗行则是“扬”。因此,“兰蕊儿似的灯花”是三顿体,接下去要用“快凋尽在残宵”这个二顿体承接。二要根据原诗对应诗行确定今译长短诗行的搭配,如“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前一行是四顿体,后一行是三顿体,今译前一行是“船泊烟水迷濛里/笛迢迢,雨萧萧”——一个三顿体跟一个二顿体;今译后一行是“人语驿馆外/在小桥”,一个二顿体跟一个一顿体。至于一行译成两行,这两行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与我们译近体诗明显不同。译近体诗时一行译成的两行,是顿数相同长度一致的,因为它是均齐节奏;词的节奏是旋律化的,有波伏,不均齐,故一行译成两行时前一行长些,即顿数多出一两个;后一行短些,顿数至少要少一个。煞尾的音组,原诗行是单字尾,译成两行后的后一行一般说必须也是单字尾;前一行一般就该是二字尾。译诗须按原诗的韵来押,转韵也要按照原诗,韵一般押在由原诗一行译成两行的后一行煞尾处。如“兰蕊儿似的灯花/快凋尽在残宵”的“宵”同“画屏上,光影无力地摇淡/艳红的美人蕉”的“蕉”押韵。在对《梦江南·兰烬落》作今译中,我们根据这样的原则对原诗的格律进行转化,其实也是试着为《梦江南》确立一个白话格律模式。今后碰到用这个词牌填的词,今译时多少也可作些参考!
讲究格律还是非常必要的。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的古体诗,大抵都是讲究格律、重视音乐美的经典诗歌文本。古诗今译者若不注意于此,完全用自由体随意地译,无疑会对这些文本造成较大的伤害。当然,这种损害的存在倒也表明,用自由体写诗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
通过以上论析,我们可以做一归结:古诗今译中语言和形式的转化工作十分重要,并且也并非绝难做到。当然,如果探讨语言和形式转化只是为了使古诗今译更加“信达雅”,那似乎是太低的要求。更为重要的还是,通过古诗今译,更多地保存古代诗词的精神与意境,使古今诗学理念实现自然有效的对接,同时返观中国现代以来的新诗,思考新诗如何通过继承和发展传统,推动自身的诗体建设问题。
注释:
①许渊冲:《文学与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②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③参见骆寒超、陈玉兰《论传统汉诗的语言体系及其表现策略》,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8期转载。
④关于雅各布森提出的对等原则,可参见高友工、梅祖麟的《唐诗的魅力》。该书接着还作了如下发挥:“在普通语言中,相邻的语言成分是由语法结构连接的;而在诗性语言中,语法限制就不再适用了,不相邻的语言成分可以通过对等原则组合起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0—121、122页)。
⑤赵仁珪、朱玉麒、李建英、杜媛萍:《唐五代词三百首译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60页。
⑥参见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3—194页。
⑦《李商隐诗研究论文集》,台北天工书局,1984年,第471页。
⑧郑海凌:《文学翻译学》,文心出版社,2000年,第155页。
⑨徐放:《唐诗今译》,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第58页。
⑩《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1、83页。
(11)陈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27页。
(12)参见骆寒超《新诗创作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406页。
(13)《唐诗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
(14)郭彦全:《历代词今译》,中国书店,2000年,第48页。
(15)《宋词三百首今译》,霍松林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许渊冲:《文学与翻译》,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