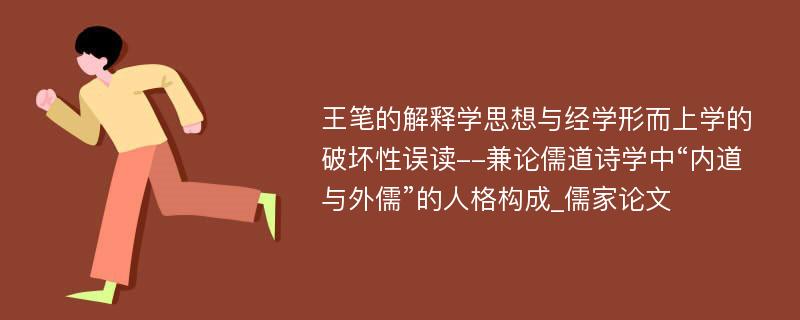
王弼的阐释学思想与经学玄学化的破坏性误读——兼论儒道诗学的“内道外儒”人格构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弼论文,儒道论文,经学论文,诗学论文,玄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古典阐释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向所引起的经学的玄学化是以王弼为肇事的历史界标的。儒家士人主体“立言”的经典文本在王弼的破坏性读解下开始走向意义的解构。王弼以玄妙的清谈即把先秦两汉多少巨儒封闭在经典文本中的儒家文化世界和儒家诗学世界颠覆得支离破碎,从而引起了一个民族文化形态和诗学理论思维的转型。
一
亚里士多德曾把语言和文字界分为人类的两大表意符号系统:“口语是心灵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1〕而索绪尔在关于语言的思考中不仅在形而上学的思路上认同了亚里士多德,并且固执于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进一步指出了书写的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仅仅是依赖于口语:“语言(Saying)和文字(Writing)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前者。”〔2〕的确, 书写的文字其存在的功能和理由是为了彰现言说的语言——口语,但文字的稳定性与口语的鲜活性往往使这两者在历史的流动中产生意义关系的脱节,从而导致两者在表意方面的悖离。而这种悖离的一方面就是书写的文字对已逝去的铭记性使人们总是倍感文字有一种凌架于口语之上的威望和尊严;因此,人们在阅读文本时总是过多地投注尊重于书写的语言——文本,而冷漠在历史中发展着的、生生不息的口语言说。也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层面意义上反思儒家诗学,我们发现,儒家士人主体“立言”的经典文本作为书写的语言形式总是与在历史中发展着的、言说着的语言脱节,在文化语境中借助对逝去历史的铭记对从而呈现出对当下文化阐释的独断性和暴虐性。而儒家诗学范畴又借助于学术宗教的神圣地位,在对文学现象的阐释中所表现出的独断性和暴虐性就更加显著了。
在先秦时期,《六经》作为儒家士人主体“立言”的经典文本,其中蕴含着一系例儒家诗学范畴。在这些范畴的两个层面中,即能指与所指之间有着稳定的语言网络关系;正是这个稳定的语言网络关系使儒家诗学范畴中能指与所指有着恒定不变的意义。这是儒家诗学范畴在先秦时期的理论特色。随着历史从先秦向两汉的延伸,栖居在《六经》经典文本中的儒家诗学范畴以其自身的稳定性逐渐脱离了在历史中发展着的、生生不息的文学语境,这些范畴负载着它们自身的原初意义成为一个个自在自为的所指,即独立于汉代文学语境而直接呈现于阐释主体思想的所指。当文学的发展超越了先秦走向汉代,面对着汉代的文学现象,汉儒出于无可逃避地对经学的崇奉,其作为文学批评主体和文学阐释主体对学术宗教信仰的无限皈依,这决定他们只有、也必须秉承和遵循着这些范畴的原初意义去阐释和读解汉代的文学现象。实际上,《六经》经典文本的诗学范畴成为了汉儒观审文学现象的语言透镜,因此体现在两汉时期的文学景观下,栖居在《六经》经典文本中的一系例诗学范畴作为主体一个个观审文学现象的语言透镜,在对文学现象的阐释和读解中其必然表现为意识形态上的独断性和暴虐性。因为文学语境随着历史的推移发展了,而《六经》经典文本的诗学范畴作为一个个能指,其仍然把它们的能指固执在原初的所指意义关系上。德里达在他的解结构主义诗学体系中,把这样的范畴在理论上称之为“超验的所指”。这就是儒家诗学在学术宗教——经学的层面上所表现出的镜式语言观。然而经学鼎盛于两汉及儒家诗学攫取学术宗教地位后对文化中心的占居,这一切均昭示着鼎盛的辉煌即将逝去,因为“鼎盛”这一辞语在历史时空中的哲学意义充其量就是走向没落的辉煌。“魏晋”——一个在华夏中世纪以玄学颠覆经学的新生代的崛起,它曾以一个时代于“清谈”中的“旷达放荡”,在对经学规范的道理理性拒斥中迷倒了后世的多少学者。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曾描述了这一新生代崛起的文化景观的必然性,他认为:“每逢儒家思想此等流弊暴著的时候,中国人常有另一派思想对此加以挽救,则为庄老道家。”〔3〕在魏晋时期, 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正是在冲突与互补中塑造了道家士人主体占据文化中心的“内道外儒”的人格类型。
在中国古典阐释学的发展历程上,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向所引起的经学的玄学化是以王弼为肇事的历史界标的。儒家士人主体“立言”的经典文本在王弼的破坏性读解下开始走向意义的解构。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储存传统的水库。实际上,主体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本质上是以自我的价值尺度检阅历史,一介孤独的个体生命仅在阐释中可以轻而易举地读破一个古旧的世界,再度建构起一个崭新的世界,历史在千百年的积淀中建构起的文化形态和思维规范在生命主体的音释面前彰显得如此脆弱。王弼——一介弱冠少年仅以玄妙的清谈即把先秦两汉多少巨儒封闭在经典文本中的儒家文化世界和儒家诗学世界颠覆得支离破碎,从而引起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和诗学理论思维的转型。两汉经学就这样在一介短命天才的清谈中悲剧性地终结了。
在这里,如果用西方阐释学理论的一个概念来说明王弼对儒家经典文本的破坏性读解,那么这种破坏性读解就是误读(Misreading)。在阐释学理论的体系中,“误读”又界分为“非自觉的误读”和“自觉的误读”两种操作方法。王弼从道家宇宙本体论崇尚的“立意”对儒家经典文本的破坏性读解——误读是就驻足在“自觉”的层面上完成的。儒道两家诗学之间的悖立从先秦历经两汉走向魏晋时,“立言”与“立意”的冲突在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的争执上已经形成了明确的逻辑线索,即“立言”与“立意”以“立象”为传导中介构成了魏晋时期诗学的“言意之辨”。从王弼的理论人格构成观审,魏晋时期,道家诗学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从而把儒家诗学从文化中心逼向文化边缘,因此当王弼接受了这两脉外力学术文化内化为自我理论人格的构成后,占据文化中心的道家诗学必然形成王弼理论人格的“内道”层面,而退向文化边缘的儒家诗学必然形成其理论人格的“外儒”层面,因此形成了王弼“内道外儒”的理论人格类型。所以,道家诗学崇尚“立意”的宇宙本体论成为支撑王弼理论人格的主体精神。
二
关于“言”与“意”的语言结构关系网络,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曾经有过精彩的理论思辨。在“立言”与“立意”的双项选择中,王弼在体认世界的态度上不同于儒家士人主体,儒家士人主体崇尚在“经”的本体格位上建构经学本体论,把“经”这样一个本体范畴和《六经》的文本形式作为观审此在世界的语言透镜;而王弼在其阐释学思想的脉博跳动上合拍于道家士人主体,崇尚道家士人主体在玄览的体悟中完成对宇宙本体——“道”的静观,从“忘言”进而走向“忘象”,把负载意义的能指符号——“言”与“象”作为形而下的物累贬抑为“蹄”与“荃”,把漂浮在语言物累之上的“意”作为他直观这个世界的透镜,从而达到对儒家诗学栖居的经典文本——《六经》进行彻底的解构。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把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在结构上划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层面,在能指和所指的网络关系之间沉思语言的本质。倘若我们把东西方诗学关于语言结构的划分作一次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诗学不同于西方诗学。中国古代诗学把作为符号的语言在结构上界分为四个层面:即“书”、“言”、“象”、“意”,从这四个层面划分能指与所指的语言网络关系。关于语言结构的四个层面的界分,早在《周易·系辞上》就有着潜在的理论表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4〕因此“圣人立象以尽意”。〔5〕。在这里,让我们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解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来明晰《周易·系辞上》的表述,使这样一个潜在的理论走向自觉。“书”是指涉书写的文本、“言”是指涉口语的言说、“象”是指涉卜卦的象数,这三者在表达意义的功能上均为能指,而“意”是所指。“书”、“言”、“象”作为能指存在的理论价值功能就在于表“意”。当我们的思考走到这里时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诗学关于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网络关系的沉思不同与西方诗学,在能指如何表意的语言网络关系中,中国古代诗学要比西方诗学细微得多。中国古代诗学关于思考能指在尽可能地逼近所指且澄明地呈现主体的思维中,又在“书写”“言说”与“意”的表达网络关系之间增设了一级能指——“象”,认为“象”比“书写”与“言说”这两级能指更能准确且澄明地呈现意义,即接近所指。因此在中国古代诗学关于语言结构的划分中,“象”在表“意”功能上是第一级能指。由于中国古代士人主体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因此主张“立象以尽意”,进而认为“象”作为一种能指较之于“书写”与“言说”更能接近主体思维的表达和呈现,所以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划分,“象”是第一级能指,“言”退居为第二级能指,“书”退居为第三级能指。主体在阐释中对意义的追寻以“书”为理解的起点,再过渡到“言”,再过渡到“象”,最终从“象”达向所指——“意”,兑现一个完整的阐释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儒家诗学崇尚在经学的学术宗教地位上“立言”,因此在能指与所指的表意网络关系中,尽管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角度看“书”是第三级能指,而儒家诗学对第三级能指——书写的经典文本的看重和崇拜超过了第一级能指和第二级能指。因为儒家经典文本的铭记性对先圣典章制度的负载及经学学术宗教的神圣地位使“立言”必然成为儒家诗学体系认同的第一级能指。
在这里我们需要再度指出的是,本文在讨论儒家诗学崇尚的“立言”与道家诗学崇尚的“立意”于冲突中走向互补时,由于儒家诗学崇尚的“立言”是在学术宗教的经典文本上完成的,因此把儒家诗学崇尚的“立言”之“言”作为一个能指来理解,是指涉书写的经典文本形式。中国文字的构成形态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中国古代诗学在使用“言”作为能指时,在书写的形态上是无法通过视觉的直观来区分其是作为第二级能指使用,还是作为第三级能指使用,因此“言”作为一个范畴在语境中的动作往往既涵盖了“书写”之“言”,又涵盖了“言说”之“言”,因此“言”这个范畴在特定的语境下具有承负着第二级能指和第三级能指的双重意义。我们明白了“言”这个能指的双重意义后,让我们的思考再回到那个以破坏性误读而导致汉魏文化转型的短命天才——王弼。
王弼在对儒家经典文本的阐释中力主“援道入儒”。出于对所指——“意”的阐释权的绝对占有,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勾划了能指与所指两者之间的语言关系网络,并在这个语言关系网络中亮出了他的阐释学思想。首先,王弼认为“言”作为一个能指其存在的价值目的在于澄明地显现“象”:“言者,明象者也”,〔6〕而“象”作为一个能指其存在的价值目的又在于澄明地显现“意”:“夫象者,出意者也。”〔7〕但是,在能指与所指两者之间的生成依赖关系上, 王弼不同于海德格尔关于作为所指的存在依赖于先在的语言能指而得以澄明表达的理论。关于这一点,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申明得非常清楚:“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非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非其言也,”〔8〕认为能指的生成取决与所指, 这也是能指存在的唯一理由,而能指存在的终极目的又不在于呈现自身形式的价值,且在于呈现栖居于其中的所指——“意”。王弼把所指——“意”认同为能指——“言”与“象”得以有存在价值的根本动因,而不是在阐释的理论上主张预先设定一个先验的能指来寻找和规范所指——“意”生成。这一理论最终也诱导着王弼以后的玄学家在对儒家经典文本的阐释过程中无限的逼向“意”,而走向对儒家经典文本的超越。其次,在能指与所指关系网络的距离中,王弼划分了“言”、“象”、“意”这三者之间的空间距离,认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9〕王弼把“象”设定为“言”与“意”之间的一个更为有效达“意”的传导中介,在阐释的方法论上否定了儒家士人主体从经典文本直接追寻意义的阐释有效性,认为“言”对“意”的澄明表达必须要借助于“象”这个中介。如果说经典文本在达意的功能上必须要借助“象”作为传导中介,在阐释学理论上,这实际上构成了对儒家经典文本达“意”功能的怀疑和拒斥。再次,王弼又回答了阐释主体是怎样从能指走向所指,最终达到对“意”的阐释权进行绝对占有的路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设置了这样一个阐释的递进过程:“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10〕认为阐释主体在对“意”的追寻过程中,先从“言”作为阐释的起点从而达到“象”,再以“象”作为阐释的中介从而达向“意”,最终把握对所指——“意”的绝对阐释权的占有。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王弼在他的阐释学理论体系中虽然要把握对所指——“意”的阐释权的绝对拥有,并且也认为能指存在的价值取决于所指——“意”;但他并没有在没有达到“意”的先决地条件下彻底地否定能指。因此王弼认为,尽管能指的存在价值取决于所指,一旦“意”寻找到它赖以澄明显现的能指时,能指便成为所指栖居的家园。因此王弼又把“言”和“象”认同为“意”的居所。关于这一点,钱钟书在《管锥编》论述《周易正义》中已有明见:“是故《易》之象,义理寄宿之蘧庐也。”〔11〕也就是说,在对“意”的阐释权的绝对拥有过程中,王弼并没有绝对地无视能指存在的价值功能,而在阐释的过程中彻底地舍弃能指去凭空地获取意义,因为阐释必须是由主体存在的前理解开始,而不是从主体自身开始。这三点构成了王弼阐释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也是王弼对儒家经典文本的进行破坏性误读的一个基本策略。也正是基于这三点,王弼才可能完成对能指的超越而完成对“意”的阐释权的绝对获得。
三
对能指的超越是王弼“援道入儒”对儒家经典文本进行破坏性读解的一个最彻底的环节。
在语言学理论上,能指与所指有着不可割舍的互为依存的关系。但是主体在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中,往往在心理上更容易折服于能指,因为尤其是作为文本形式的能指往往给人一种铭记历史和文化的威望与尊严,使主体认为文本就是历史,文本就是文化,似乎主体只要拥有了文本即便不进入阐释就可以获取他所企盼的一切。因此两汉经学家往往偏执地把自己的信仰与崇拜胶滞在经典文本上,把《六经》文本尊奉为不可妄加训解只可遵命执行的“圣经”,因此经典文本的语言界限就是儒家士人主体存在的那个世界的界限,这就是两汉经学的文本崇拜意识。一切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所言:“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孔教已定于一尊矣。……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12〕而王弼在他的阐释学理论体系中则把能指规范为主体运思达向所指的跳板,这实际上是对经典文本的蔑视。从现代阐释学理论看,主体对一个已经存在的意义的追寻必须以能指为理解的中介,阐释不可能从主体自身开始在凭空的虚构和杜撰中达向所指;在主体的阐释视域中必须有一个理解得以启动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历史或文学存在的本体形式——文本。主体阐释的运思必须从这个此在的中介迈步,才可能达向对彼在意义阐释权的拥有。王弼正是把这个中介视为主体得以启动阐释的关键点,并要求主体以能指——文本为中介跳板,一旦达向对“意”的阐释权的拥有后,则应“忘象”,进而“忘言”:“然则,忘象者,乃得其意者也;忘言者,乃得其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13〕中国古代诗学在语言结构的网络关系中设置了一个从三级能指达向所指的递进阐释过程,第一级能指——“象”是达向“意”的最后一个中介,恰恰王弼把“象”这一个最后中介作为达意后的物累最先抛弃,完成了对能指与所指之间网络关系的彻底阻断。在能指达向所指的递进程序上,王弼对第三级能指——经典文本的抛弃是釜底抽薪式的,第一级能指——“象”已经首先被主体达意后抛弃,那么第二级能指和第三级能指在阐释的逻辑进程中也就依次失去了为了达意而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出现了连锁性危机。因此王弼把能指统统贬抑为物累:“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14〕在上述我们曾指出,“言”这个范畴在特定的语境下具有承负着第二级能指“言说”和第三级能指“书写”的双重意义,王弼把“象”与“言”贬抑为物累在理论上是对三级能指——“书”、“言”、“象”的全部拒斥和全部否定。王弼把能指认同为中介而作为达意的跳板,认为主体从中介跳板达向所指后,能指在性质上则蜕变为束缚阐释的物累形式,要求主体抛弃能指,这的确为意义的阐释拓宽了理解的空间。钱种书在《管锥编》讨论《周易正义》从另一个侧面也申明了这一点:“王弼恐读《易》者之拘象而死在言下也。”〔15〕的确,从阐释的角度看,倘若阐释主体苟于“拘象”其必然“死在言下也”,就如同两汉的经学家在对《六经》文本的阐释中把自己的思想封闭在文本的语言牢笼中窒息而死一样,虽然他们终身“皓首穷经”却不曾有过瞬间的思考,最终在知识的富有与思想的贫因中了却一生。但是,把“言”与“象”认同为束缚阐释的物累形式而彻底抛弃,这无疑是为了获取对“意”的绝对阐释权而在阐释理论上走向的偏激。
在历史的进程中往往就是这样,思者以思想在扼制一个朝代积蓄已久的文化惯性,使既成的文化向另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转型时,往往只有在偏激中力挽狂澜。
四
汤用彤曾在《理学·佛学·玄学》一书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之重要问题实以‘得意忘言’为基础。言象为意之代表,而非意之本身,故不能以言象为意;然言象虽非意之本身,而尽意莫若言象,故言象不可废;而‘得意’(宇宙之本体,造化之自然)须忘言忘象,以求‘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故忘象而得意也。”〔16〕“言”在特定的语境下承负着第二级能指和第三级能指的双重意义,“言”从庄子到王弼,在不断的阐释思考中终于沦落为“言荃”。对经典文本的玄学化阐释是作为一种哲学思考完成的,当这一哲学思考消融在诗学空间于历史的延伸中浸灌着诗人的创作时,则要求诗人的诗思在空灵的意境营造中自由地驰骋,而不在文学本体的存在形式——文本的言辞上留下任何雕凿的物理痕迹。那就是后人严羽在《沦浪诗话》总纳前哲的诗思为诗的存在悟定的一方上乘的审美品位:“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17〕不啻诗的批评者如此,诗人在诗的创作中也诗意地接受着这一浸灌,张说在《闻雨》一诗中言:“声真不世识,心醉岂言诠(荃)。”〔18〕理解了哲学与诗学之间不可分延的血肉关系,也就看穿了钱钟书《管锥编》讨论《周易正义》时从哲学往诗学延伸的思路:“……哲人得意而则欲忘之言、得言而欲忘之象,适供词人之寻章摘句、含英咀华,正若此矣。……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19〕《三国志·虞翻传》裴松之注引《虞翻别传》言:“经之大者,莫过于《易》。”〔20〕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又言:“《易》为群经之首。”〔21〕而王弼正是援老庄之言误读《周易》,使《周易》偏离儒家之首经蜕变为魏晋“三玄”之一。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两者之间在思维和形态上的悖立不同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立,儒道诗学之间的悖立毕竟是在华夏文化景观内部展开的,这种冲突本身就是在华夏文化的共有语境下完成的,因此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在冲突中本身就潜在着走向互补的文化可能性和文化必然性。《周易》在思维的形态上本来也最接近于老庄,王弼在儒道诗学的冲突与互补中援道入儒,最先选择《周易》为破坏性阐释的突破点,的确为历史性英明之举。也就是这样一次个人的选择导致了华夏文化在汉末与魏晋之际的转型。
从人格心理学的视角透视,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的冲突由外在的“言意之辨”而导入阐释主体兑现为一种心理转换,使儒道的冲突在走向互补中成为王弼个人心态中的一种生存把握,王弼也正是在生存的握中使自己“内道外儒”的生存原则在对文本的阐释中展现出来,相对于“内儒外道”的人格类型,这最终也是一种全然的占有。因为“援道入儒”在阐释中使经学走向玄学化,这毕竟成为魏晋时期玄学家的一种主要生存的方式。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的冲突在经典文本的玄学化读解中汇合了。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曾描述了魏晋名士在享尽风流中禀有一种“蔑礼法崇放达”傲慢:“正始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沿老庄,蔑礼法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之倡也。”〔22〕实际上,魏晋名士大都在刻意炫耀才华和尽倾思想的自我张扬中耗尽了生命的能量,他们往往在短促的生命历程中显得格外辉煌。王弼对《论语》文本阐释的结果就是孔子的老子化与经学的玄学化,把儒家诗学“立言垂教”的生存信仰在玄学的读解中转型为“修本废言”,认定大自然运行的自在规律并不以儒家经典文本的道德律令而改变它的走向:“子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既求道中,不可胜御。是以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以淳而观,则天地之心见于不言,寒暑代序,则不言之令行乎四时,天岂谆谆者哉。 ”〔23〕王弼以儒家经典文本作为阐释启动的中介跳板, 把破坏性误读化为清谈的玄风抹淡了儒家经典文本的学术宗教色彩及凌架于一切之上的威望和尊严,以道家诗学的“立意”为透镜凝眸瞻视那个曾被儒家经学覆盖的文本世界,可以说王弼的人格心理构成是“内道外儒”式的。这种凝眸瞻视是在儒道互补中以自然律令反抗道德律令阐释,也正是在这种互补的阐释中,儒家诗学的名教才可能融解在道家诗学的自然中。
从语言学的理论上看,王弼的“忘言”与“忘象”最终是为割断能指与所指的网络关系,使能指在主体对其的超越下失去对意义的负载成为一个空洞的表达。严格地讲,能指与所指在语言结构的网络关系中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合体,两者对任何一方的失去将都以丧失自己存在的前题为代价。主体不可能超越能指凭空地获取能负载的意义,而一个失去意义的能指则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空洞表达。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曾言:“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24〕当王弼舍弃了经典文本时,最终也舍弃了儒家经典文本负载的历史与文化,舍弃了儒家经典文本以历史的铭记性对后来文化的规范性、独断性和暴虐性。〔25〕
1996年元月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注释:
〔1〕《工具论》亚里士多德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55页。
〔2〕《普通语言学都程》索绪尔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第47页。
〔3〕《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4页。
〔4〕〔5〕《周易正义》见于《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影印世界书局阮元校刻本,第82页。
〔6〕—〔10〕〔13〕〔14〕《周易略例》见于《王弼集校释》王弼著、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版,第591页。
〔11〕〔15〕〔19〕《管锥编》钱钟书著,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一册,第15、12、15页。
〔12〕《经学历史》皮锡瑞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3页。
〔16〕《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0页。
〔17〕《沧浪诗话校释》严羽著、郭绍虞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18〕《闻雨》张说撰,见于《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20〕《三国志》见于《二十五史》同上,第1226页。
〔21〕《经学通论》皮锡瑞著,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页。
〔22〕〔24〕《日知录集释》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家刻本,上册,第1012、89页。
〔23〕皇侃《论语义疏》转引王弼注,见于《王弼集校释》同上,下册,第633页。
〔25〕Project Supported by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Foundation.
标签:儒家论文; 能指与所指论文; 玄学论文; 王弼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魏晋风流论文; 儒道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周易正义论文; 读书论文; 管锥编论文; 魏晋论文; 易经论文; 国学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学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