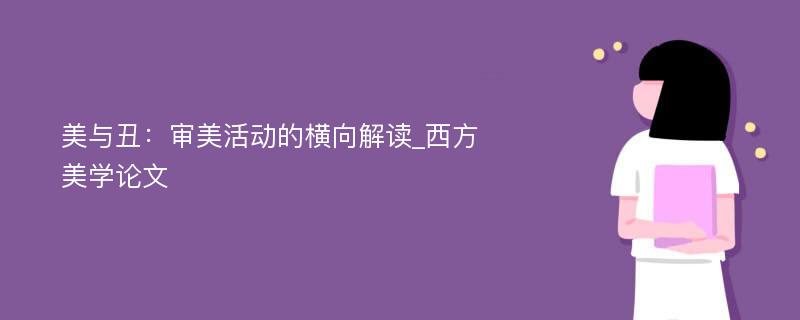
美丑之间——关于审美活动的横向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丑论文,横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审美活动从逻辑上可以展开为三个层面,这就是:纵向的展开,即美、美感、审美关系;剖向的展开,即自然审美、社会审美、艺术审美;横向的展开,即丑—荒诞—悲剧—崇高—喜剧—优美。
本文拟对审美活动的横向展开加以讨论。在这个层面,审美活动作为人的自由本性的理想实现,因为不同的实现方式而展现为不同的审美活动的类型。由此出发,首先可以把审美活动划分为肯定性的审美活动和否定性的审美活动两类。肯定性的审美活动是指在审美活动中通过对自由的生命活动的肯定上升到最高的生命存在,否定性的审美活动是指在审美活动中通过对不自由的生命活动的否定而间接进入自由的生命活动,最终上升到最高的生命存在。其具体特征可以表述为:肯定性的审美活动是将生活理想化,否定性的审美活动是将理想生活化。进而言之,肯定性与否定性审美活动之间所导致的量的变化,进一步又形成了丑、荒诞、悲剧、崇高、喜剧、美(优美)等不同类型的审美活动。在这里,丑是美(优美,下同)的全面消解,荒诞是丑对美的调侃,悲剧是丑对美的践踏,崇高是美对丑的征服,喜剧是美对丑的嘲笑,美是丑的全面消解(如图):
丑……美……丑—荒诞—崇高—悲剧—喜剧—美……丑……美
下面,我对之逐一加以讨论。
二
否定性的审美活动包括丑、荒诞、悲剧。
就美的类型而言,丑是反和谐、反形式、不协调、不调和;就美感的类型而言,丑是消极的反应,“一种混合的感情,一种带有苦味的愉快,一种肯定染上了痛苦色彩的快乐”[①],就审美活动的类型而言,丑是美的全面消解。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假、恶、落后,然而,它们却并非是丑。只有当我们从对于其中所蕴含的生活的有限的解读转而对于它们所蕴含的生命的有限的解读时,才深刻地触及到了丑。因此,我们所谓的丑,也就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假、恶、落后。在我看来,现实生活中的假、恶、落后并不就是丑,只有它们背后的那种对生命的虚无主义的选择才是丑(恶以有害他人为特征,丑则以无害他人为特征)。换言之,真正的丑只能是指对于生命的有限的固执,它是生命的意义的丧失,生命的可能性的丧失,或者说,是美(狭义的)的全面消解。而对于丑的解读则正是对这种对于生命的有限的固执的否定,并通过对这种对于生命的有限的固执的否定而间接地进入自由的生命活动,最终上升到最高的生命存在。
值得强调的是,丑不仅仅是对生活中的假、恶、落后的审美解读,而且是对生活中的真、善、进步的审美解读。当真、善、进步一旦僵滞、不前,就意味着同样固执于生命的有限,于是,审美活动同样把它解读为丑。这一点,在当代的审美活动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美学家发现:当代社会是一个丑横空出世的时代。原因何在?就在于当生活中的真、善、进步被解读为美,以至于人们干脆纵浪其中,不喜不惧的时候,甚至没有意识至真、善、进步的僵滞、不前之时,审美活动就进一步把它们解读为丑,从而使人们从中被剥离而出,孤单地立身虚无之中,熟悉的世界消失了,个体被从虚幻的共同存在状态中唤醒,而共同存在状态一旦被破坏,真、善、进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美也就失去了市场——它们不再有意义了。萨特就曾经用“恶心”来描述对于这种无意义感的领悟。确实,美(优美)是人们要执著追求的东西,但每一种美同时又是对于更多的可能性的限制,恰似追求完满是要靠牺牲更多的不完满换取的一样。它启迪了一种境界,却抽去了生命的丰富内涵。在一定时刻,冲击这种完满的标准,也是一种审美活动。而丑对美的否定,也正是对生命的限制的否定。其次,当人类一旦意识到与神、与英雄相比,人自身蕴含着许多丑的东西,人类并不仅仅与美等同,就同样会意识到,丑比美要更为普遍。审丑表面上是将现实的非人性、文明的不文明揭露出来,实际上对于现实的丑恶的揭露也就是对于自身的丑恶的揭露,因为它本来是人类自身炮制出来的。而且,从丑向美的运动,从表面看是两极对立的,但实际得到的则是两者之间出现的广阔的中间地带。这中间地带就是经过丑的消解后展开的现代的美学天地。人们的生命活动经由丑的介入而得以拓宽,对丑的需要因此也就成为人类无限展开生命的各种可能性的契机。这使我们联想到,人们总是喜欢想当然地把人类的历程概括为美的历程,但美的历程事实上也是丑的历程。丑所蕴含着的正是一种深刻的自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美总是一种限定,但丑却是反限定的,是向美的普遍性提出挑战。它所关心的不再是完美的人性,而是不完美的人性。因此,丑没有转化为美(优美),而是替代了美(优美),人类正是通过这样的例子宣谕着自己的觉醒;只爱美的人性是不完整的人性。相对于美,丑总是意味着某种同期待中的完满状态不同的东西。它使人们习惯性的美学评价落空。长期被常识所认可的美的标准,突然失去了分量,一切都落入了意义失落的荒诞之中。结果,丑把人们从日常麻木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体验到与外界对立的自我的存在,体验到孤独、无助的感觉,从而意识到日常与人共同存在的状态的虚假性,起而反叛日常的美的标准。
荒诞,就审美活动的类型而言,是丑对美的调侃,它表现为人们对于生活的空虚和无意义的一种审美解读。这种无意义的特点有二:其一,这种空虚和无意义不是指生活的某一个方面或人与世界的某种关系,而是指生活的整个存在或人与世界的全部关系。其次,这种空虚和无意义不是来自理性的某一方面,而是来自理性本身。阿诺德·P·欣其里夫说:“荒诞要存在,上帝就必须死去,而且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还不能企图设想任何一个超验的‘另一个我’来替代。”[②]这里的“上帝”无疑也包括理性。荒诞产生于面对非理性的处境而固执理性的态度。当理性固执要不就一切清楚,要不就一切都不清楚的态度时,荒诞就应运而生了。同样,当面对的是“我”的遭遇而不再是“我们”遭遇之时,考察的是我的遭遇对“我”的意义而不再是规律对“我”的遭遇的意义,荒诞展示的正是生命中的理性限度和非理性背景。所谓荒诞,也无非就是对于生命中的理性限度和非理性背景的意识。它提示我们放弃理性的意识,从而重新走向生命。
那么,作为一种审美活动的类型,荒诞的美学意义何在呢?首先,无疑在于意识到生命的空虚和无意义。上帝成为实际永远缺席的戈多。上帝被还原为戈多。不过,这还并不就是荒诞。正如我已经批判过的,意识到生命的空虚和无意义,并不意味着必然进入审美活动。以空虚反抗空虚,以无意义反抗无意义的态度,只能导致加倍的空虚和无意义。世界并没有意义,为此埋怨它实在愚蠢,但假如不知道世界又必须由人赋予意义,也许更是愚蠢。生命的伟大难道不正在于它能够在荒漠般的处境创造并确立一种神圣的、富有温情的、永恒的意义吗?因此,既然生命世界已经成为空虚和无意义,那么,就应该坚决拒绝接受甚至沉溺于这一世界,他必须保护自己不受这一世界的损害。其次,荒诞的美学意义就在于,它并非从虚无主义的角度发现世界的虚无和无意义,而是从理想的高度发现了世界的空虚和无意义。于是期待就成为对空虚和无意义的唯一回答。期待是生命的永恒渴望,是支撑着人的生存的精神支柱,是失落的赎回,是不可能的可能,期待就是愿意相信、渴望相信,就是渴慕可能性、渴慕希望、渴慕永恒,就是相信自己所未尝见过的东西,就是有限的存在对重返终极价值和生存之根的一种强大的心灵温慕,就是对理想本性的无畏期待与誓死相守。同时,期待又是生命的主动拒绝,它固执地拒绝逃避到空虚和无意义的虚无生命之中,而且不断敏锐地、深刻地揭露着世界的虚无主义和无意义。加缪说:“我在否定明晰的时候,提高了我的明晰,我在压毁人类的事物之前,提升了人类。”[③]这正是荒诞的美学意义之所在。
就美感类型而言,荒诞不再是单纯的快感或痛感,而是焦虑。这是一种“亢奋和沮丧交替的不预示任何深度的强烈经验”,杰佛逊称之为“歇斯底里的崇高”。因此,荒诞可以称之为一种生存的焦虑。相比之下,在美感类型中,荒诞最为复杂。它的愉悦是一种理智的愉悦,与优美的情感的愉悦不同;它的笑是不置可否的笑,与喜剧的开怀大笑不同;它的哭又是漫不经心的哭,与悲剧的痛楚的哭也不同(荒诞是是与是之间的冲突,而悲剧是是与非之间的冲突);它的痛感是转向焦虑,与崇高的痛感转向快感更不同;它的压抑是在人类理性困乏时产生的。既轻松不起来,也优越不起来,永远无从发泄,也不像崇高的压抑可以一朝喷发,因此,它始终是一种疏远感、陌生感、苦闷感,而不是一种征服感、胜利感、超越感。就美的类型而言,则可以归纳为:对象的平面性,主体的零散化,时间的断裂感。
悲剧,就美的类型而言,是命运对于人类的欺凌,是自由生命在毁灭中的永生。悲剧必须是庄严的。即便是坏人,也要具备“优良品格”或者“强大而深刻的灵魂”[④],就美感类型而言,悲剧是一种复杂的美感体验,其特点是在理性、内容层面暴露人类的困境,而在情感、形式层面又融合这一“暴露”(西方重“暴露”,而中国重“融合”)。对此,亚里斯多德的“怜悯感”、拉法格的“恶意快感”、莱辛的“恐惧感”的说法,是较为典型的概括。在我看来,悲剧是悲喜交集、惧悦交集,是在怜悯、恐惧中使情感得到陶冶。就审美活动的类型而言,悲剧是丑对美的践踏。悲剧是丑占据绝对优势并且无情地践踏美时的一种审美激动。应该说,由于生命的有限性所导致的生命的苦难和毁灭,是生命活动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且,这种生命的苦难和毁灭“似乎不能完全归结为罪过或错误,而更多是伴随任何伟大创举必不可免的东西,好比攀登无人征服过的山峰的探险者所必然面临的危险和艰苦”[⑤]。因此,它是生命活动中的厄运。此时,丑竟然如此嚣张,它演出着邪恶的胜利、嘲笑生命的痛苦,造就着不可逆转的失败,以至于在它面前,美犹如肥皂泡,吹得越大,就越难免于粉身碎骨的天命。
但悲剧的美学意义,却不在于展现这种丑对美的践踏,而在于展现出美的一种令人痛心的毁灭,甚至在于美在这种毁灭时所出现的巨大增值。这就恰恰表现出“人在死亡面前做些什么”的不同。因为,尽管正像《唐·吉诃德》中安塞尔在宽恕自己失节的妻子时所说的:“她没有义务创造奇迹”。对于现实的人,我们确实应该说,他们“没有义务创造奇迹”,但对于自由本性的理想实现来说,人类却必须创造奇迹,正像俄狄浦斯宁愿刺瞎双眼、自放荒原也不愿隐匿生命的本来面目,苟且偷食,也正像哈姆雷特“在颤抖的灵魂躁动不安的运动中,依靠绝望的英雄主义和纯正的眼光”(雅斯贝斯),去反抗横逆而来的命运,从自由本性出发,人类必须对现实提出抗议、提出质疑,必须不惮于捅现实的马蜂窝,必须以生命的完结去否定那种“超过人类之上的残酷力量”。人类用对现实活动的生命的有限性的直接否定去间接地肯定理想,用对于阻碍着自由的生命活动的生命的有限性的直接否定去间接地肯定自由的生命活动。
因此,悲剧表现出一种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独到的审美解读。它通过生命的苦难和毁灭,展示出:生命的秘密不在于长生不死的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生命犹如故事,重要的不是多长,而是多好。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与生命的量成正比,而是与生命的质成正比。这样,更为人瞩目的的不是生命何时毁灭,而是生命为何毁灭。只要生命能够勇敢地去创造,去追求,即便是毁灭了,也最终从有限进入无限,赋予生命以深刻的意义。
三
肯定性的审美活动包括优美、崇高、喜剧。
优美,是丑的全面消解。就审美活动的类型而言,此时,外在的一切已经失去了它高于人、支配人、征服人的一面,不难迅即激起主体的快感,内在的自由生命活动因为没有自己的敌对一面与自己所构成的抗衡而毫无阻碍地运行着,和谐、单纯、舒缓、宁静,同样不难激起主体的美感体验。就美的类型而言,勃兰克斯曾描述说:“没有地方是突出的巨大,没有地方引起人鄙俗的感觉,而是在明净的界限里保持绝对的调和。”[⑥]因此,从浅层的角度看,优美意味着球形、圆形、蛇形线,意味着“杏花、春雨、江南”,突出的不是内容的深邃、深刻,而是感性的特征的完整、和谐、单纯、自足、妩媚,易于接近、感知、把握。从深层的角度看,优美的形式对于内容的显示有其清晰性、透明性的特点。其典范的文本则是:希腊神庙与希腊雕塑。就美感的类型而言,优美则意味着“乐而玩之,几忘有其身”(魏禧)、“温柔的喜悦”(车尔尼雪夫斯基)。它是自由的恩惠、生命的谢恩,“乐”、“喜悦”的情绪始终贯穿其中,既无大起大落的情感突变,又无荡人心魄的灵魂震荡。其次,优美是种心理诸因素的和谐。对此李斯托威尔概括得十分准确:“当一种美感经验给我们带来的是纯粹的、无所不在的、没有混杂的喜悦和没有任何冲突,不和谐或痛的痕迹时也不难激起主体的情感体验,我们就有权称之为美的经验。”[⑦]
崇高,就美的类型而言,像人们熟知的那样,是恐怖、堂皇、无限的巨大、深邃的境界,是“骏马、秋风、冀北”。其中,从浅层的角度看,是感性的因素间的矛盾冲突,所以爱迪生才会称之为“怪物”,荷迦慈才会称之为“宏大的形状”,“样子难看”,博克才会称之为“大得可怕的事物”,康德才会称之为“无限”。从深层的角度看,是内容时时压抑着形式,准确地说,是形式缺乏一种清晰性、透明性,康德称之为“无形式”即缺乏某种可以准确表达内容的形式。因此,很难迅即激起主体的快感。其典范的文本是歌特式大教堂和浮士德形象;就美感类型而言,则是“惊而快之,发豪士之气”(魏禧),是“惊惧的愉悦”(爱迪生),是努力向无限挣扎。此时,生命先是受到瞬间压抑,然后得以喷发,主体由矛盾冲突转向一种处于强烈的震撼,由痛感转向快感,并产生一种超越后的胜利感。因此,与优美感相比,崇高感不再是单纯的,而是充满着复杂性、矛盾性,不易迅即激起美感体验,而且,也不再是轻松的,而是深刻的,充满了巨大的主体力量。也因此,崇高感不再是单纯的喜悦,而是热烈的狂喜、惊喜。不过,崇高也不同于悲剧,后者是恐惧与怜悯,是毁灭中的净化,而前者是痛感与快感,是抗争中的超越。因此,崇高令你震颤,但不会令你震撼;令你惊骇,但不会令你惊惧。
就审美活动的类型而言,崇高是美对丑的征服。西方美学家在谈到崇高时,往往只是着眼于外在的“大”,以及对于外在的“大”的超越,例如朗吉弩斯、博克。从康德开始才注意到内在的超越,后来黑格尔却把它阐释为对绝对理念的敬畏,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干脆又退回到外在的“大”。事实上,康德的看法才是最深刻的。只是,对于“内在超越”,还要加以阐释。歌德说:“人们会遭受许许多多的病痛,可是最大的病痛乃来自义务与意愿之间,义务与履行之间,愿望与实现之间的某种内心冲突。”[⑧]从现实活动的角度讲,这种“最大的病痛”就表现为个体生命对社会律令的冲突、感性生命对理性律令的冲突、理想生命对现实律令的冲突。而从审美活动的角度讲,这种“最大的病痛”一旦表现为个体生命对社会律令、感性生命对理性律令、理想生命对现实律令的理想征服的时候,就意味着人类的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这就是所谓“内在的超越”。它是对生命的有限的超越。我们知道,在对于外在世界的抗争中自由精神会凝聚为理性的力量,在对于内在世界的超越中自由精神会凝聚为意志的力量,但这都是对于生活的超越。而崇高则是对于外在与内在世界的同时超越,其中自由精神会凝聚为情感的力量。郎吉弩斯曾经慷慨陈言:“作庸俗卑陋的生物并不是大自然为我们人类所订定的计划;它生了我们,把我们生在这宇宙间,犹如将我们放在某种伟大的竞赛场上,要我们既做它丰功伟绩的观众,又做它雄心勃勃,力争上游的竞赛者;它一开始就在我们的灵魂中植有一种所向无敌的,对于一切伟大事物,一切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事物的热爱。因此,即使整个世界,作为人类思想的飞翔领域,还是不够宽广,人的心灵还常常超越整个空间的边缘。当我们观察整个生命的领域,看到它处处富于精妙、堂皇、美丽的事物时,我们就立刻体会到人生的真正目标究竟是什么了。”[⑨]这里,“人的心灵还常常超越整个空间的边缘”,“观察整个生命的领域,看到它处处富于精妙、堂皇、美丽的事物”,就是所谓“内在超越”。其中的关键是,不再仅仅是对社会律令、理性律令、现实律令的征服,而是对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生命有限的征服。那么,什么是生命的有限呢?马斯洛说过:“我们害怕自己的潜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我们通常总是害怕那个时刻的到来。这在种顶峰时刻,我们为自身存在着某种上帝最完美的可能性而心神荡漾,但同时我们又会为这种可能性而感到害怕、软弱和震惊。”[⑩]生命的有限,就是“为这种可能性而感到害怕、软弱和震惊”,而一旦理想地对此加以超越,而且为“自身存在着某种上帝最完美的可能性而心神荡漾”,就是所谓崇高。因此,对社会律令、理性律令、现实律令的征服,是现实的征服,可以称之为伟大,对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生命的有限的征服,是理想的征服,可以称之为崇高。
喜剧,就美的类型而言,是一种“透明错觉”,是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目的与手段之间的错位,毫无理由的自炫、自大,自以为是的优越,不致引起痛感的丑陋、背离规范的滑稽与荒谬。就美感的类型而言,喜剧不像崇高那样由消极转向积极,而是直接表现为积极的过程;也不像崇高那样靠牺牲自己来换取对对象的肯定,即通过对自身的无能的否定来肯定对象的无限,而是通过否定不协调的对象来肯定自己;不像悲剧那样导致一种压迫感,而是一种由误解而产生的紧张;不像悲剧的美感是痛感中的快感,而是直接的快感。因此,喜剧的美感类型集中表现为笑(笑是人类的特权,动物并不会笑)。这是一种轻松愉快的笑,一种突然荣耀的笑,一种预期失望的笑,一种通过夸张理想的方式来实现理想的笑,一种意识到自身优越性的笑。里普斯说:“在喜剧性中,相继地产生了两个要素:先是愕然大惊,后是恍然大悟。愕然大惊在于,喜剧对象首先为自己要求过分的理解力;恍然大悟,它接着显得空空如也,所以不能再要求理解力。”[(11)]就是对此的揭示。
就审美活动的类型而言,喜剧是美对丑的嘲笑。此时,丑在喜剧中处于绝对的否定状态,美在喜剧中则处于绝对的肯定状态。相对于悲剧,喜剧冲突的内容不是庄严的而是滑稽的,发展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结局不是悲壮的而是可笑的。因此,丑对美的反抗、挑战,实际偏偏只是一种夸饰、虚幻、无力的代名词,这就不能不导致一种美对丑的强大、无情的嘲笑。并且,正是这强大、无情的嘲笑,使人栖居于自由的生命活动之中。确实,喜剧正是通过对丑的嘲笑而企达对于生命的终极价值的绝对肯定。因此,我们可以把喜剧称之为:生命的智慧。
注释:
[①]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述评》,蒋孔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33页。
[②]阿诺德·P·欣其里夫:《荒诞》,梅森出版社1969年版,第94页。
[③]加缪:《荒谬的人》,张汉良译,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④]分别见黑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第284页,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第117页。
[⑤]麦克奈尔·狄克逊语,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张隆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⑥]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卷,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6页。
[⑦]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述评》,蒋孔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38页。
[⑧]歌德语,转引自宋耀良:《艺术家的生命向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⑨]转引自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
[⑩]转引自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11)]里普斯语,转引自《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七辑,第84—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