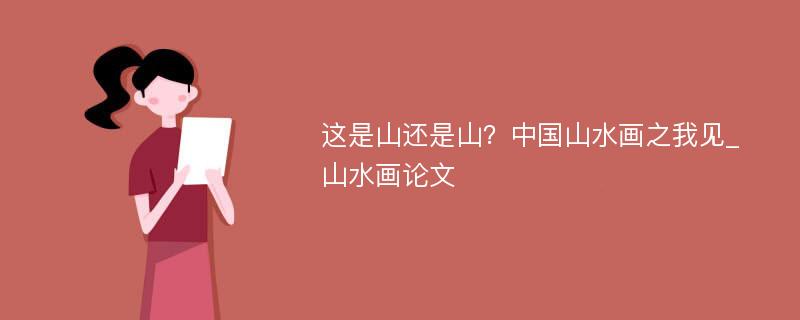
这山还是那山吗?——关于中国山水画的一个见仁见智的题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见仁见智论文,山水画论文,中国论文,题目论文,那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快餐式旅游与符号化山水
薛永年
中国是山水画大国,山水画的产生比西洋画为早,山水画的遗存数量比人物画花鸟画为多,山水画论占了古代画论的绝大部分。这其实并不偶然,中国不仅幅员广大,而且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山山水水既是先民生息发展的环境,又是他们“究天人之际”的凭借,更是他们寄托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的精神家园。李可染先生说,山水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祖国,这是指富于爱国精神的人们。对于执政者来说山水则是“江山”则是政权,画家赵原明白这层意思,所以朱元璋让他画山水,他便请朱元璋先勾几笔,然后说“江山已定”,不需要再画了,避免了政治错误。对于更多的画家来说,他们既要像荆浩一样地“图真”,把对千姿百态自然美的感受概括出来,遂为此而忘我地投身于大自然中,像石涛一样地“搜尽奇峰打草稿”,在“山川脱胎于予”和“予脱胎于山川”的艺术创造中,在融主客观为一的境界里,实现“畅神”,以富于自然美和创造个性的艺术诉诸观者。当然,没有“删拔大要,凝想形物”的艺术提炼,便产生不了艺术图式,图式一旦脱离了自然便成了晚清民初八股式的符号。符号也许是个性化的,然而一旦离开感受,就必然失去动人的魅力和流光溢彩的生命。
前些年,中国山水画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在开拓题材上,在表现人类观照自然时所显现的精神生活的多样性上,在“不与人同”的笔墨形式的出新上,都不乏成功之作。但近年也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问题之一是宏观探道多。微观探真少;问题之二是表现自我多,感悟自然少;问题之三是致力笔墨符号多,探究意境境界少。致使有些作品显得空泛雷同,有些作品显得玄虚谲怪,有些作品显得有我无他。我想,如果我是宗炳一类打算在山水画中“卧游”的人,看到这样的作品,便大有参加某个急急忙忙赶路的旅行团之感。看景点来不及品味即被导游叫走,爬山不再深入其中而是登上缆车在几分钟之内一览无余。又好像为了赶路迫不及待地买个汉堡包充饥,来不及管他滋味如何。如果我是董其昌一类的批评家,又会觉得这些作品的符号已削弱了笔墨的文化积淀与精神蕴含,并没有懂得“造化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就好像只以“酷”形“酷”貌引人注意,把个性寄托在美容上一样。偶尔参加旅游团并以快餐果腹,忽然悟出这些山水画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尚少高品位的收藏家左右了,而这些收藏家正被讲求消费文化快餐文化的“导游”引领前进。我总觉得,我们不能没有文化的消费,但更需要文化的建设。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有一定对象的山水画,笪重光的主张似乎仍未过时。山水画不仅要讲究“笔墨气韵之微”,更要讲究“天怀意境之合”,而“从来笔墨之探奇,必系山川之写照”。
复古也是一条路关键在怎么复
陈传席
绘画的问题,该讲的我都已讲过。复古问题,我在20年前写《中国山水画史》时也讲过,写《明末怪杰》时又讲过:古到极点也就新到极点。明末陈洪绶的画复古复到唐、复到六朝,在当时也就崭新一时。后来的“海派”中有两股势力,其一便是陈洪绶派,任熊、任薰、任伯年都是他的传派,一直到谢稚柳,现在画家学陈洪绶的更多。西方很多前卫派其实就学的是原始艺术,最古的变成最新的。因此现代化的家室中放一个古器,即使是一个破罐、一个烂铜鼎,都会特别引人注目,价值也超过新的家具。中国古代诗文和绘画,凡高举复古大旗的,无不取得突出的成就。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是倡导古文运动的两大领袖,尤其是韩愈,“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他并说:“愈之志在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也就是说不仅要复古之文风,还要复古之思想内容。柳宗元也如此,韩柳都是力肩复古而成为唐代最伟大的散文家,又是“唐宋八大家”中唐代仅有的二家。他们的散文一扫六朝浮艳文风,继承古文的特色,形成一种朴实明朗、深沉强烈的特点。宋代欧阳修也是力倡古文运动的,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作出卓越的贡献,宋代文学也是从欧阳修的古文运动开始有了相当大的起色,“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大家都是古文运动的产物。其实“唐宋八大家”也都是古文运动增减出来的。
欧洲的“文艺复兴”实际上也是“复古”运动。他们打着的旗号就是“回到希腊去”,要“复兴”古典文化。现代文艺上的各种派别都有人反对,但稍有知识的人都不会否认“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后人永远无法超越。可见,“复古”具有何等的效力。
中国美术史上,宋画是最了不起的,宋元绘画成为古代绘画两大无法逾超的高峰。这两个时代都是高举“复古”大旗的。我在《中国山水画史》一书中总结北宋的绘画是“保守和复古”,北宋后期绘画的复古使其绘画达到空前卓越的水平。以山水画为例:古代的山水画都是勾线后加青绿颜色,唐后期兴起的水墨山水画后来居上,到了五代宋初期,几乎无人画青绿山水。北宋后期复古,古是什么呢?荆浩《笔法记》中说:“随类赋彩,自古有能;如水墨晕章,兴吾唐代。”古代的山水画之“随类赋彩”,即青绿山水。北宋后期的山水画就是以大青绿为画家追求的风貌,现存的大青绿山水有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院画《江山秋色图》(旧题赵伯驹作)都是北宋后期的作品,也都是古代山水画中最杰出的大青绿山水。
元初赵孟頫极力排斥“近世”(南宋),同时极力提倡“复古”,他把“古意”列为绘画审美的第一标准。赵的复古,使赵成为元代最杰出的画家,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师法“董巨派的“元四家”——黄公望、吴镇、王蒙、倪云林,以及师法“李郭派”的曹知白、朱德润、唐棣、姚彦卿等,都成为画史上杰出的人物。
文学和艺术,凡是打出“复古”旗号的,都取得十分杰出的成就,而且都比打出“创新”旗号者成就高得多。这在历史上都得到公认。可见“复古”也是一条路,关键是怎么复法。
历史上的“复古”者大多是托古改制,“文艺复兴”的画家和人文学者们打着“回到希腊去”的旗号,召唤古希腊罗马的亡灵,并不是要重建奴隶制旧文化,而是要抵制摆脱当时封建思想的桎梏,建立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的意识形态。唐代韩愈的“复古”,也不是重复古人,他“唯陈言之务去”,“务去陈言”,也是以“复古”为武器,扫除六朝的浮艳之风。但他也确实在“复古”。唐人复“三代秦汉”之古必然有唐人特点,这就是新。北宋复古的青绿山水也显然比唐以前的青绿山水要充实丰富厚重得多。元人复古学董巨,但又增加了书法笔意,显然又不同于“董巨”,而且有元画的特色。认真复古的,只要有思想,没有一个同于古的。
自“五四”以来,绘画界一直是反对复古、甚至反传统的,“创新”的口号喊了近百年,近三十年来,几乎天天高呼“创新”,人人在“创新”上想点子,但又创出什么名堂呢?又有多少“新”呢?有人提出借鉴西法,有人提出“形式美”,当然,这也是一条路,于是也出了不少“花样”,也可以算作“创新”,但很多人对这些“新”不太满意。我的研究结论是:很多“形式美”不过是一些“花样”,而必须以“内在美”、“本质美”加以冲击,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新”。清僧石涛在其《渴笔人物山水图》上题字云:“画家不能高古,病在举笔只求花样。然此花样从摩诘打到至今,字经三写,乌焉成马,冤哉。”石涛是革新派大家,但他也反对“花样”,力主“高古”。现在很多画家的“创新”实际上是“举笔只求花样”,看似有自己的风格,实际上很浅薄。当然也有少数画家真有自己的新意也确实很好。但要想在格调和内涵上达到复古派大家的水平,还是很困难的。
“创新”的大旗高扬近百年了,“复古”的道路无人问津。我建议部分没有“花样”的画家重扯“复古”大旗,走一走“复古”的道路。当然这是一条艰难之路,没有真才实学和雄厚的功力,很难走通这条路,惟其“难能”,才有“可贵”。“只求花样”,笔墨功力全无,便很难深刻,也很难取得较大成就。怎样复古,怎样托古改制,限于字数,只好俟诸异日再作评论了。
山水之全与认识之偏
孙明道
在中国山水画艺术发展中,存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山水境界,同理性精神和道德实践意识相比,这种境界仿佛是永恒的绝对真理,是山水的“真”、“全”、“唯一”,是人永远探索的宇宙。人智慧的光芒,虽然照亮山水,但照亮不了山水之全,人对山水的认识,只是对黑暗宇宙中的山水之全一隅的认识,这是认识之偏。正是由于认识之偏的存在,才出现元人不同于宋人,今人不同于古人的山水观念,才于中国绘画史上出现一座又一座风格各异的山水高峰。认识之偏的存在,使现在乃至未来的山水艺术创新成为可能。可以说,中国山水艺术的发展规律,就是中国山水画家认识之偏的规律,那种代表时代的理性精神和道德实践意识,是中国山水画家认识之偏发展的一脉。所以,对中国山水艺术精神的把握,就是对理性精神和道德实践意识的把握,也就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之偏及造成其认识之偏的社会地位和心态变化的把握。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经历了由王到师,由师到臣的变化。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指出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变化引起文化形式的变化。一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山水艺术发展的全过程,正值知识分子所处臣位时期,认清这一点,对古代山水艺术精神,才会有一个明朗把握。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山水艺术精神主要是庄玄思想。这话大致不错,但倘以庄玄思想涵盖中国山水艺术全部,未免偏颇。知识分子师位时期的音乐尚“和”,与知识分子臣位时期的山水尚“逸”,都是理性精神和道德实践在外力影响下的自然流露。因为没有认识到中国古代山水艺术是知识分子臣位时期创造的一种“文”的形式,徐先生才对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和山水精神不能统一感到困惑。
如果说知识分子王位时期以“诗”推动社会教化,师位时期以“史”维护社会基本价值,那么臣位时期知识分子的“文”的文化形式,则是道统的历史责任与正统的社会现实冲突的无可奈何的产物。文者,饰也。陆机所谓“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大馨香。六朝而下或扩充为“圣人之道”,或光大为“天地一手”,如灰线草蛇,在浩如烟海的古代画论资料中时见首尾。把绘画包括山水画理解为“道”或“圣人之道”或“治世之道”的论述,都可视之为知识分子道统情结的下贯或变异。
“士人画”兴盛的北宋和“文人画”理论成熟的明季,文人对画工的轻视达到了高峰。明代之后,那些其实非常匠气的画家们,都争着充当文人画的嫡传。归究起来,无论唐朝乃至六朝画家不愿为役,还是五代北宋画家不愿为工,还是明人攻击院体,其实都可以看作臣位时期知识分子那种被人役使心态的过敏反应。
一千多年中,中国山水画经历了宋繁元简、明枯清柔的面貌变化,而奇崛或平淡两种审美格调却始终是中国山水两峰对峙的审美格局。对中国山水乃至中国绘画奇崛和平淡的对峙,恐怕不能简单地以文艺的奇正来解释。实际上,奇崛和平淡是臣位时期中国诗学乃至文学的两大旋律。那时人们尊崇司马迁的文章,说:“韩文得其雄,欧文得其逸。“以”雄“和”逸“作为两种好文章的风格。奇崛和平淡之所以成为那个时期中国山水乃至中国文学的审美风尚,恐怕还与知识分子的臣位有关。道统与正统的冲突是产生奇崛的原因,道统对正统的屈服乃至走出道统与正统的矛盾,则是他们对平淡天真欣赏的另一心理基础。按照传统的笼统说法,中国画史上有一个文人画阵营,然而这个阵营并不统一,宋人在标举“士人画”同时,就有人提“名卿士大夫之画”,近代的黄宾虹先生也以倡“士夫画”鄙“文人画”而闻名。宋人标“士人画”与明人标“文人画”内涵的不同,正是知识分子臣位时期心态的两端。以这样的立场俯视一千多年来不断解释的气韵生动现象,以及“气以取势”“韵以远出”论调,或“气”“韵”“风骨”“隐秀”等所造成的独特审美心理,或许有新的发现。在极力推崇笔墨并标榜平淡天真的董其昌看来:“以境之奇怪论,笔墨不如山水。”言辞间亦透出对“奇”的赞叹。实际上,与宋元相比,明清文人的山水创作更注重平淡与奇崛的统一,这一点有类推崇“平淡”和“硬语”的宋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认识之偏,一个时代因而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形式。曾被费正清高度评价过的唐诗和北宋山水,早已风光不在。钱钟书说,明人写诗尊唐鄙宋,结果连宋也不如。现在看来,同光诗派打出复宋旗帜,所作可能不抵明诗。现代中国山水,如果不立足于对理性精神和道德实践的继承,立足于现代的理性精神和道德实践意识,立足于现代人文精神,立足于同古人认识的差异,而是如某些人那样极其表面化地推崇晋唐宋元的“规整画”,或流于表面的形式探索,如明人想做唐诗,清人想吟宋体,其命运恐怕和文言文一样,最终只能成为附庸风雅和水平特别高的人们书斋案头的酬唱。
这山那山——山水画古今谈
林木
禅语云,初看是山,再看不是山,继之看还是山。以致王阳明的“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的心学把心与物同归于一体,大千世界都依我的知觉而存在。石涛著画语录,亦有“天地万物终归之于大涤”的说法。简单说,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前述之“山”,第一个“山”是客观之山,再看之“山”为纯观念之山,第三个“山”亦当为意与象相生相发的禅境之山,亦可为艺术之山。由此观艺,则有二层次:一,客观自然之山并非艺术家笔下之山,后者是“登山则情满于山”之情象与意象,艺术之象。二,彼时艺术之山亦非此时艺术之山也。原因亦在这个“情”与“意”之变易上。他人之情非我之情,我之彼时之情又非此时之情,则情之变,而致象之变也,奚有同焉?石涛云:夫茫茫大盖之中,只有一法。得此一法,则无往非法。而必拘拘然名之为我法,吾不知古人之法是何法?而我法又何法耶?总之,意动则情生,情生则力举,力举则发而为制度文章,其实不过本来之一悟,遂能变化无究,规模不一。石涛在古代山水画家中算是面目最多的一位,他不认定某法即“我法”而死守一辈子,这瞬时一“悟”则称关键。同一个石涛画同一个黄山,幅幅不同;同一时代的渐江与石涛同画一个黄山,亦各各不同;清代的渐江与石涛与当代的张大千、刘海粟亦画同一黄山,亦人人不同。何以如此?情感不同,体验不同,观察方式、表现方式乃至工具材料都有不同,此山当然不是那山了!
——其实,文绉绉的说了那么一堆有些经典有些俚俗的道理,不过是说中国山水画并非真实山水的客观再现,中国的山水画是“因心造境”的精神载体,是情感——这些情感在中国古人那里往往还与儒、道、释的哲理相交织——的符号化表现。山水形态的变化当然会随情而变。刘勰“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之谓。所以古人的山水不同于今人之山水,他人之山水不同于吾人之山水,而吾人彼时之山水又当然地不同于吾人此时之山水……这些其实又都是常识,但当今的时代又的确是个经常要忘掉常识——连喜欢“深刻”的理论家们都经常要忘掉这些肤浅的常识——的时代。青绿山水,水墨山水,宋人山水,元人山水,都是民族传统的构成部分,都是我们今天山水画发展的基础。
历史发展至今天,当今社会与古代社会相比较,真有天翻地复的变化,情感与体验的变化亦当与古人大相迳庭才对。今天坐飞机坐火车住星级宾馆的旅游与古人骑马骑毛驴的“行万里路”,其体验要一模一样,岂非怪事!就是今天住厌了水泥都市要去自然中偷闲休憩,那种感受要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王蒙的《春山读书图》一样恐怕也难。故今人要画出些与古人不同乃至极端不同的山水画都是应该的,要相似或太相似,那多半不正常,那肯定有矫情的性质。——至少,你又能到哪里去找这种纯粹古典意味的风景?且不说,你又能到哪里去找这种纯粹古典意味的人?这让我想到日本东山魁夷的山水。他的山水宁静、安谧、单纯而优美,当然已全然不是古典的天老地荒的“南画”——文人画一路,但你能说他不东方?不禅?不日本?不现代?然则,这山还是那山么?
从这画到那画——复制的“等值”假设
冯原
陈丹青反复用油画来塑造、或者说去“复制”中国古代山水画画册的形象,其语义背景是什么?“这山还是那山吗?”我们不妨从这个思路来研究一下。
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批历代名画“锁在深宫”,能有眼福一窥真迹的人少之又少。于是日本二玄社与台北故宫合作——使用高度仿真的印刷技术对历代古画进行复制。二玄社的复制接近于探求印刷业的现有技术极限,真正是一对一的复制,目标是要达到某种二维平面上的“全息传递”,力求“乱真”。几乎可以相信,拥有一幅二玄社的原尺寸范宽《溪山行旅图》复制品,几近等于拥有了这幅稀世墨宝——仅止在信息的意义上。北京故宫则是用“手工”仿制品来替代原作展出,虽然复制的也是信息,但“手绘”多少会使我们联想起造假画的传统。要追溯对图画进行信息复制的原动力,必会联系到“手绘”赝品的历史。迄今为止,暂时还没有什么信息经济学家来解释制造假画的商业秘密。不过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因为存在着原作品的唯一性价值,绘画的信息复制才有利可图。问题是,造假画既可以是以真品为样本,也可以全凭空“捏造”出来。这意味着,真与假的标准实际上取决于一种风格之间的“等值关系”。其存在基础仍属视觉欺骗。换言之,赝品制造者需要掌握的是复制某种风格的能力,这样他才能以风格“障眼法”来生产出真品的价值。
在生物世界里,造假与打假的视觉骗术经常关乎到物种的生存状态。有一种在珊瑚礁中生活的章鱼,其随时随地用它的软体来“复制”周围环境的能力绝对会令最高明的造假画者叹为观止。生物学家还无法描述这种现象的机制。而我却以为,从造假画者身上便可推知出章鱼必定要具备的两种能力,其一,它必须首先知晓周遭环境的“风格”,其二是控制身体进行风格复制的能力。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把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扔进海里,碰巧有某条章鱼在此隐形,我丝毫也不怀疑这条章鱼用身体去营造青绿山水的本领。不过,前提必须是先有王希孟式的风格,章鱼不能单独去创造它的“环境特征”。这个现象反过来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赝品生产的性质-接触或占有真品,是制造风格“等值关系”的必要条件。在传播不甚发达的时代里,接触到真品的机会几近是等于某种“特权”了。
撇开赝品不谈,即使以传播为目标的印刷-复制也会面临另一种“等值”问题。作为一本传播知识的书,木刻版的《论语》与最现代的铅字版相比,其文字符号传达的信息量几乎完全等值。真正的“等值”与否的问题发生在图形传播的领域里(文字的书写被看作为书法时,其符号意义才转化为图形意义。书法史上的碑学与帖学之分,也暗含了复制方式的等级高下问题)。只要涉及到图形的印刷传播,便呈现出以下的两重性:印刷既是图形的复制与传播渠道,又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复制品与原作之间的区别。
瓦尔特-本雅明(Walt Benjamin)说:“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总是可以复制的,人所制作的东西总是可以被仿造的。”同时他又提出了艺术品的“原真性”(Echtheit)概念,并认为是任何复制技术都不可能逾越的界线。他说:“即使是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也会缺少一种成份: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
中国的水墨画可算是典型的难于复制的视觉艺术种类。可愈是难以复制的类型,其原真性的相对价值定会愈高。由此甚至可以推演出关于特定文化传统的社会学结论:谁处于艺术原真性资源的垄断或独占的位置上,谁就有可能占据了文化传承上的优势地位。在中国,宋代以后出现了木刻画谱,但这种图形复制技术所导致的信息缺损过大,透过画谱习画的人便不可避免地处于透过真品学画的人的“仆从”位置上。这样的情形有岭南二苏为证。据认为,二苏的笔墨法式中透露出某种“雕版印刷味”,这都是以画谱为样板犯的错。正是因为存在着原真性和画谱的“复制错误”,二者间的区别最终会“化约”成风格因素的高下之分。相反,董其昌有机会浏览大量的原作而处于资源占有的绝对优势地位上。与董其昌相比,到底是因为在原真性资源的劣势位置决定了二苏的画运?还是归因于个人的能力才情所限?很可能它们本来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罢了。
到了现代——在这个“印刷昌明”的时代里,最有名的“印刷-复制公案”当属油画家陈丹青所创。他曾经宣称,在看不到西方油画原作的条件下,透过印刷品为中介来学习油画是可笑的途径。这实际上宣布了印刷品的罪行-印刷品等于是赝品。从芥子园画谱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四色印刷技术,都无法去撼动原真性的权威地位。有趣的是,中国油画仍然在西方原作缺席的情况下走到了今天。而经过十多年西方原作洗礼的陈氏,近期却选择了一个令人费解的主题,这个主题正是印刷品-它们不再是习画者的中介角色,而是画中的主角-中国山水画的古旧画册。陈丹青反复用油画来塑造、或者说去“复制”画册的形象,知晓了这种语义背景的人也许可以从中读出马格利特(Magritte,Rene)式的困惑,我们可以按照“这不是烟斗”的提问式,由陈氏的上下文转换成“这不是原真性”的隐喻-被复制了的复制,它还是复制吗?
看来,从这画到那画的复制,其中的“等值关系”不过是一种随时代变动而游离的假定而已。不过,也正是因为时代的发展,过去表现在赵佶或董其昌对原真性垄断方面的优势,到了陈丹青的时代里可能已算不上多大的优势了。当二玄社已经将复制技术拓展到如此精良的地步时,原真性的“信息意义”反而面临瓦解。对此,我们不妨自问:即使这幅画复制得与那幅画完全一样,而你还可以坦然把它搬回家中,你的优势又在哪里呢?
从王履的“山”到倪瓒的“山”……
陈雨杨
山作为中国绘画题材之一在汉代画像石中就已经出现,而真正将山水作为一门独立的绘画门类则始于魏晋。从一种绘画题材发展到一个绘画门类,山有着它特有的自然魅力与特殊的文化涵义;它不仅为画家存形状物提供了载体,也是文人们情感心境的一种寄托。故中国人对山水有了非同一“天下”也不舍林泉之乐的传说;有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见解;有了《归去来辞》这种千古不磨的生命呼唤;也有了无数画家们对山水描绘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将这种执着与热爱用于创作中,才会出现“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的畅想;出现“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的论述……
明初王履“以纸笔自随,遇胜则貌”,登华山,作《华山图》四十幅并为之作《华山图序》,其中阐述他的主张:“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王履心目的华山,目中的华山就是他亲自攀登的那座华山,从他的理论上讲,心是绘画的起点,而在艺术创作中,心、眼、手以及描绘对象是应达到高度统一,即笔下的山还是眼中的华山。
新安派代表人物弘仁长年居住黄山,对实景写生。作诗如下:“坐破苔衣第几重,梦中三十六芙蓉。倾来墨沈堪持赠,恍忽难名是某峰”。弘仁曾画黄山真景五十幅,画得黄山真却不是真黄山,处处不像黄山,却又处处是黄山,这大概就是“恍忽难名”的原因吧!对此,石涛做了很好的解释。他说“名山许游不许画,画之必似山必怪。变换神奇懵懂间,不似之似当下拜。”石涛巧妙地阐述了画中山与自然的山的关系,似则名山怪之,不似则愧对名山,不似之似才为高明的手段。
中国画的评判标准历来玄妙,神、妙、能、逸,令人难以揣摩,如石涛所谓的“不似之似”之间的真正尺度又在哪里呢?画中的山还是原来的那座山吗?
倪瓒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这是倪瓒半生漂泊于太湖间对绘画的体悟,他不像王履那样“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也不像郑板桥那样“胸无成竹”;更不像弘仁那样“恍忽难名”。倪瓒大胆地提出“吾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的绘画功能,以及“岂复其似与非”的评判标准。或者说,倪瓒已经不再把似与不似作为绘画评判的标准,从而提出了那句千古绝唱:“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画竹如此,画山水也是这样,倪瓒所画的山水看似结构简单,而且所描绘景致多半得之于太湖一带的实际感受,但在形于笔端时,却不再是仅仅对实景的追摹,而是一种山与水的观念合成,也就是说,自然景象本身不再是描绘的重点,着意表现的是一种恒定的秩序,一种特有的心境和一种形象之外的韵味。这是山水画的精神,也是中国画的精神之所在。
图式与精神——对当代中国山水画的思考
李健强
图式是一个西化的词,意思是指构图上的视觉形式,与传统画论中的章法布局略有相近之意,但更多的带有强烈的程式化色彩。图式的建立,一般多是以具体而独特的造型完成,也可通过抽象的极具个性的笔法展现。翻看中国山水画史,凡是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无不是在图式上有着独创性,在笔法上有着独特性。古代与今天在审美价值取向上不同,古代更重视笔法笔墨的个性,把笔墨放到了价值判断的最高位置,对图式的建立相对有所忽视。以今天的审美来看,古代最具图式感的画家要算米家山水、马远、夏圭、倪云林、郑板桥等。他们用其一生将自然中获得的形象,提炼转换成一种符号,以表达自己的情绪与心境。中国山水画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由于社会节奏、生存状态、展示作品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现代审美观念的影响,今天的画家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关注与追求图式的个性化。在今天的展览会上,作品若没有强烈的视觉形式是很难在上千幅作品中一下子抓住观众的,更无法满足现代人对视觉体验的要求。
艺术是随时代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审美在不同时期的画作上都能反映出来。宋元明清不用说,民国近代也有着不同的面貌,就是现代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一直到20世纪末,山水画风的变化仍然是一目了然的,不同的画风是通过不同的图式来表现的,画家的精神层面也只有通过新的图式、新的笔法来展现。图示与笔墨具有精神性,如范宽的雄强、倪瓒的枯冷、董其昌的亲和、徐渭的狂狷、八大的孤傲等等,他们的笔墨图式表现着他们那个时代的审美特征,表现着他们个人的趣味、情感甚至人格。这就如同书法史上的“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人尚态”一样,不同时代留下了不同时代的审美风格,用今天的话说叫时代精神。时代精神由多方面因素形成,但图式与笔法是体现时代精神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应是不争的事实。
新图式的建立,是以情感为依托的,其中既有对客观生动之形的感悟,也有对主观理想完美之形的建塑。画家应深入到大山大河中去收集、提炼、概括,寻找并建立适合自身创作图式的新方法,在把握传统血脉和现代精神的大趣味下施展其有个性的理解与创造,回避模式,回避同化。新图式的建立是新笔法产生的基础,也是画家创造具有个性化技法程式的基础,古今大家无一例外各自都创造出了一套高标准富于精神感染力的艺术图式。这图式是翻遍画史而不可见到的,是全新的、生机勃勃的,笔法也是独立的有生命力的。图式的独创性与笔法的高难度是经典作品的必然准则。我们对任何一种图式的选择都体现了我们观照世界、把握世界的态度与方法,也体现了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认识。
当代人对图式如此的刻意设计与关注,除去审美观的变化,应该说主要是受到西方视觉观念的影响。西方现代美术史就是一部图式的变革史,西方文化的背景决定了其审美传统与中国的不同,他们更多是强调造型与形式。当代山水画创作,由于受西方图式观念的影响,加上市场经济下功名心的驱使,使越来越多的画家正在远离中国山水画创作的本体,远离中国山水精神。过于刻意形式化地理解图式的概念,把图式仅仅看作一个区别于别人的简单的符号,这样的结果是某些画家不断地在简单地重复着一种图式,以至到后来把初创图式时的一点鲜活生动的东西变成了一张毫无表情的面具,画面上仅剩下技术的手段,苍白而无力。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境界“精神景观”、“人格魅力”几乎已消失殆尽。
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是强调“内美”,强调“耐品”,强调在形式中寓涵深层的“意”。当代中国山水画的现代转换,应是在尊重现代人视觉审美变化带来的对图式个性化强化的同时,不放弃自己本民族优秀的传统。中国山水画是一种山水文化,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畅神”、“以形媚道”、“天人合一”,其审美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山水画家应培养一种文人情怀,应走向自然、亲和自然、感悟自然,使人格得到修炼与净化。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境界是在追求“精神景观”,而不是“自然景观”,过于接近客观自然的“真景”,反而不能给人遐想,更不能使人产生“澄怀观道”、清涤精神、领悟天地间道理、理解天地之大美的作用。山水画的现代推进,并不是画上高压线、现代建筑、汽车等等这么简单就完事了,严格说,这只能算是一张风情画,而不是一张具有中国美学精神的山水画。五六十年代一批老画家被迫画的简单的图解山水画是惨痛的教训。画家在创造新的图式时,一定要注入新的精神,精神是人格的反映,自古中国画家就强调人格的励炼,只有高尚健康独立的人格,才可能使眼见的“自然景观”转化升华为“精神景观”。
“新”源于“心”
张伟平
山水画要有时代性,要“新”,但依托什么来创新、怎样创,则反映出每个画家不同的思想方法和认识高度。对于那些脱开山水画的基本原理、基本技法另建一种表现方式的求新方法我是反对的,因为仅仅是为了求得视觉效果的不一样而舍弃对高精山水绘画法的追求不是明智之举,他们应该自问,既然能将支撑着国画山水体系的基本内涵都舍弃掉,为什么还要将自己的画冠以中国山水画这样一个虚名呢?我们不能因为当今时代没有出《论语》、《史记》一类的“新”经典,而迁怒中文的表现能力,更不能因此舍掉这个语言系统而创建一套新语言。至于那种套用西方现代派视觉模式的做法,更是简单化的行为,“挂羊头卖狗肉”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任何想要用个人意志来改变或阻碍它发展的企图最终都会是徒劳的,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这片肥沃的土壤上的山水画,正按着自己的发展模式走向新的繁荣。时代性的本质就是历史性。历史观念是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认识统一体。翻开山水画的发展史,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不同面貌的大师们的“创新”道路历历在目。范宽“始学李成,即悟,乃曰: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于是,舍其旧习,卜居于终南太华岩隈林麓之间,而览其云烟惨淡,风月阴霁难状之景,默与神遇,一寄于笔端之间……”黄公望远法董、巨,近观赵孟頫,为了化“法”,常于“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摸写之,分外有发生之意。”这样的创新才是大师级的创新:入手端正,学法精深,终日观察体悟自然,心想手追,明透“画理”、“物理”、“情理”,化法于物与心合,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也许有人强调时代的剧烈变迁,山水画也要来一个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变化。的确,就物象而言当今社会相比古代有着千差万别。但是,中国山水画从成熟之日起就没有把描物显态作为自己的责任。人有所思,心有所识。山水画家可以同景而异趣,也可能异景而写出共识。面对摩天大楼与坐观华山是否一样能有雄奇的心境?望着远去的热气球是否也能像观大雁南飞时产生出一点思乡的惆怅?各人造化,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那些借物变而对山水画基础技法与基本构成原理进行非议的言论,是不是有被物所驭、为事所累的嫌疑呢?中国山水画家从不拘泥于对质、色、高、厚等自然属象的描绘,而是或取雄奇、浑厚之意,或表幽深、阔远之情。也许千皴万染,烘托出自己理想的意境,也许寥寥数笔,其意也尽在其中,这也是不同风格的山水画能有此异曲同工之妙的原因所在。试看当代画家李可染,为了给中国山水画创出一条新路,游遍大江南北,难道是在给景物描姿显影吗?明透的墨色,挺劲的用笔,传达的是峨嵋山的幽深,黄山的雄奇,漓江的秀润……。明代董其昌说:“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沈周说:“山水之胜,得之目,寓诸心,而形于笔墨之间者,无非兴而已矣。”
谈到山水画的创新,我们很容易将它与个性表现等同起来。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强调个性表现仅是山水画创新的一个环节,个性表现一定要有深厚的文化依托,否则就是一句空话。中国画家特别强调修心养性,因为认识世界的能力有高低之分;也强调学习传统技法,因为高深认识的表达需要高精的技法来保证。“识”高“法”精,画品格高意远,人们观而有所感,其个性表现也寓于其中了。
斗转星移,物变事迁的物质世界里,变化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如果有谁想舍本求末,寻“新”于外部,用技法的变化速度去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速度,其画面的浅薄是可想而知。但愿当代的山水画家们明辩此理,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用文心去感觉这个世界,用高精的山水画技法去表达出你的感觉,那么,你画面的“新”必将从你的“心”中自然淌出,你的个性风格也就随之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