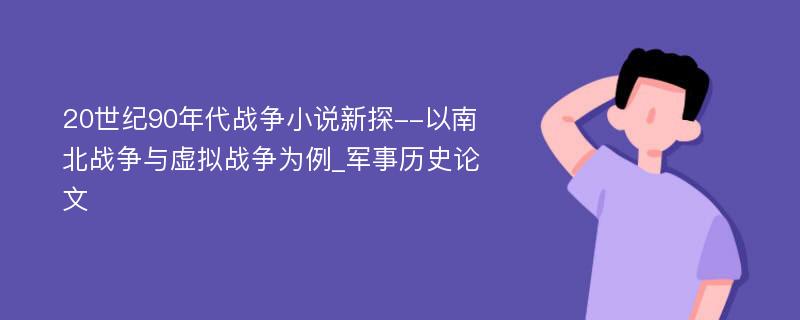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战争小说的新探索——以南线战争和虚拟战争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争论文,为例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争小说在军事文学领域当属“重镇”。一定意义而言,它标定一个时期军旅文学的水准。20世纪80年代,军事文学曾因当代南线战争和革命历史战争的繁荣而活跃于当代文坛,昔日的荣光,留给今日以无限的怀想。自80年代末期始,它“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一个群落和显赫一时的一个运动似乎一夜间销声匿迹了。”(注:朱向前:《军旅文学史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第18页。)那么,90年代战争小说的命运如 何呢?受大气候的影响,往昔的轰动效应、辉煌业绩难以再现自是历史的必然,但这并 不意味90年代战争小说创作的停滞不前。相反,在90年代多元文化交融的语境中,军旅 作家似乎获得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发展空间。他们不仅在80年代战争小说已开掘过的领 域纵深延伸炮火,而且还在80年代较为薄弱的领地精耕细作,尤其军旅“晚生代”(注 :三代军旅作家的划分见朱向前:《九十年代:转型期的军旅小说》,《文学评论》19 91年第5期。)作家的成长,更给战争小说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战争小说不乏新的探索 ,其新质在南线战争和虚拟战争小说创作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一
综观90年代的战争小说创作,爆发于20世纪70年代末,延至80年代中期的南疆战争已被大多数作家遗忘,这种遗忘是一种有意识的规避,因此带有策略的意味。“八十年代的作家在反映边境战争上,已经从诸多方面把它榨取殆尽,在战争与社会的结合部上,《西线轶事》和《高山下的花环》都把战争与刚结束的十年内乱的惨痛记忆和沉重反思结合起来。在战场上检验一群方才摆脱了梦魇,带有累累伤痕走上前线的新一代军人的精神素质,拨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心弦;在小说的艺术探索上,《亚细亚瀑布》、《雷场上的相思树》、《山上山下》等取得各自的成就”。(注:张志忠:《英雄为战争而存在》,《解放军文艺》1999年第1期。)如若说先期的探索给后继者以较小的发展空间而影响此类题材的创作,那么,“南线战争的短暂局促和历史烽烟的远逝飘渺,使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的战争生活体验储存有限,难以支持他们在战争领域中更加长久的 跋涉。”(注:朱向前:《军旅文学史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第18页。 )则是作家们规避此类创作的深层原因。90年代“重写”南线战争,军旅作家们的确面 临许多既往成就所构成的一个又一个创作障碍,然而,这并不意味后继者在这个领域无所作为。朱秀海、张伟明“重写”南线战争的《穿越死亡》、《双兔傍地走》就是成功 的例证。
《穿越死亡》的新探索就在于对一个作为战争“预备队中的预备队”的九连战士战前的心理愿望的透视,尤其对17岁的军校毕业生上官峰,从和平走向战争及战争中落入“死亡陷阱”,慷慨赴死的心理蜕变的透视。这种透视的意义,不只是对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讴歌,更是在和平/战争的大反差中,从心灵“内宇宙”的层面揭示英雄的生成 ,并且进一步阐释战争与人性的律动关系——战争不只是毁灭人性,而且也能激扬人的 主体精神,因而从一个向度抵达战争本体。《双兔傍地走》则较为巧妙地于和平/战争 、战争/和平的两重强烈反差中展开战争与人的思考。在和平环境中成长的林晓燕和一 群爱美的年轻姑娘们迈入战场,克服恐惧,荣获“八姐妹救护队”的光荣称号。但是作 者将叙述的中心置于她们从战场回到和平环境的种种行为的叙事:粗野、狂放、抽烟、 酗酒,怀有不可名状的挑战欲和破坏欲,挑战现实秩序(故意不买票乘车),把一只只漂 亮的红气球吹炸以获取畸形的快感。即便面对摄人心魄的爱情也麻木了。这些行为背后 的深层原因应该在于战争对她们心理行为的塑型。“打仗打木了,女人味打没了”。至 此,我们不难发现张卫明是从另一向度上抵达对战争本体的探索。当然,这种探索实际 上承续了80年代中期,宋学武的《洞里洞外》、《山上山下》等小说对战争本体深度探 询的路径。但宋学武小说的艺术视野有点狭窄,其审美视角仅仅投向战场,关注战时的 心理。而张卫明不仅把审美视角投向战争,而且还转向战前和战后,在和平与战争的强 对比中固定、放大女兵们的心理和行为以实现他对战争本体的思索,艺术的张力相对大 些。并且,女兵们在和平的环境和爱的氛围中走出战争的阴影,步入正常生活。这种对 战争本体的探索不是带有浓郁悲剧色彩的西方式探索,而是有中国特色的探索。
不可否认,尽管90年代的当代南线战争创作还不够丰富,但它毕竟强化或拓展了80年代此类题材创作中一些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探索性因素。甚至在某一点上,还体现出超越 性的色度。然而,当代南线战争小说创作大体上还没有逾出80年代创作的框架,因此, 它的探索是有一定限度的探索。
二
真正挑战80年代战争小说创作,或曰推动90年代战争小说发展的是军旅“晚生代”作家,和尽管成名于80年代但一直保持创作个性,富有探索精神的少数作家。由于90年代的文化语境和个人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这部分作家,在战争叙事上,明显地远离了传统战争叙事的程式,而是充分依赖想象力、释放想象力,构筑出一个个虚拟的战争叙事(我们称之为“虚拟战争小说”)以承载他们对战争的思索和追问。虚拟 的战争叙事一类体现为古代战争叙事,另一类为部队对抗性的军事演习和未来战争叙事。
古代战争题材对战争小说创作而言,实在不新鲜,但在年轻一代的开掘中,却焕发出老树新花的勃勃生机。此类题材创作中,作家不拘泥于传统的历史真实法则,不注重史料的钩沉、考据、考证。而是以“新历史主义”方法,“虚构”一段历史(没有具体的历史时代指向,甚至是很“后现代”的“戏仿”),营造一种历史氛围,悬置战争场面 和进程的描绘,建构出“另类”战争。其审美的最终旨归不在于回归历史,再现一段历 史战争风云,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而是落脚于虚拟的叙事中叩问传统战争观念,思索与 追问战争的驱动力以及如何制止战争和人类能否永久地平息战争等具有浓郁当代性的问 题。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问题,对此问题的探索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20世纪末,面对新千年,人类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历史,筹划未来。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年轻的军旅作家把审美眼光投向古代历史战争,于虚拟的古代战争叙事中,展开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决战》、《穷阵》就是这种思索和探索的结晶。为篇幅所限,仅选《决战》作一透视。《决战》中,作者以“戏仿”的手法(巩羽、司马卓使人联想到项羽、司马懿),讲述一个不知何年何月,没有具体朝代指向的南蓼和 北蓼国的战争故事。南蓼军统治将军巩羽兵败被俘,北蓼军将军司马卓念及16年前自己 被放的旧恩,放了巩羽,约定十年后再战。十年间,巩羽隐居山中,参悟阵法以雪被俘 之耻。但在与自然界和谐地相处的十年间,他也得以对既往的战争进行反思。“许多年 来,你征我伐,劳民伤财,草菅人命,彼此又得到什么呢?不过是寸土之争。”“战争 战争,战为利争,可是利益也并非唯一只有杀伐一条途径可以达到目的”。由此,他决 定化干戈为玉帛,放弃战争,并最终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决战》的结局是双方各退三 十里,形成一个六十里宽的通道作为通商、经济的自由天地,战争从此结束。巩羽从谋 战到息战的转折,背后的动因是以儒家的战争观作支撑。儒家的战争观在本质上是一种 伦理主义的战争观。“民本意识已成为沟通战争与道德两大领域的媒介或中间环节”。 “战争超越了功利层次上升至道德层次,并且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中获得道义的合理性以 及最后的归宿”。(注:倪乐雄:《战争文化与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考察》,上海 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但是,“息战”是建立在巩羽参透了司马卓的阵法使 其无法取胜,并且在最后的赌注里,两位将军以生命为代价使双方放下了刀枪。战争能 否永久停息?或者说儒家的战争观对战争解释的合理性及制止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作者 留下了一个令人思索的空间。此外,《决战》还探讨了战争的驱动力问题。巩羽梦中与 其夫人有一段对话,“你知道男人的心啊,男人的血性就是要征服,就是要叱咤风云, 纵横天下啊。我是一个文韬武略的统制将军,怎么能甘心去过那种挑水浇园的平庸生活 呢?那样的日子对于一个将军来说,与死何异?”这番话实际是战争与“战争崇拜”关系 的一种诠释,与西方的观点很相近,是个体的角度的透视。当然,这种诠释还显得有些 浅白、单薄或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失,然而其探索本身有足够的理由值得重视。“我们 不妨把这方面的探索视作一种战争文学或战争小说觉醒的开始”。“作品的创造性,以 及战争本体及价值观念的探索所达到的程度(或者说,它们的现代性程度)在这里已经无 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什么?”(注:周政保:《诗意的追寻及现代性的拷问》 ,《解放军文艺》1998年第3期。)客观地说,90年代战争小说在这方面的探索还很不够 。
以对抗性军事演习和未来战争为内容的虚拟战争小说在90年代的出现有着一定的现实 原因。尽管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但世界范围内的局部战争依然频 繁发生,军队的职责和使命并没有终结,战争的幽灵还盘旋于人类社会的上空。战争智 慧和战争技艺的习得对人类而言,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同时,它的出现也是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忧患意识影响的当代军旅作家居安思危,以其创作昭示世人的结果。 此类虚拟战争小说的叙事立足这样一个逻辑起点,即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如 何走科技建军、科技强军,如何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正是在准战争背景下, 一方面,透视军队存在的传统战争观、人才观等与新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以及和平环 境中部队内部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注重表现高科技在战争中的作用,同时也注重战 争中人的素质,人的智慧及其影响力的开掘,展示现代军人的风采。柳建伟的《突出重 围》可谓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A师和C师的准战争背景下进行对抗,但它一败再败,陷 入重围,除了或许偶然因素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太依恃传统,缺乏面对新形势所 必需的一系列新观念,如战争观、新兴的人才观、创新观等。当他们走出传统的阴影后 ,终于突出重围。柳建伟在这种虚拟的战争叙事中不仅展示当代军人的风采,而且着重 探索了新形势下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问题。
未来战争小说,目前数量较少,是一个相对贫弱的领域。但《末日之门》和《沙盘》却代表了此类小说的成就。《末日之门》被乔良称之为“近未来预言小说”曾引起一些争议。“平心而论,《末日之门》实在算不上精品之作,尽管作者投入了相当的精力,也调动了自身多年的生活积累,但从实际效果说,其作品显然过于看重了市场流行需求的口味。”(注:吴然:《论现代军人意识与现时军事文学创作》,《昆仑》1996年第5期。)的确,从叙事层面而言,作品既有21世纪印巴冲突导致战争,引起世界各大国的关注和参与,围绕北方四岛问题引发日俄战争,总统被刺,多国首脑被扣为人质,恐怖分子利用电脑网络企图控制和毁灭世界的阴谋等叙事,更有战争风云中高科技的运用, 现代武器展示和军事谋略等内容的描写。这一切似乎印证了上述的看法。但是,我们认 为作品还蕴含着深层的意蕴。乔良以其宏阔的国际视野,渊博的军事知识,较深的文化 积淀,极富想象力地描绘本世纪初的国际政治态势和世界军事风云,显现出一个军人强 烈的忧患意识和一个作家对人类前途及命运的前瞻性的思考。“它同时也是一部严肃的 警世之作。它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表达了作家超前的对于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深切 忧患和关注。”(注:朱向前:《九十年代:长篇军旅小说的萌动》,《文学评论》199 6年第5期。)此外,这部作品还塑造出不同国度的职业军人的形象。尽管他们来自不同 的国家,但却有着相同或近似的特征:忠诚、恪尽职守、熟知各种常规及现代化武器、 熟练掌握电脑技术、精通战略战术等,体现出新世纪军人的新素质,而且,这是一种全 球化的视野,拓展了战争小说的表现领域。但也因军人特征相似性的突出而使其民族性 特征弱化。总之,此类小说的探索为以后军旅题材创作及发展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论及虚拟战争小说创作,我们不应该忽略一个年轻女作家钟晶晶和她以《战争童谣》为标题的短篇虚拟战争小说。叙事中,她有意造成时代背景的空缺,给作家更大的空间,给战争叙事以更大的余地,以便对战争进行纵深的开掘。“她不管真实的战争如何进行,也不管真实战争中的人怎样期待,只顾用自己的梦幻和柔情对其进行全心构筑和演绎,——让你面对着残酷而又忧伤的毁灭,悄悄完成自己对于战争的重新认识。”(注:刘立云:《瞬间的美丽与单纯》,《解放军文艺》,1997年第2期。)《第二次死亡》 中,那个士兵的第一次阵亡是非常平庸的,毫无英雄气。他不满足于这样的死亡。作家 抓住这一点,于他弥留之际,描写他潜意识里第二次英勇冲锋,完成英雄壮举,实现其 英雄梦。这种英雄性的揭示非常独特。《遗嘱》里,两个士兵,剑和兵战前约定,战争 中无论谁负重伤,要互相留下遗嘱。当兵背着即将死去的剑行走在回去的路上时,剑用 最后的力气口述遗嘱,而此时兵却被炮声震聋了双耳,剑的话一句也没有听清楚。这有 点“黑色幽默”的色彩,于荒诞的叙事中透射出对战争本体的追问与思索。在这之前, 我们的战争小说还缺乏这种接近西方式的对战争的表现。这也是新一代作家战争观更新 的必然结果。
三
90年代文学艺术的探索精神总的来说,其锐性不如80年代。尽管80年代的探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对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就小说而言,艺术观念的更新,叙事方法、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的多样化为小说的繁荣提供了充足的原动力。战争 小说创作在艺术探索上虽然比其他小说慢半拍,但因莫言、乔良、江奇涛等作家的天赋 、勤奋而提升了艺术高度。反观80年代,尽管被命名为“无名”(陈思和)或“私人化写 作”时代,作家的艺术个性得以充分发挥,但真正在艺术探索上下功夫的作家并不多见 ,类型化写作、模式化写作比比皆是,先锋的锐性被艺术的钝性所取代。也许可以归咎 于90年代的文学“边缘化”处境和“文化守成主义”的影响,但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作家的艺术惰性。在90年代小说创作艺术探索整体不足的大背景下,战争小说的探 索基本也没有超出80年代的水准。当然也不是一点没变。就南线战争和虚拟战争而言, 比之80年代,其艺术方面的探索也出现一些新的气象。
首先,最为鲜明地体现在战争描写方面。由于更年轻一代的作家进入战争领域,因其战争观念的变化,致使战争描写出现诗意化的倾向。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战争是残酷的 、嗜血的,是大地的颤抖,是生命的毁灭。既往的战争描写常常是流血、呻吟,是断垣 残壁,血肉横飞,充盈着血腥味。然而在年轻一代的笔下,这一切却被悬置起来,成为 文本的“不在场”,取而代之的是诗意的描写。《遗嘱》中,钟晶晶是这样描写的,“ 他看见血红的人向自己涌来,血红的人腿组成一道密密的红森林。他的任务便是砍伐这 些红森林,他手中的机枪喷出一片长刃的银光闪闪的镰刀砍伐着这些红森林。”即是杀 人,死亡,我们很难嗅到血腥味,这是诗话处理的结果(可与乔良的《灵旗》对比)。赵 琪的创作被军内评论家称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诗意化的艺术表现力。“赵琪 的笔端所流泻出来的,是情感的澄澈,故事的简化,色调的淡雅,如同文人笔下的山水 画一样,计白当黑,将无作有,那一处处留白元地,明明是未曾着笔只是宣纸的原色, 却偏偏要有心人看出云缠雾绕、山泉鸣溅来。”(注:张志忠:《感悟人生——赵琪小 说论评》,《解放军文艺》1995年第1期。)其次,南线战争和虚拟战争创作的艺术探索 还体现为作家文体意识的普遍自觉而带来的文体多样化的追求。许多作家不再满足于讲 一个好故事,而是注重“讲好”一个故事。因此,他们注重叙述的视角和视点,注重叙 述节奏的把握,和叙事氛围的营造。这样,在南线战争和虚拟战争的叙事作品中,我们 既可看到传统的写实性作品,也可看到富有诗化性的文体和完全放纵想象力又带有传统 传奇性的虚构小说,因而,形成了这两类题材创作的文体多样性色彩。
当然,南线战争和虚拟战争的创作,由于创作个体和时代的影响,也出现一些不足。比如古代战争的创作出现思想大于形象的缺失。受90年代时风的影响,较为彻底地放逐了对战争的道德化思考。未来战争创作,立足国际视野时,纵横开阖,洋洋洒洒,而转向中国文化传统时,则显得底气不足。年轻一代作家因其学识和艺术修养的积淀不太厚实,在创作中显现出细处有余而宏阔不足的通病。这一切可谓美中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