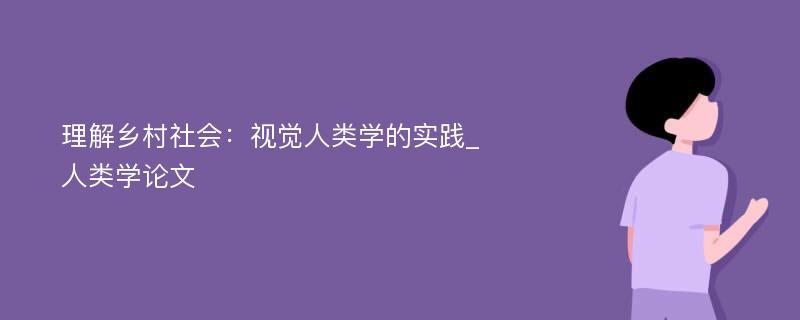
理解村落社会:视觉人类学的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村落论文,视觉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1)03-0039-05
一、视觉人类学的尴尬前行
传统西方的思想中,图像与文字之间向来关系紧张,图像被视为无法提供真理,文本则被视为探究实质的工具。①然而有点讽刺,“肤浅”的图像却更容易超越文字的门槛,进入使人理解的领域。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往往被当地文化中独特的视觉现象如仪式、服饰、景观等深深吸引,也正是这些外显的特征使研究者感受到田野初期的震撼并在后来成为推动理解当地文化的动力。接下来,这样的体验也带来一个问题:在极度依赖文字赋予意义的传统文明社会如中国,视觉表征、视觉艺术、视觉有关的行为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多大程度上能通过对视觉内容的研究来促进对区域社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视觉表达方式本身的局限成为了一个讨论众多而难以解决的热点问题。与书面文本相比,视觉呈现和意象的悖论在于:它表面上内容丰富,为观察者提供了种种具体细节,实际却忽略了整合细节的情境话语(Surrounding Discourse)。[1]胡鸿保检视了人类文明中的图像——文字的关系,论及人类学是一门由语词驱动的学科(A Word Driven Discipline),理论上经验主义者定性研究对科学的认识,以及定性研究的范式使用的大多是语词,偶尔才用数字。影像和声音等手段还只是起到补充文章的作用。视觉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反思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它的地位注定处于边缘。[2]同样注意到视觉人类学处于二分法构成的二元困境中(如文字和图像、艺术和科学、理论和实践)的还有彼得·I·克劳佛德等。[3]
另一个问题是视觉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的局限。脱胎于民族志电影摄制和分析的视觉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在引入中国时更多地被翻译为影视人类学②。早期的讨论集中在民族志电影如何精密科学地表达异文化和反映研究成果。影视人类学被看成研究和民族志写作的辅助工具而在影视工作者、致力于表现异文化的人类学者中被广泛讨论。它被定义为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4](P113)然而,研究工具并不是研究本身,也无法形成完备的学科体系。因此,影视人类学的讨论多半只能伴随民族志书写的反思和讨论。其涉及的热点问题由早期的“如何拍摄真实、科学的民族志电影”[5](P25)转向“多音位”、“参与”、“分享”,不回避研究者、拍摄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肯定人类学家以影视手段对文化建构的作用,③以及人类学电影如何有效地应用——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6][7]看似热闹的讨论背后,一些人类学家则坦言不相信影视手段能为民族志作出什么贡献。[8]
然而,持有上述观点的研究者们又不得不面临另外一个事实:人类通过图像记录、表达、保存和传播信息,创造系列性视觉符号并产生大量叙事性象征性视觉文化行为的历史,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而以现代科学工业技术为基础的“读图时代”的到来,更使得文字的霸主地位遭受严峻挑战。[2]即使在我们通常认为的“传统社会”中的视觉呈现如“传统艺术”,也在很大程度上和区域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对异文化或自身社会文化中大量存在的视觉符号和视觉传播的意义“视而不见”也许不是个好办法。
由影视人类学到视觉人类学的尴尬前行中,除了普遍认可的视觉人类学在反思人类学中的贡献外,仍有多种可能。如芭芭拉·艾菲认为,通过研究文化对视觉的影响、视觉与身体交流、视觉呈现与日常生活、图像参与建构的混合世界、新的视觉媒体等,能使视觉人类学“超越民族志电影”成为可能。[9]王海龙关注视觉符号的“使用—交换—符号”的过程和超越经济理性的“信息—体验—符号”过程,其方法为文化—行为研究。[10]邓启耀主张用跨学科研究来探讨视觉与认知、视觉符号和图像信息、视觉建构和传播等重要问题。[11][12]麦克道尔则认为,随着人类学思维由基于“单词—句子”到“形象—序列”的转变,视觉人类学是书面人类学的必要且有益的补充。视觉人类学注重的并不是影视本身,而是渗透并且编码于视觉中的涉及文化的一系列关系。[13]笔者以为,除了对视觉现象和视觉文本做跨文化比较研究、跨学科整合研究外,还应在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微观研究的坚实基础上,关注视觉现象的整合研究,关注视觉符号在日常生活中被生产、交流和建构的过程,在区域社会文化的背景上来理解视觉的意义,并由此加深对某一文化整体的理解,比过早地划定学科藩篱更为有益。或者,以实际研究代替过早定义性质和领域,而保持“其边缘性的状况能够持续相当一段时期,使得这一年轻的学科不至于落入固定僵化的学科规范之中,或者不至于发展成枯燥的官僚主义学科”。[14]
二、从视觉体验到认识村落社会
带着这样的理解,笔者在近年来两次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中注重运用视觉人类学的方法。一是以贵州屯堡人的地戏表演和地戏面具雕刻为切入点,来了解长期保留中原文化特色的屯堡社会的内聚力和村落变迁。一是透过在中缅边境的傈僳村落展开村民摄影的活动,来观察传统上无文字且自认为是“没有文化”的少数民族的人群如何对自己的环境和文化进行展演。
(一)贵州屯堡:地戏表述与再现传统
屯堡的名称可能来源于明代“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的军事行动后形成的“屯兵堡子”。地域上的屯堡是指位于贵阳—安顺直线距离一百余公里大片平地中的三百多个村寨,其名称多以带军事性质的屯、堡、官、关、哨、卡、卫、所等命名,其中又以屯、堡为多。[15]“屯堡人”则是清代载废明代卫所屯田制后上述村寨中自我认同为明屯军后裔的人群他称和自称。屯堡人中的大多数一直聚居在屯堡社区内,并基本上较为完整地保持着明代江南汉族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其文化的外显特征如建筑、服饰、集体性的酬神和娱乐活动“地戏”、地戏所用的木雕面具“脸子”等被认为在汉族各支派中都是十分罕见的。[16]
地戏又叫“跳神”,是屯堡村寨自行组织表演的一种集体活动,其剧目故事发生的年代多在明代中期以前,尤以唐宋时期的英雄征战故事居多。地戏作为一种成熟的民间仪式性娱乐活动,与屯堡人的生活共生互存,在很多村寨,至今保存有自发组织的地戏表演队伍。举办地戏与否甚至还是区分是否是屯堡人的重要标志。作为仪式的“跳神”具有强化村落凝聚力的功能,对屯堡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具有重要的意义。④
笔者的田野村落周官村传统上以地戏面具的雕刻出名,现有二百余户人家中,有三百余人从事木雕,其形式已经扩展到国内木雕市场上流行过的几乎所有类型。还有一些村民办起了木雕厂,熟练地运用人际网络、大众媒体、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向外地销售木雕工艺品。他们知道如何把传统文化植入到其木雕产品上,增加其文化附加值。
除此之外,伴随近年来贵州经济开发和旅游开发的热潮,企业在活动中的主体性、对于文化资源的强调、政府和社会一体的参与模式成为比较流行的“办节原则”。⑤在以“奇观”为文化资本的影像传播中,地戏和木雕被地方精英和政府视作重要的民间视觉资源。屯堡地戏打破原来的仪式展演时空,成为一种消费品,其形象和表演都成为政府、商人、媒介的“征用”对象。因此表演地戏也不再是一种对祖先的义务,而成为对国家以及游客的义务。仪式实践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表现方式,被各种动态、强大的权威造就的义务所推动。⑥在外来力量或者村落内部精英的组织中,传统文化往往成为一种情境性的工具。如同Emily Chao在描述了关于纳西族的历史论述转变后指出的那样,纳西族精英积极展示本民族形象,自身则更趋向于主流文化。在官方的支持下,传统文化既成为有利的文化认同的符号,又成为可以赚钱的商品。[17]
全球化进程中,地方和民族的文化特质往往成为展示的节目,在近几年,地戏队经常被请到各种场合表演。笔者在田野期间,经常拿着摄像机拍摄当地人的生活,并跟随周官地戏队参加了分别由安顺市政府和某木雕厂厂长组织的两次“屯堡艺术”宣传活动。然而,脱离了村落场域的仪式和忽视了剧情的文化展演,地戏表演者和村民成为表演的元素而非表演的主体,文化传承人本身的主位视角往往被忽略,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
不久之后,经过在家族内部会议的讨论,老人们找到笔者,谈及在上述的宣传活动中,传统地戏的精髓几乎完全被忽略,并希望借用笔者的摄像机来拍摄一次“真正”的地戏表演,因此要由他们导演,“一手一脚”都按照老规矩跳。此后戏友们开始自发选择拍摄的最佳场地,详细地告诉笔者地戏表演的特点,应该采用的拍摄位置和拍摄的角度、时间,体现了极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泰伦斯·特纳通过圣保罗的卡雅波人(Kayapa)摄制的影像来分析其自觉行为、文化架构、自我展演和政治申诉。他认为卡雅波人以影像作为自身社会中的形象表述,通过再现冲突、再现仪式来完成自身形象建构和政治诉求,成功地创造了自身的社会现实。[18](P79~94)周官村地戏队的老人们虽然不能熟练地使用专业的摄像机,但他们仍然希望主导性地利用影像展现自身的文化特色,甚至是展示屯堡人的族群性。此后拍摄的过程非常愉快且顺利,老人们不但认真地按照地戏的全套仪式过程呈现了原在村落之间展开的传统地戏,还邀请了本家族的女人们排练和表演山歌,并在最后为整个村落进行“扫场”——扫除污秽、祈求吉祥的仪式,结束后还举行了大范围内的仪式性会餐。
关于地戏的拍摄不仅仅是记录传统文化,更是当地人在自身的村落内进行主动的文化“展演”;影像不仅仅是一种“呈现”,而更多地成为一种关于文化展演的“行动”;其目的并非争取地方性的资源优势,而是当地人试图通过摄影机的媒介方式来再现传统,并在力图传承传统地戏表演方式的努力无效后,利用影像的方式为自身进行“书写”。欧挺木指出,在当代的文化场景中,屯堡村庄的地戏仪式经过一番“化石化”的建构,被重塑为屯堡居民重构自我历史谱系、搬演国家神话、展示权威边界的一种仪式展演;由于当代的地戏表演构成了一个权威边界的商榷场域,屯堡村民在其中既是国家边疆文化政策的对象,又是在文化经济的增长中成为权力与权威的积极商榷者。[19]
需要指出的是,周官村并非一个特例,而是当代面临全球化和现代化洪流的诸多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普通村落。对于视觉现象的讨论也并非针对周官村,而是针对处于广泛深刻变迁中的当代村落中的社会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屯堡村落成为一个有普遍价值的个案。而正是对视觉现象的研究,尤其是把视觉现象和人的活动结合起来的研究,使研究者能透过它们窥视文化的整体,从而加深对社会文化的认识,反过来又能再一次加深我们对田野中视觉现象的理解。
(二)腾冲古永:故乡影像与自我呈现
笔者因负责一个村民影像的活动而开始云南腾冲花村的田野调查。花村被选择是始于日渐兴起的滇西水电开发,花村从高山河谷的傈僳族聚居区迁到平地上的汉族聚居区。虽然有大额的移民补偿金、免费的住房和家具、粮食补贴和生活补贴,但优厚的条件并没让村民快乐。相反,巨大的生态和社会环境的转变让他们感到隔离和被剥夺。项目组希望通过举办强调“傈僳族传统文化”的活动来吸引村民参与禁毒防艾的活动,笔者开展的村民影像子项目则为其中之一,通过赠送10台相机给村民,并定期收集照片和拍摄者关于照片的解释。
第一批收集的照片如项目组所希望看到的那样,集中反映了“少数民族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几乎所有的照片都和节日场景、傈僳人节日服装、新村村落的景观、少数民族女性这些主题中的一个或几个有关。崭新的村落,绿色的环境,富有特点的民族节日,是拍摄者认为“好看”的注解。这种美感的展示与主流话语不谋而合,不但被拍摄者自己挑选出来作为照片展,也在后来被镇宣传部门索要,用于展示“新村面貌”。此外,很多研究者注意到,在当代的“少数民族”叙事中,女性往往成为一种被展演的形象。沃尔夫认为在此场景中的“观看”往往是一种“男人的视角”,女性形象甚至成为一种“病理化”的形象。[20](P15~31)
除了探讨女性形象泛滥之中的性别政治之外,在该例子中,我们还应注意到本地的族群已经吸收了主流的意识形态,而用一种反身性的眼光来观看和展示自身形象。因此,尽管在使用相机的培训中尽量降低外来者对本土观点的影响,但拍摄者对自我的影像展演包含了潜在的观众的观察方式。这种“反观性”的影像也出现在当地人自己的视频拍摄制作中,傈僳人YHC在2003初中毕业后,在电视中看到了以拍摄古永刀杆节为主要内容的电视片《傈僳欢歌》⑦。受此影响,当年他和父亲就买进了电脑和家用摄影机,又向腾冲的一位喜欢摄影的文化工作者学习了电脑和摄影机的操作技术,剪辑的技术则是向县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学习。目前,他已经拥有3台摄像机,一台台式电脑用于复制光盘和储存素材,一台笔记本电脑用于远地方的现场制作。他的拍摄内容包括傈僳人的刀杆节、新年、婚礼、基督教教众的节目表演等,由于有几年的影视资料积累,他们父子俩在当地小有名气,媒体和政府宣传机构也向他索取视屏的资料或请他们拍摄影像,不过,他们主要的对象还是傈僳人分布区的人群,由于YHC能讲傈僳语,又有现场制作VCD的能力,每年都能接下不少生意。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笔者回到花村收集后续的照片。和第一次的照片不同,由于时间跨度较大,照片的数量和内容都要丰富一些。在这些照片中,老家的细节、回老家的行动成为主要的表达内容,很容易发现,不管是傈僳人的形象,还是展现的内容,都有了较大的变化。花村老家位于腾冲西北部的高寒山区,槟榔江从北至南流经两岸的高山。这一带分布有琅琊山、鸡飞和头山、石洞山,以及高良工山系。照片内容涉及槟榔江一线的山川、河流、田地、地基、路口、村落设施、树林、草果地等,基本覆盖了花村傈僳人生活的环境。拍摄者对照片的解释也要比第一次的照片细致得多,往往把空间的叙述和亲身经历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花村的傈僳人由于生活在高山峡谷,活动在大片的森林中间,和自然生态关系密切,拥有相当丰富而至关重要的自然知识。因此在关于老家的照片中,自然环境被大量地拍摄,勾勒出花村傈僳人的生存环境。通过照片和对照片的讲述,笔者得以了解花村傈僳人地方性知识的基本面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照片内容往往被外来者认为没有意义。因此,拍摄者预设的观看者是同为傈僳人的群体,事实上,这些照片也往往能激起村民对故乡的共同回忆。
在田野的后期,笔者带着摄影机进入古永,拍摄傈僳人的日常生活、环境和仪式。两个月后,花村的村民向我提及,希望能用我的摄像机拍摄老家,因为有传言说水电站建成后花村老家的大部分地基将被淹没。我欣然答应,并提出拍摄的内容和方式由村民自行决定。此后村民们带着摄影机几次回到老家,拍摄故乡拆迁之后的风景。很快,我发现用不着自己操作摄像机,村民不久就学会了大致的操作,并把拍摄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显然,当代媒体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原住民记录自己的文化时,焦点并不在于要找回理想化的、接触西方文明之前的景象,而是在原住民身处的现今文化中的文化记忆和身份建构(Identity Construction)。[18](P79~94)在花村的例子中,泰伦斯·特纳的“自我展演”分出了层次,在第一种类型的影像中,村民通过“他者”的视角来向“他者”展现自身,体现了一种身份的“反观”,而在关于故乡的影像中,村民借用外界的技术和工具,在自身生活的场域中展现记忆,其预设的对象也是族群内部场景的人群。
三、视觉融入生活:行为、阐释和关系
以上的两个村落从族群构成、经济类型和地理环境都区别甚大,但在笔者的田野经历中,他们都有较强烈的应用视觉媒体表达自身的愿望并付诸实践,虽然他们经常受到主流话语的影响,并主动地利用“外界”的眼光呈现自身,但其生产的影像如果能在村落社会内部和日常生活实践中产生意义的话,他们的创造性和运用媒介的能力将被进一步激发,并和研究者产生大量的互动。
把村落中的视觉现象和视觉行为纳入到村落生活的整体场景中观察和分析,也能使我们把视野由看起来表象而难以言说的视觉文化和生活体验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不但有助于了解民族文化中的视觉现象,也有助于理解相关的人和群体,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
笔者进一步认为,从以下三个方面把“不可言说”的视觉体验还原到“可供理解”的社会生活、文化场域,将有助于进一步的讨论。
(一)与视觉有关的行为研究
村落社会虽然经常被处理为封闭和自足的实体,但如上述例子,在权力、媒介、贸易、人群、信息融合的社会中,村落社会内外实际上一直发生着频繁交流,其中,视觉媒介的交流是重要的内容。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中理解视觉现象呢?埃伦·迪萨纳亚克认为人类文化的意义必须在行为之流中得到表达,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艺术可视为具体的历史经验集合与文化的关联的一种行为表达。[21]戈夫曼则指出,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表演。表演者的期望普遍来自于他对具体场景和角色要求的主观判断,而观看者的预期则大多来自于社会规约,即在一定群体内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某一具体社会位置(Social Status)及相应的角色要求的认同标准。[22]正是人的行为连接了视觉呈现和文化场景两个方面,因此,视觉有关的行为研究是理解视觉文化、解读视觉现象的一个适宜维度。
(二)视觉表达和对它们的“阐释”
格尔兹主张把视觉艺术作为浑然植根于文化体系的一个属类,对它们的人类学研究,实际上也就是在“结构和解构的基础上,对所发生的繁复的事实给予合理的阐释”。[23](P155)当然,也应关注本土化对于视觉现象的阐释,以及这些阐释在村落社会中如何产生意义。笔者在屯堡村落和花村也观察,对于视觉形象的制造总是和对它们的评说分不开的。村民们生产的影像总是在村落内部被不断重播,并引起日常的话题。因此,对于视觉现象如何体现本土意义,不能只了解村民对研究者的“阐释”,还要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它们如何在村落的不同人群中被评价和阐释,从而了解视觉传播的方式和关系网络。
(三)影像“分享”和“多音位”的表述
笔者在田野中拍摄了研究用的纪录片,也应村民要求拍摄了仪式过程和自然环境、村落景观、家族聚落等。在播放素材给村民看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影像在村落的场景中被观看的过程就像一个小型仪式展演,观看者通过群体性的观看暂时再次进入仪式场景中,影像和影像所展现的内容一样,以多种感受渠道提供了“在场感”。也即是说,影像具有仪式性,仪式等展演可以被看作是社会文化中外显的视觉叙事,用图像志的方法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影像的制作、观看、阐释也可以被看作是多方参与的有仪式性质的活动而加以考察。
图像具有重要性的原因之一是它具有隐喻和联觉(Synaesthesia)的功能。[22]因此,超越文本的视觉媒介也许可以称得上是对事物的“诉说”所能采取的最佳方式。通过影像的分享和赋予各个层面以表达的权利,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在作品中建构和阐释文化中的形象和符号并考察交流和分享的过程。以此理解地方文化中景观、空间、仪式、服饰、身体等视觉形象的意义。
注释:
①Daniels S,Cosgrove D.Spectacle and Text:Landscape Metaphors and Parturitional Taboos in Huaulu(Searm)。转引自方怡洁《云南和顺地景中的国家象征民间化过程》,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三期。
②此术语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由J·科聂(John Collier)首先使用。1985年,当时的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埃森·巴列克西教授(Asen Balikci)将这个术语介绍到中国来,1988年,于晓刚等在《云南社会科学》发表《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影视人类学这一术语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刊物上。
③“多音位”(polyphonic)一词源于音乐学,后用于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理论,指让不同声音、不同观点在民族志文本中同时展开(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著,王铭铭、蓝达居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106页,三联书店1998年)。视觉人类学中的应用有台湾“中央研究院”胡台丽的《兰屿观点》。“分享”(Participatory)的思想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它允许在影片中反映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互动、被拍摄者在整个过程中的积极参与。代表作有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Jean Rouch)的《夏日纪事》(Chronicle of a Summer)。
④从村际地戏仪式观屯堡人族群的稳定性。
⑤《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06中国·贵州黄果树瀑布节主体活动方案的通知》,黔府办发[2006]24号。载《贵州省人民政府公报》2006年第4期。
⑥屯堡村庄中国家建构的谱系仪式。
⑦沈杰:《傈僳欢歌》(电视纪录片),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82年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