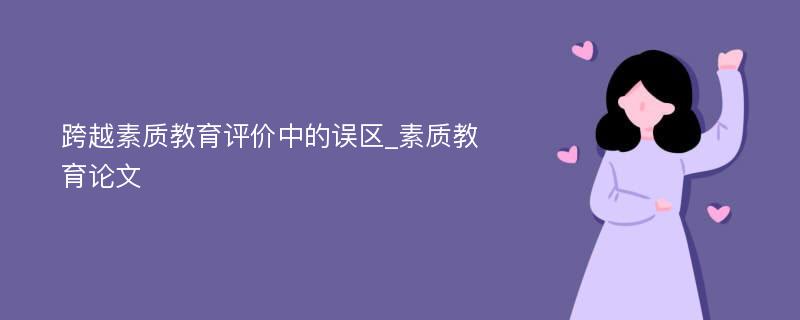
跨越素质教育评价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素质教育论文,误区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促进“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人们从一开始就把评价作为素质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功能作用寄予很大的希望。然而,当人们还在对什么是素质教育争论不休的时候,就要作出这样或那样的价值判断,这不免或多或少会陷入一定的误区。作为一项探索性的实践,这些误区是可以接受的,但要保证素质教育全面实施和健康发展,有必要总结经验教训,理智地跨越这些误区。
误区之一:“张冠李戴”的评价方案
人的活动需要评价,以便合目的、合规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素质教育活动,自然也需要进行评价,以求某种“证明”或“改进”。于是,学校自己组织评,主管部门找上门来评,素质教育评价活动也就热火朝天。不论评价者是谁,都是在执行一套评价方案,而这套方案中已对评价目的、依据、准则、原则和方法等作了系统的设计。评价方案从何而来?现实中多数学校是上级主管部门“给定”的,或者是从别的学校“借用”的,而很少是根据本校的素质教育价值取向和素质教育活动实际自主设计的。那种“给定”的或“借用”的评价方案,难免不会出现“张冠李戴”,这样的评价如同“父母包办”的婚姻。
评价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这种判断依据的是价值主体的客观需求。不是说“张冠”一定不能“李戴”,这要看这项“张冠”是否恰好反映并符合“李戴”的客观需要和能力实际。素质教育评价方案的设计总是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自主性,一般说来不具有“普适性”的通用价值。如果素质教育评价方案一定要“张冠李戴”的话,必需以共同的教育价值取向为前提,或者事先组织被评价者学习、理解直至接受这顶“张冠”中所确认的素质教育价值观和推崇的教育行为,而不应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
具体地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借用”某一评价方案,则需要明察该方案的评价目的是否切合本校实际,以确保评价的效度。目的是关于活动效果和结果的预定,它应该在人活动之前就观念性存在于头脑之中。任何素质教育评价方案都有关于评价目的的表述,诸如:“检查学校素质教育目标的达成度”,“促进学校素质教育工作的落实”等。但是,这只是该方案的一种工具性目的,而确立规定的“素质教育目标”,强化合意的“素质教育工作”,才是进行素质教育评价的实质性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借用”某一评价方案时,不仅要审视该方案中对评价活动的程序、组织和方法等设计的科学性和逻辑性。更要弄清楚该方案中所确立的是什么评价准则和价值标准(一般采用指标体系的形式标示的),对被评价者具有多大程度“合意性”。只有按照被评者的客观需要和能力实际,经过必要的补充、修定后的评价方案,才会避免“借用”评价方案容易带来的“张冠李戴”现象发生。
我们主张尽可能“自主设计”素质教育评价方案。理由有三:其一,评价是素质教育活动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不应该作为一种外在的“附属物”;其二,价值主体是素质教育活动的主体,没有什么人更了解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价值;其三,素质教育是一种“心中想着最好,行动只求更好”的持续过程,只有使评价活动与素质教育活动紧密结合,才能做到“评价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
误区之二:“包罗万象”的评价对象
评什么?这个问题时常让人处于“两难”境地:评少了,惟恐疏漏又不得要领;评多了,劳民伤财又怨声载道。在制定指标体系时,设计者以“评价的对象不应只限于学生或学校成员,几乎任何东西都能成为评价的对象”(注:陈玉琨著:《中国高等教育评价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为理论依据,于是,只要是与学校工作有关的事物,都理所当然成为评价的对象,所列评价指标少则几十条,多则上百条,而且,还要想方设法使评价标准“全面、具体、可操作”。被评者埋怨这种“什么都评,什么都管”的素质教育评价,不是把教育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而是要引入到“应标教育”中去。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理解上的偏差。把“都能成为评价的对象”的东西,片面理解为“都要(或必定)”成为评价的对象;其二,概念上的泛化。在实践中,“教育”概念已从教师对学生所做的事,逐渐泛化到行政部门管的事、校内发生的事,甚至与学校有关的所有事。于是,评价也就要包罗这些“事”;其三,认识上的不足。把素质教育这个独立概念割裂成“素质+教育”,评价的对象也就分成为“素质”和“教育”两部分。
素质教育评价的对象主要是指素质教育现象。在具体的素质教育评价中,应该根据评价目的和教育实际,对评价的对象加以筛选,而不是“包罗万象”。筛选评价对象的关键,是抓住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抓住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和传统教育之间的区别。具体地说,应着重抓住四个“点”:一是“特点”。即:素质教育的自主、个性、创新、发展等特点;二是“重点”。即:素质教育的重点和学校实施工作的重点;三是“难点”。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难点,如:素质教育思想、素质教育目标分解、素质教育方法和学生素质测评等;四是“盲点”。即现实中尚未为人们所认识或所关注的事物。由于素质教育尚处在探索之中,这四个“点”是素质教育实践所追求的,也应该是评价活动所关注的。
误区之三:“抹杀个性”的评价模式
现实中,素质教育评价的基本程序是:设计评价方案——公布指标体系——组织现场评价——交换评价结论。而评价方案的设计思路,通常离不开“指标体系——评价标准——权重系数——量化方法——加权求和”这几个基本环节。显而易见,“这种评价模式基本上属于泰勒的目标达到度评价范畴,是一种预定式的评价。因此,方案本身不涉及价值取向,也不管被评者的价值取向如何。只要用这种方案评价,就得接受指标体系所规定的价值。”(注:金一鸣主编:《教育社会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这样,所谓素质教育的自主、特色、创新、个性化、多元化,也顶多是“戴着手铐脚镣跳舞”。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素质教育中竭力倡导的“张扬个性、合乎道德、多元价值”,又要用这种评价模式去加以“扼杀”呢?为什么我们还要热衷于使用这种评价模式呢?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国教育评价理论研究还相当贫乏,实践水平也不高。其实,现有的评价模式是多种多样的。诸如:国外的CIPP模式、决策模式、目标游离模式、相互作用模式、消费者导向模式;我国评价人员也创造出“两维三系复合”模式、协同自评模式等。而且,每种模式有它特定的功能,不存在“包治百病”的模式,因而,没有必要在钻进泰勒模式“圈子”里而不能自拔,而应该根据现实的需要有所创新,有所创造。
构建素质教育评价模式,我们主张充分体现素质教育的特点:其一,指标具有开放性。目前,尚未形成一种完善的素质教育理论,也不存在公认的、科学的和可靠的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需要拓宽思路,进行积极的探索。为此,应尽可能设计具有开放性的概括性问题,而少用封闭式的指标体系;其二,尊重多元价值取向。不同的人,对教育的需要不一样,他们的教育价值取向也不同。素质教育是个性化的教育,评价应尊重多元价值取向。这不仅要融化在具体的指标体系中,也要体现在“主体参与”的评价形式上;其三,与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素质教育评价主要是形成性的评价,是素质教育实践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因此,素质教育评价的模式,应该是与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
误区之四:“模棱两可”的评价主体
目前开展的素质教育评价,主要是上级行政部门评学校,学校评教师,教师评学生,当然,也可能增加了教师和学生的互评,在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的“他评”中,无形使被评者处于被动的地位,主要有三种表观:其一,等查待整,消极防卫;其二,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其三,被动应付,我行我素。即使在有些学校开展的“自评”中,也还是感到外部“干预”、“包办”太多。总之,在评价中大家经常感到“自己不认识自己”,评价者常常“越俎代庖”搞包办代替,主体意识在“角色错乱”中变得模棱两可。
谁是评价的主体?在“自评”中答案还是明确的,但在“他评”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颇有争议。有的从职权关系上看,认为上级部门才是评价的主体;有的从素质教育实施来看,认为学校应该是评价的主体;也有的从对立统一关系上看,认为评价者与被评者构成矛盾的统一体,互为主体。之所以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要原因:一是系统中确实存在着多种主体,活动主体、价值主体、评价主体之间容易造成混淆;二是由于“他评”多为自上而下进行,容易使人们在管理者、评价者、评价主体之间作出简单的“等价”替代;三是对评价主体认识不到位,不能分辨评价主体的“形”与“实”。科学确立素质教育评价的主体,不仅关系到评价的成效,更重要的是它还影响到素质教育的行为。如果评价主体不到位或变得模棱两可,素质教育评价必定是有害而无益的。
所谓评价主体,是指对有效地开展评价活动,实现评价目的和宗旨,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方面。显然,评价主体不等同于评价活动的主持者,也不等同于具体工作的评价者。那么,究竟谁是素质教育评价的主体?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素质教育的实践者才是评价的真正主体。在“他评”中,评价主体就是被评者。主要理由是: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来看,“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当然,评价者和被评者都是人,但他们在不同的层面和维度上,其“主体”的内涵是不同的。即使在评价的组织和实施中,评价者居支配地位,但要使评价成为被评者的自主、自为行为,就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主体意识。第二,从评价的运作过程来看,评价需要以大量真实可靠的信息为基础,以客观的价值需求和能力为依据,而这些只有被评者(即:素质教育实践者)最清楚、最明白,也最有发言权。离开了被评者主体作用,评价者就会束手无策。第三,从评价双方的相互关系来看,教育评价与其他评价不同,具有教育意义,因而评价者与被评者之间犹如“师生”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第四,从评价的根本目的来看,“评价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没有实践者的协助和积极参与,任何改革都不能成功。
误区之五:“舍本求末”的评价方法
素质教育评价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听、看、查、谈、问”,即:听汇报、听课;看校园校貌和设施设备,看文艺演出;查早已做好准备的资料、文件、仪器设备;个别访谈或召开座谈会;提问或问卷调查。然后,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整理和进行必要的简单计算,对照《评价实测表》(一种具体化、量化的评价标准和记录表)进行“对号入座”或“按图索骥”式的判断(通常是量化打分)。如此感观化的信息搜集方法和简单评价技术,不禁使人产生疑问:评价是否一定要专家?评价到底有多大的信度?
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评价方法的“舍本求末”,即:误把事实判断当价值判断,或用事实判断代替价值判断。美国学者格朗兰德(N.E.Gronland)认为:评价=量(或质)的记述+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基础,但事实判断并不等同于价值判断,而必须介入“人的需要”,才能作出价值判断。比如:要检查一所学校是否有三万册藏书,这是事实判断,也是容易做到的。但是,要作出“学校的藏书是否符合素质教育要求”,或者“学校藏书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学生素质教育活动的需要”这种价值判断,却是不那么容易的事。现实的评价中,我们是否曾有意或无意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判断混为一谈呢?
当然,现实中的评价方法受到三方面客观原因的制约:一是评价指标的片面行为化。“要判断目标的达到度,就必须强调指标的行为化、可测性,这样就很容易把被评价者的注意力引到指标体系所规定的那些行为上,只注意枝节的、具体的、零碎的行为,而忽视整体水平和内在素质的提高。”(注:金一鸣主编:《教育社会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行为化、人为量化的指标体系,只需通过感知就能获得所需信息,经过简单的算术运算就能作出所谓的价值判断;二是缺乏科学的评价工具。应该说教育现象主要是心理现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隐匿性和不定性,一般不便通过外在行为就能直接把握的,往往需要科学的心理测量、教育测验和教育统计。由于我们缺乏(或还没有掌握)这些科学手段,只能“土法上马”,依靠传统的经验;三是评价者并非是“专家”。教育评价是一项科学性、专业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工作,即使是业务能手、管理行家,也不能算是评价专家。目前,我国教育评价的发展刚刚进入专业化阶段,真正的教育评价专家还很少,评价活动中一般只能临时召集一些“准专家”。
教育评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废除“科举制”后却出现了“断层”。现行中的教育评价研究,只是改革开放后受到国外现代教育评价运动的影响才兴起的。“断层”恰好“跳过”了教育评价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教育测量运动。要想改变在评价方法上的简单化做法,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教育评价方法的科学性,我们必须老老实实补上“教育测量”这一课。
结语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观和教育实践,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也迫切需要从多层面、多角度进行探讨。在这种背景下,要对素质教育作出价值判断,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以为,素质教育评价要从根本上确立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对素质教育实践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有必要以人的素质为逻辑起点,以素质教育为核心,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只有弄清理念中的素质教育“是什么”,才能知道现实中的素质教育“怎么样”,评价也才会有正确的导向。“以己昏昏”的评价,绝不会“使人昭昭”的,而且,还很可能成为素质教育实践的羁绊。
在某种意义上,素质教育“就像为伤残儿童提供特殊教育一样。每一个孩子都有权得到适合自己能力的教育,那些具有天赋才能的孩子也应该得到适合于他们能力的特殊教育,以满足他们的智力发展需要。”(注:黄全愈著:《素质教育在美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可见,素质教育的实践总是具体的、多样的,是个性化的,也是创造性的。所以,素质教育评价也应该是切合实际的、价值取向多元的,是张扬个性的,也是具有开放性的。反思素质教育评价的误区,总结经验教训,有助于提高我们对素质教育的认识,增强我们走出困境、继续探索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