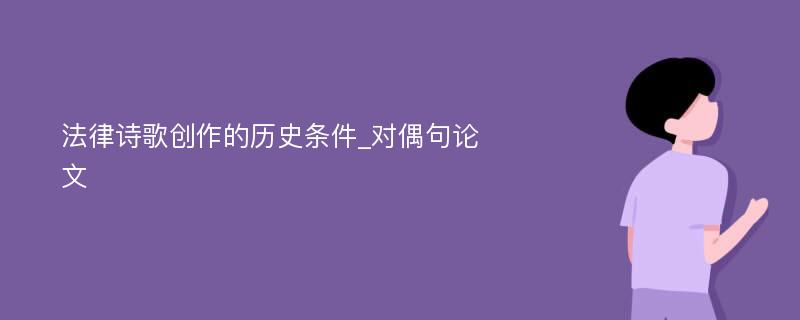
律诗创生的历史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律诗论文,历史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者们往往把律诗的创生归因于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说”的出现,这固然不错,但律诗的体制特征并非仅在声律的讲究。语言学家萨丕尔指出:“语言符号能容易地从一种官能转移到另一种官能,从一种技术转移到另一种技术,可见,单只语音并不是语言的基本事实。语言的基本事实毋宁说在于概念的分类、概念的形式构造和概念间的关系。……语言作为一种结构来看,它的内面是思维的模式。”[①]因此我们认为,对偶更是影响律诗之所以成为律诗的更为根本的条件。而在律诗出现之前,对偶已比较广泛地出现于赋的创作中,律诗采用对偶句法无可置疑地受到赋的影响。朱光潜先生早已论断:“中国诗走上‘律’的路,最大的影响是赋。”[②]但赋在西汉或更早的时代(《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荀子等人也有名为“赋”的作品)就已出现,朱先生没有详细说明何以到了魏晋南北朝,赋才对诗构成影响,对偶才成为诗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汉乐府、《古诗十九首》、苏李诗等却与对偶的自觉运用几近无关。这里自然可能存在一种文学样式对另一种文学样式产生影响的滞后效应问题,但最主要的应是诗歌转型—由古诗到律诗—的历史条件还不具备。
一、诗与乐的分离
沿着诗歌史的长河向上追溯,我们发现,先秦两汉时期虽有屈原、蔡琰等诗人,但更多的作品是无法找到它的主人的。这并非诗的作者喜欢隐名埋姓,主要是因为它是集体创作而成的,即它是民歌性作品,只有到了魏晋以后,文人作家才大量涌现。这一变化初看似无关紧要,细究却影响深远。民歌性作品在口头上创作,也往往在口头上流传,因此,诗与乐关系总是非常紧密;文人则在案头上创作诗歌,也往往把诗歌放在案头上阅读而不是演唱,因此,诗与乐的分离成历史的必然。诗与乐的分离使徒诗大量地登上文坛。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云:“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他的意思是说,曹植、陆机都写过不少乐府诗,但它们都不是用以供乐工演奏歌唱的,即都是徒诗。实际上,建安以后文人创作的诗歌,大多与乐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一直到隋朝,入乐的诗主要是民间的“清商曲辞”与“梁鼓角横吹曲”。
唐代以后,绝句与词是诗歌中与音乐关系特别密切的主要部分。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云:“唐之歌曲,用诗之绝句。”绝句有四句皆散者,叫散绝;有一二句用对偶,三四句用散句者,叫对散绝;有一二句用散句,三四句用对偶者,叫散对绝;有四句皆对者,叫对绝。四者之中,尤以散绝数量最多,约占全部绝句的三分之二以上,并且绝句之优秀者也以散绝为多。这就是说,绝句最为基本的形式为散绝。词与音乐之关系比绝句更密切,而词的最为基本的句式也是散句。似乎可以说,歌式作品以散句为主,对偶句不宜过多,而读式作品则可骈可散,在对偶句的运用上要宽泛得多。究其原因,大概有二:首先,音乐是声音在一个维度上的流动,为了有利于配乐演唱,与乐相配合的文字作品一般也要求语言平顺流畅,意义在一个维度上逻辑性地凸现,而对偶句往往展示共性存在的世界,意义在二维平面上并列呈现。其次,由于对偶句的出句与对句一般不具备逻辑上的关联(如因果、递进、转折等),它只是象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一样把两个相对独立的镜头“拼接”在一起,因此,其意义往往比较隐晦。配乐演唱是作用于人的听觉的,听觉在接受信号时要求信号的意义相对明白易懂,而视觉则无此限制。
《汉书·艺文志》载:“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作为赋的定义,这固然大而无当,但它却明确指出了赋的一个重要特点,即赋属于读式作品。因为属于读式作品,赋最早走上了骈偶之路。正因为魏晋以后,诗与乐分离成了较纯粹的读式作品,所以,才开始了与赋的大规模汇通,否则,对偶句大量地挤进诗中成为诗的一个重要特征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文的自觉与意义的淡化
鲁迅先生曾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③]文学自觉的前提是人的自觉。从汉末开其端,人不再是政治伦理道德的工具,而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他们感叹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痛惜百岁人生如露珠翻荷,努力追寻使人生过得更有价值的东西。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在这里,曹丕虽然把“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事”并举,但他论述的重点和当时及其后的文人真正关注的焦点仍是后者。而后者正预示了文学的自觉。在文学自觉观念的影响和推动下,讲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运作过程、文理的探求、作品的评议等的文章和著作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蔚为大观。虽然比较正统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里倡导文学要“宗经”“征圣”,但多数人迷恋的是形式的精致。这是一个“俪采百字之偶,价争一字之奇”[④]的时代,这是一个“由‘自然艺术’到‘人为艺术’”的时代[⑤],无怪乎被王船山称誉为“倾情倾度,倾声倾色,古今无两”的曹丕名作《燕歌行》,由于它象冲口而出“殆天授非人力”[⑥]的民歌式作品,而被钟嵘贬之为“率皆鄙质如俚语。”[⑦]
魏晋时期文学自觉了,但其后不久的大多数作家与生动的社会现实却隔膜了。建安作家大多饱尝乱离,亲眼目睹了社会上的种种惨象,感情浓郁而深厚,其诗作能抒写胸中的“慷慨悲凉”之情,内容丰盈,气势宏大。这是建安文学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建安作家被结合进曹氏集团后,安定优游,位高望重的贵族生活使他们失去了往日的激情,心灵之花日渐枯萎,文学也就成了他们手中日日赏玩的古董,华美形式成了他们注目的焦点。胡应麟《诗薮》曰:“自曹氏父子以文章自命,宾僚缀属,云集建安。然荐绅之体,既异民间,拟议之词,又乖天造,华藻既盛,真朴渐离。”而这正预示了其后作家的命运。晋以后的作家大多生活在上层,不是自当庄园主,便是做有庄园者的清客,感情比其前辈淡薄了。他们重艺轻道,重文轻质。于是,在陆机等人的诗作中,对偶作为形式追求的一个方面大量地出现了。如《赴洛道中作》其二: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街思往。顿辔倚高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几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而且,此诗中的对偶句是在同一意义层面上集中出现的。与魏晋以前的作品中运用对偶不同,它不再象匆匆赶路的行客偶而驻足一瞥沿途风光就继续前进,而是较从容地休憩下来环顾四周美丽的景色。但这也仅仅是开始,至南朝宋时的谢灵运等,甚或出现了几乎全篇皆对的空前盛况。
《蔡宽夫诗话》云:“诗语大忌用工太过。盖炼句胜则意必不足,语工而意不足,则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这大致不错。但反过来说,由于“意不足”,更有利于作家“炼句”,也不无道理。大可不必为此惊诧,其实这不过是事物的一体两面而已。“意太足”往往限制作家对文学形式自身精致化的追求,正如人们对自由挥洒的过分追求会破坏美丽的舞步,对牧童野老牧歌式的歌唱方式的过分追求会影响音准高低一样。因为,作家只注重如何把意义表达得准确、完整、条理清晰,每每忽略如何把话说得含蓄委婉精妙。作品意义淡化(即作家感情的淡薄)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作家能把注意力更多地给予形式精致化的追求与探索,从从容容地思考如何使形式精美雅致。因此,文的自觉和作品意义的淡化促进了对偶艺术的成熟与发展。
三、自然美的发现
汉末,人们对自然美的欣赏还没有进入自觉阶段,而是借山水以为精神的慰藉。正如钱钟书所言:“荀以‘悦山乐水’,缘‘不容于时’;统以‘背山临流’,换‘不受时责’。又可窥山水之好,初不尽于逸野兴趣,远致闲情,而为不得已之慰藉。达官失意,穷士失职,乃倡幽寻胜赏,聊用乱思遗老,遂开风气耳。”[⑧]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庄、玄、佛盛行,成为文人必不可少的修养,“以形媚道”[⑨]的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山水自然美终于成为人的自觉的审美对象。《世说新语·言语》篇载:“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晋书》卷五六《孙绰传》载:“(绰)居于会稽,游山放水,十有余年。”“(统,绰之兄)性好山水……纵意游肆,名山胜水,靡不穷究。”而且,于游赏山水之时,每每吟咏。《晋书》卷三四《羊祜传》载:“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孙绰《游天台山赋》也说自己:“于是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凝思幽岩,朗咏长川。”晋宋之际,自然不仅被自觉地作为审美对象,而且闯入了艺术的殿堂,日渐成为演出的主角,以至对“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⑩]感到诧异。
严格意义上的对偶,不但句子结构和相对应的词语性质基本对等,而且奇偶两句的意义应是平行的、并列的、相对的。如果句子结构和相对应的词语性质都基本对等,但意义仍一气流贯,奇偶两句仍具有逻辑上的因果、递进、转折等关系,就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对偶,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等。散句基本上是一种线性的叙述,对偶句却是面性的描绘,因此,散句长于叙述发展变化的事件,抒写流动不羁的激情,阐释逻辑性很强的理论,而对偶句则长于描绘共时性存在的自然风光或情景。如王维《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唐汝询《唐诗解》云:“此奉使出塞而赋其事。”看诗的首联与尾联(散句),确实无异于一般的叙事诗,但颔联和颈联由于运用了对偶,却几乎无事可叙,事的色彩淡化而成了境。
由此,我们发现谢灵运等人的诗作充盈着丰富精工的对偶是与其描绘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日本学者古田敬一在其《中国文学的对句艺术》一书中指出:“其(指谢灵运——引者注)表现形式几乎全是对句。大概如不是用对句的形式,象这样充分的写实的自然描写是不可能的。只有借助对句的表现形式,才可能整体地描绘美的自然。”朱光潜更肯定地说:“文字排偶不过是翻译自然事物的排偶。”[(11)]的的确确,在诗歌领域,晋宋之前,山水自然不过是运用比兴的手段或事件的背景,诗人写山水自然往往浅尝辄止,对偶句法很少运用;晋宋之际,“山水方滋”,自然美成了诗歌直接描绘的对象,对偶句法也就被诗人大规模地运用了。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自然美的发现,自然闯入艺术的殿堂并成为直接的描写对象,为对偶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可以驰骋的“练兵场”,促进了对偶艺术的成熟。
谢榛《四溟诗话》云:“律诗重在对偶”,高棅《唐诗品汇》云:“律体之兴,虽自唐始,盖由梁、陈以来俪句之渐也。”王力在其《汉语诗律学》中也指出:“对仗是律诗的必要条件。”作为构成律诗的两大基本要素:声律和对偶,缺一便不可能形成律诗[(12)]。正如植物生长得茂盛与否,取决于土壤中的空气、水分和营养元素等的合理配置,魏晋南北朝时期上述三个历史条件的同时具备与互相配合,无疑有利于对偶的大量涌现与日渐成熟。声律与对偶的探索,使唐代律诗的出现成为水到渠成的必然之事。
注释:
①萨丕尔《语言论》,第13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② ⑤ (11)朱光潜《诗论》,第202页,第201页,第205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③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之关系》。
④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⑥王夫之《姜斋诗话》。
⑦钟嵘《诗品》。
⑧钱钟书《管锥编》,第103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⑨宗炳《画山水序》。
⑩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
(12)绝句以散体为主,归入近体诗则可,归入严格的律诗则枉;律诗亦有全首不对格,前人或誉为“以古行律”,或讥为“平仄稳贴之古诗”,是为律诗之变格。
标签:对偶句论文; 文学论文; 律诗对仗论文; 对偶理论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作家论文; 律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