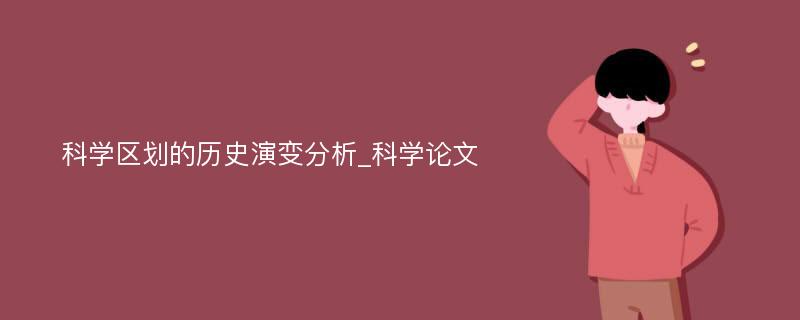
探析科学分界的历史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界论文,探析论文,科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65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4)03-0046-05
所谓科学分界(Demarcation of Science)就是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作出区分。[1]波谱尔(K.Popper)认为,分界问题是解决科学哲学中许多基本问题的关键,因此,要找到一个标准,使我们能够按照这一标准把经验科学与数学、逻辑、“形而上学”等等区分开来。
任何企图解决科学划界问题的方案都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科学和非科学有没有划界标准?2)如有标准,具体的划界标准是什么?3)划界标准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确定的还是模糊的?4)进行划界的出发点(目的)是什么?5)科学划界的单元是什么?是根据理论去区别还是根据更复杂的对象如科学实践去区别?[2](P1)
最早提出科学分界标准的是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家们。波谱尔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作了系统的探索,在西方科学哲学家中,他对该问题作了最全面的研究。[3](P13-39)自标准科学哲学诞生以来,关于科学分界的理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逻辑主义的绝对标准—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无政府主义和后现代哲学的怎么都行标准—新实在论重建的多元标准。
一、逻辑主义的绝对标准
所谓逻辑主义是指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因为他们都奉行逻辑和理性。对科学分界问题,从石里克(M.Schlick),卡尔纳普(R.Carnap),亨普尔(C.G.Hempel)到波谱尔,他们都承认科学和非科学有明确的一元标准,而且都想通过划界来拒斥形而上学和伪科学、假科学,只是在采用的标准问题上,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是可证实性,而批判理性主义认为是可证伪性。
逻辑实证主义者用意义标准来解决分界问题。他们认为凡是一个命题是有意义的就是科学的,无意义就是非科学、假科学和形而上学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与非科学或形而上学的分界标准就是经验证实原则:即任何命题,凡是能被经验证实的,就是科学的;凡是不能被经验证实的命题,就是非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
维特根斯坦说:“一切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命题是非命题或假命题,他们是无意义的。有意义酌命题可完全归结为基本的或原子的命题,后者是描述可能事态的简单陈述。”用什么标准来区分命题的有意义和无意义呢?答案是可证实性。“有可能处于科学领域的陈述是可被观察陈述证实的陈述。“[4](P40)
可检验性和意义问题,是逻辑实证主义最关注的课题。他们试图消除形而上学,想要改造哲学,他们企图使哲学成为科学,从而实现哲学的逻辑分析任务。他们试图引导哲学家和科学家避免陷入徒劳的无意义的探求中。可以说,可检验性和意义问题构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石,这一基石是由石里克奠基,而后的卡尔纳普、艾耶尔(Ayer)、亨普尔等人为修补和挽救这一原则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波谱尔等人的强有力的批判下,逻辑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步步后退,不断弱化。也就是说,从科学划界的角度看,逻辑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经历了一个不断软化的过程,卡尔纳普以“可检验性原则”取代石里克的“可证实性原则”,艾耶尔提出用“弱的可证实性”取代“强的可证实性”。波谱尔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错误在于:第一,用一个假问题代替了一个真问题。意义问题是一个用词问题,分界问题的实质是问题和事实,理论和假说及其所提出和所解决的问题。第二,可证实性就是观察陈述的可推演性。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定理、理论是从观察陈述中推演出来的。波谱尔认为,科学定律、理论都是全称陈述,这种全称陈述不只是无数单称陈述的相加,因此它们不可能从观察陈述中推演出来,也不可能被观察陈述证实。第三,可证实性标准“既窄又宽”,“窄”是指它把一些科学理论从科学中排除出去了,因为这些理论不能在逻辑上归化为单称的经验陈述;“宽”是指像占星术、理性宗教那些假科学却可以钻人科学的大门,因为它们都可以声称它们都得到过经验的证实。第四,实证主义把形而上学当作毫无意义的胡说排除,但这办不到。因为形而上学不是没有意义,并且有时还会转化为科学。
波普尔把可证伪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但他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是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以相互转化。波普尔关于科学与非科学分界标准的思想,为他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分界标准针锋相对,但许多方面是相同的,譬如,他们都相信有一个单一、绝对、确定的分界标准;他们都把经验看作是可以不需要再检验的基石。
二、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
逻辑主义的过分简单化的绝对标准很快就遭到来自各方的批判。随着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的兴起,科学划界成了一个必须诉诸历史分析才能解决的问题。科学哲学家倾向于放弃寻找超经验的、超历史的划界标准的努力,通过探索科学合理性问题来回答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问题。历史主义主要包括库恩(T.kuhn)和拉卡托斯(I.Lakatos)两个代表人物。
库恩的分界理论是从批判波普尔开始的。他首先强调了他与波普尔在科学观上的一致性:1.都关注科学发展的动态过程,而不是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2.反对科学累积观,强调科学革命观;3.反对经典实证主义,强调观察渗透理论。[2](P31)
但在科学分界问题上,他们却产生了分歧,库思对波普尔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批判:1.划界基准单元不应放在理论和陈述上,而应放在科学的实践上,应放入具体的历史中;2.他过分强调革命因素而忽视了大量的常规研究,波普尔的可证伪性主要表现在革命时期,而在常规时期却难于把科学和非科学区分开来;3.波普尔把批判当作科学所特有的个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如哲学、艺术等学科也有批判的特征。库恩把心理、社会、历史、价值观等引入其中,形成了自己的相对主义的划界标准:“在检验与释疑这两个标准中,后者既更加准确,也是更加基本。“[5](P8)“只要仔细关注科学事业就会发现,正是常规科学而不是非常规科学,最能把科学与其他事业区分开来。”[5](P8)
库恩的分界标准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释疑”活动所依据的范式,包括形而上学的信念和其它社会、心理、价值的因素,因而科学和形而上学、科学与非科学难于清晰划界。仅仅在常规科学时期的释疑活动中科学与非科学得于暂时的划分。在“科学革命”时期,原有的界限被打乱,随着范式的更替,科学的标准也随之而改变。第二,科学共同体是“释疑”的主体。一切知识都是某个共同体的知识,一定的科学共同体在特定的时期认为科学而合理的东西,就是科学的和合理的。
拉卡托斯对库恩的科学观是肯定的,尤其是对库恩以历史观点去分析科学现象,把科学理论看作有结构的变化过程,把科学看着一个开放系统,注意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影响,重视科学发展的稳定性与革命性相结合等。但是他认为库恩走向了极端,太强调非科学因素(主要指科学家个人的心理特点与“科学共同体”的社会特点,也包括信仰因素。)对科学发展的作用。他不同意库恩把科学革命看作“信仰上的非理性变化”或“宗教的改宗”。他在这方面倾向于波普尔的理性原则,认为科学革命中新旧理论的更替主要决定于理性因素,特别是决定于科学预见力。因此他批评库恩否定了一切关于知识的理性重建的可能性,并指责库恩有“非理性主义倾向”。
拉卡托斯从其“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出发,把划界问题软化为“评估”问题,是相对主义划界标准的典范。他把有关科学划界的理论区分为怀疑论、精英论和划界主义,并对前两者做了批判,对第三种也作了批评和修改。[2](P31)那么拉卡托斯的划界标准是什么呢?首先,就划界的单元而言,拉卡托斯把波普尔的理论还原成了历史的理论系列,即“研究纲领”。研究纲领由“硬核”(Hard Core)和“保护带”(Protective Belt)构成。研究纲领采用“反面启发法”(Negative Heuristic)和“正面启发法”(Positive Heuristic)两种方法论规则。其次,划界(评价)单元的扩大,拉卡托斯从历史观点出发,不但把科学研究纲领看作是一个有结构的整体,而且还认为它有一个发生、发展以至衰亡的历史过程。
从库恩和拉卡托斯这两位相对主义的代表人物的思想来看,逻辑主义的绝对标准开始被动摇了分界的标准也没有开始那么清晰了。
三、无政府主义及后现代哲学的“怎么都行”标准
如果说相对主义对科学分界的标准还只是动摇的话,那么到了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那里,就把问题彻底取消了。他根本不承认科学和非科学有什么明确的分界线,抛出了“怎么都行”的纲领,并且号召大家起来“打倒科学帝国主义”。当然,如果只是费耶阿本德一人持这样的观点,恐怕他也孤掌难鸣。问题是,由于劳丹(L.Laudan)以及SSK社会建构主义的推波助澜,费耶阿本德的一把火立即成为燎原之势。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知识的进步是有害的。如果要理解自然,要支配我们的物质环境,那么我们一定要使用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方法,而不仅仅使用其中的一部分。关于科学之外无知识的断定只不过是又一个童话而已。”[6](P306)他说,认为科学能够并且应该按照固定的普遍规则进行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有害的、对科学不利的。首先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对人的才能及其发展条件持一种过分简单的观点;其次是有害的,因为坚持规则的努力只能提高我们的专业资格,却必定以牺牲人性为代价;最后是对科学不利的,因为它忽视了影响科学变革的复杂的外部和内部条件,使科学更不适应、更为教条。在费耶阿本德看来,所有的分界标准都有它们的局限性,因此,留下的唯一规则是:怎么都行!科学分界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知识的进步是有害的这一断言有双重含义:论证科学分界是“人为的”属于分析的层面,说科学分界是“有害的”则属于“评价”层面。实际上费耶阿本德正是从这两个层面去论证他的消解划界观点的。[2](P35)在分析论证中,他申述了自己的两条原则:反一致性原则和不可通约原则,它们分别指是科学的方法论特性和理论形态的特点。上述两条原则又是以费耶阿本德自己的意义理论为前提的。
费耶阿本德得出结论说,不阻碍科学进步的唯一原理:怎么都行。他说,我们要探究的世界主要是一个未知的实体,因此,我们必须使我们的选择保持开放。他提倡一种多元的方法论,反对把任何确定的方法、规则作为固定不变的和有绝对约束力的原理,用以指导科学事业。因为没有一种方法、一条规则能避免有朝一日在某个场合遭到破坏的厄运。固定某种方法程式,不但不能自然而然地得到满意的科学结论,而且迟早会阻碍人们有效地作出科学新发现。科学无法也没有必要与其它文化形式区分开来。所谓“无法”是指,科学方法是“怎么都行”,科学理论又是相互之间“不可通约”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幅各自为政的科学图景,科学自身并不统一,对此提出一个“科学的本质标准”是不可能的。
劳丹发现,不同时期的科学就像不同时期的绘画一样,具有“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注意,寻求划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不存在一个可以作为划界标准的认识常量。称为“认识论中心问题”的划界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
在SSK建构主义者眼里,科学也只是一帮叫科学家的“工匠们”制造出来的东西,并不比其它文化更特别。因此他们否认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有什么泾渭分明的区分标准。在无政府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浩大声势打击下,科学分界问题逐渐成为昔日黄花。
四、新实在论重建的“多元”标准
消解科学分界问题,也还只是一部分科学哲学家的主张,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哲学家们正在为更好地确认和解决这一问题而努力。其中加拿大科学哲学家M·邦格(M.Bunge)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们把确立科学分界的目的做了调整,关注的是伪科学对文化的危害而不是科学的文化权威。
M·邦格指出,“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容易把伪科学,甚至反科学当作无害的东西,或者当作可供大众消费的东西。这种态度是错误的。首先,伪科学和反科学并非通过循环处理就会变成有用的废物,它们是思想的病毒,可以侵袭包括普通人在内的任何人,使整个文化瘫痪。其次,伪科学和反科学的兴起与传播是重要的社会心理现象,他们可以作为文化健康状态的标志。最后,伪科学和反科学是任何科学哲学值得加以检验的典型问题。”[7](P51)
M·邦格认为,历史上的科学划界方案之所以难于让人信服,是因为大多数哲学家都试图以一元标准(一种特征)来划分科学与分科学。科学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不可能只用一种特征来表明,伪科学也一样。判断一种知识是不是科学需要考察它的许多特征。为此,M.邦格提出了他所谓“精确的”多元划界模型.[7](P51)
帮格对知识领域定义为E=(C,S,D,G,F,B,P,K,A,M)
就任何特定时间而言,E=特定的知识领域
C=确定知识的社团(共同体)
S=承认C的地位的社会
G=C的总体看法,世界观或哲学
D=E的论域即E所谈论的事物
F=E的形式背景即E所使用的逻辑或数学工具
B=特殊背景或从其它知识领域借来的有关D的一组前提
P=问题组合或E可能处理的一组问题
K=E所积累的特殊知识储备
A=C在对E的提高上所抱的目的或目标
M=方法体系或E中所有可用的方法
M·邦格通过上述十个元素的组合制作了一个评估表,用来评价、区分科学与非科学或伪科学,并认为科学分界问题由此得到解决。
从上述划界模型看,帮格为科学与伪科学设立的是严格的充分必要条件。他指出不满足他的定义就是科学或伪科学以外的东西。他没有说明,如果一个知识领域部分满足、部分不满足时怎么判别?或者这些指标能否量化?如能,又如何量化,如何判决?
M·邦格承认科学分界问题的存在,并认为在当代尤为迫切和重要。他在批判以前各种划分的基础上提出分界标准应是多元的,分界单元应是“知识领域”,而且这种多元指标应满足充分必要、精确指标化的条件,以便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但是,他的分界指标体系虽然看起来精确无比,但实际操作时照样主观、随意,难以操作。
总之,科学分界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历经了从确定到模糊,从单一到多元,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嬗变。科学分界问题和科学活动本身一样,是历史的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水平上。任何分界标准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它们之间可以取长补短,具有互补效应。
收稿日期:2003-0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