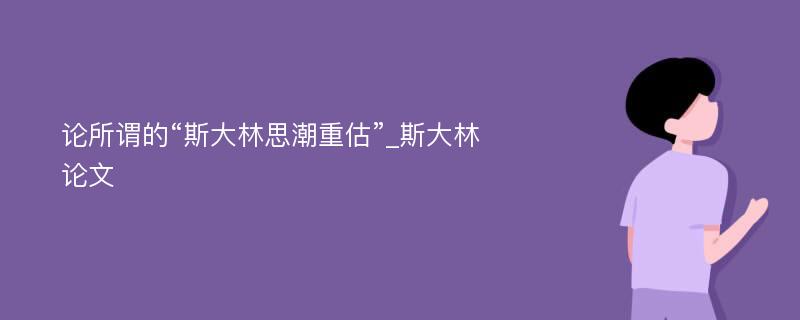
再论所谓的“重评斯大林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7)04-0056-15
近年,我国学术界围绕俄罗斯的所谓“斯大林热”,存在不同的解读。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俄罗斯在“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斯大林[1];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俄罗斯“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2]。这个问题,对于熟悉俄罗斯及其学术界情况的绝大多数学者,原本是一个不难分辨的一清二楚的问题,但因这个问题近年被掺杂进了俄罗斯民意调查中一些带有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因素,反把这个问题弄得让不太熟悉俄罗斯及其学术界情况的人们大惑不解了。由于这是通过现实社会政治思潮的棱镜,反映出的一个历史问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相互纠结,二者错综掺合在一起,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它的复杂性。既然它是历史问题与现实思潮的掺杂纠结,学术问题与民调中非理性、情绪化的因素相混淆,就需要将二者加以分析,对它们既联系又区分地加以对待。而且要搞清所谓俄罗斯“斯大林热”的意涵,也不能仅仅就事而论事,更重要的,是须放眼产生这个问题的社会政治背景,放眼学术界对整个斯大林问题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把问题辨别清楚。
在分析评价斯大林问题时,我认为,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评判之,而不能用俄罗斯民族爱国主义的价值观来看待他。因此,这个评价、判断的标准和价值观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俄罗斯近年出现所谓“斯大林热”的社会政治背景
(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出现的各种危机,促发了所谓“斯大林热”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衰退,国力下降,人口减少,社会动荡,凶杀案和恐怖事件频频发生,不仅民众生活普遍降低,连生命安全也受到巨大威胁。所有这些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直接促发了俄罗斯的“斯大林热”。
自从波罗的海三国、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而独立以后,俄罗斯的版图实际上又退回到17世纪初的彼得一世时代。它失去了气候温暖而又富裕的南方,用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的话说就是,苏联解体又把俄国人赶入了冰天雪地的寒带。
国家解体不只失去了大片国土,还丢失了一亿多人口,失掉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出海口和黑海一带的天然良港。这使俄罗斯几百年打开出海口的努力化为乌有,加上经济大滑坡,工业衰败,一下沦落到了几乎二流国家的地步。苏联解体后十多年来,俄罗斯经济危机严重,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急剧下降,贫困者经受着生活困厄的煎熬。
俄罗斯社会领域也危机重重,出现了灾难性恶化的局面,表现为社会保障体系崩溃,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酗酒、吸毒和卖淫成为社会的痛点,精神病人、流浪儿童和无家可归者大增。据统计,近些年俄罗斯即使不计算酗酒和吸毒者,心理病人总数达400万,流浪儿童达200—300万,无家可归者也有数百万之多[3](p7)。90年代末,妓女总数为300万人,其中每年有25万人以上到国外从事卖淫。俄罗斯学者痛心地说:“这样的奇耻大辱,我们国家在历史上还没有过。”[3](p8)
国家权力削弱,法制体系松弛,社会犯罪严重,恶性抢劫杀人案逐年攀升。每年有二十多万人被杀,人人无安全感,天天为自己、为家人和亲朋的性命担忧。
人口减少也成为严重的社会痛点。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升高。如果按现有人口发展趋势,一些学者预测,到2050年人口就会缩减到1亿,届时俄罗斯将“对控制自己幅员广大的领土已无能为力”,有学者认为,有的地方可能成为外来势力的托管领地[3](p14)。
所有这一切,是俄罗斯人过去连做噩梦都想不到的。所以,目前俄罗斯人具有严重的民族危机感。近些年,他们一直在探寻出路。试想,以俄罗斯人大国主义的历史传统,以其素有的民族性格和强国情结,他们会怎么选择出路?千条万条,答案归到一条:就是要有强有力的铁腕人物,要有强大的国家权力。所以,俄罗斯人呼唤铁腕、期盼强权,渴望出现一个像斯大林那样的人物来治理国家,整顿社会,重建世界大国、强国地位。呼唤“第二个斯大林”,这成了近十多年来发自许多俄罗斯人心底的一个呼声。
这是目前俄罗斯发生所谓“斯大林热”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
(二)俄罗斯当权者企图寻找“国家思想”的定位
从沙俄时代到苏联时代,俄罗斯都有这样一个传统,即要有自己的“国家思想”,或者说官方意识形态。在尼古拉一世时,曾有“专制制度、东正教和人民性”三位一体的国家思想。苏联时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自苏联解体抛弃其原有国家意识形态后,从叶利钦时期起,就开始探索“国家思想”。从叶利钦到普京,在寻找“国家思想”定位当中,先后有过下列几次调整:
——苏联解体之初,采取的是西方自由主义。当时,极端民主派得势,面向西方,向欧美靠拢。但休克疗法改革的破产,使极端民主派遭到沉重打击,他们依靠的那种西方自由主义也随之失去了吸引力;况且,俄罗斯有自己本身的传统文化,全盘照搬西方的东西,跟着西方的屁股转,也为俄罗斯所习惯了的大国地位所不容。
——大约90年代下半期至本世纪初,又探索过欧亚主义思想。俄罗斯古代,特别是鞑靼蒙古入侵,给俄罗斯带来的东方传统更多一些。但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沾染的西方基因又使它瞧不起东方。同时,这种欧亚主义起不到振兴民族精神、重建大国地位的那种鼓舞作用,所以有迹象表明,官方又放弃了欧亚思想。
——普京上台后,“国家思想”定位渐渐明朗,被确定为“强国思想”,或叫大国主义。这就是以俄罗斯强国主义、大俄罗斯自豪感为中心,高扬俄罗斯的光荣民族传统,重建它的世界强国地位。在用民族主义鼓舞人心,以期恢复其世界强国、大国地位过程中,斯大林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就成了可资利用的重要精神资源。
普京用“强国思想”定位自己的“国家思想”,同民众渴望用铁腕和强权治理国家,以期恢复秩序和稳定的目的相吻合。由于他的官方思想定位与广大民众的愿望正相契合,所以,普京受到目前俄罗斯人的普遍欢迎和支持。普京的这种“强国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中派主义或者中间主义:既不是右翼的自由民主主义,也不是以俄共为代表的左翼共产主义。普京目前受到俄罗斯民众的广泛支持,就是因为他所持的这种中间主义立场。他选择这种思想定位,也与争取大多数选票有关。这说明,大多数俄罗斯民众是抱这种思想的。
普京上台后,这些年的几乎所有内外政策行动,都可以用这种以俄罗斯民族主义为中心内容的“强国思想”来解释。
他在2000年5月7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应该了解自己的历史,应该始终记住,是谁建立了俄罗斯,是谁捍卫了俄罗斯的尊严,并使俄罗斯成为一个伟大而强盛的国家。我们应该保持这些记忆和时代的连续性,将我们历史上最优秀的传统传给我们的后辈[4]。稍有一点俄国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为建立并捍卫俄罗斯、为俄罗斯跃居伟大强国作出贡献的人物中,理应包括从留里克、莫斯科大公、伊万雷帝到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等等在内的所有人;当然,其中也包括仅在二战前后就为俄罗斯扩大版图达数十万平方公里,使俄疆域超过任何一位前任者的斯大林。要知道,这实际上是把斯大林放在同俄罗斯历史上封建帝王并列的行列里评价的。普京从这个视角肯定斯大林,就是用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国主义的价值观对他进行评价的。须知,斯大林也配得上被列入这一行列,从这一视角被评说。因为他事实上为俄罗斯帝国的开疆拓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思想中也有相当浓厚的大俄罗斯主义思想,列宁就曾对他这种思想作过严厉批评。
普京强国主义的思想和行动还表现在,2003年举行的俄军洲际导弹演习,是彰显俄罗斯大国、强国地位的一次引人注目的空前行动。普京2005年邀请各国元首参加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并举行举世注目的大规模庆典,更充分显耀了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普京总统曾多次暗示,最好改写历史教科书,向青年人展现俄罗斯昔日的辉煌。用强国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这一思想线索贯穿教科书,这是与他的“国家思想”定位相适应的。
上述这一切,都贯穿着“强国主义”这一当今俄罗斯国家的官方思想。用这一思想,即俄罗斯强国思想、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几乎可以解释普京和俄罗斯官方对斯大林的一切评价。普京对斯大林在二战中功绩的肯定,就出于这一思想。俄杜马主席、政权党领袖格雷兹洛夫在斯大林诞辰125周年时,称赞他是“一位非凡人物”,也主要是指斯大林在二战中的贡献和这期间取得的强势外交谈判地位,这无疑也是从民族爱国主义立场评价的。俄议会的一个重要派别,以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民族主义派,把十月革命骂为“黑暗”、“罪恶”,把包括列宁在内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领袖,个个骂得狗血喷头,唯独赞颂斯大林,这更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强国思想”。就连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将斯大林歌颂为“不仅是俄罗斯20世纪历史上,也是整个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这样说,不言而喻是认为斯大林的地位超过了列宁——这也是从俄罗斯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来评价的;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出发,我们是不能同意这一观点的。
当然,俄罗斯在当今出现的这种以强国主义为内容的民族主义,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发生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引起民族沉沦和国家地位下降造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民族主义向来是依据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态度的。对待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强大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对待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持不同立场的。对于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自我保护性质的民族主义,向来是持同情、理解和支持态度的;对待强大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带有进攻性质的民族主义,向来是持反对态度的。俄罗斯目前的民族主义,应该说与它在沙俄帝国时代和苏联时代的民族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不能不加分析地、笼而统之地视之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因为它是在处于某种弱势地位时带有某种自我保护意味的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给予一定理解和同情。但是,由于传统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由于俄罗斯人传统的大国主义和强国情结,对他们这种民族主义又不能同弱小的、被压迫民族的自我保护的民族主义完全等而同之;在他们这种民族主义之中,不能不说含有某种原来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积淀成分在内。因此,我们应当有所分析,有所区别,对其不同成分采取不同态度,而不能笼统予以同情和支持,或一概予以批判和反对。
我们知道,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一向被视作“无产阶级的导师”,这是斯大林的主要身份,也是他整个生涯活动的本质方面;如果仅仅用上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评价标准,即从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国主义观点评价斯大林,不能说是对他的正确评价和真正歌颂。这样来评论斯大林,恐怕连斯大林本人也不一定会认同。大家都记得,斯大林1931年在同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的谈话中,对于这位作家把他同彼得大帝所作的比较,斯大林是不同意的。斯大林说,彼得大帝是为商人和地主的“民族国家”,而他是为工人阶级,“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说,要巩固国际主义国家”。因此,他认为这位作家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是不恰当的”,他只愿做“列宁的学生”。他还说:“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么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这个大海。”[5](pp93-94)这个时候,斯大林还是比较谦虚和清醒的,他对列宁的评价是正确的,对他自己的认识也是冷静的。按他这种评价,他也比彼得大帝伟大得多。而现在,我们有些学者,对俄罗斯当今把斯大林放在同封建帝王同一行列里评说,似乎就高兴得不得了,认为这是“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不,这仅仅是把斯大林作为继承俄罗斯帝国遗产和传统的大国领袖来评说的,不是高抬,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贬抑;当然,就斯大林的这一身份来说,这也是对他不失恰当的一种评说和谈论。
而对斯大林主要的身份、本质的方面,俄罗斯官方又是怎么评价的呢?据俄塔社莫斯科2005年5月6日报道,普京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说,“斯大林时代发生了诸多罪行:政治镇压、许多民族的人受到驱逐。这一评价是原则性的。”普京又说,这个时代的教训之一就是独裁,压制自由,这使国家和社会走上了绝路[6]。普京对斯大林的定性,就是“独裁者”。俄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说,斯大林“在国内政策方面所采取的过火行为并不光彩”[7]。从俄官方代表人物这些言论看,恐怕不能说俄官方是在“重新评价斯大林”。很显然,普京总统等对斯大林的本质方面,即国内政策方面,搞社会主义的这个方面,是基本否定的。
对于斯大林这个历史人物来说,哪一身份,哪个方面是更主要,更本质的呢?无疑,是他作为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运的领袖,是斯大林体制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创建者这一方面,这才是他的本质属性。而恰恰在这一方面,普京和俄罗斯官方对他是持基本否定态度的。这难道能说俄罗斯官方是“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吗?
下面,再让我们看看俄罗斯学术界是否“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斯大林。这只有从俄罗斯学术界近年对斯大林的研究情况来了解。
二、俄罗斯学术界近年对斯大林的研究和评价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至21世纪初,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变化,决定着俄罗斯学术界历史研究态度的改变,因而发生了对俄国历史和现状的重新评价。这期间,随着戈尔巴乔夫完善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史学界的改良—修正学派为自由民主派所代替。而在1992年以后几年,随着休克疗法—激进改革遭受严重挫折,西方自由民主派的史学观又陷入危机。大体在90年代后期,新的史学观——文明观开始抬头,欧亚主义为人们所重视。但俄罗斯的政治意识形态多元化,使史学界的各种思想派别出现多元并存的局面,有新自由主义派、新保守派、新欧亚派和传统—乡士派等等[8]。
在这种史学流派纷呈并存的情况下,俄罗斯史学界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各说各话,很不一致的。但我们应该着眼并把握史学界的主流、基本趋势、基本看法,而不能用举例论证的方法,把少数思想流派的观点作为史学界的主流。
那么,怎样把握史学界对斯大林问题研究的主流呢?这应着眼于俄罗斯史学界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几个主要问题的研究和评价上。
(一)对斯大林体制的评价
对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是属于何种类型的问题,俄罗斯“历史学家多将其视为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①。学术界大多倾向认为,极权主义制度具有一系列关键的特征,如对社会实行绝对和全面的监督,一党专政,极度中央集权,压制异己思想,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民众的支持,等等②。
但同时许多学者也认为,斯大林体制的建立不能简单归咎于斯大林一个人的责任,它包含有俄罗斯传统和革命后果方面的因素。有的学者也指出,斯大林体制“是所有社会力量情绪和活动的综合产物”。不过,许多史学家也同时指出,不能忽视斯大林在这一体制形成中的个人作用[9]。
除了对斯大林体制的上述评价外,原改良—修正学派的“行政命令体制说”,还在一部分学者中间流行和存在。
(二)对工业化的评价褒贬参半
大多数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苏联工业化存在客观上的要求,是苏联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落后状况所需要的[10]。但认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框架内实行加速工业化的方针,是可行的;而斯大林却中断了新经济政策,实行了消极后果较大的加速工业化方针③。这一方针引起轻重工业、工农业严重失衡,社会过度紧张,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非常措施。也有不少人认为,工业化很快改变了苏联的落后面貌,对二战的胜利起了支撑作用[11]。总体上,史学界对苏联工业化有褒有贬,但肯定者还是不少的。
(三)对农业集体化基本否定
俄罗斯大多数史学家对使用强制、暴力手段实行集体化,消灭富农的政策,是完全否定的④。他们认为,集体化的完成使苏联社会变成两极化,一极是官僚支配着集体农庄的财产;一极是失去基本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
(四)对大清洗完全否定
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30年代大镇压是苏联国家的悲剧,普遍给以否定。认为正是这一大镇压,使苏联最终确立了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制度⑤。
近十多年来,大清洗是俄罗斯学术界研究和出版的一个热点,出版了数百种达上千册有关苏联惩罚制度历史和包括各种资料的著作⑥。研究的问题涉及大恐怖时期的死亡人数,劳动营、教养所、监狱和特别流放的总人数,等等。也出版了有关大规模镇压、劳动营制度和特别流放制的多卷本文件集。俄罗斯各地区普遍出版了有关镇压情况的资料性和研究性著作,仅普斯科夫一个地区就出版了有关他们那里镇压情况的15集资料,萨马拉出版了14卷集,鄂木斯克出版多达6卷集,斯摩棱斯克有4卷集,等等。
2004年莫斯科出版了《苏联政治清洗受害者电子画册》[12],该画册“为两个光盘,上面载有134万多苏联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名单”。据画册出版者负责人、“纪念协会理事会”主席阿尔谢宁·罗根斯基在发行仪式上所说:“在收集起来的资料中还有许多没有发表。按最小数字统计,这些受害者的名字应该还有10倍多。”[12]也就是说,苏联时代总计有1300-1400万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不过请注意,这里的“受害者”不是仅指被处死的人,而是广义的受害,即受迫害者。
的确,俄罗斯有三个州和个别城市就二战胜利为斯大林立了纪念碑,但同时不能不看到,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几乎普遍竖立了各自地区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其建筑样式都一一载入了《苏联政治恐怖牺牲者》电子画册中[13]。
(五)关于卫国战争的研究
同一般民众评价斯大林在二战中的功绩不同,史学家们关注的重点是战争初期的失误、战争中的人员损失等等⑦。民众中一些人谈二战胜利同斯大林个人相联系,史学界则认为,二战的胜利是全民的功绩[14]。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ЛЛ.C.列昂诺娃教授在涉及这个问题时说:人们将苏联社会的巨大成就——国家的工业化、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居民的社会保障(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近乎免费的住房等)都归功于斯大林。人们尤其强调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中所起的作用。不过,另一种观点才更具权威性,其中包括史学博士В.П.达尼洛夫所表达的观点:“实际上——这已为事实证明——苏联社会的所有成就都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动力推动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动力归根到底是革命的成果,它长期决定了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趋势和内容,它是人民的丰功伟绩。”[15]
从俄罗斯学者对上面这几个重要方面的评价看,这些年,俄罗斯史学界主流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评价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并未发生基本评价的更改和变化,所以,谈不到什么“重新评价”的问题。
一般来说,教科书较能反映学术界基本的、主流的观点。为了更确切地印证上述史学界的研究情况,再让我们通过两种较为典型的教科书,看看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评价。
先看看在教科书中带有左翼共产主义色彩的一部,这是由Э.М.夏金等人主编,由莫斯科大学以库库什金为首的20世纪俄罗斯史教研室评论审定的一种高校教本。对于“大清洗”,它是这么评价的:有关斯大林在战争临近时搞镇压是为了消灭“第五纵队”。教本认为,“斯大林的忠实战友莫洛托夫向诗人楚耶夫提出这一说法,是为了替镇压作辩护”[16](p83)。可见,这个教本对“大清洗”是彻底否定的。该教本认为,30年代的体制是一种“行政命令体制”。对于整个30年代,教本评论说,“尽管艰难困苦,发生了所有困难,国家面貌却快速改变了”。“虽然国家生活在这个时期有过悲剧和矛盾,也有涉及方方面面的革命改造的乌托邦计划,但强国思想、爱国主义、劳动中追求高度职业技术、追求个人幸福生活和稳固家庭的思想动机,则在社会上占有自己的地位。”[16](p91、p92)在这里,教本只能用“强国思想”、国家发展和劳动、个人家庭幸福等等最一般的思想来为30年代作说辞,而怎么也否定不了“悲剧”、“乌托邦计划”和“矛盾、困苦”等等。可见它尽管用语含糊,也不能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作多少有力的论证和辩护。
另一部也是为教育部核准的教科书——A.К.索科洛夫的《苏联历史教程(1917—1941)》。该书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说得更透底一些。它在评说俄罗斯史学界的观点时认为:“现在,对苏联30年代社会体制结构所作的解释中,以极权模式或极权制度为最流行。”[17](p213)该《教程》说,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俄罗斯史学界各种评价都有,既有“乌托邦纲领”说,也有“马克思主义特殊民族支派”说;既有“国家社会主义”、“变形社会主义”说,也有“军营社会主义”说[17](p213)。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主流史学界对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大体上仍然保持着上述观点。
除此之外,还可以从近些年俄罗斯史学书籍出版的整体情况,从这个更大、更宏观的视角,就俄罗斯史学界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研究的状况做一个概观。
笔者一直密切关注《祖国史》杂志,这是俄罗斯史学界三大史学权威杂志之一,它几乎每期后面都转载俄罗斯《图书评论》杂志发布的近期面世的有关俄罗斯历史的新书书目。对它上面的这些书目,从2000年第1期到2006年第1期,除极个别几期杂志因他人借出无法查阅外,对六年间各期杂志上的绝大部分书目,笔者都作了查阅和统计。查阅书目总计2372种,其中明显直接涉及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书籍,计165种,其中从标题判断对其持否定态度的占130种,属中性标题的占30种,属肯定或赞颂标题的有5种。这个数量统计足以说明,俄罗斯史学界出版对斯大林及其体制持否定评价的著作,要大大多于持肯定评价的著作。笔者以为,这种权威的纸质媒体资料比无法取得数量概念的电子网络资料更能说明问题。笔者之所以敢于断定俄罗斯史学界“当今否定斯大林的资料实际上还更多一些[18]”,就基于这一资料来源。有学者对我这一论断提出的反驳,是软弱无力的⑧。
有人可能会问:有的中国学者在文章中举证了一些俄罗斯学者的言论,说他们要求重新评价斯大林或为他进行翻案,对此,你有什么评论?我现在就此讲三点:1)我已经涉及了几个这类学者,如Э.М.夏金和库库什金等,他们分别是第一种教科书的主编和评论者。他们的观点在教科书中体现得较全面,看不出他们是要重新评价斯大林。有论者所引夏金的话,只是表明了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国家思想”的某种调整,根本说明不了是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2)没涉及到的其他俄罗斯学者,大体是影响不大的极少数,其中有一直持30年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观点的学者,他们几十年对斯大林观点如一,谈不到是什么“重新评价”的问题。此外,有的还是学术界的“怪人”,如那个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俄罗斯史学界就如是称。3)笔者还要重点涉及一部著作——弗·维·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19]。这本书2003年在俄罗斯出版,2004年我国就用极快的速度翻译出版了。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В.П.达尼洛夫对该书及其作者是有评论的,他说:弗·维·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中“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用了30年代法庭审判中那些被告的供词”,这样使用供词“是不合法的”,因为那些“审判中的供词是如何得到的,人们早就一清二楚了。只有丧尽天良的人,才会对通过严刑拷问取得斯大林领导集团所需口供的做法缄口不言。”[20]В.П.达尼洛夫又说,他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领导请教并询问了有关《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引用1919—1930年间和1930—1940年间被镇压者的数字资料的情况。这位学者说:“2003年5月8日我收到了正式答复,说是经查没有发现‘内务人民委员拉·贝利亚向斯大林同志呈报的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在1919至1940年期间进行镇压的资料。’因此从‘上述资料的形式’及其内容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公布的文件是伪造的。’”[20]
这就是说,这是一本含有伪造资料的,甚至拿非法审讯口供做论据,存在严重纰漏的非学术性著作。像这类非学术类著作,恐怕不能用作评价斯大林的可靠凭据。而这类书籍或文章,或此类作者,或者连这类作者都不如的节目主持人、演员关于斯大林的言论,都进入了相关学者的学术文章,并当作“重新评价”斯大林的佐证,这恐怕是不很可靠的。
综上所述,俄罗斯史学界的主流对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基本评价没有改变,这当然不能说俄罗斯出现了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
三、中国史学界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和评价
我国史学界,特别是俄罗斯东欧学界和国际共运史学界,对俄罗斯史学界有关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研究情况,是心里有数的。因此,自2003年在我国刊物上出现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的论断后,学界就普遍提出了质疑,在有的学术年会上甚至发生群起与当事人激烈争论的场面。2005年《世界历史》第2期发表笔者《俄罗斯是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对俄罗斯近年出现的所谓“重评思潮”的剖析》一文,实际上就是在这一认识斯大林问题的基础上写出来的。继该文之后,笔者又在《百年潮》2005年第6期发表《当今俄罗斯的“斯大林热”》,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4期发表《如何破解当前俄罗斯现实政治中的“悖论”?——评“斯大林热”和取消十月革命节等悖论性事件》。这一组三篇文章,用大量有力的事实,质疑了所谓“俄罗斯重评斯大林”的说法。指出,目前俄罗斯的所谓斯大林“热”,实际是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以期建立强大国家,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并且指出了《参考消息》2004年12月24日的报道《俄罗斯政权党呼吁重新评价斯大林》中有关键词的翻译错误,以及曲解俄文原文内容的标题。同时,该组文章也用俄罗斯民族的矛盾性、悖论性特点,解释了俄罗斯现实政治中的一些事态。
这些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思想理论界也引起了较大反响。《百年潮》发表的文章,据不完全了解,不仅《书摘》(2005年第5期)作为重点文章给予转载,黑龙江省《党的生活》杂志(2006年第1期)也在“佳作推介”栏目加以刊登。2005年11月,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还特约一篇讲斯大林“热”,但观点不是“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由一位著名学者应邀写出,以《对斯大林“热”的误读》为题,发表在同年11月下旬的《学习时报》上。
2005年11月25日,在由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政治研究中心和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共同发起,有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北京大学、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人民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学者出席,以“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研究”为题的研讨会上,讨论了俄罗斯学术界近些年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研究状况,特别谈到了俄罗斯民众和政治人物对斯大林评价升温,即所谓“斯大林热”的问题。参会学者在发言中对俄罗斯史学界有关斯大林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基本如上文所说的那些情况。他们特别指出,应该正确认识对斯大林评价升温这一现象,而不要发生“误读”。会议认为,“对俄罗斯史学界而言并不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21]。会上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该以什么观点评价斯大林,即评价斯大林的标准问题:“是从强国主义、民族主义出发,还是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公平与公正、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出发”[21]。
从前面我们引述目前普京和俄罗斯重要官方人物评价斯大林的言论看,无疑,他们都是从强国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出发评价斯大林的。他们评价斯大林几乎都是同对德战争胜利以及取得俄罗斯强国、大国地位联系在一块的。在近些年俄罗斯国力式微、经济萎缩、国际地位下降的情况下,他们作为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用强国主义鼓舞人心,正如我们上面所说,是应予理解和同情的,无可厚非;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中国学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跟着这种俄罗斯的强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调子跳舞。俄罗斯官方一些代表人物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把斯大林同历代俄罗斯帝王并列而肯定他的;甚至有人把这个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说得比列宁还伟大,对此我们是无法认同的。斯大林对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战争中沙俄失败感到受辱40年,在二战胜利后,他认为对日胜利是洗雪了“耻辱”;在二战前后,他以强势地位共吞并周边国家约67万多平方公里的疆土,包括属于中国的一块飞地——唐努乌梁海10多万平方公里。对斯大林这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心态和行为,我们是不能同俄罗斯人一样看待的。俄罗斯人赞扬斯大林在苏德战争中的功绩,其实也包括颂扬斯大林的上述思想和行为。这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标准评价斯大林,而是用俄罗斯“强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来评价他。
可是,我们中国学者不能这样做。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评价斯大林。用这种原则和价值观来评价斯大林,就是要把他作为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创立者来评价,就是要像列宁如何对待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那样来评价;也要像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所持的立场那样来评价。最根本的,就是要遵照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原则来评价。《共产党宣言》的主要精神,是讲未来社会应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p273)。这里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而邓小平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斯大林)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23](p250)这些话应该成为我们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指导原则。从这个指导原则来看,斯大林模式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精神的,是“僵化”的、“不是很成功的”,因此,我们应该更新社会主义,重塑社会主义的形象,摆脱斯大林的模式。我们就是从维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在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前提下,来看待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
可是,俄罗斯官方和学术界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这是斯大林的基本的、本质的方面,又是如何评价的呢?正如前面所述,他们大多是从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国主义出发肯定斯大林大俄罗斯主义的对外政策,而又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观念或自由民主主义的观点出发否定他的国内政策,他们从后一立场出发对斯大林作为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创立者所持的否定态度,十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在这里,应强调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把主观意愿和客观事实相混淆。在我们中国,的确有一部分学者和同志想给斯大林以“重新评价”,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大体与斯大林同中国革命的渊源关系有联系。但我们从主观愿望上想给斯大林以“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是一回事,而俄罗斯目前是否真正为斯大林做了“重新评价”和“重新肯定”,则是另一回事。从上面我们对俄罗斯官方评价的分析,从俄罗斯史学界研究斯大林问题的情况看,显然俄罗斯并没有对斯大林做什么“重新评价”和“重新肯定”。而一些学者将主观意愿当成客观现实,以前者代替后者,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历史研究中的所谓“重新评价”,严格来说,应是基本评价的更改和变动;而历史研究中出现一般“新的认识和新的评价”[24]、更客观一些的评价,甚至是“重新的思考”,都不能称作是“重新评价”;否则,“重新评价”云云,就太泛化了。若如此,所有史学研究,只要不是因循旧说,是否都可叫做“重新评价”呢?这样的话,也就无所谓“重新评价”了。
四、史学研究中应该怎样对待和使用民意调查资料
在解读所谓俄罗斯“斯大林热”的过程中,提出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史学研究应该怎样对待和使用民意调查资料。
在历史上,俄罗斯几百年都是一个专制国家,从来不知民意为何物。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变而大讲民意,到处搞民意调查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无论对什么问题都搞问卷调查,对包括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些原本属于历史研究范畴的事情,也搞民意调查,这就不能不是问题了。
当然,在民意调查问题中涉及历史人物和事件,也是可以的。但民意在历史人物和事件中反映出来的,首先是现实问题,是民众对有关现实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思想情绪,其次才能从特定角度折射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状况来。民意调查最有效的,是关于现实和现状涉及的民情、民意问题,比如总统候选人的民意情况,何人当选的概率大,哪个政党的支持率高,当前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等等。对此类问题,搞问卷调查是最有效的;但对历史问题,在对待属于历史研究范围才能解决的问题上,则复杂得多,需要谨慎小心。对历史问题搞民意调查,严格地说,应该是不大有效的。道理不难理解,因为民众不搞历史研究,他们不是历史学家,不了解历史上的专门性问题。直接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搞问卷调查,也是不科学的,它反映的并不直接是历史人物和事件本身,而只是民众在某个特定时期对待现实问题思想情绪的一种折射,只不过是通过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透视罢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社会心理学范围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一定要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搞民意调查,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通过民众对现实问题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并不能成为完全符合科学理性的可靠的历史评价。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意识是通过现实生活和现实状况,对客观认识对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折射的,它们只是充当了反映客体的介质和载体,对被反映者能被反映到何种程度,取决于现实、现状的情况,取决于人们对现实状况问题的态度,并不取决于被反映者本身的状况和面貌。这样一来,被反映者的真实面貌自然就得不到如实的、准确的反映,而只能是像筷子插入水中,形成弯曲的、像折断似的反映,呈现出一种歪曲的面貌。这样,就只能是折射,而不能是完全正确的反映。
目前俄罗斯的一些民意调查机构,虽然不乏对斯大林或有关历史人物事件的民意调查,但俄罗斯历史学家对这种民调是不予认同的。1999年一个著名民意调查机构进行了一次问卷民调,只有9%的俄罗斯人承认斯大林时代经济形势是严重的,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认为那个时代的经济形势是好的。这个调查结果,让著名历史学家茹拉夫廖夫很吃惊,他说:“实际上,这个时代的经济状况确确实实是难以忍受的。”[25]在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31年间,有24年是他个人专权,在这期间就发生了1932—1933年和1946—1947年两次严重饥荒,加上重工业一直投资过大,工农业失调,长期引发物资匮乏、经济形势紧张,只有1935年前后一两年经济状况稍好一些。那么,为什么当今会有那么多俄国人(即9%以外的那一大部分)错以为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形势是好的呢?就是因为叶利钦激进改革造成了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人民物质生活大幅度下降,对现状不满使人们怀恋过去,误以为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形势是好的,实际上大多数人并没有在斯大林时代生活过,只是因为对当前的不满而引发对过去的臆想和怀恋。历史学家是进行理性思维、从事客观研究的,而民众多是由现状引发而产生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情绪化想象和臆造。因此,历史学家应该以理性的思维、客观的研究,纠正民众中一些人造的神话和臆想,校正民意调查中所包含的情绪化的东西。这样说来,历史学家就有责任认真分析、仔细鉴别从民意调查中得来的资料,而不应当被民意调查资料所迷惑,完全相信这些资料,被这些资料牵着鼻子走。
目前俄罗斯民众中对斯大林评价的升温,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不满的折射,其中有不少是含有情绪化的东西。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列昂诺娃教授把这种现象称作是“对具有破坏性质的后苏联时期改革的回应”。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副所长索科洛夫则说,这是对过去行为的一种“反弹”。2006年9月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学术访问的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20世纪俄罗斯、苏联史研究中心”主任A.C.谢尼亚夫斯基,在谈到近年俄罗斯有否“重评斯大林思潮”时说,在俄罗斯学术界只是很少数人有此倾向,称不上什么“思潮”。上述情况都说明,对俄罗斯史学界来说,并不存在称得上是“重评”斯大林的所谓“思潮”问题。但我国有学者对俄罗斯学术界的这种情况却考虑不足,主要以民意调查资料为依据,断言俄罗斯在“重新评价斯大林”,这显然是不足为据的。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笔者要向对拙文《俄罗斯是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提出驳难的文章(后称吴文)作出必要的回应。拙文实际上可归结为两个论点,一是像标题所示,俄罗斯近些年的所谓“斯大林热”,实质是为复兴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由此便引申出了第二个论点,即所谓的“斯大林热”并非“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斯大林。吴文对笔者文章中的第一个论点几乎未置一词,没有拿出任何反驳的论据。至于对笔者的第二个论点,吴文先是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新评价”,演绎、泛化解释为一种“新的评价和认识”,或者“反思”历史、“重新思考历史”,接着又王顾左右而言他,抓出很枝节的问题加以发难;而在真正涉及“重评”问题时,却又暗自调换概念,把俄罗斯官方和学界无论有涉无涉斯大林的言论,统统视作“重评”的论据。恐怕论者本人也觉得有欠说服力,到最后甚至说什么发表在2003年《历史研究》第5期上的文章原本就是一篇“综述”,该文归纳、概括的“都是俄罗斯学者的”观点。意思是说,提出“重评”观点的纯粹是“俄罗斯人”,并非论者本人,因此,要讨论这个问题,就“找提出这个观点的俄罗斯人”去,“怎么找我?”[24]。话既然已说到此,读者定然也都了然其隐衷。我既已将俄罗斯学术界近些年研究斯大林的情况几乎全盘托出,俄罗斯是否存在“重评思潮”,真相已经大白,到此也就无须再说什么了。
不过,最后还有几句应该提醒的肺腑之言。前几年,如果说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时,还曾是就事论事,还是在就俄罗斯是否存在“重评”思潮作纯学术的探讨,那么,形势发展到今天,恐怕就需要作些重新思考了。因为在写作、修订这篇文章的此刻,问题已经明朗:在俄罗斯并不存在“重评”和“重新肯定”斯大林的思潮,这是肯定无疑的;存在这股思潮的,实际上是在我们国内,是在近几年我国改革争论的大潮中。这个问题,实际上同近几年我国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密切关联着,也同有些人企图利用我国改革出现的局部缺点错误,企图否定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密切相关。不是有人甚至还要“重评”人民公社,“重评”“文化大革命”吗?他们“重评”的目的,就是企图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过去。在这样的思潮面前,“重新评价”和“重新肯定”斯大林,呼唤过去的那一套体制,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当然,这并不是说与我们论争这一问题的有关学者主观上就是如此,我们绝无以此责难别人之意,更无以此归咎他人之心,但社会意识客观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和错综复杂的交织,却是一种不可否认的社会现象。就本心而论,笔者并不愿意在本文最后就所讨论的题目联系我国目前的现实改革问题,但作为一个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自己一切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与我国改革命运和国家前途生死与共、荣辱一体的具有责任感的普通学人,难道能把自己关闭在纯粹学术的象牙塔中吗?!
注释:
①参见《我们的祖国·政治史研究》(Наша Родина.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第1—2卷,莫斯科1991年版;И.В.伊万诺娃:《苏联20—30年代政权机制》(ИвановаИ.В.Механизм советсkого власти.20—30 гг.),载(俄)《历史问题》1998年第11期;Е.Г.吉姆佩利松:《苏联国家管理机关的形成和演变(1917—1930)》(Гимпельсон E.Г.Cтановление и зволюц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п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улравления.1917—1930),莫斯科2003年版;И.В.帕弗洛娃:《政权机制与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建设》(ПавловаИ.В.Механизм власти 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сталинского социадиэма),新西伯利亚2001年版;列昂诺蛙:《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现代俄国史学发展基本趋势》,在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2005年西安年会上的学术报告。
②参见Г.А.特鲁坎《走向极权主义之路:1917—1929年》(ТруканГ.А Путь к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1917—1929 гг.),莫斯科1994年版;А.Л.萨哈洛夫:《我们如何理解极权主义制度》(сахаров А.Н.Как мы лонимаем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199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学术报告;Ш.费特茨帕特里克:《日常生活中的斯大林主义·30年代苏俄社会史:城市》(ФитцпатрикШ.Повседневныйсталинизм.Социальиая историяСоветскони России в 30-е годы:город),莫斯科2001年版。
③参见И.В.切莫达诺夫《苏联有过代替强制集体化的选择吗?》(И.В.чемоданов.Былалив СССР адьтернатива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йколективизации),载《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6年第2期;П.格列戈里:《再论集体化》(ГрегоиП.Еще раз о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载《经济科学》(ЭкономичеКие науки),1990年第12期;П.с.卡贝托夫、В.А.科兹洛夫、В.Г.利特瓦克:《俄罗斯农民:精神解放的阶段》(кабы товП.С.,козловВ.А.,ЛитвакБ.Г.Рус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зтапыдуховн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莫斯科1988年版;《合作化计划:幻想与现实》(Коолеративный план:иллюэии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莫斯科1995年版,等等。
④参见В.Н.哈乌斯托夫:《评“苏联农村的悲剧·1927—1939集体化和消灭富农(文件资料)”》(xаустовВ.Н.Трагедия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1927—1939.),载(俄)《祖国史》 (“Отечествуннаяистория”)2002年第6期;И.Е.普洛特尼科夫:《20年代末—30年代初乌拉尔的农民骚动和发动》,载(俄)《祖国史》(“Отечеству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8年第2期;А.П舍克舍耶夫: 《1918—1932年在叶尼塞地区的农民起义》(А.П.Шекшеев.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постанчество на Енисее.1918—1932 гг.),载(俄)《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6年第2期;Т.Д.纳季金: 《1932—1933年饥荒年代摩尔多瓦的农民与政府》,载(俄)《历史问题》 (“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2006年第4期;М.А.别兹宁、Т.М.季莫尼:《集体农庄农民的社会抗议(4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载(俄)《祖国史》(“Отечествуииая история”)1999年第3期,等等。
⑤参见奥·弗·赫列夫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 (Хлевнюк О.В.Политбюро.Механиз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власти в1930-е годы),莫斯科1996年版;В.П.第米特连柯等主编:《苏联当局与社会:20—40年代的镇压政策》(ДмитриенкоВ.П.Власти СССР и общество:Репресснвна лолитика в 20—40-е годы.),莫斯科1999年版;В.И.巴库林:《1933—1938年基洛夫州的干部清洗》(кадровыечистки1933—1938 годы вки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载(俄)《祖国史》(“Отечеству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6年第1期,等等。
⑥这样的著作,诸如:《1937—1938年阿尔亨格尔斯克的镇压·文件资料集》(Репрессии в Архангельске.1937-1938: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阿尔亨格尔斯克1999年版;《不要忘记:纪念政治迫害牺牲者》(第1—8集)(Непредать забвениию:памяти жерт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Т.1—8.),普斯科夫1993—1999年版;В.А.弗罗洛夫:《人民的悲剧:鞑靼斯坦切列姆尚地区镇压的历史》(Фролов В.А.Трагедия народа:Из истории репрессии Черемшанского р-нататарстана.)喀山1999版;《加里宁州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册·1937—1938年牺牲者名单第1卷》(книга Памяти жерт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калининской облости.Мартиролог 1937—1938:Т.1.)特维尔2000年版;《来自忘川:1918—1954年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册:第1卷:俄罗斯联邦阿斯特拉罕州》(Из тьмы oабвения:книга памяти жертв па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1918—1954:Т.1:Рос.φедерация.Астрахан.область),伏尔加出版社2000年版;《1937—1941年莫斯科枪毙名单》(Растрелъные списки.Москва.1937—1941),莫斯科2000年版;С.А.帕普科夫:《苏维埃国家1928—1941年6月在西伯利亚的镇压政策》(Папков С.А.“Репрессив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Сибири(1928-июоиъ 1941 гг.)”)“专业”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
⑦参见Л.Е.列申主编《1941年》(ЛешенЛ.Е.1941год)(2卷本),莫斯科1998年版;В.安菲洛夫:《通向41年悲剧之路》,莫斯科1997年版;С.З.斯卢奇: 《斯大林与希特勒·克里姆林宫的盘算和失算(1933—1941)》(С.3.Стуч.Сгалин и Гитnер.1933-1941:расчеты идросчеты кремля),载(俄)《祖国史》(“Отечнственая история”)杂志2005年第1期;в.苏沃罗夫:《清洗:为什么斯大林把自己的军队变成了无首之师?》(Суворов В.Очищение:Зачем стаин обезглавил свою армию?),莫斯科2001年版;А.В.科罗连科夫:《评布鲁克米耶尔的“斯大林、俄罗斯人与他们的1941—1945年战争”》(короленков А.В.—М.Брукмийер.Стални,русские и их война 1941—1945),载《祖国史》杂志2006年第3期,等等。
⑧参见吴恩远《再谈俄罗斯反思苏联历史、重评斯大林思潮》,见《世界历史》2006年第期第37页注②和《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第102页注②。
标签:斯大林论文; 俄罗斯民族论文; 俄罗斯历史论文; 政治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彼得大帝论文; 苏联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