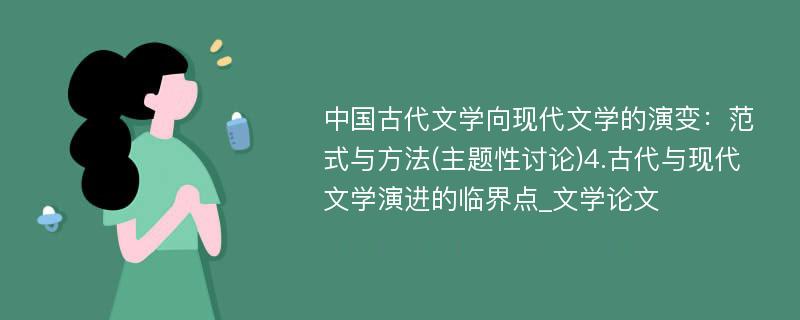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范式与方法(专题讨论)——4.文学古今演变的临界点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今论文,专题讨论论文,范式论文,临界点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学术命题,自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首倡以来,相关的学术探索新见迭出,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检视近年来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术理路,取径大体有三:一曰贯通式,即指对文学的内容、形式,文学思潮、观念的发展流变以及作家作品传播接受进行纵向的梳理研究。二曰本位式,即章培恒多次强调的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互为坐标”的研究,或以古代文学为本位,下析其流;或以现代文学为本位,上探其源。三曰临界式,即着眼于演变发生之临界点的研究。在此三种研究路径中,前两种成果最著,影响亦大,而临界点研究多为近现代学者为之,尚处于囿于一隅的不自觉状态,未有融通的学术视域和明晰的学术目标,其特性及之于文学古今演变的学术意义皆遮蔽未明,故有特加申说的必要。
文学演变的临界点即文学古今演变的关键时间点,具体指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它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亦可能是一个时段。临界点之于文学演变的意义,譬如江之入海,其境始阔大;铁之淬火,焕然已成钢。在古今贯通的文学视域中,临界点的辨析与判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它的存在使文学古今演变的概念被赋予完整的内涵而获得了合法性的意义。并且,如上所述,在具体学术实践中,文学演变的临界点研究已成为文学演变研究的一种途径,同时具备了方法论的内涵。
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范畴,要对临界点研究的内涵特性进行学术层面的界说、解析和提升,使之转化为有效的学理资源,从而为自觉的学术探索提供足够的启示和借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辨析显得颇为必要,如怎样理解文学演变的临界点?如何正确评价文学古今演变之近现代时段的功能与意义?如何深入细致地揭示文学演变发生的历史现场?本文从演变的主体、时段和过程三者入手,以文学演变临界点为主要观照视角,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析和阐释。
一、临界点演变主体的“文化转型”与“文学演变”之辨
学术界对于文学古今演变临界点的出现持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是在明后期;一种观点则认为是近现代。对于前一种观点,肯定的多是文化思潮史学者,而后者则得到多数文学史学者的认可。文化思潮史学者往往从社会文化转型的角度立论,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认为,伴随社会巨变,晚明“文学艺术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其主要标志是公安派、竟陵派诗文的兴起和市民通俗文学的繁盛,尤以后者最具划时代意义”,“这种文学思潮的实质是要求从文学复古主义和封建正统文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向反映市民阶层、普通民众与下层知识阶层生活和思想愿望、审美情趣的市民通俗文学转型”[1](《前言》)。尽管也有不少文学史学者对于明后期文学发展的特殊性进行评判和定位,如认为明后期商业货币观念的变异,使传统农耕文学发生转型,导致各种文体形式如小说、诗文的转型。而各类权威文学史教材则对文学古今演变于近现代时期之说基本达成共识。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就指出,正是在近代后期,“整个社会思想风气和文学面貌都发生了具有历史转折性的变化。这一时期,虽然旧的文学形态与守旧的文学流派并没有销声匿迹,但新的文学风气与充满新思想的文学作品,已成为文坛的主导潮流”[2](P473)。
对两种观点细加考辨将发现,二者争论的焦点在于“文化转型”与“文学演变”之别。文化的现代转型以启蒙思想的萌发作为标志,这在明代中期之后即已开始,当然,这种现代性质素的成长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进程,反复迎拒消长,从晚明到晚清,完成了一个历史性大回环,直至19世纪晚期才回到了曾经的思想断裂点上再次整装上路。如果说“文化转型”指的是文化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而“文学演变”则关注文学在古今转变中的历史命运,这在现有文学史的分期演述中大体界限分明,序列井然。
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文化转型与文学演变具有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文化转型催生文学演变,在文化变革浪潮的席卷之下,文学必然随之起舞;另一方面,文学的古今演变与文化现代性的发生并不同步,文化转型中“现代”是与传统相对的文化属性概念,而文学演变中的“古今”则更像是时间概念,尽管对于“现代性”一直存有争议,但它明显早于历史分期中的现代应无疑义;再者,文化的发展是观念形态,而文学更多的是一种文本形态,所以文学演变往往滞后于文化转型的发生。文化观念随社会变革而变革,而文本依附于文学传统则要迟缓一些,多以观念的结晶和遗存的方式面世。这些都是造成临界点理解歧异的主要原因。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明确古今演变的主体是文学而非文化,对于演变临界点就不难作出自觉的判断。
二、围绕演变临界点的“文学演变”与“文学革命”之辨
在面对文学演变的临界时段时,研究者往往会作出简约化的判断,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就是古今演变的当然临界点,从而把“文学演变”等同于“文学革命”。这种简约化的理解,有时近于粗疏。
王德威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就本质而言,五四新文学是一个文学的大收获结局,而五四新文学的建构过程则起始于“五四”之前的近代,这种建构包括文学观念的建构、文体建构、现代思想体系的建构、语言建构以及更为深层的整个文化类型的建构。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五四”不过是一个结果,而近代则表现为一种过程。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文学演变”是一个过程,而“文学革命”的发生则是结果,当无数演变的能量都积聚到一个节点上,于是革命爆发。与结果相比,过程有时更为重要。
在实际操作中,对五四文学革命及成果的过度关注,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研究者对于文学古今演变场景作出更为清晰的判断。1917年1月,胡适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以白话为正宗”,这篇名文也因胡适的号召力而成为新文化运动肇始最著名的文献之一,被认为是“白话文学革命”倡导之始。殊不知早在晚清,白话文运动即有坚定的鼓吹者,如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所论:“晚清白话文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则是裘廷梁。1898年,他在《无锡白话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痛陈文言之流弊,细诉白话之优长,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其崇白话的立足点固然在开通民智,但把文言置于白话的对立地位,丝毫不给文言一席之地,这种断然决绝的态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等人的主张已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3](P26-27)但是,当我们回望这一段历史时,晚清白话文运动先驱者的身躯完全遮没在五四文化巨擘的阴影之中。
再以城市文学的古今演变为例,以往现代文学研究者在谈到城市文学时往往将1920年代末的“新感觉派”作为标志,这是基于“五四”后思想观念和文体形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后的判断,随着王德威对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的独到阐释,被重新认识和评价的《海上花列传》,因其“预言了行将崛起的都市风貌”而被认为是城市小说的肇始之作。晚清的通俗小说发展极具多元色彩,笔者认为,问世于1848年的《风月梦》才是中国第一部城市小说。作为城市小说应该具备以下要素:一是小说场景的城市性;二是故事人物的城市属性。而最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典型地体现出当时城市人的心态,表达了对城市生活的独特反思。小说人物对城市环境的知觉方式,可能受制于城市本身的发育程度,城市小说在晚清时的出现并非偶然,尽管这时城市的整体生活内容和消费方式并没有完全脱离乡村化的底色,但城市的容量和城市生活方式的丰富都已远超前代。更重要的是,此时出现了更彻底的有闲阶层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休闲格调,中国市民似乎第一次在如此明晰的城市背景中游走活动。在《风月梦》里,作者用比较新颖的叙述方式突出地描绘了这一切。就这样,城市自身形态的发展与小说艺术表现上的进步比较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促成了最早的城市小说的诞生。
从整体来看,文学在近代时期的变革显得更加复杂与强烈,“多元性、过渡性、创造性、内在的紧张、矛盾与冲突”等构成了近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中国文学演变中存亡绝续的种种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令人眼花缭乱地杂陈交错着,正如论者所说:“中国近代文学实际上预示了中国文学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五四新文学不过是在这多种可能性中选择其一而已,即选择了面对社会现实、强调政治和启蒙、通过学习西方来实现价值转换这样一种路子。”[4]对于规范已经建立的“五四”来说,近代只是头绪纷繁的“一地鸡毛”,而这正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临界期的真实现场,惟其如此,爬罗剔抉、剥茧抽丝的探索才有了努力的方向,也才显得弥足珍贵。总的来说,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而言,多元而无序的近代文学正因这种无限可能性才较之“五四”更值得关注和审视。
三、演变临界点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之辨
临界点的确立需要有文学演变规律的整体观和辩证观,在整体改变的大势下,不同文学观念、文体形式等文学要素的演变可能产生时序、状态等截然有别的临界点,“同一性”与“差异性”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的两面。
所谓“同一性”,即指古今演变中文学现象遵循特定规律而有相似与相同的演变过程。从宏观着眼,文学古今演变之近代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变的时期,诚如李鸿章所说,乃“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文学在近代的变化可谓全方位,若将文学活动的构成视为作家、文本、语言、传播方式、读者等诸种要素的综合,那么,这些要素在近代几乎全部霍然有变。作家由古之士大夫一变而为近代之知识分子,其撰述心态和方式与前殊异。除了词赋外,各类文学体裁皆有程度不等的变化,旧日以诗文为正统而一变为以通俗小说为中心。文本形式如此,文学语言也由文而白,文学传播方式纳入大工业生产的轨道,销售变为商业化、市场化运作模式。因为现代传播的迅疾广泛,文学作品由从前士大夫读者的案头之物而一变为平民读者的日常文化消费。所有的这些变革都指示同一个方向——文学近代化的全面启动。
尽管文学体系各要素已发生全面变革,新文学的因素大都已经萌生。但是各要素在近代的变革并不平衡,有些要素因为缺乏有力的外部驱动,还未能形成整合之势,更遑论顺利完成转型。从微观的、具体的考察来看,文学古今演变的临界点充满了“差异性”,即演变方式和形态出现了诸种不同,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由于演变主体差异,演变程度有深浅之别,演变结果亦有不同,或转型、或衰退、或消亡。在晚清各体文学中,时代机缘各不相同,顺利转型如小说,由于梁启超大倡“小说界革命”,通俗小说的发展在20世纪初即成潮涌之势,后一直跻身于文学主流,直至20世纪末才同文学一起边缘化;古文则一变为散文后略有衰退,题材与形式对传统有承袭亦有一定发展;赋体文则成为被冲击和扫荡的对象,而在20世纪趋于完全没落。二是演变节点前后时序不同。无论是文学思潮、文学主题,还是文学体裁、语言、修辞技巧等的古今演变,彼此间必有时序前后的不同,故无须赘言。三是演变临界点的形态不同,或为一个时间点,或为一段时期。1902年,梁启超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成为翻译小说古今演变的标志性事件,此前翻译小说数量有限,此后则数量剧增。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序》中感叹说:“吾感夫饮冰于《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据陈大康统计,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王朝最后九年所出的小说总数占近代小说总数的88.78%。其中,通俗小说占总数的89.90%,翻译小说所占比例则达到94.26%[5](P2)。1902年由此成为古今文学演变之分野。而更多的临界状态会持续一个时期,在变与不变之间多有反复回环。如前所述,白话文运动自1898年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首倡,几度反复,其中著名文人林纾甚至由开始的支持者蜕变为众矢之的,历二十年,直至1917年胡适再举大纛,群起响应,方奏一锤定音之功。
就文学体系各要素而言,演变主体的属性存在着事实上的差异,大致可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类。所谓显性演变主体,指的是文学体裁、文学语言、艺术技巧等较为显豁,易于把握的演变主体。相比而言,以往为研究者所关注的多以此类为主,成果亦较为突出。所谓隐性演变主体,则指文学思潮、文学主题、作者观念等较为抽象和较难把握的演变主体。由于特定阶段的文学体系要素众多,纷繁复杂,对于文学思潮、观念等的考察,牵一发而动全身,故急需倡导一种横向的、断面的临界点研究模式,通过建构立体的时空坐标,还原历史现场,在文学史独特的截面中厘清各因素之间千丝万缕的脉络与联系,进而前后牵引,左右关联,才能弥补古今演变研究常见的纵向、单一研究模式之不足。
综上所述,对于“文学古今演变”这一核心关键词,本文分别对“文学”之主体、“古今”交接之时段、“演变”的过程,作了较为详尽的解析。唯有明了文学演变临界点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所表现的差异性,方可避免研究的模糊性、笼统性与单一性。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自应开展秉承宏观、回归细部的切实研究,使这一研究既具周延性,亦具纵深感,惟其如此,方能将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