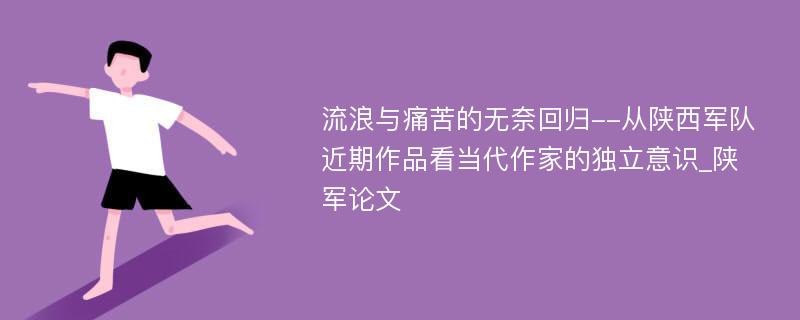
无奈的流浪 痛苦的回归——从“陕军”近作看当代作家的自主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作论文,痛苦论文,无奈论文,意识论文,自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当代文学中的自主意识经历了觉醒、展示、高涨、迷惘的发展过程,陕西作家的创作忠实地展示了包括作家自己在内的文化人的自主意识。无奈的流浪,痛苦的回归,是这个过程相反相成的双重变奏。陕西作家的创作既是新时期文学诞生以来作家表现自主意识的总结,又是另一个新的开端。其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也有困惑。
【关键词】 自主意识 精神家园 精神流浪 精神回归
一
当代中国文化人的自主意识,实际上已经陷入了破碎的迷惘之中,这是一个必须承认的现实。造成这种迷惘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发生在当代的令人眼花瞭乱的社会变革,这个变革不是社会某个具体的局部意义上的修修补补,其要改变的也不是我们生活的某些细枝末节,它是对于我们旧有的观念、意识和生活方式的一次革命,已经而且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在实质的意义上改变社会和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冲击面前接受检验,每一种观念都要在新浪潮中接受洗礼,作为代表社会意识与观念的发展趋向的文人、作家更是首当其冲,无论你的精神指向如何重新确定,变是必然的,甚至是迫不得已的,因而迷惘也是自然的。其二,当代文人的自我意识是在旧的信仰变作废墟的过程中建立的,它借助的力量是外来文化,它使用的武器是破坏性的批判,它生长的土壤是否定了民族文化传统之后文人们自己虚构的一片灿烂原野,自始至终洋溢着没有明确指向的反叛精神。在痛快淋漓的、带有报复心理的反叛之后,留下来的只能是空白和迷惘。迷惘的自主意识在这双重夹击之下变成了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虽然在撕心裂肺般地啼寒嚎疾,但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容身的棲栖之地,于是,游荡的灵魂产生了回归愿望。这就是“陕军东进”六部作品(陈忠实:《白鹿原》,程海:《热爱命运》,京夫:《八里情仇》,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废都》,老村:《骚土》)中表现出来的与以往不同的自我意识倾向。
六部小说,各具特色,各有侧重,但我们都能从中品味出小说深切的历史感和作家所表达的要回归历史的强烈欲望。他们要在自己的小说中写出历史,不愿其笔下的人物陷入难以自拔的精神流浪,企图在历史中给他们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不论作家们的努力在多大意义上获得成功,但他们的愿望和心态是共同的。正是这种愿望和心态使他们的精神探索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其中包含着一部分游荡归来的热切,这也是“陕军东进”在读者中产生强烈共鸣的重要原因,因为有文化的公众同样在身受精神迷惘的煎熬,希望包括作家在内的有识之士给他们指一条明路。
回归历史,是因为我们曾经出走,重新走回历史的时候,实际上历史已非原先的历史,重归的流浪者也已持有一种崭新的眼光和心态,这种新的心理特质的出现在于它找到了支撑它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当然也是在历史中找到的。把自我的心灵和自主意识融入历史文化,从自己脚下的土壤和精神赖以生长的传统中寻找真正的精神力量,全神贯注地塑造充满生命意识的强健的灵魂,窥视这个灵魂的种种痛苦和挣扎,这就是“陕军东进”作家群全力追求的目标。他们对历史的观照和依恋决不是简单的重复,心灵的回归实际上饱含着复兴和创新的企盼。六部小说中创造的可称之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至少可以成百计,几乎每一个人物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在性格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不同程度上体现着作者对他们所代表的生活和人群的批判意识,这是人物形象富有生命力的缘由之一。但是其中却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朱先生是当代文学在现时代少有的几近完美的人物形象,这位其貌不扬、乍看之下让人觉得“不咋样”(白嘉轩语)的读书人是作家竭力宏扬的历史文化精神的象征。他饱读儒学,却又不以儒士自居,更不拘泥于儒学,成为寻章摘句的无用的雕虫;他平易、谦和、儒雅的神情风度;上识天文,下察地理的预言式的忠告,都使他在白鹿原上被人当作神一样供奉起来,以致朱先生自己感慨:“看来我不想成神也不由我了!”认定朱先生为神,这自然是白鹿原上的凡妇愚夫们的浅见。白鹿原上最有见识的人白嘉轩却断定“那是一位圣人”,并且认为“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凡人和圣人之间有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界隔。圣人不屑于理会凡人余多嫌少的七事八事,凡人也难以遵从圣人的至理名言来过自己的日子。圣人的好多广为流传的口歌化的生活哲理,实际上只有圣人自己可以做得到,凡人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朱先生的完美和他所向无敌的人格力量足以使他有资格充当一个精神的领袖,作者之所以要把他塑成圣人目的也在于此,在朱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陕军作家们对历史文化的依恋的最后答案。凡人成不了圣人,连白嘉轩这样有能耐的人也难望其项背。白鹿原上虽然只有一个圣人(有一个就足够了),但芸芸众生却能在圣人精魂的光照和荫护下秩序井然地过他们凡俗的生活。白鹿原上的凡人们需要这样的光照,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作家十分深切地感知到了这一需要和焦渴,所以把他心灵中的一腔挚爱都贯注于朱先生身上,因而这个形象才如此这般地光彩照人。
既然历史是如此地让人迷恋,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力量又来自这样的历史,在人欲横流、精神溃败的当今世界仿佛依稀让人看见一个可以回归的精神梦幻,为这一历史作传的心态和愿望在作家的心目中自然萌生了。“写出史诗”或写出具有“史诗意识”的作品来,一直是当代作家们追寻的目标,并把这一目标当作自己文学生涯可以盖棺定论的标志。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一愿望总没有改变。当新时期的文学在社会变革的大潮多少有些迷乱的时候,这一愿望似乎消退了,但旋即又被陕军作家们以自己作品的实绩推到了一个耀眼的地位上。高建群在《最后一个匈奴·后记》中写道:“本书旨在描述中国一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因为具有史诗性质,所以它力图尊重历史史实并使笔下脉络清晰,因为它同时具有传奇的性质,所以作者在择材中对传统给予了相应的重视,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碑载文化的重视。”这一段直露的表白能够代表陕军作家的共同心态,其中所叙的观念与史诗的品格颇有类似之处,这就是把真实的历史与奇异的传说结合起来,使历史本身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因而增加其庄严和凝重。在过去的历史精神中寻找今天人们精神生活的归宿之处,是作家们为处于精神炼狱中的公众找到的一条出路。不论这条出路最后是否能够走通,其探索中所付出的虔诚和劳作已经足以使他们在当今中国的文学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占据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
陕军作家在创作史诗作品方面的追求,表现了一种高尚的殉“道”精神,虽然“道”各自有所不同,其结果也五花八门,良莠共陈,但其“殉”的精神却是一致的。他们恪守柳青遗下的“创作以60年为一个单元”的箴言,守候着自己心目中的神明,默默地耕耘,其执著与精细的确让人叹服。从这种心态来分析“陕军东进”这一文学现象,便不难理解他们何以在相近和共同的时间与背景之下散射出耀眼的光芒。没有这份执著,缺少这份勤勉,任何意义上的才气都会黯淡无光。陕军作家在历史面前要坚定地“殉道”,目的是在给历史作传。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种被他们依恋和认同的历史精神所唤醒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他们自己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追求,强烈地催促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他们既知“天命”而且也在“拼命”,陈忠实曾经说:“如果50岁还写不出一部死后可以作枕头的书,这一辈子白活了。”其实,陈忠实们的期望绝不是用自己精心营造的心血之作死后作枕头,他们的实际期望是即便作不了丰碑,也要作墓碑,作枕头只是一个起点。安慰自己的同时更希望他人或后人来瞻仰,来凭吊。
陕军作家的这种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确得益于三秦大地深厚的文化传统及其动人心魄的感召力。陕西的一位评论家说:“陕西作家群的共性,是作家站在当代的高度上,俯看自己脚下的那片土地,那群人和那段历史。他们能够创造今日辉煌的原因,除了陕西作家们普遍特别能吃苦外,还有三秦大地上的文化积淀。”正是因为有了对土地、人群和历史的强烈认同,文化积淀的种种因素才通过作家们的创造被带入小说,成为作家借助的一种具有崇高感的力量,使得小说中的形象及其生活与这个民族的发生、生存和存在联系起来。意识到今天我们的存在与过去历史之间的联系并非仅只陕军作家,而对过去的历史表达出由衷的敬意,寄托了自己的梦想,通过阐扬历史精神而表达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的善良祝愿的却是陕军作家特有的精神特质。他们在主体意识上对历史文化的回归和依恋使当代文学在表现作家的自我意识方面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在反叛和流浪找不到出路,走进迷惘之后,这种旨在复兴的回归也许正孕育着新的希望。
陕军作家们在他们熟悉挚爱的黄土地上进行历史文化层面上的精神漫游时表现出了从容自在的心态,字里行间流露出他们与土地、历史、人民血肉相联的自信。“陕军东进”的每一部作品在心灵上给读者以震撼的重要原因也在于此。这是陕军作家们生活在这块文化传统十分厚重的土地上的幸运。但当他们沉迷在这幸运的滋养之中时,却有另一种不幸在等待着他们。这就是历史文化精神固然有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某些普遍方面,但同时也带有不可逃脱的局限。特别是地域色彩浓厚的历史文化精神在另一个参照体系中观察时其局限性尤为突出,表现在作家身上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烙印,这烙印不是后来被外力加上去的,而是与精神的机体一同生长,我们在欣赏其机体的健硕时,又不得不接受这个烙印带来的丑陋。这种局限带来的反差清晰而明确地体现在作家的心态和他们的作品里。我们看到的“陕军东进”中的作家和作品在赞美他们认同的历史文化时是义无反顾的,而在批判现实,解剖现实社会中人的心灵时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冲突。
二
三秦大地的历史文化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是农业文明的精神升华,并且持久而广泛地存在于农村的现实生活之中。恰好“陕西代表作家大都出身于农村的赤贫,进入文坛无一不经过曲折的顽强奋斗。”这些饱受乡村文化即传统文化熏陶的才子,似乎是赤手空拳地征服了让他们从小羡慕的城市,进入文坛的胜利使他们骄傲,城市割断了他们与视为生命源泉的乡村的联系又使他们痛苦,灵与肉的矛盾演化为乡村与城市在意识上冲突,这是他们精神苦难的根源。
其实,作家们在征服城市的奋斗历程开始的时候并非两手空空,他们拥有的最锐利的武器是乡村和深厚的传统文化锻造的心灵,其中包含着他们过去的全部生活和他们认定的人生价值,城市教给他们的知识层面上的文化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一个表达他们自己心灵的形式。翻开包括陕军作家在内的所有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作家的早期作品,不难发现他们几乎都是以自己清新、纯朴的山野气息满足了城市人脆弱、躁动、好奇的心灵,他们看着这些城里人手捧他们熟视无睹的几枚野果发出声声惊叹时,不由得露出了几分农民式的狡黠的窃喜,仿佛觉得城里人也不过如此。于是他们一本一本拿出了野气扑面的杰作,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乡村故事,其中的人物和情感洋溢着城里人难得一遇的清香。在征服了城市的时候,来自乡村的作家们几乎也迷失在城市的喧哗之中,于是他们也象城里人一样浮躁起来。按照正常的逻辑,既然从乡村来到城市,并且以自己艺术魅力征服了城市,在城里以上等人的身份生活着(不管承认与否,事实如此),拥有城里人的喜怒哀乐其实也是顺理成章。近代文明开始之后的中外历史大体都有这样一个进程,乡村青年征服了城市,平民跨入了曾经是上流社会独霸的领地,于是社会进步了,历史发展了。但是,陕军作家们却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那颗征服城市的心灵并没有完全消融在喧闹的城市里,没有成为城市里平民或“贵族”的一分子。而当作家们在城市中刚刚过上相对从容的日子的时候,心灵的野性开始萌动了。这是他们征服城市的雄心的副产品。
萌动的野性心灵开始重新审视曾经征服过的城市,他们发现对城市的拥有只是幻影,生活在城市里,但却难以融汇到城市之中。世俗的公众认定他们享尽了都市的奢华,而作家的灵魂却时时提醒他们在城市里其实还是一无所有,孤独的心灵几乎成了都市里一座座荒凉的村庄。回顾自己征服的历程,他们懂得了,城市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都不值一钱,“几十年奋斗营造的一切”“只是浪了个虚名”,而这虚名又使他们“苦楚难言”。追根溯源,是城市的文明毁坏了曾经拥有的一切,使他们忘却了自己的根本。他们孤独的心灵厌恶了以城市生活为标志的现代文明。如同他们曾经征服过城市一样,他们又开始了对城市的批判,不肯安分的灵魂又踏上了新的苦难的令人心碎的历程。
陕军作家们对都市文明的厌弃和他们感到的心灵的孤独有两重含义:其一,以都市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虽然是历史进步的环节,把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带入了工业文明,但这个过程中确实也夹带了许多肮脏的生活垃圾,构成了人类社会新一轮的堕落和罪恶。这些生活的垃圾恰恰对应着农业文明令人着迷神往的许多方面。作家们在乡村形成的纯朴心灵对这些方面的厌弃是本能的。其二,作家们在进入城市时也曾全盘接受了城市的一切表象文明,也象城里的文化人一样谈论着各种时髦话题。城里的文化人谈完了这些话题如同丢弃旧衣服一样把它放在一边,自己该做什么又做什么去了。他们通常不会去寻求最后的答案,因为永远有数不清的时髦话等着他们去做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的解释。而乡村造就的心灵在这里却分成两类:一类人拼命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怕别人看出他们的乡下人的影子,而千方百计地追赶城里人,他们表现得比城里人还要城里人。一类人将信将疑地学着城里人,同时又不断地拷问自己的心灵,愈来愈发现自己的心灵与这种所谓城市意识、现代文明的格格不入,于是陷入了孤独。前一类人虽然浅薄,但他们扮演着喜剧角色,除了引人发笑之外自己也觉得开心。后一类人尽管有几分深沉,却在自己的心灵中上演了一场悲剧,给自己和别人留下的只有痛苦和悲哀。这种厌弃和孤独通常纠缠在一起,很难分辨清楚,因而崇高和卑琐经常交替地出现在一部作品、一个人物和一个作家身上,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很难用简单的善恶优劣评价“陕军东进”的作品和作家的根本原因。
陕军作家们就是在这种孤独之中明确地意识到什么是自己的本,什么是自己的末。他们认定自己从乡村带来的、充溢着乡村传统文明的心灵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在城市奋斗营造、给自己带来欢乐烦忧的一切都是虚幻的细枝末节,在本与末的冲突中,他们象一切有智慧的人一样站在自己立足的根本之上。并且用历史文化的眼光审视这一切,用独特的审美心理在作品中将其叙述得尽善尽美,仿佛惟有如此,才能满足他们充满渴望的心灵需求。《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骚土》在写到这一切的时候仿佛游鱼归渊,作家怡然自得的心态溢于言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态,我们才能从这些作品感受到历史文化的无所不在的巨大力量和对处在迷惘之中的灵智的启迪。与此相反,这些作品在写到令人厌弃的都市和都市文明时,却摆出了一付讨伐和批判的姿态。六部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不约而同的倾向:小说中罪恶的起因几乎全部在城市里面,作品的许多细节对城市文明恶浊的一面的批判是入木三分的,我们能够感受到作家们怀有的特殊的复仇心理,因为这一切差点毁灭了他们的灵魂。
站在乡村的立场上批判城市文明,呼唤历史文化精神的回归,并不是从中国开始,在中国也不是由陕军作家们发端的。19世纪的欧洲许多启蒙主义的作家已经作过了这样的批判。从那时起,形形色色的认定现代文明毁灭了人类的真正价值的作家、艺术家、文人不但把这种批判事业继承下来,而且号召并且带头走上了背叛现代文明、回归自然、寻求灵魂解脱的道路。中国作家、文人却与此有所不同,他们的心灵至少与西方的作家文人一样敏感,甚至因为他们从赤贫的乡村走来,乡村意识特别浓重而敏感到了脆弱的地步。他们的批判可能是锋利的,其中也包含了一定的真理的成分。但独独缺少行动能力,他们不可能挣脱城市的牢笼走向自由的乡村,乡村生活的苦难让他们余悸难消,所以他们宁可在城市里“受难”,也不愿在乡村里“享福”。事实上,他们在城市里保持的“心灵”也有了诸多的变异,乡村里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容纳的空间。他们不愿意回去,实际上也回不去,只能一片困惑与迷惘中孤独地固守在城市中。等待他们的只有痛苦和堕落。
三
当人们的主体意识在精神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孤独便成了司空见惯的精神状态。主体意识强劲的人(不仅仅是文人),他们的精神指向和精神活动达到的境界总有些别人不能企及的状态,茫然四顾,无人理解,无人论说,更无人同行。走进孤独的人先前以为自己的精神探索应当是人类的普遍准则,而凡夫愚妇们总是醉心于琐屑的生活,没有在精神升华上下功夫,于是文人们便感慨“世人皆醉我独醒”,到处诉说孤独带来的痛苦和折磨。后来又发现这“孤独”乃是常人难以窥见的至高至纯的精神活动,“层次”低的人自然没有这个福分,于是“孤独”又成了值得夸耀的一件美事,认定凡是大有作为的人其精神世界必定是“孤独”的。害怕孤独而又炫耀孤独,这种自相矛盾的心理是当代中国文人独有的。人们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奔来走去,却不能以一颗平常心坦然地面对孤独。这是因为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似乎已经没有一座可供其精神最后归宿的精神家园。
在“陕军东进”的作品当中,我们似乎曾经看到过一个精神家园的影子,这就是隐藏在民族和地域的秘史之中的历史文化精神,作家们发现并且修复了这一家园,以供他们创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能够在其中安放自己的灵魂。这个精神家园最安稳、最恰当的存身之所,是在白鹿原上。陕南小镇,悠悠黄土,都是白鹿原的陪衬和补充。作家在这里确实是不遗余力地营造了这个精神家园。白鹿原,不纯粹是个地理名词,更主要的是精神象征,它的风土民情,它的子孙后代,它的神奇传说,都是精神归依的通途。白鹿原就是这个精神家园的现实存在的形式。但可惜的是,这个完美的精神家园只能生长、存在于白鹿原上及与白鹿原相类似的地方,一旦离开了能滋养其机体的土地,精神家园必然要枯萎、丧失和死亡。在骚土之上,陕南小镇,肤施城里,已经多少有点变味,进了西京之后,这个精神家园连影子也消失了。鬼魅狰狞,上帝无言,几乎所有的人物都陷入了丧失精神家园的孤独,在他们身上也折射出作家们无奈的心态。
一个美丽、善良而且有文化的少女,因为穷困,被居心险恶的妖人之子推入了不能接受的婚姻的陷井,她生来的善良阻止了自己以死抗争的行动。残废的丈夫虽然与她一样善良,但却只能带给她精神上的折磨和形体上的劳累;热恋的情人在动荡的年代受尽了非人的迫害,失去了合法的身份,又险些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死!为了家庭的生存,情人的安全,她被迫接受仇人强暴式的凌辱,她用自己的肉体和人格的尊严换取自己和她所爱的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存权利;敏感的儿子在感觉到这一切的时候对她生出了近乎本能的鄙视和仇恨,但她不能解释这一切,又无法诉说这一切,只能由自己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她承受这一切的唯一力量就是她的善良。这个女性似乎是一系列悲剧的起源,又是一系列悲剧的承担者。茫茫世界里,万千人海中,只有她一个人孤独地牵着命运的手在一步步走向没有尽头的人生。合法的丈夫上吊了,儿子因为误伤了自己的生父,经历了一次几近乱伦的初恋卧轨了,情人被儿子误伤生死不明,仇人在报应中失去了行动能力,一切悲欢离合都远离了她的灵魂,她没有也不可能在尘世中得到救助,走向上帝和天国似乎是唯一的出路。这个女人就是荷花。她的孤独是我们这个时代苦难的象征。
一个出身乡村的穷困青年,因为敏感、勤奋,因为要追求理想,所以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取得了一般人眼中的成功,但这个外县的小诗人偏偏生就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生命的情绪特别饱满,一生的使命就是要进行探求生命本源的灵魂漫游和挣扎。他探求生命的起点和终结都是漂亮的女性和以这些女性为象征的自然。他对所见的美丽女性都有心旌摇荡的冲动和想入非非的感觉。他是一个“泛爱主义者,爱一切美丽的事物和美丽的女人”,他所钟爱的美丽的女性其实就是他所认定的生命和生命的价值。这个境界只能存在于他的精神世界里,拿世俗的标准衡量这样的生活完全是在痴人说梦,他的灵魂脱离了现实,在一片美丽的虚幻中漫游。他自己周围的现实生活也与他的追寻发生尖锐的对立,迫使他不得不承认现实的命运,成为一个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的精神经历着无所依托的孤独,这个青年人就是南彧,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分裂的象征。
一个经过苦心孤旨地经营和奋斗获得了完全成功的乡下青年以“精神帝王”的身份生活在一座古城里,他名声显赫,不爱钱但又不缺钱花,南彧式的精神探索和苦闷在他早已成为过去,他已用不着这样苦苦追索生命的价值,因为生命的价值正以十分现实的方式满足着他日常的生活与生存的全部需求。但他却感到巨大的空虚,他生活的目的只有一个别人无法理解的境界,这就是“求缺”。他之所以“求缺”,是因为他还有“理想”,他要写出一部梦想之中的大作品来。日常生活的庸碌阻塞了他据说是如喷泉奔涌的才华,以美文而著称的作家只给人AI写作了一封情书,这件可怜的善举据他本人承认是怀着对一个懈逅女子陡然而生的充满肉欲的情爱写成的。因为他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所以不受一般社会道德的限制,也就没有常人的道德感。因为他给自己确定的社会角色自认为不能用一般的道德准则来评价,所以在做出种种不道德的行为时坦然从容,毫无愧色。他自认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城市感到精神的孤独,灵魂的破碎,是生活的那座废弃的都市迫使他如此这般。但我们从他冷静的选择,自在的行为中不难发现一切都是他自己的灵魂驱动的结果。这个人就是庄之蝶。他孤独,没有人理解,原因在于他给人看的只是自己的躯壳,一般人崇拜的是他头顶上令人目眩的光环,他真正的灵魂不能也不敢在崇拜者面前真实地展示,他更没有殉道的精神把自己的一切撕破给人看,充当一出不太崇高的悲剧的主角。他只能假借“孤独”的名义去做那没有道德意识的“求缺”的勾当。他的孤独是我们这个时代一部分人无可挽回的堕落的象征。
所有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都处于无所求助、无所依靠、无所归宿的状态,这份无所不在的孤独感力透纸背,直逼我们的心灵,确实有一股森森的寒意从中升起。就连那个精气十足的朱先生也无可奈何,只能站在白鹿原的上空象一颗孤独的晨星注视着下界的凡人。只有带着强烈的同情与铭心刻骨的感触才能写出这样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形象。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体味品察着人物的精神境界,他们自己的心灵里同样也有一本难念的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物形象的孤独某种程度上就是作家自身的孤独,他们也有一颗同样破碎的心灵和苦难的精神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作者的孤独和精神苦难怎样走进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的主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更加强化了人物形象灵魂的孤独、苦闷和破碎。作者与人物双重孤独的叠加彻底摧毁了他们找到精神家园的可能,这样的精神与心灵惟一的结果就是彻底的迷惘,迷惘如果受到世纪末情绪的感染,化合而成的就是媚俗和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