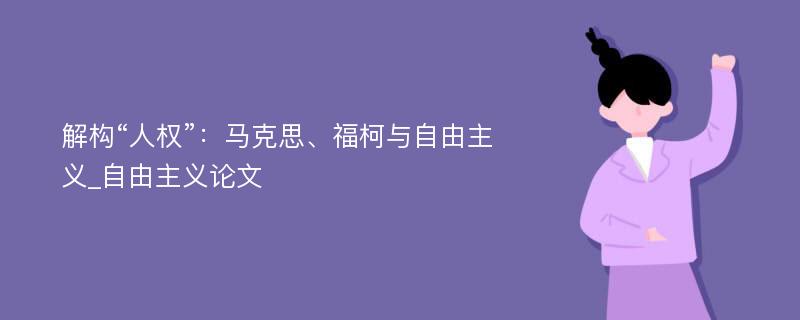
解构“人权”:马克思、福柯与自由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自由主义论文,人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 an)在1982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解构》,此书可视为这一话题在美国的代表作,瑞安认 为,解构主义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政治上,与马克思主义都有正面的可比性。如两者比较, 一个共识即是哲学不能避开政治,政治反之也常立足于哲学前提。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此共 识一则见于马克思在阶级斗争的学说中扬弃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概念,二则马克思主义的政治 批判,也在其反形而上学时,运用了解构分析的武器。(注:参见陆扬《德里达一解构之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242页。
在这里,我们无意评述瑞安的此一说法,我们只是想借以激活马克思:主要以马克思在“ 德法年鉴”时期对“人权宣言”的解构性批判为例,同时参照福柯的“权力哲学”,以期阐 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分界点。
一、马克思对“天赋”、“人赋”人权的解构
面对“人权”二字,解构主义有两件为难之事,一个字对一件。以解构主义的眼光看,整 个“人权”概念无疑属于那种不光彩的在场形而上人本主义——并不是说这个概念在策略上 也不可用,而是说它没有本体论根基。这些诸如,“平等、自由、安全、财产”之类的权利 依附于什么样的主体呢?马克思对“人权宣言”的批判,合乎逻辑地需要从其“人权”及其 “主体”的解构着手。
说起来似乎难于理解的是,无论是今天人们谈论人权,所凭据1949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 宣言》及其后补条约之类的文件,还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人权宣言”,即“真正的、发现这 些权利的北美人和法国人所享有的人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6 页。
)而产生于美国和法国的第一批在历史上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人权文件,我们都无从看到这些文件对“人权”这个概念进行分析和缜密的审视 。有人将此视作是“因为它们的目的是实用性的和政治性的,而不是学术性的和哲理性的。 依这些文件的作者之见,人权概念是十分简单明了的,问题在于付诸实施”。(注:
[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等译,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这种看法实 质上没有触及“人权”这一概念的核心,勿宁说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消解了它。
我们认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人权宣言”都预制了“人的权利是谁给的?”这一政治、 伦理思想史上宗传的问题,并给出了回答。在提供马克思对此一问题的看法之前,有必要提 及“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论。
按照近代启蒙思想家的理解,凡是由自然而来的东西都是自然的(natural,naturel),人是 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的权利就是自然的。无论是卢梭的(以及尔后被法典化为美国革命的 《独立宣言》和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的)天赋人权,还是柏克的(以及尔后发展为历史学 派的)人赋人权,都强调自己乃是自然的。天赋人权强调其天然(nature即天性,也即是自然 或人性)的成分,人赋人权则强调其传统(它也是自然形成的)的成分。双方在强调其自然的 根源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不同的则在于天赋人权论强调权利的先天方面(天赋的),而人赋人 权论则强调权利在社会上约定俗成的方面(人赋的),尽管无论先天的还是后天的(约定俗成 的)
都是自然的。具体地说:
天赋人权论抽象地从“人”的概念的两个主要的逻辑特性,即人区别于单纯的“物”(thin g )以及人作为人应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被对待出发,去先天地、超验地假设“权利主体”和“ 主体的权利”。诸如,人是生来自由、平等的,人生来就享有生命权、财产权,如此等等。 可是,这些形而上学的权利一进入到现实生活中来,就像光线穿透到一种稠密的介质之中一 样 ,它们由于自然的规律,是会脱离它们的直线而折射的。因而,在人类的复杂的事务总体之 中,人的原始权利经历着如此之多的折射和反射,以致于如果谈论它们,就仿佛它们始终是 处于它们原始取向的简单状态之中一样,那必然只是想当然的荒谬观念,或者只是就“当然 ”方面立论。
不同于洛克、卢梭的“天赋人权论”,A·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讨论“人权”时 ,提出了相类于柏克的“人赋人权论”。依麦金太尔之见,那种在近代思想家中被说成自然 权利或人的权利的那种权利,在了解了下述事实之后,人们自然会对居然存在这些仅因人是 人便具有的权利感到有些奇怪。麦金太尔首先指出了语言学事实:1400年以前,在古典的或 中 世纪的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中,没有任何恰当的说法可以用来表达我们说 的“一种权利”概念,更不用说古英语了。在日语中,甚至到了19世纪中叶仍然是这种情况 。麦氏指出,从此一事实中当然不能推论说当时根本不存在自然的或人的权利;但是,从中 可推论出:当时无人知道存在着这种权利。更不要说存在人权概念。相信这种权利与相信独 角兽或巫术(belief in witches and in unicorns)是一样的。在指出享有权利的主张是以 某些社会性规则的确立为先决条件之后,麦氏继续写道:“18世纪自然权利的哲学捍卫者们 认为人们拥有这种权利的断言是自明的真理”,这就如同20世纪的道德哲学家们有时诉诸于 他们或我们的直觉进行道德论证,其论证总是以“糟糕透了的信号”。(注:
Alasdair MacIntyre:After Virtue: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iversity of Not re Dame Press,1981,PP.69—70.
)想必麦氏深谙人性 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的目标也有着最大可能的复杂性。因此之故权利——权力就没有单纯的 意图或取向(多像福柯的言说,后详)是能够适合于直觉把捉的。进一步,麦氏还把自从联合 国发表《人权宣言》以来,不为任何断言提供充分理由这一作法,与罗纳德·德沃金声称, 这种权利的存在虽无法证实,但仅“从一个陈述无法被证实这一事实中得不出它不真实的结 论”的辩护一并指控,并指出像德沃金这样的声称,同样可用来为有关独角兽和魔力的声称 辩护。
在麦金太尔的诸多陈述中,似乎以为能归属于传统的东西本身就是善的。无疑,麦氏的历 史主义的力量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弱点的根源。与麦氏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正义观、人权 观受对立阶级的经济利益规定。
马克思正确地看到了:现代社会结构实质上是冲突而不是一致的。这不仅体现在我们的生 活形式充满多样化破碎观念,而且还体现在这些观念同时被用以表达对立的、互不相容的社 会理想和社会策略,并且把一种其功能在于掩饰深刻经济冲突的多元政治辩术提供给我们。 而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要求的“人权宣言”就是一种政治辩术的范本。因此,马克思告 诫人们,我们不要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政治解放运动的限度方面欺骗自己。这一思 想渊源于“德法年鉴”。
如所周知,进入“德法年鉴”时期,随着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转向共产主义,他开始致力于 解 构“人权宣言”所宣示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权理想国”。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就是:直接批评黑格尔把人的肉体“出生”与人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为王权和长子继承权 辩护的“动物世界观”或“天赋人权论”。如马克思详尽阐明的那样,人作为社会的主体, 既有肉体的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与前者相联系的个人称之为“肉体的个人”;与后者 相联系的个人称之为“国家的个人”。国家的职能和活动不是和“肉体的个人”发生联系, 而是和“国家的个人”发生联系。依此,马克思否定了个人权利来自于出生,以及把自然的 个人当作权利根据的观点,强调权利是社会的产物。马克思肯定:“出生只是赋予人以个人 的存在,首先只是赋予他以生命,使他成为自然的个人;而国家的规定,如立法权等等,则 是社 会产物,……所以个人的出生和作为特定的社会、特定的社会职能等等的个体化的个人之间 存在着直接的同一,直接的吻合,就是一件怪事,一个奇迹。在这种体系中,自然界就像生 出眼睛和鼻子一样直接生出王公贵族等等。”(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7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已清晰地感觉到权利的象征意义。原来,这权利就是个人的象征。顺 便指出的是,无论是马克思嘲笑黑格尔将出生同某些个人的国家要职结合在一起,并把此一 观 点等而视为“动物生来就有它的地位、性情、生活方式”的观点;还是当代新自由主义者罗 尔斯主张“天赋(自然资质)并非私有财产而是公共财产”,因而,应该勾销人生来就遇 到的社会偶然因素对分配的影响的观点,一般地说,今天的人们都能较顺利地接受的。但是 ,马克思与罗尔斯的理论预设和逻辑支援背景不同。罗尔斯是通过考察“原初状态”以确认 个人,这种自由的个人进入“契约”状态而被罗尔斯当作“社会化的鲁滨逊”来描写;马克 思则是通过考察社会以确认个人,现实的个人的存在的真实性在于其社会性、历史性。
基于对个人存在之真实性的如此理解,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揭示了“人权宣言”对于人权所 理解的“人”的实质性内涵:“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7页。
)在获得人权主体此一层阶的解构 性认识后,马克思继续问道:“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称做‘人’,只是称做‘人’,为什 么他的权利称为人权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7 页。
)这是从理论上进一步解构这种人权的主体。马克思勘察到,这 “只有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政治解放的本质来解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7
对马克思来说,把人理解为市民社会的成员,这直接与政治解放所造成的人的二重化的发 展有关。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标志着“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它使“市民 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粉碎了原来束缚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精神的羁绊,使人们脱离了旧 的 直接的政治共同体,成为利己主义的独立个人,获得了作为利己主义的人的自由并承认这种 自由。但是,正因为如此,政治革命没有对市民社会本身的组成部分“实行革命和进行批判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
443页。)而是把市民社会、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看作“自己存在的基础”。所以,马克思指出 ,政治革命有自己的“限度”,这种限度在于: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 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克服市 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相互异化,而是通过把人二重化而导致了这种异化。具体地说:通过政 治解放所获得的不同于公民权的人权,只是“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 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
437页。)例如,自由这一人权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它的实际应用就 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它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的。这里所说的人的自由,是作 为“孤立的、封闭在自身的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8页。)它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作自己 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因此,自由也成为与人相外在的东西,国家可以成 为共和国,自由人同样不自由。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的核心是:揭示“人权宣言”中的“人权”及“人”,按其认识基础来 说,正是对单子般的个人所做的原子主义、分离主义的理解。使马克思不解的是“一个刚刚 开始解放自己、粉碎自己各种成员之间的一切障碍、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怎能郑重宣布 和他人以及和这个共同体隔绝的自私人的权利……。后来,当只有伟大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 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的时候,当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必然要被 牺牲掉、利己主义应当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时候,居然再一次宣布了这种权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9—440
一句话,资产阶级的“人权理想国”对于脱离社会的自私权利的肯定,在逻辑上不仅是与政 治解放所形成的政治发展态势相背离,而且是与政治解放过程的完成对人的行为取向所提出 的要求相冲突。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者竟然相信自由的个人权利这件事可以限制在私人领域 , 这就违反了历史和现实。因为,在现代社会,私域与公域交错渗透,以至于除非“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否则就不能有真正的个人自由。
二、马克思与福柯互读:自由主义的矫情
纵观自由主义思想流变,虽然其内部存在着对“个人自由”与“社会平等”的不同偏重, 但是,自由主义者谁都不怀疑男男女女想要什么,人人想得到的是天赋的人权。然而,事实 上 ,无论是在“过去”的维度还是在“当下”的维度,即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时期,马克思挑明 ,因为,实际上,“人权本身就是特权,而私有制就是垄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9页。
)所以,真正的自由、平 等从来也不曾存在过,人与人的关系从来就是强制和压迫的关系。卢梭似乎预见到了一定会 有人攻击他的理论矫情,所以他预先就声明他只是要探讨权利而不想争论事实。但是,假如 卢梭在面对马克思对“人权”概念的理论解构后,却毫无困窘之态,那么他似乎特别缺乏诚 意。
随马克思之后的当代新自由主义,也完全没有受惠于马克思的这一严肃认真的批判,相反 ,却把这份巨大的解放人类的遗产庸俗地简化成惹人嫌的“自律的主体”。罗尔斯宣扬的是 某种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自由平等的个人”,把这种“理性人”看作绝对先于其社会 条件的赤裸裸的自然原子,通过它的内在实体之外的一套纯粹契约关系与其他的反社会原子 连接起来。不知道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在现代社会还要严格限制甚至剔除了影响个人间社会平 等的诸种历史性因素,来吁求“个人权利”。同样,德沃金的自由主义式的平等概念也无法 取信于人。一方面,德沃金提出“每个公民都有一种受到平等关注和尊重的权利”(right t o equal concern and respect),(注: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 ass,1977,PP.272—273.
)即所谓中立性论旨,以便防止社会偏袒某种人生理想 ,使个人选择至高无上。这一说法的缺陷并不是偷偷地隐藏了一种善的观念,而是以它的善 观念不像一个肯定性的善观念,而是否定地批准多元性肯定观念的方式,不分青红皂白地把 其他“善”压在此善之下,差不多犯了逻辑混乱的错误。正如查尔斯·泰勒洞见到,给予一 项权利就意味着它所保护的能力应该得到积极培养,如果保护一种能力但对它的发展漠不关 心,那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优先考虑,首先意味着道德上有 义务参与维护可以保证权益得到维护的那些制度,实际上决定了对政治之善的积极关注。没 有义务的“人权”只能是阶级特权。这表明,对个体权利的优先考虑所需要的道德和政治条 件 ,事实上只能是对它的成功削弱。只要个体的权利以财产为基础(当然,这并非罗尔斯的立 场,而是哈耶克、诺齐克等“原型”自由主义者的立场),自由国家就恰恰产生出种种不平 等和剥削,颠覆自己本来要张扬的对善的生活的追求。
从这个观点来看,正如自由主义对待其他自由一样,尽管它并不阻碍个体以任何一种方式 自由地获取财物,但是它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已经得到某种特权地位的人才拥有获 取它们的机会。以教育为例,由于教育的内容(尽管它提供给所有人,或者恰恰是因为这一 点)
最终要靠个人的主动性及家庭财产状况才能获得,所以它才产生了最难触动的结果。而 且由于有最攻不破的特权统治,一种地位的高下之分与教育的关联,教育才不像一种社会经 济方面的差别,可以凭自由主义者的美好愿望或一场“文化革命”勾销掉。此外,作为现代 生活之基础的分工,产生彻底而极端的专业化,使得社会差别在这个方向上总是日益扩大。 能 够得到的教育资源越多、越集中,有理智天赋或者没有物质忧虑的人,就会有更多的机会超 出大众的水平。社会总体知识水平的提高,并无助于自由主义想象的普遍平等的实现。对此 ,马克思早已阐明,当资产阶级把政治解放看作为“整个社会的解放”的时候,它实际上“ 假定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既有钱又有教育,或者可以随意取得它们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
463页。)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政治解放只能是符合处于资产阶级地位的人的解 放。
透过马克思的这一语境,我们也可以在福柯那儿领会到相似的语气。
与马克思一样,福柯始终对历史上深受权力之苦的人们表示同情。福柯的权力知识论是从 个 体生存伦理的视角挑战知识本身的正当性。他不是说知识即权力,而是说知识与政治权力有 内在关联。福柯欲反抗与知识勾结在一起的权力效果,最终为的是救护作为个体的主体自由 。福柯申言,“所有的知识都依赖于不公正”、“知识的本能是邪恶的”,即“某种残忍的 与人类幸福相对立的东西。”
福柯的权力知识论是依照对“启蒙运动的启蒙(enlightenment about Enlightenment)”精 神写成的。自由主义、启蒙精神及其教育观念和解放观念从中遭到解构。福柯翔实地分析、 说明了权力是如何渗透到学校、医院、监狱及社会科学之中,描述了自由主义、人本主义价 值是如何同统治技术交织在一起,并支持了统治技术。按照福柯的理解,从洛克、卢梭到罗 尔斯、诺齐克等人,无不是把头等紧要之事看作为如何用个人权利理论限定国家的权力。何 谓“正义”?按照个人权利行使权力。何谓“非正义”?违反个人权利行使权力。不同的自由 主义者,虽对于“权利”的实质内容有不同的规定,但他们坚执于“权利——权力”的基本 思考模式是一样的。并且,在自由主义看来,此种正义论模式仍然可以合理地推进,说明现 代性在伦理上的稳步进步: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制等等。但是,福柯提醒人们,不 要太多地用贸易——司法模式来考量权力。权力不仅是传统所认为的永远是“否定性”的“ 禁 止”,实际上,权力是能创造现实的。因此,对福柯来说,人们不能只去追问权力“属于谁 ”,“通过社会契约合法地授予谁”,“有没有异化压制谁”等等;权力有更为复杂的表现 形式,更应从斗争、冲突、“势”与“均衡”、战术和战略的视角去思考它的运作。
福柯如此看待权力,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压迫机制。对已经停止去批判地思考它自己的思 想前提和存在理由的现代性进行“解构”。从而,福柯揭明了“知识、学术、理论同真实历 史”之间的背反关系:自由主义把现代性进程看作是公民主权的凯歌前进的表象背后,还伴 随着不为人们所察觉的另一种权利运作的蓬勃开展:规训机制的发展和普遍化。启蒙运动既 发明了自由权利,也发明了要按某种规矩,遵循某种规则并达到某种效果的“纪律”(disci pline)。而旨在原则上平等的权利体系的一般法律形式,正是由我们称之为纪律的那些实质 上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微观权力系统维持的。
如果,用“修辞的”读法再来读马克思,我们看到,福柯也相似于马克思读出了“政治解 放限度方面的欺骗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政治革命宣布人的“出身、等级、 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并且“不管这些差别而宣布每个人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 参与者”等等。然而,国家在政治上废除了这些差别,并不意味着这些差别及其作用在实际 上被消灭。相反,这些差别作为没有政治意义的社会差别仍然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而且, 国家“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这些因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 才会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所以,在“人权理想国”中,每个人 在理论上赋予的不可剥夺的平等人权,恰恰是对大多数人的实际剥夺而形成尖锐的冲突。比 较 着说,福柯也以其批判性和反意识形态性,揭示了在启蒙的华美约言所许诺的道德背后, 仍然是色拉西马库斯和尼采所见的狡猾的、为己的、私的权力。自由主义所相信的相对正义 的 政治被福柯以各种势力的永恒冲突、战争的赫拉克利特景观所取代。
但是,无论我们读毕福柯之后再来读马克思会产生多么大的启迪,马克思毕竟无法坐实在 解构主义中,解构主义的弱点恰恰在于它不能从方法论上承认一个准自主的逻辑观念。当福 柯最终向往争取个体生存意趣的自决权,却又始终拒绝明确提出现代性的主体模式和社会组 织形式的替代物时,他也就无以说明,在当前时代,用他的话讲,在一个到处充斥着权力关 系的时代中,“自我的技术”,即创造“新的主体性”何以可能?既然,福柯括掉了谁控 制、使用权力和为了谁的利益控制、使用权力的问题,那么,毫不奇怪,在“我们应当获得 什么样的自由,以及为什么要获得自由”的问题上,“福柯只得含糊其辞”。(注:[美]斯蒂文·贝斯特等《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 999年版,第88页。
)这原本与 福柯学说主体离心化思想背后,暗含着一种新的人学倾向:剥去知识对个体的遮蔽,并因此 回归个体的自我生存,确立自我关怀的小我相联系。然而,福柯的这一目标是虚假的,因为 ,他的理论与它自身的意图难以一致。假如我们透过福柯的修辞虚饰,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福柯倒退到了马克思之后。对马克思来说,解构绝不是一种纯粹消极的或虚无主义的努力, 解构绝不排除“积极的”结果的实现,马克思非常明白,不存在不“采取某个立场”的伦理 学或政治学。因此,马克思描述了当人们之间的实际关系完全合理时,将会出现“个性自由 ”取代“个人独立”,并且,告诉我们自由的个人在什么基础上进入他与他人的自由联合之 中。这可以说是马克思理论的关键部分或“活”的资源。
三、马克思的“初衷”
当马克思谈到应当克服人们迄今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 物的种种虚假观念时,马克思的著作确实不厌其烦地表示,人权从本质上看是阶级特权,道 德就是阶级意识形态,但是洋溢其中的道德热情和义愤也使我们奇怪马克思何以会如此“忽 视”自己进行社会批判的基础。对此,解构主义者用一个绝妙的办法解释道:马克思事实上 的确相信道德,但是他并不知道他相信,因为,他把道德话语认作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传统的 贫困的法理学概念了。因此,伊格尔顿提醒我们,“如果,马克思以为因此就要珍视那些公 正和权利之类的概念,他就的确错了。”(注:[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这似乎是说,马克思实际上把道德关怀中的人 权还原为一种应当被超越的历史权利,但是,还是同一个伊格尔顿却给自己的断言加了一个 “删除号”。说,对马克思来说,人权问题是被转换了,而不是被简单抹去。转换的方式是 :马克思的诸如,人的能力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自由的个人联合体,等等表述,转换成一些 高度抽象的表述,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口号,也就是公正分配原则,如此等 等。所以,共产主义不会是超越了公正观念的社会,相反,公正在这个社会里将见诸实践。 就这样,伊格尔顿终于使马克思向解构主义者靠拢并携起手来。无独有偶,麦金太尔在另一 个语境中毫不含糊地谈起马克思的思想并作评论道:马克思描绘的“自由的个人联合体”, “并没有告诉我们自由的个人在什么基础上进入他与其他人的自由联合之中”,这并不奇怪 ,“抽象的道德原则和功利事实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诉诸的联合原则,而且马克思主义者 在实践中正好体现了他们斥之为意识形态的那种道德态度”。(注:Alasdair MacIntyre:After Virtue: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iversity of Not re Dame Press,1981,PP328.
)看来,麦金太尔在本质上 还是把马克思看成是启蒙思想的个体主义的后代。因此,马克思的自由、群体、权利、自我 实现等理想不免包含启蒙传统的“胎记”。这又是另一种对马克思的解构式解读。
我们并不感兴趣这种解构主义的截断式或非连续性解读。因为,我们无法同意解构主义将 思想发展最真处看成是话语断裂、话语布展的边界和理论逻辑的异质性。这权可视为一种解 释策略。我们格外关注的恰恰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连续性,这是由马克思本人的“思想 造型”决定的。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理想并没有诉诸于道德世系中的人权,人权作为政 治解放的集中表现,只能是一种呼唤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权利。用共产主义的价值诉求取 代对人权的追求,这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说: “至于谈到权利,我们和其他许多人都曾强调指出了共产主义对政治权利、私人权利以及权 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权所采取的反对立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8—229页。
)在同一段话里,紧接着马克思建议我们 再看一下 “德法年鉴”,那里指出特权、优先权符合于与等级相联系的私有制,而权利符合于竞争、 自由私有制的状况。时隔20多年,在1864年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一封信里,抱怨青年意大利党 人强其所难地要他在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协会临时章程》写的绪言里加进一两句关于义 务、权利、真理、道德和正义之类的话。但是,他安慰恩格斯:“这些字眼已经妥为安排, 使它们不可能为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页。)马克思还在1877年的一封信中,抗议有人企图用“现代神话及其 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诸女神”(注:[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取代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可见,后学把马克思 之被动采纳“权利”等概念的初衷,却渐渐视为本当如此的必然,实际上,就是忽视了马克 思自己指明的“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页。)的提示。这表明:“人权 ”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事关“个人权利是如何可能的?”实际问题。立足 于中国本土,面对这样的实际问题,在当下我们的问题意识又该是什么呢?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福柯论文; 人权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哲学家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解构主义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