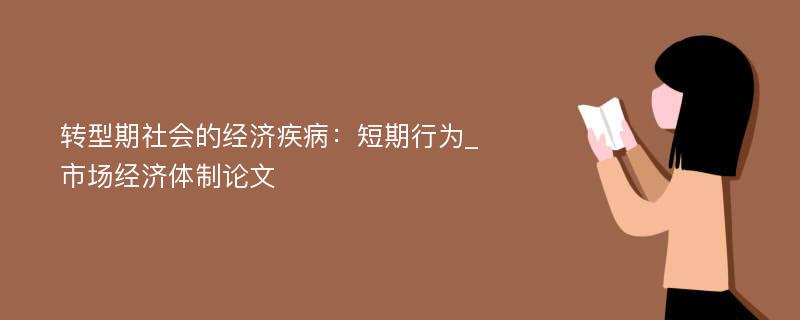
转型社会的经济病:行为短期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F120.2
经济学家常用长期和短期概念来区分市场的进入情况以及厂商生产要素的调整情况,它是经济学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而这里的短期则与此不同,它是指经济行为人或经济活动主体过分追求目前利益的一种倾向,行为短期化或者短期行为就是行为主体为实现短时期自身收益(福利)最大化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及行动过程。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病症,行为短期化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危害着经济和社会的平滑过渡。
在转型时期,由于社会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社会生活会发生剧烈的变革。过去状态下的正式约束即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相继被突破,而新社会状态下规制人们行为的各种正式约束的确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加之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社会运作的目标并不很明确,这样,在旧状态向新状态过渡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个空档。由于这时的社会状态既不同于转型以前又不同于转型以后,呈现出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是,社会博弈规则不明确加大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大了经济活动的风险,从而在这种状态和环境下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的行为包括投资行为、消费行为等似乎变得更加不可捉摸,更无规律可循了,这时人们的行为最突出的表露就是短期化。在社会转型时期,行为短期化表现为一种必然。
当代的中国正处于巨大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之中,其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和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体制的变化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骤然成为黑白分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旧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消亡,新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生成,此长彼消,在两种体制中间给经济行为人留下了一个不很透明的灰色空间。从我国的改革历程来看,渐进式改革一般被认为是一个特色。改革伊始,目标并不明确,“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过程中人们的认识迥异,政策也还时有反复,这就更加降低了经济行为人活动空间的能见度。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之下,长期的经济活动风险过大,许多经济行为主体就只能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目前利益上,追求目前收益的最大化,这样,短期行为或行为短期化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转型时期的行为短期化可以在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中表现出来,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来看,短期行为就一直伴随左右,成为阻滞新旧体制平滑过渡的不容忽视的因素。比较典型的短期行为有:
——国有企业运营中的短期行为。改革之初,尽管已经察觉出国有企业的诸多弊端,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去认识国有企业内部的深层次矛盾,没有认识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而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对原有国有企业制度进行修补,从放权让利、利改税发展到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及关于股份制的是非争论等都毫无例外地表明了这一点。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目标长时期不明确,使得国有企业内部短期行为盛行,诸如:分光吃光、竭泽而渔、杀鸡取蛋;该摊入成本的不摊、该提折旧的不提;不注意后续生产能力的培植,造成企业后劲不足,发展乏力;更有甚者,把国有企业的一部分资本金挪出企业体外,注入私人公司,为个别人谋取利益,或者干脆直接挥霍殆尽,造成国有资本的严重流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现在我国国有企业处境异常艰难,虽然我们加大力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改组、改造和改制,最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当我们回过头来反思一下国有企业过去改革的历史就会发现,行为短期化是改革以来国有企业处境困难的催化剂,而它本身又盛行于社会转型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目标不明确,转轨时间的拖长直接促成了短期行为的盛行。
——市场运行中的短期行为。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随着体制的变化,造成两种体制的同时并存,时常发生碰撞和摩擦,一方面经济活动仍然带有浓厚的行政命令色彩,另一方面则由于市场交易规则不健全,时有重复交叉、相互矛盾的现象,再加之市场发育不成熟、不完善,就导致了市场运行中的短期行为。残留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合法性使得依靠手中权力来获取收益的人,明知大势已去,但也要借助于通过行政命令向市场设置障碍这个最后机会而攫取好处;市场交易规则不健全使许多具体的交易实际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市场上的坑蒙拐骗行为时有发生、假冒伪劣商品也屡禁不止,市场活动主体就是利用这个转型时期的规则空档来牟取收益的最大化,即使是一些合法经营者有时也会受到这种既得利益的引诱,相当多的经营者只顾目前所能取得的利益,甚至只考虑一次交易的成功,“一锤子买卖”是典型的短期行为;市场发育不成熟、不完善主要是在转轨时期我国的市场层次比较低,国内统一市场还未形成,地区封锁、部门分割、行业垄断的现象还比较多,结果是在短期内割裂了市场,阻滞了物资的流动,使部门、地区和行业获得收益,但从长期来看则限制了市场功能的发挥,“保护主义”最终保护了落后。
——经济管理者和改革者的短期行为。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我们来说毕竟是一个崭新的东西,所以伴随着这种经济体制的转变常常是管理机构缺乏经验,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茫然失措、争论不休,把许多经济转轨时期出现的特殊经济现象在认识上不能适度定位,没有考虑到它自身的过渡性质,更多的是,经济管理者把精力花在忙于应付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具体问题上,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也是忽左忽右、反复不定,这在实际上扮演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庸医角色,是一种十足的短期行为。对于很多改革者来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满腔热血为之奋斗的改革事业竟需要耗费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想到经济改革是一个在较长时期内才能见效的过程,哪怕是一项小小的改革也是那么困难,那么耗费时日和精力。现在看来,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和最终确立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有几代人的努力。当初叱咤风云的改革者,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已经临近退休年龄,使他们不得不开始为自己打算,这也就是我国近来报章杂志连篇累牍报导的“五十九岁现象”(退休之前最后利用职权“捞”一把)。
短期行为充斥于转型社会,造成了许多危害。
首先,短期行为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储蓄和投资。在一个稳定成型的社会经济形态里,储蓄和投资都有一定的规律性可循,资本的积累来自于储蓄,即通过推迟目前的消费才能积累资本,它体现了一种时间上的机会成本,而投资则是在一定时期内花在资本货物的生产上或者净增加的存货上的支出,它受技术、政治、政府政策、心理、资源等外在因素和利息率、预期利润率等内在因素的制约,在正常情况下它是连续进行的。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生活的不稳定性和政府政策的经常变化增加了不确定性,特别是从前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的经济转轨情况看都不同程度地伴随着通货膨胀,这就影响到人们储蓄和积累资本的积极性,遏制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影响储蓄的另一面是使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许多非理性的消费或挥霍行为(如歌厅里为点一首歌而“一掷千金”等)。同样,社会转型时期的不确定性阻碍了人们的投资,使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阵发性,即便如此,其间也夹杂着大量的投机行为。从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际情况来看,难以得到外部资金支持的个体、私营等民营经济投资主体主要依靠自身的积累,它们只能投资于周期短见效快的轻型小型项目,投资领域狭窄且新的投资机会较少,它们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生活中及时捕捉着任何可以发财致富的有利机会;对于那些既非国有又非私有的含国有股份的外商投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等投资主体,则能够得到强有力的外部资金支持,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类企业往往是新组建的,由于它们缺乏在某一产业进行经营的实际经验,也由于它们很少对某一产业领域进行深入的了解、缺乏垄断性的技术和营销知识,所以在短时期内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实际生产能力,它们真正关心的是利用社会转型时期的不确定性,运用其雄厚资金进行投机炒作,从而雄厚资金成为破坏经济稳定的利器。对于个体、私人投资主体来说是等待机会,而对于大的股份制经济等投资主体来说则是创造机会,但无论如何,这些机会对于社会经济生活都构成或大或小的破坏力。
其次,短期行为的盛行增大了改革的制度成本,延缓了社会经济的转轨过程。在社会转型时期,制度变迁和制度建设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过程,其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成本构成和成本水平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有不同的基本运作规则,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用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则来替代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作规则,这种替代不可能是无代价的。在我国,从对计划经济的改革开始直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全确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权且按照远景规划所称,到2010年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其间需要耗费巨大的制度成本:改革的规划设计和组织实施费用、清除旧计划经济体制的费用和清除制度变革所遇到的阻力的费用、制度变革造成的损失以及机会成本、改革过程中为应付偶发事件而耗费的成本等等,而在这期间所盛行的短期行为增大了这种成本。短期行为的特殊的破坏性集中体现在,每当改革过程中经济发生暂时困难的时候,它就会变本加厉,对经济生活中的矛盾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加大解决困难的费用。譬如,我国改革初期较长一段时间,旧体制下抑制型通货膨胀的释放使物价总水平大幅度上涨,但是由于存在大量的投机炒作使物价总水平的上涨演化成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就加大了价格模式转换的难度和成本。又如,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困难重重,虽说是存在产权问题,但多年来政府讳言产权改革而热衷于采取一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即短期行为)是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才被迫提出对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改组,这就需要更大的实施成本。由于短期行为的盛行,使经济转轨时期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社会经济运行更加无序,这就在无形之中又为改革增添了一项任务,从而会在客观上延缓社会经济的转轨过程。
由此看来,在社会转型时期,短期行为对于社会经济生活具有破坏作用,使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生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捉摸,这就需要积极探求医治短期行为这种社会经济病症的方策办法,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和平滑过渡。
为此,应该通过设定一系列的规则、制度来减少转轨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经济活动主体认识环境的能力,同时,也通过制度和规则来规范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在社会转型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许多约束人们行为的规章制度被新的经济形势所突破,这就迫切需要新的规则和制度去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既然我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已有几百年的时间,它们有许多成熟的管理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惯例可供我们去借鉴和学习。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向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发展的景象,所以,市场经济运作的一般原则是相通的,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就应该利用这种节约成本的后发性优势,“拿来”这些规则和制度,为我所用。在这一点上人们已广泛达成共识。现在的问题是,引进或者“拿来”的规则和制度只能通过国家有意识地确定为正式约束。规则和制度的引进很容易,但是,它适用或者不适用,与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各种非正式约束的相容程度如何,即存在着制度的本土化问题。综观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虽都以市场来配置资源,但都结合本国具体情况,形成带有本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由此,我国在确立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和运行规则时,既要把它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要把它溶于我国的文化之中,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然而,要消除短期行为这种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病症,最根本的手段和办法却是尽快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通过缩短社会经济的转轨过程来减少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消除短期行为赖以生长的土壤。我们的改革、旧体制的消亡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生成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同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时采取的所谓“休克疗法”,而渐进改革就必然为短期行为的盛行提供生存的空间。渐进改革是由于目标和现实的距离造成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在改革之初并不明确),而经济改革的现实只能是逐步废除旧的体制,逐步构造和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何以如此,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构造必须依照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办事所使然。既然这样,要人为缩短社会经济的转轨过程似成为不可能。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这个过程是有人参与的,因而,人在其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当我们认识到了经济运行的规律性和发展过程后,虽然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通过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地向市场经济迈进,才能最终克服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短期行为等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病症。
